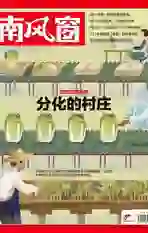“民告官”再出发
2014-09-10叶竹盛
叶竹盛

2013年的最后几天,《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终于提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台面,开始被审议。这是《行诉法》自1989年通过后的首次修订。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回忆说:“1982年向彭真同志汇报,地方和群众有一种说法,‘官告民,一告一个准,民告官没门’。彭真同志对此极为重视,认为这关系到维护人民权益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要解决!’”1989年,《行政诉讼法》通过,“民告官没门”的历史走向终结。
据统计,这部法律实施20多年来,法院总共审理了约200万起民告官案件,民告官已成社会常态。然而,制度阀门虽已打开,实践道路却布满坎坷。
近几年,民诉、刑诉两部诉讼法相继修订。3部诉讼法修订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期间,除了向社会公布修正案草案外,还附带一份草案说明。其中介绍,前两部诉讼法修订的原因是旧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而行诉法除了“不适应”外,还有语气更重的“不协调”,此外还专门强调,“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反映强烈”。
从“没门”到“路难行”,此次修订无疑是“民告官”的再出发。
在北京执业的律师王令和李仁杰在6个月内到外地省份办理了4件行政诉讼案件,均遭法院拒绝,不予立案。其中两件案子,立案庭法官分别给出的理由是,“我就是不立案,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和“被告区政府的意见是让你们冷静一下,所以我们不立案”。两位律师接连碰壁之后,宣布不再承接该地区的新案件。
“在起诉阶段,从《行政诉讼法》实施的效果来看,这是被告最容易守住的一个环节,也是原告最难突破的一个环节。”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者马怀德常年观察的结果。
20多年200多万起民告官,仅从这一数字来看,难以得出立案难的结论,但稍一分析,数字背后的现实就水落石出。平均到每一年是十几万起行诉案件,而全国法院每年一共审理700多万件案件,“民告官”所占比不过百分之一二。与此同时,全国每年另有近千万件信访案件,其中相当部分涉及行政行为,相比之下,十几万件更显得渺小。
广西某人口近百万的一个县级市,其法院2011年和2012年只分别受理15件和11件行政诉讼案件,该院分析认为首要原因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提高了,并没有提到“立案难”的问题。
应星和徐胤两位学者研究了两座分属华北两省的城市后发现,两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均接近,前者虽然只有500多万人口,但年均受案量约1000件;后者有700多万人口,年均受案量却不到300件。两位学者分析后认为,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地有关立案的制度不同,前者城市所在省份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行政诉讼受案目标管理制度,且将立案数量作为法官考核的指标之一。另外,该省较早就开始推行行政诉讼案件异地管辖、提升审级和指定审理制度。类似情况下,由于立案的具体制度设计不同,行政诉讼的受案量就有比较大的差别,说明立案问题的确影响到了“民告官”的真实需求。
面对行政诉讼立案难的局面,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连续下发多份文件,其中《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行政诉讼立案工作,不得随意限缩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得额外增加受理条件。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行政诉讼立案监督,对于符合立案条件不予受理的,及时予以纠正,防止因当事人告状无门而到处上访,激化社会矛盾。”
此外,最高院还专门下发了《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要求基层法院“不得随意限缩受案范围”,要求各地坚决清除限制行政诉讼受理的各种“土政策”。
但是根据《法律年鉴》对最高院2009年文件下发前后几年的行政诉讼结案数的统计来看,这些言辞可谓严厉的文件几乎没有起到作用,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按大约5%的缓慢速度增长。
此次修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草案说明,“立案难”被认为是三难的“难中之难”,草案对症下药,采取扩大受案范围、可口头起诉等5项措施。
梅春来律师却对草案能否根本解决问题表示担忧:“现实的规则是法院不受理行政诉讼都不是立案庭决定的。一般的行政行为是由行政庭庭长决定的,对行政机关有不利影响的案件报院长决定,对当地党政机关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要请示当地政府和党委意见,有的甚至还要获得上级法院内部默许。”
他建议,要真正解决问题,应该借鉴《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同样都是行政案件,行政复议为什么没出现立案难的问题?”梅春来认为首先是因为行政复议有自动受理机制,其次是因为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将面临被起诉到法院的压力,而法官不立案则缺少类似的监督机制。因此他建议,要根本解决“立案难”问题,可以考虑建立自动立案制度,“从当事人邮寄或递交起诉状之日起7天内未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一律视为受理”。
对于艰难通过立案关的行诉案件来说,后路也不平坦,有不少甚至连开庭的机会都没有。据最高院数据,2011年,全国以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结案的行政案件,占全部一审结案总数的7.8%,是民商事案件的7.8倍。
清华大学行政法教授何海波统计,行诉案中原告撤诉的比例居高不下,从行诉法施行之初的20%一路攀升到最高60%,直到近年稳定在40%左右。何海波观察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近年来撤诉案件中,只有不到10%是因为被告行政机关主动改变了行政行为而原告自动申请撤诉的,那么其余90%是出于什么原因撤诉呢?他推测,有可能是被告承诺给原告一些好处,“例如行政处罚决定不撤销但也不执行”。
几种情况相加后,法院最终以判决形式结案的比例只有不到三成。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包万超对2000年至2011年间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法院越来越倾向于不支持原告的判决,从2000年17%的胜诉率,一路下跌,直到2011年只有7.09%。
据不少行诉法学者观察,行诉法作为一部基本法律,最初之所以在中央层面迅速通过,除了解决“民告官无门”的问题外,潜在的用意是借此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以落实中央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与此同时,又不能破坏地方政府施政的能动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在维稳和经济发展方面。
据何海波统计,公安案件曾经长期是行政诉讼的第一大类案件,曾占所有民告官的45%,此后比例不断下降,到2010年只有8.2%。与此趋势相反, 城市建设(包括规划、拆迁、房屋登记等)行政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仅5%的比例,跃升至2010年全部一审行政案件的18% ,成为占据首位的民告官类型,占据第二位的是国土资源(包括土地、林业、草原、矿产等)行政案件。显而易见,这3类案件的起伏趋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相吻合,并且三者均涉及维稳和经济发展问题。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既然肩负“维护”的职能,在本已寥寥无几的原告胜诉案中,即使行政行为存在明显的违法问题,法院也几乎不采取直接变更的判决。据最高院统计,在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近13万件一审行政案件中,变更判决只有137件。
与民众胜诉率极低相对应的是“官告民”几乎一告一个准的局面。行政诉讼中有一类是政府部门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法院向民众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据包万超统计,2000到2011年间,这类“官告民”的总数高达300多万件,而“民告官”只有120多万件。 更为惊人的对比是,当“民告官”的胜诉率只有不到10%之时,法院支持“官告民”的比例常年高达90%以上。
2000到2011年间,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决定类的“官告民”的总数高达300多万件,而“民告官”只有120多万件。 更为惊人的对比是,当“民告官”的胜诉率只有不到10%之时,法院支持“官告民”的比例常年高达90%以上。
即使艰难地闯过了立案关和审判关,当事人最终胜诉,却仍可能“栽”在执行难上。不久前,广东省雷州市一位副市长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政府为何不履行省高院判决时,回答说“不要盲目相信法院”。这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部分官员仍未改变尊重法院判决的心态。
各种难题的症结被归咎于一点: “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据最高院统计,2011年,全国行政案件的上诉率达到了72.85%的历史最高点。更为明显的数据是进京上访数量持续走高,2011年全国行政一审受案数量仅占所有总类案件的1.8%,但当年到最高法院登记申诉上访的行政案件却占全部的18.5%。这些数据表明,基层法院即使立案和判决了,作为原告方的民众也多数不服,继续寻求上诉等救济渠道。
根据种种数据,最高院法官李广宇、王振宇、梁风撰文分析说,“基层法院的一审功能几乎形同虚设。”因此他们提出,若不改革现行行政审判体制,“其他方面的努力再大、再多,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设立直接接受最高院监督的行政法院系统。
改革之路与“民告官”之路一样艰辛。2005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已形成建议稿初稿,但直到2008年,行诉法修订才列入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8年至2012年的立法规划,直到换届也未见最终落定。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份大幅涉及法治政府的全面改革总纲出台,或许是借此改革的势能,行诉法修订最终正式提上了台面。草案说明中罕见地两处直接引用三中全会决议的有关精神作为修订的理据。例如,跨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已在多个试点被证明有效,在写入修正案时,草案说明便援引了全会“关于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决议内容。
细心的人会发现,公布的草案中,第一条删除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中的“维护”,只留下“监督”。若此条最终通过,则表明至少在立法层面上,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开始被扭转。
尽管学界和民众普遍欢迎此次大规模修法,但常年办理民告官案件的袁裕来律师却“冷眼旁观”:“立案难、判决难、执行难的根源是什么?表面来看,似乎是法院不敢依法立案、不敢依法审判、不敢依法执行,实质上却是法院敢于不依法立案、不依法审判、不依法执行。”法院种种“敢于”对民众说不的底气,显然不是来源于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因此,他认为,不从根本体制上转变,限制干涉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的种种权力,赋予民众真正制衡法外权力的力量,那么行诉法的修法尺度再大,也未必见效。
解决“三难”,“民告官”再出发,此次修订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