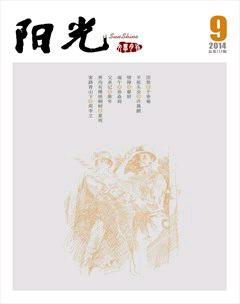客路青山下
2014-09-02周李立
一
钟家的祖先是有些浪漫主义情结的。
在南宋绍兴年间那些南迁的队伍之中,钟家祖先钟世昌的路数有些不一样。他坚持认为自己和家人不能随波逐流,他一心一意要“择良木而栖”。也许他觉得既然已经上路,就该寻个好地方,宁缺毋滥。
他一路挑挑拣拣,始终不能满意。他的固执和浪漫之处在于,他心目中“良木”的标准实在很难把握——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落脚,他只是在冥冥之中觉得他还没有找到。他完全没有标准,他听凭感觉。
那时天下还是赵家的,总体而言,不是很太平。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蹄声不时就惊扰到宋朝皇帝们的梦境。可能是品质不高的睡眠让宋朝的皇帝们多数都显得敏感而神经质,最终他们再也无法在北方维系一个王朝的统治。他们带着一个王朝上路了。
南宋王朝将都城建在湿热的江南之地,尽管初来时水土多有不适,但王朝的天子们却终于可以在烟雾缭绕的水岸边的宫殿里祈求一段安稳而短暂的睡眠。
王朝的南下也牵连着它的子民。子民们多数是世代农耕、养殖的农夫,信奉所谓故土难离的古训。只是他们遇上的是一个战事频仍的岁月,这让故土难离也成为一件很难坚持的事情。
多数百姓们其实也不太知晓天下大势,他们眼里的天下只关乎他们的家族或村庄。但战争伤民,王朝之间争夺天下的政治,其实全靠百姓供养。如若再遇三五个荒年,再擅长耕种的农夫也只能望天叹气,埋怨老天不公,没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他们就这样直接承受着生活的胁迫,选择离乡背井亦非他们所愿。他们不过和天子一样,必须换个地方祈求上天再给个活路。
他们毕竟是农夫,毕生所求亦不过是一块可以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于是他们自欺欺人地想,也许水土丰美处,他们也可以认作故乡吧。
天子的睡眠与农夫的性命,我相信它们对当事人带来的痛苦程度其实不相上下。后来天子们“只把杭州作汴州”,一晌贪欢,在历史上备受诟病。但天子的逃避与隐忍却让农夫得以片刻喘息。农夫们对南迁一事仿佛要更豁达一些,客居的生活从抵达的那一刻便迅速开始——不然还能怎么样呢?他们的喟叹从来也不会进入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
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数百年的时光,窥见一些蜘丝马迹,从中感知到他们那复杂的客居心情。是的,我觉得那更多其实是无奈,从自我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他们该是多么无奈:他们以“客家”自居,把对中原土地的思念都寄托在微小的生活细节里。
他们终于以一种无奈的方式,坚守了故土难离的古训。
那一年钟家祖先钟世昌四十二岁。年龄让他更愿意替后代考虑而不是自己。其他的农夫看着脚下,他的目光落在后代,他不是在给自己找家园,他是在给后代找故乡。
他是带着老婆孩子及二百多只鸭子上路的——这支庞大的队伍行进缓慢,没多久就人困鸭乏。他们一路向南,所经之处皆是山水相依。江西赣州这块多山多水之地,四时皆是绿意葱翠,景色并不单调。山水之间,赶鸭人指挥着自己的队伍,从赣州兴国县竹坝出发,六十里路竟走了若干天。
他也许偶尔也会想起他的祖先——据家谱上写,他是唐朝玄宗时期中书令(宰相)、越国公钟绍京的第十六代孙。一个遥远年代的宰相,在迁徙的路途上并没带给他的十六代孙什么优越感,但钟世昌或许比早年从北方南下赣州的祖先还要幸运一些。因为他迁徙的终点很快就要到了。
赣州被称作客家南迁的第一站,钟世昌从赣州兴国出发,走到兴国相邻的赣县时,他找到了那个让他“有感觉”的地方。
后人传说,是一个梦让他选择留在了白鹭。做梦选址的方式和此地白鹭的名字都极为符合他身上的浪漫主义倾向。不过对一个赶鸭人来说,浪漫主义倾向其实并不实惠。所以他也许还看中了流经白鹭的那条天赐的水路——鹭江,也许还看中了离江不远的那条山脉。他在冥冥之中的选择其实正是所谓“狮蹲、虎跃”的绝佳风水。
其实,钟世昌选择在白鹭驻扎的具体缘由我们尽可随便揣摩,反正钟世昌当年一厢情愿之下选定的安家之地,已经被此后八百余年的岁月所证明。
二
赶鸭人身后八百余年,鹭江边一座名为白鹭的村庄还活着,是的,它依然存活。
如今很多村庄都已经死去了。它们死去的方式各异,无名的小村庄被城镇吞噬,连屋瓦都不再剩下;也有的村庄人烟已去,仅留空洞的柴门;稍有历史的古村镇被粉刷封存,真空包装,隔绝了人间烟火;发展太快的村庄已是城市面貌,失去昔日村庄的容颜……它们与汉字里的“村庄”二字已相去甚远,徒有村庄之名,却无一例外仅余一具具蝉蜕后的村庄躯壳。
白鹭村还活着。活着的村庄是现在进行时的,它不属于过去,也不在乎未来。它就在当下活着,随随便便却又堂堂正正。
它的状态似乎有些随便,任凭千呼万唤,它才终于于不起眼处现身。它背靠满坡果林的青山,像一块月牙静卧。远远的,只能看见一片飞檐青砖墙。也是需经人指点才能看见,村庄前那一条绿水,原来是鹭江。鹭江与村庄之间随便躺着一条普通的柏油路。路边堆积着砖头石块,还没修好的样子,细看却又是修了很多年的样子。这是一座不太着急的村庄。它都活了八百多年了,急什么呢?
但我仍然急于进入它深幽的内里。我毫无准备地扎进了村口第一扇敞开的门里,以为白鹭大名在外,门里自然会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却没想仍是砖瓦散乱。
修葺房屋的工匠看见有人来参观他的工作,也并不在意,他依然专注在手上的活计,只有硕大的电风扇吹起他沾染石灰的工装。他的工具们占据了半间堂屋。在客家人“四水归一”的天井里,也架着他的“人”字形木梯。他踩在木梯上,高于众人,目光却仍然向上,像个君王。他在打理老屋的墙壁屋顶,像打理一个心爱的姑娘。这姑娘久经岁月风霜,但人去屋不空,反倒是留下诸多昔日印迹:木墙壁上写着五颜六色的粉笔字,细看竟是小学生作文的语气“星期天天气很好,我们去放风筝……”之类,想必是曾经的小主人兴起时的题字;半架自行车,缺了一个轮子;暖水瓶、电饭锅、半旧的一只鞋子、不明功用的木桶……物什痕迹堆积在一起,仿佛主人昨天才刚刚离开,明天就会回来一样。
也许是见惯了江南古村梳妆打扮妥当的光鲜样子了,突然看见这般散乱的古村,犹如看见未经粉黛的姑娘,初感意外,却终是惊喜。我想起这时代的人们,他们总是口口声声要去看未经雕琢的自然、古意或生活本身,而未经雕琢的生活不就本应如此散乱随意吗?
我终是带着贸然闯入者的心虚退了出来,安慰自己这只是处例外——不小心刚好闯入了正在整饬的房屋而已,其他的院落房屋应该已梳妆妥当了。然而沿院落之间的狭窄弄堂进入村庄,看见的仍然是这样的散乱随意。它真是太随意了。“江南古村”“历史文化遗产”这类高帽也没让它想起来可以摆摆架子。它低调地保持着一种日常而亲切的面貌,仿佛几百年来都未改变过。
这是炎热的夏日中午,村庄的弄堂里没有行人。阵阵蝉鸣反而让四周更显安静。也许村民们都藏身在古老房屋的一隅荫凉处,暂时将他们的村庄承让给兴冲冲的外来者。然而生活的痕迹却是藏不住的,那些藏不住的痕迹都在坦诚的告诉我们,他们仍然拥有着这个村庄,他们仍然拥有这个祖先为他们挑选的青山下的家园。
曲折弄堂的两边,不时出现虚掩的院门。门内,颇具雕塑感的骨感老太,用表演性的动作捶打着手里的木桩。木桩落入地上一截一尺高的圆形竹筒内,声音浑厚。她没有在表演,她已经这样动作了许多年,那动作已经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的一部分怎么会是表演呢?老人像一名铁匠锻打兵器一般,锻打着木桩下的擂茶。其实那专属于客家人的擂茶,又何尝不是老太用来抵抗岁月的兵器呢?或许老太一生对它古怪香味的迷恋,近似后人们钟爱摩卡咖啡的味道。
祠堂前的空地上,老头们坐成一排,听凭幽凉的穿堂风拂过他们藏蓝色的衣襟。他们在白鹭村已经住了一辈子,闭着眼睛也能在盘根错节的村庄内部找到最好的纳凉地点。暑天漫长的午后,他们就这样相互陪伴,打发缓慢的时光。他们看我的眼神竟然如此相似,安稳、笃定。这神色仿佛代代相承,从赶鸭人那里就已是如此了。白鹭村民同为钟姓后裔,家族血脉竟都这样坦然地写在脸上。
祠堂前的空地上,半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追逐而过。钟家的子孙,就骑在那些彩色的车轮上进入我们当下的时代。只有老人的村庄是暮年的村庄,白鹭却仍是孩子们的村庄。不知谁家门前的石板上晾晒着两双小小的蓝色塑料凉鞋。这家的房子或许有了年头——又或许白鹭所有的房子都有年头了——才会挂着某某祠堂某某文化遗产的门牌。这门牌让孩子的凉鞋更显可爱亲切,颇似正装西服上落上的一朵野梅花,令人会心一笑。反倒是那画蛇添足的门牌——是不属于这里的外来品——对比之下,便显出生分了。
但那蓝色塑料凉鞋的小主人终会长大,他们也会像几百年来的钟姓子弟们一样,离开村庄,成为茫茫人海中普通的一分子。有一天他们也许还会回到白鹭村,也许不会。可能走出去就不再回来的年轻人会更多一些。世界仿佛越来越广阔,却又仿佛越来越狭小,年轻人走得越来越远,却又仿佛越来越无处可走。无论如何,在白鹭村度过童年岁月的孩子们,走到多远的地方,心中都会装着一个蓝天青山之下的家园,那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希望是。
这座常住人口不到两千人的小村庄,到了夜晚应是更加宁静。偶尔有狗吠,在曲折的“丰”字形小弄堂里久久回响。没有路灯,宁静也许会加重黑暗的程度。只有每当月亮出来,夜晚才会稍微明亮一些。在那些苍老而黑沉的房屋里入睡的孩子们,他们会做什么样的梦呢?
三
在钟世昌的祖先还在朝为相的唐代,诗人王湾就已经在离乡的征途上惆怅万千了,乡愁让他吟咏出的诗句深沉平静:“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离乡背井与思念深深,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裹挟交缠,产生复杂的情愫。行程上的青山绿水,在异乡人看来都是触动情感阀门的钥匙——他们不敢轻易为之动心,唯恐心潮泛滥就不可收拾。
总是要离开家园的,就算不为求生、也不躲乱世,也要走出家园才能施展才华,施展抱负。历朝历代的读书人们,待在家里最多只能修身齐家,只有走出去才能治国平天下。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这样看来竟犹如一部不断离乡的异乡人的历史。条条客路,就是穿起中国历史的经纬脉络——它们印刻在大地之上,比纸上的历史更坚实。
钟世昌的后代们也是要离开白鹭村的。
在钟世昌身后六百多年,清朝,钟氏家族在白鹭村已开枝散叶、繁衍数代。他们利用鹭江直通赣江的水路便利,经营竹木生意而富甲一方。富裕起来的钟家后人除了买田置地、修建讲究的住宅,也开始追求精神文明。他们尊学、重教,众多子弟成为读书人,读书帮助他们明理,也让家族因之而愈发兴旺。学而优则仕,钟氏家族门前的功名石随即也一根接着一根的立起来。这些荣耀的石柱在清朝乾隆道光年间最为密集。那高高耸立的细长的石头,在钟家人眼里,是那一片片青砖黑瓦的祠宇门前最好的装饰物。
只是功名终究是过眼云烟,那些曾密密麻麻的功名石,如今已所余不多,留存至今的,也是历经风霜难免残破,如今人们只能凭借青石上斑驳难以辨认的刻印,模糊地想象钟氏家族曾经的荣耀。
其实建筑比功名石更能佐证钟氏家族及白鹭村的盛极一时。
我觉得钟愈昌修建恢烈公祠时,心里一定想的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他把盖房子当作了归隐生活的高潮,人生的自我实现,倾注热情、财富与智慧,盖得风生水起。
钟愈昌是乾隆盛世年间的清太学生,告老还乡之后便开始修建一座后来被称为“山沟里的大观园”的建筑。建筑按计划修了三栋,分给了三个儿子。如今仅存两座,另一座毁于石达开之手。
传说辞官的钟愈昌在离开皇宫之前,获皇帝亲赠的金銮殿里的金砖一块。有了皇帝来添砖加瓦,他的建筑更加有了底气。
皇帝的金砖如今仍然安放在恢烈公祠建筑的中栋——友益堂正厅的两把太师椅之间。只是金砖当初的光华尽已褪去,如今只显出一种黯沉的色泽——那比黑更黑的颜色,也许就是传说中的“铅华”。
抚摸金砖那一刻,对于金砖的那些传说,我开始相信了。它告诉我,它也是从故宫金銮殿上一路辗转至此的客人,它也历经了青山下长长的路途,历经了物是人非的岁月。
金砖所在的友益堂,正厅前的大天井内,一雄一雌两株罗汉松的枝干伸展出奇崛的造型,并在天井与屋内投下斑驳的树影。当年树下的园林盆景现今已无踪迹,只有树与巨大的水缸仍然在提醒着世人昔日的繁华。
那的确是繁华:整座建筑的大小天井十六个,窗户格心镶嵌着的都是云母做的薄片,每一块外墙砖都是名牌——都有“日升记”的标记,瓦檐均置“云头瓦罩”……精美的建筑在当年象征的是钟愈昌的雄厚财力,在眼下则成为白鹭古村的荣耀。
其实白鹭村民更津津乐道的好像并不是那位钟家老爷如何财大气粗,也不是钟家老爷一门四代都在朝为官的显赫仕途,而是他的一位小妾。
四
我很想知道那位后来被尊称为王太夫人的女子,在作为小妾被钟愈昌娶进门时,有没有坐过“落性”?当地客家人的婚嫁习俗中,新娘在拜堂成亲前,都要在脚不能点地的椅子上坐上半天儿,把悬空的双脚坐麻了,也就把姑娘的心坐踏实了。落性一坐,便是沉淀后的水,从此收心,生活中便只剩下了安稳的日子。但没有人告诉我,没有八抬大轿抬进门的妾,是否也需要和正室一样坐坐“落性”?
我总觉得,钟愈昌的这位小妾要么是落性坐得过于好,要么是过于不好,因为她太不同寻常。说她落性坐得过于好,是因为她太踏实,以妾的身份掌管钟氏大家族的家业,不踏实一点儿怎么行?说她落性坐得过于不好,也是因为她太不踏实,她不仅做着钟家老爷才能做的经营家业的事情,而且想法太多,要开办义学、救济灾民、建立义仓……就连白鹭传统的东河戏,传说也是她根据故乡苏州的昆曲而创。
她一生未被扶正,生儿子之前也从未被允许踏入钟家祠堂,自然也进不了家谱,但死后,对她的赞誉却始终在钟家后代中口口相传。
当年那个进不了祠堂的小妾,后来有了自己的祠堂——王太夫人祠。祠堂是儿子为她修的,不排除母以子贵的缘故——儿子钟崇俨官至嘉兴知府,在钟愈昌的三个儿子中出息最大。
二进天井式、上下两层的王太夫人祠比白鹭村的其他六十八座祠堂更显端庄简洁。白鹭村民认为,王太夫人祠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女性祠堂。在我看来,其实都不必说女性祠堂天下是否仅此一座,仅仅是为女性修祠堂的举动就值得一说。勤劳务实的客家百姓,在多年客居生活的重负之下,不得不信任那些能带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善良又有能力的人。现实的生存需要超越了性别的固有观念,如同当年他们真心诚意地接受王太夫人对钟家家业的管理,只是因为她具备这个能力。
开义学、办义仓、救济灾民……她一生都在偏安一隅的村庄做着不为天下人知晓的慈善事业。在传媒业未发展的年代,慈善还仅仅是慈善本身。她的事业在她死后也未中断,儿子、孙子延续了她的义仓、义学传统。连她的祠堂也贡献出来成为办义仓和义学的最好场所。
王太夫人祠堂与钟愈昌所建恢烈公祠相联通。不知王太夫人在当年那些伏低做小的日子里是否心有惆怅,但我觉得那些善事也一定让她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五
向晚时分的白鹭村竟然顷刻阴沉下来。不知何处刮来的狂风,吹乱头发也刮来浮沙。在古老的村庄里回荡着的这当下时节的风带来了雨,雨滴仿佛在一瞬间就砸落了下来。那和历史一般瞬息万变的风云,如此难以捉摸。
不变的仍是村外连绵青山浮现出的峥嵘轮廓,这和赶鸭人钟世昌当年看到的景致,其实也无太多不同吧。
周李立: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生于四川。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发表小说和散文作品多篇。中短篇小说集《欢喜腾》入选2013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