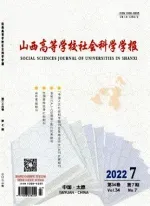刑法司法解释视域下的法院案例指导制度
2014-08-15周洁
周 洁
(太原科技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正式开始实施。最高院所施行的案例指导制度其主旨是通过统一法律适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从而使各级人民法院在裁判中统一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同时通过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使人们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接受指导性案例的教育指引,形成对于法律的一体化遵守。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并非完全的新生事物,从1984年最高院创办《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正式发行),就开启了在《公报》上刊发各类典型案例,用以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模式。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化就是在总结多年案例发布指导经验和有关地方法院推行案例指导制度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表面看似乎没有相关性,一个是关于法律的具体适用,另一个是关于法律的解释;但是,从深层次看,二者有着很必然且有待厘清的关系。尤其是案例指导制度与刑法具体适用解释之间的关系昭示着我国刑法适用解释的价值正在被最高院所认可,并将借助指导性案例的渠道来发挥其作用。
二、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定位
案例指导制度的精髓在于发挥司法的独立性价值,将弥补立法缺陷和顺应社会发展、统一法律适用的着力点,从以往惯于依赖立法和变相立法(颁布抽象司法解释)转向司法,将法律的生命力延展更多地诉诸于法律适用本身。在抽象司法解释饱受争议的刑法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确认案例指导制度的指导意义并使其制度化,旨在以指导性案例的方式统一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典型案例的样本效应来指导法官的司法实践,以弥补抽象司法解释的诸多不足,是案例指导制度的解释学意义之所在。
(一)案例指导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适用机制
指导性案例是通过典型个案的裁判来具体诠释法律条文的规则内涵,明确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这些都是司法权运用的当然内容,也是法律适用过程中司法权的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的方式。区别于英美的判例法制度,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是为法律适用创设规则,而仅仅是指导法律适用。“我们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是一种新的‘造法’制度,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和制度。”[1]
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制度机理是以例释法,通过典型案例的法律适用来指导司法实践。具体而言通过对典型案例裁判中对案件事实的描述、证据的分析、裁判理由的论证说明,使各级法院的法官藉此来学习和领会判决中对事实的解构,对证据的认定,对法律含义的解读,从而使各级法院的法官从中领会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适用规则,精确对法律的理解,统一对法律的适用,这应该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深刻意蕴之所在。为了真正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指导性案例应当在案件事实及其法律意义的认定上具有特殊性、疑难性、典型性和规范指引性,案件不仅要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裁判结论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方面也应具有示范性,这样才能凸显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维护司法公正的职能。“通过案例指导制度实现同案同判,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是最高人民法院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的内在动因,也是其赋予案例指导制度的基本目的和功能。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2]
(二)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在于判决理由的说明
指导性案例是在生效刑事判决的基础上生成的,刑事判决的规范化是遴选的基本条件,案件事实的典型性是遴选的前提条件。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标准之核心要件则是:裁判结果必须正确,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适当,裁判文书事实认定准确与裁判说理充分;能够全面展示出案件的全貌,通过归纳案件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及对法律条文的分析和论证,准确地阐释适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据。我国的指导性案例侧重于案件事实上的典型性和对以后类似案件裁判的指引和参照意义,这种参照的依据在于典型案例裁判中的实质推理的正确性和说服力。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法院在参照适用时,只能作为“判决理由”的依据而不得作为“判决依据”加以援引。所以,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一方面依赖于辨法析理、论证充分的刑事判决;另一方面指导性案例的示范作用,无疑也将积极推动我国各级法院法官刑事判决书书写的规范化和判决说理性的增强,从而促使判决书质量的提高和法官素质的提升。
(三)案例指导制度的优势在于其实务性和开放性
“指导性案例能够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去阐释法律规定,使抽象、枯燥的法律条文或法律原则变得生动、具体。这种以案释法的方式,是帮助理解法律的最生动的教材。”[3]这正是案例指导制度的实务性优势。指导性案例来源于各级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选取的都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案件,其判决理由的说明更多地注重具体个案的特殊性,使刑法条文的抽象规定通过具体案例情节的展示而更加形象具体。这是刑法典的条文、立法解释以及抽象的司法解释都欠缺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开放性则在于司法实践总是不断发展的,指导性案例不像立法和抽象的司法解释那样,一旦颁布就会在较长时间内发挥效力,不可能朝令夕改。而指导性案例则可以因案件的变化而变化,旧的典型案例可以被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刑法规则的内容也会随着新的典型案例的适用而获得新的解读,以此推进法律文本内涵的丰富和法律外延的扩展,从而赋予刑法规范更强的生命力。
三、案例指导制度的解释学解读
不可否认,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法典的抽象性、滞后性等缺陷,为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规范提供相对明确、具体的指引。但是,司法解释,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抽象性解释,仍然不能摆脱作为一般规则所具有的原则性和局限性。司法解释“不能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去阐释某一法律规定的含义,它走的是‘从一般到一般’的道理,而‘从一般到个别’这条路子仍然是封闭的”[4]。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习惯于以“补充立法”的方式弥补成文法缺陷,包括制定立法解释和统一的司法解释,都是在立法的视角下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然而西方大陆和英美法系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已经证明,立法永远无法与司法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相契合,制定法的缺陷只有交给司法实践去完善和弥补才是可行的出路。因此,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融合的法治轨道上。借鉴国外判例法的有利因素,总结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审判经验,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立法和司法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选择。案例指导制度具有抽象司法解释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并通过弥补其不足,彰显自己特有的价值。同时,案例指导制度与刑法具体适用解释之间有着十分密切和互为表里的联系。
(一)案例指导制度克服了抽象司法解释的弊端
案例指导制度实现了具体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对接,克服了以往抽象司法解释对立法与司法权协调的失范,克服了法律解释与具体法律适用相脱节的诸多弊害,是对抽象司法解释缺陷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制度革新。虽然指导性案例也必然涉及法律的解释和适用,但是它与抽象司法解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础。其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指导性案例展示的是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状况,与具体案件事实密切相关,其法律解释逻辑、裁判依据、判决理由是因案而异的,其结论只对以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并不具有普遍的法律强制适用效力;而抽象司法解释(除了批复式司法解释)却几乎不与具体案件发生关联,主要是对刑法典法律规定的细化或补充,所以表述非常简洁,往往只有结论,而看不到其解释的理由与逻辑分析。司法解释是从规则到规则的解释,解释结论仍然是概括和原则性的,而且抽象司法解释一经颁布实施就具有与刑法典一样的普遍适用效力。指导性案例并不具有这样的规范约束效力,其只对以后各级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有参照、指导作用。这种参照和指导就是要求,相同案件原则上应当遵照指导性的案例的判决来适用法律,不相类似的案件则可以不必遵循指导性案例的判决结论。所以,抽象司法解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规范指引,而指导性案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适用范例展示,二者无论从制度的法理基础看,还是从各自的适用效力来看都是完全不同的。案例指导制度正是为了弥补抽象司法解释的不足而确立的,如果将其等同于抽象司法解释,那是对该制度极大的误解和歪曲。然而,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又与其作出的抽象司法解释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典型案例的裁判及其结论会成为最高院制定抽象司法解释的依据,司法解释就是在对大量典型性案例裁判结论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法律的细则性规定和补充。另一方面,就最高院做出的四类解释(“解释”“规定”“批复”“决定”)中,“批复”式解释是针对下级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的答复。通过批复可以明确法律条文在具体适用疑点上的适用意见,明确有关法律条文的内涵,实践中对于统一法律适用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因为“批复”的背后都有案件请示制度的支撑,而案件请示制度是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因此受到了理论界较多地批判,取消的呼声一直很高。因此,案件请示制度未来面临着被取消的命运,“批复”式解释也因此可能走向终结;而案例指导制度将成为“批复”式解释很好的替代品。
(二)案例指导制度是对个案解释的认可
案例指导制度虽然与抽象司法解释不同,但是却与具体法律适用解释即个案解释有着司法原理上的互通性,案例指导制度就是对具体法律适用解释的认可和呈现。有些学者就曾指出,目前的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就个案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自然发展[5]。抽象性司法解释不足以弥补成文法固有的缺陷,无法适时应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司法人员在适用法律时尺度不一的问题。具体解释与抽象解释相比的优势在于其更贴近个案事实的特殊性,能够更加现实、具体地反映法官个人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更多地结合了经验知识和生活逻辑,能更好地体现个案处理的个别正义,以及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法治诉求。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和示范性,在于其能够迅捷地反映社会实际案件的特殊性,以及典型案件对于法律规则的适用需求,法官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对适用法律理由的说理和论证,来阐释法律具体条文的内涵,使原本抽象的法律规定具体化,使许多新的法律规定因适用而直观化和明确化。有研究者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1月至6月刊登的案例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复述法律规定的从61%降至23%,解释法律规定的从32%上升至53%,填补法律漏洞的从7%上升至14%[6]。由此可以看出,指导性案例在指导侧重点上的演变,即由简单地呈现法律适用结论开始更多地向解释法律和赋予法律条文以新的内涵的转变,这也正是指导性案例独立价值的显现。如在案例指导制度实施以来,最高院公布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刑事指导案例中有两个故意杀人罪的案例。两个案例均涉及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选择问题,两个案例均在裁判理由部分着重分析了案件的性质、起因、案发经过、案发后被告人的表现,以及适用死缓的理由。这样的指导性案例使我国刑法中抽象的死刑适用条件在具体案件中得以直观化和具体化;在死刑和死缓的选择上,也体现了最高院在限制死刑方面的态度和取向,对下级法院以后裁量类似案件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此外,这两个案例还都涉及到《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关于限制减刑的适用。通过个案情节的展示,明确了这一新制度的条文内涵、适用情形和限制减刑的裁量限度,使其他法院的法官在今后适用限制减刑这一规定时有了具体参照的样本[7]。每一个典型案例都是法官具体法律适用解释的一个典范之作,为使这样的具体个案解释具有恰当性和合理性,必须对其予以必要的约束和监督。因此,经过筛选的典型案例应该在法律适用上具有这样的示范作用。法官在适用刑事法律时,对刑事法律的解释是法官的司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官的天然权力。法官的这种司法权力只能在法官办案的过程中使用,并且要依照一定的原则和规范使用。它的效力只能及于具体案件,但是它的影响力会超出具体案件本身[8]。
相对于抽象司法解释做出机关的权威性,具体解释会面临许多质疑。为此,指导性案例需要经过严格的推荐、遴选、审议和讨论程序。指导性案例的筛选、推荐的过程中就是对法官适用法律、解释法律状况的全面判断和衡量。当然,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设计也会对具体案件适用解释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同时,法官的判决是否公正,审理案件时对刑法的解释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立法意图,解释是否合理,也要接受当事人、辩护人、检察官乃至社会舆论的监督。为了使法官更好地履行解释法律、裁决案件、公正司法的职责,我国现有的判决书网上公开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监督措施。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公布了《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但由于规定太原则和粗略,不易操作而没有很好地实行。2007年,《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因地制宜制定公布本地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逐步落实裁判文书的公开工作。此后,各法院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布实施办法,并且也开始了公开裁判文书的具体工作。如北京、河南等地法院,已经建立起功能较为完备的裁判文书库,面向社会公开。但是,全国大部分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件公开工作并没有真正落实,即便在作为典型的地方法院,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也远没有做到及时、全部的公开。2013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开始实施,对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布细则做出了较为详尽具体的规定。如果这些规定能够被各级法院真正地贯彻和落实,这将对提高我国审判文书的质量,提升法官素质、促进具体个案解释的规范化以及真正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都将十分有益。
[1]刘作翔,徐景和.案例指导制度的理论基础[J].法学研究,2006(3):29.
[2]郜永昌,刘克毅.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J].法律科学,2008(4):136.
[3]孙 谦.建立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探讨[J].中国法学,2010(5):79.
[4]罗豪才.行政审判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431.
[5]李纬华.从案例指导实践看案例指导制度的三个问题[M]∥苏泽林.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和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04.
[6]秦 旺.论我国案例指导的制度建构和适用方法——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为分析样本[J].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2007(4):217.
[7]陈兴良.死刑适用的司法控制——以首批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J].法学,2013(2):43 -57.
[8]包 雯,魏 健.论刑法适用上的个案解释[J].河北法学,2004(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