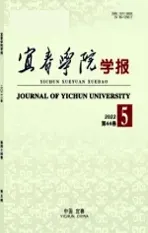不屈的生命之歌—— 《我的童年》叙事伦理分析
2014-08-15雷莹
雷 莹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人文科学系,福建 福清 350300)
《我的童年》[1]原名《我的生涯》,记述了萧军从1907年出生至1917年离开故乡这十年的生活经历,是作者唯一一部正式自传作品。该作品最早从1947年5月到1948年7月连载于《文化报》,1982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我的童年》作为中国现代自传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中国现代自传的著述都未提及该作品。
与《沫若自传》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自传经典作品不同,《我的童年》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来整饰自我的生命体验。本文拟从叙述伦理切入,研究该作品的叙述特征。
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2](P4)因此, “叙事伦理学是更高的、切合个体人身的伦理学。”[2](P6)
中国现代自传的出现与个人的发现、个性意识的觉醒有密切的关联。作者在自我的个体叙事中传达出对社会人生的理解,这种人心秩序的传达正是叙事伦理的基本内涵。自传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但是作者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在写作中总会与社会话语相呼应。中国现代自传兴盛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五四时期的人文主义观念与话语和“阶级的人”的观念与话语并存,与此相对应的是,自传文本中呈现出启蒙话语与救亡话语相交织。作家们通过写作自传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自我反省,并期望通过自赎可以赎众。自传中书写的人生经历都有历史事件的投影,他们通过对自我人生经历的梳理,审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反思个人和民族的命运。郁达夫和郭沫若都刻意将自己的出生和当时的重大社会事件联系起来,使历史成为自传中的关键词。如郁达夫在自传的第一章《我的出生》中就写道:“光绪的二十二年 (西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已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传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症,是神经质的。”[3](P352-353)郭沫若也明确提出,自己写作自传的动机是 “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4](P3)因此,他们在叙述自己的童年经历时,将个人的遭遇与国家民族的灾难融为一体,呈现自己童年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在这些自传中,叙事看起来是围绕个人,实际上民族、国家和个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们言说的是反传统群体的使命感,以叙事来规范和动员个人的生命感觉。按照刘小枫的分类,这应该属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次年的公开发表,是解放区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革命化的主题提炼、“工农兵”化的题材选择、阶级化的作家切入生活视角成了解放区的文学规范。一部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热切地宣传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被驯化,主动放弃自我,将个性融入集体性,并最终实现大众化。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宏大的生活世界以符号霸权的形式篡改着国人的生命记忆,而萧军却没有止步于对历史符号的迷信,自传的自我诉求可以看作离经叛道者对权力话语的抗争。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解放区,时代伦理规范强调的是集体意志,在文本的叙事中往往是历史的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历程,民族、国家、历史比个人命运更重要,个体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于普遍的历史规律中。萧军在自传中有意疏离用时代伦理规范来完成意识形态的规定叙事,而采用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形态讲述童年经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2](P7)《我的童年》讲述的是传主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作者并没有将个人创伤体验上升为家国叙事,而是遵照个体生命自身的召唤,用富于创意的、印刻了个体感觉的语言描述自我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和深度情感。
《我的童年》消解了传统自传的时空概念。时间和地点的确定性是一般自传作品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但在《我的童年》中时间和地点都只是一个背景,一种很模糊的存在。自传开篇没有写传主出生的时间,故事开始的年代非常不明确。自传第一章的开头是:“母亲生下我七个月就死去了”。这种含混性的时间描述就显示了,《我的童年》没有《沫若自传》等自传文本对史诗性的着意追求。自传包括了13个独立成篇各有标题的片段,在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中流量出一些时间的痕迹:“后来我到了五岁”,“七岁那年的春天”,“大约是八岁那年”等,这些模糊的时间概念体现着时间的推移与跳跃。这些大的时间点是作者在叙述中为了引出事件而提出的,“我到了五岁”,奶娘就被无情地解雇了,“七岁那年的春天”,“我”被送进了父亲开商号的镇上入学,“大约是八岁那年”,“我”经历了家庭的破产。各篇的标题分别为《母亲》、《家族》、《乳娘》、《姑母们》等等,从整体上看自传的叙述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为了维护各个章节的完整性,有些事件被提前叙述。如第五章《姑母们》中详细叙述了五姑的出嫁和婚后的生活,在第十一章《归来以后》开头又出现:“回来不久,五姑和姐姐,竟一同出嫁了。”因此,文本中小的时间段,更是充满了跳跃性。在《我的童年》中,传主成长的纵向线索变得模糊不清,缺乏对往事有条不紊的整理和分析,因此,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的发展轨迹只能散落在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诸时间中,导致以时间为载体的人生经历变得支离破碎。作者在追忆自己的童年经历时,往往只对在自己内心留下深刻印记的往事加以展开,现实从回忆中形成并为其确立了恒常的生命存在形式,因此时间的先后显得微不足道。作者解除了时间的束缚,以这种自由度更大的片段式结构进行自传创作,传达出童年经验在他内心深处产生的心灵回音。
其次,自传中的地域范围也十分模糊。郭沫若、沈从文、张资平等人在自传对故乡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都有科学性的客观描述。而《我的童年》的第二章《故乡》中写道:“这是属于辽西省松岭山脉附近一所不算太小的山村”。构建宏大历史框架必不可少的社会历史遗迹在该自传中更是不见踪影。自传中只有《入学》和《破产》两章叙述了父亲在镇上的家,剩余的故事就发生在村里。《流亡》中视线短暂地转移到了“义州城东边接近热河省边境蒙古一带地方”,传主居住的地点更加模糊,“秃秃的小山,干干的河床,零零星星的人家”。文本中地域的模糊性抵消了叙述上空间的宏大感。自传所描绘的生活世界是将传主作为认识主体,通过自身的情感和体悟,将外部事物内化为主观体验后,投射在内心的景物。这种观察和呈现外在景物的方式是与传主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与作者的主体性相联系。自传中时间和地域的模糊性,使宏大叙事中重要的时空背景在文本中处于残缺和无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作者刻意用个体叙事摧毁严肃、认真的宏大叙事,使宏大叙事呈现为一种虚拟的存在,而让个体叙事中心灵和生命的故事给读者更大的冲击,这是萧军对个性、自由的理解和尊重在起作用。
作者放弃了史诗性的宏大视角,从个人化的视点切入,书写具体可感的片段式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文本中具体的生命历程与生存境遇,赋予了自传更鲜活的生命性和体验性。作者站在个人化叙事立场上,一方面将传主置于漫长而丰富的人生历程中,探寻个体生命逐渐成长和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另一方面聚焦于传主周围各色人等的错综复杂的人性欲望与人际纠葛,对个体的复杂性进行了主观化阐释。
由于时空的模糊性,读者的目光更会被吸引到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生活世界,更能深入故事的深处和细部,关注个体生命的成长轨迹。第一章《母亲》的结尾这样写道: “母亲啊!在生前你被欺侮,死后也还要被歧视!我开始懂得这人间!一颗小小复仇的灵魂,它开始由柔软到坚硬,由暗晦到晶明,在我的血液中被滋养,被壮大起来了!——它一直陪我到今天。”萧军的母亲在他七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关于母亲的记忆,只有周围人的讲述及其唤起的自我情绪和感受。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为了抗争遗忘而不断地强化,使作者说出这些话的情感和力量远远超过了关于母亲的这些片段本身。当前的感受和重现的记忆使读者可以触摸到“一颗小小复仇的灵魂”。第五章《姑母们》在叙述五姑时插入了五姑和父亲认为“我”将来一定不会有出息的预言,“对于这些预言我不独不再重视,而且朦胧中反而增加了我一种报复的力量:……我必须要出息啊!”“预言”不仅使作者追述了过去之“我”对未来的理解和看法,显示了过去之“我”由于生活的束缚而产生的焦灼和困惑,而且引出了当下之“我”对自己性格的反思。“从小以来,我不懂得应该真心惧怕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我只有力不从心的痛苦,很少有惧怕的心!有一种茫然的、蔑视一切的、不怕任何破败的,最终以一死了之的决心,来和一切搏斗着。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原始性的脆弱,并非经过提炼可贵的韧性的刚强,可惜这种恶劣的习性它还一直在我的身上保留到今天!虽然它一直被我的理性严苛地管束着,提炼着……但有时它——这只原始的兽——还要反叛!有时伤了自己,有时也伤了人!”第五章的结尾写道:“从此,朦胧中似乎渐渐萌芽了一种决心,就是:不再向任何人寻找温爱了。要从这无爱的人间站立起来,用一种冷淡的、蔑视的、残忍的自尊和顽强,搏斗着,忍耐着,在生满着荆棘和蒺藜的生活旷野里——孤独地穿走下去吧!让那搏斗的血迹作为后来者的路标罢!”传主认为自己已失去了姑母的关爱,立志在生活的沉浮中勇敢而孤独地面对悲苦的现实人生。苦涩的经历换回的是自己对人生真谛的理解。这是此篇的高潮,勾勒出传主带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人生的孤程中艰苦跋涉的图景。自传中不断穿插呈现的喜怒哀乐正是个体生命的在世性情,虽然这些只是传主人生历程中的某些片段感觉,但是传主就是依靠这些片段感觉捱过人生中的伤痛时刻,这些都清晰地体现了传主的存在气息,作者拾起记忆里的片段,跳跃性地叙述着那些在精神世界留下痕迹的生活事件,一个个交叉重现的片段拼出了传主的人生画面。
《我的童年》中有大量篇幅叙述传主的几位亲人,及其对“我”生活和成长的影响。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优化和净化,记忆会不断改变所存储的内容的颜色。尤其当作者远离家乡之后,童年时代家庭生活的记忆会因时空的间隔、情感和心理的间隔,而幻化成亲切可爱的图景。因此,在一般的自传中,顽劣苦涩的生活事件会变成趣味盎然的生活画面,性格暴虐的父母由于作者的缅怀之情也会变得和蔼可亲。中国古代讲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即使尊长有千般不好,作为子女也要尽力维护他们的荣誉和尊严。然而,《我的童年》却敢于正视家庭关系和家庭矛盾的阴暗面,撕破了亲情的面纱,审视亲人的性格和灵魂,在表达自己深切的理解和感激的同时,直接地呈现了他们卑微、丑陋的一面。对于最爱“我”的祖母,作者也客观地剖析了她的性格。自传既表现了祖母的勇敢、坚强、乐观,又写出了她的自私、不公和势利。“我曾亲眼见过她和二叔一同打过二婶母,而且打到从嘴里流过血!”在他笔下,家庭矛盾尖锐,亲人之间关系恶劣,甚至相互仇视。祖父和祖母之间以及祖母和父亲之间都充满矛盾,常常为琐事陷入混战。每次祖父回到乡村,祖母总要抓住机会吵闹一番。 “每次祖母总是一马当先采取着攻势。其余儿女们如果在场就为她在精神上助着威,或者沉默,或者巧妙地笑着,或者有时插进一两句讽刺的小话,于是一场戏剧就开了锣。”祖母和父亲之间也经常为了钱而争吵,用恶毒的语言诅咒对方,“那些毫无恩情而可耻的语言,竟象刀剑一般在祖母和父亲之间闪电似的彼此刺击着”。“父亲和三叔之间的感情是超乎一般人的敌对性地存在着,他们打起架来竟是用刀和用枪。直到近乎中年,他们每人脸上的伤疤还是鲜明地存在着。”作者通过具体的场面描写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人与人之间毫无亲情可言的生活画面,表现了他大无畏的反抗传统的勇气。
作家并不像伦理学家那样自上而下地,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二元对立的基本规定和性质出发,进行逻辑推论与分析,做出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作者选择了自下而上的、感同身受的体验过程,从而获得真正的来自心灵的悟解。如果道德只在人的身心之外发出训诫的力量,那么它的力量是软弱或无意义的。只有在个体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里挣扎、锤炼,沾着体验者自身的血肉和痛苦,并渗入个体的心灵内部,道德才能呈现出它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实现的过程,对于亲身经历的个体来说,是异常艰苦的。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提供了个体性的生存困境和各种悖论,对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叙事中如何表达伦理观念,而是如何组织生活片段使他们成为秩序。在《我的童年》中,萧军没有依据既定的道德原则和话语体系整饰自己的生命体验,而是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来凭吊个人生命痕迹,将个人的在世性情呈现在读者面前,探究传主的内心世界,揭示隐秘又说不清的情感。
[1]萧军.我的童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3]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3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