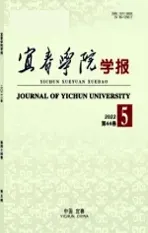以文代墨作丹青——宗璞小说的“散文画”叙事
2014-08-15陈洁
陈 洁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散文画”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最初应用于孙福熙的《赴法途中漫画》①,叶圣陶先生1921年在《文艺谈》(十五)②中写道:“绍虞说孙福熙君的《赴法途中漫画》可称为‘散文画’,是一种综合的艺术作品。孙君那篇文章随意取所见,用画家的手段表现出来,而又不单是写实,处处流露作者的情思。”在这两句话中,叶圣陶准确地概括了“散文画”的基本特征,即把文字和绘画相结合,运用绘画艺术的技巧来写文章,以作画的笔法记录生活,描写生活,在文字中渗透画家的情感和思考,形成一种文画交融的审美风格。继叶圣陶之后,1925年朱自清先生在读孙福熙的另一部散文集《山野掇拾》③时说道:“孙先生是画家。他从前有过一篇游记,以‘画’名文,题为《赴法途中漫画》;篇首有说明,深以作文不能如作画为恨。其实他只是自谦;他的文几乎全是画,他的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画!他叙事,抒情,写景,固然是画;就是说理,也还是画。人家说‘诗中有画’,孙先生是文中有画;不但文中有画,画中还有诗,诗中还有哲学。”④朱自清先生的这些评论可以说又进一步深化了“散文画”的审美内涵。他认为孙福熙的散文之中,不但叙事、抒情、写景是画,连说理也是画,也就是说这种“散文画”不仅有事、有情、有景,而且还有诗性的哲思。由此可以概括出“散文画”的三个层次:第一是“文中有画”,有景语 (包括生活场景和自然风景);第二是“画中有诗”,有情语;第三是“诗中有哲学”,有思语。
“散文画”理论在现代散文家的笔下得到了大量的创作实践,郁达夫《故都的秋》、《钓台的春昼》,朱自清《荷塘月色》、《绿》,鲁迅《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这些作品无一不是经典的“以文作画”的妙品。而沈从文、丰子恺等文画皆擅的作家,又同时游笔于散文和小说这两种文体之间,进一步推动了“散文画”理论从散文到小说领域的拓展。进入新时期文学,作家的创作技巧不断革新,他们追求与绘画艺术结合的自觉意识也愈加强烈,小说更大程度地向绘画渗透。小说家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专注于人物和环境的精雕细刻,也不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上费尽心思,他们淡化情节,分解结构,疏远背景,在小说的诗情画意上追求艺术的真实感。当代女性作家中,杨沫、林海音、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残雪、张抗抗等都深谙“画笔”,徐小斌在她的《写作与色彩》中更是坦言:“色彩是我一生的爱好。最早的理想是做一个画家。至今我都认为,没有选择画家这个行当是我一生的错误……后来才知道,文字也是有色彩的,于是才有了对于文字的迷恋。”她们的纷纷加入,使得小说的“散文画”叙事更加明朗清晰。
当代作家宗璞经历过抗战,经历过反右斗争,经历过文革,是个从动荡中走出来的作家,她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在她的身上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传统和现代的交融。自195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红豆》开始,她一直以独特的气韵活跃于文坛。历史沧桑,身世飘零,怀旧忆人等感伤主题使她的小说总是隐隐地沾染着诗性的魅力。而潜藏在文字背后的女性视角又常让她的小说带有某种散文式的抒情。“宗璞长于诗书之家,自小喜爱鉴赏名画,曾经潜心揣摩过许多中外绘画作品。她在线条、色彩、构图方面禀具的慧心和敏感,为她引绘画因素入文提供了便利条件。”[1]正是这样的宗璞,在小说中以文代墨,用故事和情感展开她柔缓细腻的丹青书卷。
一、景语构图: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现代著名画家潘天寿先生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对画的结构布置如此说到:“画事之布置,须注意画面内之安排,有主客,有配合,有虚实,有疏密,有高低上下,有纵横曲折,然尤须注意于画面之四角,使与画外之画材相关联,气势相承接,自能得气趣于画外矣。”[2](P371)这段话强调画家在作画时要把握好各种布局和节奏,注意画面内外的和谐,这样才能得绘画之自然气趣。而在小说的结构技巧中,叙事节奏的把握往往也决定着整个故事的气势和韵律。宗璞的小说创作,善于把众多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放置于看似平常的生活情境里,故事在诗意化的场景中缓缓展开。但在疏淡过后,她会突然浓墨重彩,截取烙有伤痕的关键性情节,使得这些看似随意点染的小细节,在画面之中顷刻尖锐起来,再与之前早已做好铺垫的舒缓的留白交相辉映,从而酝酿出一种温柔的刺痛,构成张弛有度的小说节奏。她的小说不必处处刀光剑影,却能时时扣人心弦,这其中又以她的长篇系列《野葫芦引》最具代表性。
《野葫芦引》第一部《南渡记》故事开始时为吕老太爷 (吕淸非)的出场布置了这样一幅祥和的图景:
吕老太爷每天上午诵经看报……随身必带一只小宣德炉,有五斤重,每天点一炉好香,一上午让这炉香陪着。老人生活俭朴,只是每天这炉香要求苛刻,必定要云南产的鸡舌香,别的香一点就头晕,如果不点也头晕。念诵的经是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念到“菩提萨婆诃”,大声念十遍,再小声念别的,念一会儿就看报,如果报还没有来就要问报来了没有,怎么不送进来。下午午睡很长,起床后的时间如果可能,就是说如果外孙可以奉陪的话,就把它都交给外孙。
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吕老太爷一天的生活场景,作者所用的笔法非常平淡,只是简单地勾勒日常琐事,画面之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影子:老人、报、香和《心经》。然而到小说的结尾部分,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侵入北平,女儿和孙子都举家南迁,只有老人怀着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孤独地留守老宅。这时的他戒掉了看报的习惯,因为报纸只会徒增家国沦丧的悲哀。此前和外孙谈天的“人生第一乐事”也不再会有了,因为他活不到外孙回来的时候了。面对日伪政府威逼利诱的“汉奸”头衔,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服药自尽。在他临死之前,有两个细节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一是侍者在为他点香时,“先拈了三小块鸡舌香放在炉里,见所剩无多,又拈回两块,节省着用。”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炉香,作者如此轻轻的一个笔尖,香炉的图像意义就得到彰显,香尽人亡,绝妙地点染出祖国沦丧,家园零落的凄楚。另一个细节是当老人服下安眠药静静躺着的时候,不知情的侍者拿起《心经》准备递上,“老人摇摇头,眼光是茫然的”。在这幅老画上,这一个小小的着墨就使得画面里最惹眼的反而不是垂死的老人,而是被老人弃在一旁象征平和的《心经》。最初鸡舌香和《心经》都代表着老人的安适和闲情,但当民族苦难降临的时候,老人果断放弃这一切个人利益,宁以一死换名节。一炉香、一部经,浅浅的几个画面既营造出深深的悲凉,又凸显出整个故事的主干,线索清晰、层次井然、疏密有致。
在《野葫芦引》第二部《东藏记》当中,作者这种从细微处见真情的手法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东藏记》紧承《南渡记》,主要写吕淸非的小女儿吕碧初和丈夫孟樾带领三个孩子逃离北平之后,暂居西南城市昆明时所经历的悲喜。作家不写士兵、不写战场,只把眼光投射在后方的几个小家庭。时而是舒缓的小情调,时而是紧张的“跑警报”;有故旧重逢的喜悦,也有突然袭来的噩耗。作者既掌权大局,又留意微末,舒缓处见缜密,紧张中又留空隙,没有大气磅礴的豪迈挥洒,却有蓄势而发的微妙玄机,不管是着眼于整个结构的情节选取,还是聚焦于具体场景的细节设置,这样的叙事安排,都可谓张弛有度,游刃有余。
二、情语描线: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
文学是时间的艺术,绘画是空间的艺术。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追求线条勾勒的立体效果,而绘画当中的人物画又特别讲究造型,讲究人物瞬间情态的传达。读图风尚的流行,使得许多小说家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借鉴绘画当中的塑形技巧,以期拓展文字的图像空间,增强小说人物的内在张力。当代女作家叶文玲曾坦言自己的小说《茧》是看了罗中立画作《春蚕》中的人物描绘,再用同样的方法观察了自己的母亲与另一位老大娘后选定一个视角而创作的。在绘画当中,线条本来是没有情感的,但它经由画师的运作而不可避免地浸透画家的主观情思,优秀的人物画画师都知道如何选取视角,如何运作线条从而出色地完成一次生动传神的人物塑形。
宗璞是个有一定美术鉴赏力的人,她在散文《三幅画》中谈到自己向汪曾祺索画、然后框画的经历,只有对画有特殊感情的人才会有如此举动吧。而她在另一篇散文《丁香结》中写道;“在细雨迷蒙中,着了水滴的丁香格外妩媚。花墙边两株紫色的,如同印象派的画,线条模糊了,直向窗外的莹白渗过来。让人觉得,丁香确实该和微雨连在一起。”又如《西湖漫笔》中谈到她看山水的心情:“正像看达文西的名画《永远的微笑》,我曾看过多少遍,看不出她美在哪里,在看过多少遍之后,一次又拿来把玩,忽然发现那温柔的微笑,那嘴角的线条,那手的表情,是这样无以名状的美,只觉得眼泪直涌上来。”这两段话不仅表现出她对印象派画作和达芬奇画作中线条处理特点的了解,同时也表露她个人常以绘画的眼光观察周围生活的习惯,而且这种观察还是极其感性,极其诗意的,因为看着看着还会掉泪。
以画理入文,宗璞小说的“散文画”不但善于在笔端融汇个人情感,而且还把绘画中讲求灵动的艺术格调移植到小说的人物刻画中,用简洁的线条,跳跃的笔墨,驾轻就熟地勾画物最生动、最精彩的细节,寥寥几笔,轻轻几画,人物塑造形神兼备。她在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对女主人公“梁遐”的刻画就是如此。这个故事讲述在1975年9月到1976年“四五运动”发生的这段时间里,中年女大提琴教师慕容乐珺因亡友 (蒙冤自杀)的情谊,短暂收留他的女儿梁遐,并教她弹琴。作者透过乐珺的视角,紧紧抓住梁遐“笑”这个画面,集中视野,变换线条,粗细结合,最终成功塑造出梁遐的形象。故事一开篇,梁遐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读者视野:
她身材苗条,举止轻盈……电灯开了。乐珺看见粱遐是个很美的姑娘,她上身穿着米色外衣,里面是黑色高领细毛线衣,下身是深灰近乎黑色的长裤。一头蓬松的短发,有些像男孩。脸儿又红又白,唇边挂着微笑,眉毛很黑,很整齐 (不少人以为她是描出来的),一双真正的杏眼,带点调皮的意味 (后来乐珺知道,那其实是一种嘲讽的神情),正瞧着乐珺。
这段描写虽然也很细致,但只可算是作者以粗线为人物做的底稿。从这幅人物肖像里,读者只能粗略地了解到梁遐是个年轻漂亮,活泼率性的女孩。接下来,作者就匠心独运,从梁遐的各种“笑”里疏疏淡淡地描细笔。
起初当乐珺问梁遐为何学音乐时,“‘混饭吃呗!’粱遐又清脆地笑了。”而当别人在她面前提到革命时,“正说着,她忽然又咯咯地笑了起来。‘革命两个字倒好听,可他们害死我爸爸,也说是革命!’”这两处的“笑”明显有着不同的含义。其后,当梁遐与把她爸说成是“走资派”的姨妈大吵一架之后“嘴角上却带着笑,还是那种嘲讽的,又加上了轻蔑的笑。‘真可笑!’她说,索性咯咯地笑起来。”1976年春天,当外面的局势日趋紧张时, “她很少说话,也很少咯咯地笑了。”、“这二十多天来,她似乎长大了不少,嘴边嘲讽的微笑很少出现了。”最后,当梁遐终于决定“我要负责了!”时:
粱遐微笑了,那是正经的、纯真的微笑。
粱遐没有再说话,她的笑容渐渐变得冷硬了,脸上又出现了嘲讽、痛苦的神情。
粱遐则简直是在发抖了。突然间,她迸发出一阵大笑,声音有些凄厉,但还是清脆的。
她们走到抄诗的人群中。多少人如饥似渴地抄着那火热的诗句。
这几处作者的笔墨都可谓吝啬,但是各种细微的线条综合起来,再添进开篇的粗笔底稿,整个人物就显出神采了,梁遐的形象也顿时跃然纸上。她从上辈的冤屈里承受伤害和羞辱,以致于怀疑真理,鄙视世界,对一切都抱有轻蔑的嘲讽,“她那清脆的笑声比哭还要使人痛苦”,她压抑着内心的热血和激情,在迷茫和失望中“混生活”,她的“笑”有委屈和酸楚,也有冷漠和嘲弄,然而当“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这种“笑”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严肃和深沉,因为她注定要以火一样的激情投入到运动潮流之中,高昂地为新时代的到来摇旗呐喊。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宗璞敏感、温柔,她的用笔常常含情,可这种情又总是蕴有节制,在创作这幅人物画的过程中,作者的线条从粗到细,情感也从淡到浓,循序渐进,故事忧而不伤,怒而不炽,画面精巧灵动,人物形神俱现。
三、思语着色:言近旨远的主题渲染
中国作家冯骥才在讨论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时说:“文学是用文字的绘画,所有的文字都是色彩气。”⑤他在这里不仅指出了文字的绘画性,更强调了在“以文作画”中色彩的关键性作用。而法国美学家丹纳在谈到造型艺术中色彩的表情力量时也说道:“色彩之于形象有如伴奏之于歌词,不但如此,有时色彩竟是诗歌而形象只是伴奏,色彩从附属品一变而成为主体。”[3](P407)其实,在具有 “散文画”特征的小说创作中,色彩也有这样转客为主的功能。因为色彩虽然是一种直观的感觉体验,但它与人的情绪、意识、心理等间接感受密切相关。作为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文学来说,色彩往往能够营造某种氛围、传递某种象征、奠定某种基调,从而在作家表达主题时发挥意想不到的潜藏效应。特别是在小说中,有时候需要花许多笔墨来描写环境和形容气氛的场合,只要通过简单的上色处理就可以收获到立竿见影的表达效果。
色彩在宗璞的笔下,与其说是一种写作技巧,倒不如说是一种自然而言的思维习惯,她把生活中喜爱的色彩画面融入小说背景,寄主观情思于文字色调,以看似直白的方式在小说中构建一种蕴藏深意的思维空间。细读《南渡记》和《东藏记》的开篇,你会发现作者在讲述故事前早已为全章铺好底色:
这一年夏天,北平城里格外闷热。尚未入伏,华氏表已在百度左右。从清晨,人就觉得汗腻。黑夜的调节没有让人轻松,露水很快不见踪影,花草都蔫蔫的。到中午,骄阳更像个大火盆,没遮拦地炙烤着大地,哪儿也吹不来一丝凉风。满是绿色的景山,也显得白亮亮的刺眼。
这是《南渡记》最开始的一幅画面,画面里最浓的色彩是白,带有炽热和焦躁的白,而这种白恰好是这个故事最真实的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的前夕,北平城的上空应该是到处都布满着白色恐怖吧!作者没有一开始就写人们此时的生活和心态,而是从虚处着笔,在用色调晕开基调之后,再舒展故事画卷。再看《东藏记》的第一句话:
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蓝。
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蓝,只要有一小块这样的颜色,就足以令人赞叹不已了。而天空是无边无际的,好像九天之外,也是这样蓝着。蓝得丰富,蓝得慷慨,蓝得澄澈而光亮,蓝得让人每抬头看一眼,都要惊呼:哦!有这样蓝的天!
蓝在色系里代表清澈,与《南渡记》的北平相比,《东藏记》中偏居西南一隅的昆明确实少了些动荡,而多了些安宁,它不是前线,没有直逼视野的白色光,对于刚刚逃难过来的孟家人来说,这里是祥和而美丽的。但是蓝同样代表着深邃和忧伤,它会如大海一样,随时在平静中掀起波澜。在昆明,这样“澄澈而光亮”的蓝天里会突然出现敌人的轰战机,一颗一颗黑色的炮弹从天而降,击碎你的家庭,击碎还在梦中的你,这“非常非常的蓝”不是正好以极美的画面反衬出时代潜藏的不安吗?这些看似随意和无心的着墨其实都浸染了作家的别有用心。
宗璞的另一个短篇小说《鲁鲁》写到一条叫“鲁鲁”的“矮脚的白狗”,它经历过两次易主,每一次换主人,它都会因不情愿和难割舍而极度疯狂和悲伤。小说一开头就讲到它的旧主人死了,被迫来到新主人家,它起初不适应,但是慢慢地它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着许多美好动人的回忆。但到结尾的时候,要搬走的这家人无奈中又把它交给了新的主人,这一次它更加歇斯底里,它发了疯似的寻找旧主人,为此还跋山涉水经历了艰苦的旅程,可是人去楼空,只能原路返回,为了表达它的思念,它常常独自去到当初和旧主人分别的地方,虽然那个地方对于一条狗来说有太多的路程。故事结局,鲁鲁“坐在大瀑布前,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小小的白狗坐在那“白帐幔似的”大瀑布前,注定会像它的哀号一样,隐没在跌宕的水声里。就这样鲁鲁淡出了画面,也但淡出了故事,眼前只有一片跳荡的巨大的白色落水。白色是淹没,是消失,是无望,这更加深了这个故事在人们心里留下的悲伤的回音。在这里,色彩无声地倾诉着写作者的心意。正如徐小斌在《写作与色彩》中所说的:“写作,是意外的不可言喻的色彩。”
宗璞小说善于选景,善于用简单的笔法处理复杂的结构和深远的层次;她也长于抒情,文章随处可见浪漫抒情的底色写意,“无论读宗璞哪种题材的作品,你都能读出其中蕴含的诗情与诗意。”[4];而绘画里的着色艺术,在宗璞那里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5]宗璞小说以景构图,以人含情,以色蕴思,这种景、情、思交融的艺术作品恰如一幅柔婉动人的“散文画”,在文字与图画的轻盈跳跃中,以有限笔墨,造无限艺境。
注释:
①《赴法途中漫画》是孙福熙的一系列游记文,全文共10篇,1921年1月11到3月21日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游记栏”)。后又因郭绍虞的推动而转载于《新潮》杂志第3卷第1期。
②此文最初刊载于1921年4月5日的《晨报》,是目前为止“散文画”这个概念最早见诸文字的证明。
③《山野拾掇》原是孙福熙1922年7月26到9月5日在法国乡间习画时的日记,后来他把这些旅行日记整理成82篇连续的游记散文,在《晨报副刊》(1922年10月1日到1923年7月20)连载。
④此文作于1925年6月9日,原载《我们的六月》。
⑤转引自赵玫:《艺术天空的闪电》,《光明日报》1993年5月22日。
[1]吴延生.简论宗璞散文的细节描写技巧[J].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7,(9).
[2]周积寅,史金城.近现代中国画大师谈艺录[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8.
[3]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何西来.宗璞优雅风格论[J].文学评论,2004,(2).
[5]贺国光.淡妆浓抹总相宜——论宗璞创作的绘画美[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