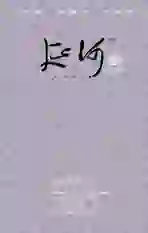纪念那个坐在炕里的人(创作谈)
2014-08-12王明明
王明明
我对上坟这件事有了点特殊的理解,发生在前年。那年,我带妻子回东北老家办婚礼,同时决定两个人一起到祖母的坟上烧些纸钱,那也是我第一次带着人(而不是被带着)去给祖母上坟。时值盛夏,坟上长满了绿葱葱浓茂的高草,竟让人觉不出坟墓本身那或萧索、或悲伤、或压抑、或惧怕的气氛,满是生机。我走上坟墓,挥舞着镰刀,打理着祖父祖母的“家”,汗流浃背,同时,开始思考上坟的意义。
突然发觉,上坟,不单是一种对祖辈某个人个体的怀念,更是一种传承、一种指引、一种家族精神的延续。
家族—现代社会里将会越来越少出现的词汇,却在我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祖父一生育有七子,我出生时,他早已去世多年,我对祖辈的理解就顺理成章体现在祖母身上—那个坐在炕里的人,那个说一不二的人,那个直到两鬓斑白、儿子们各自成家立业仍在家族里享有地位的人,那个历经世事个性坚韧的女人。
2011年,我在《黄河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摇曳的烟火》的小说,以除夕夜一个少年爬山到瞭望台陪父亲守夜为故事背景,试图表现一些成长中涉及到对父辈以及对幸福的理解和一些莫名的情愫。这篇小说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坟》的诞生,都是一个跟爬山、跟走一段艰辛路相关的故事,只是这一次,要表现的主题无疑更加突出,但同时导致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简单、直白,缺少了一些韵味。
一个人的路要怎么走,千万种走法、千万种选择,我想多数人都会更愿意自己去决定自己的人生,可当时代越来越进步、我们越来越“成熟”、个性越来越解放,自己可以随意在那一千种一万种中自由选择时,我开始有些怀念父辈那个时代大家族里的那种“长者指路”式的幸福,诚然那种路是窄的,但却是幸福的,因为无需你动脑判断,也不用你衡量是否合适,你只需一条路走到黑,身体会累,但精神轻松。
可事实上,困顿和茫然成了这个时代里人的一大共性。我们即使不被他人左右,也似乎在被命运左右。我们孤军拼搏,四处碰壁后,正需要有那个坐在炕里的人给予我们温暖。我想,上坟,就是纪念一种出发,是回归本源的东西,如同画了一个圆又回到远点,体现出一种传统,一种哲学意味。
这是一篇很简单的小说,说简单主要原因在于我总是试图在最普遍的生活中找到文学元素,但我自知文学化的手段又跟不上。其实想说的都在作品里,创作谈属于重复,全是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