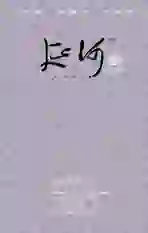我再好,不在你身边
2014-08-12舒眉
舒眉

还不到五更,明爷就醒了。
人老了,瞌睡越来越少,醒得一天比一天早了。夏天还好,到了冬天,外面黑洞洞的,感觉像是半夜里。屋里屋外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明爷翻了个身,继续躺着,躺一会儿,再翻一次身,面对着窗户,窗外还是黑魆魆的。这么着翻了几次身,窗外还是不见一丝亮光。黑夜似乎是有重量的,睡不着躺在炕上,感觉身体各处都压得生疼,炕上厚厚的褥子也不觉得软和。明爷摸索着拿起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机看了时间,才五点半呢。手机是外孙女青儿用过的,去年就给了明爷了,说她自己又换了新的,还给明爷教了怎么用。明爷已经七十六岁了,眼睛花了,晚上看东西更是模糊一团。青儿给明爷设置了最大的字体,时间就显示在屏幕上,大大的数字,按任意一个键,灯光就亮闪闪的,很清楚呢。青儿还给明爷设置了快速拨号,按数字1就直接拨给丫头爱玲了,也就是青儿的妈妈,按2是儿子爱光,小儿子爱国两口子都是哑巴,没电话。再往下的3,明爷让青儿设置了全爷的号码。
全爷是明爷的兄弟,以前两家人常有过节,甚至还狠狠地吵过几次架,原因无非就是你家的树欺了我家的田,我家的牛啃了你家的苗之类的事情。都是女人孩子们在那里扯着嗓子嚎哭叫骂,明爷没有掺和过,全爷也没有。只有一次,还是女儿爱玲结婚不久,怀孕刚刚四个月,回娘家时不小心流产了,爱玲的婆家还在三十多公里外,来不及送过去,明爷把女儿从乡上的卫生院接回自己家里休养了几天才送回婆家去。在农村里,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爱玲还没有送走呢,全爷和全奶就找明爷来了,说虽然不是一家,但总归都是娘家,就隔着一道院墙,现在他们被血冲了门,晦气得很,让明爷赶紧把女儿送回去,还要请人来“收拾”一下。明爷也知道这个理,但总归是自己的亲闺女,也是全爷的亲侄女,小时候,还骑在全爷的肩上去公社看戏,全爷疼得跟自己亲闺女似的,明爷想全爷不会计较这些吧?可全爷不但计较了,还提出要求,要让爱玲的婆家人来给他们家的门楼披红挂彩,放鞭炮。明爷答应了,让爱玲的婆家人提了重礼,上了全爷家的门,一切都按全爷的要求做了。但明爷心里觉得全爷做得有点过分了,亲兄弟亲侄女的,怎么搞得比外人还生分?
过了几个月,全爷的儿媳妇生孩子,难产,折腾了一夜,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全爷一家人自然悲痛难言,就把根源归到了爱玲在娘家流产的事情上。全奶在街门上边哭边骂,骂爱玲是扫帚星,说就是爱玲害了他们的孙子。明奶气不过,两家人狠狠地吵了一架,就差打起来了。明爷全爷也吹鼻子瞪眼睛地说了狠话。那以后两家人好多年没有来往。后来爱玲生了大女儿青儿,又生了惠儿,生了儿子杰杰。全爷的媳妇也在三年之后顺利生了儿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两家的关系才慢慢缓和了一些。现在,青儿都已经二十五岁了,孙子孙女们都成了大姑娘大小伙子了,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也有外出打工的,像长硬了翅膀的鸟,全都扑棱扑棱飞出去了。这两年,大儿子爱光也在城里工地上干活,家里只有儿媳安萍种那几亩地。小儿子爱军是单院另过的。平日里,院子里空落落的,明爷转出转进,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明奶去世以后,明爷落了单,忽然觉得日子长得不知道怎么打发了,白天等不到太阳落山,晚上又等不到太阳出来。过上个几天能和全爷靠着南墙喧谎晒太阳就成了他过日子的盼头。但全爷忙,这样的机会很少。全爷儿子媳妇在镇上开了个小商店,离不开人,家里的十几亩地平时就是全爷和全奶两个人务弄着呢。冬天农闲的时候,全爷还要去放羊,每天赶着十几只羊出去,天色暗了才回来。全爷今年也七十二岁了,身体还算硬朗,虽说全奶的腿不是很灵便,因为长年腿疼,都弯成O型了,走路很慢,但顿顿能给全爷做可口的热乎饭,明爷现在觉得全爷比自己有福气。
明奶在世的时候,明爷可不这样想,不管明奶做啥,他都挑剔,今天说盐淡了没味,明天又说醋酸了难吃。就一碗饭,能挑出明奶的许多不是来,明奶也习惯了,明爷就是这个样,一辈子了,明爷一直挑剔着明奶,而明奶对明爷总是有点怯意。明爷年轻的时候浓眉大眼,高高的个子,娶了明奶之后曾被招工到鞍钢去当工人,都上了大半年班了,愣是被明奶和婆婆想法子叫了回来,明奶是怕明爷在那么远的地方当了工人扔下自己孩子不回来。明爷回来了,就再没有回去,一辈子都有点不甘心,心里对明奶就存了怨气。对明奶没个好脸色。明爷回来不久就当了生产队长,后来又当了大队长、大队书记,被公家的事情牵绊着,很少待在家里。干到五十多岁的时候,才退居二线。明爷退下来的时候土地已经承包到户了,明爷闲不住,自己又办了个煤球厂,经常待在厂里。后来儿女们相继成家,明爷也干不动了,正好回家抱孙子,再后来连孙子孙女也都长大成人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家里就剩下了老两口,两个人才算是真正在一起过起了日子,明爷还是对明奶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很少给明奶好脸色看。
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明爷天天数着时辰过日子,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想起明奶的好来。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与明奶相关的,炕上的被褥是明奶盖过的,也是她亲手缝的,桌子上的花瓶是明奶赶集的时候买的,当时明爷还嫌颜色太俗了,现在却是这个阴冷的屋子里明艳的色彩,让人看着温暖。明爷身上深蓝的中山装——明爷一直穿中山装,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卖的了,是明奶交给一个西安老裁缝做的,鞋里面的绣花鞋垫也是明奶纳的——都已经磨毛了,明爷有点舍不得垫了,怕一天天踩在脚下,那些色彩艳丽的花朵都烂掉了。院子里的花谢了,来年还能再开,可再没有人为明爷做绣花的鞋垫了啊。炉子上挂炉条的那个铁丝圈也是明奶自己拿个钳子拧上去的——明奶去世却已经六年了!这六年,明爷觉得比六十年还长。明爷常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老辈人说的话:独柴难着,独人难活。有些话,只有自己经历了才能明白,可是等到明白的时候,已经迟了。要是早一点发现明奶心脏不好,去医院看看,也许明奶不会走的那样快?
又辗转反侧半天,天还是黑的,屋子里似乎越来越冷了,身子下面的火炕还热乎着,手脚伸出被子就感觉冻得很,连头脸也是冰的。明爷于是起来捅炉子。可明奶就是在早上起来捅炉子的时候突然跌倒的。明奶在的时候,明爷瞌睡好得很,每天早上明奶起来捅炉子的时侯,明爷还睡得正香呢,明奶总是轻手轻脚的,把晚上封好的炉子捅开火心,再添上点煤,一会儿屋子里热了,明爷才起来穿衣服。明奶早已经准备好了早饭,明爷洗完脸,热乎乎的饭就端到眼前了。那天和往常一样,明奶在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去后院,把大煤块杂碎了,装了一簸箕拿到屋里来,明爷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明奶说自己感觉胃不太舒服,有点模糊的疼,吃了药,就早早上炕睡了。早上明爷还睡着,先听到明奶起来捅炉子的声音,迷糊中又听到沉闷的一声响,不再有声音。感觉有点不对,起来一看,明奶躺在地下,手里还握着炉条……等明爷赶紧喊来儿子爱光,打电话叫了镇上卫生院的救护车,明奶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医生说,是心梗。明奶就那么突然地走了,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现在,是明爷自己起来捅炉子了。明爷每天早上先捅开炉子,再回到被窝里躺一会儿,等到屋里暖和了再穿衣服。明奶走了以后,明爷再也没有那么好的瞌睡了,一个人睡在大大的炕上,总觉得满屋子的空旷把身子压得生疼,哪里都不舒服。这是个满间炕,占了整个屋子的二分之一,最多的时候大人孩子一起睡过十个人。女儿女婿,三个外孙,再加上家里的几个孙子,炕沿上一排头,他说一句,你说一句,眨眼的功夫就半夜了,还不肯睡。才闭上眼睛,天又亮了,人多了,屋子里的空气稠得像蜜,墙上的表的指针也像按上了翅膀,转得飞快。孙子们小的时候,最爱在炕上玩,被子枕头都是他们的玩具,你哭我喊的,大炕就像个小戏台一样,那时候多热闹啊!那时候,明奶喜欢这样的热闹,因为明奶的喜欢,明爷就有点厌烦,嫌吵。孙子们不像明奶一样顾忌着明爷的脸色,可这劲儿闹腾,但热闹也只是短短的几年,后来,这炕上就剩下明爷明奶两个人了。明奶一走,就剩下明爷了一个人了。白天还好,可以出去在田埂上走一圈,碰见个人,还能说几句话。尽管腿脚不那么灵便了,走几步就觉得气拉不上来了,但总比黑魆魆的夜压在头顶上好些。明爷觉得越来越长的夜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自己的胸口,让自己喘不过气来。
热炕以前是明奶煨的,现在是大儿媳安萍煨。明爷总嫌安萍煨的炕不好,要么太烫,要么就是温吞吞的,有几次,甚至是冰的,明爷早早拉开了被子捂着,睡觉的时候被筒里却还是冰的,只好自己拿了手电筒去到后院看,原来火没有点着,只好自己勾着腰,抱了把柴草重新点火。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到老了,反而要自己亲自干了,明爷对儿媳安萍渐渐有了不满。这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就这一件事情。明奶以前做好了饭,总是双手端着给明爷,等明爷接过碗,再把筷子递到明爷手里,等明爷开始吃了,才去端自己的碗。安萍给明爷端饭的时候总是把筷子放在碗上面,然后把碗放在明爷面前的桌子上就转身走了,有时候明爷还在门外吸水烟呢,安萍从厨房里端了碗直接到上房里,把碗放在桌子上就走了,出门的时候喊一身:爹,吃饭了!这是喂猫喂狗呢,还是打发要饭的?明爷心里越来越不舒服,想发脾气,骂人,嘴还没张开,安萍却陀螺一样早转到自己的屋里去了。明爷当大队书记的时候,那可真是暴脾气,眼里揉不得沙子,谁要是犯了错,明爷张嘴就骂,谁都不敢还嘴。人见了明爷都怯乎着呢。在家里,明奶和儿女们也怕明爷。现在真是老了啊,老了就在儿子媳妇手里活人了,这是最让明爷难过的。明爷再不顺眼也忍着不说了,儿子也就罢了,媳妇还隔着一层呢。当年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明爷就对安萍不是很满意,嫌她个子太矮了,说矮个子女人心眼儿多,但儿子看上了,明爷也就勉强同意了。结婚后儿子媳妇生活得还算挺安稳,很少听见他们小两口嚷仗打架闹过矛盾,明爷也就在心里渐渐接受了安萍。再说,也不在一起过日子,两个儿子都是单锅另灶自己过的,明爷和明奶谁跟前也不去,老两口自己过。六年前明奶走了以后,明爷也坚决不和儿子媳妇一起过,自己一个人做饭吃,但一个人的饭实在不好做,明爷以前又没有做过饭,自己做的饭,自己吃着也没滋没味的。有时候懒,就多下点面,连着吃几顿,这样对付了一段时间,明爷病倒了,脸都瘦成巴掌大了,灰白的头发没有一点光泽。
儿女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定让大儿子爱光和明爷生活在一起。明爷还死犟着不愿意。女儿爱玲说:养儿防老,你这个样子一个人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们做儿女的脸往哪里放呢?知道的说你喜欢清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养了三个白眼狼,你也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人家背后不知道怎么看你的笑话呢?明爷勉强同意了。
说是和爱光一家一起生活,但实际上经常在家的也就是明爷和媳妇安萍。以前明奶在世的时候婆媳之间二十几年了没有过磨牙拌嘴的摩擦,但也不热络,安萍性格温和,不多说话。虽然在一个院子里住着,也还相安无事,但不在一起生活不知道,在一起生活日子长了,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就让明爷心里不舒服,时间久了,就对安萍积聚了太多的不满。
后院里柴草满地都是,以前都是明奶打扫的,明爷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需要天天去做的活。明奶不在了以后,安萍从来不去扫,明爷看不下去了经常自己去打扫一下,安萍并不觉得,还是不扫。实在太乱的无法下脚了,才清理一次。洗衣服的时候,安萍总是把一大堆衣服往洗衣机里一塞就完事了,从来不把明爷的衣服被褥单另洗。明奶以前都用手洗的,尤其是明爷的衣服,要先洗,洗完了明爷的衣服再洗其他的,明爷的衣服还要和其他的衣服分开叠放。安萍不管这些,明爷也就不让她洗自己的衣服了。实在脏了就泡在盆里自己揉一把,或者等女儿爱玲来了再洗。镇上逢五赶集,每次赶集的时候,安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大早就去镇上逛,半后晌才回来,都四十六七快五十岁的人了,头发烫得羊毛一样弯曲,还染成黄色的,儿子爱光不在家,她收拾成那样给谁看呢?这几年,镇上有了烤饼馒头店,安萍就不自己发面蒸馍馍了,隔几天就去买一塑料袋回来。早饭的时候就熬小米汤吃买来的馒头,买来的馒头都是用了发酵粉和蓬发剂,哪有自己家里发面烙的好吃?明爷一点胃口也没有。以前明奶自己烙的饼子蒸的馒头,明爷虽然嘴里挑剔着,但一顿能吃好几个呢。闲下来的时候,安萍不知道收拾屋里,就爱约上几个女人去街上瞎逛,买回来一大堆衣服。今天一套,明天一套的换,安萍还爱穿红色的衣服——三十不挂红,四十不挂绿,明奶一辈子都没穿过一件红衣服,结婚的时候也只是穿了一件紫色阴丹布的花布衫。现在想起来,明爷觉得明奶这一辈子有点可怜,自己亏了明奶。明奶跟了自己一辈子,明爷没给她过好脸色,没穿过好的,更没吃过好的,说走就走了,哪怕有个病痛,让儿女侍候上几天,也让人有个心理准备啊……
等屋子里有了热气,天也渐渐亮了,明爷起身穿衣服。院子里已经有了动静,是安萍开门的声音。农闲的时候,爱光在城里给人装修房子,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孙子立伟去年考上了省城兰州的大学。孙女娇娇在城里上高中,两周回一次家。平时家里只有安萍和明爷两个人。明爷住在上房里,安萍在西面的厢房里。大大的院子中间是水泥砌成的花池。上房是坐南向北的,屋子里光线不太好。一年四季都有点阴,尤其明奶走了以后,空荡荡的屋子更显得阴冷,很早就得生炉子。隔壁的院子是小儿子爱国的,但明爷很少到小儿子的院子里去。明爷不喜欢小儿媳妇。
小儿子爱国是三岁那年发高烧吃错了药变成聋哑的。明爷心底里一直觉得对爱国有愧。三岁的爱国都已经会说话了,人特别聪明,明爷也偏爱爱国。但一场莫名奇妙的高烧,将聪明异常的爱国烧聋了,十聋九哑,原本已经学会了说话的爱国渐渐变成了哑巴——也不是哑,能发声,但不会说话,张口说话也是依依呀呀的,谁也听不懂,大家都叫他哑巴。虽然成了哑巴,但爱国的聪明没有被烧掉。学什么会什么,地里干活的农具,家里做饭的家什,那时候都是请工匠们来做的,爱国自己琢磨着,就鼓捣出来了。他会做扬场的木锨,会做捞面的笊篱,最让人惊叹的是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爱国,居然自己刻了一副拓印纸钱的模板。村里人都说是爱国太聪明了,连老天都嫉妒了,所以才烧坏了他的耳朵。明爷也在心里渐渐认可了这个说法,不然又能怎样呢?聪明归聪明,但总归是个哑巴,爱国到了二十五岁还没有说上个媳妇,明爷托人到处打听,才给爱国找了个媳妇,叫何艳,也是哑巴,是先天的聋哑。介绍的人说这丫头虽然聋哑,人很聪明,麻利得很,是个好劳力,针线茶饭都好,还爱干净,无论多忙多累,家里都要收拾得干干净净。娶进门,果然是介绍人说的那样,里里外外一把手,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像城里人一样,衣服被褥过几天就洗一次。明爷很满意,逢人就夸何艳。但没过两个月,何艳的肚子就凸出来了,很显然是怀孕已经五六个月了。这给了明爷当头一棒。明爷气冲冲去质问介绍人,但人家也不知道情况,总不能把人给退回去吧。儿子爱国什么也不知道,娶了媳妇之后脸上洋溢着快乐,干活也更有劲了。明爷心里却像吃了个苍蝇一样膈应。这可真是吃了哑巴亏,明爷心里窝了一口气。后来明爷打听到了,原来是何艳的一个姨夫做下的事情。那个姨夫还是公职人员呢,在乡上的派出所,穿一身威严的警服。何艳结婚的时候他还来送亲,喝得醉醺醺的,拉着明爷的手说姑娘就交给他们了。明爷当时还想,这个姨夫真是个好人啊,没想到竟是个畜生!这事不能再追究,媳妇何艳也是受害者——她受了欺负也说不出来啊!可明爷从此见不得何艳。三个月过后何艳生了个丫头,明爷没有正眼看过一眼,更不用说抱一抱了。等孩子刚满一岁,明爷就张罗着分了家,把爱国何艳分出去另过了,让他们住在西厢房里,另立锅灶,眼不见为净。明爷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几年后爱国又单另修了一院房搬出去了。后来何艳又生了孙子亮生,亮生耳聪目明,长得和爱国小时候一模一样,刚一岁就能叫爷爷了,明爷心里虽然疼孙子,但也很少去抱,很少领着亮生玩。何艳虽然先天聋哑,但不缺心眼,知道公公不喜欢自己,也就很少过来。只有年头节下,才过来这边的院子里帮着明奶做饭招呼人,有时候家里做了好吃的,也让亮生给爷爷奶奶端过来。平常十天半个月,也不进来一回。
明爷穿好了衣服,在炉子上坐了一壶水,就出了门,站在院子里的花池边上伸了伸胳膊——这胳膊腿真好像不是自己的了,硬撅撅的,伸也伸不直。安萍从后院出来,哐啷一声摔上门,满脸的着急,看见明爷就说:爹,你咋不关水龙头?你看看去,后院淹成啥样了?
明爷愣了一下,说:我关上了啊!昨天下午我关上的,怎么没关?
安萍没好气地说:那你自己看看去!
说着,嘴里还嘟囔着,跑到自己屋里去了,明爷也没有听清楚她说了什么。总归是埋怨的话吧,明爷想。
后院就在上房的后面,养着三头牛,还有十几只鸡,一条狗,最南面是大棚猪圈,养了六头猪。后院里给牛饮水、给猪饮水是从厨房里连接了一条皮管子出来,厨房就在上房的右手。明爷推开后院的门,就看到满院子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满院的柴草都冻到冰面上了,估计是淌了半夜的水。幸亏是初冬,要是在腊月里,水管子都该冻裂了,但这满院子的冰,也得几天好好收拾呢。这几天气温越来越低了,啥时候才能干呢?安萍不比何艳勤快,不经常打扫后院,后院里经常满是柴草,不像何艳的后院里,啥时候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一点,明爷对安萍最不满了。
昨天下午明爷去厨房里接水,停水了,明爷记得自己关了水龙头的。是安萍自己忘了吧?她是不是以为明爷真是老糊涂了?糊涂到连个水龙头也不记得关上?明爷心里窝了一团气,关了后院的门出来往上房里走,看见安萍站在院子里,拿着手机在给爱光打电话,说明爷把后院淹掉了。让他赶紧回来收拾。明爷听了心里更不是滋味。
明爷慢慢走回上房里,炉子上的水已经开了,滋滋滋冒着热气,屋子里已经很暖和了。明爷却没有倒水洗脸,索性脱了鞋,上炕睡下了。
儿子爱光回来已经是中午了,进了门先到了上房里,看明爷窝着被子躺着,就问是不是生病了?明爷说没有。爱光也没顾上多问,转身出门去了后院。
等爱光两口子收拾完了从后院出来,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安萍去厨房做饭,爱光来到上房里,明爷却不在屋里。屋里有点冷,炉子里的煤火快要灭了,爱光赶紧添了点煤。出来问安萍:爹不在屋里,去哪里了呢?
安萍正在和面,说:没看见他出去啊。可能是去外面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吧。
爱光出了门,在院子周围逛了一圈,没找到明爷。又来到隔壁爱国家里,爱国一家人正在吃饭,也没有明爷。爱国的女儿姗姗,也就是那个刚结婚五个月就生下来的丫头,已经二十岁了,在城里一个酒店里当服务员,最近有人来提亲,所以昨天刚回到家里,过几天要相亲呢。姗姗不聋不哑,对自己的哑巴爹娘好得很。对明爷也很好,她也知道明爷不喜欢自己,但每次回家来还是要给明爷买点蛋糕之类的吃的。姗姗在酒店里挣的钱从不乱花,都拿回家来交给爱国。爱国经常在人前竖起大拇指夸自己的姑娘呢。
从爱国家里出来,爱光朝全爷家走去。明爷肯定是去全爷家里了。来到全爷家,却没有人,连全爷也不在家。全奶正从后院煨了炕出来,脚步蹒跚,身体随着脚步左右摇摆着,看上去人又矮了许多。说全爷放羊去了,还没有回来。全奶一身的病,是个药罐罐。从四十几岁开始腿就疼,不到五十岁得了哮喘,一到冬天,咳嗽气喘,好几次上不来气差点没命了。后来又切除了胆囊,前年又被查出来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都说全奶可能没几年活了,儿子们也早早给她做好了寿材寿衣,谁知道全奶还好好的,先走掉的却是一辈子没有害过大病,平日里连头疼脑热也很少的明奶?看来真应了俗语说的“药罐罐不倒”。
全奶一见人,说不上几句话眼泪就止不住地流。看到爱光进来,她忙着让他进屋,又和爱光说起自己的腿,说儿子整天在镇上忙着挣钱不回家来;又说家里的一大群羊,几头牛,还有地里的活就是全爷一个人的;说全爷和自己命苦。又提起十七岁就跟人跑了的姑娘桂兰,说那个狼吃的,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这么多年也不回来看看爹娘,怎么那么狠心,连爹娘死了她也不回来看看吗?说话间,眼泪就顺着满脸的皱纹流淌,全奶不时拿袖子抹脸。全奶的两个姑娘,大的翠兰嫁得远,几个月才回娘家来一次,小的桂兰才十七岁就跟一个外地木匠跑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前些年,全奶全爷觉得丫头给自己丢了人,从来不在人跟前提起桂兰,全爷说就当是她死了,就当是自己养了个白眼狼。这几年,可能是人老了的缘故,全奶总是提起桂兰,先是狠狠地骂,骂完了又念叨说自己赶着死之前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上桂兰的面了。爱光也不好说什么,随便说几句安慰的话,刚要起身,院门响了,全爷吆着十几只羊回来了。看到爱光,全爷就说明爷已经回家去了。原来明爷找到全爷放羊的地上去了,和全爷喧了一个下午。
爱光出门的时候,全爷跟着送出来,对爱光说:娃子啊,人老了就变成老小孩了,心眼就小了。你爹一辈子性格刚强,受不得委屈,你和安萍多担待着点吧!
爱光回到家里,明爷已经上炕睡了。安萍做好了饭端过来,明爷说自己和全爷在地上放羊的时候已经吃了全爷带的饼子,饱着呢,不吃饭了。又说他累了,想早点睡。看明爷紧闭着双眼很疲倦的样子,爱光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和安萍吃了饭,也早早睡了。爱光只请了半天假,明天一早还要赶回去呢。
第二天早上,爱光出门的时候,明爷还没有起床。他光来到上房里,给明爷捅开了炉子,添了煤,说一声:爹,我走了!过两天活干完就回来了!明爷“嗯”了一声,没有起身。
等到天大亮了,明爷才起来穿衣服。出了上房门,看到安萍在西厢房的门前面晒蒜辫。看见明爷出门了,安萍赶紧去厨房端饭去了,明爷却径直穿过院子,出了街门,往西南边走去了。安萍端了碗出来,不见明爷,赶紧出了街门,明爷已经走了很远了。安萍不好再喊,就只好把碗端了回去,放在了炉子上。安萍早上特意熬了明爷爱吃的洋芋榛子汤,还捞了一碟酸白菜。明爷却看也没看,径自出门去了。这大清早的,他去哪里了呢?
明爷去了仁奶家里。
明爷兄弟三人,明爷排行老二,仁爷是老大,比明爷大十几岁,明爷的爹死得早,明爷全爷两兄弟的媳妇都是仁爷张罗着娶回家的。仁爷在十三年前就去世了。仁爷走的时候,七十三岁,仁奶和仁爷同岁,又活了十三年,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也是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上房里面,儿女们轮番侍候着。六年前明奶突然走了,仁奶听到消息老泪纵横,哭着骂老天糊涂了,怎么不把她收走,倒让比她岁数轻的明奶先走了。但人的生死怎么能由得自己决定?两年前,仁奶有点糊涂了,一天到晚呆呆的,眼神空洞,常常认不得人,嘴里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念叨的都是已经去世多年的人和过去的事情,有时候说仁爷就坐在上房的炕上抽水烟,说仁爷刚才给他说什么了,说她早已经死去多年的一个兄弟,穿一身毛蓝的新衣服来看他了,等等,听得人毛骨悚然。都说仁奶可能不行了,可仁奶倒比以前能吃饭了,以前从来不爱吃的东西也吃得津津有味,刚出锅的汤面也不觉得烫,大口大口的吞咽。给多少吃的,都不知道饱,吃了睡,睡醒了吃。清醒的时候却还记得日子,记得每一个儿女和十几个孙子的生日,提前几天就念叨着,但除了大儿子爱强的儿子勇生,仁奶的孙子们都不在跟前了。仁奶糊涂的时候,连儿子女儿也不认得,就知道吃饭。不管是谁,啥时候问她都说是没吃饭,饿了好几天了。爱强的媳妇刚刚给她喂了饭,碗还没收拾呢,进来人问她吃饭了吗,仁奶就撇着嘴要哭,说没吃。爱强的媳妇大声说:怎么没吃?我一天三顿端来的饭都填了炕洞了?倒到闸里了?仁奶就不再说话了,可怜巴巴地看着媳妇,脑子似乎是明白一些了。明爷过个十几天来看一次仁奶,陪她说一会儿话。说说以前的一些事情,仁奶见到有人来看自己就哭,眼泪顺着满脸的皱褶流,嘴撇得像小孩子一样,让人看了心酸。先前明奶在的时候,经常过来和仁奶拉拉家常,年轻的时候,妯娌之间也闹过是非吵过架的,到老了,反而亲得像姐妹一样了,都说先走的人是有福的,看来真是这样啊,明爷现在是深有体会了,一个人的日子,难熬啊。
仁奶的院子比明爷家里的还要大,这个曾经生活过二十几口人的院落现在就剩下大儿子爱强一家人了,曾经的热闹和喧闹再也找不到了,偌大的院子空了半边,显得空旷凄凉。明爷进了街门,看到仁奶的孙媳妇冬梅抱着一床棉絮要出门。说是要到镇上去重新弹一下,往小康楼上拿——一开春,爱强一家也要搬到村上的小康楼上去了,这个院子里就剩下仁奶一个人了!冬梅知道明爷来看仁奶,就把他让进了上房。上房里仁奶的二女儿玉秀正给仁奶梳头。玉秀今年也已经五十六岁了,两鬓间全是白发。玉秀他们兄妹八个人,仁奶谁跟前也没有去,就和仁爷两个人过。仁爷去世了之后,仁奶也坚持不跟着哪个儿子过,一个人守在上房里,说是怕仁爷回来了屋里没人,其实明爷知道明奶还是怕看儿子媳妇的脸色。前几年仁奶还能自己做饭,后来手脚不灵便了,就是跟前的两个媳妇谁先做好了端过来一碗,女儿们也大包小包地提了芝麻糊、方便面、牛奶蛋糕来。农忙的时候,仁奶自己也能吃上,饿不着。从两年前仁奶糊涂了之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儿女们聚在一起商量,在外面的儿子谁也不愿意把仁奶接到自己家里,最后决定每个人来伺候一周。仁奶大小便失禁,自己无知无觉,换洗很麻烦,时间长了,女儿们不说,媳妇们开始嫌弃,妯娌姑嫂之间为了伺候的时间长短闹了不少是非。守在跟前一个院子里的只有大儿子爱强一家,爱强也六十几岁了,弯腰驼背的,但还能支撑着下地干活。二儿子爱勇前些年单另修了一院房子搬出去了。在城里的两个儿媳起先也还能按时来侍奉着,以为不过就是几个月的事情,但一晃两年过去了,仁奶还是老样子,能吃能睡的,除了人糊涂着,啥毛病也没有。媳妇们就不愿意再来了,轮到他们侍候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给爱强,说自己有事走不开,让他帮忙照看,给他些钱也行,爱强能说什么。日久天长,爱强的媳妇也是满腹委屈,逢人就说自己的不满,骂妯娌不自觉,也骂婆婆仁奶老祸害。骂归骂,却还是得侍候,人家在外面,就你在跟前守着,你能眼睁睁看着不管?三姑六婆的,来看看仁奶,地里的农活再紧,也得放下来陪着,倒杯水做一顿饭招呼,就是其他儿子女儿来了,也一样少不了要给他们倒一杯水,陪着说半天话,都是做儿女的,凭什么侍候了他们的娘还要侍候他们?话传到其它儿子那里,他们也振振有辞,说爱强两口子不是东西,他们每次回来都大包小包地提着东西,爱强的媳妇还没个好脸色。爱强两口子侍候自己的娘还挣兄弟的钱,占了便宜还不知足。爱强一家人反而落了满身的不是。兄弟姊妹间闹得很不愉快。就差反目成仇了。
明爷进了上房,玉秀刚给仁奶换了干净衣裤,侍候仁奶吃东西呢,见明爷进来,连忙下了炕,给明爷倒水。明爷坐在了炕沿上。这也是满间炕,比明爷家里的还要大。炕角里两摞高高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炕中间靠墙的地方码着三摞枕头——一切还是仁爷活着的时候的样子,好像并没有过去十几年的光阴。仁爷就是在这间炕上病了一年多之后咽气的。这间炕,曾是多么热闹啊,仁爷的儿女多,孙子也多,逢年过节都回家来,这一间炕是睡不下的。仁爷仁奶生了十二个子女,活下了八个,男女各半。后来八个儿女又生了十九个孙子。是全村有名的大家大户。现在,儿孙们都相继飞走了,这个院落就像一棵冬天的大树,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树木不能抗拒严冬,人也不能避免衰老,可是,人老了,可真是难活啊……
从仁奶家出来,明爷觉得自己的腿一点劲都没有了。其实他昨天一天就没有吃饭,下午和全爷放羊,也没有吃全爷带去的饼子。路边的几颗白杨树光秃秃的,曾经茂盛浓密的树叶早已经落光了,也还有几片枯黄的叶子还孤零零地挂在枝头,在风中颤抖着。明爷想,人老了,就跟这枯黄衰败的树叶一样,总要落下枝头的,但什么时候落下来,却由不得自己,仁奶、还有自己,不都是寒冬了还留在枝头的枯叶吗?这样想着,明爷就越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了。
明爷走得很慢,心里有点凄凉。冬天的田地里光秃秃的,视野开阔,能看出去很远。远处的公里路上不时有车辆走过。路旁是村里新建的小康楼,村里好多人家都搬到小康楼上去了,和城里人一样住上了有暖气有卫生间的三室两厅的楼房。留下老人在老院子里守着牛羊牲畜。爱光也登记了一套房子,钥匙也拿到手了,一直搁着,没有去住。明爷嫌楼房不接地气,不愿意搬过去。爱光就一直没有装修。爱国的一院房子刚修好不长时间,是几年前设计的小康住宅的样式,很紧凑的小院,不比楼房差,就没有登记村上的小康楼。明爷来到了爱国的院子里,爱国不在家,哑媳妇何艳手里比划着,嘴里依呀着,明爷知道爱国是去镇上送菜去了。爱国两口子虽然是哑巴,但干活利索,又肯吃苦,庄稼种得细致,日子过得并不比别人差,前两年又在姐姐爱玲的帮助下,建了个蔬菜大棚,种反季节蔬菜,冬天也不闲着,能挣不少钱呢。爱国和镇上的几个酒店、饭馆、菜店都说好了,菜收下来就直接送过去。早上一家人起来铲韭菜,爱国这会子刚走。
明爷很少到爱国这边来,何艳有点诧异,以为明爷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赶紧忙着给明爷倒水拿馍馍,让明爷吃。何艳拿出来的饼子烙得金黄,是她自己发面做的,明爷闻见了面粉的香味,肚子里也咕噜咕噜地响起来,但明爷咽了口唾沫,忍着没吃,啥也没说出了门。
虽然没看见爱国,但明爷心尽了,明爷知道爱国的日子其实过得挺舒坦的。这些年,明爷其实一直就知道,何艳是个好媳妇。如果不是那件事情,何艳真是无可挑剔的。唉,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谁都不是光光鲜鲜的啊。
回到家,安萍不在,院子里静悄悄的。明爷进了上房,炉子边上放着他的花瓷碗,碗里是明爷爱吃的洋芋榛子汤,搁了很长时间,已经坨住了,上面结了一层皮。炉子烧得正旺,显然是安萍又添了煤。明爷动也没动一下碗筷,直接上了炕,拉开被子躺下了。
明爷这一躺下,可把安萍急坏了。早上安萍见明爷出了院门直接往南面走,就知道是去仁奶家里了。以为过一阵子就会回来的,也没在意。这几年来,明爷越来越像个小孩子了,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和安萍置气,几天不和安萍说话,经常跑出去和街东面的德爷喧谎,到了吃饭的时候也不知道回家,两个老汉都七十多岁了,靠在东墙跟,晒着太阳,一喧就是半天,也不知道喧些啥。安萍给明爷把饭留下,冬天的时候放在上房里的炉子上,夏天就放在厨房的灶台上。最不好弄的是春秋房里的炉子拆掉的时候,热饭很麻烦,还得重新生火。安萍热了几次饭,心里就不乐意了。明爷还嫌安萍让他吃剩饭了,两个人都是满腹委屈。爱光是个孝子,看见明爷不高兴,就对安萍没好脸色。两口子老为这个事情吵吵。爱光常说的话就是:我爹还能活几天了?安萍就不再说什么了。
两年前,德爷也走了,明爷这下可没处去了。全爷天天忙得没空,仁奶也糊涂了,明爷一个人进来出去没个说话的人,有时候安萍看着明爷脸上落寞的神情,心里也不是滋味,但安萍心底里也是委屈的,自己这些年也不容易,真是里外不是人,出力不讨好啊。
到了下午,明爷还是没有吃饭,安萍怎么说他也不起来,也不答言,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安萍想了想,就去叫全爷。全爷正在地上放羊呢,等下午把羊赶进了门,才过来。看明爷躺在炕上,也没说话,就在炕沿上坐下了,点了一支水烟抽起来,一袋烟抽完了,明爷还是不说话,全爷问:你这么睡着想干啥哩?
明爷还是不说话,眼泪却顺着眼角的皱纹往枕头上流,很快枕巾就湿了一片。
“唉——”又过了好久,明爷长长出了一口气,兄弟啊,我这样活着,还有啥意思呢?阎王爷咋不把我收走呢?
全爷看着明爷脸上的褶皱和顺着褶皱往下流的泪水,看着明爷花白的头发和苍白瘦小的脸,想起了明爷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的明爷可真是英俊潇洒,意气奋发,先被招工去了鞍钢,让人羡慕,后来从鞍钢回来又当了大队书记,工作雷厉风行,脾气火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大队里从干部到群众,没有一个不服明爷的。就连仁爷,他们的大哥,尽管像父亲一样给明爷娶了媳妇成了家,也常常被明爷训斥呢,谁能想到,老了的明爷也是这样的脆弱,难行?
全爷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把水烟锅子在炕沿上磕了几下,包好了,别在腰里。安萍已经给全爷说了事情的经过,全爷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全爷的两个儿媳妇还没给全爷端过一碗饭呢,两个人都在镇上开铺子,忙着挣钱,过年过节的也不回家,把家里的事情都撂给全爷,全爷又能说什么?安萍这样侍候着明爷,全爷觉得安萍是个好媳妇呢。这会子却也不能向着安萍说话,想了半天,全爷说:再不要胡闹了,娃子们都好着哩,你快起来吃饭吧!
明爷不再说话。全爷又坐在炕沿上劝了半天,明爷还是不说话,全爷也没治了,全爷本来就不善言辞,按明爷的话说全爷就是一个没嘴的葫芦。平时和明爷在一起也是明爷说得多,他只管听着。明爷说起理来,那可是三皇五帝张天子李霸王一套又一套的呢,经常被本家户族的请上去说理,调解家庭矛盾,婆媳纠纷。现在明爷这样,全爷可没法子给他说理,更没本事劝他起来吃饭。
听见全爷出了上房门,安萍一掀门帘也从她屋里出来了。全爷说:你给你姐打个电话吧。你爹听爱玲的话。
送走了全爷,安萍关好院门,又来到上房里给炉子里添了煤,封好了,才回到屋里给爱玲打了电话,说了原委。爱玲说明早上就赶过来。
爱玲是明爷的三个子女中最像明爷的,长相、性格、脾气,就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神态,和明爷就像是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一样,唯一的遗憾是爱玲是个丫头。明爷一直觉得儿子爱光的性格过于绵软内向,整天像个闷葫芦一样不多说话。小儿子爱国本来挺聪明的,却又成了聋哑,只有爱玲,从小就能说会道的,长大了为人处世也大方豪爽,有点男子气。明爷喜欢爱玲,也只有爱玲说的话,明爷能听得进去。
第二天一大早,爱玲就坐车赶过来了。爱玲今年也五十岁了,两鬓间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眼角也有点下垂,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年轻时候的爱玲可是真漂亮呢,和明爷一样的大眼睛双眼皮,两条辫子油黑,个子高挑,开口说话脸上就带了笑,很招人喜欢。明爷到县城里开三级干部会,认识了城门边上的一个大队书记,两个人很投脾气,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爱玲被那个大队书记介绍嫁给了他的侄子,嫁到了城门跟前,俗话说“离城三里,不算乡里”,爱玲变成了城里人,让周围的人羡慕了好长时间。但城门上毕竟不是城里,爱玲并没有和真正的城里人一样坐在阴凉房里上班。爱玲婆家也和娘家一样种地,不同的是城门跟前的地少,而且大部分都种蔬菜。爱玲并没有像娘家村里人羡慕的那样过上“清闲日子”,尤其是连着生了两个女儿之后,爱玲的日子更是忙碌而紧张了。那时候正是计划生育抓得最紧张的时候,城里人一对夫妻不管男女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相对宽松一些,也只能生两胎。爱玲第一胎生了女儿青儿,怀第二胎的时候就盼着生个儿子,怕万一又是个丫头,被乡上的计划生育工作组的人拉去结扎了,就偷偷找了个地方生下孩子,谁知道偏偏就又生了个丫头。爱玲性格要强,一定要生个儿子,在公婆面前争一口气,就和明爷商量,把女儿偷偷送到了娘家,让明奶偷偷养着,对外面就说是女儿生下来就糟掉了。明爷心疼女儿,心里也希望女儿能生个儿子,在婆家有地位,就把刚生下来的惠儿接到了自己家里让明奶喂养。三年之后爱玲又生下儿子杰杰,才去结了扎。爱玲家里地本来就少,再多养一个孩子,日子就过得很紧巴,孩子在明奶家里,明奶也是有儿子媳妇一大家人呢,爱玲每月都得给孩子买奶粉,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吃药打针都得花钱。明奶不说,爱玲也知道明奶手头没钱。明爷在村上当支书,清廉得很,家里柴米油盐的事情从不过问。爱玲每次回娘家来,大包小包地提很多东西,再给明奶留点钱。那几年,爱玲可没松活。后来,城门跟前的人都建起了大棚,种上了反季节蔬菜,爱玲的日子才渐渐好起来了,孩子都相继上学了,女婿也买了一辆卡车跑长途运输。家里的地还是爱玲一个人种着,经济虽然宽裕一些了,却还是忙得很,种大棚蔬菜,每天早上都得收草帘,晚上又得放下来保温,而且不像种庄稼,有农闲的时候,爱玲是一年四季都没个空闲。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更比别人忙。很少回娘家来。明奶意外去世,爱玲心里充满了愧疚,给自己做了个规定,无论再忙,一个月必须回来看明爷两次。明奶在世的时候,明爷一直是强悍的,说话做事还是以前当干部的时候那样利落,爱玲一点也不觉得父亲已经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明奶突然离世,明爷一下子就像霜打了的庄稼一样蔫了,脸色不再红润,腰也驼了,头发也白了一半,看上去灰突突的。最让爱玲看着心里难受的是明爷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不再像以前那样迷恋电视节目,饭量也一下减了,整个人好像缩水了一样瘦了下去,行动语言都有些呆滞了。爱玲每次回来,都觉得明爷又老了许多,看上去孤苦伶仃的,让人心里直发酸——但又有什么办法?自己家里一摊子也离不开人呢。幸亏有安萍,一天三顿能让明爷吃上个热饭,明爷有个头疼脑热的安萍就去村上的诊所买药。爱玲在心底里对安萍是感激的。
爱玲进了院门,安萍迎上来,满脸的着急,夹杂着委屈的神情。爱玲把手里提着的菜和肉递给安萍,让她忙去,就进了上房。明爷听见爱玲的声音,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赶紧迎出来。爱玲进了屋,看到明爷躺在炕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爱玲叫了一声爹,他也没答应。
爱玲见明爷这样僵着,就坐在了炕沿上,说:这天冷的,还没数九呢,就把人冻得手都伸不开了。
明爷不接话。
爱玲翻身又下了炕,在炉子跟前暖了暖手,揭开炉盖捅了捅炉火,又问:爹,这炉子还行吧?晚上睡下冷不冷?你不要把炉子封得太死了,多烧点煤不要紧,可别把你冻病了啊……
明爷还是不吭气。爱玲转身又坐在了炕沿上,揭开被子摸了摸炕,被窝里热乎乎的,又说:爹,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气我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家里忙得抹不开身呢?一大棚韭菜刚刚装了车,我找了三四个人铲了整整一天才铲完,今年的韭菜价格好,全都送到新疆去了,等今年忙完了,我把几个大棚租给别人,就闲一些了,我经常过来陪您!我来的时候带了些刚铲下来的韭菜,等会给你包饺子去……
看明爷还是不说话,爱玲又说:爹,还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呢,青儿考上“三支一扶”了,要分到学校里当老师呢!你的愿望青儿给你实现了!
明爷听了这话,睁开了眼睛,看了爱玲一眼:真的?
爱玲说:这大的事情,我还能哄你啊?
那太好了!青儿是明爷的第一个孙子,尽管是外孙女,但明爷还是很看重。青儿也讨人喜欢,一直很懂事,今年已经二十五了,大学毕业在家里待了三年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复习考试。按明爷的意思,女娃娃家,当个老师最好。青儿连着考了两次,这次终于考上了,是一件大喜事呢。明爷知道现在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呢,青儿自己争气,凭本事考上了,那为家里省了多少事啊!明爷的眼睛竟然有些湿润了,这孩子,没白疼她啊!
爱玲说:说的是啊,青儿本来也要来看你的,但这个考试的结果刚刚出来,还要等着准备面试呢。
明爷说:让丫头好好准备去,看我做什么?你也不用来看我了,赶紧回去吧,该干啥干啥去。
爱玲刚要张口接话,明爷又说:你快回去,七天之后,你再来,啥事都没有了!
爱玲没听来明爷的话,说:咋不来看,青儿说从小到大,就你最疼她呢!她还说这次考上“三支一扶”的人都要分配在偏远乡村的小学里实习,她希望能分到你们村上来呢,这样就可以天天陪你了……
爱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两行眼泪从明爷的眼角流了下来,滚落在了枕头上。爱玲鼻子一酸,眼睛里也有了泪,转过身悄悄擦了。明爷一辈子刚强,最见不得人淌眼泪,没想到人老了这眼泪竟由不得自己,遇到个大事小情的,话说不上几句,眼泪就来了。爱玲转过脸,看到明奶在墙上的相框里看着自己,也看着炕上躺着的明爷,一时间竟不知道再说啥了。爱玲有些生自己的气,本来是劝明爷来了,怎么反而被他连带着淌眼泪呢。
正踌躇间,门“吱呀”一声,安萍端着两个碗进来了,每个碗里卧着两个荷包蛋,放下碗转身出去,又端来了一盘葱花饼——知道爱玲爱吃这个,特意做的。安萍对爱玲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当初明爷看不上安萍,爱玲从中做了不少工作,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呢。进了这个家门之后,爱玲说话做事都公道,不偏不倚,安萍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姐姐。爱玲给安萍使了个眼色,安萍从炉子前面走过来,站在炕沿跟前,说:爹,起来吃饭吧!
明爷还是不吭气,又闭上了眼睛。
安萍看了看爱玲,又说:爹,是我不好,水龙头是我忘了关了!我一时着急,说话有点冲,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
明爷还是不说话,定定躺着。爱玲对安萍说:你忙去吧。爹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多大个事情啊?一家人有个啥原谅不原谅的!
爱玲等安萍出去了,拿起葱花饼咬了一口,说:娘家的饭就是好吃啊!我一年到头的,也只有到娘家来才能吃上一顿便宜饭啊。
见明爷又不接话了,爱玲干脆直说了: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安萍犯了啥了不起的大错了,你这样对人家?再说,就算安萍错了,她已经道歉了,你还想要咋样啊?
明爷听爱玲这样说,才开了口:你快快回去,不要再管我了,等七天之后你再来!
爱玲还是没明白,愣了一下:为啥七天之后再来?
明爷又不说话了。爱玲咽下一口葱花饼,忽然明白了明爷的话,常听人说一个人七天七夜不吃饭不喝水就会饿死,看来明爷这一次心里真搁了事啊!人都说老小孩老小孩,明爷真是耍小孩子脾气了。爱玲装没明白明爷的意思,说:那你继续缓着,我真走了,家里还一摊子事等着呢!青儿的奶奶腰疼病又犯了,得送去城里住院呢!
嘴里说着,一抹身就下了炕,端起炉子上的碗,我吃完了荷包蛋就走!以前妈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回来都给我打荷包蛋,这安萍还挺有心的,妈不在了,我每次回来,她都会给我打荷包蛋呢!爹,她给你也端来了,你也吃了再睡着吧!
明爷瓮声瓮气地说:不吃!
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横竖都是我不好,老没用,是你们的负担。不如早早死了干净!还吃啥呢?
爱玲一听这话,好容易止住的眼泪又下来了:好我的爹爹哟,你这是说的啥话?你这话让我们做儿女的咋受呢?谁说了你是负担了?
谁也没说,是我自己这样想的!我活着也没啥意思了!
咋就没意思了?是吃不上穿不上了,还是谁给你气受了?你说说咋就有意思了?爹,你也要替我们想想呢,我们一天忙得驴推磨一样,你就别添乱了!三个儿女中只有爱玲敢这样和明爷说话,明爷也不生爱玲的气,倒是爱光在明爷跟前一直毕恭毕敬的,说话总是小心翼翼,反而经常被明爷经常呵斥。说他没点豪气,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这两年,才渐渐说得少了。
明爷见爱玲流眼泪,话有点软了:丫头,不是我给你们添乱,有些事情,你不明白啊!
我不明白?我明白得很呢!爹,我知道你想啥哩,我也是给人当了二十几年的儿媳妇了,咋会不明白呢?说良心话,安萍算是老实人,好着哩!别的不说,就一天三顿,能给你端上碗热汤热饭的,我就从心底里感激人家哩!
爱玲从嫁过去就一直和公婆在一起生活,二十多年了,知道当一个好媳妇不是说两三句话的事情。爱玲的女婿是家里的长子,爱玲嫁过去的时候,一个小叔子和一个小姑子还在上中学。等到供他们都上了完大学在城里分了工作,小叔子又面临着娶媳妇买房子。爱玲刚嫁过去那几年,是公公婆婆当家,爱玲两口子忙了一年下来,收入基本上全都支援了小叔子了。爱玲想买件新衣服也得问公公伸手要钱,感觉心里委屈,却也不好说啥。后来公公去世了,婆婆身体也不好,常年腰疼,一天都不能离了药片片,家里家外都是爱玲一个人忙着,小叔子一家在城里上班,两三个月才回来一次,婆婆当成亲戚一样款待,每次来都要让爱玲杀鸡买肉好吃好喝的招待。那小叔子一家也安然享受,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也是儿子,也应该赡养老娘,这也就罢了。有时候,城里的儿媳妇来了,婆婆还嫌爱玲做的饭菜不丰盛,没有七碟子八碗地招待,言语间难免露出不满。都是儿媳妇,爱玲一日三餐地侍候着,反而尽被婆婆挑剔,城里的小婶子,两三个月打一个电话问侯一声,婆婆就高兴得人前人后的夸她孝顺懂事。时间久了,爱玲心里的委屈渐渐积攒,也就有了怨气。一个屋檐下住,一个锅里吃,日子久了,婆媳难免有言冲语撞,眉高眼低的磕碰,爱玲算是深深领会了以前奶奶说过的那句话,“远香近臭”。所以对安萍,爱玲不仅仅只听明爷的一面之辞,而是将心比心,多了一份理解和感激。
明爷说:照你这样说,全都是我的不是!全都是我不好!
爱玲还没张口,明爷又说:你明白得很!明白得很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安萍好得很,你们感激了就找上个供桌供起来!
爱玲擦了一把泪:爹呀,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也不是安萍就好得很,谁都是妈妈养下的,哪能没个缺点毛病呢?我们做小人的要尊敬孝敬老的,老的也要理解体谅小的呢!就说我吧,你觉得我好得很,我也觉得我好得很,但我婆婆也嫌我这不好那不好呢!
顿了一下,又说:你觉得我好得很,可我天天不在你身边,那还不是啥用不顶?
明爷不再说话,爱玲下了炕,往炉子里添了些煤,又说了一句:我再好,也不在你身边啊!
停了一会儿,见明爷还不说话,又接着说:爹,你也想想,在你身边天天为你生炉子煨炕的,一天三顿热饭热汤端给你的,是人家安萍呢!你常说安萍把碗礅到桌子上了,脸色不好了,她也不容易呢,进了我家的门二十年了,你就把她当成是自己的丫头行不?就好比是我给你使小性子了,说话冲撞了你了一个样,你跟自己的丫头计较啥呢?我倒是想天天把一碗热饭礅到你面前呢,能行么?
爱玲说完了,也不再看明爷,端起空碗去了灶房里。一会儿进来,看到明爷已经侧了身将自己的胳膊放在了头下面,知道明爷心里的疙瘩松动了,就笑着说:爹,为这么个事情你想不开,传出去也不怕坏了你的一世英名?快起来,我给你舀洗脸水去!
洗脸水端来了,明爷坐起了身,叹一口气,说:丫头,你说得对哩,理是这个理,但事情到了自己头上就总觉得气不顺呢,自从你妈丢下我走了,我觉得一个人的日子难活啊……
边说着,边洗完脸,接过了爱玲递过来的碗,碗里两个荷包蛋还温热呢,明爷的眼泪又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