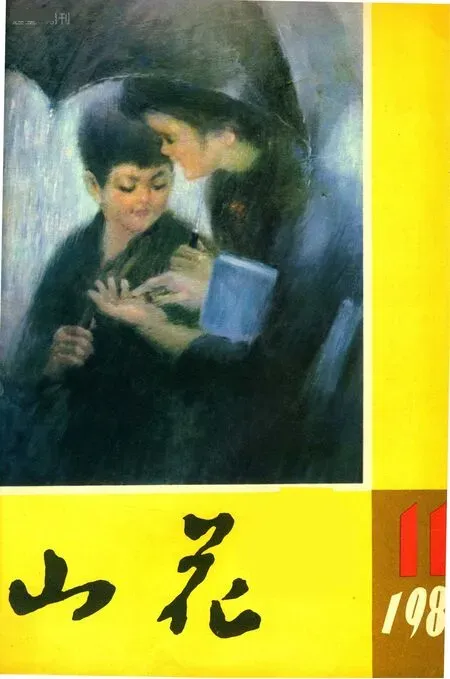牺牲者的挽歌:解读淮德拉、爱碧与蘩漪
2014-08-08
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以及曹禺的《雷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情节上,后两部剧目续写着家庭中继母与儿子之间的乱伦关系。对女性人物的细腻刻画和表现也是三部剧作的共同点。李健吾在谈到《雷雨》时,曾如是说:“容我乱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尤瑞彼得司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辣辛的Phe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1]实际上,三部剧中,无论是《希波吕托斯》中的淮德拉、《榆树下的欲望》中的爱碧,还是《雷雨》中的蘩漪都称不上是最主要人物,然而,她们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以及悲惨的命运却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反而将男主人公对比得黯然失色。不过,淮德拉、爱碧与蘩漪之间也是不尽相同的,也正是缘于此,在文学史上,她们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笔者认为,等待三位女性角色的命运之所以是悲情的,是由于她们各自充当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的牺牲品。具体而言,淮德拉是天神斗争的牺牲品;爱碧是欲望的牺牲品;而蘩漪是封建婚姻观念和男权主义思想的牺牲品。
一
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对家庭问题,尤其是女性问题非常关注。他所生活的年代,“婚姻制度逐渐固定为一夫一妻制,妇女开始被禁闭在闺阁中,一般不得参加公众活动,更说不上享有政治权利,地位已接近奴隶。”[2]无疑,《希波吕托斯》中也无不渗透着欧里庇得斯对女性的同情。
谈到淮德拉的悲剧,毫无疑问的是,天神之间的斗争是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她的悲剧还蕴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
首先,淮德拉与希波吕托斯的冤孽之情与她的家族史暗含玄机。在淮德拉之前,她的母亲帕西法厄与海里的一头公牛相爱,并与其产下一头名叫弥诺斯牛的怪物;而她的姐姐阿里阿德涅为忒修斯的缘故抛弃狄俄倪索斯,后又遭到忒修斯的舍弃。因而,淮德拉不禁认为,家族中由来已久的孽缘注定了自己终究在劫难逃,自己是无法逃脱命运的诅咒的。
其次,淮德拉的个性也是导致她最终走向悲剧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淮德拉给人的印象是极具主见、心思缜密并且暗藏心机。当突如其来的爱情打破生活的平静时,她依然能够坐怀不乱、头脑清晰、顾全大局。在恋情泄露之后,淮德拉虽然不免忐忑,她却超乎寻常,迅速地恢复了头脑的冷静。与此同时,淮德拉又是一名理智胜于情感,母性胜于感性的女人。在情感面前,她出于对名誉的考虑,对孩子的未来的考虑,毅然选择抛弃爱情,选择死亡。她决绝的话语让人不禁顿生敬畏,“我就为此非死不可,朋友们,好叫我不被人发觉辱没了我的丈夫和我所生的儿子,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行动和说话,兴旺起来,住在有光荣的雅典城,并不因为他们的母亲而有什么不名誉。”[3]不过,乳母有句话说得好:“凡人不应当对于生活太过求全。”[3]事实上,面对生活的风云变幻,人也无力事事求全。淮德拉也是如此。她虽然心思缜密、暗藏心机、聪明过人,但始终还是无法面面俱到,难免百密一疏。她的性格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帮助她谋划计策的同时,却也加速了她的毁灭。她的聪明、她的老到在这部剧作的语境中反倒成了她自掘坟墓的利器。因此,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凡事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所谓的好与坏必须依据具体的语境辩证地分析。
二
《榆树下的欲望》是奥尼尔创作于1924年的一部反映乱伦题材的悲剧作品。该剧的创作思想与奥尼尔的信仰危机和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奥尼尔对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说法笃信不疑。尼采的影响令奥尼尔丧失了对宗教的信心,陷入了信仰危机。再者,当时的美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陷入无尽的恐慌、迷茫与混乱之中,而传统的宗教信仰、家庭伦理与道德观念也不断受到颠倒黑白的社会价值理念的冲击。此外,奥尼尔也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通过对人的激情和性本能的分析,找出产生悲剧的根源”。[4]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家庭伦理、情欲与物欲自然而然成为了这部剧所探讨的核心内容。
郭继德先生在评价这部剧时如是说:“奥尼尔在《榆树下的欲望》(1924)中别出心裁地通过写乱伦题材,写财产欲的危害和造成的恶果,成功地创造了一种近乎亚里士多德式的怜悯和恐惧的悲剧氛围。”[4]那么,作为这场错综复杂的迷局之中的人物之一,爱碧无疑也是这种危害和恶果的受害者。她的悲剧是在贪婪的物欲和本能的情欲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命运多舛的生活使得爱碧对属于自己的东西如饥似渴。所以,为了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属于自己的财产,三十五岁,依然丰满、依然充满活力的爱碧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年过古稀的凯勃特。不过,在争夺田庄的道路上,伊本却成了她的绊脚石。面对这种情境,爱碧毫不退让。在对伊本劝诱无果的情况下,在凯勃特对伊本寄予希望的情况下,爱碧,犹如《希波吕托斯》中的淮德拉,不惜采取卑劣的手段,借助谎言挑拨凯勃特与伊本之间的关系等待坐收渔翁之利。不过,爱碧犯了与淮德拉相同的错误,聪明反被聪明误。她编造的谎言最终却将自己逼向了悲剧的悬崖。凯勃特将所谓的“实情”告诉伊本之后,伊本犹如遭受晴天霹雳一般如梦方醒,对爱碧恨之入骨。他甚至怀疑孩子就是爱碧争夺田庄的一枚棋子,爱碧跟自己所有的感情都是为争夺田庄而密谋的诡计。伊本过激的反应把爱碧逼得走投无路。为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爱碧无情地将嗷嗷待哺的婴儿亲手杀死。与此同时,她这种残忍的行为也将自己送上了通往悲情的不归路。显而易见,是爱碧的占有欲和为夺取田庄而自作聪明编下的谎言一步步将她推向悲剧的边缘;是伊本的占有欲使他丧失了理智,怀疑爱碧真挚的爱情,导致孩子的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的惩罚。
然而,爱碧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却不是物欲,而是无法抑制的自然本能——情欲。有评论认为,爱碧“为了证实自己对伊本的爱情的纯真而杀死了儿子,说明她的情欲(也可以说是要冲破清教主义思想束缚对真正爱情的渴求)超过了对农场的占有欲,导致了她个人和这个家庭的毁灭”。[4]是爱碧的情欲使她爱上了不该爱的伊本,是爱情使她不顾一切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又是爱情使伊本不惜生命与爱碧同舟共济、面对死亡。两人之间的爱情的确有感人至深之处,但恰恰也是爱情使两人走向毁灭和死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爱碧的悲剧是由于她对于真诚纯洁而又符合自然人性的爱情的追求所酿就的。纯洁的爱情使她真正成熟起来,可是爱情的悖论又酿成了她的悲剧人生。”[5]
三
《雷雨》是曹禺先生的处女作,创作于1933年。当时的曹禺深受易卜生戏剧中所宣扬的揭露社会阴暗面、主张人性解放、女性解放等思想的熏陶,以及希腊悲剧的影响。因而,通过对蘩漪的塑造,曹禺旨在批判封建思想的糟粕和男权主义思想对女性的压制。与淮德拉和爱碧相比,蘩漪的悲剧色彩毫不逊色。她的形象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蘩漪,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环境下遭受封建思想和男权思想迫害的一个女性群体。用曹禺本人的话说:“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生,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6]由此可见,蘩漪的悲剧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休戚相关的。笔者认为,酿成其悲剧的主要原因一是封建婚姻思想,二是男权主义思想。
蘩漪的悲剧是从嫁给周朴园之后开始的。周朴园虽然接受过西式教育,但是思想上仍然是旧社会的一套封建礼教,信守着旧式家庭的封建思想。因此,她与周朴园的婚姻之间并没有丝毫的爱情可言,更谈不上任何精神的慰藉。再者,蘩漪与周朴园之间有着巨大的年龄差别,显然,他是无法满足蘩漪的生理需求的。面对这种冷淡的婚姻生活,蘩漪唯有寻求其他的对象来释放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爱。可是周萍无法承受乱伦所带来的罪恶感,无法继续与蘩漪之间畸变的爱。因此,蘩漪终于忍无可忍,她无拘无束地发泄着内心的狂躁:“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指周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7]质言之,蘩漪的感情生活是不幸的,周朴园从来没有给过她爱,而周萍虽然给予过她一份真挚的爱,却又残酷地将这份爱夺了回去。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封建婚姻观念而酿成的。封建思想建构下的婚姻对于蘩漪而言,无异于一座活埋人的坟墓,憋得她透不过气来。
蘩漪走向悲剧结局的另一个罪魁祸首是男权主义思想。在周家这个旧式大家庭里,掌握绝对权力的无疑是周朴园。面对丈夫的男性霸权,虽然蘩漪也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皆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她不得不躺在楼上的房间里,终日郁郁寡欢,忍受着牢狱一般的生活。终于,在周朴园的精神摧残下,再加上儿子的死亡和周萍的饮弹自尽,蘩漪再也无法承受精神上的重负,真的变成了一个疯女人。值得注意的是,《雷雨》中有几处对蘩漪的描写让人不禁联想到《简·爱》中那个阁楼里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譬如:“忽然一片蓝森森的闪电,照见了蘩漪的惨白发死青的脸露在窗台上面。她像个死尸,任着一条条的雨水向散乱的头发上淋她。”[7]甄蕾认为,“虽然身处两个不同的时代,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度,然而伯莎·梅森和繁漪却如同一对孪生姐妹共同遭受着男权社会的压迫,她们都被男性压迫者污蔑为“疯子”,困兽般地被囚于男权世界的牢笼之中。”[8]两人的相似之处恰恰说明,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压制是她们悲剧人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体而言,淮德拉的悲剧是由天神之间的斗争和她的性格所决定的,她只是天神阿佛洛狄忒实施报复行动的一名小卒,她的牺牲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是值得同情的;爱碧之所以走向悲剧的结局是由于她内心日趋膨胀的物欲和情欲作祟,渴望占有田庄、渴望占有伊本、渴望拥有爱情是她最终走向死亡的症结所在;而蘩漪的悲惨命运是由封建婚姻观念和男性霸权所造成的,她不甘沉沦、勇于抗争、追求真爱的勇气也令人唏嘘不已,质言之,三个文本、三个角色的互文性一方面体现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财富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也将女性在男权世界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现得生动贴切。
[1]转引自吴正毅.于巧妙借鉴中凸显中国文化特色——《雷雨》与《希波吕托斯》、《费德尔》之比较[J].文教资料,2007(36):26.
[2]刘意青,罗经国,李赋宁主编.欧洲文学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5.
[3]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M].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4]郭继德.前言[A].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5,5,5.
[5]张小平.《榆树下的欲望》: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叛[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2(4):55.
[6]曹禺.雷雨·序[A].雷雨·日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74,374.
[7]曹禺.雷雨[A].雷雨·日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甄蕾.犹斗的“困兽”同声的反抗——评说伯莎·梅森和蘩漪[J].名作欣赏,2006(1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