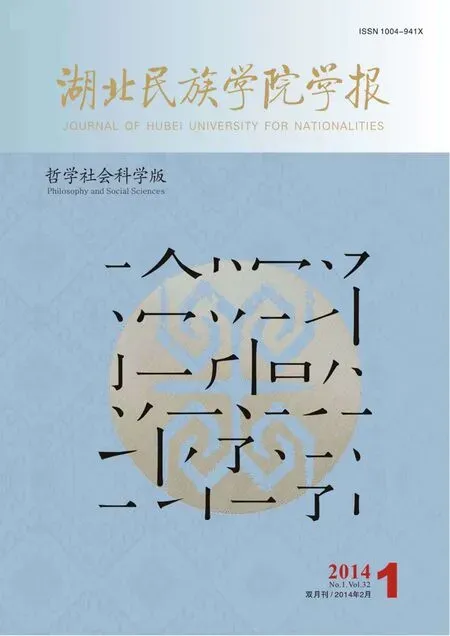“荣耀与辉度”:一种政治建构维度
——对《尼加拉》的再解读
2014-07-31张琪
张 琪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荣耀与辉度”:一种政治建构维度
——对《尼加拉》的再解读
张 琪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格尔兹的民族志《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通常作为阐释人类学的经典被解读,实际上本书的另一大启发在于通过“剧场国”概念,提出“荣耀与辉度”的政治建构维度,它不仅诠释国家权力和社会正义的诗性,并且是政治建构获得历史意义的真正来源。
格尔兹;尼加拉;巴厘;剧场国;仪典;政治学;国家理论
通常情况下,格尔兹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以下简称《尼加拉》)是作为“阐释人类学”的经典文本而被解读的,要么从文本和写作技巧方面来评议作者的阐释方法[1],要么是遵循同样的阐释主义,运用新的历史资料和田野调查修正格尔兹对十九世纪巴厘社会的研究结论[2]。《尼加拉》的阐释文风是格尔兹继“巴厘斗鸡游戏”之后最为系统和精到的表现。他认为经典人类学对社会学“社会事实”概念的借用生硬而肤浅;到了象征学派时期,社会事实关系的研究逐渐被象征关系的研究替代,但象征学派仍然将仪式看成一种一般化的、周期性的、韵律化的过程,而不得其真正寓意[3]20-42。格尔茨的这种批评换种说法其实就是:不论经典人类学还是象征学派,对文化(特别是宗教和仪式)的关注始终徘徊在“关系”和“结构”之间。只不过经典人类学将关系和机构囿于共时性的讨论中,而象征学派将关系和结构拓展到了历时性的维度上,这一点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为代表。因此,格尔兹提出研究文化的真正要领在于将文化看成“剧场”,运用类比、剧作分析、表演行动和情感张力的方法来揭露文化的本质,其中剧作分析包括“剧场与背景的关系”和“剧场的修辞”[3]20-42。“剧场国”之“剧场”,其首要指向的是格尔兹对文化的看法,亦即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剧场”,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是“剧场国”。
不过,十九世纪的巴厘有其特殊性,它的剧场属性不是泛化意义的“文化即剧场”,它在格尔兹的“剧场论”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尼加拉》出版时间为1980年,而上述的“文化即剧场”的论调出现在1983年出版的《地方性知识》中,从这个先后顺序可以看出,格尔兹的剧场论其实就得益于《尼加拉》的思考和写作。巴厘所表现出来的外化的、夸张的,可以跟真是戏剧相媲美的剧场性促使格尔兹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演剧机构,只不过尼加拉是表达上的一种极端,而其他类型文化的自我展演较温和而已。不过,越温和的剧场,也就是格尔兹所说的“默默无闻的背景”和“朴素平凡的场景”就越需要深描式的阐释,这是格尔兹的“微观主义”[4]27-28。于是,巴厘的特殊性将“剧场”引向另一个维度:不仅是泛化意义的“文化即剧场”,而且是的确与众不同的、高度表演性的、位于“剧场性之巅”的剧场。强大的“剧场性”渗透信仰、仪式和各种社会组织,并内化为人的精神气质,以致于国家层面也要以它来实现“政治”目的。因此,我们还应该将《尼加拉》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范本进行解读,格尔兹是想用尼加拉模式来构筑一种全新的“国家理论”,这一点在以往并没有得到重视。
一、“何为戏剧”与“为何戏剧”
格尔兹在开篇指出,尼加拉是前殖民时代印尼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尼加拉模式的完整性就是印尼历史的中心性。尼加拉需要放置在“尼加拉-德萨”*这两个词都是梵文借词。历史上的东南亚国家有一个漫长的印度化过程,从公元前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零星接触到公园2世纪首批印度化国家的建立,一直持续到公元15世纪满者伯夷王国的灭亡。对这段历史的粗略了解有助于理解巴厘岛的神话和种姓制度。参见(法)赛代斯.蔡华等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这对二元对立的概念中来理解,在巴厘文化中表示“宫殿-乡村”、“首都-地区”、“国家-地方”等概念的对立。在“尼加拉-德萨”这种文化构型上,巴厘的政治本质是展示性的,它从未走向专制和集权化,在统治方面显得淡漠且犹豫,它走向的是排场、庆典和狂迷性的公共戏剧,它并非要制造什么政治效果,它们本身就是结果和目的[5]12。
理解巴厘政治的戏剧化要从“典范中心观”入手,它是从印度教和印度文化中继承而来的,这是隐藏在戏剧性背后的一套关于主权本质和根基的观念。在典范中心观中,王室-首都是“印度诸神的永恒世界”这个超自然秩序的典范再现,国家分裂是世界从典范开始“衰降”的过程。巴厘人力图通过对神话中辉煌时代的再现,特别是满者伯夷帝国秩序的遵循、模仿和展示来维系自身对于整体国家的想象,对整合的而非四分五裂的世界的想象,对于秩序重建的想象。
国家越是分裂,就越需要展演性、仪式性的典范作用,典范中心的领导其雄心越大,就越依赖更大的联盟,王国的结构就越脆弱,这又反过来促使他们更加虚张声势,举行更辉煌的仪式,结构的分裂与典范的展演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怪圈。在这种模式中,权力越高,展演成分越大。但这种权力仅仅是象征性权力,而非实际操纵国家政治、军事和财政的权力。因为在分裂过程中,实权已经落到了不断分裂的各等级的小王国中。政治意义上的分裂与象征意义上的整合,二者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维系这种平衡的是背后的一套信仰体系,也就是印度式的宇宙观,包括:时间的起始(开始于尼加拉)、对空间的看法(王室-首都-国家庙宇与诸神体系的结构对应)、人观(即人的由来和本质,从神到人的衰降)和社会观(巴厘国的起源、对典范的遵从)。
二、“戏剧性”的表达
巴厘的戏剧化政治在日常生活中有诸多表达机制,主要存在于尼加拉和德萨的内部组织形式、运作方式以及二者的关联中。
(一)尼加拉的组织形式
首先是种姓制度。种姓间的主要关系是高等级婆罗门和低等级首陀罗之间的被杜蒙称为“矛盾涵盖”的一种关系*矛盾涵盖的意思是:关系项A-B,既是对立关系,又是涵盖关系,“A涵盖B”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A代表A-B这个整体。依据这种说法,参见(法)杜蒙.王志明译.阶序人[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印度教文化中神性阶层的婆罗门与巴厘世界的道德、制度、宇宙观的联系比首陀罗要紧密,观念上更具备合法性,衰降而来的其他种姓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涵盖在婆罗门之下。婆罗门可能成为君主、国王,统辖其他种姓,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并非实权拥有者,掌握实权的可能是与之对立的首陀罗。总结起来便是首陀罗靠实际权力确立权威,而缺乏道德支撑;婆罗门有天生的道德优势,但却掌握不了权力;中间种姓可以游走于两端。
其次是上层阶级的亲属制度。特点有三:一是实行基于父系继嗣的内婚制;二是家系群体只在内部分化,新群体在经济协作和仪式操作上与原群体不完全分割,它的权威、道德与宗教信仰的合法性仍然依附于父系家族的全体家族成员,格尔茨把它叫做“准宗族”制度[5]30;三是分化群体间充满冲突和利益斗争,但靠家族力量来整合,家族越大越分化,结构越脆弱,家族的整合作用就越明显,此乃家族内部结构的动态模式。
然后是庇护关系。尼加拉的庇护关系分为三层:第一层,政治型庇护,包括种姓内部的各层次群体之间的庇护和因越级婚姻而建立的种姓庇护,它们是宗派斗争和种姓对立之上的整合。第二层,宗教性庇护,这一点其实就是婆罗门与低种姓的矛盾涵盖关系。婆罗门掌握着道德权威、精神权威、宗教权威,神圣祭司这类精神与宗教的核心人物就出自婆罗门,但他们在实权政治上却并不占优势,双方互不信任但又相互需要。第三层,经济庇护,主要指华人、穆斯林等从事经济贸易的群体从种姓群体那里获得经商贸易的权利,同时用金钱回报。
最后是王国的结盟。在各个地方盘踞制霸的家族王国为礼仪、庆典而结成联盟,这是文化与象征目的而非社会目的的结盟。结盟协议的功能仅仅是观念性的,因为其中的合作项目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涉及盟国自身利益的联合军事行动、建立物资同盟等都不在其内。协议效果的保障靠大家对习惯法的共同遵守,而不是现代意义上有法律保护的真正契约。众协议当事人在立约者,即克隆孔君主的见证下签订协议公约,克隆孔君主其实不过是一个证明人、使节的角色,他在各地方性君主的眼中并无实际分量。
(二)德萨的组织形式
第一类组织形式是村庄。村庄主要负责的事务有建造谷仓、安全巡逻、判决离婚等,总结起来就是主持公共生活。村庄中生活的人很好地体现了市民性,但这里的市民性并非世俗性,也不是都市性的意思,它表示一种对公共生活的追求,对公共秩序、良好的互助关系、道德调整、法律控制的追求。村庄是纯粹的执行机构,搬演政府的权力而不操纵权力。
第二类是灌溉会社。村庄组织人们的日常互动,灌溉会社则是将土地、劳动力、水和农业技术进行组织的生产机制。比照灌溉渠主流和支流的层级,设立多层次的灌溉会社负责相应的水利设施调度。每个层次的灌溉会社都有一套相应的权力制度、法律制度(主要是民间法、习惯法、乡规乡约和集体劳作的口头契约)和仪式制度。围绕灌溉会社,权力、经济、法律、信仰、仪式全都交织在一起,灌溉会社制度具有了相当高度的组织性、法治性以及科层性,所以格尔茨称其为“水权金字塔”[5]84。但越高层次的灌溉组织,其真正施加给水利建设、管理和生产的力量越来越少,最高层次灌溉会社仅仅负责仪式以及基于共同道德的关系调整。
第三类是庙会。这里的庙会是一种仪式组织而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民间信仰活动。庙会所占据的空间可以用风俗村落来形容,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人们共享一套神圣信仰和道德基础,其实就是一个信仰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这些庙会体现和界定着地方社会的整体秩序。
(三)连接尼加拉与德萨
尼加拉和德萨的关联是靠Perbekel政治人体系,其中包括四种政治人:君主(特定领土上的,不是典范中心的最高君主)、代理人、庶民和依附者,他们依次对上一等级人负责。但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模式,不是每一层级都嵌套在同一地域范围中,权力大小也不体现为管辖范围的大小。例如代理人所管理的庶民交叉分散各地,君主的属民也不集中,可能遍布任何地方;土地的拥有者既是庶民也是君主,拥有政治权力不必然意味就能获取大规模的农业财富;佃户对土地的租种权和继承权与这块土地在不同君主间流转不相干。可以说,政治权威结构、地域结构、生产结构、土地租佃结构并不存在一致性。越上层的政治人,对土地、耕种、生产越没有实际的接触和操作,尼加拉的政治权威对德萨的土地经济所施加的影响微乎其微。
三、提出“剧场国”
格尔兹从神话讲到种姓,从亲属制度讲到群体间的庇护、结盟,从灌溉会社的多层体系讲到政治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作为“总体性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实则有着精妙的同构性,见表1。
很明显,这六个方面具备相同的结构特征:即越往上,权力越小,而文化意味越强,对国家的实际操纵越弱,负责仪典、展演,在荣耀、集体欢腾和群体审美的基础上建构权威,满足对秩序的想象;越往下,权力越大,文化意味越弱,对国家的实际操纵越强,负责公共生活、经济生产,在分配、劳动力动员、资料管理、司法审判等各个领域中展现自己的权威所在。巴厘存在于这种向心与离心的背反中,文化是至上而下,审美递减,权力是自下而上,实务递减。十九世纪的巴厘就是这样一种在总体上呈现辉煌与庆典的国家,靠辉煌与庆典的剧场氛围来维系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是“巴厘剧场国”。在这里,格尔兹再次用有关巴厘国家庆典、火葬和宫廷仪式的详实材料加强展示剧场性,我们从中看到庆典仪式的象征内涵,以及国家为了营造辉煌,是如何不遗余力地进行夸示和炫耀。

表1
至此,格尔兹终于提出了“剧场国”的概念。然而这个概念不仅仅在于呈现一个另类的民族志文本,它还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普理查德的《努尔人》一向都是被认作是政治人类学的先驱作品,但从其文本和理论诉求来看,普理查德只是提供了一种人类学理解“非国家社会”政治的视角,他对“社会何以可能”的关心甚于对政治理论的关心[6]。后来利奇写作《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普理查德等人的静态社会观提出挑战,并建立了一种基于理想型建构的政治“钟摆模式”[7]。无论是普理查德还是利奇,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只能叫做人类学的政治研究,而没有野心与人类学之外的主流政治理论进行对话,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打算用人类学方法建立任何政治学理论。到了格尔兹的《尼加拉》,他力图与人类学以外的政治学进行对话,用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格尔兹的“尼加拉人类学”是一种政治学,这是一条观照更为远大、更富野心的人类学进路,试图实践人类学对现实权力世界提出见解、质疑与“人本主义”改造的承诺。
四、荣耀与辉度
格尔兹总结了四种前人所建构的传统政治学意义中的“国家理论”[5]147-148。第一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霍布斯将国家视为庞然巨兽,国家,特别是宗教统治之下的国家会吞噬个体。第二种是“精英论”。右派帕累托主义和左派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国家是被精英掌控的阶级对阶级的统辖。只不过在前者那里,精英论调是他们所推崇的,而在后者看来,精英论是应该被废除的,它是榨取非精英群体劳动剩余价值的借口。第三种是“民粹主义”,其主张国家为全民所有,是共同体的一种衍生,而非政治人的特权土壤。最后一种是“政治多元主义”,其主张国家不是单一的权力来源,各种联络感情的、宗教的和职业的团体都是平等的权力主体,从而形成一种权力多中心现象,而民族国家不过是众多团体之一。
格尔兹的主要批评是,以前做政治研究的人都已经忘记从词源学上寻找国家的涵义。他发现,国家这个词除了地位-等级、治理-国家技术的含义之外,本来就有荣耀和辉度的含义[5]145。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无非就是有关地位、等级、治理和国家的话题,它们同时指向两个关键词:“权力”和“理性”。不可否认,政治需要权力和理性,但只有权力和理性的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社会内部各种关系、各种观念和信仰相容,对一个实体国家来说,又在多大范围内能保障政治之下的法制、行政、经济、教育、公共福利在整体的运作上是逻辑自洽的,这是个问题。“荣耀和辉度”的国家含义表面上看是形而上的,但实际上它承认国家作为全民整体的代表,推崇对国家的认同和信任,追求个体对整体社会的信仰与恒定支持。国家一旦拥有荣耀与辉度,正如十九世纪的巴厘国,即使走向分崩离析,即使遭遇殖民霸权,它仍旧能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给内部的人以安慰和希望,给外来者以震慑。荣耀和辉度的国家必然与展演、剧场、仪式相关,所以它是直接的、激情的,从而也最能反映本质。
格尔兹回溯前人国家理论时,有关仪式在国家中的功能部分是他自己的推导,而相较于这些国家理论,荣耀与辉度之国中的仪式则应该有完全不同的作用,虽然格尔兹并没有说明,见表2。
五、另一种政治建构
可以说,前人的四种国家理论中,国家的尊严都来自于特殊的手段,如格尔兹所说:“国家的尊严性部分的功能就在于迎合实效性部分”[5]146。需要指出的是,格尔兹并不否认国家和王权需要实效性的统治,并非拿地位和权力不当回事。在《地方性知识》中,格尔兹也表示,借助于神圣性,地位得以彰显和稳固,权力得到信奉和景仰[3]159-197。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巴厘国中的“地位”不是手段、伎俩或者算计的结果,而是一种辉煌,是有关权力的诗学,而非权力的构造术[5]148。巴厘这个“国家”是通过建构神灵信仰,神灵信仰再建构王权实现的,是观念世界向实体世界衍生的产物,而不是靠国家军事力量与各种法律、规范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的军事力量意味着恐吓,各种法律和规范则要求划清利益边界,对分配和持有进行干预,这让社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有关“正义”和“公正”的大讨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康德,从边沁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再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和诺奇克(Robert Nozick),缺乏“荣耀与辉度”的国家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巴厘剧场国解决了国家层面的“正义论”问题,制度化的仪式和典礼成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荣耀和辉度成为一种诗性的正义,在其中,全民共担社会责任、共铸国家精神、共享历史财富。

表2
另外需要注意到,格尔兹在《尼加拉》中还尝试提出一种不一样的历史的书写方法。这是一种累进式的,能体验到连续时间流的方法,对比编年体的阶段叙事,它更能展示历史的连续性,而非让人困惑于历史究竟是因果关联的,还是一代代之间断裂的,还是在不断地循环。格尔兹所采纳的这种见解受到他在书中开篇所提到的“科林武德”的影响。科林武德认为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是“心灵”,而非能够进行统计和归纳的自然事件,历史研究的本职工作就是要深入到他们正在研究其行动的行动者们的思想里面去,而非只满足于决定这些行动的外部情况[8]319-320。格尔兹认为欲达此目的,依赖于能否建构一种有效描述社会文化进程的模式[5]3-9,格尔兹在巴厘的历史中找到的模式是“尼加拉-德萨”模式,其文化心理层面的表现就是荣耀与辉度的“剧场国”。因此,国家仪典性的一面,亦即象征、信仰和情感的总体才是真正让历史具备连续性的因素。如果历史不是史学家的事件集合,而是一个团体或一个时代的集体心灵[8]309,那么“荣耀与辉度”才是政治建构获得历史意义的真正源泉。
最后还得明确,格尔兹无意推翻其他类型的国家理论,因为“剧场国”不是悬壶济世的良方,“荣耀与辉度”也阻碍不了民众对社会现实的知觉。巴厘国的剧场性和它的分裂性是硬币的两面,甚至可以说,巴厘的剧场性是满足分裂性所需的产物。因此有人批评说“荣耀与辉度”仅仅是文化特例,它只适用于东南亚及其印度教传统,格尔兹对传统政治理论的挑战作用甚微[9]。但无可否认的是,格尔兹提供了一种看待国家的视角,使人明确了建构政治的多重维度和多种可能的路径。当代国家的治理必然是程序性和技术性的,但如果忽略掉甚至抹杀掉表达交融、情感的神性和仪典性的一面,则可能在维系稳定和寻求发展的过程中四处碰壁。
[1] 李昕.《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文化的文本式阐释的一个范例[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114-118.
[2] Graeme MacRae,Negara Ubud.The Theatre-state in Twenty-first-century Bali[J].History and Anthropology,2005(4):393-413.
[3]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 (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5] (美)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M].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 (英)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 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7] (英)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 [M]. 杨春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 (英)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 David N,Gellner,Review Article.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J].South Asia Research,1983(3):135-140.
责任编辑:毛正天
2013-11-15
张琪(1987- ),男,重庆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信仰、亲属制度。
D06
A
1004-941(2014)01-01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