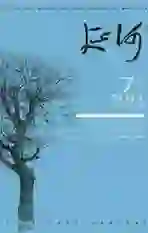农具之锈
2014-07-25李亮
李亮
我要说的不仅是铁,还包括木头和一些植物的藤蔓,以及被这些铁、木头及藤蔓压损的骨骼。
红嘴鸦和野雉鸡消失了十几年之后才又逐渐出现,在这个逐渐递减递增的过程中,高原上的植物们像火焰临风,即将熄灭下去却又重新熊熊燃烧起来。这种燃烧带着一种收复的意味漫过山坡,漫过村庄边缘整齐的庄稼地。当这绿色之火同样蔓延过祖先的坟头时,他们就要彻底被烧成灰烬与黄土混合在一起了——就像他们从未到达和在高原上生息过。
深邃的绿色再次像祖先们未到此地之前那般严密地包裹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高原上犹如童话或者神迹再现。于是,曾经是鸟儿们的天空和树枝被重新还给鸟儿,曾经是动物们的灌木丛和领地被重新交还给动物。绿色纵情舔舐着高原上每个发黄易燃如旧画稿般的古老村庄。对于植被曾一度稀少的黄土高原,这本该是充满生机和欢悦之情的燃烧,但我们的心却为何这般荒凉。
农具们在角落一放就是好多年。有的在某些墙角,有的在某些仓窑的杂物堆里。除了偶尔透过窗棂或双扇木门缝隙钻进来的阳光和阳光中的浮尘拜访它们之外,再没有眼光一遍遍洗刷出这些农具耀眼的光芒,再没有坚厚糙砺的手掌打磨出它们光滑映人的包浆,再没有呼吸沿着曾经年轻的肩胛骨或臂膀传递给这些铁并使它们也有了体温,也再没有宛若诗经中记载歌唱的那些人类与自然通过农具而交流出的空灵之音。这些农具如今多数已哑了喉咙,熄了目光,再不轻易被碰触。
数千年来或者更久远的时光中,整个北方大地上,武器与农具在人们手中轮番更替。后来,当马蹄踏起的烟尘终于逐渐沉淀平息下去,一部分人依然选择在马背上生活,他们扬起的牧鞭啪啪作响,清晰地界定出了游牧与农耕生活的界限。另有一部分人则终于扛起了犁铧,脚步尚带着一丝悲怆走向了连绵不绝的山峦。但是他们的一部分灵魂还是始终属于游牧生活的,于是,世人眼中的黄土高原便往往离不开一群散落在苍茫中的羊子和一个孤独的牧羊人。牧羊人或者静默着抽一袋旱烟,或者扯着嗓子朝着更远处的大山和天空吼两句信天游,像是宣泄离开马背却重新被大山囚禁的困顿,或是一种对血液深处仍保留着的辽阔的回应。
铁首先以其深沉、坚毅和冰冷成为制造农具的元素。这种金属向来有着矛盾的个性。它可以成为生产生活中看似最多情的农具,多情到土地的一垄一行都由它来照料和铺垫;它却也可以是战场上最无情的枪头,毫不留情地完结一切弱者的生命。这种多情和无情多像那些让女人们迷恋的英雄男性特质。
由生铁打造的铧对最初在黄土高原定居的人们而言意义非凡。它从远古时期的某一处土壤开始,被时光之手稳稳地扶着,不疾不徐,一路犁出农耕文明的诗行。终于,铧头反射的光芒也照亮了第一批在黄土高原上定居的人们的汗光。这种照亮甚至是一种点燃,一种召唤。于是,在垦荒为田的信念之中,每一页犁铧后都紧随着农人的脚步和蓬勃而出的庄稼。
无法想象在纯手工业时代,打造一页铁铧需要多久时间和多烈的火候,以及多么坚实的臂膊和锋利的眼神。在专业打铧人的注视中,一页完成了的铧是具有情感的。它的边缘即将被植物和土壤的气息所渗透,它的身体即将映照农人们的身影。铧的内心注定是温柔敦厚和生动迷人的。
但铧本身的阳性特质并未因此而降低半分,它们沉稳、坚固、锋利,在泥土的打磨中愈发光华灿灿。这种光华如太阳一般亮丝缕缕,召唤农人们每个春天抖擞精神,召唤一切适时的庄稼列队等候。由耩和铧组合起来的犁铧分明是能与地母交欢的充满力量的阳性,它们所耕耘犁出的土地上,无数种子一次又一次被播撒。
黄土高原上的巫师们或许会责备这种对犁铧充满生殖繁衍意味的表述。在高原深处,每一寸土地在人们的眼里都有神性,不合时宜的掏挖或修建都有可能冲撞了土气,冒犯到土地中的神灵,一些或大或小的惩戒便随即降临。此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由巫师作为媒介来询问神灵,当得知确切原委后,“安神谢土”的宗教仪式就会在院落中展开。陕北人讲究生铁可以辟邪,而“耩”不知何故又与“姜太公”同名,每当举行这样的仪式,人们便取陕北古文化中“姜太公所到之处,百无禁忌”之意,一页犁过地的铧便会和耩身一起被端正地栽到这户人家的窑洞上方,就像一只光芒四射的箭头指向天空。这个类三角形如图腾一般稳坐在大山深处和陕北人内心高处,镇邪避灾,沟通着天、地、人之间的信息和情感。
相比之下,犁铧像是统帅,其他农具的气场要小一些。但它们同样不可或缺,就像每个季节篇章中的小标题一般,各有使命,各司其职,有着开启和总结的功能。
镢头看起来诚实而稳重。越揣摩越觉得它像陕北人的脾性,一旦决定对谁好了,那便是直掏心窝的真诚和情意,正如下镢那一瞬间的力度。
镢头被农人们反复抡起又掏下,重复的动作像是直尺上的刻度般富有规律,而每个刻度都包含了准确的丈量与力度。春日的地皮被瞬间切开并翻转,土壤就在这一掏一翻间像刚刚新生一般蓬松起来。通过断裂的界面,农人能清晰地判断这一片土地上积攒了几分雨水,渗透了几分霜雪。于是,在某处犁牛和犁铧到不了的地方,便逐渐出现了一小片补丁般色泽湿润的地面。这样小片的地一般都用来种洋芋。此时的老镢成了绣花针,一针一针细细纳过去,每一个针脚都随后会长出葱茏的洋芋植株,它们会开花结果,并把根茎严密地藏起来,等到秋季的土地再一次被翻开时,交还给农人们一个个沉甸甸的惊喜。
但一个人肩扛镢头走向山间的画面是孤独的。那样雄浑连绵的大山,那样多而深狭的山沟,一个人走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这时,肩膀上的老镢头就是唯一的伴儿。它不是那么沉,也不是那么轻,通过肩膀上那个最舒适的支撑点,老镢头感知到了人的呼吸与思想,人也知道了自己此刻并不是孤独的。这种相依相伴没有任何喧嚣华丽的形式,却是那样温情脉脉与真实。
铁锨就像老一辈的村支书们一样平实可靠。一般的家户至少都会有四五把,它们筑墙打坝,填补坑洼,不怕累不怕脏,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出现。且随时会应需单独出战或组成一支小分队,可以说是最有兵士风范的农具。
在过去的陕北村庄里,新窑洞打成并圈好自家院子的领地后,便要用打窑时攒出的黄土筑出院墙。一个没有围墙的院落就等于是一座城少了城墙,有种风吹雨打的飘零感。院墙不仅划定界限,还可适当地保护隐私。打墙时,随着设定好宽度的四根或六根木椽被放置和固定好,铁锨便开始把黄土不断铲进木椽间留出的空间,并用力拍击使之固定成形。靠着铁锨们宽厚的身板,有力的臂膊和闪亮的眼神,一堵堵坚实挺拔的土墙便逐渐随着木椽的抬高而拔地而起,最终会连绵包拢起一个个单元格似的家庭。此外,在土墙围拢起的院子中还要规划出猪圈驴圈牛棚鸡窝,再留出一块小菜园种点西红柿黄瓜和豆角,在这些过程中,几乎每个步骤都离不了铁锨,它们跟随着主人忙前忙后在各个辖区,修整铺垫出家园应有的稳妥和平展。
锄头更像善于休整草木的资深园丁,颈上那个细弯儿使它看起来用起来更加灵巧。它在绿色的田间左右开弓,翻飞不停,杂草就像是污垢一样被麻利地清除掉。如何避开庄稼,如何辨别可以夺走养分的野草——在锄刃与土壤接触的那一刹那,就要像熟知交通规则一般,锄刃该怎么走,怎么绕,每一个动作用多大力道,每一个动作持续几秒。好的农人早已使锄头本身有了眼睛。
锄地是保证收成必不可少的步骤和任务,有勤快的农人们一个夏季会锄三四次。大自然的竞争法则充溢在每个环节和角落,人们要做的就是默默遵守。所以,锄地更像是一场场盛会之前的反复准备与打扫,农人们如同擦拭一件件宝贵的器皿 一丝不苟地对待。而这样的陕北夏季虽然曝晒,但绝不闷热。往往是山谷间吹来的风摇动着庄稼们的叶子飒飒作响,偶尔有几只粉蝶飞近飞远,某一支酸曲远远地像飘在风中的丝线。这时的劳作被包裹在众多欣欣向荣的生长之中,充满了丰富的层次。
而这样细致的准备工作最终也会得到回馈,当收获的时节来临,整个田野都是亮闪闪的,像是对农人们曾闪烁在田间的汗光的回应与辉映。
关于镰刀,老人们有个可怕的故事。说一个不务正业的年轻人被逼去地里割麦子,他把镰刀架在脖子和肩膀之间,一边走一边哼着歌,正走着,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只野兔,于是年轻人口中喊道,“呀,兔子!”同时兴奋地猛然一拽镰刀把儿想去追,却见他的头在瞬间被镰刀刃生生地割了下来——故事听着不太真实也很血腥,但老人们讲这个故事有一定寓意。农具们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征,它们的刃可以换回成石的粮食,但稍有疏忽,也是割裂血肉的利器。农具在被驯服成为农具前,一定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野性,有理由相信历史中的那些农民起义,人们最本能举起的武器就是这些农具。所以,合格的农人一定先要不动声色地揣摩每件农具的脾气与性格,再加上日复一日的相处与较量,才能彻底掌控这个身份特殊的群体。
所以,看到父辈们磨镰刀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杀气。伴随着父辈们粗糙的大手撩洒上来的清水,镰刀片子在已经被磨出流畅曲线的青石上来回滑动,镰刃就在滑腻的石浆中一点点闪现出光华。镰刃这时是火热的,油锅最灼热的那个点一般,当清水再次流淌冲刷而过时,似乎能听到水刃相交的瞬间那一连串清脆的爆响。这种声响很明显能激发起镰刀们收割的欲望。麦子、谷子、糜子和荞麦们正在列队等候,就像一群群成熟饱满、风姿各异的女人,当父辈们拿着镰刀走向它们时,天地间都充满着一种野性的较量与征服的意味。
终于,当这些收割回来的粮食们被堆积在打麦场上时,连枷上场了。连枷制作起来很不易,农人们除了要搞清楚机械原理,还得细心地绑好连枷扇子。那时的铁丝都算稀罕之物,所以连枷扇子只能用割成线的驴皮来捆绑固定——驴子在陕北可谓鞠躬尽瘁,即使死后,有的驴皮还被蒙了三弦琴筒子,依然在农人们的手中发出喑哑的鸣叫,有的则被用来缝绑诸如连枷这样的用具,它们得以在死后以另一种形式与主人的生活继续亲密接触。
打场时,农人们两两对站或是两排对站,抡着对等的连枷按照顺序和规律,一起一落地敲击着那些谷穗或麦穗。在这看起来极富韵律的动作中,庄稼的籽粒纷纷掉落下去,活泼泼地奔向地面,像一场欢腾喜悦的雨。
春种一粒,秋收一石,这是多么奇妙慷慨的馈赠与恩赐。很明显,连枷不会伤害到这些粮食颗粒,它只负责清点和阅读又一年土地交出的总结书。或者,连枷们也能读懂粮食之间的血缘关系,因为它们现在敲落的种子,正是远古时期同样被某些连枷打落的粮食们的后代。从古至今,连枷的身影也曾被诸多画像砖和壁画定格,它们的家族跟着庄稼们同样在复制和繁衍,唯一不同的是不同时代的连枷用来敲打不同时代的粮穗。对于粮食作物本身,这是多么深远的传承。对于连枷,这是多么持久的辨认和思索。对于在不同时光中挥舞着连枷的农人们而言,这又是多么坚固的命运。
连枷之后,木叉在竖着触角等待。它常常孑然独处,像村子里头脑简单的光棍汉。木叉制作起来要简单得多,只需在树上找到合适的双股叉、三股叉或是四股叉的略微粗壮的枝干,再在火中煨一下使之变软,接着按照力学原理把前端的分叉曲一下并使之定型便可。等到干后剥掉树皮,一枝滑溜溜的看起来有些滑稽的木叉就做好了。除了负责挑起草料送进牛槽驴槽,它的主要用途便是挑起被连枷们击打过的庄稼秸秆,为木锨的出场清理出舞台。
木锨像个僧人,总是平和地与周遭对话,有着禅修的沉静。它们的锨头是被打磨和熨烫弯的一块轻薄木片,这样一片轻巧灵动的木头适合不断上扬。它轻柔而没有锋利的刃,不会发出令人不安或激动的金属声响,更不会深刻地切入或挖掘。秋日的打麦场上,农人吹起口哨引来阵阵微风,用木锨和簸箕在风中扬起庄稼,清理杂质土粒。冬日的院落里,因其清爽不粘的特质,农人又用它铲起同样寂静的积雪。每当看到木锨,就能听到打麦场上风声与谷粒麦粒之间的对话,能听到雪花飘落覆盖在悠长岁月上的微小声音。
当陕北的山野由于空间巨大而显得万籁俱静的时候,斧头在某座大山中“箜——箜——箜——”的砍伐之音听起来虚中有实。这边一声,对面的山洼就应一声,前一声重而实,后面的回音听起飘一些柔一些,像是安谧的影子跟在惆怅的主人身后,不远不近。加上偶尔的野喜鹊叫声,简直是诗经中描写的声音和意境。在灌木和树丛的掩映之中,看不到人在哪一处,只能听到并不急促的砍伐之声。这样的砍伐一般不会持续太久,但时间因为山谷间的回音而显得多了一倍。当农人终于背着成捆的木柴出现在村口的道路上时,他的额头正流淌着咸湿的汗水,和木柴紧紧绑在一起的斧头正闪耀着亮汪汪的银光,像是在那些砍伐的声响中又沐浴了一回般满足。
但砍伐绝对是有规则的,不到万不得已,农人们绝不会去伤害任何一棵活着的树。那些山野林间掉落的干枝拾掇起来,依然会响亮地燃烧在灶台之中。但柴垛中还是会有一些木柴需要劈开。在陕北,劈柴是件有趣的事儿。对于较为粗壮的木柴,人们直接把它竖着放倒在地上,再给木柴前端垫上横放的另一根粗短木柴,这样可以省力和保护院落的地面。这时,一脚用力踩住木柴使之固定不动,另一脚稳稳踏在地面上,咬紧牙关,抡起斧头,对准木柴前端猛然一劈,然后再用力把嵌入木柴的斧头左右活动一下,看看是否能罅出更大的裂缝来。劈柴的人此时往往是怒目圆睁,臂膀圆抡,口中或许还喊着嘿嘿的号子,看起来像入阵杀敌的猛将。
用斧头劈开的木柴最后被整整齐齐地堆放到柴垛上去,被斧头剖露出来的颜色和纹理显现出一种神秘感。木柴的碎屑有时会被用作楔子,在需要的时候楔入农具们容易松动的地方,有时也会被楔入摇晃的木凳中,而钉楔子时,斧头的后背能给予恰到好处的力度和施力面。就这样,它制造裂缝,却又修补裂缝,使得岁月侵蚀中的松动与衰老变得坚实可靠。
但陕北的斧头不仅仅是素食者,它有时会和杀猪刀一起被当作年节时割砍猪肉羊肉和骨头的用具。也许偶尔还会在乡村中某个充满风暴的家庭中充当凶器。加上盘古开天辟地和和沉香劈山救母的传说,斧头身上简直充满了一种撕裂和重塑并存的气质,有时劈砍出生的火焰,有时又劈砍出死亡的深谷。但只要是静止的,人们看到的斧头便永远是被打造和征服得滑溜光洁的一块铁,安静而乐居一隅。
铡刀看起来是农具中的彪形大汉,但它外形粗犷,内心婉约。它或许被迫有过暴力的举动,但本质上它只想品尝植物的汁液,辨别植物内部的组织与结构,或是伴着不同的铡草节奏欣赏农人们的舞蹈。它深知对于家畜们而言,最美妙的音乐一定是野草和庄稼秸秆们被铡开时发出的声响,最美妙的舞蹈则莫过于男主人和女主人之间默契的铡草动作。男人略弯着腰,铡刀刃像渴望喝水的干燥的唇,女人则蹲在地上,把散发着清香的野草或秸秆们稍加整捋后送到刀刃之下。男人飞快地按下铡刀刃,继而又轻巧地微微弹起,女人就在这个空当中把草和秸秆往前一抬一送——这绝对是个舞蹈,轻巧中不失稳重,稳重中又有一丝豪放。嚓。嚓。嚓。每个伴奏音乐的点都那样准确而富有感染力。铡好的食物迅速把自身的香味抛在空气中。这时,老牛晶亮的眼睛,驴子晃动的长耳朵,铡草者偶尔的交谈和笑声,天边即将落下去的夕阳,所有的一切都如此轻松愉悦。
如果农具们也有性别,那么犁铧、镢头、铁锨、锄头、斧头、木锨和铡刀无疑都是深具阳性特质的。它们从被锻造好的那一瞬间就开始为天地的交合和生命的诞生繁衍而准备。它们是支撑着整个农业社会的梁柱和骨架。它们中的随便一样都可在时光深处撬起一大块带着泥土的农业史。
如果可以把凡是适宜于农人们使用的劳作用具都称为农具,那么这个范畴内便会多出一些具有阴性特质的农具们,这部分农具与日常生活更加贴近。它们有着自然界中所有阴性的文静、细致、容纳和宽厚。它们料理着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春夏秋冬,几乎每个季节角落都有它们的身影。且它们始终具有敞开和奉献的性质,敞开着面向天空,面向风,面向阳光或是农人们的面庞,再奉献出自己所有的情愫。
它们的名字也很多。笸箩、簸箕、筐、筛、粮囤、口袋——听起来有些细碎,但正是它们用本身固有的经纬织起一张细密的网,打捞和储存着农人们生活中的成果,并使这些成果各尽所用。
笸箩像老祖母。经过岁月的涤荡,她的内心能盛容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生活史,还有更广袤的大自然。这种宽广的盛容和笸箩多么相似。春播前,它盛容并晾晒种子,秋季时,它又盛容和晾晒农人们的收成。其余时间里,它还可以盛容松散的荞麦皮,盛容磨成粉后的任何粮食,盛容陕北女人年节时蒸制的面鱼儿和花馍馍。
笸箩有时被搬去碾道或磨道。碾子吱吱嘎嘎,石磨轰轰隆隆,面箩在女人们的手中一遍遍过滤着碾磨过的粮食。面粉米粉均匀地洒落堆积在巨大的笸箩里,这种堆积听似无声,其实却是一曲与碾磨合奏的音色丰富的交响乐。这音乐覆盖了它底部的每一个缝隙又逐渐淹没上来。笸箩在这样的时刻是享受的,它沉浸在这充满面粉米粉香甜气息的音乐之中。
但逐渐地,笸箩的每个缝隙都积攒了抖落不掉的粉末,也积攒了岁月中漂浮掉落的尘土。它的皱纹看起来更加沟壑分明,饱含情感。如果一只笸箩可以使用完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农人的妻子们把同样磨碎的青春和年华也洒落积攒在了笸箩的众多缝隙里。面对一只已经松散老旧的笸箩,你会看到一些陕北女人的生活经历。
簸箕没有笸箩这样老。它看起来像个走路一阵风,说话尖嗓门,做事稳准快的老婶子。或更像是在质检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的妇女,基本没有任何杂质或是不合格产品能逃得过她的检验。
向日葵花盘里的瓜子们看起来个个饱满油亮,但是只要倾倒在簸箕里左右晃动并上下扇动几下,令人惊讶的场面便出现了,许多没有仁儿的瓜子纷纷长了翅膀般自动飞落出簸箕。而麦场上,女人们抖动簸箕使它们如蝴蝶扇动的翅膀,粮食中的杂质和瘪籽便也会纷纷被清理出去。这个去伪存真环节如此重要而有趣——土地长出来那么多庄稼,庄稼又结出那么多籽粒,如同洋洋洒洒写出来的一大篇文章,许多瘪籽就是那些修辞手法,它们一定也是有作用的,例如维持生长秩序、平衡竞争等,或许只因被季节漏掉了一个小小的步骤而不能成为繁衍下一代的合格者。簸箕理解这些额外的情节,但它为农人铁面无私地辨别出哪些才真正适合保留,因为这样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来年的收成。
除了筛选粮食,簸箕还往往被用作拣出米虫的工具。突然的暴露和平坦使最灵活的米虫也无处可逃,包括微小的虫卵也只需扇动簸箕便可清理干净。正因如此,簸箕永不说谎和欺骗农人。
筐子和筛子多是农人自己编制。柔韧匀长的荆条成捆地割回来后,等到农闲时节,再把它们一根根按序排列编织。编织者不管年纪多大,此时眼里都会闪现着一种顽童才有的光彩。从孩提时代,人们就似乎喜欢着类似的编织游戏。在陕北,这个活计多属于老头们。每到了给筐筛们扭沿子的步骤时,老头们便会显现出一丝喜色,他们灵活而细致地给筐筛们装饰上最后的艺术花边儿。他们眼中光芒闪动,像是正给自己羞涩的老婆子戴上一顶花头巾。
编好的筐筛随时可以投入使用。胳膊上套着小圆筐去春天的山坡上掏掏小蒜,夏天的林子里摘几个蘑菇,秋天的田地里挖挖洋芋,冬天的地窖里拾几根萝卜。这让农人们的生活多了几分从容和消遣,也多了几分精致的情结。
筛子则因为通风和受光面大而被用来晾晒。干杏皮、干桃皮、萝卜干、大红枣、马杜梨,能想到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色素的零嘴儿都是在筛子里用阳光和风加工出来的。过去的清贫岁月里,对于孩子们而言,筛子里永远盛放着母亲或外婆、奶奶们积攒着的慈爱与盼望。
在过去的陕北,编制粮囤是每个农人必备的技艺之一,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粮食本身。粮囤有大有小,每家至少要有六七个。最大的粮囤两米多高,为了防潮防漏,用时需配上木质的囤架使之离开地面,并把剁碎的衰草和着泥在粮囤内糊抹一遍并晾干。合格的粮囤可以储存粮食长达十多年。每年打好的谷子、豆子、麦子和荞麦们被储存在这些粮囤之中,密集而沉重。粮食对农人和农人的孩子们始终是有奇特魔力的。偶尔站在比粮囤更高的位置俯视这些粮食,观测它们散发着不同光泽的颗粒,会感觉这颜色和颗粒的大面积集聚带着一种奇特的诱惑性,这种诱惑会使人不能自抑地去触摸这些粮食。带着莫名的激动和膜拜感,抓起一把囤内的粮食再撒落下去,那种掌心的冰凉和细微的响声会使人暂时忘却一切。
还有一种介于筐和囤之间的编织器物因其乐趣而不得不提。在陕北冬日,人们会使用一种名为“猫见愁”的带盖儿笼子。这个半米多高的笼子不参与其他生产劳动,只负责保管过年时的鲜肉。天寒地冻时分,把鲜肉放进“猫见愁”盖上盖子,其透气性恰好能使外界的冷气进入以保持肉的新鲜,同时可以防止一切除人之外的动物接触和偷食。想象一只猫咪围着这个散发着香味的“猫见愁”挠头抓耳的急切样子,真会为陕北农人们的智慧和这个戏谑的名字而莞尔。
口袋匠人听起来像是童话中才有的人物,但上个世纪他们曾踏足陕北的角角落落。在陕北人的生活还依赖着羊群时,口袋匠人靠为农户们编织羊毛口袋为生。一个羊毛口袋需要五斤到六斤羊毛。最好是黑山羊羊毛。他们在院落中把羊毛细细地捻成毛线,再像织布那样把毛线逐渐变成口袋。就像神安排在世间只专门掌控一些特殊技能的神秘人物,他们的前世今生似乎掩藏着某些秘不可宣的古老传说。
羊毛口袋结实耐磨,农人们在春秋农忙时节用它们送粪驮粮。比起一两年就要更换的帆布口袋,羊毛口袋可以用十多年而不破损。而伺候这些口袋中的高级货,人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它们的干燥,仅此而已。细细想来,羊子对于从前的陕北真是有着巨大的恩情,人们食羊肉,穿羊皮,铺羊毛毡,再用羊毛交换或编织必需品,就连女孩们玩耍的一种名叫“个托”的玩具,也是用羊骨涂上红漆制成。羊子们竭尽全能奉献了一切,甚至于死后,它们的毛还编织在羊毛口袋中,帮着陕北人颗粒归仓地驮回养活生命的粮食。
如果我描述的这些关于农具们的事情都是正确的,那么农人们的生活看起来如此充满着诗情画意。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们的生命有理由被夯得更加瓷实而层次丰富一些,或是被庄稼们的色彩绘制得更加饱满多姿一些。但这种试图把最艰辛的劳作描述成舞蹈,描述成音乐,描述成画面感的写作注定会迷失在随即而来的矛盾之中——相比城市生活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农人们只有四个生活环节。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其他一切都围绕着这四个环节来运行。这种重复和运行每年都在进行,一直到这个农人再也无法扛起农具走向大山。这种在时光中逐渐消失的归属性使农人和农具们眼神变得浑浊。没有了来自粮食和田野的热切召唤,农人最后的生命阶段往往是落寞孤寂的。但即便如此,那些衰老佝偻的身体往往还要靠着院落的土墙,试图眺望远处的田地和大山,就像那些同样由于衰老而被更换掉的农具们在角落里试图眺望农人一样欲语还休。或许对于土地而言,农人们才是使用年限最长且最忠实的农具,他们只信奉天地自然,并用一辈子的虔诚和狂热证明了这一点。
农具们的使用寿命同样令人唏嘘。因为磨损,犁铧每三五年就要更换,铁锹、镢头和锄头们则因迟钝和变形每两三年就要更换。这是怎样的一种消耗速度和力度。这么多的铁被农人们用生命加热,又在浑厚的黄土层中迅速地被损耗。黄土吃了多少铁,又吃了多少人。整个农业社会中有多少人前仆后继地奔向土地,他们身后就跟着多出几倍的农具,它们紧随人类身后一批批地消损在时空中。
陕北所有的农人都称呼自己为“受苦人”,他们大多不怎么说话,只期许着子女们能逃离这种受苦的命运。他们用农具们把生命修整成方砖,并试图在黄土中铺砌出向上的阶梯,好让后来人能走向他们想象的高度和宽度。但是,当手掌中再也没有了农具把子磨出的老茧,脊梁再也不用承受日头的炙烤,甚至再也不会为浪费掉任何一粒粮食而叹息的时候,这些后来人却为何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极少鸟鸣虫唱与夜晚的安谧,缺乏洁净的阳光和雨水,没有猎猎山风或山谷间的寂静,更没有村人们如老酒一样醇厚的乡情——这些后来人陷入一片片坚硬荒凉的水泥地,每日进出于欲望之门,似无法扎根之草,如无处栖身之鸟,身后有喧闹驱赶,前方无葱翠之林。
而那些不得不中途抛下农具来到城市的农人们,他们陷入了一种更加生硬的尴尬。对于他们,从前的生活被抽空,以后的生活无法饱满。城市间所有的东西都比黄土更浩瀚,且这种浩瀚没有黄土那样可四时变化的温度和接纳,它们始终是冰冷和拒绝着的。
农具们只能沉默。它们看到走出大山的农人和孩子们被什么巨大可怕的东西追赶驱逐着,但它们无法抚慰,更无法发出任何响亮的喊声示警。
农具们依然选择守候在曾经的家园之中,一遍遍回忆那些与土地和粮食交谈的岁月,回忆从前农人们手掌的摩挲和温度,哪怕这些业已破损坍塌的家园即将彻底被植被们湮灭。
想着想着,这些记忆就凝成了一粒粒伤感的锈。
责任编辑:王彦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