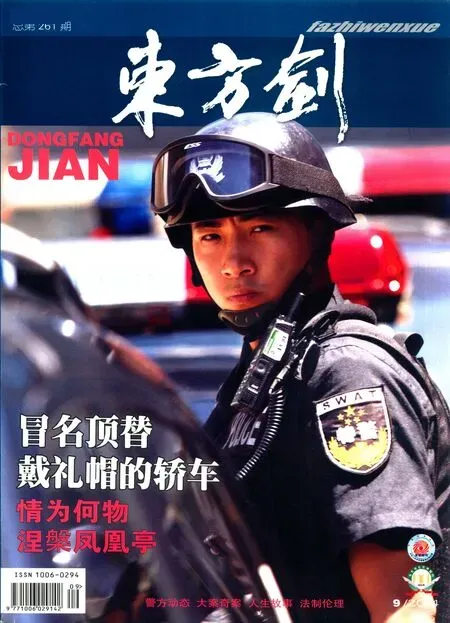大钟背后
2014-07-24孙建伟
◆ 孙建伟
大钟背后
◆ 孙建伟

一
登上“朴茨茅斯号”的时候,凯文还在向伦敦方向回望着,又想起了临行前舅舅对他说的那句话,你真幸运凯文,好好干,一定会超过我的。十几天后邮轮靠了岸。凯文一抬头,海关大钟就闯进了他的视线,因为它占据了沿江鳞次栉比各式风格建筑的制高点。舅舅说过,这个钟楼的高度亚洲第一。几分钟后,他听到了熟悉的威斯敏斯特报时曲。凯文有点飘忽起来,定了定神,才明白这是从心里滋出来的一种骄傲,几天来拥挤不堪的船舱带来的不快瞬时了无痕迹。很快,他将在大钟所在的这幢大楼里工作,成为中国海关的一名雇员,江海关关员。很多英国年轻人都向往这个职位。不过,凯文一点都没沾过曾是江海关高级内班职员的舅舅的光。伦敦办事处恪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规矩,不管是谁,都必须经过平等严格的考试和考察,听说一位剑桥的博士都出了局。所幸,凯文通过了。
前来接他的是艾弗里,一个身材粗壮满头红发的家伙。比他大了几岁的艾弗里话多,有点儿自来熟,凯文内向,明显接不上艾弗里一连串的问题。艾弗里看着这个新来的同事,撇了下嘴角。
黄包车在弹硌路上跑着,过一座木桥的时候,车夫加快了速度。凯文突然捂紧了鼻子,桥下枯水散发的臭气显然把他熏着了。到达桥顶,凯文的眼睛又烫了一下,车夫的脊椎弯成了一连串突出的珠子。艾弗里穿着白皮鞋的脚心安理得地踩在车杠上。凯文心头掠过一阵悸动。车夫随着艾弗里的手指在连环套似的小巷中穿行着。窄陋和臭气迎面逼过来,随处可见的苍蝇,忽然窜入阴沟里的老鼠,不知从哪里出来的乞丐和孩子迅速向黄包车聚拢,他们的指甲里嵌着黑黪黪的污渍,在凯文的眼前晃动。艾弗里说:“这里是华界,我想让你开开眼界。不过,别去理睬他们。以后你会见得更多,会习惯的。”
第二天清早,凯文按时到了外滩。进了海关大门,他看到的格局跟他所见过的伦敦市政厅基本一个风格,这让他很快恢复了自信。走到副税务司办公室门口,他在门上敲了一下,一个慵懒的声音传出来:“谁,什么事?”
“福克斯先生,您好,我叫凯文,是来报到的。”
“凯文,凯文,啊,想起来了。我正在等你。”副税务司福克斯蹙起的眉头舒展开来,眉梢那几根窜出来的翘毛滑稽地跳了一下,和他下垂着的八字胡呼应着。凯文忍住了笑。叶片顶端包着黄铜的新式吊扇发出呼呼的声响,似乎有点力不从心。尽管是在室内,盛夏上海的空气中涌动着蒸笼一般的气息,可福克斯熟视无睹。他高高的衣领和领结庄重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亚麻布外衣胸袋里的紫色手帕平整熨帖地露出一个标准的尖角。凯文有点不自然了,他衣着随便,更肆无忌惮的是汗不断从脑袋上沁出来。福克斯朝他扫视了一眼,看到了这位新来的属下目光中的敬畏。他咳了一声,拿起几本小册子:“凯文,这是介绍江海关以及它的工作规则之类的东西,你得好好看看,两天之后我将根据你的掌握程度决定你的工作。明白吗?另外,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应该学一些汉语,包括上海本地方言。这将会对你有帮助。当然,学费得由你自己承担。”凯文一直以敬畏的眼光看着这位滔滔不绝的上司,等他说完最后一句话,他微微前倾着身子说:“是,先生,我明白了。”
凯文跟着艾弗里去港口的一个管区巡查。从现在开始,艾弗里成了他直接的上司。艾弗里显得趾高气扬,一路上指点江山,评头论足。
“看见那些大大小小的船了吗,凯文?”艾弗里指着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只,“检查这些船将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它们将会给我们带来税款,也会带来不少麻烦。你得有足够的准备。”
二
几个星期过去,凯文渐渐熟悉了他需要检查的那些埠头。可他一低头就反胃。江水浑浊得不堪入目,各种来历不明的漂浮垃圾和乱七八糟的排泄物包围着船坞,秽气袭人。身形高大壮实的印度巡捕懒散地靠在船舷门旁,警棍拖在腰间晃荡着。肋骨突出肤色黝黑的挑夫们则视线茫然地用他们的竹烟杆吞云吐雾。
凯文跟在艾弗里的身后,艾随时会把货物清单递过来,看他是否能马上就对这些货的税款一目了然。在中国代理商面前,艾弗里摆足了架子。代理商们乖巧地递上雪茄,艾弗里嘴上叼起一根,把更多的装入口袋。当然还有他喜欢的酒。可是凯文拒绝接受这些东西。规则上写着,任何人都不得从同海关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员手中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再说他的确烟酒不沾。艾弗里说:“别把这些规则当真,谁会为了几根雪茄大惊小怪?嗨,我让你见识一下那玩意儿。”他对一旁站着的代理商指了指一包货物,做了个“打开”的手势。艾弗里用手指沾了一下,放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点点头,再送到凯文面前,“你闻闻,上等的印度货。”凯文立刻回忆起曾在街上闻到过的那股味道。艾弗里斜着眼对代理商说:“竟敢私带鸦片上岸,胆子不小。”代理商并不害怕,只是谄着脸,不作应答。
大商船“哈里森号”白色的船体在阳光照射下晃得更加耀眼,凯文跟着艾弗里踏上舷梯,那里早就候着一个中国代理商。此人一身丝质长衫,虽然是热天,但他脑袋上还覆着一顶镂空的白色小圆帽,也许是为了保护稀疏落拓的头发。由于他的下巴窄小,所以整个头部就像一个上下两色界限分明的椭圆形球体。他弯着腰向艾弗里递上一份货物清单,然后对两人分别作了个揖。艾弗里跟他应该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说:“晚上好,乔先生。”凯文瞟了一眼艾弗里正在翻阅的清单,很多都属非法。但艾弗里却对这人完全没有刚才的那种跋扈。乔先生把两人请进餐厅,艾弗里坐下来就说雪莉酒,接着问凯文喝点什么。凯文根本没想到这儿来喝酒,屁股就没搭上凳子,但看到艾弗里的眼神,仓促地说,那就啤酒吧。这顿饭吃了大概有个把小时,艾弗里微醺着,乔先生把嘴凑到他耳朵旁,低声说着什么,艾弗里点着头,然后大笑,使劲拍着乔先生的肩,然后举起手中的苏格兰威士忌,“乔,再干一杯。我们签字。”凯文忽然说了一句:“我们是否需要去看一下。”艾弗里目光复杂地对他瞥了一眼,又转头对乔先生说:“怎么样,让我的同事再看一下?”乔先生说没问题,就叫人打开货物包装。艾弗里打了个响亮的嗝,腆着肚子在一堆包裹前走了一遍,回头对凯文说道:“看好了吗凯文?如果没什么,我们就签字吧。”他自己先签好,然后交给凯文,凯文只得签上自己的名字。乔先生这时忽然在餐厅门口喊道:“艾弗里先生,您忘了一样东西。”艾弗里如梦初醒一般,示意凯文等一下,疾步走向餐厅。一会儿艾弗里出来了,手里捏着一个信封,仍跟乔先生说着什么。看到凯文迎上来,就向乔先生挥了挥手,乔先生则立地不动,作揖道别。
黄浦江上桅杆林立,更远处的烟囱吐着浓烟,夜色正空濛地洇渲开去。白天江面上的龌龊和污浊在它的掩盖下化成一大片无尽的黑。江景变得疏漫而迷离。凯文觉得自己也渐渐被这黑遮蔽了。
三
夏去秋来,树叶从夏日的挺拔青翠迅速凋萎成枯败,只有一个季节的荣光。现在它们只能投入风的怀抱,然后又被抛弃,在马路上铺成遍地的金黄尸骸。跑马厅一年一度的赛马又鸣锣了。
这是个休息天。凯文是第一次踏足,裹在一帮同事中间,无所适从。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押赌。马廊里的本地小贩们叫卖着茶水和各种自制饮料,一个壮汉手里握一把长薄刃刀喊着,立秋最后一批西瓜了,再不吃就没有啦。凯文听得懂不少上海话了,但他觉得,如果一边看赛马一边吃西瓜,真是太煞风景了。趁着同事们沉浸在喇叭声里不断报出的赛马投注时,他悄悄离开了。
衣衫褴褛的乞丐和烟鬼游魂一样在大街上飘忽着,一辆外壳上涂着“卫生稽查”字样的厢式小型货车停在一堆垃圾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握着铁锹开始清铲,但他们马上听到了一阵枯涩的啼哭,再一看,竟是一个女婴被丢弃在这里。凯文听人讲起过,这不算什么新鲜事,只是他今天亲眼所见了。车把女婴带走了,他久久凝视那里,不知道女婴将会被送到何处,是传教士的育婴堂吗?她将来又会如何?好久才把思绪拔出来。那天他没叫黄包车,就在街上闲逛,后来逛到了码头。靠近码头的小路上开着许多小妓馆,主要招徕海员的生意。凯文走过来,妓女当然不会放过他。说实话,眼前这些活色生香的肉体对他25岁的身体的召唤非常强大,他清晰地感受着自己的坚硬和膨胀,但是转而就感到失态了,简直毫无羞耻,好像他的衣服被唧唧喳喳的姑娘们的目光剥光了,好像在她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展示他的粗鲁,于是他逃了,身后挟着妓女放肆的笑。
礼拜天,他在一种怪异的情绪中不知不觉进了教堂,他感到空虚而怅惘,可耻的色欲躲在被叫作心灵的某个地方窃笑着,不时冒出头窥探一下,面对上帝,他简直无地自容。
码头上,“哈里森号”装载的货物非常壮观,十几个苦力扛着最后几个棉包鱼贯踏上搁在船尾的跳板,被用力扔到主甲板上的棉包发出沉闷的声响,等待海关的检查。凯文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情报,说这条船藏匿鸦片。他没跟艾弗里说,并比他早到了码头。正在跟一个船东模样的人说话的乔先生认出了凯文,立刻满脸堆起笑意朝他走去。凯文礼貌地点了点头,但神态依旧很严肃。
“这上面装了什么,乔先生?”
乔先生面带谦恭,却答非所问:“这些货我们都付过税了。”
“能给我看一下货物清单吗?”
乔先生把清单交到凯文手里的时候,很自然地把宽大的袖口往后抻了抻,凯文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只长长的信封。乔先生继续说道,“你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有问题他们会很快处置的。”
凯文看着清单说:“可是这里根本没写棉花呀?”
“一定是误会了吧。不过我可以卸船接受检查,凯文先生。”
“乔先生,你知道,一条船不是说卸就能卸的。所以我希望你能跟我说明白。”
“凯文先生,其实你我都应该明白,这是一桩合法的生意。我敢担保。”那只长信封不知什么时候又攥在了他的手里。
“恐怕这件事我得向上面报告。”凯文目不斜视。
“报告什么,凯文?”一个声音插入了他们的谈话。
“啊,是艾弗里先生。您的同事凯文先生认为这条船有问题,恐怕不能按时启航了。”
艾弗里的眼睛盯着凯文:“是这样吗,凯文?我记得你应该和我一起在这儿的,是吗?”
凯文有点不自在,他躲着艾弗里直视他的目光,说:“艾弗里先生,我觉得这条船有问题,所以得仔细查一下。”
“你觉得有问题,好吧。乔先生是合法代理商,他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不过,你得考虑一下,如果查不出问题,那么这船的港口停泊费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到时候由谁来承担,这个你考虑过吗?”
本文针对多子带合成技术中子带内幅度与相位误差利用定标数据进行了计算,并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流程。针对子带合成技术中子带间误差提出了一种基于原始数据的计算方法,该方法根据图像对比度最大原则,采用两级计算方式,提高了子带间误差计算的精确度。最后利用定标数据和机载SAR实测数据进行成像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误差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凯文沉默了,他不敢确保情报完美无误,而且如此大量的货物查起来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查不出,停泊费的确是个问题。艾弗里显然对自己瞒着他来检查很不满。他和乔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乔手里的那个信封究竟是什么呢?和上次在艾弗里手里的那个是一样的吗?这么多的问号一下子纠缠在一起,让他昏沉。虽然不甘心,但说出来却成了这样:“艾弗里先生,也许是我多心了。”
艾弗里对乔先生挤出了笑:“乔,凯文和我都不想为难你,例行职责罢了。好了,我们这就在‘哈里森’的离港许可证上签字。”说着他从凯文手里接过单子刷刷签了字。
乔先生一直笑容可掬地站着,双手接过了许可证。
四
深夜,凯文忽然被一阵接连不断的巨响吵醒了。空气中开始弥漫浓烈的硝烟味,他赶紧翻身起床,胡乱抓起外套披在身上。又是一声炸雷般的巨响,然后是“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凯文忽然感到恐惧,用手捂住耳朵。难道打仗了?但是巨响过后,竟然是小孩的欢呼声。凯文搞不懂。他只能紧闭窗门,然后坐着,直到爆响渐渐稀落。第二天凯文才知道,昨晚是中国的农历除夕。他的上海话老师告诉他,巨响是炮仗的声音,分单个和成串的,所以声音就不一样了。“除夕”的意思就是用炮仗来驱除一头长着触角、凶猛异常的名叫“夕”的怪兽。然后新年就到了。凯文联想到了女王诞辰的庆典礼炮。
年初三凯文接到一份请柬,邀请他第二天到四马路上的天华茶园听戏。落款是宏坤。凯文拿着这份请柬,想了半天也猜不出这个宏坤是谁。对于中国戏,他没有一点概念,他决定去开开眼界。一进戏院,他就被喧天嚣闹的声音包裹住了,头一下子胀起来。难道中国的春节就是各种热闹噪杂的声音组合吗?他正想着,一个小伙子迎了上来,用英语说:“欢迎您,凯文先生。”凯文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小伙子的手往前面一指,“有位先生在那儿等您,请跟我来。”凯文就跟着小伙子一直走到最前面,那里摆着一张八仙桌,上面摆开了瓜子、花生、茶水和一些他见过的小糕点。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凯文先生,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凯文一惊:“原来是乔先生。那个……”“哦,恕我疏忽,宏坤是鄙人的名字,写习惯了。请坐。”“原来如此。”乔先生说:“这是凯文先生到上海的第一个春节吧?我想让你感受一下中国春节的味道。以前我也请艾弗里先生来过。”乔先生坐定后把身体往凯文这里欠了欠,大着声说:“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京戏,讲究唱念做打。锣鼓和大镲是主要的乐器。”凯文皱了皱眉头。这段戏结束后,走出一位身材瘦小的姑娘,比她手里拿着的乐器高不了多少,乔先生对凯文轻声说,“这乐器叫琵琶。”凯文点点头。姑娘坐定后,拿起琵琶拨了一下,声音单薄却清亮,与刚才的喧嚣完全不同。姑娘先说了一句话,声量极具穿透力,戏院里一片寂静。凯文有点吃惊,她这么瘦小的身体怎么能发出如此响亮的声音。接着琵琶声响起来。凯文自然听不懂多少,但一曲唱毕,他觉得余音绕梁,这种一会儿清丽婉转一会儿粗犷豪放的腔调全由她一个人模仿出来,在凯文看来相当于奇迹。
乔先生对他说:“这个曲目叫苏州评弹,凯文先生听懂了吗?它叫《三笑》,是一个在中国人尽皆知的爱情故事。”
“啊,真是太有意思了。很好听。我不能全听懂,但是我知道里面那个男人很聪明也很幽默。”
“凯文先生真是欣赏大家啊。真是不虚此行啊。”
凯文笑了:“感谢你乔先生,送给我这么好的春节礼物。以后我还会来听的。”
“一个人?”凯文不解。
“对,这叫堂会。不过,你得支付一个戏院所有的票房。”
“啊,那我可听不起。”凯文耸耸肩。
“开玩笑啦,凯文先生,你什么时候想听就跟我说,这个女戏子随叫随到。”
“什么是……女戏子?”
“就是唱戏的女人嘛。她还刚出道呢。”他又凑近凯文,很得意的样子,“是我捧的场。看来今天效果不错。明天的《申报》上会出现她的名字,她就要红了。你明白吗?哈哈。”乔先生自顾自地大笑起来,还情不自禁地拍了一下凯文。凯文看着他,有点茫然。
五
散场的时候,乔先生特地把姑娘叫过来与凯文相识。姑娘羞怯地看着凯文,凯文想以英式礼节拥抱她一下,但她却往后缩着。乔先生笑了起来:“人家还刚出道,不懂你们洋鬼子这一套。她叫明玉。”他把凯文叫洋鬼子,似乎两人有了深交。又转过头来对姑娘说:“明玉啊,这是凯文先生,我的朋友,江海关稽查科署理四等总巡。啊,跟你说这个也不懂。凯文先生很喜欢你的评弹,以后他想听什么,你要随叫随到,晓得吧?”
“乔先生,我晓得的晓得的。”
“记得回去跟你们班主说一声,就说我说的,啊。还有,正月十五叫他来见我。”
“我晓得了,乔先生。我走了。”
凯文目送明玉离去,又看了看乔先生,两人对视了一下,微笑着告别。
第二次见到明玉是在一个月后。凯文那天在报纸上看到她的演出消息,下班后先到花店买了一束花,然后买票进了戏院。那晚明玉演出的时间明显长于春节那次,因为台下一直鼓掌,不让她下去。凯文明白,她真的红了。演出结束,凯文把一张字条嵌在花丛里,是用中文写的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然后交给一个小男孩,让他去给明玉。
凯文后来想起明玉来找他时的那种神情仍是久久萦怀。黯淡,紧缩,哀怜,就像一条被困滩涂的鱼,全然没有舞台上的自如。但他从未对她说过这个感受,即使后来他们有了肌肤之亲,甚至同居,甚至生儿育女。
凯文打开门的时候,明玉站在那里不敢看他。他把她让进来,她还是低着头
说了几句话,凯文问明玉:“你是很早就认识乔先生了吗,他很照顾你是吗?”
明玉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她站起身说道:“凯文先生,我要走了。”
“你这就走了?我还要跟你说话呢。”凯文突然觉得很想跟明玉说话。但她仍说:“凯文先生,我看过你了,所以要走了。”
“那我可以请侬再留下来吗?”
明玉犹豫了,她忽然又问:“凯文先生,你吸鸦片吗?”
“鸦片?哦,不,我不吸。你为啥问我这个?”
她迟疑了一下说:“因为我吸过,乔先生也吸。鸦片是好东西。”
“为什么?”凯文有点惊讶。
“因为鸦片可以让人舒服,啥烦恼都没有了。”
“你有啥烦恼,乔先生不是对你很好吗?”
明玉沉默着,然后悠悠地说:“乔先生说,你是个聪明人。他还说,中国有句话叫与人方便于己方便。否则大家都会很难堪。”
凯文十分茫然:“什么方便?中国人的事总是那么难懂。”
“我也说不太清楚。”明玉说完就走了。
六
在凯文的概念中,他就是明玉的保护人,当然他从她身上可以找到性的释放和情感安慰。明玉也认可并沉醉于他们的这种关系。凯文对乔先生通过明玉来控制他的企图心知肚明,也无意拒绝。如此一来,究竟如谁所愿就很难说得明白了。与其说这是乔先生希望的结果,倒不如说凯文控制了局面。凯文有绝对的自信掌控这种“碟中谍”的斗法。他也最终弄明白了“与人方便于己方便”的意思,但他不会就范。他要把乔的这个女戏子内应变成他的人。这一招在中国兵书里叫作将计就计。当然,他得谨慎小心,还得装出被他拉下水的样子。作为青帮头目之一的乔像猴子一样精明。他担心明玉会因为被帮会窥探到什么而遭到惩罚甚至生命的威胁。要把乔捏在手中,就必须抓到他的把柄。
艾弗里怒气冲冲地来了,涨红着脸质问凯文为什么要故意为难“哈里森号”。这是凯文早就料到的事。这家伙一定跟乔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凯文说:“艾弗里先生,我绝不是故意为难,这本来就是我的管段,检查也是按海关规则行事,有什么错吗?”
“别忘了我是你的上级,跟我说什么海关规则。还记得那次装棉花的事吗?耽误了交货时间,让他们赔了一大笔钱。为这事,乔说应该让我们来承担损失。”
“他可真好意思说得出口。”
艾弗里面朝窗口,黄浦江水在这个阴雨天显得晦涩浑浊,毫无生气。他叹了一口气说:“凯文,你现在的日子挺不错,有了一个情妇,可能时常还抽两口吧。我想,就靠我们的薪水,没点额外收入可不能维持多久啊。你得面对现实。”
“我承认你说得不错,但我这个人有点……就像中国人常说的,对,不识时务。”
“你这是嘲讽我吗?是说我为了钱不顾规则。哼,我告诉你,这里向来就是这样,没人拒绝。你明白吗?这是这里的生存规则。至于什么管段,让你换一个巡查的位置,太容易了。天哪,我真是想不明白,你真是不知道还是装的?”
“艾弗里先生,我真的不知道这里的所谓生存规则。再说我没有理由拒绝执行海关规则而去迎合它。如果我惹你生气了,只能请你包涵了。”
“哼,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如果你还懂得一点利害关系,就请闭上你的嘴。”艾弗里来时的红脸变成了铁青,然后转身就走。
凯文偷偷笑了,这是他要的结果。然后他让明玉去找乔先生,告诉他晚上到四马路上的一品香西餐馆见面。
乔先生如约而至。
乔先生见面就问:“上午接到明玉的传话我很高兴,凯文先生有何吩咐啊?”
“我一个小巡查哪敢吩咐乔先生,是我一直忙于公务,想找个机会感谢乔先生介绍我认识明玉小姐,抱歉了。还有,乔先生的那批货明天到我这儿来,我会安排好的。请放心。”
“啊呀,凯文先生这么照顾我乔某人,乔某感激不尽啊。明玉还不错吧?”说着他从西装内袋神速抽出一个信封,递给凯文:“请笑纳。”凯文拒绝着,乔先生说:“凯文先生,这是规矩,否则我怎么相信你呢?”凯文说:“那好,我遵守规矩。”
从这时起,凯文与乔先生过从甚密,艾弗里不知就里,向乔先生打听,乔先生却只是应付。至于凯文,自从那次谈话以后就跟艾弗里掰了。
七
凯文的计划如期进行,乔先生已对他深信不疑。他必须先把明玉安顿好,他甚至让乔跟戏班打招呼,不要安排她太多的演出。他迷上了这个姑娘。
凯文在静安寺路租了一间房和明玉幽会。他没能抵御住明玉的蛊惑。那天晚上,他又一次抚摸了她的身体,她颤栗着。她常常这样颤栗,这让凯文对她的身体更加迷恋。他习惯了在颤栗中进入她。她开始尖叫,先是压抑,很快放肆而疯狂。是凯文从未见过的疯狂,他暗暗惊讶。后来她就提到了鸦片,她说来之前刚刚抽过一次。她在他身体上逗弄着:“洋鬼子,要不要来一下?”凯文经过情欲洗礼的大脑忽然缺氧,觉得有点疲乏,鼻腔里突然闯进了那种油腻腻的气味,他冲动着回击她的“挑衅”:“你可以,洋鬼子有什么不可以。”
凯文出手的决定是在他的一位英国籍同事在查缉一条走私船时突遭杀害后作出的。《字林西报》刊登的一篇调查对此事竭尽渲染,福克斯副税务司因此授权海关人员可以携枪检查。凯文认为给此事定调为时过早,因为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他想此时把乔的走私公之于众也许不失为一个时机,甚至可以为这起谋杀事件提供某种线索。在上海,帮会的力量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华界还是租界,总有帮会的影子忽隐忽现。在此之前,他把明玉带到评弹的诞生地苏州,让她躲起来,然后把他掌握的有关乔的走私证据向福克斯和盘托出。但他没想到,福克斯对他的举报并不太感兴趣,轻描淡写地说:“这不算什么。倒是关于你,凯文先生,我这里有不少对你不满的报告。你可得想想自己怎么跟人相处。否则哪一天,你突然被挤出去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可不是什么好滋味。”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难道真的像艾弗里说的那样,就连福克斯先生也被所谓的生存规则主宰了吗?至于谁对他不满,向福克斯打小报告无需多想就知道是他的上司艾弗里。事后的了解很快证实了他的想法。但凯文不会去找他当面对质,他现在只能沉默,虽然他已失望之极。
消息是一点点溜出来的,乔先生突然失踪了。个把月之后,有人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发现了疑似乔先生的一具尸体,却因高度腐烂而面目全非,所以对尸体身份的鉴定颇费周折。但乔先生的确失踪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就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几颗金牙成了唯一的线索。乔先生的大太太惊魂未定地回答着法医关于金牙的位置和数量等问题,她希望不是她的丈夫,哪怕失踪,没得到最后的证实还能存有一丝希望。但她带着颤音的回答恰恰与尸体口腔里唯一遗存的玩意儿完全对应。这几颗金牙的服役期才一年不到,是她陪丈夫去镶的牙。
法医的最终确认使大太太的颤音立刻演变成跌宕起伏的夸张而琐碎的拖音。尽管有点刻意和作势。
谁是凶手?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人都为此煞费苦心,凯文心里默默指向一个人,当然只能暂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但他隐约感到,他的机会来了。
他开始像一个侦探那样暗中调查乔先生的死。这个人曾经是他的对手,他潜在的敌人,也是企图收买他的人。一个对手的突然死亡并没有阻止他的继续关注是因为跟另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艾弗里。这位上司实际上也已成了他的对手,甚至比乔先生更可怕。在凯文看来,这两个人之间的依存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所以乔的死一定与艾弗里有关。越来越多的征象表明,凯文的想法正在向残酷的事实靠近。工董局中央捕房的侦缉也有了进展。但这时艾弗里突然销声匿迹了。
凯文笑了。
八
离公共租界核心地段遥远的麦特拉司路(今平凉路)。此地满目荒凉,与乡间无异。
凯文站在一间破败的小屋前,在那扇老旧不堪的木门上敲了好几次后,艾弗里终于现身了。他的目光更显阴鸷,头发凌乱,眼袋鼓凸,见到这位下属非常惊讶,可人家分明微笑着,不知道是嘲笑还是释放善意。艾弗里感到汗毛倒立,寒气向骨头深处徐徐渗透。此时上海已入腊月,朔风扯开嗓子唱着奔放的歌谣,唱得小屋外墙战战兢兢。艾弗里不说话,等待凯文先开口。
凯文也在等。两人僵持着。凯文应该有一种满足感,至少艾弗里不可能再用那种颐指气使的腔调跟他说话了。艾弗里的颓丧是因为他居然被这个看不顺眼的下属找到了。这是一种从心底里漫起的悲哀。
艾弗里终于听到凯文开了口:“艾弗里先生,我今天来是来跟你谈一笔生意的。”
“好啊,说出来听听。”艾弗里竭力掩饰自己的不安。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不忍,所以我有个机会也许可以改变你目前的状况。”
“改变我?那我可真得好好感谢凯文先生了。”艾弗里语含讥诮。
“不信吗?反正我很有诚意,就看你了。我能找到你就已经说明一切了。”这句话使艾弗里浑身又战栗了一下。他竭力安定了自己说道:“我虽然眼下落魄,但至少还活着。好吧,说说你的建议。”
“那我就直言相告了。你手里还有鸦片吗?”
“你这个正人君子也想弄那玩意儿?别开玩笑了。”
“不开玩笑,我是代人买的,最好整批收购。我已经打听过了,你手里有货想脱手,所以凭我们的关系,你应该会照顾我,当然也解了你的燃眉之急。”
艾弗里心里更对这位下属惊惧了,他一直在防御着,但凯文紧追不舍:“你也许解释不清是怎么弄到这批货的,而且,乔的那些兄弟正在追查它的下落。”
“哼,信口雌黄。”
“其实我对这种传闻不太感兴趣,我只关心我们能不能成交。”
艾弗里终于就范。
这次险中求胜的低价收进高价卖出使凯文一下子发了。而他囤积的部分则是左右这个市场的基石。所以他很快控制了市场,年轻的凯文先生成了一个富翁。随后他怀着矛盾的心情离开了海关,用第一桶金投资实业。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他与一名英籍工部局董事的女儿结了婚。与其说是结婚,毋宁说是找一个后台。他仍然流连于明玉的床榻。明玉成了真正的名角,她的名字占据着每天大小报纸上的戏曲广告。直到她有了身孕。凯文殷勤地陪着她,听她讲中国戏曲故事。然后,他们的孩子问世了,凯文给儿子取名吉姆。
关于艾弗里涉嫌谋杀乔先生的调查仍在继续中,由于迟迟未公布结论,人们对此事众说纷纭。议论最多的是艾弗里在地下鸦片交易中与乔发生争执,认为搬掉这个心机重重的“合作伙伴”是迟早的事,于是暗中雇凶杀了他,然后独吞鸦片。不论结局如何,艾弗里已经声名狼藉。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全面废止鸦片,凯文把鸦片全部交了出去。鸦片在烈焰里扭曲着化为灰烬,凯文鼻腔里塞满油腻的焦臭,啼笑皆非。他从一个清贫公正的海关关员到冒险投机鸦片发财的富翁,最后又回到了原地。明玉对他说,你没钱不要紧,我来养活你。”
1950年代初,而立之年的英国贸易专家吉姆应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邀前来洽谈商务。结束公务后,吉姆特地转机停留上海,像他父亲当年第一次站在黄浦江边那样,举头凝视外滩沿岸那个鹤立鸡群的建筑物:海关钟楼,然后将去寻找他生母的下落……
发稿编辑/浦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