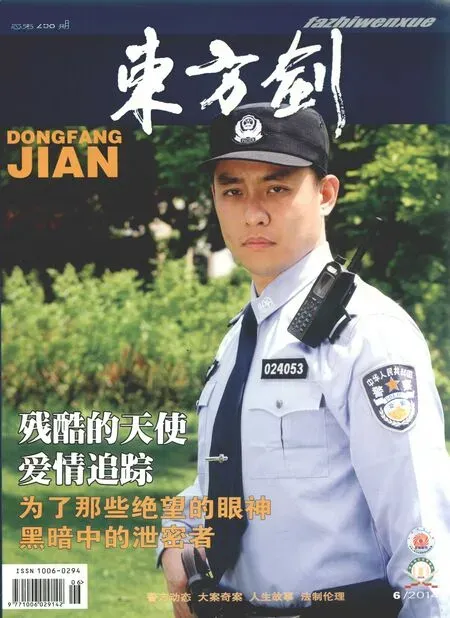残酷的天使
2014-07-24日下圭介李重民
◆ [日] 日下圭介 著 李重民 译
残酷的天使
◆ [日] 日下圭介 著 李重民 译

为破案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生怕有疏漏的,就是警察。嘿!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的。而且,大多数的警察也正是这样努力的。
那起案件发生时,我工作的警署搜查一课恰好正处在这样的状态里。不知为何,杀人案件接连发生,结果设立的搜查本部竟然多达四个。所有的案件全都是根本看不见前景,不问昼夜手忙脚乱地好几天不回家的刑警更是不足为奇。从本厅来的同事脸上已经无法掩饰不悦的神情,署长的焦虑也越来越明显。
要说在这样的状况中新接手的案件,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接到报案说,有个72岁的老人,因煤气中毒死了。
猝死就是猝死,所以除了勘查人员和外勤巡查之外,我和刑警有村两人赶赴现场。
死去的是一位名叫饭塚敬藏的男子。地处旧住宅区的二层楼房间,楼下除去浴室和厨房,有三间房。敬藏是在面朝院子的六叠卧室里死去的。院子现在来看算是很宽敞,但建在斜坡上,所以从敬藏的房间要下去五六节楼梯。
案件的发现者是死者妻子菊子,65岁,头发大多已经花白。年轻时也许是位美女,个小却优雅。据她说,她从旅途一回到家,发现丈夫已经死了。这是5月22日夜里的事。
“你去哪里旅行了?”有村问。
“去甲府。那里的外孙女结婚,我去参加她的婚礼。”
“婚礼仪式什么时候举行?”
“是20日,没错。你说说,现在的婚礼都很奢华吧。连对方都要换好几套衣服,而且要换三次呢!带有家徽的和服,晚宴服……”
“那么,你是20日出去的吧?”年轻的有村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催促道。
“不是。出去是19日。说婚礼仪式从正午起,所以当天去会很匆忙。我是乘坐夜里8点从新宿发车的特快。”
“回来呢?”
“6点半左右吧。”
“你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情况?”
“打开房门……”
“你看到了,房门是锁着的!我觉得很奇怪啊。话虽如此,就是那样啊。丈夫在家,却为什么锁着门?”
“你带着钥匙吧?”
“是的,要给你看吗?”
“不用,算了。那么,你就打开门进屋了?”
“那是当然的。不打开门就进不去吧。”
“走进房门,你做什么了?”有村那张圆脸增加了几分红晕。
“我叫丈夫,但他没有答应。于是我愈发感到不安,便跑进六叠房间啊。这样一来,你想,满房子都是煤气味……我慌忙打开窗户……并关上煤气闸……”
“是煤气闸打开着啊?”
“因为是打开着,所以我要关上吧。”
有村的脸变得更红了:“打开着的是哪个煤气闸?”
“就是那个。”菊子用手指着的,是在东侧的窗下。
“当时你丈夫已经……”
“冰冷了。”从菊子的眼睛里,第一次溢出了眼泪。
敬藏的尸体躺在被褥上。是个眼窝凹陷、颧骨突出的清瘦男子,睡衣敞开的胸膛清晰地现出肋骨。散发着臭味,是已经在腐烂。详细的情况要等尸检以后才能见分晓,但就算在我看来,死亡后也已经过了有四十个小时以上,这是一目了然的。
菊子哭出声来。
“我去甲府期间……说去一趟不容易,所以可以住在女儿家里……因为我已经有六年没有去甲府了。”她好像是在为自己辩解。
趁着她抽抽搭搭地哭着的间隙,有村继续在提问。
根据她的回答得知,敬藏好像担任过几所私立中学和高中的事务长等职。不过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以后又去书法班干过,但那也是只干了几年就不干了。六年前开始闲赋在家,完全没有职业。有着两间房屋出租,所以老夫妇两人的生活看来也没有困难。
有村的提问是非常准确的。这是职业习惯形成的,感觉不到热忱。我能觉察到他对这起案件不太愿意接手。他另外还在侦查杀人案件,是一起还能让媒体趋之若鹜的案件,他把精力都倾注在那个案子里,这样的事件大概不会入他的法眼吧。
我也是一样,不愿意接手这起案件。然而,我与有村的情况不同。我55岁,还有两个星期就要退休了。三十余年,几乎是做了一辈子刑警过来的。不可思议的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感到感慨和依恋。妻子说要把乡下的土地卖掉,造一幢小型住宅,正干劲十足。独生女儿的婚事也已经定了。我的心已经转移到了另外的事情,即,我想休闲一段时间,去参加我早就感兴趣的寻觅名胜古迹的旅游。
“你丈夫的身体呢,平时没病吗?”有村的提问在继续。虽说不愿意接手,但大致的情况摸底还是不能省略的。
“不。算不上健康……他患有风湿病,腰腿不便。因为白内障,视力也明显衰退了。”
“那么,夫人要出门四天,他不是很不方便吗?”
“食物等东西我事先买好放着。如果要用厨房,丈夫自己也会出来……”菊子静静地答道。
我打量着屋内。可算是一定程度的职业意识吧,职业习惯还保留着。
很平常的日本式房间,只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就是,放在铁架上的大型玻璃鱼缸。氧气在透明的水里冒着水泡,大大小小约有五十条热带鱼在优雅地游动着。
“真漂亮啊!”我窥看着喃语道。这是我来这里以后说的第一句话。
“是我丈夫喜欢养鱼啊,”菊子平静地微笑着,她已经不哭了,“喜欢每天喂它鱼饵。用手指一敲玻璃,鱼就会游过来啊。我即使再怎么敲玻璃,它们也不会理睬我。”
我试着敲了敲玻璃,鱼儿们都没有理我。
房屋呈南北窄长,东侧与南侧面对院子。东侧有个宽大的窗户,南侧像是支出院子似的有个玻璃门。玻璃门下部几乎靠近门槛的地方有洞,裂缝呈蜘蛛网状破碎着。洞大致有苹果那么大,仔细一看,碎片都洒落在席子上。
“夫人,碎了啊。什么时候碎的?”
“哦,我出门前还没有碎,大概是丈夫因什么东西弹碎的,还是刚才我想要打开窗户时踢着的?反正,我也记不清了。”菊子这么答道。
但是,我却没有因此而释然。如果是从内侧碰碎的,一般来说碎片应该向外洒落。可是,我没有追问。因为不向外洒落的情况也会有的。
“你出门时,关门,是关紧的吧?”有村问。
“是的。这一点也……”菊子答道。
为了仔细,有村察看了所有的窗户和门。
我也大致查看了其他的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收拾得干净整洁。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品,不难看出一对老年夫妇朴素的生活样态。我还察看了厨房。在洗物槽里的滤水筐里,茶碗和小皿等盖着抹布放着。
我将茶碗拿在手里察看着,这不是出自侦查上的关心。是伊万里(译注:日本佐贺县有田町一带出产的瓷器)一带的夫妻茶碗,已经褪色的色调,令人感觉到已经有些年月了,仿佛渗透着夫妇两人长年的生活烙印。我自己也是对这样的事颇有伤感的年龄了。
接着,令我感到眼睛一亮的,是钓鱼用的携带式冷藏箱。这也完全是出自我个人的兴趣。我喜欢钓鱼。尽管这么说,但以前一直忙于案件的奔波,很少能出去钓鱼。一旦退休,我准备好好地过过钓鱼的瘾。因此,我也想拥有这样的冷藏箱,可以将啤酒等放在里面冷却着随身带走,也可以将钓到的鱼保持新鲜的状态带回来。
这是24升型的吧。在冷藏箱中算是大型的,有苹果箱那么大。我如果早晚要买的话,就要挑个大型的。我打开上面的箱盖看了看。里面当然是空的,但在合成树脂的底部,有一道像火柴杆那么大的黑色痕迹。仔细一看,像是烧焦的痕迹。
“是你们家的吗,这个冷藏箱?”看见菊子出现,我便问道。因为我没有感觉到这样的物品适合只有老年夫妇两个人生活的家庭,当然我也没有算得上是讯问的意思。
“不是的。是从这前面泉田家借过来的。是想带点什么东西作为礼物去甲府,那边是山区吧,我想他们会喜欢新鲜的鱼之类的。我去鱼铺,正好有活的对虾。”
离开菊子家,我与有村分手了。拜访泉田,除了泉田开着一家快餐厅、我肚子饿了之外,没有别的理由。
那是一家装潢得十分简洁的餐厅。然而我走进去,店里已经开始在打扫了。
“客人,已经关门了。”
“啤酒和下酒菜,随便什么来一点吧。”
“请你去别处。到这前面的大街上,还开着的店家有很多呢。”
面对男子像赶我走的口气,我顿时来气,于是说道:“我想问问有关饭塚敬藏的事。”
“你是警察?”
“是的。”我出示了警官证。
男子的脸色顿时变得僵硬了。大约三名店员瞬间停下手中的工作望着我。这司空见惯。一听说是刑警,人们大多会露出这样的表情。我当然知道这副表情与憧憬或尊敬相去甚远。
“敬藏先生怎么了?”
“死了,是煤气中毒啊。”
“你说死了?”男子怯怯地开口道,“呃,把父亲叫来,敬藏的事,我父亲知道得很清楚。”
男子这么说了之后,我没有要求他,他便将店里的人员向我作了介绍。我也没有想听,却知道了他们店里有夫妇两人和打工的男女大学生各一人在干活。
“你吃点什么?”
“有吃的?”
“呃,鸡肉炒饭或咖喱饭还是有的。”
“给我来碗鸡肉炒饭。我喜欢红饭。”
“啤酒呢?”
“来一瓶。”
这时,进来一个刚开始拔顶的男子和一个相对而言瘦削的女子。介绍说,男子名叫泉田干治,女人是他的妻子正子。两人都已经过了六十岁,但看上去很精神。
“听说敬藏先生去世了,是煤气中毒吗?怎么又……”泉田问道,一边为我斟着啤酒。
“好像是自杀吧。”我答道。只能这么认为。有村确认过,房子的窗户和房门都锁着。就是所谓的密室。现在,不会产生一氧化碳的天然气在城市里已经普及,但这一带的煤气还是在使用旧的管道。
“那个人吧……会自杀啊?”正子感到纳闷。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生性好强、喜欢管闲事、在平民区里常见的女人。
“奇怪吗?”
“可是,他不是那么懦弱的人。要说起来,他是一个绝对不会退缩的人,总是认为这世界上自己最正确。”
“你是说,顽固?”
“说是顽固,也没有那么愚呆。说顽固,还有些弱啊。记得什么时候,在社区会上有人提出要挂外灯时,激烈反对的就是敬藏先生啊。说我们夜里不出去,没有必要挂什么外灯。分摊的钱,最终是我们承担呀。因为是社区会长,是吗,他爹?”
“呃,已经死了的人,你就不要再说这些话了。”泉田制止道。
“可是,这是真的。我这个人吧,不会流下虚假的眼泪,编什么谎话说他是那么好的人……听说敬藏先生以前是个色迷。学校的事务长,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被人辞退,好像也是因为这个。”
“喂!”泉田拍拍她的肩膀。
“哟,这是真的呀!是听公民馆长说的。说他年轻时还养了个二奶。”
“嘿,他真有钱养二奶啊?”
“呃,就连我的孩子他爹在被店铺的租金逼得焦头烂额时,都会和小岩的小料理店女人……”
“敬藏先生的确很顽固啊。”泉田急忙纠正了话题的轨迹,“可是,像他这样以自我本位活过来的人,上了年纪体质一弱,不会是觉得没有依靠了吧。尤其是如同他拐杖的菊子出去旅行,他第一次独自在家,突然感到寂寞,便想死了?”
“他一个人在家,这是第一次吗?”我问道,因为番茄酱用得太多,我嘴里塞满着鸡肉炒饭。
“首先,菊子一个人出门去,这事从来没有过啊。社区内的妇女会或老人会组织在外住一宿的旅游,她就从来没有去过。”
“岂止是旅游,就算是去看戏,都不让她去啊。那个人,很喜欢看戏。听说菊子以前演过戏。”
“嘿,演过戏?”我抬起头来。
“是以前啊,是很早以前。是独生儿子去世的时候,所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吧。菊子是在糕点厂工作的,现在叫打零工。那里的从业人员组织了一个剧团,菊子是硬被拉去的。”
“是当演员吗?”
“不是。听说她怕难为情,所以一口回绝,便让她在幕后做事。”
“不过,说起演戏时的回忆,她倒是好像很快乐啊。”泉田一副沉静的语气说道。
饭塚敬藏的尸检结果,第二天出来了。
死因还是一氧化碳中毒所致,没有任何外伤。发现时死亡后已经过了45个小时至60个小时。就是说,是在20日上午4点左右到晚上7点钟之间死亡的。经血液化验,得知他喝过酒服过安眠药。安眠药虽不是致死的量但是量很大。
去找他经常就诊的医生了解,据说敬藏偶尔会诉说自己睡不着,所以给他配了安眠药。再向这位医生询问,他说敬藏的风湿病突然恶化的可能性很小,但好转的可能性更是没有。因白内障就诊的眼科医生也是同样的口气。
“是自杀啊。肯定的。”课长露出释然的表情。
当然,我也是一样,算是松了一口气。
饭塚敬藏是个硬气的男人,凡事都必须以自己为中心。可是一开始衰老,他就被大家疏远,没有人再愿意跟随着他。没有比像这样的男人更熬不住孤独的了。唯一的“自己人”菊子出去旅行,独自度过夜晚,寂寥深深地铭刻于心吧。
自杀——不管怎样,对警察来说,自然是一件可以了结的事。
下班时间已过,我开始做回家准备。虽然正是最繁忙的时候,但对我却没有委派像样的案件。退休的日期屈指可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要摆脱像战场似的工作岗位,是需要勇气的。我打量四周,感觉自己像逃兵似的。我在座位上站起来。
这时,课长喊我,说有个电话点名要找我,对方在电话里说,为饭塚敬藏的事,要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事。
我接过电话。是泉田干治打来的。他说了一件的确很奇怪的、不合情理的事。我说见面再谈,便放下听筒。
“反正是一件已经了结的事,你不要弄得太复杂啊。”课长比我年轻十岁,他的眼睛在金属框眼镜背后歪斜着。
我被泉田干治带去的,是一幢砂浆旧住宅。走上红锈的铁楼梯,在二楼的一间房间前,泉田一边敲门,一边喊着:“久保,是我。”
打开房门,整个房间一览无遗。一对夫妇抱着婴儿正在圆桌前吃着晚饭。
“久保,这位是刑警。”泉田说道。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啊?”还很年轻的妻子蹙起了苍白的脸。
“你说的那件事,你再说一遍啊。”泉田催促道,“你说看见了敬藏的幽灵,不是编造的吧?”
“你自己擅长编瞎话,所以连刑警都请来了。”妻子发牢骚道。
“是喝醉了在梦里看到的吧?呃,你,是那样吧?”
“不。我的确看见了。喝醉是真的,但是……”久保好像是当真了,放下筷子走上前来。还不是酷暑的季节,却上身穿着衬衫,下面穿着过膝衬裤。我听泉田说,他在罐头厂里工作,平时很认真,但酒风很差,一喝醉就吵架。这个久保在去泉田儿子的餐厅里吃午饭时,说了件离奇的事。
“说是白色的吧,是真的呀!而且冷冰冰的,说我被勒住了脖子呢。真是吓死人了。”久保做着手势说道。他好像微微有些醉,口齿过分伶俐。
“你按顺序说一遍,”我说道,“是什么时候看见的?”
“上个星期六,不,已经是星期天了。我在朋友家里喝酒。”
“是20日吧?”如果那样,就是敬藏死去的那一天。我对这无聊的话产生了几分兴趣。
“呃,是20日。”
“几点的时候?”
“呃……1点左右吧。”
“胡说,”妻子插上嘴来,“你说看见奇怪的东西,气咻咻地奔跑上来时,已经过了3点了。”
“总之是20日天还没亮的时候。你说的幽灵在哪里呢?”
“饭塚家的……是突出在院子里的房间吧。据说是在那个房间里死去的吧。后来我听说这事,还感到毛骨悚然呢。”
“是在房间里吗?”
“正是如此啊。是这样,白色的。在席子上扭动着吧?痛苦得这样……扭动着身体。”久保扭拧着自己的身体做动作给我看。
“在房间里,你怎么能看得出来?”
“我走进院子里……”
“你为什么走进院子里去?”
“哎,你尽干蠢事,所以……”妻子坐立不安了。
“我不是特地来盘问这件事的。你可以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劝解道。
“穿过那里的院子,是一条近道。另外一个,穿过后面房子的院子,就是这里。围墙塌了。”
“只是进院子,房间里能看见吗?”
“那个院子,是有阶梯的。”
“嗯。是连接六叠房间与院子的阶梯吧?”
“你会问我为什么会登上阶梯吧。你即使这样问我,作为我来说,我就没办法回答了呀!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登上阶梯。我一喝醉,就不知为何会那样做。因为那里有阶梯。这个回答好吧。我没有恶意,这是真的呀!”
“嘿,行了。一登上阶梯,透过窗玻璃就能看见里面?”
“是啊。窗玻璃下面是磨砂玻璃,上面是透明的吧。窗帘也有隙缝。”
“于是,白色的幽灵在扭动?”
“真是那样。巨大而白色的,这样七倒八扭的……怨恨……”
“还发出声音了?”
“我觉得有声音。嗯,有声音。”
“你听到了声音?以前你不是没说过吗?”妻子用鼻子冷笑着。
“里面是暗的吧?”
“可是,也不是漆黑的呀!朦朦胧胧的,有青白色的光。有趣的是这以后啊,警察先生。我登上去想要看得再仔细一些,这时,脚尖将玻璃的下方踢碎了。我果然是喝醉了呀!”
“玻璃碎了,我知道啊。”昨天,我亲眼察看过。
“接着,幽灵哇地摊开双手出来……你不相信?不会相信啊。可是这是真的呀!”
“不是骗人的呀!这个人。”妻子帮着说道,“回到家的时候,他脸色吓得煞白啊。”
“我不认为是骗人的,”我说道,“是难以相信吧。”
“是真的,从玻璃的隙缝间摊开两只手,哇地幽灵就出来了,所以我就从阶梯上滚落下来了。这里的伤痕,就是那时产生的。幽灵也走下阶梯来,手绕住我的脖子……是冰凉的手啊。反正,是在梦里啊。后来我就连头也不回地逃回家里来了。”
“夫人,当时,他喝得相当醉了?”
“走路已经摇摇晃晃的。不过啊,这个人不聪明,醉得那么稀里糊涂,才闹出那样的趣事来啊。”
因为长年的刑警生活,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幽灵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一走到外面,漆黑的天空里,挂着半轮明月。
在饭塚家,今天应该是临时的守夜,所以泉田邀请我说想去看看。我觉得很费事,却也没有拒绝的理由。现在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回到警署里去。我不想去汇报幽灵的事,把已经疲惫不堪的后辈们搞得精神错乱。
附近的邻居和亲戚们都来了,但人数还不多。真正的守夜是明天晚上,听说葬礼告别仪式是守夜的第二天。
点完香以后,马上回去总觉得于心不安,所以便去客厅里。
这样的时候传出了孩子不合时宜的笑声。大概是亲戚的孩子吧。三个人将照片排列在一起察看着。两个像是小学生,一个是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
“是婚礼仪式上的照片吧?”我插嘴道。
“呃,”女人答道,“正要出门的时候印好的,所以就带来了。”
“你是菊子的女儿吧?”我说道。谈不上是感觉,她那胖乎乎的逗人喜爱的脸神与菊子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一看就明白。
“是的。母亲19日起去了我们家,我想留她住三个晚上,昨天晚上回家。就是这样。人生真的是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啊。前天我还带她去了塚仙峡,她还非常高兴……”
女人让我看照片。与家人在一起的照片,塚仙峡的照片,还有在婚礼上的照片。所有的照片上都留有菊子的身影。所有的照片她都很幸福地笑着。
“这个呢?”我将一张照片拿在手里。
照片好像是在甲府车站的站台上拍的,映着以特快列车为背景的菊子。
“是母亲到达时的照片。”
“行李很少啊。”我说道。照片上的菊子只是提着一只旅行用的小提箱。
“是啊。我说,上了年纪,所以行李还是少点好。因此,婚礼时要穿的衣服事先都用小包裹寄送的……不过,你的意思……”
“对虾,没有带来吗?”
“对虾?”女人直眨眼睛。
听说菊子在敬藏死去的六叠房间里,也有还没有打过招呼的原因,我去了那个房间。我很不擅长丧事时的寒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我与生前的敬藏连一面之交也没有,所以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总之,我把双手支在席子上鞠着躬。
“热带鱼很漂亮啊。”与其说些不知轻重的话,还不如赞美养鱼缸。
“有七种也不知八种鱼。数量有五十条吧。”
“有那么多?全部都是敬藏先生买的吗?”
“是的。直到一年前吧,他身体情况还算好的时候,也到街上去散步,顺便自己买回来的。那以后,是我去买的,他说要补充死去的鱼。所以鱼的种类我还记得啊。”
菊子一种一种地告诉我,但我认识的就只有大鱼鳍和黑花纹的、色彩鲜艳的神仙鱼,和体色红蓝相间发光的霓虹裙脂鲤。
神仙鱼只有两条,全都是像幼儿的手掌那么大,在鱼缸里是最大的。霓虹裙脂鲤有十几条。正如它的名字,将闪着光的漂亮的小身躯聚在一起,或左或右地游动着。
一条神仙鱼不知想些什么,突然在鱼缸里呈对角线一圈一圈地开始游动。摇着巨大的尾鳍,冲势很猛。平和的水里立即出现很大的波动。小鱼们争先恐后地逃散开去,简直像被骤风吹散的枯叶似的。
霓虹裙脂鲤群也向四处逃散。然而,一条逃错了方向的霓虹裙脂鲤受到神仙鱼的袭击。看样子是用刀刃似的背鳍直接冲击过去的。
受伤的霓虹裙脂鲤颤动着背鳍喘息着,但神仙鱼再次袭击,用它那锋利的牙齿咬破了小鱼的肚子。
这是瞬间发生的事。我和菊子愣愣地互视了一眼。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吗?”
“不。不过,从今天早晨起,这已经是第三条牺牲了。是怎么回事啊?丈夫在的时候,鱼缸里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的。”
这时,泉田走进来。
“夫人,冷藏箱我要带回去啊。”
“哦,谢谢了。放在厨房里。”
“夫人,”我冷不防说道,“那个冷藏箱,你不是带到甲府去了吗?你说过是要带去的。”
“结果没有带啊。想带去才借的,还是因为体积太大了呀!”
的确,小个子老女人抱着这个冷藏箱去旅行,不是个合适的东西。
“听说,您是刑警吧?”
我一穿上鞋,一个脸长得像熊似的女人向我打招呼。我回答说是的,女人便像要诉说重大事情似的朝四周扫了一眼之后,把我喊到背阴处。
“我是住在前面那户房子里的,我看见过一件奇怪的事啊。”
又是奇怪的事?我脱口而出:“看见幽灵了?”
女人扬起细细的眼睛睨视着我:“我不是和你开玩笑啊!我每天晚上到二楼的阳台里做美容体操……”
我决不会说出“好像没有效果啊”的话来:“那么,你看见什么了?”
“有人进入那个房子里啊。19日夜里很晚。”
“19日深夜……”
是菊子把敬藏留在家里出门去旅行以后。
“是啊。进去的人,我认识。我可以说吧?”
“你说。”其实我并不想听。
“是对面隔壁枝村先生的夫人啊,叫弘子。我刚看见她进去,不到一分钟就又出来了。”
“也许是找敬藏先生有事吧?可是,那么晚会有什么事呢?”
“那种事,我不知道啊。……刑警先生,你不要说是我说的啊。”
我叹了口气,有些哭笑不得。我信心十足地进行查访时,日继一日地空手而归是常有的事。我正要想溜走时,对方主动诉说起来。
梅雨期的晴天,刮着和煦的风。
“我要为这起事件去走访……”我对课长说道。
课长看穿我想要外出的心思,便说道:“你慢慢查。”
托课长的福,我得以偷偷地从警署那幢灰色的大楼里溜出来。
然而,我不能真的一点儿事也不干。与其说这是我的,不如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悲的习性。
弘子28岁,与银行职员结婚第四年,总有着一种阴郁的感觉,但勉强说得上是美女。
“听说,19日夜里,你去过隔壁饭塚先生的家里啊?”我啜着端出来的红茶,问道。
“是的,去过,是夜里11点之前。”弘子没有丝毫的犹豫,答道。
房间里收拾得非常整洁,也许是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书架上排列着外文书的书脊。
“为什么事去的?我想请教一下。”
“是菊子打电话来。她丈夫养着热带鱼,为了将鱼缸里的水温保持恒定,是有恒温装置——设有温度自动调节器的加热器的。她在出门前好像不小心把软线从插座上拔出来了,说希望我去看看。”
“难怪。如果软线拔掉的话,水温会下降,热带鱼会死。虽说充其量不过是鱼,但从养鱼人的角度来看,会担心的吧。但是,菊子为什么不把电话打给她丈夫呢?”
“说他应该已经睡着了,所以不想把他喊起来。是这么说的,但是……”
“但是什么?”
“菊子很怕敬藏先生。记得什么时候,热带鱼死时,他甚至打她,骂她养鱼的方法不对。我是偶尔去送传阅板时看见的。”
“不小心拔掉了加热器,当然是怎么也不能说的。因此,你就去了。隔壁的房门钥匙怎么样?”
“我有备用钥匙。她说万一自己把钥匙掉了会很为难。”

弘子家租的是饭塚家的房子。菊子是房东,所以在菊子的眼里,弘子是很容易依靠的对象。
“用备用钥匙走进六叠房间,敬藏先生怎么样了?”
“房间里很暗,但他睡得很沉,还打着呼噜。”
“你说很暗,没有开电灯吗?”
“如果开灯的话,也许会把敬藏先生吵醒的吧。如果吵醒,半夜里有个隔壁的女人在房间里,会把他吓坏的。如果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我自己也不愿意。”
“你的心情我理解。插座在哪里?”
“打开门,在门的右边,下方。”
“马上就找到了?”
“是啊,马上。”弘子点点头。
“可是,很暗吧?”
“插座的地方,菊子在电话里告诉我了。虽说很暗,但热带鱼鱼缸里装着照明用的荧光灯。靠着那光,可以微微地看见房间里的状况。”
这我也想起来了。鱼缸有塑料盖,还装有荧光灯。大概是为了能清楚地看到水里的状况。久保看见的白色光,其实就是这个荧光灯吧。
“插座那里,软线脱开着吧?”我继续问道。
“是的。正如菊子说的那样,是缠着红色带子的软线。”
“你把它插进插座里就回去了。就这些吗?”
“讨厌啊,你是说我其他还做了什么吗?虽说是受人之托,但夜里偷偷摸摸地去别人家里,我总觉得很后怕啊。我这样的人,从走到房门口起,心里就咚咚地乱跳。所以按她的吩咐,我把插座插进去之后,马上就回出来了。从进门到出来,不知是三十秒还是四十秒吧。”
弘子很快就出来,这是由目击的女人证明的。
“那么,你没有走进六叠房间里吧?”
“是的,也许踏进了一只脚。”弘子清楚地回答。
也许是她在探摸着插座时,无意中碰到了煤气闸?我的头脑里闪过这样的想法,但很快就打消了。煤气闸在窗户下面,是与房门相反的地方。将席子纵向摆放有两张席子的距离,就是说相隔四米,而且在那中间,还有敬藏睡着。
不管怎么说,此后经过了好几个小时,敬藏才死的。我想象不出弘子做的事情与敬藏的死有没有关系。
我说着“打搅你了”,便站起身来。
弘子将我送到门口,忽然想起似的说道:“前天傍晚,我见到菊子了呀!是站前的百货店里。”
“你说前天傍晚,她是从甲府回来吧?也许是去购买晚餐用的副食品。”
“若是食品专柜,是在地下吧,菊子是从上面下来的。我从三楼乘坐下楼的电梯,她已经在电梯里了。提着百货店的纸袋,我若无其事地窥探了一下,里面放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这么大小的东西。”弘子用双手表示像自己的脸盘那样的大小。
“是用报纸包着的东西吗?”
“是啊,好像很小心的。电梯里很拥挤,她说不要压我的纸包,会压坏的。我被她骂了呀。平时她是个很温和的老奶奶,所以我还大吃一惊呢。”
若是22日傍晚的事,就不会与事件有关联吧,但作为猜谜游戏,好像很有趣。
——在百货店里购买的东西不是食品,用不是包装纸而是报纸包着的大物件,是容易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无聊的时候,我也会胡思乱想。
这天是敬藏的正式守夜,在菊子家里,人数也有所增加。线香的香味很浓。
在养着热带鱼的六叠房间里,我见到了菊子。菊子穿着黑色和服式样的丧服,非常般配。
“哟!霓虹裙脂鲤又死了吧。是被神仙鱼咬死的吗?”我看着鱼缸说道。
“是吗?是又咬了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菊子的脸很忧郁。
“神仙鱼,意思是天使之鱼吧。也有残酷的天使啊。”
神仙鱼悠然地在水草间游动。
“我退休以后也想养热带鱼。不过,还需要有很多不同的用具吧?”
输送氧气的气泵,净化装置,照明,还有与恒温装置联动的加热器。全部用电,所以要分别安装软线。加热器是棒状的玻璃制品,令人联想起试管。
“你养鱼的话很好,因为鱼不会诉说不平,也不会反抗。”菊子微笑着。
“听说,19日夜里,你想起软线也许被拔掉了。”
“没错,是那样的。我出门前,放在架子上的火车票不小心掉落在墙壁的夹缝里。我用尺子划拉出来,那时嫌麻烦把软线拔掉了。”
“难怪。这种事经常会有。”
“正是出门旅行前心急慌忙的时候吧。就这样不小心。到了晚上忽然想起来,就从甲府的女儿家打电话给邻居。是快11点的时候吧,我还觉得给人添麻烦了,但好歹也是有生命的东西。”
“真难为你啊。”我呢喃道。
“你指什么?”
“不指什么。是指与生物打交道啊。不过,敬藏先生平时是几点睡下的?”
“上了年纪,所以很早就睡了。6点前后就已经吃晚饭,8点就上床了。”
“是吗?可是夫人……”
“嘿,还有什么?”
“不。其实我快要退休了,渐渐地接近进入老年人行列的年龄。上了年纪,并没有不愿意,而且还很高兴。你说奇怪吧?”
于是,菊子一副认真的表情,说道:“黄金时代不尽是年轻的时候啊。把没做完的事拿起来继续做下去,这也是一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吧。”
令人心情舒畅的风拂面而来,摇动着院子里的嫩叶。
我感到有些累,嗓眼里很干燥,所以去泉田的快餐厅想要喝杯咖啡。店里正是空闲的时候。在角落里的餐桌边,秃顶的泉田一副像看着艺术品似的表情摩挲着崭新的钓竿。
“爱不释手啊。”我招呼道。
“啊,钓了很长年月,但一点儿也没长进啊。不过,只是悠悠然地被海风吹吹,心境也会很宽畅的。”
“我也马上就有闲工夫了。你要教我一次。”
“其实我预定从今天起要去伊豆,但妻子骂我,说有敬藏的守夜、葬礼,说邻居之间的交往也很重要,这样的时候不能杀生。”泉田一副心猿意马的表情。
“你的冷藏箱很好啊,就是借给菊子夫人的那个。”
“被划了道伤痕啊。”
“我也看见了,是细长的像被烧过的伤痕。”
“嗯。嘿,幸好不是看得见的地方,使用也没有妨碍。可是,是什么伤呢,会把冷藏箱烧焦了?那对夫妇又不抽烟。带到甲府去,是谁不小心放过香烟头吧。”
“不。听说没有带到甲府去啊。”
菊子说因为体积大所以不带了。我把此事告诉了泉田。
“那家伙很怪异啊。”泉田点了支烟说道。
“怎么怪异?”
“有个我们店里也去采购的冰库。那里的店员19日傍晚来配送,说起将干冰送到菊子那里去,菊子约好7点10分前送到的,早去了20分左右,结果挨菊子训斥,说太早了。”
“嘿!”的确是很怪异的。
“是将装有干冰的冷藏箱抬着试试,便改变主意了吧?因为重量比想象中重。老年人马上就会改变主意的。连我都是那样。”
泉田的解释合情合理。
“他爹,去旅行吧。不是约好的?”妻子说道。
“我这样约定过吗?”
“你又来了!不是说过好几次了?你说退休后一起去旅游。我一直很高兴呢。不过,你如果把以前的约定全都实现的话,我现在衣服和戒指应该有很多吧。”
“我全都为你做过吧?”
“你什么也没有为我做啊。你说为我做了什么?哎,你说说看呀!”
我哑口无言。结婚三十年来,为妻子做了些什么?能回想起来的一件也没有。
我要退休了,还有一个星期。办理退休手续时毕竟摆脱不了某种情感,但没有到胸膛里发热的程度。为了工作四处奔波忙不得暇的时候,心想有空闲后想做的事很多,做也做不完,但一旦获得了自由,那种欲望似乎也减退了。
“呃,饭塚敬藏的事件,结果还没有了结吧?”
“不是没有了结,是了结了呀!是敬藏先生自杀。报纸上不是也刊登了一篇小小的报道吗?”我啜着啤酒说道。
多达五十个的鱼缸排成一大溜。所有的鱼缸里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热带鱼。像穿着长袖和服似的漂亮的鱼,像玻璃工艺品似的鱼,看上去很凶猛的鱼……既有神仙鱼,也有霓虹裙脂鲤。
“很难养吗?”我问中年店员。
“不是特别难养。嘿,开始时劝你养些普通的鱼。”
“你说的普通的鱼,就是神仙鱼和霓虹裙脂鲤吧?”
“是的。若是那些鱼,养起来没问题。”
“不过,神仙鱼有时会咬死霓虹裙脂鲤吧?我亲眼看见过。”最终我说起了自己亲眼看见的过程。
“很少见吧,因为神仙鱼是很老实的鱼。能猜测到的是,鱼缸里放入的鱼太多而处于过密的状态。”
“我觉得不那么过密。”
“那就奇怪了。哦,对了,还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将大的神仙鱼和小的霓虹裙脂鲤同时或者脂鲤先投放在鱼缸里,如果相反,在先养着神仙鱼的鱼缸里,后把脂鲤放进去,神仙鱼就会咬啊。”
“嘿!你说是老资格虐待柔弱的新手吧?这故事无论哪个世界里都有啊。”
“是担心居住权受到侵害吧?”店员笑了。
“鱼认得出鱼的脸吗?”
“应该认得出吧。”
这时,一对母子过来买鱼。
店员从指定的鱼缸里用网兜利索地将鱼捞起。我呆呆地望着。反正,我有的是闲暇时间。
店员将水灌入两层的塑料袋里,将捞起的鱼放进塑料袋,然后安上小型氧气罐。塑料袋像甜瓜似的膨胀开来。用橡皮筋紧紧地扎住塑料袋口,用报纸包好后交给对方。
“是用报纸包吗?”我问。
“是啊,为了保温。这样放着的话,若是现在这个季节,三个小时没问题。”
谜团解开了。在百货店里用报纸包着出售的容易坏的东西——
从甲府回来的菊子购买的,是热带鱼。买的多半是霓虹裙脂鲤,所以才受到了先住进鱼缸里的神仙鱼的袭击。
“怎么样?你先开始养热带鱼?”店员说道。
“嗯。你先帮我把养鱼的用具凑齐。可以便宜点。”
“爸爸,我买礼物来了。冰淇淋,这里的好吃。”女儿真奈嗲声嗲气地说道。
“又要幽会?不是晚了吗?”
“还刚刚10点。”真奈笑着,打开冰淇淋盒。真奈24岁,秋天就要出嫁。我朝女儿丰满的胸脯扫一眼,感谢上帝她不像我。
从打开的盒子里冒出白色的雾气。
“简直像玉匣子(译注:古代传说中从龙宫带回来的藏有珍宝的玉匣)啊。”
“是干冰呀!现在办婚礼等场合都用的。新娘新郎从白色的烟雾中缓缓地登场。”
“嘿,你们的婚礼也是这么办吗?”
“哪里,没有那样的兴趣啊。而且听说,干冰这东西突然一发热,就会散发出一氧化碳。”
妻子是第一次坐飞机。倚靠在机窗边,恰好天宇一片碧蓝,下面被一片云层覆盖。
我们出去旅行。妻子选择的是包价旅游,知床、道东游玩一圈四日三宿,每人六万九千八百元。
飞机下面云层的流动极快。看着这简直像是舔嘴唇似的动向,觉得这就是白色幽灵的真面目。喝得烂醉的久保在敬藏的房间里看到的,就是干冰的烟雾。
干冰溶化产生的烟雾是碳酸气,一遇到高温,就会变成一氧化碳。菊子肯定是在剧团后台干活时获得的知识,才知道这一点的。
菊子事先将干冰装在冷藏箱里,然后出去旅行。冷藏箱底部放着热带鱼用的加热器。只是软线脱开着。在冷藏箱盖子上留出隙缝,五六个小时不会很快溶化。
夜里11点左右,她打电话给隔壁的弘子,托她将软线插上去。弘子这么做了。因为是在黑暗里,所以软线的一头连着哪里也无法确认,这无可厚非。在热带鱼的鱼缸里,一般来说软线的种类有很多。
加热器发热,立即将干冰溶化,烤焦了冷藏箱底部。变成白烟的气体比空气还重,在席子上匍匐、盘旋,阻止了熟睡着的敬藏的呼吸。让敬藏服安眠药的,肯定也是菊子。
可是,鱼缸里没有了加热器,因此出门三天期间水温当然会下降,热带鱼会死去。这是菊子所担忧的。如果事先委托弘子办这些事,热带鱼死得蹊跷,会引起弘子的怀疑的。
如此一考虑,菊子便在旅途回来时顺便去百货店里购买了热带鱼。然而想不到的是,热带鱼大部分都还活着。虽说是热带鱼,危险的是水温降到二十度以下,这个季节即使没有加热器,也不是那么容易死的。这是我在热带鱼店里打听到的情况。菊子将买回来的霓虹裙脂鲤与鱼缸里剩下的鱼放在一起,神仙鱼就露出凶残的牙齿。
“残酷的天使啊?”我嘀咕道。
“呃?”妻子将目光从机窗前移开,问我。
“没事。我说的是鱼。”
“是钓鱼?买冷藏箱?”妻子愉快地说道。
“嗯……不,不买了呀!”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
“我觉得像是买给你用的吧。”
发稿编辑/浦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