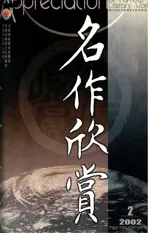琦君小说中的故土经验——以《橘子红了》为例
2014-07-13史皓怡宁波大学浙江宁波315211
⊙史皓怡[宁波大学, 浙江 宁波 315211]
作 者:史皓怡,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琦君将她散文里剪不断理还乱的怀乡之情与亲友之思延续到了小说创作中,她的小说仿佛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承载着她关于上个世纪前半段的江南深厚的记忆和怀念,“具有中国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化性、人道、人性、人伦的文化内涵”①。琦君代表作《橘子红了》1987年6月发表于台湾《联合文学》,1988年3月转载于《读者文摘》,这部小说以少女的视角,叙述了一幕发生在民国初年旧家庭的女性悲剧。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以及对于亲人的遭遇无可奈何的叹息与惆怅,使得这部作品成为解读琦君小说中故土经验的最佳范本。
一、家园。对于写作而言,地域性几乎是一种源头性的力量。②故乡的所见所感是作家的原初记忆,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琦君小说中关于故土的书写多取材于她少年时期在浙江永嘉的生活经历,表现出对传统民族文化深刻的认同感,这一文化心理的表征是对故乡风物的描绘,深层结构则体现出在文化思维影响下的情节走向。
琦君的作品总能酿成一种情感的氛围,并按照一定的情感结构线把灌注了情感的形象组合起来。③在《橘子红了》中,她以“橘子”切入,开始了对乡土生活的描绘,给人一种真实、纯朴之感。瓯柑是温州特产,个小,味道微有苦涩。琦君少年时期所生活的潘氏庄园建于高坡之上,庄园内就有一片橘园,面对着翟溪的青山翠林。这片伴随琦君生长十二年的风景已深深烙印于她的脑海,所以她才能在小说开篇以寥寥数笔就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人物生活的环境——“抬头望远处,红日衔山,天边一抹金红,把一树树的橘子都照亮了”。橘子不仅是琦君寄托乡愁的意象,也寓意着秀芬在大伯家中的命运,秀芬尚未来到大伯家时,橘子是青的,来到大伯家后,在等待中橘子一天天长大、变黄,橘子红了时,大伯回来了,秀芬与大伯圆了房,已是一颗“熟透的橘子”,但此时秀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她被大伯“尝了一口”就丢掉,最终腐烂在泥土里。
小说中诸如“迎娶秀芬”“观音殿求子”等情节充满了浓郁的温州地方民俗色彩。温州靠海,迷信盛行,自古便有“尚巫渎祀”之风,群众大多敬神好佛。小说中秀芬来到大伯家第二天清早便被大妈嘱咐要“先拜灶神,再拜祖先”,大妈在碟子中分别摆上带壳的花生、红枣、桂圆、柿子和梨子,寓意“利市利市(即大吉大利),早生贵子”;大伯归来与秀芬拜堂入洞房前须先拜祖先、放鞭炮(温州人称“百子炮”寓意“百子千孙”)都体现出温州人这一特点。此外,琦君还将温州方言用于文章的叙述中,如将长不大的青橘子称为“痨丁橘”(“痨丁”在温州话中是骂小孩子长不大),在数橘子时以“双”为单位(温州人喜欢用“对”为量词,一支笔被称为“一把笔”),进一步加深了小说的乡土气息。
琦君自小生长于瓯越之地的大户人家,一方面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另一方面又受到永嘉地区“事功之学”的影响,这使得她“能够很好地协调情与爱、礼与理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转化融通,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超物性灵出世带来的精神逍遥,又有面对现实现世的人世生活姿态”④,因此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奇妙的“节制感”。秀芬与六叔是小学同学,她小时候就对六叔萌生了情愫,但重逢时两人已成为叔嫂,因此不得不克制情感。六叔在橘园中递给秀芬梨子并说“不要分离”,以此表达他的情意,若按一般家族小说的模式,此后故事的发展无非两种:一是两人的情感逐渐升温,不顾世俗礼教压迫在一起;一是六叔知难而退黯然离开,从此消失在秀芬的生命中。但琦君既没有通过其他情节去增加他们之间情感的浓度和热度,也没有让六叔从此消失。在六叔离开、大伯回家的这段时间里,秀芬很快将自己的视线转移到大伯身上。秀芬对大伯有种世俗的感情,她觉得“躺在他被窝里,就像躲在一个没有风、没有雨的山洞里,暖和又安心”,她只有在大伯疏远她的时候才会想念起六叔,只在让秀娟写信劝六叔回乡玩玩时主动提起过六叔,因为她知道“女人家的命就捏在男人手里”。她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与大伯圆房后,“一心一意的等生孩子”,“等孩子长大了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但这并不意味着秀芬对六叔感情的结束,直到小说末尾,琦君才通过秀娟的视角发现了秀芬珍藏着六叔送她的笔记本和绣好却迟迟不敢送出去的香袋,使读者清晰地察觉到秀芬对六叔深埋于心的感情——这份感情更注重精神和伦理的完善,“牺牲了肉的欲望而保全了灵的圣洁”⑤。
二、母亲。琦君四岁时被伯父潘鉴宗和伯母叶梦得收养,伯父因公务繁忙,无暇照料关怀琦君,纳妾后对她更是疏远,好在伯母待琦君视如己出。伯母勤劳、善良、慈爱、能干、敬重依顺丈夫,是个温良谦恭的旧式妇女,虽然遭受了失去爱情的痛苦和煎熬,却格外关爱琦君。这种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使得母亲(即伯母)成为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源泉。在琦君谈及《橘子红了》创作原由时提到的“纪念逝世的亲人长辈”,让“敬爱的亲人长辈刻骨铭心的创痛、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为“世人所知”所指的应就是伯母的遭遇。琦君为母亲鸣不平,但并未单纯地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指责伯父,而是用隐而不露的曲笔,把旧社会中妇女被丈夫抛弃、默默承受痛苦屈辱以至于情感扭曲而麻木写得入木三分。《橘子红了》中的大妈正是这种叙述策略下的典型形象。
在琦君的笔下,大妈“讲话斯斯文文,心地厚道,待人和气”,慈爱,勤劳,但就是这个“豆腐心肠”的大好人却做出了最残酷自私的事。她因自己无法生育,主动替丈夫纳妾,希望以孩子为砝码把丈夫从二姨太身边夺过来。她将自己的“匮乏”转移到秀芬身上,说起秀芬时“好像自己在收个干女儿,或是讨个儿媳妇,一脸的欢乐”,疼爱秀芬“跟疼女儿一般”,但秀芬的身体在她眼中不过是自己被“阉割”的生育功能的替代品,她所有的举动只是企望重塑这个女人而已,其实质是通过拒绝,承认自己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的现实,以此获得幻想中“丈夫回到身边”的满足。“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弃妇还不算,又拉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跟她陪葬。”⑥大妈表面关爱下所隐藏的一己之私造成了秀芬心灵和肉体上的双重戕害,“妻以夫纲”的封建思想使大妈充当着男权统治的代言人,企图让秀芬臣服于父亲的律法之下,间接造成了秀芬的死亡:一方面,她对秀芬进行“催眠”,使得这个十八岁的少女将生孩子当作人生的希望与寄托,孩子没了,自然会万念俱灰,走向死亡;另一方面,若不是她渲染二姨太的敌意造成的恐惧,秀芬也不会踏上出走这条生命的不归路。
小说中更为完整意义上的“受虐者”秀芬是另一层面上的母亲,是“好几个旧时代苦命女孩子的糅合”,体现了理想中的传统女性“自我牺牲”的品格。但这种“自我牺牲”因结局惨淡而被定义为“受虐”,是“返求回到主体自身的自我之上的施虐”,将外在的遭受痛苦的客体内化,使其转向自身去“侵略自己”。秀芬经历的残酷与牺牲具有明显的“侵略性”: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在家遭遇同父异母哥哥的冷眼,定亲不久新郎便得痢疾死了,她成了望门寡,被大妈用五百银元礼金买来给像父亲一般老的男人做偏房,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与六叔心心相印,但“无可奈何”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与大伯圆房后一度燃起生活的希望,却备受冷落,怀孕后以为可以用孩子唤回大伯,却在二姨太威胁下惊惧出走导致了流产,在悲病交加中郁郁而终。她对于自身“命运”毫不抵抗、逆来顺受的态度强化了这种“侵略性”。这种“侵略性”植根于秀芬的“大户人家的男人总是好的,做小有什么要紧”的对平安夫妻生活的幻想之中,而大妈的关怀成为她不惜“自我牺牲”的支撑,直到临终前她说“他不会再回来的,我也等不了他”时,这份幻想才真正破灭。值得一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秀芬并没有死,在大伯逝世后她被逐出家门,流落他乡,受尽折磨。琦君不忍心她在“幻想”的“自我侵略”中孤单挣扎几十年,选择给她一个“一了百了”的结局,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与此同时,秀芬之死既未唤回大伯,也未使大妈对自己的命运有所觉醒,这样的结局更加发人深省。
三、结语。琦君的故土记忆中重复着一幕悲剧:“男权思想统治下女人所忍受的苦痛是悲哀的,然而他们却把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和伤痛的责任归于女人本身,并把苦痛不断转移,不断复制,世世代代相传。”⑦“这究竟是谁的过错?难道真是先生所说的,前生定数的吗?还是她命苦,不该生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时代呢?”关于秀芬之死,琦君在小说末尾连用三个问句,但并未给出自己的答案。如果单纯以女性主义批评视角,通过将“母亲”置于与丈夫或家庭的对立面以获得女性被压迫、被屈辱的主题内涵来观照这部作品则有些片面。骨子中的悲观气质和少时的佛学熏陶使得琦君不愿也不擅长剖析挖掘这种现象之后的深刻意蕴和人的内心世界,而是将此消融在对于故土的风物、习俗津津乐道的散文化描述中。这不得不说是琦君小说创作的一大遗憾。
① 章方松:《琦君的文学世界》,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② 沈苇:《尴尬的地域性》,《文学报》2007年3月15日。
③⑤ 李源:《一个寂寞的歌人——论琦君的创作》,《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④ 陈力君:《低吟慢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琦君的文学世界》,吴秀明:《中文学术前沿》(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 白先勇:《明星咖啡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⑦ 孙良好、李沛芳:《追忆·怀乡·闺怨——关于琦君的〈橘子红了〉》,《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