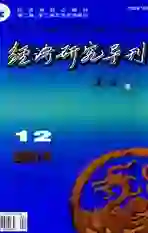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批判的双重维度及其启示
2014-07-11王丹
王丹
摘 要: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西方近代人权观的法哲学批判,指出了人权的历史性;通过对资产阶级人权实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揭示了人权的具体性。人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应然性与实然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
关键词:人权;批判;人性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2-0256-04
西方近代人权观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或神话学的。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理论本质上则是人权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的批判理论,或是作为批判形态的人权理论。因此,正确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批判理论,对于我们以辩证的态度看待人权问题,有着许多启示。
一、对近代人权观的法哲学批判
作为批判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观,首先是要对西方近代人权观进行法哲学批判,彻底颠覆近代人权观的形而上学基础,消解西方近代观所宣扬的“普遍的”、“永恒的”人权的神话,把人权从抽象形态还原为历史形态。西方近代人权观,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抑或是卢梭的人权观,都始终没有离开过形而上学的根基。之所以这样来指证西方近代人权观,主要原因在于,西方近代人权观离开人权的现实基础,只是抽象地、形式地探讨人权问题,在现实的经济基础之外去探究人权的终极依据,把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权利抽象化为“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把特定历史阶段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暂时的历史权利抽象化为“永恒的权利”,把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权利抽象化为“普遍的人权”,最终陷入人权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这种人权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在理论上表现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二是把人作为抽象的、孤立的人去对待,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构建人权概念。
针对西方近代人权观本质上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的第一个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1]然而,由理性所构造正义、平等和人权只是虚幻的神话,在恩格斯看来,“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1]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在人权问题上所受到的时代限制,马克思同样在《莱茵报》时期也遇到过,即他所说的“苦恼的疑问”,也就是理性和现实的矛盾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要彻底化解这一矛盾关系,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意识和生活的关系,是意识决定生活,还是生活决定意识;二是作为理性、意识的产物和形式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中所讲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抽象的人,抑或是现实的人。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那么,生活如何决定意识?他们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为作为“意识”、“观念”的人权观找到了赖于产生和存在的物质生活基础。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彻底颠覆西方近代人权观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基础的革命性变革。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同如何解决西方近代人权观本质上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的第二个特征的问题是一致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肯定了“生活决定意识”这种考察方法的同时,紧接着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因此,在他们看来,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条件出发来考察人,就不能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只能是“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又把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具体化为经济关系。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社会关系的产物”[3]。这就是说,作为社会性的人,他的基本权利总是要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凌驾于一定的经济关系之上。而从抽象的人和抽象人性论出发来构建其人权观念,是西方近代人权观本质上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又一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脱离人的社会性抽象地谈论人性和人的自然权利。与抽象的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被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以及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统统都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宾逊故事的错觉。
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从资产阶级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说明西方近代人权观的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指出了人权的历史性。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指出:“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批判关于人权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比黑格尔更有批判性的言论的。”[4]这里,他们引用黑格尔的话,意指人权问题和人权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人权问题和人权概念不是没有产生的过程的,并不是全盘否定“天赋人权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作为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成员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这一基本人权的出现是在人的古老的、自发的平等观念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封建统治者的阶级特权,给商品所有者能够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 [4]endprint
马克思在反对近代西方启蒙学者脱离人的社会性抽象地谈论人性和人的自然权利的同时,又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限度。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马克思首先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历史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5]但他同时又认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结果的人权,虽然摆脱了封建专制和特权等级,但深深打上了政治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烙印。因此,资本主义政治解放是有限度性的。他认为,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5]。
二、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批判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在颠倒西方近代人权观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基础的同时,又对资产阶级人权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把对西方近代人权观的批判性分析进一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联系起来,揭示了人权的具体性。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活动出发来说明西方近代人权观的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指出了资产阶级人权的具体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如何生产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之后,指出:“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他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也讲道:“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6]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在18世纪,资产阶级说理解的解放,即竞争,就是给个人开辟比较自由的发展的新活动场所的唯一可能的方式。”[7]
第二,马克思从特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界定资产阶级人权观中的“人”。马克思在考察有关“人权宣言”的文件时,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权宣言”所理解的“人”的实际内涵。他指出:“人权之作为人权时和公民权不同的。和公民不同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5]把“人权”中的“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是马克思对“人权宣言”关于人权主体的理解的一种还原。然而,“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作‘人,只是称作‘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作人权呢?”[5]马克思认为,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直接与政治解放及其所造成的人的二元化发展有关。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5]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政治解放时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5]这也就是说,政治解放在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的同时,又使人获得了国家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地位,人从这种公民地位中获得了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权利。然而,人获得了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则意味着对等级和特权的否定,它使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彼此进行平等的竞争成为了可能。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出发来揭露了资产阶级人权观的狭隘性,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人权只是形式上的,而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所谓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权只是形式上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谋求自己私利的道德幌子。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7]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交换还体现着一定程度的自由、平等的话,那么一旦他们离开流通领域而进入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8]平等就转化为实质上的不平等,即“平等地剥削劳动力”;“自由这一人权的运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正是基于对资产阶级人权本质的这种认识,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7]他强调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要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真正的“人的权利”,“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2]而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只有“否定私有财产”[2]。但是,在他们看来,对私有财产的废除不能“同这种废除本身的条件分离开来”,“如果把废除私有财产置于同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之外,只是把它视为蛰居者的臆想,那么,这种废除就成了纯粹的空谈。”[2]
三、对如何认知人权问题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近代人权观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法哲学批判和资产阶级人权实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知人权问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论争是当代国际人权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人权观坚持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天赋人权论,认为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表现为自由、平等、生命权、财产权。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即自然赋予的,都是不可剥夺的、不可转让的。因此,在他们看来,人权的内容和标准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这种人权理论被称为普遍的人权理论,或称普世主义的人权观。当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到西方普世主义的人权观的责难时,他们一方面承认人权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强调人权又有特殊性。1993年代表发展中国家人权观的《曼谷宣言》指出:尽管人权具有普遍性,但应铭记各国和各地区的情况各有特点,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应根据国际准则不断重订的过程来看待人权。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已经指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但是,否认资产阶级人权是普遍的人权,并不是否认人权的普遍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联结而存在,而特殊性总是要表现普遍性。相对于人权的特殊性而言,人权的普遍性表现为人权主体、人权内容和人权价值目标的普遍性。然而,人权的普遍性要求一旦要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时候,它就必然会化为特殊的东西,表现为不同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历史文化背景、一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条件下的具体性。endprint
第二,人权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人权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应然性。他们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反对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反对将权利诉诸神性,而主张诉诸人性,并从人性中引申出自由、平等的人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1]这便是近代人权要求或应然意义上的人权概念的由来。然而,这种近代人权要求从一开始还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表现为封建的等级特权被打到了,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权却被合法化了,无产阶级却被排除在了“人权”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和人权制度的批判,以及要求无产阶级要实现人类解放就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真正的“人的权利”,正是表明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批判的不是应然的人权,而是实然的人权。他们对无产阶级人权理想,即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及其实现条件的阐述,也表明了人权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
第三,人权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5],而人权实质上就是保证人们具有参与自由竞争的资格的权利。马克思在转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政治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这一观点后,他揭露其实质时说:“这里所说的人的自由,是作为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5] 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权的观念是建立在个体性的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则是在肯定人的自由个性的前提下更注重自由的个人的联合,把个体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集体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人权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有机统一。
第四,人权是形式性与实质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必然要求的普遍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必然带来的阶级对立和压迫之间的矛盾出发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人权只是形式上的,而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对此,恩格斯有过评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因此,人权,虽然曾经是或依然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但由于历史辩证法的作用,资产阶级人权必然会被“扬弃”为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的人权。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这里,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的人权不仅包括政治上的平等等形式方面的内容,而且包括社会、经济上的平等等实质方面的内容,它所要求的是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而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这样,无产阶级人权内容从政治和公民权利拓展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利。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5-448.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21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10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5-146.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9-44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8-480.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0.
Abstract:By reversing the metaphysical base of the modern viewpoin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west,Marxism points out that the human rights has its history,by politico-economical analyzing viewpoint of human rights of the bourgeoisie,Marxism exposes its concrete character,and by negating the opportunistic and utopian socialist viewpoint of human rights,Marxism emphasize on the realities of the theory of human rights.Human rights shall be the unity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between ideality and positivity,and between sociality and individuality.
Key words:human rights;critic;human nature
[责任编辑 吴 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