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绘画中的“理趣”观
2014-07-01奚林元
奚林元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1231)
论两宋绘画中的“理趣”观
奚林元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1231)
两宋时期,山水画不满足于景物本身真实的显现,而是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认知思维,向事物内在的“性理”开掘。纵观宋代山水、花鸟,可以发现“理趣”成为这一时代主要的审美倾向。
宋代绘画;理趣观;画学研究
朱良志先生在《扁舟一叶——理学与中国画学研究》一书中专列章节对“理趣”进行详细论述。他认为:画学中的“理趣”说最主要的根源来自新儒学。事实上的确如此,自理学之祖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对宇宙本体进行探讨始,后世理学家普遍认为:万物皆有理也。因此对于事物的认识就不能仅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还要深入挖掘其存在的根据。即“理”的发现才是根本。如张载曰:“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语录》中)。程颢、程颐以“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程颐曰:“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程氏遗书》卷十八)。“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令。……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更是认为天下无一物不具“理”。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由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语类》卷一)。又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的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语类》卷十五)。
由上述可见:理学大师们都主张对万事万物深究其理。具体途径乃为“格物致知”。“格物”与“致知”本是《礼记·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时,提出的“致知在格物”之说。但并未对其进行解释。后程氏兄弟,把它与《易传》中的“穷理尽兴”结合起来给以新的阐释。曰:“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1]。后朱氏承续程子之意,把“格物”解为“即物而穷其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很显然,他们都强调主体达到“致知”的境界乃是以对“外物”之理的穷尽为前提。但是,我们应注意的是:这种认知方式有别于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因为理学家们在根源处承认“物物有理,万理相通”的“天人一体”的哲学观念。所以,“格物”论的根本意旨乃在于发明本心。程颐认为:人心常常因为欲望的遮蔽,难以发现天理,而即物就是“去蔽”明理的途径。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2]。又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3]。
但正如朱良志先生所指出的:“我们不能说北宋写实之风就是在‘格物致知’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尊重绘画自身发展的逻辑,绘画史毕竟不是思想史,当黄筌之辈在细审物理之时,宋代的理学还未形成。但是这一理论在加强宋代的写实画风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4]。绘画史表明:神宗熙宁时期,山水画与花鸟画开始从五代至北宋初年的着重外在形似转向对事物内在性理的探讨,而此期新儒学有关性、理之学也恰好形成。张载于熙宁九年时,在他的《正蒙》中确立了“穷理尽性”的学说,程颐也在熙宁初年形成自己的理学体系。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理学对画学及实践产生影响的结果。而事物性理的发掘,必然有赖于审美主体意识的发扬。
从山水画方面来看,如果说李成、范宽的作品还重在“以物观物”的话,那么,神宗画院代表郭熙则开始注重在心性上讨生活了。“境界已熟,心手相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将就,率意触情,草草便得”[5]。郭氏不再以景物本身为旨归了,而以“心与物合”的“境界”为其创作之源了。因此,郭熙尤重审美心胸的涵养。“今执笔者,所养之不扩充,所览之不淳熟,所经之不众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纸拂壁,水墨邃下,不知何以掇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溪山之颠哉?”[6]
显然,他强调了创作主体“内有”在兴发中的重要作用。从其传世作品亦可看出与北宋李成、范宽意旨的区别。范宽《溪山行旅图》采取“高远”透视法则,把高山雄伟的气势、浑厚的质感刻划得近物逼真。李成则擅长于“平远寒林”的意境中取胜。尽管现已无他的真迹存世,但从北宋时期的一些近似风格的作品中仍可看出一斑。如《寒林平野图》、《读碑窠石图》。王诜认为李成山水“墨润而笔精,烟岚轻动,如对面千里,秀气可掬”。《图画见闻志》曰:“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峰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李成惜墨如金,善于从杂多纷繁的景场中概括出洗练的形象、“淡远荒寒”的境界。但是,当我们翻检到郭熙的画迹时,会发现无论是“文李”还是“范武”“观物取象”的方式都还太执着于物象本身的真实。亦即是说:它们并未从根本面貌上对五代以来的画风进行改变,至到郭熙出才使山水画达成“可居”、“可游”的艺术世界。如《早春图》这一经典名作营造了一个咋暖还寒时的早春景象。但是它不再仅以对象本身的“形理”相似为目标,而明显地融入了作者对“早春”生意的感受。在画法上,作者采用了以“实写虚”的方式,使读者能够在盘桓远逝的山峦中返现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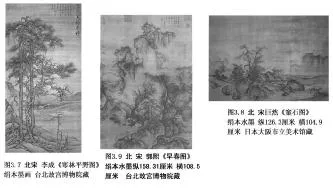
郭氏在画论领域提出的“高远”、“深远”、“平远”之境,核心在于“远”。“远”则使物我的对象性思维得以消解,“不以目见,而以神遇”,从而反观内心的真实意境。“意境”论早萌芽于六朝,兴起于唐代,但却成熟于宋代。就绘画而论,郭熙的山水画与同期的崔白等人的花鸟画突出了这一历史转型。《宣和画谱》曰:“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击取。自崔白、崔悫、吴元瑜出,其格遂大变”(卷十五《黄居寀》条)。“格变”体现在“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当崔白的《双喜图》与黄筌的《写生珍禽图》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可以发现“生机意趣”与“类同死物”的区别。另外,传世的《寒雀图》、《竹鸥图》也是崔白的作品,它 寀们在用笔上率意粗劲,与黄居的《山鹧棘雀图》相比,一动一静、一豪放一工致,两者的差异是极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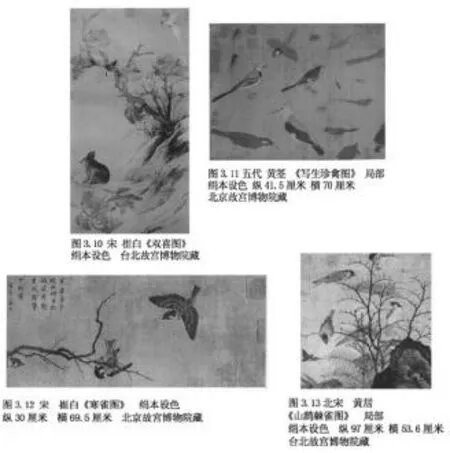
郑午昌先生在《中国画学全史》中早已指出:“宋人善画,要以一‘理’字为主。是殆受理学之暗示。惟其讲理,故尚真;惟尚真,故重活;而气韵生动,机趣活泼之说,遂视为图画之玉律。卒以形成宋代讲神趣而仍不失物理之画风”。用画史的具体实例可以印证这段话的确很中肯。宋代是“重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兴盛期,但是艺术家们很善于吸收其学说的合理内核,成功地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上完成了主体能动作用的推进。蜀学代表苏轼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践活动中提出的“士夫画”理论,对宋代的“传神”、“写意”精神客观上起到了发扬光大的作用。从主观上来讲,与郭熙的山水、崔白的花鸟一样,都是为了反对神宗时期画坛上陈陈相因的画风,以及由于商品化大量出现的劣质作品。但当时工笔写实画法尚有发展余地,苏轼的诗、文、理论又遭到禁遇,故苏氏、米芾提出的“士夫画”在北宋并没有大的发展,经南宋的过渡,到元代才发展成占画坛主流的文人画。
综上所述,自北宋神宗熙宁以来,绘画深受理学“性理”学说的影响,院体画一反传统旧的“体物”观念,开始由面对事物本事向“物我双致意”的思维模式转变。在实践上,出现了一大批注重“物理人性”巧妙结合的、具有平淡远逸画风的山水花鸟作品。以苏轼为核心的“士夫画”集团,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文人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基础。南宋时期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院体倾向于“以小见大”的布局,引发人们对无限宇宙之理的沉思,正是继北宋中后期审美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产物。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两宋的绘画真实观虽较唐人带有更多的“人性”意味,但也同时具有明确的“我思”认知成分。这体现在创作者用已有的知识去映照自然本身。一是先验的道德理性观念。朱良志先生指出:“宋代花鸟画为何获得突出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皇家提倡),但是最根本的则是思想观念的原因,追求花鸟画中的‘道德理性的趣味’是潜藏在画家心目中的不言之秘,他们普遍重视花鸟为人的道德品格的象征”[7]。
二是既定的“格法”。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曰:“若不从古画法,只写真山,不分远近浅深,乃图经也,焉得其格法气韵哉?凡画有八格:石老而润,水净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云烟出没,野径迂回,松偃龙蛇,竹藏风雨也”[8]。
以上两种“观物”方式,一方面透显出主体意识的增强,不满足景物外在的形色神韵,企冀发掘事物的内在性理,另一方面都必然不能使物我的生命本真得以契合,只会使自然万物在主体意识的灌透下出现伪装的面目。这显然有违于艺术自身的规律。
[注 释]
[1]《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97.
[2]《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3.
[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6.
[4]朱良志.扁舟一叶——理学与中国画学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60.
[5]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112.
[6]同上,113页。
[7]朱良志.扁舟一叶——理学与中国画学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11.
[8]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138.
J205
A
1671-5136(2014)01-0134-02
2014-01-05
奚林元(1959—),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与设计教育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