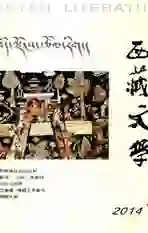我曾经是个猎手
2014-06-20扎西尼玛
扎西尼玛
我年轻的时候,是我们那一带人人称羡的猎手。记得在很小的时候练习弹弓,14岁的时候练习弩弓。17岁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有机会接触到各式步枪了。最先是火绳枪,然后是中正式步枪和三0步枪(外号大鼻子)、英国大十响、半自动步枪,还有一种叫“日本加酷”的狙击步枪。我跟枪很有缘,枪法似乎也是禀赋,放出的每一枪八九不离十都可以击中目标,很少浪费子弹,自夸一点么是百步穿杨的功夫,被人们成为“神枪手”。因为对枪的酷爱,在我担任大队(现为村委会)民兵营长期间,我还学过射击理论。在射击实践中掌握了独到的射击目测、射击速度、仰射、俯射的方法。我还养过一条猎犬,悟性极高,每次在猎场上都能准确地知道我的想法,配合得非常默契。啧啧,造孽呀,我捕杀过的野生动物大大小小500多头只了,有黑熊、马鹿、獐子、岩羊、野兔,还有各种野鸡,嗡嘛呢叭咪吽……那时候,我真没有宗教观念的束缚,心里没有涂炭生灵的罪恶感,还认为不让一个猎物从自己手中逃脱就是一个好猎手,一个有高超狩猎本领就是一个好男儿。真是放肆得无法无天啦,脑子里只有打猎,似乎打猎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那时候,每到周末,就邀约几个要好的朋友背上枪,带上足够的弹药钻进山里。天啊,卡瓦格博神山一带都打过,甚至还跑到西藏的芒康、左贡、波密、八宿、贡觉去打。在卡瓦格博神山地区,年少无知的我,竟然在圣地里的规堆(莲花寺)、规缅(太子庙)杀生。罪过啊,规缅庙下面有个叫射击场的地方,那是一座藏在茂密树林里的巨大岩石,当时明永冰川的冰舌刚好就在这个位置。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黑熊啦、獐子啦、岩羊啦这些动物就会跑到这里饮水。我就藏在岩石下面的林子里大肆杀戮。斯农河沿岸原来獐子很多,下游地带的獐子都被我斩尽杀绝了。我打猎打的最凶的时候是在1970年代,进入1980年后因为工作变得繁重多了,不可以像以前那么“枪不离身”了,猎瘾还是时时发作,啊啧啧,人管不住自己的心哪,是太可怕啰,一有空闲的时候,我们还是上山照打不误。老天有眼,1986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把我从疯狂的造孽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归人心。
1986年春节初五那天,按照习俗,我们村所有的男性都到“布拉亚”山头的敬香台焚香酬祭山神。祭山时,先要用香柏叶燃起浓烟,撒上五谷,点上净水,高诵焚香文,放枪,鸣炮,高声呼喊,感谢山神的荫庇佑护,给山神助威加油,把福气召回村子。然后大家坐成一圈,边吃喝,边说笑。吃喝好后,除了幼小的孩子外,成年男子都要按年龄大小一次出场“笔协”(称为刀赞,赞颂山神、给山神助威,也有娱神的意思)。轮到我时,我突然感觉到空中旋下来一口大钟,把我吸进钟内,身上的力量都被吸走了,只觉得全身绵软无力,对周围的事情完全失去了知觉。大家以为我喝醉酒了,既不吃,也不说话。等我稍微缓过神来的时候,人们已经下山了,我的两个儿子也已经跟着大伙走了。我想站起来,可是下身好像瘫痪了。很奇怪,当时心里没有惧怕的感觉。我就双手撑地一点一点往山下挪。过一会儿,身子能够站起来了,我就慢慢走下山。到山脚的时候,人们已经等在那里。我就走到人群中间,拔出腰间的长刀,唱起刀赞词:“呀卡热几安呢给阔热几噻,今天太阳圆圆,今夜月儿圆圆,今天咱们村庄圆圆。我们布村人今天不团圆何时才团圆。”人们这才发现,我行为有些异常,但没有太在意。回到村里的时候,人们没有散去,聚到米玛家。这时我看见天空中走来一队人马,人们背上插着花花绿绿的令旗,快要降到米玛家屋顶的时候,突然从屋顶上腾起一团蓝烟,这队人马立即掉头回去了,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虚空里。那时我们村里只有两个人会吸香烟,我走进米玛家屋子里的时候,他俩正在大口大口地吸烟,嘴里吐出一团团烟雾。我上去抓住他俩的衣襟说:“今天是喜庆的日子,阿尼(爷爷)卡瓦格博神带着部众和眷属本来要到咱们村里做客,人神共乐的时机千载难逢,结果被你俩的毒烟给熏跑啦,你俩既然这么喜欢抽烟,干脆把烟吃掉。”我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香烟盒揉碎了,往他俩嘴里塞。我又看见米玛家的神龛上供着塑料做的花、苹果、桃子等摆设,就对他们家人说,应该把自产的果品做供品,如此假模假样没有诚心,真是不懂规矩,这样会亵渎神灵的。这时,人们才发现我已经疯掉了。好多人送我回家。路上,我看见长在村里的两颗古柏树在玩命似地打架,噼噼啪啪,不可开交。金雕、乌鸦和蜜蜂在中间劝架。回到家里,屋里突然冲进来好多动物,有黑熊、马鹿、獐子、山驴、岩羊,像滚滚洪流一般把屋子塞满了。都是我在“赞日”(赞即厉神之一种,赞日即赞神寄身的山)上猎杀的动物。它们或龇牙咧嘴,或瞪着红红的眼睛,朝我扑过来,用犄角顶撞过来,我拼命避让,撞到板壁上,被板壁堵住,我挥拳打去,先后打倒了三面板壁。它们还在拼命追杀,我下意识地用心向卡瓦格博山神求救:“阿尼卡瓦格博,求你救救我吧!”这时,从卡瓦格博晶莹的山峰中走出白色一人一骑,那汉子英俊威武,左腰佩宝剑,右腰挂着箭囊,腾云驾雾来到我家屋顶,说到:“都回去吧。”那些动物听到号令,纷纷掉头出去了。之后我昏迷了三天,醒过来后老听见一个声音在一个辨不清方向的地方对我说:“以后再不要打猎啦,把你的猎犬丢到江里,要不然它到别人手里,还是照样要杀生呢。”我就照着做,我的疯狂就减轻了一些。后来,我供职的单位派车把我送进医院。之前,单位来接过两次,村里的老人都以不适合送医院治疗为由拒绝了。我住院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睡过去三天,醒来后病就好了。我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打的是什么针水,听说那个针水很贵。
其实在1985年连续发生过三件很奇怪的事。后来才想到那是劝告提醒啊。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5年。记得那天是藏历四月十日,我和马席、扎史都居(他俩已经去世)、培楚去明永山上打猎。我们第一天走到规缅(太子庙),晚上就住在那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出发继续上山,到规堆(莲花寺)的时候坐下来休息。我们发现敬香台旁边的古冷杉树下放着一个皮箱子,用铜锁锁着。马席说打开看看,我说,最好不要动,可能是收藏箱子的这户人家遭遇什么灾难,就把箱子(主要是箱子里面的物品)送回来了(当地民间有这样的观念:私自收藏寺庙的法器和物品,会招致人畜生病,甚至亡命,运气不顺、做事不利。)我们又往上爬了大约两百多米,这时太阳光刚好照到敬香台旁边那棵古冷杉树的树梢,树梢上冒出一股青烟,螺旋式地往天空中直直升去。我对三个伙伴说:看,那棵树上烧起香啦。他们也清清楚楚看见了,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马席说,我去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于是他跑下去看,周围没有一个人,敬香台的炉膛里也是空空的,他觉得蹊跷,还找来树枝掏炉膛,可是除了一层薄薄的冷灰,什么也没有。他还爬到树上看究竟,结果什么烧火点烟的痕迹也没有。他纳闷了,摸着脑门说:“看来卡瓦格博山神是真的存在啦,既没来过人,也没有烧火的痕迹,敬香台也没来过人。”我心里觉得不对劲,可又说不清楚,但还是对伙伴们说,今天不要去打了,咱们还是回去吧。马席有点不高兴了,大声叫起来:“那怎么成?那怎么成?咱们这次出来就是打猎来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马席的脾气我是很清楚的,只要认定的事情要让他改变主意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我就不再跟他争执。我们沿一条陡峭的山脊往上爬去。前面树林里到处都是铁丝扣子,也不知是什么人放的。我和马席每人养着一条猎犬,我的猎犬叫松格,全身白毛,能嗅出金属味,他的猎犬叫通纳,全身黑油油的。刚走几步,通纳就被铁丝扣套住了后腿。马席觉得触上了霉头,很晦气,就随手抄起拄杖用的木棍往通纳身上一阵猛打,通纳凄惨地尖叫起来。这时眼前突然变得昏暗,抬头发现天阴下来了。再往上的路上,地上有密密麻麻的野兽的足印。可奇怪的是,平常一嗅到野兽足迹就亢奋不已的松格和通纳此时却耷拉着耳朵,根本就没有追寻猎物的心思,像两条看家狗似地在我们脚边东躲西藏。天空开始飘起细雨,越往上走雨点越来越大。我们只得赶紧爬到山腰的石板屋里住下来休息。那天晚餐煮的是米饭,水刚涨开,马席就往里倒进去半斤核桃油,结果米饭怎么也煮不熟。没办法,我们只得将就着吃,结果大家都闹起肚子,又拉又吐,脑袋昏昏沉沉,全身像面条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第二天,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翻过山梁,走到斯农山头。扎史都居是斯农人,这次出猎也是听从了他的建议,他说斯农这边的这个山头上岩羊很多。我们倒是看到了数不清的岩羊踩下的蹄印,可是连岩羊的影子都没见着。那天起大雾,我们走迷了路,摸摸索索走到了一处悬崖边上。所幸还是找到了一串山驴的蹄迹,循迹走一阵后找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攀着树藤下到崖脚。我们第一次意外地空手而归。
接下来的第二件事发生在藏历七月十五日。我的侄子吾堆约我去打猎,这次出猎的目标是我们村北面的一个山上。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拍扎山头时,太阳也出来了。拍扎山头刚好在卡瓦格博峰的正对面。因为夜里下过雨,拍扎山头和卡瓦格博峰之间架着云桥,大团大团的白色雾气从谷底往山头升腾。我正陶醉在这如梦似幻的美景中,突然听见吾堆惊叫起来:“看,有人!有人!”我循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距我头顶约150米的空中,云层洞开直径大约15米的洞,洞的内沿镶着鲜亮的光环,洞中真有一个人影。我还没琢磨过来,吾堆又惊叫起来:“二叔,你仔细看看,那是你,真的是你!”我定睛一看,连自己也吓了一跳,真的是我,我的上半身,看得真真切切,身上背着枪,穿着翻过来的山驴皮缝制的皮衣,清清楚楚的黑白相。我一下子感觉浑身发热发汗,隐隐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妙,就放弃了打猎的念头。我们到一个岩洞里坐下来休息,我对吾堆说:“这事儿千万不要声张出去,家里人也不要讲。”我还告诉他,我要写信给国家科学院,请求科学家的解释。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守住口风,跟他家里人讲了。这事儿就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我妻子心里很不安,就去找红坡村的“莫玛”(女性通灵者)求卦。莫玛刚从雨崩圣地朝拜回来,住在离我们村很近的荣中村。莫玛说:“吆,这人虽然造很多孽业,可还是禀性不错啊。这个景象是一次难得的开示呀!山上的动物都是卡瓦格博的穹吹(山神的家畜),如果再不收手,可要丢掉性命哦。如果此刻能够洗手不干,还可能换回很好的福分,与善业结缘。”我终究没有相信莫玛的话。怀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找到当时在县检察院工作的好朋友取扎,和他商量后请他的同事多吉代笔给中国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请求解释。三个月后,我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回信,大意是说这种情形可能是空气和阳光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的作用而产生的自然现象,这种自然现象叫做“海市蜃楼”,过去四川峨眉山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民间传说有这种经历的人可以获得好运气。当时我认为相信科学家的解释没有错,原来心里的那一丝不安又烟消云散了。
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终于醒悟过来,涂炭生灵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猎,也不曾产生过想去打猎的念头。
1985年藏历11月初15日那天,我和同村的江初、钟开明去我们山上打猎。到了山头上,我让江初去放狗,我和钟开明坐在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等待猎物出现。两个小时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开始犯困,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也不是完全睡死。我做梦了,梦见在前方150米的山崖上跑下来一个戴着白帽子的男孩,看上去六七岁的样子。那男孩跑到崖脚下就站住了。这时候我醒过来了,正在回想刚才的梦境,突然看见梦里男孩出现的地方跑出来一头山驴,山驴沿着男孩下来的小路跑下来,到崖脚男孩站定的地方不走了。我想,这头山驴必是今天的第一个猎物了,还觉得今天运气不错呢,刚才的梦大概是兆示吧。我就举枪瞄准山驴的头部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一连放了九枪,可是一反常态,居然一枪也没有打中。要在往常的话,这头山驴早就倒地毙命了。然而,更让人惊诧的是,山驴开始变小了,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掉了。我心里立即感到强烈的不安,提枪跑过去看,子弹全部打在石崖上,深深的弹痕清晰可辨。我开始感到害怕,就想山神是真的存在了,我一定触怒了他,我丢掉手中的枪,摘下帽子,朝着卡瓦格博方向跪下,叩头磕拜,向他致敬,并从内心里虔诚忏悔。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