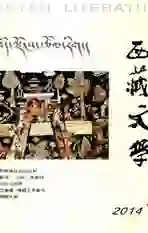人在他乡(短篇小说)
2014-06-20潘新日
潘新日
一
年初三,我和正江一起回到拉萨。
闲下来,正江一个人躲在屋里睡大觉,他说他高山反应很厉害、头痛。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很商业化,一看,就知道是个做生意的小老板,我说我反应不大,我到大街上看美女去,正江说,你爱看就看吧,反正也不花钱养养眼睛。我满脸坏笑地说,我要把拉萨最好看的美女领回来,到时你可不要眼馋哟!
大街上,有很多美女,穿着十分时尚,甚至有的竟穿着短裙,那白晰的大腿。啧啧!我用手扶着眼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女人是什么呢?我在想,是美人鱼,不对;是美女蛇,不对;是勾男人魂的魔鬼。对,我想起在郑州时,我们报社美编张开说的一句话,他是一位漫画家,却没有画一幅美人图,他说他怕女人,怕女人那双勾人的眼睛。勾人的眼睛。女人会勾人么,我看见一个个女人就像一朵朵浪花在人流里漂着,没有人在意我的存在,那匆匆的身影只是眼前风景,看了就会赏心悦目,没有什么留恋的地方。
我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内地女孩向我走来,屁股一扭一扭的,高跟鞋哒哒的响声很有节奏地响着。她的脸蛋很美,虽略施粉黛,却看不出任何修饰,一只大耳环半垂在肩上,皮肤白晰、身体窈窕,绝对的美人。她会去干什么呢?我想,我看着她向我走近,长发飘逸的样子让我的眼神黯然失色,她一步步走近,我甚至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一个少女的香味,我的眼神很直,犹如丢了魂。
我冲她笑笑,她的脸上微微漾起一丝微笑,而后,那香味便淡淡而去。
我目送着这位女孩,一直到她消失到一个胡同里。
夕阳的余辉照在路边的玻璃上,折射的光剌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随着眨动看七彩的星星,我数不清有多少女人从眼前晃走。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我的心情也渐渐暗下来。
我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我明天还去看美女。
二
从作家班毕业,我到报社干了几年记者,听正江说,在拉萨做生意挺赚钱,就跟着正江来到拉萨了。
正江比我大两岁,是我采访时认识的朋友,他老婆开了个印刷厂,闲着没事,他就找我喝酒,洗桑拿,他的洒量不大,却喜欢酒。他说,酒这东西是个好东西,喝醉了就什么也不想了,那种感觉美得很,于是,没事我们就渴酒,喝醉了就说胡话。
正江去年来到拉萨,自己投资办了个板房厂,他说,拉萨是个好地方,生意好做,还好玩,他把我带过来,让我做板房厂的厂长。
不过正江很喜欢他的事业,我却看不上这份工作。
正江很知足。他说,在家里天天闲着没事,还要看老婆的脸色,自己单干了,自己说了算,还自由,他每月给我开五千元的工资,五千块也不少了,除了吃喝还有四千块的节余。他说,人活一辈子,也就是和钱打交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钱多钱少,开心就行。
我住在正江的前排,没事的时候,正江就打电话喊我到他住宅去玩。我在正江床下发现两双女人的高跟鞋,很精致的那种,正江没有掩饰,他弯腰从床下取出这两双鞋,用嘴吹去上面的灰尘,拿出鞋油为鞋子上油,直到把这两双鞋擦得贼亮,才小心地放在地上。
正江说,我们的生意是拉萨的独门生意,都是老客户上门的,我没有反应。眼睛依然盯着那两双闪着亮光的女式高跟鞋。心情十分黯然。
晚上,工布江达县来了一个客户。这个来自四川名叫钱子的客户,在米那山上开矿。他定了几百平方的活动房,合同签订后,正江请钱子喝酒。
喝完酒,钱子非要请我和正江唱歌。
钱子要了一大堆啤酒,每个找了一个小姐,钱子不会唱歌,歌声比狗叫还难听,一曲完了,在场的人还要很违心地鼓掌。
我无心唱歌,就和身边的小姐聊天,小姐很温柔,让我想起在郑州的妻子,我想妻子该休息了,儿子可能还在做作业。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妻子从郑州打来的,我躲进屋角,用手捂着耳朵,妻子的声音很小,她盯嘱我不要喝酒,不要贪玩,要注意身体,我敷衍几句,便挂上电话,又坐到小姐身旁。
正江也不喜欢唱歌。他和那位小姐打得火热。两个人悄悄地说着情话,我找了两颗开心果打过去,骂道:“一对奸人,说什么呢,这么亲近”。正江显然不在乎我的言辞,只冲我笑笑,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依旧含情脉脉地说着话。
不一会儿,下雨了,雨点打在玻璃上,噼噼叭叭直响,稀稀疏疏的雨点摔在玻璃上,流成了一个个歪歪斜斜的人字。
第二天,天晴了,天空像被雨水刚刚冲涮过,湛蓝湛蓝的。
正江说:我还睡我的大头觉。
我说,我是喜欢到大街上看美女。
三
我站在街上看美女,看着看着,心中便不自觉地掠过一丝醋意,感觉自己不该结婚结的太早。
眼前走过一个女人,楚楚动人的女人,不算十分漂亮,却显得特有气质,她袅袅娜娜地从我身边走过,走到一辆丰田轿车旁,熟练地打开车门,车子冒着黑烟消失在人群中。
我目送着小车里的女人,心里暗暗骂道:“妈的,好白菜都让猪拱了”。我猜想,这女人不是富婆,就是别人养的金丝鸟,我的心又开始不平衡,临出门时,我老婆也交待我傍个富婆,现在就我这个吊样,别说傍个富婆,就是扫大街的大姐也不一定看得上,想到这我的脸上不禁挂着一丝苦笑。
这时,我又看见昨天那个少女向我走来,我又闻到从她身上飘出的淡淡的香味,我的心情有些激动。心里砰砰跳个不停。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样子,跟着那位少女拐过一条小胡同,胡同里是一片别墅,别墅围着围墙,大门把守着保安,少女掏出一个白牌牌向保安亮了亮便径直走了进去,我是一个来拉萨打工的文化人,自然没有白牌牌,自然进不去,进不去我不进,就站在大门目送着少女走进别墅。
少女飘进屋里,我的眼神也飘进屋里,一时间我像失去了什么,但我还是记住了她住的别墅的位置。
那栋别墅造型别致,欧式的那种。白色的窗户显得很整洁,上面放着几盆吊兰,长长的茎已经垂了下来,像要出墙的欲望,长长的相思细细地垂着。
眼睛这东西就是无聊,无事了看什么美女,看什么不好啊!在我无意之下,我发现我的双脚已经站在花坛边。闲着没事,可以用双脚量这个花坛有多大么,比看美女有意义,我围着花坛边一步一步地量。一米、两米……走了一圈又一圈,总也量不出准确地数字。
量不准就不量,我开始欣赏花坛里的花,初春的拉萨,高山上覆盖着冰雪,而花坛里的花开的正热闹,五颜六色,好看极了,花坛很大,足有半亩地大。
这时,一名大个子保安,跑过来,大声叫道:“哎、哎、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说,这花坛里的花不是让人看的吗?我在这看花不算犯法吧!
大个子保安说,你像一个贼一样,先是盯着那个女的,盯着她住的别墅,现在,又鬼鬼祟祟的在花坛边溜达来溜达去的,不是来踩点的吧?
我掏出原来的记者证,在大个子保安眼前晃了晃,说,我是记者,想对这个小区进行采访,还有那个少女。
大个子保安狐疑地看着我,嘴里嘟囔道:“那你也没必要在大门前晃来晃去的,像个贼似的。”
有我这么文雅的贼么?我冲他瞪了一下眼睛。
难说,昨天,我们还抓住了一个翻进屋子偷东西的贼,也戴着眼镜,挺斯文的。
大个子保安回到大门边的太阳伞下,用手舞着黑色的橡皮棍,像在和我示威。
我悻悻离开胡同,见四周无人,抬腿照着墙边的电线杆就是一脚,电线杆是不会感觉到疼痛的,我的脚反倒疼起来。
一阵风吹来,墙上的塑料袋和纸片随风飘向天空,慢慢落进别墅里,我的心也随着风飘进别墅,我在想,那个少女究竟是干什么的。
四
我自言自语地说,女人是衣裳,看美女就是看衣裳。
我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这些破衣裳,让我穿还不穿呢!
这时候,我觉得一个大男人无所事事,站在大街上看美女是一件无聊至极的事情。
这时候,我觉得在厂里为正江算算帐也是件有意义的事。
我返身向厂里走去。突然,我的脸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我用手捂着脸,猛然发现一个男孩正端着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我正要发火了,小男孩却转过身跑了。
五
正江的女人来了,就是床下那两双高跟皮鞋的女主人,我认出就是那天陪正江唱歌聊天的女人,我去的时候,正江正躺在床上,那个女人正在卫生间为正江洗内裤和袜子。
正江悠闲地躺在床上,长长的手指夹着香烟。嘴里哼着小曲,见我进来,用手指着床边的凳子说,坐、坐,你到哪去了,刚才,监督局的罗布打来电话让我们晚上一块去吃藏餐,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我这才想起自己出门没带手机。
罗布开着车来接我们,正江的女人在屋子里磨磨蹭蹭不肯出来,正江急了跑到屋子里去喊。
罗布也跟了过来,他推开门,猛地愣住了,坐在正江床上的分明就是她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妖妖。
妖妖也好奇地睁大眼睛,她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正江看出了什么,苦笑着说,原来你们认识啊!
罗布没有吱声,脸色十分难看。
妖妖没有参加晚宴。
正江和罗布都喝了很多酒,两个人都醉了。
妖妖回来的时候,正江正爬在床边吐酒,妖妖找来痰盂接着。
妖妖说,罗布是她第一个情人,那时,她刚从四川来到拉萨,没有工作,没有住的地方,一次在洗木桶浴的时候,妖妖认识了罗布,她们便好上了,妖妖十分感激罗布,罗布也十分爱妖妖。一天妖妖上班回来,看见罗布和另一个女人躺在床上,妖妖一气之下离开了罗布,这么多年了,她一直躲着他,不知是上天的故意安排,还是一种巧合。今天,他们在这种场合相遇,妖妖的泪珠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地落在正江的心上,正江抱住妖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我再次到正江住宅的时候,放在床下的那两双高跟鞋不见了,正江还没起床。
我说,正江,那两双鞋呢?
正江像明白了什么,趴在床下找那两双鞋,可是,那两双鞋确实不见了。
正江起床,赶紧拨妖妖的电话。
妖妖的手机关机了,正江联系不上。
正江开着车到处找妖妖,妖妖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音讯也没有。
正江有点沮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抽闷烟。他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那一个个旋转的烟圈分明就是一个个大写的零字,他自己对自己说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空啊!
我劝正江振作点,别为一个风尘女子垂头丧气,不值。正江一听,大怒道,我不准你这么说妖妖,她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难得的好心的女人。
看着正江认真的样子,我不敢再说什么,悻悻地离开了正江的住室。
路上,我一直在想,就为一个风尘女子值得吗?正江是着了魔了,肯定是。
六
傍晚时分,天上乌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风呼呼地刮着,谁家的衣服被风吹得乱摆,大都是女孩子的衣服,我有心把它们收进屋里,但又害怕别人误会,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那些衣服收进屋里。
雨噼哩叭啦地下着,夹着雪花,我刚要躺下,一阵敲门声把我叫起,我打开门,张开湿淋淋地站在门前,他打了个喷嚏,骂起拉萨这鬼天气。
张开来拉萨三年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报社的同事,联系十分密切。他有一台挖掘机,生意不是太好,这几年运气不佳,还欠了一屁股债,心理不是很平衡。
张开年轻的时候是混黑道的,那时,整个一座县城没有不知道他的,但不知为什么,高考时,他却考上了一所大学的美术专业,让跟着他的一帮弟兄很是不理解。
张开脱下衣服,露出他肚皮上和肩膀上的几道刀疤,我说这都是你年轻时留下的纪念吧?张开苦笑着说,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还不是凡人一个。
张开穿上我的衣服,在屋子里打转,挖掘机没活,他心里很急。一会儿,他的手机响了,是他老婆打来的,是向他要钱的,他说话很冲,火气很大,对方没有了声音。
我不想要我老婆了,但心里很矛盾,张开满脸愁苦。
我现在的这个“老婆”,你见过的,我们一块生活三、四年了,她对我很好,他老公比她大十多岁,她不愿回那个家,愿意跟我过,这几年除了感情我没有给予她什么,还花了她几万块钱,现在我矛盾着呢?
张开眼里含着泪花,又是一个被情所困的家伙。我窃笑起来。
雨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明媚的阳光像久违了的孩子,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张开拿出自己的衣服在门前晾晒,他吹着口哨,灵动的哨声在院子里飘扬,让我想起了江帆。
江帆是我作家班的同学,原来是一家市级文联的专业创作员,虽然是一个女孩,也吹得一嘴好口哨,后来,调到北京一家歌舞团做了一名专业口哨演员,我猛然想起她现在就在拉萨演出,我拨通了她的手机。
江帆正在彩排,听说我也在拉萨,问清我的地址,便匆匆打了辆车来到我的住处。
张开伸出他那双又嫩又白的手和江帆握手,江帆迟疑了一下,把手递过去了。
江帆看上去比上学的时候好看些,她十分欣赏张开的口哨,说有机会带他出去演出,张开高兴得手舞足蹈,长这么大,还真的没有上过舞台,真有这样的机会,他或许会走红的。
我说,你们俩都走红了,可我还是一个普通人,那时别忘了难兄难弟,他们俩就笑,就像真的已经是名人的了,很骄傲地昂着头。
江帆讲起她的男人,一个刚刚提为县长的大男孩,这两年也变了,有了女人,还为那个女人买了房子,买了车。江帆很后悔失去这次爱情,她说:他男人是个好人,不仅工作卖命,待人心肠也好,离就离,合不来就离,也少了些烦心的事。
江帆的话给了张开很大的启发,毕竟是在京城工作的人,见多识广,把人生看得很开,不像他,在婚姻问题上总是犹犹豫豫的。原来老以为自己是心太软,现在看来是自己的见识太少了。
吃晚饭的时候,江帆把她的领导也叫了过来,说是她的领导,其实是她的情人,她毫无顾及地挽着那个已经谢了顶的老家伙,很绅士向我们介绍,“这是我老公”。老家伙向我们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老家伙去卫生间了,我十分不安地问江帆,他可是有妻室的人啊!你一个黄花大闺女就跟了他。
江帆很不以为然,都啥年代了,这算啥,常年在外,可以相互照顾,多好!
看她满脸的不在乎,我的心一阵酸楚,我不知道岁月会这样无情,她不仅改变了人生的命运。还改变人生的态度,我眼里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哪去了?
七
十字路口,红绿灯、交警、车辆,这些组合起来,就成为城市独有的景观。有的地方就有十字路口,有十字路口就有红绿灯,有红绿灯就有警察。
在我们厂门前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准确地说是一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安红绿灯却管不住车,尤其是那些公交车,不管有没有警察,不管是绿灯,还是红灯,只管闯,而且,随处可以停车,在这个路口,我经常看见公交车和摩托车相撞的事情发生。受害的往往是行人和骑摩托车的人。
警察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在路边竖了个牌子等写上事故多发地段的字样,还用红漆画了个大×,但牌子竖归竖,事故依然发生。
不过,也有遵守交通规则的,大都是一些外地车辆,遇到这种车辆,公交车司机会从车窗探出头大骂道,走啊,眼睛瞎啊!没有警察,看不到还用得着等候。怕什么。
正江开始也很遵守交通规则,但时间呆久了,也开始闯红灯,闯得多了,也不觉得道德不道德,反正只管闯就是了。
早上,正江闲着无聊,开着车邀我到茶馆喝茶,我坐在前面,为的是看美女方便,他也一路调侃他在郑州是多么牛,车里是省委和市委的特通证,还安着警报,遇到事比警察还牛。
正江正说着,又到了那个丁字路口,眼看红灯就要亮了,正江一踩油门,车子冲了过去,这时,一辆丰田车突然间也闯了红灯从对面开过来,正江一打方向,两辆车擦了个边过去了……
两辆车都刮了一下,停下来,我这才看清,开车正是我看到的金丝鸟,正江和金丝鸟下来看看自己的车,都觉得车受伤不大,正江问金丝鸟,你车买保险了吗?
金丝鸟说是全险,正江说我也是全险。
正江说,我们别找警察了,十分麻烦的,找个地方修一下,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就完了,金丝鸟点点头。
正江约金丝鸟喝茶,金丝鸟犹豫了一下,把车调过来,跟着正江来到茶馆。
茶馆里的人很多。正江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金丝鸟把坤包放在坐位上,看了我一眼。
我们见过的,我说。
什么时候,金丝鸟眨了一下她好看的大眼睛。
就是前天,我没事在大街上转悠的时候。
是么,我怎么没注意。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记得你。
金丝鸟从包里掏出两张名片,递给我和正江,说道:请多指教。
我接过名片,见上面写着:红都广告影视有限公司懂事长、总经理、刘海燕。
你是做广告影视的?
是的。
来拉萨多长时间了?
八年了,我老公来我就来了,金丝鸟,不,刘海燕漠然地说。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房地产,那个别墅就是他建的,不过,他现在不是我老公了,他和朋友钱子每人都找了个四川妹子一起过了。
是那个白窗户别墅吗?我问
你怎么知道?刘海燕有些惊奇。
我怎么不知道,我是做记者出生的,我有些虚伪地回答。
你认识钱子,我们关系也挺不错的。正江用手抹了一下嘴。
不提他了,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刘海燕似乎有些感伤,她把脸扭到一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男人都是负心汉,艰苦的时候,还恩恩爱爱的,有了钱就不能在一起过了,真是。
正江似乎看出了什么,他端起茶对刘海燕说,喝茶、喝茶,别提那些不开心的了。
刘海燕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都是命,尤其是女人,命运好不公平啊!
你们老家是哪里的,来几年了?刘海燕话锋一转。
我们是郑州的,刚来,正江认真地答道。
我也是郑州的,我们是老乡哎,刘海燕有些激动。
这么巧,正江也附合着道。
来拉萨做什么?
做点小生意,不值得一提,正江有些汗颜。
刘海燕端起茶杯轻轻地咽了一口茶,那姿式很淑女、高雅,很像个有教养的女人,我的心里掠过一丝惬意。
你做过记者,也算文化人,我们可以合作的。
我……恐怕不行,我的脸一红。
写剧本么,大都是独脚本,很好写的,说着,刘海燕从坤包里拿出一叠影视作品的脚本。
大家谈得很投机,末了,刘海燕非要请我和正江吃饭。
刘海燕饮酒很凶,几乎一口一杯,我和正江都瞪大了眼睛。刘海燕说,没办法啊,作为一个女人干事业难啊!要么用酒量打倒对方,要么用金钱打倒对方,要么就用身体,后两者我都不愿意,我能用的只有喝酒了,这也是我无奈之下练出来的。
酒过三巡,刘海燕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很好看的红晕,我发现她的眼睛有些勾人,
我甚至不敢看她的脸,我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不简单。
正江却不怕,他的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硬着舌头说,妹子,你喝晕的样子真好看。
是吗,男人都这么说我,刘海燕用手拍了拍正江的肩膀,就像久违的老朋友。
正江嘿嘿地笑了,我看见正江不怀好意的眼神。
刘海燕醉了,倒在了正江的怀里……
八
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刘海燕打来电话,让我到她公司去拿本子,我匆匆说了两句就挂了电话。
正江敲我门的时候,我还在酣睡,他说我手机打不通,才来敲门的,我拿起手机一看,已经没电了,昨晚酒喝多了,忘了充电。
正江说刘海燕急着找我,手机打不通就打了他的手机,让他来叫我的,我这才想起早上刘海燕是给我打过电话的。
我匆匆忙忙地洗把脸,刮了刮胡子,便急急忙忙地向刘海燕的公司赶。
刘海燕的公司离我们住处仅一墙之隔,我一袋烟的功夫便到了目的地。
刘海燕正和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子说着什么,见我敲门,便停下交谈,和我聊起来。
我说我是河南省首届作家班的学员,是写小说和诗歌的,但对剧本不是太懂。刘海燕说,文学都是相通的,你会做好的。她还说,我不会白用你的,我公司开的稿费比文学杂志开的稿费高十倍还多,真的,她冲我瞪着那双勾人的眼睛。
我依然不敢碰她火辣辣的眼光,把眼睛躲到一边。
刘海燕把本子递到我的手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这是预付金,稿子杀青后,再付全部稿费,说完,她起身从身后的书柜里拿出一条中华烟递给我。
拿着吧,你挺能抽烟的,我也用不着。
我不便推辞,便把这些东西收拾在一起,站起身对刘海燕说,盛情难却,让我试试吧!
第一个剧本是写文成公主的,只是一个小片断,我很快就写完了,给刘海燕打电话的时候,刘海燕感到很吃惊,她说,这么快啊!我说,是啊!就这么快!
审完稿子,天已经黑了,刘海燕请我吃晚饭,她请来北京的剧作家丁光头作陪,丁光头是个名声很大的作家,在我面前显摆,很张扬的样子,吃饭也很挑剔,我有些看不惯,想离开饭局,刘海燕就用脚碰我,示意我不要生气。
吃完饭,刘海燕从坤包里掏出一沓钱,对丁光头说,不好意思,由于你很忙,也顾不上我们公司的活,我们的合作至此为止。
我有些不解地望着刘海燕,但她镇定自若,丝毫没有在意我和丁光头的反应。
路上,刘海燕长舒了一口气,对我说,解脱了,一切都解脱了,你不知道,为了买他写的剧本,公司花钱不说,老娘还要陪睡,现在好了,有你了,不用愁编剧刁难了。
她显然有些兴奋,车速也比较快。
九
这以后,我天天到街上看美女,准确地说是看刘海燕和她老公的小老婆。
拉萨的天黑的晚,赶到街上,那里依然十分热闹,人流和车流不断,有时候,我中午也去。中午太阳很毒,我只作短暂停留,来二十分钟,去二十分钟,没人的时候,我就看路边的红绿灯,一闪一闪地有节奏地机械地跳着。
超市门前偶尔也能遇见几个熟人,碰见丁光头时丁光头正在搬家,他虽然和我搭话,已经没有吃饭时的张扬,他递给我一支北京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条长长的烟柱。
他说,刘海燕这女人很阴险。
我说,我不了解。
他说,刘海燕是用在先,不用人在后。
我说,不知道。
他说,刘海燕在床上很温柔。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小子可能要走桃花运了。
我说,不可能的。
他摇摇头,伸出手和我握别。
我目送着丁光头钻进出租车。丁光头从出租车的窗户里探出头,叫道,兄弟,没事到北京找我。
到北京找你,没有电话、没有地址,鬼知道你住在哪?
丁光头的反常表现和话语让我心里感觉有点堵,刘海燕真的是那种人吗?
我正在发愣,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我回头看是四川的包工头叉子。
叉子的大姆指上长出一个小指头,是六指手,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叫叉子。
叉子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发愣,我说,我的头脑发热。
我说,不是病,是头脑发热。
叉子说,就应该去看医生。
我说,跟你说了不是病,看什么医生。
叉子还想说什么,但终没有开口。
叉子拉着我走进超市,非让我帮他挑选一套时尚女装。
我问是给谁买的。
他说,当然是你嫂子了。
我说,哪个嫂子,是小嫂吧!
叉子憨憨地笑着没有吱声。
叉子花了几百多元买了一套女式套装,他认真地把衣服装好,然后,提着它走出超市,就像没有我的存在。
我今天怎么碰上了这两个人,看着叉子下电梯的背影,我“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我出门的时候,叉子站在门口等我,他给我让了一支烟,问道,唉,女人在生日最喜欢什么?
我说,还用问,当然是钻戒了。
叉子说,那我就买钻戒。
我心想,买钻戒,你小子买得起么,分别时,叉子边走边嘟囔,买钻戒,买钻戒。
十
闲下来,正江睡大觉。
闲下来,我就到街上看美女。
我感觉一条街就是一个人生的舞台。形形色色的人都在上面表演。美女表演青春!老人表演着沧桑,残疾人表演着凄凉,而我在表演着无聊。
正江的好朋友丹多开着车从我身边驰过,见我站在那,停下车示意我上去。
我坐上车,丹多问正江在哪?
我说在屋里睡觉呢?
丹多便把车开到正江的屋门口。
丹多和正江耳语几句,正江脸色大变,他急忙起床简单地洗把脸,便匆匆开着车一个人走了。
傍晚的时候,正江回来了,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问正江什么事这么急?
正江说,妖妖,也就是你嫂子,昨天在一家洗浴中心卖淫被拘留了。
我说,那嫖客呢?
正江说,你认识的,是监督局的罗布,也拘留了。
我说,不是花点钱就可以摆平吗?
正江说,现在拉萨严打,抓一个拘留一个。
我说,你见到妖妖了吗?
正江摇摇头,拘留所没有熟悉人。我今天给他存了500元钱,但东西却送不进去。
每月的十四日是探监的日子,一大早,正江便把我叫起来,让我一起陪他去看妖妖。
排队的人很多,正江抱着一床背子,手拿一条烟在窗口前焦急地等待着。
十二点多的时候,轮到正江了,他把身份证和被子、烟递进窗口。
警察把烟甩出来,吼道,烟不能送,拿回去吧!
正江从窗口开了条子,把条子递给看门的警察,警察带着我们向探望室走去。
来探望的家属很多,正江跑着寻找妖妖,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妖妖。
正江打了个电话在那里等着,好大一会儿,妖妖才在一个女警的押解下来到窗口。
妖妖穿着看守所的黄马夹,脸上很憔悴,见到正江,她的眼泪涮地一声流下来。
正江的心情很痛苦,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他一时想不起该说什么。
妖妖哽咽着对正江说,烟,我想吸烟想吃肉。
宝贝,我送不进去啊!正江十分着急地说。
你找熟人想办法送点进来,妖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正江。
正江说,好吧!
会见一会儿便结束了,正江随着妖妖的行走而移动着,他想多看一眼妖妖。
我说,为一个风尘女子值得吗?
正江说,闭嘴,我不准你这样说她。
我说,发什么火啊!
正江说,就是不允许你这么说她,她家有卧床不起的老母,下有两个娃娃,一个女人家有什么法啊!
这时,杨丰从看守所走出来,正江眼睛一亮,走上去和杨丰打招呼。杨丰是看守所的一个警员,去年常在一起打麻将。杨丰问正江有什么事没有,正江说,女监2号的妖妖是他的女朋友,让杨丰捎些烟和500元钱给她,说着,把腰里的烟一骨脑地往杨丰兜里塞。
从看守所出来,正江长舒了一口气,他想总算把香烟和钱送进去了,有这一条烟和1000元钱,妖妖不会吃太大的苦。
闲下来,正江就一天天地数着过日子。
闲下来,我就到街上看美女。
时间一恍就过了两周,大清早,正江喊上我到看守所去接妖妖。
看守所的大门紧闭着,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到看守所走出一个人。
正江急了,就到窗口问警察,警察说,今天放了一些人早走了。
正江问有没有女子,警察说,都是女的。
没办法,正江只好悻悻地开着车往回赶。
路上,正江是给妖妖好友王丽打电话问妖妖去她那里没有,接着给丹多打电话,问见没见到妖妖,两个人都说没有见到。
正江很狐疑,不知道妖妖到底跑到哪去了,按理讲,她出来第一个就应该给正江打电话的,他十分着急。
人在看守所失踪了,正江很恼火,他又把车开到看守所,看守所值班的警察一听,也急了,他让正江先在外面等一下,他到办公室去查一下。
过了一会儿,警察回来了,告诉正江妖妖明天才能到期,让正江明天来接。
第二天一大早,正江就在拘留所门前等,接到妖妖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妖妖和另外一个女孩像小鸟一样从看守所的树林里飞出来。
妖妖看见正江兴奋得抱住正江抽泣起来。正江用手拍着妖妖的后背,轻轻地说,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咱们回家吧!
正江把车开到一家餐馆门前,要了一锅蹄花大虾,看着妖妖狼吞虎咽地吃着。
妖妖说,你真好,从此我要好好爱你。
正江很感动,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从此,正江的床下又有两双女式高跟鞋躺在床下。
闲下来的时候,正江就睡大头觉。
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到街上看美女。
十一
刘海燕从办公室出来,一眼就看见丁光头的一个纸条帖在公司的门上,刘海燕快步走过去,一把撕了下来扔在地上。
刘海燕不知道纸上写得是什么,坐在那里生闷气,办公桌上的电话晌了,她也懒得去接,秘书小红走过来,接了电话。
是丁光头打来的,丁光头在电话里奸笑着,他让小红转告刘海燕,他很想她,也很爱她。
刘海燕接过电话,骂丁光头是个流氓,是个人渣,丁光头也不还口,静静地听着,末了,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我见到刘海燕时,刘海燕已经哭成了泪人,我的心也一阵发酸。
刘海燕说,作为女人又有啥法呢,刚开始,她对丁光头还点好感,因为他有才气,能说会道,特别是她刚离婚情绪低落的时候,丁光头知冷知热的话语让刘海燕很感动。
刘海燕请丁光头写剧本时,丁光头已经辞去他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的工作,第一个剧本出来时,刘海燕喝多了,那晚就住在丁光头那里。
从那时起,丁光头每写一个剧本都要刘海燕到他家去催,不然,剧本就迟迟不到。
时间长了,刘海燕就烦起了丁光头。但那时,公司里没有编剧,刘海燕只有忍气吞声,说这些话的时候,刘海燕一脸的无辜,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两只手不自然地搓着。
刘海燕擦去眼泪,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让我看。
信是她的女儿写的,她希望爸爸妈妈能重归于好,我想,此时的刘海燕一定很矛盾。
我说,你自己决定吧!
她说,不可能了。
我说,为了孩子。
她说,他伤我太深了,就像伤口无法愈合。
我说,努力地做,会有效果的。
她说,心死了就永远不会活。,
我,你……
沉默,我们沉默很久。
刘海燕让小红找来摄像,安排第二天去林芝排广告的事,她问我有没有时间,陪他们一起去,我说,对不起,明天没有时间,改日吧!
从刘海燕公司出来,我无心看街上的美女,也没精神看闪动的红绿灯,脑海里回荡着刘海燕的话,我不明白,做女人真的那么难么。真是人在他乡,各有各的辛酸事。
丹多不知什么时候从地上冒了出来,他没有开车,一个人步行,看见我就远远地打招呼。
丹多说,你怎么在这里,正江的老婆,就是妖妖刚才服毒了,已经住进了医院,你还不去看看。
我说,不会吧!上午还好好的。
丹多说,这样的事我还骗你。
于是我们俩一起打的往医院赶。
十二
妖妖的鼻子上面插着氧气管,正江坐在病床上边,见我和丹多来了,慢慢地站起身,示意我们坐下。
吃了一瓶安眠药片,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医生刚为她洗过胃,正江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丹多问,她为什么想不开啊!
正江说,我也不知道,只感觉她今天有点不对劲。
丹多说,不会是受到什么刺激吧?
正江说,真的不知道
这时,一个胖护士手里拿着单子问道,谁是病者家属,请到药房交费。
正江站起身和护士一道向药房走去。
傍晚的时候,妖妖醒了,正江看见妖妖醒了,两只眼睛因充血变得血红,心痛得直掉眼泪,他俯身亲吻妖妖,他的泪花和妖妖的泪珠混在一起,顺着妖妖脸颊和眼角纵情地流着……
妖妖是正江的最爱,虽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但这种爱一直让正江难过,他无法割舍,用心经营着这片爱的天空。
妖妖把正江的手握得紧紧的,生怕他离开自己。经历这场死难之后,妖妖更加珍惜正江,更加珍珍惜这份爱。
本来,我一直对正江的恋情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看到他们倾心相恋的样子,心里也不自觉地掠过一丝悲凉,丹多的眼睛也潮湿了,他把头扭到一边,任眼泪涮涮地流淌。
他说,他曾经爱过一位姑娘,把心都交给她了,但她却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永远地去了。
那天,也是在医院里,他拼命地捶着她,而她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甚至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
丹多把头高高昂起,头发随着心颤抖着。
我掏出香烟,燃着递给丹多,他大口大口地抽着,香烟在房间里弥漫,就像一颗沉重的心绪在慢慢地打开。
天黑了,正江把脸从妖妖的脸上移开,他轻轻地把妖妖的手放进被子,掏出手帕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此刻,他无法平静自己情绪,跑到水管边用凉水冲了冲头。
他让我俩先回去,自己守着妖妖。
我和丹多走在马路上,看着路灯把我们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就像变了形的人字,丹多用脚踢着一个空易拉罐,一脚踢过去,易拉罐在马路上翻着跟头,划出一阵无奈的响声。
丹多喝了很多酒,他甚至不能站立,歪歪斜斜地钻进出租车。他不让我扶,也不让我碰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藏语。
丹多的女人和妖妖是好朋友,都是来自四川,她们家住的很近,妖妖没事的时候,经常到她家去玩,丹多没有把妖妖看成外人,当作自己的亲妹妹,妖妖出事了,丹多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的女人说。
我把丹多送回去的时候,天已经破晓了,丹多家的小狗不停地冲着我叫,丹多一脚把它踢出好远,那条狗尖叫着跑了出去。
看着那条狗落魄的样子,我的心里有些发笑,人啊!就是这样,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纠缠着你,让你不得安宁。
大街的那头,张开傍着一个女孩不知道从哪里转出来,向我打着手势。我走过去,张开向我介绍那个女孩,让我叫嫂子。我见过张开的老婆,确实没有这个女孩长得好看。
我说,你的艳福不浅啊!
张开说,哪里,这都是命,现在好了,婚也离了,有了可心的女人,今后要好好的珍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我说,那要祝福你们。
张开说,艰难啊!能在一起过也是缘分,人在他乡,有个人照顾好啊!
早晨的阳光格外明媚,那一片落红随着风在我眼前漂荡,金珠西路沐浴在阳光里,街上的行人很少,我独自一人在游荡着,我把领口翻起,头缩着想到昨天发生的事,一切就像一场梦,我不敢相信。
今天,正江在医院守护他的女人。
今天,我依然站在街上看美女。
十三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 又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站在大街上,我一遍又一遍地背着戴望舒的《雨巷》,我真的希望能遇见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钱子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他用手捂着自己的肚子,像生病了。
我走过去,扶住他,他疼地弯下腰,我这才看清钱子的眼睛已经被谁打成了熊猫眼,胳膊上也有伤。
谁打的?
唉!别提了,刘海燕原来老公养的那个小妖精,以前和我相好,他们两个同居以后,我经常去幽会,这不,一不小心,被撞上了,他那帮小弟兄像恶狼一样,唉哟、唉哟……
看着钱子远去了背影。我无心再看美女。一个人孤独地向家里走去。
闲下来的时候,我开始写剧本。
闲下来的时候,我不再到街上看美女。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