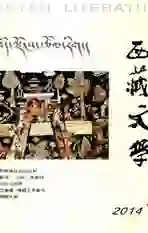三代人的梦(短篇小说)
2014-06-20德本加
德本加
1
大家都这样说,如果没和拉先离婚,她也不会招惹这么多是非,这叫咎由自取!如果不是一个没脑子的家伙,谁还会娶她,她就是一辈子守寡也是活该!我来到这个岗位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不是很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因此,我想这件事问才吉大姐她一定会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回答,但是才吉大姐现在在哪里呢。
才修是我唯一的酒友,所以我记得那天我俩好像是去喝酒的。一进那家逼仄的小饭馆,才修尽可能地凑过来在我耳边絮叨了几句,用嘴巴往一边指了指。左侧的桌子旁一个古铜色皮肤的小伙子在吃饭,他的旁边还有一个女孩。她不知是在假装害羞还是怎么回事,吃了几口之后面带微笑地盯着小伙子的脸,还在低声说着什么。小伙子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只是专心地吃饭,对女孩不加理睬。才修看着那情形,露出一丝微笑,使劲摇着头。
我确实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我听说那个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小伙子是拉先时,我不由再次仔细地看他。他大概二十五岁的样子,吃饭时不停地颤动着的那两撇胡子我始终也忘不掉。他俩不是早就离婚了吗?听人说那次是她的错。那今天他不会是又跟她在一起了吧?啊啧啧,她到底是谁呢?
2
1919年秋天下了一场大雪。有些人说从他们记事起就没有下过这样的大雪。
吃了晚饭,男人披着白毡衣到羊圈边上睡觉去了。女人给自己铺被褥时想起昨晚因为太挤把自己的脑袋都挤到枕头边上了就把枕头给加长了。她又点了一盏酥油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觉得一天的活计到此结束了。但是她又往火塘撒了一把柏树枝,向三宝祈祷一番后才钻进被窝里希望能有一个好梦。说不清是不是到了午夜时分,梦里一个披着白毡衣的男人进来睡在了她的旁边。他没说一句话就钻进了她的怀里。她的每一根感知的神经都在向她证明着那个人就是自己的丈夫。一种愉快的感觉传遍了她的全身,她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了。
“昨晚那个人是谁?”第二天,男人有点不高兴地问。
“谁?”
“那个穿着毡衣的。”
“谁不知道你的毡衣,肩膀上还有一块补丁。”她以为他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
男人出去放羊了,女人则开始怀疑起来。这时,她的心里不可抑止地生出了想扶养一个孩子的念头。之前他俩没有孩子。
雪的反光像月色一般把夜晚的景致给照亮了。矗立在后面的神山贡布拉格像平常一样雄伟壮观。午夜了,在雪的反光中他又悄悄地来了。雪很厚,“吱吱”的脚步声不是很清楚。他还是披着白毡衣。他把白毡衣盖在身上后就轻轻钻进了她的怀里。是他!她觉得浑身舒服,不想说一句话。他俩没有说话。她的手碰到了锅。她随手抓住毡衣的领子盖在他的身上。夜晚寂静依旧,雪地依然白晃晃一片。她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沉。睡梦中他俩在云里雾里欢愉,就像在天界一般。没有了一丝人的习气,沉浸在天界的幸福中。突然,一声惊雷之后,他就无影无踪了。这是个梦。那声惊雷把她从睡梦中惊醒之后,她还在找他,但是他已无影无踪了。
早晨,她烧好早茶,提着半勺子奶茶走出屋子朝着贡布拉格神山撒去时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贡布拉格神山的正前方印着一张黑黑的大手印。大手印的每一根指痕似乎在抚着山的两侧。啊啧啧,她想起了昨晚的梦。开始她的心里一阵恐慌,接着渐渐变成了一种敬仰。那天下午,几个牧童首先发现了那个奇特的大手印,接着这个游牧村落就变得沸沸扬扬了。人们在挖空心思地议论纷纷。
“肯定是地震了,你看山崖都滑坡了。”小孩们说。
“不是,像是桑烟缭绕的样子。”老人们说。
“怎么可能呢!保护神展开了双手,要赶紧煨桑祈祷。”活佛和头人们说。
就是让无数个人支着耳朵听上七七四十九天,她也没向任何人说过有关那天晚上的任何事。那年夏天,她生了一个孩子,取名为格贡拉雅。
3
“她叫华措,二十二岁。”才修又谈起了她。我也开始在他的话语间猜想她神秘的面容。
“她很漂亮。”
“漂亮?”
“是啊!”才修硬是喝完了一瓶啤酒,使劲摇着头说,“确实很漂亮!我敢肯定你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但是她生不逢时啊!漂亮的女人们都有自己的使命,她们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也是因为人类的某种需要而存在的。但是从古至今那些青春活泼的少女,尤其是那些美丽的女孩,她们的情感往往被权力和金钱所掌控,到最后她们自己也意识到没有完成赋予自己的那个使命,便有了‘悲剧这个词存在的意义了。你认为呢?”
“好像你也很牵挂她啊。”
“我不知道。不管怎样,她和拉先离婚是个错误。问题在于他们之间出现了第三者。”
“谁是第三者?”我盯着他的脸看。
“我也不知道。从大伙儿的嘴里传着各种各样的话,但是这些话也未必可靠。以后总会水落石出的。”
“喝酒!”
拉先去某个大学进修了。据说他走时脸上的表情很正常。同事们把他的行李绑在车上,还像平常一样开着各种玩笑。最后,他自己也抑止不住离别的伤感,和同事们一一握着手。等他上车时,他们才看见他的脸整个地红了,眼里闪着一丝晶莹的光。
拉先走了。他没有任何留恋地在朋友们的关怀和祝福声中走了。他走后的一个月里,这个小镇里许多“新闻”像风一样飘荡着。这些“新闻”大概也是从这个小镇边缘的中学——拉先和华措当初结婚时的那间小小的屋子里传出来的。从一个人的嘴里传到另一个人的嘴里,传着传着人们就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到最后惊诧不已,甚至在突然间哈哈大笑了。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些,虽然所有的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需要生活着,但生活毕竟还是很公平的。
“他俩之间相差二十五岁。”
“是因为金钱。”
“是啊,活佛也回去和自己的老婆办离婚手续了。”
4
阿妈像往常一样靠着锅台后面炕上叠起来的破皮袄坐着。她手里没有念珠,嘴里也没有发出念诵嘛呢的声音,只是一个人想着什么。平常每当太阳升起或者太阳落山时,她都会往锅台边上的那个扁平的铁勺里撒上一把桑料,然后蠕动着嘴唇念起经来。
天快黑时,拉杰把羊群聚拢到帐篷前面就进来了。朦胧的火光下只有自己的影子在晃动着。拉杰站在屋中央像是在发呆又像是在想着什么。一会儿传来了一声叹息,那声音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阿妈—”拉杰突然跑向锅台的后面,“阿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阿妈……”
一会儿之后传来了一声很微软的声音:“我没有煨桑,今晚你要煨桑。”
拉杰第一次拿起锅台边上那个铁勺,盛上火往上面撒了一把桑料。缭绕的桑烟一下子从帐篷的天窗飘向了天空。
“好孩子,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吗?”她颤抖着声音叹了一口气说。
“阿妈,你怎么了?”
“……没有,我没事。今晚我给你讲你阿爸的事情,你要听好啊!”
在朦胧的火光下一个故事的讲述开始了。
“……你父亲名叫格贡拉尤,他是神山贡布拉尤的幻化之子。他在安多一带几乎家喻户晓。你是格贡拉尤的儿子。你本该生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你现在十六岁了,但是你整天和孩子们打架,把衣服弄的破破烂烂之后才回家,这怎么行啊!从今往后不许你再打架!虎父无犬子!你的阿爸死了已经十六年了!
“你阿爸活着时用活的山羊来祭祀,每年要祭祀好几次。那是他必须要做的。因此,无论遇到什么事,贡布拉格都会亲自来护佑他,解决所有的麻烦,这是真的。
“有一次你阿爸和我俩去农区买面,二十头牦牛驮了四十个驮子,往回走了两天的路程时有六头牦牛爬在地上吐出舌头不动了。那时天也快黑了,我俩就下了马。你阿爸支起三块石头生火,我赶紧去提水烧茶,把路上的干粮都拿出来了。但是你阿爸不喝一口茶,他洗了手往火堆上撒了一把桑料,站了起来。啊啧啧,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像是发生了幻觉,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骑着白马穿着白衣的人,把那几个牦牛抱起来立在地上之后就无影无踪了。
“后来我俩就没有任何麻烦地回到了家里。”
拉杰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阿妈的嘴里看。他在羡慕自己传说中的父亲。他不相信自己是他的儿子。
5
活佛和华措结婚那天,我叫上才修去喝喜酒了。婚礼现场的布置跟内地差不多,挂满了各种颜色的彩条,屋里屋外的墙上贴着大红的“双喜”。十多桌酒席排成了三行,每桌酒席边上围着七八个人。还有几个坐小轿车过来的大人物。活佛也跟平常大不一样,穿了一套笔挺的黑西服,还打着领带,看上去似乎小了十多岁的样子。他很恭敬地在招待那些大人物。
“他发福的体型和身高很不协调,像个矮子一样。”才修在我的耳边说了这些话,冷笑了一声。
“闭嘴!咱俩不是来喝喜酒的吗?”
“你看,除了几个厨师,他们单位的年轻人一个也没来。”
一会儿之后,才修又耸了耸肩膀看着我继续说:“你知道活佛和拉先是什么关系吗?”
“不知道。但是当拉先知道这些时,他俩一定会彼此怨恨的。换上你也不例外。”
“你错了,拉先早就知道这事。”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大伙儿都这样说。”
“我不相信。”
“拉先走时还去拜见了活佛。”
“为什么?”
“他带了两包茶和一条哈达去祈请活佛保佑呢。听说那时他的眼圈也是红的。”
“请活佛保佑什么?”
“听说是为了进修的事。他请活佛……哦,她来了,你看看,她今天穿的多华丽啊。”
我也赶紧顺着他的目光看。活佛和一个姑娘从后面的小门进来了。她是华措吗?我不由地给了自己一个问号。她穿着一件新的水獭镶边的氆氇袍子,头上戴着的礼帽上插着的两朵紫黄色花使她增色不少,平静的脸上挂着一丝迷人的微笑,那微笑里似乎暗藏着一种能把人的魂儿一下子勾过去的力量。她和活佛一起为客人们敬着酒,这时给我的一种新的感觉就是他俩应该是一对父女。
回到宿舍时才修有点醉了。他又说起了她:“她怎么样?我说的没有一点夸张吧?”
“那迷人的微笑使她增色不少。”
他一边抽烟一边使劲摇着头:“有时候我也这样想,那些美丽的女孩之所以美丽,就是因为有迷人的微笑的装饰,如果世上缺少迷人的微笑,哪还有这么多美丽的女孩啊!”
“我也这样认为。”因为他的醉我也附和道。
一会儿之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地看着我说:“如果这个地球不是圆的,她也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啊。”
“是啊,人的命运是很难说清楚的。”
6
1936年,一千多名马匪到贡布神山一带收苛捐杂税,部落的百姓们慌慌张张地将牛羊丢弃在山沟里四处逃生去了。
天快黑时,格贡拉雅像平常一样煨桑,滚滚的桑烟遮天蔽日。他备上马鞍,背着那把老式的叉子枪,单枪匹马地就上路了。来到一个山口,他下马准备稍事休息时,一只喜鹊落在他前面的土块上“嘎嘎嘎”地叫了三声就飞走了。他赶紧骑上马往下走时,啊啧啧,前方的山脚下一伙匪兵赶着驮着驮子的马和骡子黑压压地沿着一条山道正向他的方向走来。他一边祈祷贡布山神,一边对着匪军把叉子枪支在地上大声地喝了一声。那伙匪兵一时像是洪水被大坝拦住一样踌躇不前。那个络腮胡子的匪兵头子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嘶哑着嗓门喊道:“我们是马司令派来守卫边防的,你这个自不量力的家伙胆敢阻挠我们吗?”
阿妈对拉杰讲他的父亲的时候这样讲过:“确实是贡布神山护佑了他。马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时,他的身上只是留下了一些灰色的印痕。这样说你肯定不相信。但是他一个人堵住匪军,七七四十九天没让一个匪兵冲出山口。最后,他的子弹全部打光了。”
从没有子弹的那天下午起,他觉得匪兵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那时,他为了让匪军上当,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往咕如大森林的方向跑。匪军也紧紧地追在了他的后面。
茂密的森林中人和马很难穿行,他爬到山顶时东方的天边已露出了鱼肚白,才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穿了没多久的那身羔皮袍子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零乱不堪。一解开腰带满怀的子弹就叮叮当当地撒落一地,他也不由地摇了摇头。
他在那里藏了八天八夜也没见匪军有一点动静心里就放松起来,最后竟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一阵子他在睡梦中听见了马的嘶鸣声。他一下子醒过来起身看时,看见自己的马正竖起耳朵围着他转。他知道有敌人就往前走了几步,没想到前面竟是一个无底深渊。随着一声呼哨声,五百余名匪兵从他的身后围了上来。匪兵们看见他手里没有武器,就壮着胆子到了他的跟前。
“哈哈哈,你有本事就飞上天吧!嘿嘿嘿,给我活捉这个家伙!”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匪兵头子捋了捋胡须发出刺耳的声音大笑着。格贡拉雅像是一只毫无畏惧的老虎昂首站在峭壁上,使那些匪兵们不敢继续靠近,像草人一样颤抖着。那个匪兵头子一时也呆在那里不动。
“哈哈哈,听好了,我格贡拉雅傲立天地间无人匹敌,你们不要痴心妄想抓到我!看哪!”他一边呼唤着贡布山神的名字,一边像大鹏展翅一样从峭壁上跳向了深渊。匪兵们站在原地惊讶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有些哆嗦着连手里的枪也掉在了地上。
匪兵们毫无办法,最后只好打听着去了他的部落。格贡拉雅到家里拿了两褡裢子弹和一把镶着银子的枪又去打匪兵了。他和匪兵周旋着打了六年,上至阿沁雪山脚下,下至神山拉日宗嘎,到处都有匪兵的尸首。六年间他只回了三次家。
1947年,匪军把他们全家和部落里五十个年轻人赶上了绞刑架,并到处放话如果格贡拉雅十五天之内不归降就要杀了他们。
村边的格贡神殿旁排列着五千余名荷枪实弹的匪兵。那个蓄着山羊胡子的匪兵头子在绞刑架下带着满意的表情走来走去,偶尔看看腕上的手表。一碗茶的功夫,突然间一声枪响,远处卷起一阵黑旋风,随之格贡拉雅骑着一匹马冲来了。他没带任何武器。
“哈哈哈,我相信你会来。确实是条汉子。马司令很赏识你啊!如果你能受降于马司令,起码也会给你一个师长的位子,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藏族不是有句谚语叫‘一条好汉再猛也不算好汉吗?啊?哈哈哈。”匪军头子使了一个眼色,格贡拉雅的家里人和五十个年轻人被松开绑赶到了一边。匪军头子再次看着格贡拉雅微微地笑。
“哼哼,你没听说过我们藏族还有句谚语叫‘与其像狐狸一样夹着尾巴逃跑,不如像猛虎一般带着微笑死去吗?”格贡拉雅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他的亲人和年轻人都哭了起来。匪兵们惊恐万状地倒退着。整个村落的人大声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啪—啪—啪—”
三声枪响接连传遍了广阔草原,峡谷之间,山岭之巅,云层之上,化成了人世间最最辽远的一曲悲歌。连续十五天贡布神山的山体被一层灰蒙蒙的雾笼罩着,若隐若现……
7
商店门口几个牧民盘腿而坐,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他们的话题是关于阿尼才吉的死。
“她是活佛妃子的继母。”
“不是亲生母亲吗?”
“不是。听说她是捡来的,到现在也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那个老太婆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啊!”
那天我在街上再次看见了她。她抱着一个约莫两岁的孩子和几个老太婆一起往百货商店的方向走着,跟以前相比变化真的很大。原先苗条的身材几乎已经变形了,硕大的屁股像是牧民家里的皮囊;原先挂在脸上的迷人的微笑全然不见了,眼神中充满了狡黠的光。这时,我的心里不由地生起一丝失望的感觉。
旁边的几个小伙子看着她轻蔑地说:“骄傲得什么似的,像头母猪!”
“她抱着的小孩是前一个老婆生的,她还说是她的儿子!”
“活佛不是在宾馆里也有一个相好吗?听说前天他俩吵起来了,那个外地来的生病的姑娘也站在了活佛一边。其实那姑娘也没什么病!”
我想再仔细看看时,她已经进了百货商店,旁边那几个小伙子也不见了踪影,真是两头都没捞着啊。我只好两手叉在胸前看着自己的脚尖回到属于自己的小屋了。
没过一星期活佛和华措离婚了。这几天对我来说是“收获”较多的几天。一些人还像以前的我一样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着“不可能”。但是此刻的我却有着不一样的想法,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对他们说:“世上的很多事就是在不可能中发生的,就跟我们心中的一些想法往往是靠着机缘巧合来实现没有任何区别。”我四处打听这件事的原委,想找个机会消除人们的好奇心。
引起这件事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如下:
A.活佛自从在外面有了一个相好之后,偶尔晚上也不回家,第二天脸色像蔫了的萝卜一样钻进家里倒在沙发上一边休息一边说:“昨晚上面来了几个很重要的客人就……”
B.她给曲藏活佛写了那封信之后自己懒得上街就让那个“病姑娘”去送。下午活佛回家坐在沙发上时,那个“病姑娘”笑眯眯地把信交给了他。
这事再往细里讲就是这样:
星期六晚上,学校团委举办了一场舞会。大概到了十二点,华措回家打开门时很吃惊。今晚他没有出去,一个人靠在沙发上喝酒,差不多快喝了一斤了。
“回来了?”
他看见华措进屋,就一直用发红的眼睛盯着她看,有点失落的样子。她不在意地把旁边的小凳子放在了一起。
“在我身边你就那么痛苦吗?”他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不敢看她似地低下头,用右手扶着额头,“我看见你的信了。”
“什么?”
“寄给曲藏的那个。”
她很惊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站起身走来走去,愤愤地说:“那你去宾馆晚上也不回家是怎么回事?我一个人在家里受不了!你知道在外面在说什么吗?我还要装作没有听见那些闲话的样子!没想到你还偷看我的信!”
她哭了起来。
“这些就不要再提了,总之这事算是完了。如果你真不想呆在我身边,或者在我身边你受着那么大的委屈,咱俩可以离婚。”他硬是往嘴里灌了一口酒。
“这……这算是什么理由?”
“不是,我也不会让你吃亏的。这个家里你想要什么……不是,这个家里一半的东西归你。如果还有什么困难,我都会全力帮你的。”
听说在离婚证上签字时,她的脸上像以前一样挂着迷人的微笑。
8
“打倒牛鬼蛇神!”
“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要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
晚上,村子中央的一个破院子里高喊革命口号的声音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呼呼作响着。火堆边上拉杰穿着一件油腻的皮袍,手里拿着一本红皮的毛主席语录,滚瓜烂熟地背了一则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其他人也跟着他喊,那叫喊声布满了村落的上空。
一会儿,从火堆里蹿出了一片一片的火苗,人们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披着豹皮的驴子,作恶多端的臃忠你听好了,你为什么把这些‘牛鬼蛇神的器物给藏起来了?快说!你想欺骗谁?还吹嘘自己懂害人的巫术吓唬过哪些人?这些是不是你的罪过?快说!”拉杰用食指指着一个大胡子的老头不停地问着。那个老头弯着腰、低着头,像是在认错似地颤抖着,不敢看拉杰的脸,会场上的人们也不敢说话。
第二天晚上,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把雍忠老人的手从后面反绑起来,脸差点就挨到地上了。拉杰的鼻尖上闪过一丝奸笑说:“嘿嘿,你这个人民的敌人!现在你念咒啊!来咒死我啊!你的本事哪去了?”
老头子依然不敢说什么。那些戴着红袖章的猛地推了一把,他就像一棵根子腐烂了的老树一样倒在了地上,右手的袖口触到火堆上散发出一阵焦味。
第三天晚上,拉杰像往常一样穿着那件油腻的皮袍,拿着毛主席语录,背了一小段,喊了几声“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今晚他似乎更加激情高涨,昂首挺胸地说:“月底要把每个村子的各类反动分子召集到公社学习班召开一次批斗大会!反革命分子臃忠也是这次批斗的对象!他在五八年披着僧侣的破袈裟和解放军作对,现在又使用‘牛鬼蛇神的伎俩蒙骗人民群众,这样的罪魁祸首我们永远也不能饶恕他!”
臃忠老人站不稳脚跟。
半夜时分,拉杰回到家时老婆生了一个女儿,他很高兴。天刚亮,几个红卫兵慌慌张张地跑到了他家里。
“他死了!”
“在哪里?”
“在会场里吊死了,还在一块白石头下面压着这张纸条。”说着把半张破破烂烂的砖茶的包装纸递给了他。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些字和很多图案,字面的意思大概如下:“你这样一个不怕因果报应的家伙成为格贡拉雅的儿子实在很可悲!我咒你的后代掉进一条逆流的河里从此断子绝孙!如果不这样,就证明我确实无能!”后面还写着个梵文。
9
我在屋里正在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我被小说奇妙的艺术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深深吸引,忘记了时间的存在。突然,“咣当”一声门被打开了,才修急匆匆地冲进屋里说:“快快,有人跳河自杀了,快去看!”
“是谁?”
“谁知道呢,快走吧,大伙儿都走了!”
河流的拐弯处聚集了很多人。人们拥挤着把脖子伸向河边发出各种疑问:“从哪里跳进去的?”“是哪里的人?”“是谁?”等等。这里的河面大约有二十多米宽,河水在这里缓缓地往左转了个弯就逆转方向从对面的断崖边上向前流去了。有一两个人脱了外衣趟到河里左顾右盼地摸索着什么,但也不敢往河中心走,摇着头回来了。周围的人们只是干着急,没什么法子。才修毫不犹豫地脱掉衣服准备跳进河里时,几个老头从后面抓住他骂道:“你想送死吗?不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急多深吗?”才修似乎也感到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
“听说是个女的。”
“应该是华措,和活佛吵架后她往这个河边跑了。”
“不是早就离了吗?”
“是啊,但是分家时活佛没给她那个沙发就吵起来了。”
“就为那个?”
“就为那么点东西?”
我不相信。我什么也不想说,也不想听周围的人们说着的那些话。这些年我耳闻目睹了很多像梦一样的事情,我实在是感到厌倦了。
华措死了。人们都跑去看她的尸体时,只有我一个人低垂着头留下来,毫无知觉。我缓缓抬头放眼望去时,天地间空荡荡一片。这道狭长的河谷寂静一片,这条寂静的河流也缓缓地逆流着。这时,我的视野里模糊地浮现出了以前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渐渐融入到了荡漾的河面上,让我油然而生出一种困顿的感觉。最后剩下的竟是巍然屹立在前方的贡布拉格神山,不远处湍急的逆流河,还有毫无知觉地站立着的我的影子了。
10
我和才修围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着时,中间肯定是少不了一瓶酒的。我俩之间的共同话题早就不存在了,因而这会儿也没什么可聊的。但各自又想找点话题出来。
“拉先也一样,几乎一事无成。”
微微有点醉意的才修想起什么似地说了这句话。今天我的心情也不怎么好,拿起酒杯喝了一口。他侧眼看了看我又说:“实在是很可笑,前天我去州上时看见他了。他和他老婆从大街上迎面向我走来了,他还装作没看见!”
“他的老婆是谁?”
“我俩在饭馆里不是看到了吗?就是她!确实是个傻女人。拉先在大学呆了两年,再呆一年就毕业了,但是她没让他去。”
“为什么?”
“谁知道呢!说是不这样就要离婚。拉先不忍心丢下刚满一岁的女儿就答应了她。但是现在他俩很幸福。”
我不想再问什么了,静静地沉思。平常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听,那怕听见外面有人说话也会很烦。我喜欢安静。他像是知道了我的心思似地冷笑了一声准备继续喝酒时,酒瓶早已空了。
我俩出门时,夕阳的余晖照在周围的大楼上,像是刷了一层红土,鲜艳无比。刚刚结束播音的路口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里传来了十一届亚运会的会歌。歌声淹没了这个闭塞小镇上的所有声音。
“我们亚洲
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
河像热血流
……”
(译自《岗尖梅朵》)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