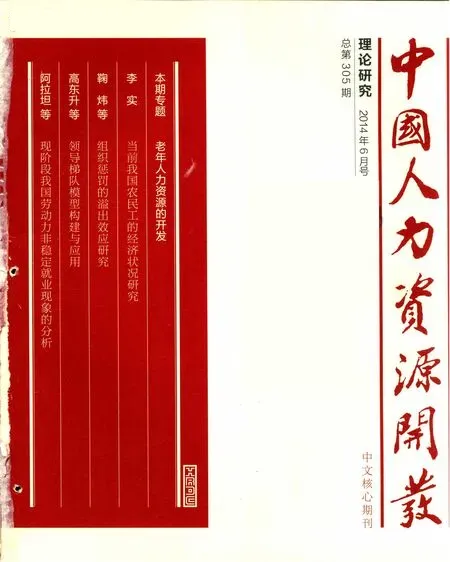现阶段我国劳动力非稳定就业现象的分析——以浙东S市服装加工业劳动力就业情况为例
2014-06-11
●
■责编/倪超 Tel: 010-88383907 E-mail:nc714@163.com
劳动力市场上的非稳定就业(Contingent Employment)现象是近年来国内外劳动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Polivka 和 Nardone(1989) 提出了一个全新概念:非稳定就业也叫权宜性就业(Contingent Work),用以描述劳动就业市场上劳资双方皆不期待雇用关系的持续、工作时数不固定和无预期就业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Kalleberg(2000)将兼职工、租赁工、契约工、外包工等工作者的“非全时性、非延续性和不稳定性”就业状态概括为非典型就业(Nonstandard Employment)。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转型期社会变迁的特点,讨论了中国劳动力非稳定就业与工作无保障现象(胡鞍钢、杨韵新,2001;李强,2002)。刘爱玉等(2012)也曾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不稳定就业问题的基本表现、成因和前景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本文将承接前述研究,集中对服装加工行业的非稳定就业现象进行讨论。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非稳定就业现象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我国的非稳定就业问题则主要出现在以制造业、加工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部门。这一特殊性无疑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相关产业部门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分析我国劳动力非稳定就业现象,就需要进入到具体产业的劳动力就业状况中,这样才能发现其运作的逻辑和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服装加工产业一直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产业类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2011年“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总额为1591亿美元,在主要进出口商品中出口总额仅次于“自动数据处理及其部件”(1853亿美元),位居第二。可以说,服装加工业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中发挥“比较优势”(林毅夫,1988;2003)的主要产业。①但随着近年来国内劳动力价格升高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服装加工业连同其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前景受到较为严峻的挑战。
正是在上述产业环境背景下,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服装行业的劳动力非稳定就业展现出了“组织化”的新特点。这种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表现为服装加工业工人自组织的“炒工”团体,以及在服装加工业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的一种“趋于固化的非稳定就业”态势。
一、服装加工业中“炒工”团体的角色
“炒工”也称“插忙工”,是指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工人们基于地缘、亲缘或其他私人关系网络组织形成的一个流水线生产团队。团队规模从十几人到二十多人不等,团队成员也因擅长的流水工序有所差异。
“炒工”团体一般在工厂和家庭作坊从事服装加工劳动。当地服装加工厂在短时间内需要完成大量订单任务“赶工”,面临用工压力时,工厂会雇佣这些“炒工”团体入驻工厂工作直到订单完成。散布于工厂附近的家庭作坊,其劳动力也主要来自“炒工”团队。“炒工”团体一般承包工厂或家庭作坊的一个或多个生产线,并与其形成短期雇佣关系。劳动报酬结算方式为:在订单任务完成后,企业与“炒工”组织的带头人单独结算。所谓“带头人”是家庭作坊或工厂与寻求工作的工人之间的重要中介。家庭作坊与工厂通过“带头人”可以迅速地招募到能够直接上流水线操作的熟练工人;而“带头人”依据自身做工经验判断每个订单样式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决定是否接单,以及如何组织生产。在S市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上,若干人数不等的“炒工”团体在不同的工厂或家庭作坊的流水线之间流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非稳定就业”。据浙江本地媒体报道,在当地的“炒工”工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在订单旺季“炒工”甚至能占据部分工厂流水线工人的一半以上。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组织化的“炒工”,一方面在数量规模、成员构成和技术熟练程度上的特点能够适应流水线作业的需求,可以快速加入到订单“赶工”任务中;另一方面,“炒工”组织也为工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找寻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此种“炒工”团体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了服装工人的“非稳定就业”。如前文所述,“非稳定就业”具有工人就业时间短且非正式、没有劳动福利和保障等特征,那么,这样一种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目标与分工明确的“炒工”团体的出现,则使“非稳定就业”的现象具有了一种“组织化”的特点。
二、S市服装加工业“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现象的主要参与主体分析
当前服装行业的非稳定就业现象与多数产业工人的农民工身份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要讨论由“炒工”团体所构成的“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这一特殊现象,除了农民工的身份因素之外,我们仍需进一步考察S市服装加工业所处的产业背景,以及“炒工”团队运作环境中的几个主要要素:企业、家庭作坊、“炒工”团体“带头人”和“炒工”工人。
1.服装加工企业
通过了解S市11家服装加工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们发现当地服装加工业呈现出高度出口外向型的特征,并处于全球服装产业链条的末端(见表1)。

表1 浙东S市11家服装企业基本情况表③
对于当前出口导向型服装产业所面临的经营压力,学界已有诸多探讨,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点:(1)“三率两价”(汇率、利率、出口退税率;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对服装企业的综合影响(吴哲,2008)。(2)新《劳动法》客观上造成的挤压服装企业利润空间的结果(李钢、沈可挺、郭朝先,2009)。(3)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导致出口型服装企业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等。
我们在S市观察到的“炒工”现象,与该市服装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及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宏观产业局势给S市服装业的生产经营带来的压力,具体表现为订单总量减少和生产工期缩短;加之服装企业本身具有季节性生产周期,出现了企业在订单淡季无力雇佣大量工人,而在订单旺季又急需提高生产能力的问题。为了缓解此种周期性压力,雇佣非稳定就业工人成为了企业的一个选择。
在订单旺季,短时间内招募熟练的生产线工人,并实现高效率流水线人员配置,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而雇佣“炒工”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经验策略。除此之外,由于一些大客户要求订单必须在工厂内部生产,企业需要向客户委派的“验厂专员”证明自己的工厂有能力完成订单,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工厂通常选择经验和技术水平高的“炒工”入驻工厂完成生产。
2.订单分包与家庭作坊
如表1所示,接受调查的11家服装企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将订单外包。例如,企业PH010外包比例高达50%,而外包比例最低的PH003和PH005这两家企业订单外包率也达到了10%。此外,当地服装加工企业劳动力流动比率基本保持在15%至30%之间。根据企业PH010和PH006的负责人介绍,订单外包分为服装整件外包和工序外包。因整件外包相对节约成本,在我们调查的11家企业中,除了企业PH006之外,其他几家企业基本采取了整件外包的形式。
如此高比重向外发包的订单,主要流向工厂附近民宅中的家庭作坊。家庭作坊多由曾在工厂工作多年、有一定的流水线管理经验的工人所开办,主要从工厂接收外包的加工订单。家庭作坊的劳动力主要由非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构成。这些工人与家庭作坊经营者之间形成短期的雇佣关系:雇主与工人之间并不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工人根据雇主手中订单的数量多少、产品种类导致的报酬增减以及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频繁地更换雇主和工作岗位。在这种劳动力流动性极强的状况下,家庭作坊完成外包订单任务就面临了一定的风险,此时雇佣“炒工”团队也成为家庭作坊完成生产、规避风险的重要策略。
3.“带头人”的角色
在这样劳动力流动率极高的“非稳定就业”市场上,“炒工”团队的“带头人”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一则访谈中我们接触到了一个“炒工”团体的“带头人”徐师傅。他曾在两个“炒工”团体中做过工人,当时的“带头人”分别是自己的表哥和在老家的学艺师傅,最终都因薪酬过低而出走。在这个阶段,他不但掌握了流水线作业的技术,也积累了自己成为“带头人”的人力和社会关系资源,逐渐组织起了以弟弟、妻子为核心的“炒工”团体,规模曾一度达到30余人。不过,徐师傅后来也遭遇了自己弟弟另起炉灶、挖走工人的打击。④
通过徐师傅的经历,我们了解到带头人角色的特点:(1)“带头人”是“炒工”团队的组织者,通过熟人网络组织生产、约定薪酬、寻找合作老板、带领“炒工”进驻家庭作坊或工厂工作。(2)“带头人”不从事生产,一般负责管理生产流程,在收入分成中占较大比例,与工人之间形成一种非正式的管理关系。(3)这种非正式的管理关系和收入分配方式,使得“炒工”团体呈现出相对不稳定的特征,团体成员独立出来“单干”的情况经常发生。(4)“带头人”的角色需要具备一定的服装加工经验和评估生产、交易风险的能力,并非任何一个工人都能胜任。例如,徐师傅的弟弟另起炉灶后不久,就因为接单不够慎重,无法按照要求生产出成品,又不得不来找徐师傅帮忙。
4.“炒工”工人的逻辑
就访谈材料来看,工人组成这样一个“炒工团体”的主要原因可能有:
第一,“炒工”的工资高于普通工人,准确而言是单位工作时间工资较高。以“质检”工序为例,“炒工”的工资要达到13元至15元一小时,远高于当地工厂合同工人8到10元的价格。由于服装行业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相对于成为正式的产业工人,他们更倾向于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报酬,即加入“炒工”团队,以改善家庭在乡村的生活水平。
第二,对于没有技术和经验的农民工而言,加入“炒工”团体可以较快、较全面地学习到相关的生产技术。如徐师傅介绍,在他过年回家时,常有亲友希望他的“炒工”队伍能带上他们孩子,不需要支付工钱,只是希望孩子可以学习到服装缝纫技术。
第三,年青工人认为工厂的管理制度过于严苛,而加入“炒工”团队工作时间则相对灵活。陈玮(2013)的研究表明,工厂女工一旦组建了家庭,为了满足来自自我或他人的家庭角色的期待,倾向于退出工厂,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工作。
综上分析,我们对于当前我国服装加工业劳动力的“非稳定就业”现象进一步形成如下结论:(1)与20世纪末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下岗工人再就业时的非稳定就业不同,服装加工企业的非稳定就业,受到处于跨国产业链末端这一“结构性位置”的影响。(2)相较于通常意义上的非稳定就业,由“炒工”团体构成的劳动者非稳定就业现象表现出以“带头人”为核心的自组织特点。(3)企业、“带头人”和工人之间的紧密合作,使非稳定就业在S市劳动力市场呈现“固化”的趋势,即更多工人加入到“炒工”团体谋求工作,并长期处于一种非稳定的就业状态中。
三、产业链末端的“非稳定就业”的不稳定性
在S市服装加工业中出现的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现象,本质上是由于服装加工业处于国际产业链条末端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位置,产生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非稳定的结合方式,背后包含着来自资本和劳动力双方面多主体的运行逻辑。表面看来,这样一种“结构性位置上的非稳定就业”,提高了“炒工”工人的劳动价格,缓解了企业需要应对的经营压力,吸收了家庭作坊的小额资本参与到生产组织当中,并给予了少数具有能力的劳动者晋升为组织者或管理者的机会。但是从长远来看,由组织化的特征所带来的“非稳定就业的固化趋势”,势必给服装加工业的总体发展带来问题。
首先,当地服装企业工人的流动性在提升。接受调查的11家服装企业的工人流动率颇高,大致在20%至30%之间。在“炒工”现象出现后,相当一部分工厂工人转向加入到“炒工”团体当中,增加了服装企业用工的不稳定性——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能力难以保障,在更高程度上受到“用工荒”的威胁。部分企业为了保证用工的稳定性,甚至采取扣押工人工资的手段,而这又进一步恶化了劳资关系。此外,雇佣“炒工”团体增强企业应对“总订单量减少、单位时间订单量增加”等问题的能力,使企业在经营压力面前更具弹性;但客观上,却阻碍了企业通过改善产品结构、提高管理水平等方式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可能,这对整个服装加工业的产业升级带来了负面影响。
其次,在组织间合作方面也存在着“不稳定性”,具体表现为发包层级可能是不稳定的。在订单发包过程中,工厂、家庭作坊和“炒工”之间的转包链条被不断延长,形成“层层转包”的现象,即:更多人变成中间环节,通过转包订单赚取利益,最终会导致链条终端的工人收入进一步减少。这一现象在另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中已较为普遍,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如果进一步渗透到服装行业,最终也会对服装行业本身产生不利的影响。
最后,这种“不稳定性”也表现在组织内部。“炒工”团体本身也是十分不稳定的非正式组织,“带头人”与“炒工”之间的纠纷也时有发生。由于“炒工”团队是一种非正式组织,相关机构难以介入干预,《劳动合同法》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程度将会大大降低。劳资纠纷难以在法律框架下获得解决,无疑也为服装行业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转带来了挑战。
四、“非稳定就业”现象的隐性威胁
西尔弗(Silver,2003)提出了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的趋势。本文所研究的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现象,则展现了资本构筑的全球产业链条的另一侧面: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沿着资本运作路径一直波及到产业链末端,对劳动力要素产生了新的影响。作为对这一冲击的回应,不同经营主体(企业、家庭作坊)的经营逻辑、工人的谋生逻辑以及生产组织者(“带头人”)的组织逻辑共同构造了劳动力市场上特殊的组织化非稳定就业现象。
通常意义上,劳动力的非稳定就业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较大的用工压力,但S市服装业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炒工”团体,不但缓和了企业的用工压力,甚至更符合企业应对当前经济形势下“订单总量减少、单位时间内的订单量增加”的需求。这一特殊的现象背后是一种非稳定就业的劳动力组织化的现象,代表着“非稳定就业”的一种固化的趋势。此种“固化”并不是指非稳定就业劳动者人数保持在一定规模,恰恰相反的是,非稳定就业因劳动者的组织化特点趋向于一种常态,人数在不断的增加。通过进一步讨论,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劳动者“组织化非稳定就业”的现象,从长期来看阻碍了整个服装加工行业的产业升级,从而对整个服装行业的发展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威胁。同时在劳动力的权益保障方面,“炒工”团体的出现也给在法律框架下规范劳动市场带来了挑战。
因此,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虽然在短期内对企业经营和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从整体和长远来考察是值得重视的特殊现象。对于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在权益保障方面的问题早已引起学界和相关部门的关注。通过本研究,我们认为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这一特点,为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工作造成了更为复杂的困难。
首先,“炒工”带头人作为一个介于劳动力与企业工厂之间的特殊角色,在生产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现象的普遍存在,极可能成为“层层转包”订单的土壤,让“带头人”从中获利,进而减少农民工的劳动报酬。
其次,劳动力团队的组织化过程,越来越脱离地缘或亲缘的联结关系,亦即“炒工”工人的结合、团队的组织化逐渐脱离基于地缘和血缘纽带的组织化逻辑,而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基于生产流水线需求重新进行再组织。这一变化带来的后果是,在原本缺少法律合同硬性约束的劳动关系中,一些基于乡土文化伦理道德的约束因素也在逐渐退化。在这样一个既无硬性的法律制度约束,软性的制约因素又逐渐淡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带来劳动工人团队在重新组织过程中的“黑恶化”问题,造成带头人对团队工人的盘剥。
再次,“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现象增强了劳动力市场上淡化劳动合同作用的趋势,使得原来就已施行困难的社会保障更加难以有效贯彻。从生产链条的构建来看,工人、“带头人”和工厂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但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这种合作关系又依赖于十分复杂的非制度化操作。工人与“带头人”之间的关系难以在法律框架内获得恰当的定义;“带头人”与工厂负责人之间的个人合作关系,也没有促成工人与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因此,工人的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障在此种复杂的关系链条中更加难以落实。对此,浙江一些地区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介入和规范“炒工”市场⑤,其主要方式为“督促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纳入税务机关正常管理”等,试图通过对“炒工”团体赋予“劳务派遣公司”的法人身份,实现政府监管。
五、政策建议
对于上述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我们认为不仅要对“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的现象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探索处理的可能。这种可能也应该从农民工工人的需要与劳动力“组织化”的特点入手,需要企业、地方政府监管以及制度性政策三个方面的措施来应对:
第一,虽然“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是一种农民工自组织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用工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很多企业未能很好地保障劳动者工伤、医疗乃至劳动报酬等权益,从而又强化了非稳定就业的组织化现象。如前所述,“组织化的非稳定就业”为企业应对经营压力带来了一定的灵活性,但从行业的长期发展来看,这一现象对于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更难以改善其所处的产业链条中结构性弱势地位。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无疑是“饮鸩止渴”。因此,企业应认识到稳定的劳动力就业对其发展的重要意义,保障劳动力的基本权益。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就是在为企业具备长期、稳定的劳动力提供保障,更是在为企业在结构性弱势地位上谋求更具抗风险能力的发展提供保障。
第二,对于“炒工”现象,我们并不能因其潜在的问题直接取缔或清除。此种做法不仅在操作上不现实,而且也会直接伤害工人和用工企业的利益。因此,在承认此类组织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将其纳入到监管渠道中来,应是工作的着眼点。基于浙江部分地区的经验,在登记既有“炒工”团队,使之具有劳务派遣公司的法人身份的同时,政府部门可加强与这些劳务派遣公司之间的接触,帮助构建劳务派遣公司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这一过程,一方面提供了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定义工人、带头人(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人)和企业之间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就业平台可以更为直接地了解到组织化的工人团队就业及相关权益的保障情况,对“层层转包”、工人团队“黑恶化”进行有效的监管。当然,如何构建兼具服务与监管职能的就业平台,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摸索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当地劳动监管、工商部门以及企业和街道工会的共同合作。
第三,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一直是当前改善农民工待遇和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实现农民工在城市中“落地”,才能使得农民工工人分享城镇发展福利,且在劳动力市场上更自由、稳定地实现就业。这就需要在农民工的劳动、医疗、养老及子女教育方面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特别在子女教育方面进行改革,这是减少劳动力流动性的较为有效可行的举措。在像S市这样的高度密集的产业区,建立供农民工子弟就学的学校十分关键,这不仅仅解决了留守儿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劳动就业方面,提供了“稳定”的因素。诸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得以解决,势必增加他们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甚至某一企业稳定就业的可能。因子女教育产生的稳定就业需求,可能通过农民工所处的劳动组织产生扩大化的效应,进而实现更多的稳定就业。
综上所述,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组织化非稳定就业”现象有其自身的产业背景和运作逻辑。在客观地对待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一特殊现象的同时,需要企业经营、政府监管和制度改革等多方面的合作,才能获得妥善解决,进而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秩序,保障劳动者权益,使产业稳定、健康的发展。
注释
①据中国海关《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纺织品.成衣出口额占全球出口份额已从2000年的18.3%增长到2010年36.9%;2011年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欧盟(21.5%),美国(15.8%)以及日本(11.07%),占总额的48.82%;而出口服装单价,也从2005年的每件1.82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每件3.33美元。参见:中国海关:《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2011-2012》。转引自:中国-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研究课题组:《2012-2013年度大上海地区服装行业及劳工状况报告》。
②参见http://www.cnjxol.com/xwzx/jxxw/jjxw/content/2008-08/23/content_810002.htm。
③依据访谈调查资料整理。为保护相关企业相关权益,我们对我们将这11家企业的名称以企业代码代替。
④访谈材料 Case 27 访谈人员:卢晖临、陈玮、薛红、涂真。
⑤参见:http://news.163.com/10/0726/05/6CGC971600014AED.html。
1.陈玮:《从工厂到作坊的选择——服装工工人的生产政治》,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2.胡鞍钢、杨韵新:《就业模式的转变: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状况分析》,载《管理世界》,2001年第2期,第69–78页。
3.李钢、沈可挺、郭朝先:《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提升出路何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调研》,载《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9期,第36–46页。
4.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3–25页。
5.林毅夫:《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进行结构持续升级、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载《中国经济观察》,2003年第2期, 第1–5页。
6.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载《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7期,第4–8页。
7.刘爱玉:《社会学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刘爱玉:《就业不稳定与无保障:基本表现、成因与前景》,载《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04期,第84–90页。
9.吴哲:《纺织服装企业面临“三率两价”压力》,载《南方日报》,2008年4月18日。
10.中国–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研究课题组:《2012-2013年度大上海地区服装行业及劳工状况报告》,2013年4月。
11.Kalleberg A.L.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 Part–time, temporary and contract work.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1): 341–365.
12.Polivka A.E, Nardone T.On the definition of contingent work.Monthly Labor Review, 1989, 109(12): 9–16.
13.Silver B.J.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