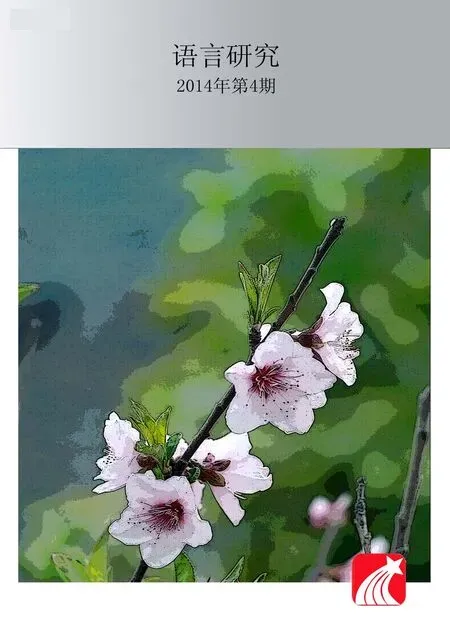《马氏文通》前西人的汉语量词研究
——以《语言自迩集》为核心
2014-05-30宋桔
宋 桔
(复旦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433)
一 引言
丰富的量词系统是汉语的特色之一,马建忠(1898)称之为“别称以记数者”,归入形容词。黎锦熙(1992/1924)第一次提出“量词”这一名称,列入名词;王力(1984/1947)称之为“单位名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正式确定了术语“量词”,并将其归为一个独立的词类。
一般认为关于汉语量词的“现代化”研究多始于1989年(何杰2001),但是“研究中国语言学是不能限定国籍的”(周法高1980:16),在《马氏文通》建立中国现代语法研究体系之前,来自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外交官们在传教、贸易、政治等因素对汉语巨大需求的影响下自发编写了一批用于汉语教学的论著。(贝罗贝2000,何莫邪2000,张西平2003)虽然这些文献中的绝大部分是面向汉语教学的,但事实上保留了西方学者在拉丁语法体系下对汉语语言规则进行早期探索的珍贵资料,其中的一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汉语研究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在姚小平(1999)、张西平(2003)等的带动下,借助《马氏文通》前西人汉语研究的讨论,此类文献逐渐成为汉语、对外汉语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以下称威氏)编写的《语言自迩集》(Yü-yen Tzŭ-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1867/1886/1903,以下称《自迩集》)①1867年版主编威妥玛,第二版由威妥玛和禧在明(Walter Hillier,1849-1927)联合编写,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有较大修订;威氏去世后的第七年(1903年),别发洋行整理、发行了第三版,是第二版的删节本。该书的编写者除威妥玛等西人外,还有应龙田等一批中国文人,以下以“编写者”概指此编写团队。关于中方编写人员,参见宋桔(2012);关于《自迩集》三版间的具体修订以及对于其中保存资料的价值,参见宋桔(2013)。中汉语量词的相关内容被誉为“第一次成功地讨论了现代汉语的量词及其语法功能”(张卫东2002:2)。
《自迩集》三版中的“量词章”以及西人编写者通过英文翻译、注释阐释汉语量词语义、用法的具体内容构成了《马氏文通》前西人汉语量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文将以《自迩集》为核心,结合16-19世纪西人与现代汉语学界对汉语量词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语言学史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的双重视野下论证西人早期汉语研究的特点与价值。
二 16-19世纪的量词研究概述
西方传教士从16、17世纪就开始了汉语量词的研究。最早在一些字典、辞书中出现了个别的量词列举和释义,后来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论述,甚至成体系的词表。马西尼(2008:61)指出“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1652年编撰的《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是西人所编注意到汉语量词用法和特征的第一本书”。
随后,意大利方济会传教士叶尊孝(Basillio Brollo,1648-1704,亦称叶宗孝)编写了两部汉语拉丁语词典,即《汉语拉丁语部首词典》(Dictionarium Sinico Latinum,1694)和《汉语拉丁语语音词典》(Dictionarium Sinico Latinum,1669),附录了83个量词。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亦称弗朗西斯科•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1703)在第十二章介绍了“数词和量词”,整理了56个量词,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也解释了79个量词。
至19世纪中期,西人汉语量词研究已颇具深度。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的《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1857/1864)①1857年伦敦会印刷处(London Mission Press)初版,1864年上海美华书馆(Presbyterian Missionary Mission)再版。本文引自1864年版。是笔者所见文献中收录量词数目最多的,区分出了“Distinctive numeral particles(特殊量词)”、“significant numeratives(核心量词)”、“collectives numeratives(集体量词)”、“numeral particles to verbs(动量词)”四类,合计183个。
初版于1867年的《自迩集》在“言语例略”章(Yen Yū Li Lūo,the Parts of Speech,以下称“词类章”)专列了一节“THE CHINESE NUMERATIVE NOUN(汉语量词)”,列举并详细解释了65个汉语量词的词义和用法,并在全书范围内对量词的实质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在基本观点、词表、阐释模式上充分展示了《马氏文通》前西人对汉语量词研究的继承性、独创性与现代性。
三 量词的实质:分类与陪伴之争
《自迩集》的编写者这样界定量词的实质②引文的中英文内容、标点均自《自迩集》原文,“翻译”为第二卷对第一卷的英译,“注释”为第二卷页下注文。由笔者翻译的内容用( )标出。《自迩集》原文繁简混杂,引文皆转录为简体,有需要则注明。引文出处以简略形式著录,格式为“章节名 版本.卷数、页码”,如“词类章1.1p.282-283”,即该引文出自《自迩集》第一版第一卷,第282-283页,下同。:
至于汉话里头那名目、又有个专属、是这么着话里凡有提起是人是物、可以有上头加一个同类的名目、是要看形像的用处、做为陪伴的字、即如一个人、一位官、一匹马、一只船、这四个里头、那个字、位字、匹字、只字、就是陪伴人官马船这些名目的。(《词类章》1.1p.282-283)
(翻译)[THE CHINESE NUMERATIVE NOUN.]Chinese noun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the following peculiarity: whenever a noun, person, or thing occurs in Chinese,there may be prefixed to it an associate (or attendant) noun, between which and itself there is, with reference to form or use, an affinity.(《词类章》1.2p.105-106;2.1p.486)
威氏认为可以在汉语名词前加一个与它同类的名词,作为该名词“陪伴的字”,即“an associate (or attendant) noun”,如“个”、“位”、“匹”、“只”等,是隶属于名词的“附属成分”。“陪伴的字”第二版改为“陪衬的字”(《词类章》2.1p.344),突出了名量间的主次隶属关系。
《自迩集》全书并未明确将“陪伴的字”这个词组界定为指称量词的“术语”,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准术语”可能曲折影响了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对汉语量词的分类界定①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根据宫胁贤之助的《北京官话支那语文法》(1919)提出的“陪伴字”来指称“个体量词”。陈望道曾在《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1972)对这一术语提出质疑,黎锦熙(1978:7-8)反驳论证,给出的《北京官话支那语文法》的原文为“连接于数词之后表示事物种类性质的那种词叫做陪伴词。……如三碗饭、八刀纸、那一张椅子、这一件事情、买了一件好衣裳”。结合《自迩集》第一版出版后引入日本,及其对明治时期汉语官话教材的影响来看,我们推测宫胁贤之助所用的术语“陪伴字”很可能就源自《自迩集》,但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的文献考证。。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翻译借用“[ ]”补充的“THE CHINESE NUMERATIVE NOUN”。单词“numerative”从中世纪英语动词“numerare”派生而来,意思是“to number(读数、计数)”,同表示数词词类的“numerical”同源②结合艾约瑟(1864:127)的论述“Words such as pair, set, suit, in a pair of shoes, a set of china, a suit of clothes, are called Numeratives by De Sacy”(像“pair(双)”、“set(组)”、“suit(套)”这样的词被 De Sacy 称作“Numeratives”),术语“Numeratives”很可能最早由法国的语言学家Antoine Isaac, Baron 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在19世纪初发表的一些阿拉伯语的教科书中用过,但具体哪本教材尚未能确认。释义可参看陆谷孙(2007:1339)。。这一英文术语正是威氏对汉语量词的定性,分析这一定性的意义需结合《自迩集》前西人对汉语中这类词的指称。
据马西尼(2008:61)引用的拉丁原文,卫匡国《中国文法》(1652)和叶尊孝《汉语拉丁语部首词典》(1694)选用的术语皆与“Particulae”相关。万济国《华语官话语法》(1703)用西班牙语“De los Numerales”来指称量词。可见,三者都是将汉语量词与数字一起讨论,归入“Particle(小品词)”范畴的。
进入 19世纪,另一种观点将汉语量词等同于名词来讲(内田庆市 2009:212)。他们采用的术语“Classifier”的实质即“分类、计算”③这个术语强调汉语量词可以作为名词的分类依据,现今大多的英汉词典也都采用了这个术语。如《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英汉双解》(第三版,第92-93页)、《牛津英汉双解语言学词典》(第67页)、《英汉大词典》(第342页)。。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汉语札记》(Notitia Lingae Sinicae,1728/1831/1847)④该书1728年在广州写成,1831年马礼逊通过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出版了拉丁文版,1847年美国传教士裨雅各将之译成英文,在广州出版。本文参考为1847年英译本。1847年版的英译者裨雅各(James Granger Bridgman,1820-1850)就用这个词来指称量词⑤笔者未见到拉丁文原文,此处的英文术语翻译应与裨雅各的看法有关。英文原文为“The author takes leave of this subject rather too hastily, and the beginner would receive a very erroneous idea of the number, uses, and importance of the Classifiers,from these few lines.)”(马若瑟1847:30)。在接下来的注文中裨雅各还说“要想得到更详细的叙述,可以看《拾级汉语》(Easy Lessons in Chinese 1842)一书的第7章第173页”(For a full list of them, see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chap VIIth,page173)。《拾级汉语》中记录了28个常用量词和42个次常用量词,但说明的对象是广州话,故未列入本文的比较对象。;美国人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21-1902)与张儒珍合编的《文学书官话》(Mandarin Grammar,1869)中,量词章的标题为“分品言”,显然高丕第也认可“classifier”这一术语。《官话口语语法》的论述最为明显,直接将量词称为“a secondary class of nouns(次级名词)”(艾约瑟1864:127)。马礼逊(1815)也认同这一分类,但他在解释时更加强调了量词与数字相关的计算功能。
威氏采用“陪称的词”和“Numerative”的做法显示了他与“名词范畴”派相近的观点。《自迩集》中,他为选用“Numeratives”进一步做了一番说明:
总之,细察那陪衬字的实用,像是把一切能分不能分的名目明白指出的意思。何谓不能分名目?即如皇天之天、后土之土,是独一无二不能分晰的专项,那儿有陪衬的字样呢?那些有类能分的总名目,要分晰时,此陪衬字样,颇为得用,其用谓何?乃能指出所说的名目为总类之那一项。
如今把那些陪衬的字眼儿,连正主的各名目,一并开列于左,为学话的便用。(《词类章》2.1p.344)
(翻译)[These attendant nouns, therefore, will be spoken of henceforth as Numeratives,] and a list is now given for the use of the student of all the numeratives in connexion with the nouns to which they are attached.(《词类章》1.2p.106;2.1p.486)
此段是对量词最核心的阐释,第一版的“明白指出一切能分不能分的名目”,在第二版改为“那陪伴字的实用,像是把总类专项分晰辩明的意思”(《词类章》1.1p.282),对汉语量词的功能有了更为明确的概括。
结合引文举例可知,“陪称字”的实质即区分两类名词:一类是指称可再细分事物的“总括名词”,一类是指称不能再细分、表独有事物的“专有名词”(如“皇天”、“后土”等)。陪伴字可与前者组合,如“匹”使“一匹马”从名词“马”的大类中区分出来,使原来不能用于计算的总括类名词“马”借助“一匹马”的形式应用于计算。
英文翻译在最后一句前用“[ ]”添加了一句说明“These attendant nouns, therefore, will be spoken of henceforth as Numeratives(所以这些陪伴字从今往后称为Numeratives)”。可见,威氏也认可汉语的量词是名词的一部分,但他又认为量词最核心的作用是使它修饰的普通名词指称的事物可用于计算,故《自迩集》不再用“attendant nouns(陪伴词)”,而以“Numeratives”来指称这一类词。
四 量词的分类:中外同归
《自迩集》按是否可译将量词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英语对译词的量词,如“head(头)”、“stand(架)”、“fleet(艘)”等(《散语章》2.2p.4)。另一类是在英语中无对应形式,如“一个人”这样无法直译的数量名短语:
Where it comes between a number, one or more, and it’s substantive, it cannot be translated.For 一个人, one man, 三个人, three men, the Cantonese, in the broken English which is the lingua franca of the open ports of China, would say, “one piece man”, “three piece man”.We have nothing analogous to this in our language①译文:当某个量词在一个表示“一”或多的数字和实词之间时,这种组合中的量词(在英文中)是不能被翻译的。例如“一个人(one man)”, “三个人(three men)”, 在广东的洋泾浜英语中会翻译为“one piece man”,“three piece man”在英语中没有这种相同的情况。.(《散语章》2.2p.4)
在此,编写者以洋泾浜英语“one piece man”的错误表达为对比,凸显了这类结构的英汉差异。
在威氏之前,艾约瑟(1864:133)也曾指出可翻译出来的量词大多是表示事物性质或用于测量的词,但与威氏的举例论证方式不同。
现代汉语语法学界普通认为用于计算不可计数事物的量词(或这样用的名词)是各种语言都有的;对其它可计算的事物也使用量词则是汉语的特点之一(吕叔湘1991,王力2004/1980)。而应当承认,早期西人对汉语量词分类的思路与之是类似的。
五 量词的功能:陪衬、替换与泛指
功能方面,《自迩集》将其集中在三个方面:陪称名词、在上下文替换名词、在名词后表示泛指总称,以下分述三类功能。
首先,编写者指出量词最主要的功能是与名词结合,量词“个”、“位”、“匹”和“只”就是“陪衬人、官、马、船这些名目的”(《词类章》2.1pp.344-345)。这一功能在形式上表现为:一方面“大部分量词都不能脱离它们所联系的名词单独使用”(《散语章》1.2p.85);另一方面名量搭配是有规则的。这种功能是西人对汉语中数量名结构这一语言形式的认知。
其次,编写者也指出在上下文语义明确时,量词可单独使用:
又有本名目刚先提过、接着说的话、、设若有人买了牛、他告诉我说、我昨儿买了牛、我问他买了多少只、他回答买了十几只、这就是牛字作为本名目、那只字就是陪伴的、有陪伴的替换本名目、本名目就可以不重复再提了。(《词类章》1.1p.282;2.1p.344)
这种用“陪伴字替换本名目”的目的是使叙述更加简洁,避免名词的多次重复。
除《通用汉言之法》(1815)提到的量词具有“mentioning one of a thing(提及一个事物的用法)”外,目前未见类似论述。《自迩集》的这一分析应该与其以当时实际使用的口语为教学语言相关。
最后,《自迩集》还关注了无数词时量词直接附于名词后的情况。关于这一结构的语义功能,在不同版本出现了两种界定。
第一版中,编写者指出“量+名”组合有两种功能,一是表示名词的复数,另一个是表泛指或类属:
Some numeratives are occasionally placed after the noun with which they are joined, and whenever they are, that noun must be construed as in the, or.(《散语章》1.2p.85)有时一些量词放在它联系的名词的后面,只要这样,名词就一定要被分析为复数,或者是表示类属的词。在第一版的例证注释中,编写者也提到了指示复数的功能:
这陪伴的字、都不但竟是加在上头、也有可以随着本名目说的、比方话里说马.船.的.大.数.儿.、也可说马匹、船只这么样。(《词类章》1.1p.282-283)
(翻译)These attendant nouns are not exclusively prefixes of the nouns they accompany; They sometimes follow them.In speaking, for instance,, we may say 马匹(horses),船只(shipping).(《词类章》1.2p.105-106;2.1p.486)
编写者认为“马匹”、“船只”这类结构表达的是名词复数,即“很多马”、“很多船”的意思。
在第二版中,编写者删除了有关表复数语义的内容,全面转向了“泛指”论。其中最明显的是以下这段文字(《词类章》2.1p344-345):
这些陪衬的字、不但竟能加之于先、也有加在名目以后之时。、也能说马匹、船只。
编写者仅保留了第一版的一种界定,即“马匹”、“船只”用于整体性地概说这一名词所指事物,属于泛称性、类属性的功能。第二版新增的注释更明确地说明了这一功能:
那一条大道中间儿走、两旁边走人。On that high road the middle is for carts and the two sides for people on foot.
(注释)Note that 车is generalized by the numerative following instead of preceding it.(《散语章》2.2p.126)“车”被在它的后面的量词泛化了,这个量词不是在“车”的前面。
“辆”使“车”成为类指性词语,不再具体指哪辆车,而是泛指“车”这个概念。
这种“名量式”起源于宋以后,元明小说中已有“官员”、“船只”、“马匹”、“车辆”的说法。王力(1984)也认为这是一种量词“称数而用”的功能,是词汇复音化的结果,可用于表达总称的概念。可见,《自迩集》第二版修订后的论述与现代学者的界定已比较接近。
六 《自迩集》量词表及语义分析的创新
《自迩集》共计列举解释了65个量词,与前代相比所涉数量并非最多,但阐释部分较为突出。在列举量词后,不仅解释词义、说明用法、列举实例,还通过英文内容补充说明,增加了相近量词的比较分析等。以下总结了《自迩集》量词分析的三点创新:
(一)所选量词:继承前贤
由本文附表可见,《自迩集》所列65个量词的绝大多数在前人论述中都出现过,其中17个常用量词,如“个”、“位”、“张”、“只”、“句”、“卷”等,从卫匡国(1652)量词表一直延续到《自迩集》。
《自迩集》首见的量词仅“八抬嫁妆”的“抬”和“一垜砖”的“垜”。其他如《自迩集》与卫匡国(1652)和艾约瑟(1864)共有“扇”,《自迩集》与万济国(1703)和艾约瑟(1864)共有“篇”、“捆”、“桩”,马礼逊(1815)与艾约瑟(1864)共有的“架”、“方”,其中仅艾约瑟(1864)和《自迩集》共有的是“剂”、“处”、“副”、“棵”、“道”和“堵”。这些兴替不仅体现了西人研究者在语体、方言及选词标准上的差异,也可作为汉语量词演进的辅助资料。
据全文排查,我们推断威氏在编写量词表过程中参考了艾约瑟(1864)量词表,理由有以下两点:
首先从所收词汇来看,《自迩集》64字表与艾约瑟表的近似度最高,甚至排序也与艾约瑟(1864)“Distinctive numeral particles(各类量词)”中前48字表几乎完全一致,仅删除了其中表示牛的“牸”、表示树木的“株”、表示羊的“腔”、表示事件的“端”、表示水果的“枚”等偏书面的词,添加了艾约瑟(1864)后续词表中“间”、“句”、“捆”、“粒”等口语常用词。
若排序的一致可用声母音序来解释的话,那么《自迩集》中针对《官话口语语法》量词解释的修正,则是威氏参考了艾约瑟更直接的证据。以下仅举一例:
艾约瑟指出“‘帖’是一张纸、一张卡的意思。如‘一帖膏药’、‘两帖金箔’”(艾约瑟1864:136)。威氏针对性地指出了他认为正规的字形“贴”,并在“贴”的用法上作了修正:
贴:除了一贴膏药没别的话、(《词类章》1.1p.273)
贴:除了一贴膏药没别的用处。(《词类章》2.1p.337)
即“贴”仅用于“膏药”,用于“金箔”含义不同,且全书未见作量词的“帖”。可作比较的是,“帖”在艾约瑟之前也被视为量词,马礼逊曾指出“‘帖’是投递给官府的请愿书或求见函的量词,如‘奉禀一帖’”,可见《自迩集》的阐释不是针对《通用汉言之法》(1815)的。
(二)量词语义、用法分析的创新性
虽然《自迩集》与《官话口语语法》所选量词表较接近,或者说威氏是在艾约瑟大量词表中选取了一部分当时北京官话口语常用的量词构建了《自迩集》表。但通过两者原文的比较,我们认为威氏的创见凸显于《自迩集》丰富而细致的词义和用法阐释之中,特别是在量词搭配理据、近似量词语用、语义比较等方面。
《自迩集》尤其注重某个量词与具体名词组合的理据,指出“要看形像的用处”(《词类章》1.1p.283),即参考它的性状、功能及名量语义间的密切程度,与前人重搭配举例的论述不同。
一方面,编写者注重将名词与量词的本义或引申义结合起来。如指出“封”的本义是封地,之后引申为封印,再引申为“把……封起来”,这个动作的结果就是“含而不露”(to keep concealed),故可与把文字封起来的“信”搭配(《词类章》1.1p.278;2.1p.341)。又如“文”,前人仅指出可搭配“铜钱”:
文the numeral of Chinese copper coin, which foreigners call cash.(马礼逊1815:58)“文”是铜钱的量词,外国人成为钱。
文the numeral of copper cash.(艾约瑟1864:133)“文”是铜钱的量词。威氏则进一步将“文”与中国文化中钱币的铸造历史结合起来(《词类章》1.1p.272;2.1p.344):
文、那文字除了铜钱之外、不当陪伴字样、问其原由、是周朝铸钱、上头加字文的时候儿起的。
即因周代铸币上开始有了文字,故可用本义为“纹样”的“文”来陪称。虽然解释本身与事实有所出入,但这种结合文化的教学方式是直到今天仍被提倡的。
另一方面,编写者擅长由名词描述的形象、动作入手联系量词的用法。如“管是中间儿空的横长东西的陪衬字”(《词类章》1.1p.276;2.1p.339)、“一捆柴火、一捆草、一捆葱、这些个都是因为有束在一块儿的意思”(《词类章》1.1p.276;2.1p.339)、“因为门合页的外形样子像扇子,故可把‘扇’作为‘门’的量词”(《词类章》1.1p.276;2.1p.338)等。
与形象相关如“粒”,马礼逊(1815:32)与艾约瑟(1864:135)都用英语中表示谷物的单位量词“grain(颗粒)”来解释“粒”的语义。威氏则指出“一粒米、一粒丸药、都是指那东西的形像而论”(《词类章》1.1p.276;2.1p.339),在论述中凸显了“粒”与所描述事物小而圆的形象的关系。
与动作相关如“刀”,前人的解释注重“一刀纸”所指的具体数量,马礼逊指出“‘刀’是一定数量纸的量词,例如‘一刀纸’是一定数量的纸;100张”(马礼逊1815:55);艾约瑟认为“‘一刀’即指一百张或多于一百张纸包在一起”(艾约瑟1864:141)。《自迩集》在数量的说明上比较模糊,但重点解释了为何可用“刀”作量词(《词类章》1.1p.254;2.1p.337):
刀、刀就是一刀纸这一句话里用的。。
即用“刀力切得开”是这里可用“刀”作为“纸”的量词的理据。
由具体词义联想量词的搭配规则拓展了前代解释的范式,为汉语学习者习得量词提供了直观、形象的依据,极具实用性。某些内容甚至可称为今天对外汉语教学界从认知角度探究量词语义、语用特征等问题的最早实践(参见王汉卫2004,李计伟2006,李月炯2007,缑瑞隆、黄卓明、刘钦荣2009等)。
(三)重视近似量词间比较
在单个量词解释的基础上,编写者增加了语义或功能相近量词的比较分析,与前代相比,在论证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见。
一方面是同一名词搭配不同量词的情况。例如(《词类章》1.2p.108;2.2p.493):“‘一担柴火’是用扁担挑的两头,‘一捆柴火’是棍子挑的一头”;“垜”适用于摆得整齐的东西,而“堆”适用于摆得杂乱的东西。
另一方面是同一量词可搭配多个名词的情况。如编写者以是否表尊敬来辨析“位”和“个”,并指出“在英语中一般使用一些特定的名词而不是量词来表示对他人的尊敬的”(《词类章》1.2p.108;2.1p.489)。又例如“件”和“桩”的差异在于量词“桩”具有在很多事中凸显某件事的功能,即“话里说有一桩事情、是在多少事情里、单要提出这个来说、是特立的样子”(《词类章》1.1p.279)。
这里最突出的例子是《自迩集》对量词“间”的分析。早期如Brollo(1694、1699)、万济国(1703)等未涉及这个词,至19世纪,西人对量词“间”的含义和用法已较为明确:
间,the numeral of houses, as一间屋,a house; 你一间屋真好, your house is a very good one.Also the numeral of the rooms of a house; as 一间房子(a room).(马礼逊1815:48)“间”,是表示房屋的量词,如“一间屋(a house)”,“你一间屋真好(your house is a very good one)”。也可以做一个房屋中的房间的量词,如“一间房子(a room)”。
间,a apartment of a house.一间房, an apartment in a house; 两三间楼,two or three rooms upstairs.(艾约瑟1864:134)间,表示一所房子。可以说“一间房”(an apartment in a house);也可以说“两三间楼”(two or three rooms upstairs)。
马礼逊和艾约瑟以“间”对应英文“house(房子)”、“room(房间)”的翻译方式说明了“间”的多用途,但在论述中并未作辨析。
《自迩集》则通过举例着力阐明了“间”与“house(房子)”或“room(房间)”结合的语义异同(《词类章》:中文1.1p.280-281;2.1p342-343。英文1.1p.107;2.1p.487):
间:四根柱子的中间儿就为一间、故当房子、屋子、这些名目的陪衬、可也‘得分别着用。(间is the space between four wooden pillars; it is consequently the numerative of house, room, &c.;)
人若说我买了房子、那是买了。说那个房子好、那就是统一个大门里都算上。或问那个房子里有多少间、那人回答有三十多间、那都是。王公府里、大约北面都有楼、上下两层、各分五七间不等。我们俩在一个屋里住、这句话、是那几间屋子连到一块儿、出入都是由一个门走。或说我们俩住一间屋子、那是四根柱子的中间儿、一个单间儿。这一溜房子有多少间、是问这横连着的房子有多少。
这是量词章节中最长、最详细的一段分析,我们整理如下:
首先,编写者解释了“间”的本义是“四根柱子的中间儿”,在功能上,可以用于陪称“房子”,也可以用于“屋子”。
其次,举例说明了整个一处房子,可以称“所”、“处”、“个”;如果问整个房子里有多少“间”,这个“间”的概念是不分大小的。对于一个独立的“楼”来说,在房子外面说就是“五七间房子”;在房子里面说就是“五七间屋子”,名词不同,但量词不变。所以,如果说的是“一个屋”,那是指进出一个门的一整个房子;“一间屋”指的是一个单间。如此细致的分析在当时的西人量词研究,甚至当今的国内量词解释词典中也很难见到①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间”的量词用法分立了两个义项:“1一间屋子;房间。2量词,房屋的最小单位”(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62页);刘子平编《现代汉语量词词典》对量词“间”的解释是“指房屋的最小单位”(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第133页)。。
综上所述,《自迩集》对量词的语义分析和搭配规范阐释全面、详尽,不仅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且在诸多方面有所创见。虽部分内容未尽完善,但不得不称许威氏在汉语量词系统整理、量词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名量搭配的理据探索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附表:《自迩集》65个量词在16-19世纪前人汉语量词表中的分布:

2 张 √ √ √ √ √ 35 面 √ √ √ √3 阵 √ √ √ √ 36 把 √ √ √ √ √4 乘 √ √ √ 37 包 √ √5 剂 √ 38 本 √ √ √ √ √6 架 √ √ 39 匹 √ √ √ √7 间 √ √ √ √ 40 疋 √ √ √ √8 件 √ √ √ √ 41 篇 √ √9 只 √ √ √ √ √ 42 鋪 √10 枝 √ √ √ √ 43 所 √11 轴 √ √ √ 44 扇 √ √12 句 √ √ √ √ √ 45 首 √ √ √ √13 卷 √ √ √ √ 46 抬14 炷 √ √ √ √ 柱 47 擔 √ √ √15 处 √ 48 刀 √ √ √16 串 √ √ √ √ √ 49 道 √17 桩 √ √ 50 套 √ √ √18 床 1699 51 条 √ √ √ √ √19 方 √ √ 52 贴 帖20 封 √ √ √ √ √ 53 顶 √ √ √ √ √21 幅 √ √ √ √ 54 朶 √ √ √ √22 副 √ 55 垜23 杆 竿 √ 竿 √ 56 头 √ √ √ √ √24 根 √ √ √ √ 57 堵 √25 个 √ √ √ √ √ 58 堆 √26 棵 √ 59 顿 1699 27 颗 √ √ √ √ 60 座 √ √ √ √ √28 口 √ √ √ √ 61 尊 √ √29 股 √ √ √ 62 尾 √ √ √ √30 块 √ √ √ √ 63 位 √ √ √ √ √31 管 √ √ √ √ 64 文 √ √ √ √32 捆 √ √ 65 眼 √33 粒 √ √ √ √
该表第一行以编写者姓名的首字母和年份分别表示卫匡国Martini(1652)、Brollo(1694、1699)、万济国Varo(1703),马礼逊Morrison(1815)和艾约瑟Edkins(1864),打钩表示在该书的量词表中收录了这个量词,若有同义的量词则在表格中照录。其中卫匡国Martini(1652)和Brollo(1694、1699)的量词表数据引自马西尼(2008:69-78)。
贝罗贝 2000 20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学研究状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弗朗西斯科•瓦罗 2003 《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何杰 2001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修订版),民族出版社。
何莫邪 2000 《马氏文通》以前的西方汉语语法书概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缑瑞隆、黄卓明、刘钦荣 2009 示形量词“股、束、缕、绺”的用法及认知基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黎锦熙 1992/1924 《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
黎锦熙 1978 《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商务印书馆。
李计伟 2006 量词“副”的义项分立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李月炯 2007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与对外汉语量词教学》,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陆谷孙主编 2007 《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吕叔湘主编 1991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马建忠 2007 《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马西尼(Masini, Federico) 2008 西方传教士汉语量词研究综述,CasalinFederica(ed.),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China and Japan, Roma: Tielle media Editore.
马修斯 2006 《牛津英汉双解语言学词典》,杨信彰编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内田庆市 2009 关于马礼逊的语法论及其翻译观,《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2期。
宋桔 2012 《语言自迩集》之协作者《瀛寰笔记》之主角,日本关西大学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会编《或问》第22辑。
宋桔 2013 《自迩集》诸版本及其双语同时语料价值,《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王汉卫 2004 量词的分类与对外汉语量词教学,《暨南学报》第2期。
王力 1984/1947 《中国语法理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力 2004/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姚小平 1999 《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的历史功绩重议,《当代语言学》第2期。
张卫东 2000 《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译序,威妥玛著、张卫东编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西平 2003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周法高 1980 论中国语言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论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Joseph de Prémare 1847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émare.Translated by J.G..Bridgman.Canton: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rository.
Joseph Edkins 1864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Language.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Morrison Robert 1815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erampore: Mission press.
Richards, Richard Schmidt等编 2005 《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英汉双解》(第三版),管燕红、唐玉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Thomas Francis Wade 1867Yü yen tzu êrh chi..London: Trubner & Co.
Thomas Francis Wade, Walter Caine Hiller 1886Yü yen tzu êrh chi.Shanghai, London: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W.H.Allen & Co.
Thomas Francis Wade, Walter Caine Hiller 1903Yü yen tzu êrh chi.Shanghai: Kelly & Wal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