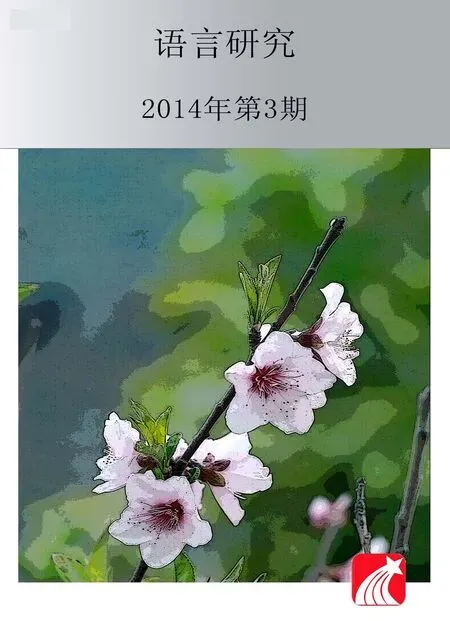连词“别说”与“不但”
2014-05-29周莉
周 莉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大部分学者(邢福义2001、董秀芳2003、周静2003)普遍认为连词“别说”相当于“不但”①以往认为连词“别说”既可用于前分句,也可用于后分句,而本文讨论的连词“别说”只是用于前分句中的“别说”。我们认为前后分句中“别说”在句法结构、语义和语用功能上均有不同(周莉2013)。,二者可互换,但简丽(2005)却指出“别说”和“不但”存在着不可替换的情况。综合以往研究,我们发现仍有如下问题亟待解决:(1)“别说”和“不但”在何时可替换?(2)“别说”何时替换为“不但”,又何时替换为“不但不”?(3)二者替换后表达效果有无差异?如果有,那么这种差异缘何而来?即导致二者不同语用功能的根源何在?以上问题都与这两个连词的来源密切相关。
要说明的是,相同连词所在句式的语义基础会因与其连用成分的不同而不同,如“不但”在“不但……而且……”中,受“而且”影响,其语义基础并不单一:主要有并列、因果、转折等几种(邢福义2001:223-226);而“不但”在“不但……连……”中,受显示极端情况的后分句影响(邢福义2001:229),其语义基础都是并列关系。为考察连词的自身作用,我们选定体现“别说”和“不但”共同语义基础的格式【__+p,就是q也/都……】(p和q分别代表前项和后项)来说明二者的关系问题。
一 连词“别说”的用法和来源
连词的核心功能是连贯。我们把连贯功能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语篇连贯,指语句内部分句内容之间的连接;另一个层次是认知连贯,指语句所表达的言者认知的连接。连词“别说”在【别说+p,就是q也/都……】中,表面上连接着语句p和q,而实质是连接由p所表达的言者认知结果M和q所表达的言者认知预期N。其中,认知结果M是言者通过外界刺激后得到的已知信息;认知预期N是一种与言者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指言谈事件中发话人的知识状态。连词“别说”实现的就是认知连贯,即发话人在他的主观量级②关于“语义量级”问题可以参看Fillmore&O’Connor(1988)和沈家煊(2001b)。上,用“别说”否定p表达的认知结果M的主观量不足而完成q表达的认知预期N对M的递进。连词“别说”的认知连贯功能源于其基本概念义“不要说”,下文将重点论述二者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先描写“别说”的递进用法。
(一)连词“别说”的用法
以往对递进类型的研究多以发挥语篇连贯功能的“不但”为例,分析复句前后分句p、q的形式关系。如周静(2003)提出同向递进和异向递进。而我们对实现认知连贯的“别说”所表达的递进关系分析则跳出分句p、q形式本身,联系言者的认知结果M和预期N之间的关系来谈,把它分为同质递进的“别说1”和异质递进的“别说2”。
要说明的是,关于认知结果M,发话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如对话中别人的话语、叙述中自己的前提话语和公众的共识等。为突出“别说”的递进类型,我们以对话为例,发话人的认知结果M由引发语列中对方话语获得。
1 同质递进的“别说1”。认知预期N与认知结果M在同质认知前提下,发话人用“别说”来否定M的“量”不足而形成N对M的同质递进。李宇明(2000:270)把这类否定叫做“同纬度否定”,指出这种否定的作用不在于否定事物所具有的性质,而在于校正性质的级次。如:
1)甲:小李学英语已经十年了,看英语文章没问题吧?
乙:别说看英语文章,就是写英语论文也没问题。
乙通过对话中甲的明示p“看英语文章没问题”得出认知结果M“小李英语水平高到可以看英语文章”,乙通过q“写英语论文也没问题”表达他的预期N“小李英语水平高到可以写英语论文”,二者同质,即都是说“小李英语水平高”。在这一前提下,N、M在乙主观量级上形成一个语用量级序列:英语水平高的维度:[M:看英语文章<N:写英语论文]。二者的语用量级差使得乙用“别说”否定M的“主观量”不足,进而引出高于M的足量认知N,实现主观量级的递进,表达乙认为“小李英语”比他已认知的“高水平”还要“高”。此时,“别说1”可替换为“不但”,二者替换后存在着主观评价义的差别(邢福义2001)。
2 异质递进的“别说2”。认知预期N与认知结果M在相反的认知前提下,发话人用“别说”对M的“质”进行语义否定得到~M(~为命题逻辑中表并非的否定符号)的同时,又对~M的“量”进行语用否定,最终形成N对M的异质递进。
2)甲:小李学英语已经三年了,能看英语文章了吧?
乙:别说能看英语文章,就是看英语句子都不行!
乙通过甲的明示p“小李能看英语文章”得到认知结果M是“小李英语水平高到可以看英语文章”,而乙通过q“看英语句子都不行”表达他预期N“小李英语水平差到不能看英语句子”,N与其认知结果M就形成对立的异质认知。于是,乙用“别说2”直接对认知结果M的“质”进行了语义否定,得到乙所理解的~M“小李英语水平差到不能看英语文章”。在此基础上,N与~M在乙主观量级上形成的量级差又使得乙用“别说2”进行了二次否定,这次是语用否定~M的“量”不足,从而引出N以完成递进,即乙表达他认为“小李的英语水平不但不高,反而很低”。邢福义(2001)称这类递进关系为“反递关系”。这样,“别说2”就通过双重否定功能实现了乙的认知预期N对与之异质的认知结果M在认知层面的递进,实现认知连贯的功能。这就不同于以往仅从语篇形式上对复句前后分句p、q间关系的分析。
可见,“别说2”的“否定义”有着双重作用:一是否定认知结果M的“质”,使认知内容由异质变成同质,得到~M与N同向;在此基础上,还具有否定~M“量”的作用。在这种双重作用下,“别说2”实现递进关系的表达。我们把异质递进表示为下图:

这就解释了王健(2008)指出的现象:当不含“别说”的分句是一个否定命题时,无论含“别说”分句中是否出现否定性成分,都只能作否定解读。如例2)前一分句就只能理解为“别说不能看英语文章”。可见,在异质递进关系中,后分句实现的是对前分句中认知结果的否定形式的递进,而非发话人认知结果本身。这时,“别说2”相当于“不但+否定词(不/没)”。
(二)连词“别说”的来源
对连词“别说”的来源,以往学者普遍认为它要由短语“别说”经过词汇化的中间阶段,之后才能形成,如董秀芳(2007)认为它由副词“别说”发展而来,侯瑞芬(2009)认为它由动词“别说”发展而来。我们认为由于汉语的短语和词同构,所以,连词“别说”不必一定经过词汇化的中间过程,它完全可能从短语“别说”直接发展而来。我们认为连词“别说”是由短语“别说”中组成成分“别”和“说”各自的基本概念义分别发生语义演变的结果。
1 “说”的语义演变:通过语用推理得到其“认知结果义”。“说”的语义演变是由其概念义“话语发出”经演绎推理①演绎推理是借助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后件式,由后件过渡到前件的一种必然性推理。其结构为:大前提(事理)只有P,才Q;小前提(事实):Q;结论:必然P。后的结果。具体过程如下:
演绎推理:大前提:只有已经获得认知结果,才有话语的发出
小前提:有话语的发出
结论:必然已经获得认知结果
可见,连词“别说”中的“说”经过演绎推理表示“已经获得认知结果”。这一表认知的推理义与其概念义“话语的发出”没有直接的衍生关系,无法用传统的虚化关系来解释。目前,学界(董秀芳2003,李明2003,谷峰2005)普遍认为“说”的“言说义”通过“言为心声”的隐喻途径获得其“认知义”,而我们认为“说”的语义演变是在语用推理中通过小前提对结论的认知转喻而获得。因为发话人总想“用有限的词语传递尽量多的信息及态度和情感”(沈家煊 2001a),所以,会在语言交际事件中“引入语用推理”,而当“表达发话人态度和情感”的“语用推理”在不断的使用中被逐渐“固化”,成为该语言表达式的语义内容,就出现意义的“主观化”(Traugott 2002)。这样,连词“别说”通过其中“说”在语用推理中获得的推理义就表达了说话人“自我”的立场、态度和评价,要么认为p不值一提而贬低p;要么认为p不在话下而褒扬p(韩蕾2008)。连词“别说”具有了“主观性”,发挥了主观评价功能。
2“别”的语义演变:语义否定—→语义+语用否定—→语用否定。否定词“别”(不要),属于语用否定成分。“语用否定义”相对于“语义否定义”而言,这对概念由沈家煊(1993)提出。他指出二者的不同在于否定点的差别:“语义否定”否定的是句子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即否定句子的真值条件;而“语用否定”否定的是句子表达命题的方式的合适性,即否定语句的“适宜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这“适宜条件”是指为达到特定的目的和适合当前的需要,语句在表达方式上应该满足的条件,如Grice(1967、1975)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中“适量原则”。如沈家煊举例分析,
3)a.今天天气不暖和(冷得很)。——语义否定义
b.这天气不是“暖和”,是“炎热”。——语用否定义联系“别说”两种递进类型:“别说1”中“别”在同质递进例1)中就是“语用否定”;而“别说2”中“别”在异质递进例2)中就是双重否定“语义否定+语用否定”。“别”作为语用否定成分,它的“否定义”形成了这样一个序列,即【短语“别说”中“别”的“语义否定”(如“别说你不在乎”)—→“别说2”中“别”的“语义否定+语用否定”—→“别说1”中“别”的“语用否定”】。可见,连词“别说”包括了“语义否定+语用否定”和“语用否定”两种否定用法,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别”只是否定“说”的得体性而断定它只具有单一的“语用否定”用法(侯瑞芬2009)。
3 连词“别说”=“别”(语用否定成分)+“说”(认知结果义)。由语用否定成分“别”与“认知结果义”的“说”复合就得到连词“别说”的整体构式义即“发话人否定自己已获得的认知结果”。连词“别说”的这一语义内在要求它在结构上一定会引导分句p出现,且此分句无论其具体内容如何,都可以被理解为表认知结果M的语句,否则,“别说”就无法实现它的认知义。既然p表达认知结果M,那么,就决定连词“别说”所连接的p、q间的递进关系要在言者的认知层上展开,即“别说”的使用模式:【别说+p(发话人认知结果M),就是q(发话人认知预期N)也/都……。{发话人的主观量级上:(M/~M)
4)a.别说刮风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们的礼兵哨也是笔直地站在国门口的。
b.不但刮风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们的礼兵哨也是笔直地站在国门口的。
通过例4)a中的N“下刀子”这一虚化的主观项而实现表达的真实。这正是陈汝东(2004:233)对“夸张”的分析,“它通过语言意义和现实的严重背离再现现实,其目的不是为真实而真实,而是为真实而虚化。”二是即使连词“别说”中的N是客观存在项,如例1)乙中N“写英语论文也没问题”,“别说”的“主观性”也使整个句式在客观陈述之外带有主观评价义。这样,我们从语义演变角度,把连词自身的语义分析和语用功能有机结合起来。
二 连词“不但”的用法和来源
(一)“不但”的用法
“不但”在格式【不但+p,就是q也/都……】中,连接语句p与q,实现的是语篇连贯功能。周静(2003)分析格式内填充项p、q间的递进关系包括两种:客观递进和主观递进。如:
5)a.不但p我们班的同学尊敬张老师,就是q全校各班同学也都尊敬她。(客观递进)
﹡b.不但q全校各班同学尊敬张老师,就是p我们班的同学也都尊敬她。
6)a.不但p小王来了,就是q小李也来了。(主观递进)
b.不但q小李来了,就是p小王也来了。
例5)a中q形成对p的客观递进。因为p“我们班的同学”和q“全校各班同学”存在的范围差距是客观的,所以,二者不可调换;而例6)a中q形成对p的主观递进。因为p“小王来”和q“小李来”本来不存在程度差距,是主观认为它们之间有差距,这种差距是主观的,即在发话人主观量级上,就重要程度而言:[p“小王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理解周静(2003)提出的“不但”既可以表示主观递进义也可以表示客观递进义,这一观点实质谈及的是“不但”所在格式中填充项p、q之间递进关系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而非“不但”所在格式义本身。韩蕾(2008)曾明确指出连词在句式中本身所标明的格式语义(如“不但”在【不但+p,就是q也/都……】中所表示的格式义)不同于格式内填充项p、q之间的语义关系。这二者涉及到的是两个层次的语义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不但”自身的格式义。
通过前面分析,我们发现无论p、q之间的递进关系是客观还是主观,而作为p、q本身表达的内容都应该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即“不但”表达的是客观递进格式义,实现语篇连贯功能。它完全不同于表达主观递进格式义,实现认知连贯功能的连词“别说”,即在【别说+p(发话人认知结果 M),就是 q(发话人认知预期 N)也/都……。{发话人的主观量级上:(M/~M)
(二)“不但”的来源
关于“不但”的来源问题,我们赞同刘立成、柳英绿(2008)的如下分析:
短语:不+[“仅”类词及其所限制的成分]→词汇化:[“不仅”类词]+“仅”类词原限定成分。
他们认为连词“不但”的成词经历了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即“不”和“但”本来不处在一个句法层次上,但由于长期相邻使用,同现的结果就使得二者被看作一体。如:
7)“可骇哉!可骇哉!卿不及天师详问之,不[但知是]。”(《太平经》)
8)[不但]天爱之也,四时五行、日月星辰皆善之,更照之,使不逢邪也。(《太平经》)
连词“不但”的形成就是跨层结构的词汇化(董秀芳 2011:35),指的是仅在线性顺序上连接但并不构成一个句法单位的成分序列变为词的现象。这一类词的形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不构成句法单位的成分在线性次序上要紧密相连;另一个条件是不构成句法单位的成分一定出现在某个特定的高频使用的句法构式(construction)中(董秀芳 2011:265)。“不但”就处于“否定词+限定副词+被限定成分”这一句法构式中。尹洪波(2011)发现否定词和限定副词共现(如“不但”)时,否定的作用是对已知量的校正和修补,会导致“增量”。而“量”的变化对复句逻辑关系有所制约,即“增量”往往隐含着“递进”。所以,“否定+限定(不但)”就只能用于语用否定的同质递进,可替换“别说 1”,而不具有异质递进中语义和语用双重否定功能的“别说 2”的用法,与之替换时要增加语义否定功能变为“不但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连词“不但”形成于句法驱动下的变化。由于这种跨层结构词汇化中形成的“不但”未经历语义推理的演变过程,它自身没有“主观化”,所以,“不但”只能表达客观递进格式义,无法表达主观评价义。它在夸张辞格的使用也受到夸张项的限制。因为“不但”之所以能在夸张辞格中出现,这与“不但”本身并无关,而是通过“连—也”强调地显示情况的极端使后分句形成夸张用法(邢福义2001:229)。句式后分句中夸张的极端项q受“不但”的客观递进格式义影响,其内容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如例9)b中q“地上掉根针”。而主观递进格式中“别说”的夸张用法,既包括这种内容存在的客观极端项,也包括内容不存在的主观假设项,如例4)a中“下刀子”和例10)a中“(50岁的)他20岁”。后一种夸张用法中的“别说”是“不但”所无法替换的,如例4)b和例10)b都不成立。只有夸张项内容客观存在的“别说”能被“不但”替换。如例9)b。
9)a.房间里真静,别说时钟的滴答声能听到,就是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到。
b.房间里真静,不但时钟的滴答声能听到,就是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到。
10)a.别说他50岁没我跑得快,就是他20岁也没我跑得快。
﹡b.不但他50岁没我跑得快,就是他20岁也没我跑得快。
三 连词“别说”和“不但”的不同来源途径及其用法
(一)连词“别说”和“不但”的不同来源途径
由以上对连词“别说”和“不但”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用法直接决定于它们不同的来源途径。虽然它们都由短语形式发展而来,但语言变化背后有很多方面的诱因,包括句法驱动和语义驱动(贝罗贝、李明 2008)。虽然句法演变可能会引起词汇化的发生,但并不是词汇化发生的必要条件(董秀芳2009)。在句法演变之外,语言变化还有内在力量即语义驱动下的变化。我们认为“不但”就是句法驱动下的演变,由“不”和“但”经跨层结构的词汇化而来;而连词“别说”就是语义演变的结果,由“别”和“说”分别语义演变后复合而来。我们把二者的来源路径简示为下图:

(二)连词“别说”和“不但”的不同来源途径决定其用法
由于连词“别说”形成于语义演变,根据 Traugott(2002)的观点:语义演变源于语用推理,是转喻在起作用;这个转喻过程,大多涉及主观化,所以,语用推理≈转喻化≈主观化,即新义 M2=源义M1+X(说话人的主观性)(贝罗贝、李明 2008)。这样,“别说”就在语用推理这样的“主观化”过程中自身具有了“主观性”,形成主观递进格式;而“不但”形成于句法演变,无法具备语义演变带来的“主观性”,就形成了客观递进格式。
二者不同的格式义使得“别说”既有“不但”无法传达的主观评价义,也可用于“不但”无法出现的夸张辞格,即那些夸张项并不客观存在的夸张辞格。这样,我们就从连词“别说”和“不但”的不同来源途径上找到它们各自用法的理据,对它们的不同使用情况作出根本性的解释。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把连词“别说”和“不但”的关系总结为下表:

连词“别说”别说1 别说2 不但用法理据 语义驱动下导致“别说”的“主观性”句法驱动下的短语词汇化语用功能 认知连贯+主观评价 语篇连贯句法格式义 主观递进格式 客观递进格式夸张项内容客观存在,可替换为“不但”可替换 不但,-主观评价义不但不,-主观评价义二者关系 不可替换 夸张项内容主观存在,不可替换为“不但”别说,+主观评价义
连词“别说”在语义驱动下,通过其组成成分“别”和“说”分别的语义演变在语用推理过程中具有了“主观性”。“别说”语义中的“主观性”决定它在结构上的使用模式【别说+p(发话人认知结果M),就是q(发话人认知预期N)也/都……。{发话人的主观量级上:(M/~M)
可见,连词的用法与其来源紧密相关,我们跳出传统的句法驱动下语法化虚化路径的局限,从不同的来源路径就能找到不同连词的用法理据,对汉语连词也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附记】论文初稿曾在“第七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2013.12,新加坡)宣读,并得到张先亮、彭小川等先生的指导。
贝罗贝、李明 2008 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研究,载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陈汝东 2004《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丁力 1999 反逼“别说”句,《语言研究》第1期。
董秀芳 2002 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语言研究》第3期。
董秀芳 2003“X说”的词汇化,《语言科学》第2期。
董秀芳 2007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董秀芳 2009 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中国语文》第5期。
董秀芳 2011《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谷峰 2005“你说”变体的使用特征及其语法化,《中国语文研究》第2期。
韩蕾 2008 连词“别说”功能探析,载齐沪扬主编《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侯瑞芬 2009“别说”与“别提”,《中国语文》第2期。
简丽 2005《“别说”句式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明 2003 试谈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载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商务印书馆。
李宇明 2000《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立成、柳英绿 2008“不但”类连词的成词理据,《汉语学习》第3期。
沈家煊 1993“语用否定”考察,《中国语文》第5期。
沈家煊 1998 语用法的语法化,《福建外语》第2期。
沈家煊 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沈家煊 2001a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沈家煊 2001b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中国语文》第6期。
沈家煊 2004 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王健 2008 说“别说”,《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吴福祥 2004 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邢福义 2001《汉语复句研究》,商务印书馆。
尹洪波 2011 否定词与范畴副词共现的语义分析,《汉语学报》第1期。
尹世超 2004 说否定性答句,《中国语文》第1期。
周换琴 1995“不但……而且……”的语用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周静 2003《现代汉语递进范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周莉 2012《现代汉语“别说”的语义、功能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周莉 2013 前后分句中不同的连接成分“别说”,《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Fillmore,C.J,P.Kay&M.C.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The case of Let Alone.Language,64(3): 501-538.
Grice,H.P.1967 Logic and Conversation: The William James Lectures.Harvard University,MS.
Grice,H.P.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In Cole,P.& J.L.Morgan(ed.)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raugott,E.C.&R.Dasher 2002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