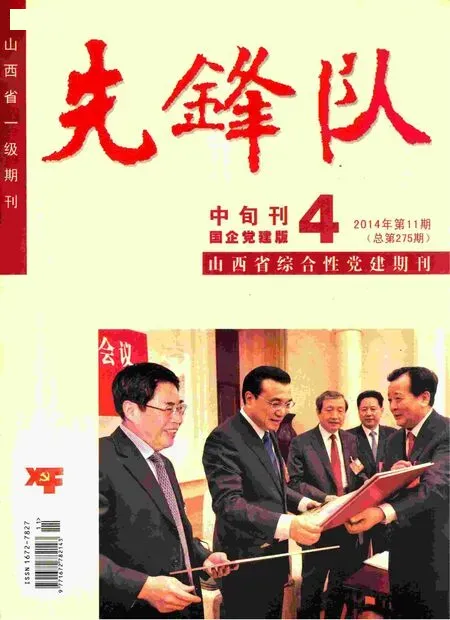人在外头心在家
2014-05-28张石山
■ 张石山
从山西往北,跨越长城是内蒙。在万里黄河的第二个大折弯,在晋陕蒙交界处,繁盛着原生态民歌蒙汉调。数百年来走口外的山西人,带去了农耕文明,也带去了响遏行云的爬山调。爬山调遇到雍容华贵的蒙古长调的抵抗,文明碰撞犹如阴阳拮抗、太极团娈,数百年的酝酿,培植出了一支文化艺术奇葩——蒙汉调。
有一首著名的蒙汉调这样唱道:
人在外头,我心呀嘛心在家,
家里头扔下了一朵牡丹花。
晋陕豫交界处,是黄河的第三个大折弯。黄河由此一路向东,直奔大海。从表里山河的山西南下,跨越黄河,就到了中原大地河南。
河南有清明上河图描绘过的开封,有号称牡丹甲天下的洛阳。
于是,这儿的一首民歌《编花篮》这样唱道:
编,编,编花篮,
编个花篮上南山;
南山开满了红牡丹,
朵朵牡丹开得艳!
黄河上游,青甘宁交界处,是黄河的第一道大折弯。黄河从青藏高原第一台地俯冲而下,打破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的界限。这儿千百年的多民族文明碰撞交融,托举起黄河文明的一颗明珠——号称西北魂的花儿。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花儿与少年》中,有这样一首歌:
走过了一山呀又一山,
山口里呀有几朵牡丹;
白牡丹她耀人哩呀,
红牡丹红得要破哩!
“白得耀眼,红得要破”,活色生香,摇撼心旌,原生态民歌对牡丹的形容、把人们对牡丹的欣赏艳羡,推到了某种极致。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至少早在隋唐,牡丹就被推举到国花的地位。
当令季节赏花,观赏花王牡丹,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不只是骚客诗人的偏爱,而成为大众的乃至是全民的审美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成为产业。一日之驱驰,何止千里;国人赏花,不惜驱驰千里。国色天香,趋之若鹜。
有“菏泽牡丹冠中华”之说。蒲松龄老先生在他的不朽名著《聊斋志异》中,有专写牡丹花仙的“葛巾、玉版”。
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说。前些年,山西省作协组织活动,我随团去了开封洛阳,曾经一饱眼福。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是也。
其实,就在我们太原,在古城著名的双塔寺,也有牡丹。这儿,纬度靠北、海拔偏高,牡丹花期稍晚。僧人们守护着钟罄木鱼、古佛青灯,也守护了一片植于明代的牡丹。据称品种名贵,观之赏心悦目。善哉善哉!
到公元2010年暮春,晋南临汾古县,有国家级牡丹节盛大召开。规模之浩大,气氛之热烈,有与洛阳、菏泽鼎足而三之势。
晋南,乃中华文明之根的生长发育之地。夸张些说,到这儿你下车伊始就要小心——不小心就会踩到文化!
古县,是晋文公称霸时代的晋国属地。三家分晋之后,归属赵国。赵国一代名相蔺相如,就出生在古老的古县啦!
蔺相如不惧强秦,完璧归赵,义服元戎廉颇,使之负荆请罪,一代名相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传说、留下了成语、留下了辉煌、留下了文化。
在这片古老的文化之地,集天地灵气、采日月精华,竟然葆育了一株生长于唐代的牡丹!
这株牡丹,植于盛唐;身姿虬曲,铜枝铁干;树围团团,伞盖俨然;花开时节,姹紫嫣红。
洛阳尔,菏泽乎,古县兮,谁家牡丹更好?何处堪称国色?
质言之,锦绣中华,无处不锦绣;国色牡丹,无花不天香!
作为三晋学子,山右草民,钟爱家乡、偏爱故土,乃是人之常情。
外地人认为:山西人只知道挖煤,山西空气污染最严重;山西煤老板等于暴发户,山西老大爷代表最保守——等等如何,不一而足。
古县举办牡丹节,是一个信号。
我们不再只依赖黑色,我们开始关注绿色。我们不再只是向大地山河索取,我们开始回报反哺地球母亲。
全人类只有一个家园;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也只有这同一个家园。
我们开始懂得了负荆请罪;
我们开始谋划完璧归赵。
自然和谐,是我们的古老哲学,是我们的古老智慧,是我们的古老追求,是我们的古老律令。
自然和谐,是我们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之一。
我们还能够回到、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吗?
我们还能够“完璧归赵”,还能够把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生机勃勃的、自古而然的地球,自豪地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吗?
古老的古县,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悟以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
人在外头,我心呀嘛心在家,
家里头扔下了一朵牡丹花。
高天,大地,还有那株植根于唐代的牡丹,在看着我们。
白牡丹她耀人哩呀,
红牡丹红得要破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