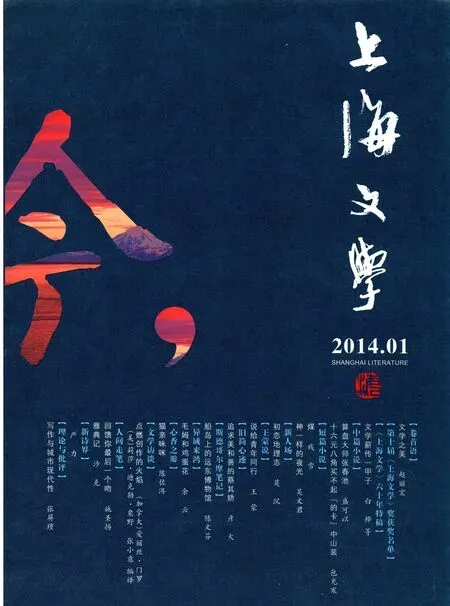猫亲咪咪
2014-04-29陈佐洱
陈佐洱

咪咪初来
1989年初夏的某天傍晚,小女儿从人大附中放学回来,书包鼓鼓的。她进门诡秘地一笑,说:“我给你们带了个小朋友回家。”
书包扣解开,它就探出脑袋晃了晃。简直是只可以托在手上的“掌上猫”,全身的绒毛雪白,稀稀疏疏,盖不住毛下面嫩红色的皮肤,应该出世才几天。
小女儿讲述,这是在甘家口路边买的,三元钱。带它回来是因为它太无助,弱小,而且右眼老流泪,发炎。
家里立即引发一场讨论。那时养猫可不像现在那么方便,超市里既没猫粮也没猫砂,何况我们刚从遥远的南方举家迁居北京。主理家政的妻子一面叨咕“把它送回去”,一面爱怜地找出支红霉素眼药膏为它治眼睛;我和小女儿踊跃保证,承包找猫砂运猫砂的活儿。正好那天三弟来作客,他打了个圆场说“这猫养好了,将来准是只好猫”,一语决定了命运。
我们争先恐后地从厨房端来一小碟牛奶,围着看它一口一口舔得精光。然后,看它抬起頭来环视每张脸,发出了雏凤新啼般的第一声:“喵呜——”。在全家一片欢笑中,它肚皮贴着地板,钻进了书架底下的狭小空间。
小小猫的叫声轻柔、尖细。我曾以为这只是它幼年时的发声,没想到整整二十一年,直至老逝,它都还是那样的声音。这声音可与它的一生经历、它的性格不太相符。
我给它起了个很普通的名字:“咪咪”。
咪咪断奶后的饮食,就是自来水和剩饭剩菜,每星期有一两次加餐煮小鱼。曾听说五棵松外有专门的猫粮卖,我们骑车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那家卖农药化肥,顺带出售自制猫粮的采购店,如今家喻户晓的“伟嘉”牌猫狗粮当时还没在北京市场问世呢。
自行车是支持咪咪生活的重要物流工具,除了运送吃的,还运输拉的。每星期,总有一天夜幕降临后,我和家人要外出为它找猫砂,好在附近正大兴土木,建筑工地不少,我们带着小铲子和麻袋,从工地的沙堆上刨下点表面的干沙。半麻袋干沙够用一周,多了也扛不动。工地上的人都很友善,听说了用途,表示理解。
咪咪“三好”
咪咪的生活习惯好。饭碗搁在厨房里,盛沙的便盆搁在卫生间门外,几乎不用怎么教,它就自然而然地适应了。爱干净的它,天天用前掌蘸口水洗几遍脸,常常埋头用舌梳理全身细细密密、毫无杂色的白毛,越舔毛色越亮。
它很享受十天半月一次温水澡,那也是我们全家二十余年里既忙又乐的时光。它身上涂满洗浴液,湿淋淋地站在大面盆里,水齐脚踝,由于毛贴身,好像一下子瘦了许多,我们在它头顶上举着花洒,直到上下左右冲淋得干干净净了,它还不愿意离开。可是被大毛巾一裹,抱到桌子上享受电吹风时,它又高兴了,不时甩头,水花溅到周围人的脸上。
咪咪好聪明,来家不到半年,就能听从各种简明的指令,比如“过来”、“下去”、“走开”、“不许”等等。不到一年,就能按指令表演四五种近乎马戏的动作,比如家人无论在哪儿喊“咪咪你在哪里呀?”它就会连声答应着噔噔噔小跑过来。家人说“握手”——它会蹲坐着,大方地伸出一只前掌;“还有一只手”——它会收回那只前掌,再伸出另一只。我更喜欢坐在地板上,把它叫到跟前,再指令它“趴下”——它会前腿伸直,后腿跪曲,趴伏下来,“给我当会儿枕头猫”——它会一动不动地让我的脑袋枕在它的后背上,我可以闭目养神,可以看书读报,同时听着它发出“呼噜呼噜”的猫喘,持续十来分钟。即使时间过长,它受不了了,也只是稍耸耸肩,轻轻叫一声,提醒我该起身了。
就像淘气的孩子,咪咪一直渴望知道门外的世界,自以为是,跃跃欲试。尽管每次开门时都警告它不许外出,可有一次,蓄谋已久的它终于抓住机会,“喵呜——”一声,如离弦的箭般地冲了出去,三步并作两步蹦跳下楼。我们住的是高层塔楼式公寓,我立刻让妻子守在十五层的楼梯口,自己乘电梯直下底层,然后边呼唤着“咪咪”的名字,边沿着扶梯拾级向上寻找。一路找到七层,听到了它急切的呼应声,有懊悔,有求助。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咪咪蹲在楼道里,守望着那套与十五层自己家同样位置的单元门,叫唤开门,见我走近也不移步,生怕错过了“家门”打开。
咪咪好教育,只需一根手指摁它头呵斥几句,它就牢记在心了。经过这番教训,咪咪再也不敢擅自出门了。即使开门诱导它出去,它反而两眼警惕地直盯门外,缩起身子倒退数步。
并不美满的婚恋
咪咪长大了,长得身材魁梧,虎头虎脑,右边的眼睛灰蓝色,左边的眼睛橙黄色,无论瞳孔张大或眯成缝,任何时候都炯炯有神,那一身雪白发亮的皮毛不仅人见人爱,更是让它的同类钦羡不已。它究竟是什么种族的猫?女儿查阅资料,引经据典说,咪咪属于短毛波斯猫,传说祖先在中东是守护神殿的。而我认为该叫它“北京猫”,因为它生于斯长于斯,而且上一辈肯定也在斯地北京。
我们公寓楼下住着一对导演、演员夫妇。有一天我下班回家,那导演拦住我说:“知道你全家都爱猫,那只大白猫是公猫吧?我家也有只波斯种的母猫,很乖巧,但是我俩经常出差拍戏,实在照顾不过来。送给你们,攀个亲戚,怎么样?”
果然是只娇小伊人的纯白猫,一双大眼睛都是灰蓝色的,但叫声却异常粗重,由表及里,正好与咪咪是阴阳两极——我从导演手里接过它时端详了一番。
带回家,第一时间是很受欢迎的,因她的叫声与当时正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主角名字“那五”谐音,它就取名“那五”。可是两三天后,欢迎它的只剩下咪咪了,那五只认得饭碗,不认得便盆,随地大小便的毛病怎么也不改,不但大大增加了家务工作量,而且给本不宽敞的两居室带来了不小的环境污染。更有甚者,由于它和咪咪一见钟情,半夜粗重的叫春声不仅搅得我们全家人都睡不好,还搅醒了邻居们的好梦。后来,它俩居然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也继续着恋爱游戏。咪咪对它的追求几乎疯狂,那五欲拒还迎的矫情用“装腔作势”形容也不过分,那五“逃”进卧室跳上了床,然后回头唤咪咪,等咪咪追上床,那五又“逃”向餐厅上了餐桌;咪咪追上餐桌,那五又上了冰箱,两只白猫终于在地理位置的最高点上成就了“好事”……
书上说,猫怀胎六十五天就能生仔。那五来家两个月光景就挺着大肚子了。咪咪对它是呵护有加,饭盆里的猫食总是等那五吃到咂嘴舔唇,咪咪才凑近吃剩的;那五犯了错,谁要是去抓它,咪咪会冲上前护着妻子,发出从未有过的连声“喵,喵,喵呜”,既像央求,又像是抗议。
用妇产科的术语,那五“快便顺产”,诞下一只全白毛、红嫩嫩的小公猫,比咪咪来我们家时还要小,只有一根手指那么长,微张眼,吮吸着那五涨红的乳房。小夫妻俩守护神似的守着宝贝独生子,连我们都也只能远远观望。一旦门外走廊有人走动,咪咪立即叼起儿子,那五殿后跟着,“举家迁徙”躲得远远的。
才几天,可爱的小宝宝夭折了。女儿判定,是被它没有养育经验的父母亲压在身底下憋死的。可是咪咪不认为儿子已死,还是不让我们靠近,继续把宝宝叼来叼去,那五照样跟在后面,并且照样随地大小便。
那五屡教不改的卫生习惯和半夜肆无忌惮的叫喊,使我們下决心让它离开。楼下导演夫妇家老是“铁将军把门”,就在机缘巧合下把它转送给了甘家口某设计院的一位爱猫人士。从此再也没有它的音信。
咪咪在一阵狂热的早恋之后,不得不经历丧子和夫妻分离之痛。不仅如此,我们还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做了绝育手术。不知这些为了人的举措是否不人道,咪咪从医院回家,麻药效力还未过,躺在地上几次三番站不起来,可是终于跌跌撞撞,蹒跚走向便盆解手的情景印入了我的脑海。每当我听见别人调侃它“太监猫”的时候,我的心骤然一抽,会重复思考上述问题。
人猫相依
好在咪咪没有记恨,顺应了命运的安排,不久身心便得到康复。我们更加关爱它,甚至宠它。比较高档的超市开始出售有商标品牌的猫粮猫砂了,我们总是挑贵的买,你去趟超市买点,我去也买点,往往供过于求,需要储存起来了。
咪咪一天两餐,上午猫粮,下午改成了不掺剩饭剩菜的小猫鱼。天冷了,晚上水泥地板凉,它试探着想跳到我们床上来睡,我们在脚跟头的被子上铺条大毛巾,咪咪立刻认同这是它的“床”。每晚“床”铺在谁的被子上,熄灯后它就跳谁那儿睡,不越雷池一步。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咪咪隔着被子和自己睡,有它那团温温暖暖的十来斤重压脚,睡得更香。
咪咪对我们也更加亲热。每当家里人从外面回来,屋里还毫无动静,它却先知先觉,奔向门口迎接,先听到它柔和、尖细的叫声,后听到钥匙开门声。人一进屋,咪咪就会用脸蹭你的裤腿,围着你转,边转边叫个没完。
一次,我一人在家,急性胃肠炎发作,肚子绞痛。咪咪十分同情我,寸步不离地陪我一趟趟上厕所,跟我去五斗柜找药。我躺在床上,它一反常态,哪儿也不去,静静地伏守在床边,偶尔还昂头低声问候。
我们之间已经能进行二十多种基本会话,不仅是发出及执行指令,而且能够交流情感,以致所愿所望,所思所想,有商有量。比如,咪咪在书架上打瞌睡,我担心它碰倒了摆在身旁的花瓶,就喊:“咪咪,下去!”
它睁眼看了看我,嘴里咕噜了声,又埋头睡下,还用一只手遮住半边脸,耷拉下耳朵。这是它提请求,意思是“让我在这睡会儿吧”。
我提高调门说:“不许,下去!咪咪听见没有?”
它一惊,弓起背,伸了个懒腰,不情不愿地扑地跳落下来,嘴里嘀咕着——那是发牢骚。
咪咪待人接物确实亲疏有别。我常说它除了“三好”,还是只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三有猫”。咪咪进家时,大女儿正在国外学习,但函电交驰中听说了种种故事,于是回国度假时给它带来好些礼品。咪咪对于这些美国宠物店的新款玩意儿照单全收,每样都玩得很投入,可是对大女儿本人却虎视眈眈,尤其见到我们对这位“客人”如此亲密无间,竟发出酸酸的怨言,甚至凑上来争宠。善良的大女儿蹲在它面前,很友好地说话,想摸摸它的头,竟被它猛地伸出利爪,抓得手背上鲜血直流。大女儿委屈得掉下眼泪。我们对咪咪几番严肃教育,但它的妒火直至大女儿启程离家仍没熄灭。
有人遛狗,我们遛猫,不时带咪咪出外走走。起初,它一离家就紧张兮兮,甚至伸爪抠住抱它人的衣服。经过劝慰后,它才放下心,好奇地东张西望。那时,我们家已经从甘家口百万庄搬到翠微小区,星期天抱它坐在楼下的草坪上,四肢贴地伏在我身旁,任周围邻里的孩子们嬉闹奔跑,咪咪视若无睹,定若泰山。可是有一回就不同了,有人牵着只哈巴狗来到了草坪上,那狗个头比起咪咪来至少翻倍,它一见我们就无厘头地吠叫,似要挣脱链绳冲将过来。我忽地从草地上立起,正要再弯腰抱咪咪,没想到咪咪已蹿前两步挡在了我的脚跟前,弓起背,平平挺直尾巴,也龇牙咧嘴地向那狗高声叫喊起来,虽然那声音还是尖尖细细的,但音调刚直,微微颤动,像一把风中的利剑。
这是我在咪咪生平中唯一听到的如此雄赳赳的声音。就这样,它的蓄势出击把那只狗儿镇住了。
伴我走香江
1994年的春天,我迎来从事港澳工作六年后的新挑战,奉命赴香港出任专责政权交接谈判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妻子随任,咪咪的去留怎么办?我决定咪咪也同行。好在在北京办理出境手续并不复杂,我们带它去市动植物检验检疫局做了体检,打了防疫针,领取了完整一套证明文件。
3月11日中午,经过三小时飞行,抵达香港。咪咪从货舱里出来就得送去隔离观察——“坐移民监”。据说港英的法律规定,凡来自英国等英联邦国家的动物如证明文件齐备,可以及时放行入境;如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需关一星期“移民监”;而来自中国内地的,尽管健康、防疫等证明文件齐备,也得按照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规定,关四个月“移民监”,食宿费用由主人自理。

刚踏上香港土地就面临一个遵守当地法律的问题,我仅同前来接机的中代处同事打了个招呼,就直奔启德机场外,找到装在笼子里即将运走的咪咪。望着它哀怨、惊恐的两只蓝黄眼睛,说了不少安慰话,就此告别。
为了雪洗国耻,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中英谈判桌上忽而刀光剑影,忽而觥筹交错。6月30日,我和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的同事们努力与英方达成了到任后的第一个协议,确定了未来中国驻军海陆空布防用地的安排。下午回到宿舍,未歇口气,我就匆匆赶去港英政府渔农处的域多利道狗房,看望北京大白猫咪咪。
过去三个多月里,我们每次“探监”,都令咪咪兴奋不已。但是就在前两天谈判颇为紧张的时候,狗房管理处打来电话,说咪咪病了,精神萎靡,脑袋上的细毛突然掉光了半边,可能得的是某种皮肤病。
巴士沿着起起落落的海岸线从卑路乍街曲折西行,终于停靠在一座红色的消防大楼附近——香港巴士到站是没有售票员报站的,全凭乘客自己认得目的地。我下车走向一段林木茂盛的斜坡,转两个弯到达狗猫同监的域多利道政府狗房。
咪咪的“牢房”在百米以外的尽里头一排,进入大门时相互根本见不着面,可是我分明听见了它的叫唤声,它一定已经听到了我渐走渐近的脚步。那叫声由声嘶力竭渐渐变得软声细气、柔情万种,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情,我也忍不住不停呼唤它。
这场人猫相会的情景可以用两个词形容:“久别重逢、问寒嘘暖。”之后,我来到管理处办公室了解咪咪的病情,并且向照顾它的公务员们致以谢意。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正在播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签署关于未来军事用地使用安排协议的场景,接待的公务员特别客气,他们介绍说咪咪大约半个月前开始出现症状,狗房接连找了三位兽医为它诊治,抹了好几种抗真菌的皮肤病药,都不管用。接连几天,狗房都到附近海边去买新鲜小鱼喂它,也不合口味。后来一位英国兽医翻阅了大量资料后诊断,咪咪可能是精神受到重大刺激所致,就像人类的“鬼剃头”现象,一夜间掉光了头发。好在“移民监”期限快到,希望这之前我们可以多来看看它,安抚它的情绪。
为此,我又折回“牢房”,与咪咪隔着铁栅栏好一顿“谈心”,起先它困兽犹斗似的不停在笼子里转圈,希望我能接它出笼,然后放慢了脚步,接着蹲坐在我面前,无奈地听我说话,偶然答应几句,再然后觉得我说来说去了无新意,一歪脑袋自个儿梳理起胸前的皮毛……
果然,咪咪“坐监”期满,回到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宿舍不久,就身心怡然如初,秃了半边的脑袋上又长出细密、洁白的绒毛来。
第二年冬季,是我出任中方代表以来最艰难的时期。由于英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连续五年以超过GDP五倍的速度大幅提高社会福利,并扬言还要干五年,我在跨九七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制第五次专家小组会议上发炮,指责港英当局改变了与基本法相衔接的量入为出理财原则,在临撤退前大撒金钱,收买人心,警告照此下去未来的中国香港特区将难以为继,可能“车毁人亡”。始作俑者末代港督彭定康恼羞成怒,当晚就率领一众港英高官对我围攻,接着又策动各种媒体对我的讲话断章取义,大肆抨击,一星期内出现了上千篇大大小小的文章,对我高压下来。我的妻子也承受到有生以来最大的压力,甚至不愿上街,害怕背后有人指指点点。
我从北京出差回来,与她促膝谈心,咪咪就坐在我俩之间。我摸着咪咪圆滚滚的脑袋,说:“历史是公正的,会善待我们。在政治斗争中,智慧和正气一定要比感情更高。”我轻哼電影插曲《驼铃》,不无苍凉的曲调和旋律,从心田贴己流过。刚才还兴高采烈迎我进门的咪咪此刻一脸缄默,仰头瞪着一蓝一黄的大眼睛,不时扑扇一对不大不小的耳朵。
光阴如梭,到了1997年6月下旬。全世界都在倾听香港回归祖国的脚步声。有关实现香港平稳过渡的十四项重要谈判业已完成,突然闲了下来反而不习惯,我倚坐在宽大的窗台上,翻看当天报纸,忽然想起了咪咪,随口喊道:“咪咪,你在哪里呀?”
“喵呜——”一声,它从厨房噔噔噔小跑过来,跳上窗台。
“趴下,给我当会儿枕头猫。”我枕在它的背脊上,边继续读报边对它说:“好了,我们快要回家了。”
咪咪短促地回应了我一声“喵呜”,等我从它背上起来,它立刻就地打了个滚,蜷着身咬咬自己的尾巴,这都是它开心的表示。
桑榆日近情义长
1998年3月,我们带着咪咪回到了北京。咪咪好像老成持重了许多,在新的家里翘尾巡视,每一个角落它都到过,每一件拉回的行李它都嗅闻个遍。按照猫的年龄,活了九岁就相当于人过了孔夫子说的天命之年,过去它对陌生人一般不理不睬,现在只要叫它声“咪咪”,它就会礼貌地回应一声“喵呜”。要是它正专注其他事或打瞌睡,也会望你一眼,张张嘴巴,像是打个招呼,并不发出声。
咪咪是不是老态龙钟了呢?未必,它还挺注意锻炼身体,不定哪天早晨吃过猫粮,它会突然憋足劲儿,在家里楼上楼下蹿跑几圈,跑的时候目不斜视,什么诱因也没有,跑完之后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每周大约跑那么两次,高兴时接连两三天都“晨练”。
可是咪咪忽然练不动了,不吃,不说话,只喝水,喝完就钻到床底下躺着。我们呼喊“咪咪你在哪里呀?”它初始还答应,后来连答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用扫帚柄把它从床下拨出来,一看全身皮毛腊黄,明显削瘦许多。
妻子诊断咪咪肯定吃了有毒的东西,导致急性肝损害,皮肤、黏膜和眼球巩膜等部分才出现黄疸的症状。宠物医院的诊断是一样的,立刻给它挂瓶,开保肝药。究其原因,肇事者应该是我,我下班回家路上,见昆玉河边有人在捞小鱼,挺新鲜,就买了些,没想到那是些被毒死的鱼。
刚动完肿瘤手术的妻子每天把咪咪抱在怀里,一小勺一小勺地喂牛奶,除了牛奶,它什么也不吃。靠着这幼年时的唯一营养,挺过了三星期,咪咪终于拖着虚弱的身体从床底下走出来。
经过这场大病,咪咪的性格更加“耳顺”。它的生活中多了个伴儿——小女儿把她在美国养的一对“猫儿狗女”中的猫儿Kissy,“Cargo hold”货运来北京。Kissy完全是只美国宠物,也是“太监猫”,智商远不如咪咪,那扁脸大眼长毛的长相和扭捏作态的举止,都与咪咪迥然不同。我们唤“Kissy过来”,它摇摇摆摆走到跟前又扭头离开,走两步停下来,用粗大的尾巴搔你的腿,等着你挠它黑白相间的长毛脑袋,连吃饭也是那作派,先要对饭盆看几眼,扭头转一小圈,才回过身来大开朵颐。
咪咪对Kissy的加入并不排斥,同吃一盆粮,同用一马桶,相安无事,但不知是性格还是年龄代沟所致,相互间不甚亲热,白天各行其是,晚上各睡一张四方形的旧沙发垫子,虽然摆在一起,颜色一样,可绝不会睡错。
两只猫有一惊人之举,至今让我叹为观止。我妻子逝世之前,在医院病床上艰难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Kissy,咪咪……”
这句临终牵挂,在家的猫们好像心通灵犀听到了。当晚,亲友们来家布置简单的灵堂。等客人们一走,咪咪随即领着Kissy来到铺盖白布的灵台前蹲坐守灵。夜深人静,我睡不着,发现它俩依然那样蹲坐着,我想起了关于咪咪祖先是中东神殿守护者的传说。天熹微放亮时,我再去窥探,它俩还在原地肃穆守护着……
也有老马嘶风时
有位老年综合病的专家说,延年益寿之道在于心宽,放得下。
咪咪过了猫的平均寿龄十五岁,对谁都和颜善目,它与早年它曾心存妒忌的我的大女儿成了好朋友,甚至女儿一家偶尔来京,热情过度的小外孙握住了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尾巴,它也只一抽尾,不愠不怒地躲到一边去。对于我们唤它,指令它表演,它虽也服从,但显露勉强,动作有些懒散,有时候索性用一个无声的呵欠抱歉,不表演走开了。
咪咪一双漂亮的眼睛渐渐黯淡失色,但脑子清醒,仍然重情重义。寂寞时我把这体重减轻了的“老朋友”抱上膝头,和它说说话,在它身上打拍子,唱了一首又一首童年的歌。它都眯缝起眼惬意地听着,听着,比平时寡言的我更加寡言,可我觉得它善解人意。
宠物的衣食住行在“全球化”中越趋讲究,但咪咪曾经沧海难为水,不稀罕。它唯一的嗜好就是十多年如一日的下午那顿鱼,偶尔过了三点不端出来,便满屋子地出声催喊,更像是在争取生活对自己的一份关爱。这时,我们家的亲戚、管家小李就得停下手中的其他活儿,去冰箱里取猫鱼,还得故意皱眉应答它:“咪咪,头都给你吵得昏了——会给你煮鱼吃的!”只要这一声,咪咪就消停下来。
小李管着两只猫的吃喝拉撒睡,咪咪表现得对她尤其依恋,每天晚上,总要小李亲自送它去睡觉。它先是呆在小李房里,陪她读报或玩电脑,实在困了,就两手往小李床沿上一搭,伸长脖子轻柔细声地“喵呜”一声,意思是“很困了,送我去睡吧”。
它的红沙发垫子其实就在隔壁洗手间里,但非得小李起身说“好吧,你在前面走”,它才迈着猫步踱向洗手间,小李跟上去关门,它才“上床”就寝。而那时的Kissy早已在另张“床”上呼呼大睡了。
白天的时候,小李常把咪咪的红沙发垫子搬到阳光最足的客厅立地窗前,让咪咪去那儿看风景或休息。整面立地窗都是朝南临街的,我从马路对过的公交车站下车,踏上跨街人行高架桥,就能远远望见公寓六楼贴着立地玻璃窗有幅色彩亮丽的图画——浑身雪白的咪咪蜷伏在红色的垫子上——它是在俯瞰满街生动的车水馬龙,或闭目养神吗?
暮年的咪咪虽然体弱心静,但是一生维护尊严的刚健个性未因衰老而折,我亲眼目睹了咪咪和Kissy的一场纠纷。冬日的阳光透过客厅立地窗玻璃,暖融融地照在咪咪和它躺着的红垫子上。东摇西逛的Kissy走来了,用手拨弄咪咪的胡子,咪咪正入梦乡,也不睁眼,只扫了下尾。没想到Kissy又伸出手捣乱,这下真把咪咪急醒了,朝同伴“唬——”吼了声,同伴也回吼,意思是“让开,让我来躺一会儿”!咪咪不干,霍地跳将起来,扑向Kissy,Kissy没料到“舅舅”变脸这样凶,扭头便逃,于是两只猫在客厅里一前一后奔跑着,两圈过后,Kissy已经吓得抱头鼠窜,咪咪也已气喘吁吁,回到红垫子上续自己的梦,Kissy则起码几天不敢再觊觎那窗外的风景。
咪咪拖着精瘦的身子,活到了颐养天年的2010年——猫龄二十一岁,据说相当于人类一百四十岁左右。
我九十四岁高寿的母亲见到它,常带笑说:“咪咪,我要叫你一声猫兄了!”
送别猫亲
“五一”节小长假,我们出门去了,留下小李和咪咪看家。临走时,咪咪就不太想吃东西。到达南方的当晚,小李来电话说,咪咪根本不吃了,宠物医院医生说它“超老”,症状是肾功能、肝功能衰竭,其实它的所有器官都已衰竭了。
我们叮嘱小李天天送咪咪去医院挂瓶输液,尽一切努力延长它的生命。每天一两次电话,得知咪咪每况愈下,起初还能喝点儿水,后来靠针管塞进嘴里喂些牛奶,最后连牛奶也喂不进了,浑身发烧。小李把自己的一件毛衣剪开,给它穿上。假期的第五天,小李在电话中哽咽说:“咪咪在等你们回来……”
“咪咪,你等等,再等一等!”我心里呼唤着,收拾行装连夜飞返北京。一进家门,看见咪咪侧躺在洗手间里的红垫子上,呼吸微弱,时不时抽搐。它看见我们,长长地“喵呜——”了声,挣扎着站起来,顷刻又倒下来。我抱住它,久久抚摸着它毛发不齐整的脑袋,把能对它说的、它听得懂的好话反复说给它听:“好猫咪咪,咪咪好猫,咪咪乖呀,咪咪乖乖!我们回来了,来送你了……”
凌晨一时零七分,万籁俱静,咪咪又尖细痛苦地“喵呜——”了一长声,再次挣扎着想站起来,却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咪咪的墓地选在一片它经常在窗口望见但从未到过的翠竹林里,陪葬品有煮鱼的小锅、猫粮和红垫子。为它殡葬的人是小李,还有与它相识以来一直倾注关爱的新的女主人。
时过一年,Kissy无疾而终,享年十四岁。宠物医院的医生说它也是“内脏器官都老化了”。Kissy的墓地则在一棵小杏树下,陪葬品与咪咪相若,只是小锅换成了它俩共用的饭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