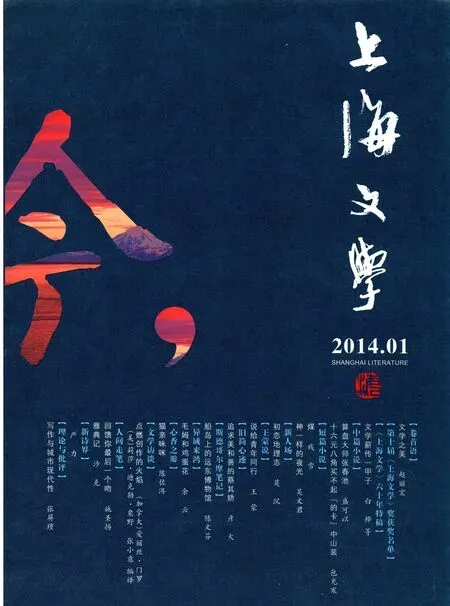令渠述作与同游
2014-04-29郜元宝
郜元宝
杜甫号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还说“诗是吾家事”,“歌诗”一项,被姓杜的包圆了。诚然是“诗圣”,一千多年过去,没有哪个不服的。
许多文人创作谈,和杜甫一样,也总能找到神秘的机缘,似乎命中注定,不写作,毋寧死,而一旦拿起笔(打开电脑),就万事和谐,浑身舒畅,并且凡有述作,皆可永久。
每次读到这种天才的自述,我都很沮丧,因为自己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说起来一点也不堂皇,无非敢于下笔,勇于投稿,又遇到许多好心的编辑和宽容的刊物,没太碰钉子,渐渐就俨乎其然,当仁不让,甚至麻木不仁起来,仿佛人生天地间,不免要写点什么,不免要发表点什么,不免要对别人发表的什么信口雌黄,说三道四。得罪了!
所以当《上海文学》创刊六十周年之际,除了由衷地表示祝贺、感激,我还油然沉浸于一种心情之中,叫做诚惶诚恐、惭愧不已。
比起这份杂志几代编者对文学的无私奉献,自忖还是太多鄙吝之心;比起这份杂志在文学盛时开疆拓土的勇气和才情,自忖还是太过保守和愚钝;比起这份杂志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毅然坚守,比起他们对新老作者一如既往、一视同仁的鼓励与呵护,自忖真是贡献太少、无以为报;比起这份杂志各擅胜场的无数优秀作者,自忖更是太过贫弱。
岂敢恬然以《上海文学》作者自居,附骥尾以达千里?惟愿见贤思齐,有以自振而已。“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真的作者莅临,倘能叨陪末座,屏息倾听,也就欣然有喜,夫复何求!
工业社会发轫之初,黑格尔就预言艺术即将消亡,但在他身后,各门或新或旧的艺术依然存活,直至于今;
二战结束时,阿多诺的名言不胫而走:“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就是野蛮。”但各种或新或旧的诗,以及和诗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写作,也依然存活,直至于今;
数码时代揭幕,纸质媒体不断被宣布死刑,但包括文学刊物在内的许多纸媒还是顽强支撑着,直至于今。
过去依赖简帛纸墨,如今更过转移到网络,但风景不殊,正自有媒介之异,何况网络传输和保存手段,远非简帛纸墨所能望其项背。
诗、艺术、文学、纸上书写、印刷乃至文字本身,或许真有关乎灵魂的永恒质素,可以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尽管被恒久记录的,并不全然美善,但美善必定也在其中。
是所祷也,因寄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