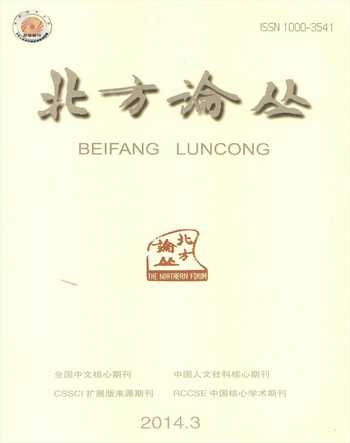聚众案件与清代せ层政权的社会控制机制
2014-04-29周蓓
周蓓
[摘要]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州县衙门既是国家对地方社会实行控制的中心,也是基层民众和官府交涉互动的场所。通过考察州县官治理策略与聚众案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清代官府针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机制,从中思考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关键词]聚众案件;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94-05
Abstract: Group Events reflect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of Grassroots society. The county government is such a place, in which the state controls local communities; grassroots society and the official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ses and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ntrol strategy,focuses on the official prevention, governance and control mechanisms for the group events, explores effectiveness and limited of local government social control mechanism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group events;local government;social control mechanisms
清代,聚众案件包括聚众闹赈、抢米暴动、抗粮抗租、宗族(乡族)械斗、打教、聚众强劫,等等,表现形式多样。县级行政辖区是较大规模聚众案件的集中发生地,也是社会控制和行政管理相对薄弱的一环。清代地方官府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策略对于当今社会控制体系的建立健全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历史经验。
一、知情而治,防之未然
“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1](《自序》)。州县官首先要对地方情形、民生风俗了然于心,知情而治才可能做到掌控有度。陈宏谋主张,州县官要人手一册州县舆图,不但州县官自己可以凭图熟悉地方,“上司问及,可以随事登答”[2](卷二十,《饬去州县舆图檄》);诸如“借还常平,借还社仓,劝种桑蚕,兴立义学,选充乡保,稽查匪类,缉拿窃贼”等事务,只要“一展舆图”[2](卷二二,《通饬留心图册檄》)便可以一目了然。了解民情的另一条途径是咨访当地士绅。事先准备一本“客言簿”,向他们询问“里中有无匪类、盗贼、讼师”,以便日后查用[2](卷二二,《学治臆说·称职在勤》)。
地方绅士借助其声望和财力积极参与地方行政,在诸如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教育、保甲、地方团练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下层士绅包揽钱粮词讼,带头闹赈,挑动民众抗粮,借地方公事之名挟制官府;或是组织纠约宗族械斗,窝盗分赃,为朝廷所深恶不容。雍正帝曾言:“绅士居乡,傥有违理肆行之处,令有司约束劝导之者,无非欲其同归于善,并非令地方官有意摧折之也”;“其小有过愆者”,尚可以劝戒之法“令其悛改”,而对敢于聚众抗官、藐视国法者,“则置之于法,以警其余”[3](卷五五)。礼罚分明,用之防之,官与绅之间的进退博弈是地方治理不能回避的话题。
发挥基层社会内部控制体系的功能,使之参与和协助地方治理不仅是来自最高权力者的统治意图,是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州县官防范聚众案件发生的组织基础。以“息讼”为最终目的的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司法调解机制,是力图将社会内部矛盾和冲突解决在萌芽状态,消除在基层。族长、乡约或长老等乡村头面人物往往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州县官指导其调解纠纷,管束族人,直至双方“甘结和息”,社会恢复平常,地方官府在其中所起的是引导、协调、促进甚至强制执行的作用。
乡村辽阔,地方官耳目难周,基层组织和地方社会力量分布广泛,信息反馈和沟通较之官府更直接、更快捷、更深入,因此,地方官会依靠、敦促或规定他们要观察基层动向,及时反馈,便于官府第一时间得知案发情况。如对于械斗案严重的闽粤地区,州县官“择各乡村衿监耆民责令随时查察,收缴铳械,一闻构衅之端赴县密报”[4](档案号:04-01-01-0624-002),官府酌加奖赏。四川省盗匪四起,道光年间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谕令各属州县官利用分布在各处乡村堡寨的乡保、场头为眼线,动态巡查四境,一遇报案即连同差役赶赴现场,跟踪追击。
此外,就地方治安、防匪缉盗等相关事宜颁行张贴告示,晓谕民众,这也是州县官防范未然的手段之一。道光元年(1821年),巴县衙门为防范盗匪案颁发告示:
示仰各乡场约客、团首、铺户、居民人等知悉:尔等每逢场期,务于该场栅外两头防守稽查,务使匪徒不能入境。如场内遇有匪徒绺窃滋事,刻即鸣锣截拿。如遇夜晚以及乡僻山村,遇有窃匪,团众协力擒捕,务获解县,以凭尽法严惩,并将出力之人从优奖赏 [5](p.365)。
通过告示的舆论宣传作用,告知乡民如何防范盗匪,如有案件猝发,如何缉拿。同时,将团首、场头等人应当助官一道稽查协捕的职责标明纸上,一方面令其照单遵行;另一方面,用这种广而告之的方法能使盗匪有所凛畏,闻风而退。
同光时期,在广东任知县的徐庚陛曾就民人聚众放火焚寺的案件出示《禁聚众示》。告示中,徐庚陛首先自责“教督无方”,旋即将朝廷惩戒聚众案件的光棍例告谕民众,使之不要知法犯法,同时表白自己没有向省府请兵捉拿肇事民众的良苦用心。因为大兵一到,炮火无情,有可能伤及无辜,甚至玉石俱焚,这是双方均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继而寄希望于乡绅、宗族能够发挥管束乡民和族人的作用,将案件消弭于未然 [6](卷六,《禁聚众示》)。
二、治之已然,控之燎然
官之设衙,意在地方建置一个政务处理中心,大多数民众视见官为畏途,但发生利益纠葛、受损或是有相关利益诉求之时,依然会有民众选择县衙作为主张和保护其自身权益的裁决点。
以聚众闹赈案为例,乡民因灾失收,饥荒难度,或因歉收导致米价高昂,遂至县衙报灾求赈,要求官府开仓粜米或借贷仓粮。他们结群拥挤至县堂哄闹,如若诉求受挫,便会哄堂闹署,强借官仓、富户,抢夺米店。县官循例勘灾放赈,一面开仓平粜,一面动员乡绅富户一同帮扶救济,为防止饥民流民横生,滋生祸乱,官绅采取合作,度过危机。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浙江太平县上年被灾歉收,乡民赴县请粜,“无知童穉,拥挤喧哗”[7](卷三八九),尽管原来调拨的漕米已在前几日粜完,但县官睹见民情汹涌,仍下令再次开仓碾粜。
从一些案例中发现,清代基层社会有的争端和冲突在演化为聚众案件之前,当事人曾诉诸官府,纠纷虽经官府调解裁断的努力却以致命的暴力告终,这种情形多见于宗族(乡族)械斗的案件。例如,福建同安县詹、叶两姓自嘉庆五年至十九年(1800—1814年)连年械斗,查其缘由,皆因嘉庆五年(1800年)十一月间,罗溪乡举人叶瑞莲,革生叶淳等“因谋并乡村,借派不遂,书召林汀元、陈山来等千余匪焚毁祠屋,抢劫财物,掳索男女,杀灭詹端、詹锐”。当时的知县孙树楠断令叶瑞莲等“公出洋钱一千九百元赔偿,出给告示,谕令息事”;谁料想,这不是两姓械斗的终止而仅仅是开始,詹、叶族人由此一衅相因,互相报复,詹姓族人叠次上控,直至都察院[8](档案号:04-01-01-0590-004)。暴力争端并非完全代表地方官府审理的失败,表明官方干预民间纠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影响这类案件的背景和影响因素会一直持续地发生作用,冲突再度发生将很难避免。
面对骤发的群体事件、暴力事件或冲突,州县官往往先采用常规的劝谕疏导方式尝试解决,若方法失效或是局面混乱难以控制,便会动员手中的兵役进行弹压。采用抚驭交替、剿抚结合的手段,力图尽快平息,因而治与控之间如同扳机连发一般密不可分。倘若出现局势混乱,有失控的趋势,典史、巡检等担负有治安缉捕的佐杂官员,或是知县本人就会带同县署配备的差役驱逐人群、捕拿为首之人。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江苏昭文县发生一起聚众抗粮大案。七月间,为首的金德顺欲图包揽漕粮征收不遂,“起意闹署,并打毁与县往来绅家”。金德顺等人到县衙喧嚷,后又打杀两名差役。署县何士祁带兵役下乡抓捕,金德顺等带领众人拒捕夺犯。知县感到局势无法控制,于是“上省请兵”,巡抚李星沅命苏州府知府桂超万带兵前往弹压。这时,抗粮的民众分为三路,“聚众万余人矣”,而桂超万所带勇丁总共100人,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桂超万思忖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须先稳住民众的情绪。因而在二十五日贴出六言告示,采取抚谕手段告诫粮户,此次带兵前来只是为了擒拿为首的金德顺,民众如能放弃与官府对抗,朝廷将会从宽处理,形势暂时没有进一步恶化。二十六日,桂超万再出六言告示,重申与官府对抗的结果只能是“骨碎如粉”,因不忍看到生灵涂炭才再次贴出告示,实属“一片婆心”。此时,他采取恩威并施之策。
桂超万一队人马到齐后,于二十八日又出四言告示:
刁民闹署,拒捕抗官。首犯不献,实属冥顽。
万不得已,整旅桓桓。守分良民,闭户勿观。
恐飞炮子,误致伤残。被逼百姓,早散求安。
是夜,桂超万领兵到达案发地点,发现众人看见告示后均已散去,于是“出示悬赏查拿”,陆续将首要各犯十余名拿获。桂超万亲自到乡村劝谕安民,随后带兵返回省城。巡抚李星沅见此次枪炮未发,贴出三张告示就将案件平息了,“颇悔调兵”。桂超万听说此事后“面呈供折”曰:“三路聚众已有号合,非兵,断不能散,非散,断不能拿,即告示亦借兵威耳。”李星沅阅后深感言之有理,一起聚众闹漕、抗官拒捕的大案终因知府桂超万办理得宜而没有酿成巨案[9](卷五)。
州县官手中仅有的差役兵力不足以应对大型聚众案件时,唯有向省里的督抚请兵,由督抚派委适当的人选带兵负责弹压,此时,知府、道员和地方驻军应对燎然而起的突发事件和防守地方的作用便凸显出来。道府在案发时不仅要亲自领兵剿办,事后还要亲临当地安谕百姓,既显示兵威赫赫,也宣扬皇恩浩荡。诚如桂超万所言,剿以抚为先导,抚以剿为后盾,剿抚兼施。“弹压”一词实存随机应变、刚柔并用之意,还须得一“宽严互用、抚驭有方”的干员运用得当,方能化解祸端,平息骚乱。基层政权必须得到来自上层政权的军事力量支持才能够如此迅速地控制局势,防止事态恶化。
三、可控或不可控——基层政权控制聚众案件的可能性
在清廷处理聚众案件的机制设计中,基层政权的防范——治理——弹压是实施控制的三道基础防线,但在基层社会矛盾的漩涡里,官府和官员有时非但没有成为案件的“灭火器”,反而是激发其产生和蔓延的触媒,其原因何在?
矛盾冲突往往是围绕利益产生的,钱粮税捐首当其冲。清代对官员实行低俸制,微薄的官俸无法应付日常开支,必须从制度外谋取灰色收入来弥补开销不足,在朝廷征收定额之外浮收钱粮是其中最稳定的一项。围绕在钱粮税捐周围形成官和绅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州县官浮勒中饱,生员包揽索费,胥役则游移在官绅之间,或代官浮收,或苛索粮户,上下通吃。双方争夺之下,处于竞争劣势的生员便会越级上控,有的以控告书吏浮收为名,实则隔山震虎,目标指向的是幕后指使的州县官,希图借上层政权的力量抑制基层政府对其利益的侵夺。如道光六年(1826年),浙江仁和县民徐凤山聚众闹漕,要求释放上年因赴京控告仓书勒折浮收而被判军流的沈培政和徐寿高方肯完粮[8](档案号:04-01-35-0252-033)。咸丰初年,东南财赋之区沦陷,贪吏朘削,以至民不聊生,强者抗拒,弱者流亡。有的州县收漕竟有应交一石浮收至两石之多,导致民怨沸腾,激成事变。江苏嘉定、青浦,以及浙江临安、新城、于潜、长兴等县,均因钱漕浮收遂有聚众戕官之案件,“究其起衅根由,皆此不肖官吏贪婪所致”[10](卷一百五)。
地方官的陟黜奖惩系于考成,考察的重点是钱粮和刑名两项。如若催科不力,钱粮不完,各级官员将面临停升、罚俸、降级、革职等程度不一的处分。时人甚至直言“征比累民,考成累官,此尤政之大蠹”[2](卷一百十四,《上汪稼门方伯论渠工书》)。州县官一面加紧催征,对拖欠的粮户杖责、监禁,对催讨不力的胥役勒限、鞭扑;一面设法垫交缺额,挪移填空,以图规避处分。催征过紧,可能导致粮户聚众抗纳;垫纳挪移,州县官则会通过浮收或预征的方式弥补先前的损失。于是,浮收勒折、预征派累又可能成为聚众抗粮案的导火索。
清代明确规定,拟罪在杖徒以上、须通详招解、报部定罪者,以及奉各上司批审须详覆者,名为案件;拟罪在枷杖以下,一切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细故,属州县官自理范畴者,名为词讼。州县自理案件要求20天审结,寻常命案州县限三个月、盗劫和情重命案州县限两个月必须上解府州,如有延迟,将关涉考成。衙门内负责佐理刑名的幕友为了保全官员考成通过,只悉心办理案件,对于词讼则漫不经心。
由于词讼无关考成,州县官任意积压,以致小讼拖成大案,易结之案变成无结之案。而审理时,或草率决断,或一味宕延,或强制和息,基层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冲突结于堂上却未能终于堂下,告官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讼断而祸未息,案结而聚斗起——纠众械斗者,结伙盗劫者,伙党仇杀者,依旧猖行。程含章在《论息斗书》中指出:“地方官惟知鱼肉乡民,不理民事,民间词讼延至数年不结,甚或数年不得一见官面……由是官视民如寇仇,民亦视官如豺虎。上下隔绝,情意不通。此所以愈治而愈坏也”[2](卷二三,《论息斗书》)。宗族(乡族)械斗这类案件背后通常有着势力强大的宗族、乡族作为支撑,并形成民间的一套善后处理惯例,如赔偿尸亲、贿买顶凶、引匪助斗,等等。县官不及时处理民间纠纷案件,命案隐匿不报,胥役家丁需索受贿,基层司法诉讼体系失效是械斗不止的原因之一。
命盗之案查拿限期紧迫,又须上解府司,州县官于此亦有对策,一曰讳匿不报,一曰化大为小。嘉庆初年,广东潮阳县和平乡马姓与梅花、金埔两乡郑姓素不和睦,两姓互斗案件共57起,其中56起为命案,均发生在知县李树萱任内。此外,还有未经通报的案件12起,计53命。李树萱因命案过多,案犯难获,遂将此十二案抽藏卷宗,讳匿不报。直至尸亲马世敬等赴督抚衙门具控,上司批饬严查,李树萱才开始着手办理。但他为了规避处分,将人命案有的牵混到其他案子里,谎称“案已通详”;有的则捏称案犯已病故、外出,或假称案中并无其人,是尸亲误控,企图“捏详销案”。直到署惠潮嘉道吴俊亲赴督拿,才将凶犯全部拘捕到案[8](档案号:04-01-08-0081-026)。至于化大为小,更属平常,州县官往往涂改报案日期,“分案通详”,将一衅相因的大案分割成一个个小案,单独上报,以减少每个案件的伤亡人数,将械斗、命盗重案粉饰分解成为寻常命案,逃避处分。对于盗匪案,州县官则讳盗为窃,意存消弭,或大伙强盗仅抓获数名即草率完案。
清代州县官以“一人政府”[11](p.334)的全职全能模式独撑一县之治理,朝廷为其配备的资源极其有限,他势必要动员地方社会资源参与配合。衙门内,靠的是胥吏、幕友和长随;衙门外,官府主导的保甲组织,以及士绅阶层为主导的基层社会组织为其提供了权力延伸的网络,知县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够施政敷治。然而,“今之吏治,三种人为治,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2](卷二一,《学治臆说·论用人》),是这三种人在行政运行中操控着县衙的三班六房。书吏盘踞在内,与幕友连为一气,把持刑名;胥役缉捕在外,或受会党、盐枭、土豪、巨盗贿通,得钱卖放,或借勾摄之事,持票吓索,通吃两造。衙门内凡此通病种种,致使州县官听讼不畅,案积尘埋。
嘉庆年间,包世臣以幕友身份为工科给事中胡承珙拟就了一份《条陈积案弊源》的奏折,折子里以命盗案犯递解到省为例算了一笔账。从县到省的距离,以一天走50里计,往返大约需要3个月。一个案犯的递解成本“总以五七十金为率”,而这些费用均由原来负责该案的差役赔垫。差役每月的工食银极低,只得先借库银,不足部分便借案索取签票,借票索诈与案子相关之人。而在较为贫穷的地区,差役无力垫赔解费,抓获命盗案犯后,如果事主势力较弱,官府即“薄加惩创,不行详办”。其结果是:
其民习见杀人不死,为盗无刑,所以贫僻下邑,民风更坏。是故大狱之兴,源于小讼之不结;小讼不结,源于胥役之贿搁;胥役贿搁,源于解犯之赔垫;解犯赔垫,源于发审之展扣[12](卷七,《为胡默庄给事条陈积案弊源折子》)。
发审、驳审制度造成案件在各级衙门中巡回旅行,法定的审理期限被不断展延,基层胥役的递解成本也在不断递增,此诚胥役借案需索“滔滔不可禁止”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中央制度设计中的漏洞,其运转诚非州县官所能够左右的。
基层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以士绅为首的基层组织配合与否,影响着州县官对地方的治理和局面的掌控。官与绅、官与民是一对矛盾统一体。首先,地方官需依靠宗族、乡族组织完成粮赋征收,地方政府包括县官本人所不可或缺的经制外收入也得从民间汲取;其次,借助地方社会力量推行教化,约束族人,将社会矛盾纠纷消解于乡村内部,减少县衙的诉讼压力;再次是组建保甲组织,将民户编连成组,实施联合防卫,维持社会治安。在基层社会一方,基于对现有秩序的认同,绅民均会将自己自觉地纳入到官方的统治体系,如求赈、求粜、告官、上控、协同剿匪等行为都是这种认知的突出表现。但在利益追逐之下,士绅也会与官府展开对抗,如抗粮、纠斗、窝赃、通匪等,背离官方为其设定的轨道。
面对庞大的辖区人口,州县官支配的武装配置中只包括三班衙役和有限的地方驻军,其中,能为一县治安所有效使用的兵力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衙役本身需承担衙门的各种杂务,而且与地方社会各种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既要用也要防。一旦遇到大规模聚众案件发生,州县官无力弹压,需要动用军队,而地方驻军的统辖权在各省督抚手上,必须向上司申请。徐庚陛认为,州县官向上请兵弊大于利,军队“呼唤不灵,调派不服,非但不能得力,反难禁其驿骚”[6](卷五,《覆本府条陈积弊禀》)。申请调兵的公文运转不仅颇费时日,等兵弁调拨到位,案件形势已发生变化。况且军费开支要由县里筹措,县官没有指挥权,军队又不听调遣,有时非但不能助力,反而要防范营兵滋扰地方。因而地方官通常招募乡勇壮勇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通过地方绅商募集资金,维持一支“或多或少具有常设性的雇佣军”[13] (p.171),基层社会的剿匪行动大多数都需要他们的参与配合。
理想状态下,父母官亲民勤理,“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14](卷三四,《职官典》),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安定祥和。而在基层政权的行政治理中,以州县官为首的官衙群体对基层利益的分割和侵蚀势必会引发冲突,各种利益群体在其间明争暗斗。处于劣势的贫民百姓有的铤而走险,为盗为匪,有的组织或加入秘密社会,通过底层团体寻求互助。伴随社会经济变迁,冲突和对抗在变化中不断增多。加之考成压顶,儒家法约刑简的“息讼”思想被虑于处分的州县官堂皇借用,以“压讼”、拖宕、讳匿等各种方式隐瞒地方社会的实际状况,直至聚众案件爆发,惊动高层,才会采用常规性的应对措施收拾局面。官府处于强势的情况下,政令下达、应急调度尚能迅速到达基层,剿抚兼施,案件较快得到平息;至民强官弱,县官自忖难治,遂退而观之,有的则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顾此失彼。本应作为基层政权补充力量的基层社会内部组织,却时常在州县官处理聚众案件中暗中掣肘,有的成员甚至带头与官府对抗,令资源配置乏缺的州县官更加孤掌难鸣。
囿于以上种种,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控制机制的最前端——基层政权——同时也是实际操控层面,其制度预设与治理实践之间明显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使得案件是否能够及时控制变得难以预测。
结语
防止未然,治之已然,控之燎然,可视为控制聚众案件发生的上中下三策。州县官在基层掌握地方舆情,施行教化,抚民有方,利用基层社会各组织建立自我防卫体系及相应的预警制度,是为上策;理讼解纷,赈灾养贫,防盗缉匪,及时解决基层社会矛盾,适时缓解阶层间冲突,运用常规治理手段,将聚众案件控制在萌芽状态,是为中策;冲突骤起,措施不当,激变事端,或民间由私斗变为战争,盗匪猖獗,事态失控,州县官不得不请兵上司,借助兵威,或剿或抚,为的是将燎然之火扑灭,是为下策。而问题却时常出现在中间的治理环节,在利益支配和考成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州县官非但不能履行其守土安民的职责,反而变为激变良民的祸端。同时,有限的配置性资源与无限责任使得基层控制环节更多地依赖于上层政权的强势和稳定,官强民弱则基层政权控制力尚能游刃有余,官弱民强则基层政权步履维艰、自顾不暇。
任何看似完美的社会控制体系都只是补偏救弊的应急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摆脱清代统治阶级所采用的居于聚众案件末端的反应式控制,而代之以聚众案件发生或扩大之前端的控制模式,须得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和齐备社会危机的预警机制,并为各社会群体提供一个合理的表达和沟通渠道,以期缓解由于彼此间矛盾和冲突所带来的压力。唯此,对于社会冲突的控制才有可能得以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1]徐栋.牧令书[M].官箴书集成[Z].合肥:黄山书社,1997.
[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2.
[3]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Z].
[5]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6]徐庚陛.不慊斋漫存[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3卷[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7]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Z].
[9]桂超万.宦游纪略[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0卷[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10]清文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包世臣.齐民四术[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3][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4]清朝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