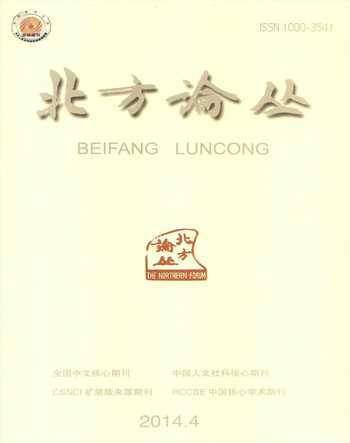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举要
2014-04-29李生龙
李生龙
[摘要]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主要有三个:其一,对庄子文学地位之评论。或称其书为“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或尊其为“文章家鼻祖”,或将之列入“宇宙四大奇书”、“天地四大奇书”。其二,对《庄子》文本之评析。涉及《庄子》文本的总体艺术审美特色,内、外、杂各部分之特点,各篇要旨,还具体到节、段、句、字,颇多精当之说,体现了前人对《庄子》文本钻研、涵咏工夫之深。其三,庄子对后世作家、作品影响之探析。涉及《庄子》对诗、赋、散文、小说等各类文体之影响。
[关键词]宋至清;庄子;文学评论
[中图分类号]I2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4-0011-06
对庄子的文学评论,《庄子》书中就有。如《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云云,就可以看作一种文学评论。其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大抵皆寓言也”云云,也可以看作一种文学评论。不过,真正的文学评论是在中唐古文运动以后,到宋代才比较具体且视角较广。各种诠注评批、别集、序跋,以及诗话、词话、赋话、文话等,都有对庄子的文学评论。故本文从宋代开始讨论。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涉及范围甚广,这里主要列举三个方面。
一、 对庄子及其文学地位之评论
早在西晋,儒家倾向明显的玄学家郭象就已在《〈庄子注〉序》中称庄子:“不经而为百家之冠”。郭氏讲的“不经”,字面上可泛泛地理解为不符合常规,实指不符合儒家经典。郭的评论意为,相对于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庄子居于首要地位。细细推敲,郭氏所评的“诸子之冠”,还主要指庄子哲学思想方面的“知本”,文学意义并不明显。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庄子》:“晚周诸子,莫能先之”,看上去与郭氏无异,实则鲁迅的立足点在文学,其“诸子”包括儒家。郭象的评价后世曾有人质疑。明代孙应鳌为王雱的《南华真经新传》作序,回应这种质疑说:“世评《庄子》不经而为百家之冠,夫‘不经何足冠‘百家?盖徒见决圣智、弃仁义诸语,为悖尧舜周孔,皆泥其辞而不达其意。”[1]意曰,庄子只是言语上同儒家相悖,实际上并不反儒。唐代成玄英《〈南华真经疏〉序》说庄子:“钳键九流,括囊百氏,谅区中之至教,实象外之微言”,“九流”、“百氏”当然包括儒家,而“至教”则表明庄子地位在儒家之上。成氏本人是道士,加之唐初的崇道语境,故有此种评价。成玄英的评价比郭象高,却不如郭象的评价那样为许多人所接受,这是因为郭象的评价比较适合后世儒学语境的缘故。
从中唐开始,《庄子》被尊儒尚文的韩愈、柳宗元、李翱等所重视。韩愈在《进学解》中所开列的古文典籍包括《庄子》,为后世重文之士推崇《庄子》提供了理由。北宋崇儒气氛浓厚,不少崇儒的文士,如苏轼、王安石、王雱等喜欢《庄子》,但心思多放在对《庄子》中的反儒言论加以 “回护”上,尚未能论及庄子的文学地位问题。到了南宋,对庄子的文学评论多起来了,对其地位的评论也就重新成了话题。如林希逸《〈庄子口义〉发题》借用陈亮的话说庄子:“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郭子玄谓其‘不经而为百家之冠,此语甚公”,就是有名的评论。
明人对庄子的文学地位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些评价非常之高。如杨士奇说:“《南华经》矢口而言,粗而实精,矫偏而论,正而若反。读者须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以习见参之,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也。”按:此条不见于今传杨士奇之《东里集》,见于明人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之《南华附录》卷8,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27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第172页。陆西星《读南华真经杂说》亦有此语:“《南华经》皆自广大胸襟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实精,矫偏而论,正而若反。读《南华》者,须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以一习见参之,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独以其文也。”见《南华真经副墨》,《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7册,第28页。陈治安所录是否为陆西星语而假托杨士奇,姑存疑,然为明人对庄子的评论则无疑。清代藏云山房主人所撰《藏云山房老庄偶谈录·杂说摘要》录此作陆长庚,即陆西星语。见《南华经大意解悬参注》。清人徐廷槐《南华简抄引文》引此数句作“前人每论《南华》,矢口而言,粗而实精,正而若反,此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今之论庄者引此以为徐廷槐语,不确。徐廷槐既曰“前人”,则表明非己语。称《庄子》为“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是从阅读效果立论,认为《庄子》同诸子比较,其思想与表达的自由更能拓人胸襟、开人眼界。蔡毅中《〈南华真经评注〉序》说:“余尝读《庄子》,谓其言虽无谓而独应,若超无有而独存,其狂怪变幻,能使人骨惊神悚,讵不称文章大观哉!……庄子者,九经之庶子,而老氏之忠臣也。老氏于礼也犹曰乱首,充其说诈为仪、秦,惨为申、韩,流污为乡愿,庄子不失其派,尤能扩大之,信可为百家冠矣。”[2](p10)蔡氏称庄子为“百家冠”,表面上是继承了郭象的说法,实际上有自己的视角:他既肯定庄子的文章堪称“大观”,又肯定了《庄子》为儒经之“庶子”、老子之“忠臣”,从庄子对儒、老的继承与开拓角度论证了庄子在诸子百家中的突出地位。明代陈治安从文学影响的角度说:“《淮南》《吕览》袭其词,退之、眉山善其法,大哉庄子文也!乃文章家鼻祖,其精神至今犹在。”[3](p29)称庄子为“文章家鼻祖”,是从庄子对后世的影响着眼,从肯定庄子为文可为后世法的角度肯定了《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文学特色说,宋代就有人认识到《庄子》同楚辞一样,其突出审美特色是“奇”。如苏辙曾说:“微言精老易,奇韵喜庄骚。”[4](p54)陆游也说:“遗文诵史汉,奇思探庄骚。”[5](p4296)古人又常以有价值又不易见之书为“奇书”。“奇书”兼有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内容新颖脱俗,形式翻空出奇,自出机杼,出人意表,不同一般,即使书肆流行,家藏户有,也可以称之为“奇书”。明代“嘉(靖)、万(历)间,三大师(指禅师雪浪恩公、臞鹤悦公、湛怀义公)比肩长干(今属南京),而老庄盛行于世。先是历下(指李攀龙)、娄东(王世贞)、谼中(汪道昆)诸公,皆以著作显,竞搜奇猎艳于漆园,而三大师独标名理”[6]。在文人普遍把《庄子》当作搜奇猎艳渊薮的氛围中,《庄子》进入“奇书”之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明人有3种“四大奇书”之目,其中两种包含《庄子》。第一种是王世贞把《史记》《南华》《水浒》《西厢》合称为“宇宙四大奇书”;第二种是冯梦龙、李渔把《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合称为“四大奇书”[7](p1)。第三种,今人多未道其详,只标举出了清代李绿园《〈歧路灯〉自序》的“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盲左,曰屈骚,曰漆庄,曰腐迁”。李绿园所谓“古有‘四大奇书之目”,具体“古”到什么时候,却未见有人指明。其实张溥《庄子序》给我们提供了某些信息:“若其(指庄子)文章,变化离奇,神鬼杳眇,山川、风雨、草木,其观已止。先辈云:‘六经而外,惟《左》《史》《庄》《骚》为天地四大奇书。非虚谀也”[8](p5)。张溥所说的“先辈”具体指谁,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明代早于张溥的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五四《黄先生墓志铭》有“文喜左氏、庄、骚、太史,得其旷婉”[9]之语。再往上溯,南宋陈傅良就已把左、史、庄、骚并列:“六经之后,有四人焉,据实而有文彩者,左氏也;凭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皆前未有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立之士,其谁能之!”[10](p190)此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都曾引用,为宋人之说无疑。到清代,除李绿园,乔亿也说:“诗学根本《六经》,指义四始,放浪于《庄》、《骚》,错综于《左》、《史》,岂易言哉!”[11](p1069)可见以《左》《史》《庄》《骚》为“四大奇书”,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庄子》进入“四大奇书”的过程表明了庄子文学地位的不断上升。
清代对庄子地位的评论近于传统说法者颇多,但也有一些新的视角。最著名者如金圣叹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称为“六才子书”。“才子”这个概念,虽是文人的同义语,却又不同于一般的文人。金圣叹解释说:“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12](pp4-5)可见金圣叹心目中的“才子”是指具有巨大创造能力的作家。
清初宣颖《南华经解自序》说:“呜呼,庄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少时读《史记》,谓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及览《李太白集》,称之曰‘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予私心向往,取而读之,茫然不测其端倪也。”[13](p1)他虽然不称庄子为“才子”,而称其文为“千古一人”,从纵向的角度抹倒了千古文章,把《庄子》推尊为第一,与金圣叹称庄子为“才子”实殊途同归。
有意思的是,到清代,一些评论庄子的学者不只是评其思想文字,而是把庄子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对待,评出庄子的精神气质来。如林云铭说:“庄子似个绝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矢口便骂,眼大如许;又似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14](p11)又如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无端”、“庄子每多愤世嫉邪之言,又喜欢讥诮出名大户”、“庄子最是深情”[15](p6)等等,都令人想起历史上某些文人或才子的形象。
总而言之,庄子的地位在历史上凡有三变:先是作为诸子出现,从韩愈说他得子夏门人田子方之传始,其后不断有人把他看作儒门别派,成为“准儒士”(笔者另有文谈及此,此不展开),到清初成了“才子”。从这个变化可看出庄子的地位有一个由诸子、儒学,到文学的大致转移过程。
二、对《庄子》文本的文学评析
宋以降对《庄子》文本评论极多,涉及《庄子》的总体艺术审美特色,内、外、杂各部分的特点,各篇要旨,还具体到节、段、句、字,细致、具体,颇多精当之说,体现了前人对《庄子》文本钻研、涵咏功夫之深。对今天的读《庄》论《庄》者亦有启发、借鉴价值。因所涉甚广,这里只能择其大者、精者而言之。
宋代即有对《庄子》总体上的艺术、审美特色的评论,而且这些评论对后人有一定影响。如宋代叶适云:“夫举世俗所以屈庄周之文者,以其虽一切寓言,而能抑纵舒敛,自无入有,殆若天成,而实言者或不及也。”[16](p1)明代唐顺之《答茅鹿门第二书》以本色论文曰:“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跟叶适讲的“天成”就有一定的联系。清代宣颖说:“古今格物君子,无过庄子,其侔色揣称,写景摛情,真有化工之巧。”“化工”说跟“本色”说也有关联。清末刘熙载《艺概》说《庄子》“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又可见“化工”说的影响。南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十《人间世》尾评:“愚尝谓秦汉以来诸子立言者袭《南华》语意不少,独经中设譬引喻,未尝蹈前人一辙,而愈出愈奇,是谓文可文,非常文也。”[17](p337)指出《庄子》有“设譬引喻”的特点。宣颖《南华经解·解庄小言》说:“《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对《庄子》设喻特点的诠释较褚伯秀更为精辟。
从宋代开始,研究者就开始分析内、外、杂的思想差异。如宋末元初道教学者褚伯秀说:“内篇命题本于漆园,各有深意。外杂篇则为郭象所删脩,但摘篇之首字名之,而大义亦存焉。”[17](p409)“《南华》一经,肆言浑浩,湍激籁号,作新出奇,跌宕乎诸子之表,若不可以绳墨求。而内篇之奥穷神极化,道贯天人,隐然法度森然,与《易》《老》相上下……善学者于内篇求之,思过半矣。”[17](pp398-399)后来王夫之《庄子解》站在儒家的立场辨伪,他认为,内篇之文意皆连属……杂篇除《庚桑楚》《寓言》《天下》外,每段自为一义而不相属。这些都尚未完全论及文风。宣颖《南华经解·解庄小言》说:“庄子真精神只作得内七篇文字,内篇为之羽翼,杂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随手存记之文。”诸家都似有重内篇而轻外、杂之意。刘凤苞《南华雪心篇·凡例》则认为,内外杂各有特色:“《南华》内篇为悟道之书,精密浑成,大含元气;外篇尽行文之致,洸洋恣肆,推倒百家;杂篇则随手存记之文。亦得零金碎玉,美不胜收。”这些评论,对我们认识《庄子》各部分的风格差异和文学价值有启发作用。
对《庄子》的每一篇文章都逐段评议、末加总评自南宋始。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刘辰翁《南华真经校点》、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均为如此,评点涉及思想和文学,但以思想为主,文学只是偶及之。后者还有集评性质,分段罗列前贤评语,再附上自己意见,文末还有“总论”。明清出现了相当一些偏重文学批注的集评本。如署名归有光、文震孟的《南华真经评注》,沈汝绅的《南华经集评》,潘基庆的《南华经集注》,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等等,都收录了大量前人的文学批注。一些集评、集注所涉前人评语有的比较可靠,有的则并不完全可靠。
宋以来对《庄子》各篇的评析散见于各种评注本者俯拾即是。评论的视角多种多样,有的是提挈一篇思致关键,有的是点破一篇思想主旨,有的是指明一篇表达方法,有的是分析一篇层次结构,有的是综括一篇技巧美感。这里按《庄子》篇目先后略选数条,以见一斑:
陆西星评《逍遥游》:“意中生意,言外立言,絖中线引,草里蛇眠。云破月引,藕断丝连。作是观者,许读此篇。”(《南华真经副墨》)
刘辰翁评《齐物论》:“庄子文字快活,似其为人,不在深思曲说,但通大意,自是开发无限。”
杨慎评《齐物论》和《养生主》:“内篇之文,繁而美者《齐物论》,简而美者《养生主》。”[18]
苏辙评《养生主》:“庄周《养生主》一篇,诵之如龙行空,爪趾鳞翼,所及皆自合规矩,可谓奇文。”[19](p382)
胡文英评《人间世》:“想庄叟落笔时胸次有无限悲感,借此以为发泄之具,而人且比于旷达,真瞋目而不见丘山者。”
胡文英评《德充符》:“通篇细腻风光,远行近折,倘执着剩水残山,反错过真源妙境矣。”(《庄子独断》)
刘辰翁评《骈拇》:语至刻急,每结皆缓,若深厚不可知者。优柔有余,得雄辩守胜之道。自经而子,未有成片文字,枝叶横生,首尾救应,自为一家若此。(《南华真经点校》)
归有光评《盗跖》:“至圣至知反为盗资,绝圣弃知,天下自安,通篇一意。”[晋]郭象注,[明]归有光评,[明]文震孟订正《南华真经评注》,此条又见于高秋月《庄子释意》,应该可信。
陆西星评《天道》:“《天道篇》辞理俱到,有蔚然之文,苍然之光,学者更当熟读。”(《南华真经副墨》)
林云铭评《秋水》:“是篇大意自内篇《齐物论》脱化出来,立解创辟,既踞万仞山巅;运词变幻,复擅天然神斧。此千古有数文字,开后人无限法门。”(《庄子因》)
陆西星评《徐无鬼》:“此篇多有隐晦难解之语,如层峦叠嶂,争奇献怪,游涉此者,即可新耳目,长意见。读《庄子》至此,不得草草,三复愈有深味。”(《南华真经副墨》)
很多评论对《庄子》中的段、节、句、字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其中也有许多精彩之语。段、节、句、字四者的分析往往结合在一起,用以概括整体,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彰显亮点,提醒关注点。评论或长或短,随菜下箸,不拘一格,经常下数语便能见出真知灼见。这里引林希逸《口义》的评语为例。林希逸分析《逍遥游》第一段(从“北溟有鱼”到“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说:“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广大之乐,却设此譬喻,其意盖谓人之所见者小,故有世俗纷纷之争,若知天地外有如许世界,自视其身虽太仓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晋人所谓蜗角蛮触,亦此意也。”分析大鹏“怒而飞”一句说:“鸟之飞也必以气,下一‘怒字,便自奇特。”分析“齐谐者,志怪者也”说:“《齐谐》,书名也,其所志述皆怪异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经》之类。然此书亦未必有,庄子既撰此说,又引此书以自证,此又是其戏剧处。”分析《齐物论》:“汝闻天籁而未闻地籁”到“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一节描写大风的文字:“子綦因子游一问,知其亦有造理之见,欲以天籁语之,遂如此发问也……庄子之文好处极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书中此为第一文字。非特《庄子》一部书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无此一段文字。诗是有声画,谓其写难状之景也,何曾见画得个声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声也;‘于与‘喁,又是相和之声也。天地间无形无影之风,可闻而不可见之声,却就笔头上画得出。非南华老仙安得这般手段!每读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已也。此段只是说地籁,却引说后段天籁,自是文势如此。”这些分析有段、节、句、字意义的诠解、提炼与扩张,有相关学科知识的沟通以及相邻艺术的通贯,处处渗透着评者独诣的文本解会与审美颖悟,能很好地引导读者分享对《庄子》文本的理解、欣赏、阐释与再创造。
三、庄子对后世文学影响之探析
以今天传播学、接受史的眼光反观庄子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说不完的话题。大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艺理念、审美观念,小到构境运思、文体选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等,都可以从后人的作品中找到庄子的雪泥鸿爪、蛛丝马迹。如果不考虑人们在实际创作中对庄子的接受而仅仅只及评论,则宋以后评论者的关注面似还没有今天这样广阔,大抵集中在一些明显受《庄子》 影响的作家、作品。以作家论则涉及汉以后诸多作家,以作品论则涉及诗、赋、散文、小说等各类文体。
宋人已关注庄子其人其文的影响,评论的方法多样,角度不拘一格。例如,文学家曾巩说:“司马迁学《庄子》,班固学左氏,班、马之优劣,即《庄》《左》之优劣也。”黄庭坚则说:“司马迁学《庄子》,既造其妙;班固学左氏,未造其妙也。然《庄子》多寓言,架空为文章;左氏皆书事实,而文调亦不减《庄子》,则左氏为难。”[20](p327)这是通过《庄》《左》《史》《汉》之比较显示《庄子》对司马迁之影响。朱熹论邵雍,说他“为人似庄子,只是庄子见较高、气较豪,康节则略有规矩”[21](p3342),是通过比较显示庄子对邵雍为人识见、气格之影响。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十《人间世》尾评说:“愚尝谓秦汉以来诸子立言者袭南华语意不少。”则是从思想、语言的承袭来说明庄子对诸子散文之影响。
宋人谈及《庄子》对杜甫、韩愈、苏轼的影响者较多且较具体。如陈善说:“杜诗有高妙语,如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可谓深入理窟。晋宋以来诗人无此句也。‘心地初乃《庄子》所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之义也。”[22]这是举一个语词来说明《庄子》思想对杜甫诗歌之影响。黄彻说:“《庄子》文多奇变,如‘技经肯綮之未尝,乃未尝技经肯綮也。诗句中时有此法,如昌黎‘一蛇两头见未曾‘拘官计日月‘欲进不可又‘君不强起时难更,坡‘迨此雪霜未‘兹谋待君必‘聊亦记吾曾,余人罕敢用。”[23](p76)此为举诗句说明《庄子》对韩愈、苏轼诗歌造语奇谲多变之影响。谢枋得说:“韩文公(愈)、苏东坡二公文皆自《庄子》觉悟。此集可与《庄子》并驱争先。”又评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此序谈诡放荡,学《庄子》文。文虽学《庄子》,又无一句蹈袭。”评苏轼《前赤壁赋》:“此赋学庄骚文法,无一句与庄骚相似,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潇洒神奇,出尘绝俗,如乘云御风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视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挂之齿牙,亦不足入其灵台丹府也。”[24]吴子良说:“《庄子·内篇·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观之,万物皆一也。东坡《赤壁赋》云:‘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盖用《庄子》语意。”[25](p549)这些评论都揭示了韩愈、苏轼学《庄》之精神而不蹈袭其语词的特点,涉及文、赋等文体。
明人谈及《庄子》影响的评论也很多。如王衡《〈新刻葵阳黄先生(洪宪)南华文髓〉题辞》:“昔称善学《南华》者,无逾苏长公,能识广大于变化,故其赋《赤壁》《游铭》《大觉鼎》诸篇,机神固不殊焉。不然,而章句之徒相与摘而用之,至棘喉滞吻,是胡宽之营新丰也,是优孟之学叔敖也。糟粕是读,斫轮且犹笑之,何况于清评乎?”[26](p3)陈治安说:“《淮南》《吕览》袭其词,退之、眉山善其法,大哉庄子文也!乃文章家鼻祖,其精神至今犹在。”[3](p29)沈一贯说:“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辩说者取其辞。《庄》之所以畜于今者,以学士大夫好其辞也,而义则尠有过而问之者。”[27](p2)林尧俞说:“晋室诸贤,亡不祖述《庄》《老》以资谭柄,所谓燕函粤镈,夫人而能也。今儒术大明,二氏稍绌,顾结撰之士,往往拾其余渖,果贫腹,炫绮观,凫乙瓻痴,宁免纰漏。”[28](p5)显然,明人不仅注意了《庄子》对前人的广泛影响,而且关注了《庄子》对当代的复杂影响。明代庄子的影响,甚至及于科举。刘士琏《南华春点》就是为科举而作。其自序云:“大都制举子业者,取古文为骨力,取时文为精采。而古文自六经《左》《史》而外,似难乎其为言矣……谬觉《南华》一书,灵足以济经,逸足以用史。再其真落于幻,幻归于实,实变而化,虚圆之妙,诚如摇波之月,戛涧之松,若有若无之间,令人不可方物……予因春官点次,题曰‘春点,付诸梓行,用以见举业家,亦各有一得之愚。” [29](pp2-3)
清人对庄子影响的关注承前代而有所拓展,例子极多,这里只举一个方面。自韩愈把“庄骚”并举后,宋以后常将庄子与楚骚并论,清人更有不少兼而论其影响者。如乔亿说:“诗不缘于《楚骚》,无以穷《风》、《雅》比兴之变,犹夫文不参之《庄子》,虽昌明博大,终乏神奇也。”[30](p1116)方东树说:“以六经较《庄子》,觉《庄子》新奇佻巧;以六经较屈子,觉屈子辞肤费繁缛。然而一则醒豁呈露,一则沉郁深痛,皆天地之至文也。所以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庄以放旷,屈以穷愁,古今诗人不出此二大派,进之则为经矣……渊明似庄兼似道,以皆不得仅以诗人目之。”[31](p5)刘熙载说:“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曲江(张九龄)之《感遇》出于骚,射洪(陈子昂)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太白之诗以庄骚为大源。”[32](pp2421-2424)这些论说,可见出清代人已看到《庄子》同其他文学影响的交互性与复杂性。
《庄子》具有小说的某些特征,今人有诸多专论。有人称庄子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父”,有人称庄子为“中国小说创作之祖”,父也好,祖也好,地位虽然一个比一个抬得高,仍都有不准确之处,因为庄子之前或同时,类似于小说的东西如《穆天子传》《山海经》之类,都被视为小说,也不好说这些作品就没有主观创造的因素。实际上,《庄子》之所以被视为小说,主要原因是具备了小说同寓言共有的虚构特征。《庄子》书中 “寓言十九”“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已指出其虚构性。司马迁在《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强调:“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呲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汉代人已认识到小说有“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虚构的性质,寓言的虚构同小说的虚构很难截然划界,故小说兴起之后,《庄子》很容易就被视为小说。宋人黄震说:“按庄子以不羁之材,恣汪洋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未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涯涘,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明代沈津《庄子题辞》重复此说,并指出其与司马迁所说的联系:“按庄子以不羁之材,恣汪洋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太史公所谓寓言是矣。”[33]刘辰翁也以“小说”评论《庄子》的某些文字。如评论《胠箧》:“故尝试论之,世俗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两句说,“起语突兀,本是小说家,充拓变态,至不可破。”评“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数语,说“小说家时时有之”。可见在南宋人心目中,《庄子》具有小说特点,是一种共识。明代胡应麟从志怪小说角度评论《庄子》:“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固极诙诞,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汲冢琐语》十一篇,当在《庄》《列》前,《束皙传》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盖古今小说之祖,惜今不传。”[34](p474)胡应麟认为,《汲冢琐语》才是“古今小说之祖”,与黄震称《庄子》为“古今诙谐小说之祖”虽有不同,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近乎寓言。清代林云铭则从《庄子》与传奇小说关系的角度说:“《庄子》当以传奇之法读之。使其论一人,写一事,有原有委,须眉毕张,无不跃跃欲出,千载之下可想见也。” [14](p12)这确是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王雱.南华真经新传[C]//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十四.
[2]蔡毅中.庄子序.南华真经评注:卷首[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19册.
[3]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序五[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26册.
[4]苏辙.和张安道读杜集〔用其韵〕[C]//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5]陆游.散怀[C]//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潘之恒.《道德颂》序.僧悦:董山藏草[C]//禅门逸书初编:第7册[Z].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81.
[7]李渔《三国志演义》序[C]//李渔全集:第10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8]张溥《庄子南华真经评》序[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27册.
[9]文渊阁《四库全书》[M].
[10]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 南华附录:卷七[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第27册.
[11]乔亿剑溪说诗:卷上[C]//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一[C]//金圣叹全集: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3]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4]林云铭撰,张京华点校庄子因·庄子杂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胡文英撰,李花蕾点校庄子独见·庄子略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6]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三[C]//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7]胡道静,陈莲笙,陈耀庭,等选辑道藏要籍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8]杨慎丹铅余录·总录:卷十二、丹铅余录·摘录:卷十一[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王正德余师录:卷三:苏籀记苏辙语[C]//历代文话:第一册.
[20]范温潜溪诗眼[C]//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邵子之书[C]//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1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2]陈善扪虱新话:卷七“杜诗高妙”条[M].上海:上海书店,1990.
[23]汤新祥校注,黄彻著巩溪诗话:卷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4]谢枋得文章轨范[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C]//历代文话:第一册.
[26]王衡《新刻葵阳黄先生(洪宪)南华文髓》题辞.黄洪宪评辑.新刻葵阳黄先生南华文髓[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18册.
[27]沈一贯《庄子通》序[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9册.
[28]林尧俞《南华经荟解》序[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第13册.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
[29]刘士琏自序《南华春点》[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29册.
[30]乔亿剑溪说诗:又编[C]//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1]方东树著,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2]刘熙载诗概[C]//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3]沈津庄子类纂·庄子题辞[C]//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6册.
[34]胡应麟二酉缀遗:中[C]//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己部.北京: 中华书局,1958.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