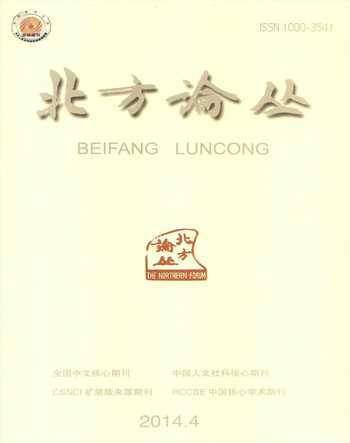元代作家的民族、遗民身份ぜ拔难叙事扩张和抒情自由
2014-04-29何跞
何跞
[摘要]元代的文人构成具有一些特点,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主导下的元代文人具有了民族差别特性,而元代文学也具有异族征候。从纵向历时的视角来看,则涉及遗民身份及其所主导的遗民文学。元代文人的身份差别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身份文学。而关于元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也具有一些特色:一是基于叙事抒情的杂糅多体性,这以元曲为代表,表现为叙事的介入和抒情的自由解放;二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样式中的抒情呈现出自由之势,并相应地有了个性的突出和心态的平和,平易正大和奇崛的文风都是文人相对自由的存在状态所促成的。
[关键词]元代文学;作家作品;民族;遗民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4-0007-04
每一个时代的文人们都有不同的身份,影响其不同的创作。身份差别下生成的文学也具有一定的整体特点。在元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文人们有着更为突出的身份差别。范梈《木天禁语》:“翰苑、辇毂、山林、出世、偈颂、神仙、儒先、江湖、闾阎、末学。已上气象,各随人之资秉高下而发。”[1](p.751)他将元代文人分为这样诸多不同的身份,如在朝、在野、释子、道人、儒士等。而且他认为,不同身份的文人会有不同的气质禀赋,也影响到诗歌的气象风格。这里,我们可以从横向共时和纵向历时两个角度考察元代文人的身份差别,以及这种身份文学中的元人身份意识。而对元代文学的整体特点,则可以从元曲和诗文两类不同的文学样式,以及抒情叙事两个文为功用上面来进行把握。
一、横向共时:民族性主导下的元代文人民族差别特性和元代文学的异族征候
从横向来看,对元代文人的身份可有多种划分标准。以民族的标准可划分为,少数民族作家、汉族作家;从地域上可划分为,宋金、元朝统治区、元大都、南北、各行省的文人;以在朝在野的标准又可分为,遗民、隐士、士夫、政客等;以学术思想为标准可划分为,理学、道学家、释子,并生出士人和经学的论题;以文人主要擅长的文学体裁可以划分为,诗人、文章家、小说家、曲家及诗剧、诗曲、文曲、文剧、诗文等文人的多元通融;以才艺为标准则分为,文人、书法家、画家等,如王冕等人;以性别标准可分为,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文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然是身兼多重身份,而我们以不同的划分标准审视,其实也是对文人自身的多个属性和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以学理概念为基础和工具,更准确详细地对其进行研究把握。总之,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元代文人们不同的身份及其身兼多重身份的特点。在此视角下,又可以看到多重身份对元代文人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以及这些身份特点在其中所投射的印迹,甚至由此所形成的一种风格特点。从这个理论基础出发,可以产生出许多研究论题,可以突出元代文人的某种身份特点来进行研究,可以有地域文学、女性文学、诗学、曲学、民族文学、理学家文学、画家文学等多个研究域。我们也可以综合考察元代文人的多个身份特点,进行学理上的交叉比较研究,如理学与文学的研究、画家文人的研究、遗民诗人的研究,这样生出的论题又会很多。
而在元代文人的身份中,相当突出的一点,也最具有元代本色的一点就是民族身份。蒙思明认为,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使得元代社会包含着各类矛盾:如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康里军人与一般平民之间的矛盾、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甚至算端与母族之间的矛盾[2](p.8)。
其中,民族矛盾是很明显的一种,可以说是元代社会各种矛盾产生的基础和背景。关于民族矛盾,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将其与阶级矛盾相提并论,然而,这是有失偏颇的,阶级矛盾的分析法并不适合于所有的研究,很简单,就像蒙思明所说:“既是阶级矛盾为主,就不能是民族矛盾;既是民族矛盾为主,就不能是阶级矛盾。”[3](p.12)民族差别问题一直贯穿并笼罩着元代历史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纵遇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4],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是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而红巾军“穷极江南,富夸塞北”的起义理由也带有浓厚的南北之分和民族怨气。这种不平和怨恨,甚至及于为元朝所用的汉族官僚士夫,要杀戮士夫。
研究民族差别对待,这与元代文学本身的民族特征,后人对元代文学的接受和研究存在有关,可以说这种差别对待,正是源于元代文学本身浓厚的民族差别性。民族性的问题作为一个时代特点,整体笼罩着元代文学的书写,而元代诸多文学作品往往有一种浓厚的民族气息、异族特点或是受其影响,以排斥或认同的形式与其间接关联着。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气候,也是一时代文学的大脉动,需要从宏观上把握这种大时代特色和文学动向进行研究。这种元代文学的大征候及文人们在此之下的律动吟唱风格,其实在与其他汉族一统的王朝,如汉、唐、宋等的对照比较中可以明晰地显露出来。元代文学的异族气象与唐宋等朝的汉文化气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把握元代的异族征候背景时,却不能夸大这种民族差别,把客观存在的民族差别性异化为一种民族矛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涵盖一切研究。正如邓绍基先生在为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长期以来,谈论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总是比较强调民族矛盾和‘九儒十丐这类问题。但当这类历史事实和稗史记载被当作一个无所不纳的框架,或者由此形成为一种套说的时候,反而会导致种种失去历史真实性的误说。”[5](p.2)
民族差别不全是民族矛盾,还存在交叉融合。元代文学的书写大多还是用汉文书写的,这就体现出异族融合、他语书写的问题。在元王朝建国之前,蒙古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蒙鞑备录》记载,成吉思汗建国之前“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6](p.91),“后来逐渐采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蒙古文。1269年,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采用藏文字母创制了‘蒙古新字作为官方的蒙古文。而于文学创作,尚是一片‘不毛之地”[7](p.260)。
就是在这种异族参与、他语书写的大趋势下,元代的文坛还是呈现繁荣的景象,清代顾嗣立编选元诗就说:“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8](p.1987)。足见异族性对元文学的发展不是限制,而是增进。
元代文人,统治和主导风尚的统治者们及文学的广大受众,所有的群体都大量地掺入异族身份,必然使整个文学现象和风气都注入异族的因子,在包括审美、形式、题材、题材、思想、价值观、性情等方面,都渗入异族的风格。而文人主体及其影响者和受众身份的异族加入,他民族的异风异调的渗入,对元代文学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文人、学人群体混杂,其自我意识也渐淡,少数民族以讲述先民英雄故事为尚的文学被发扬,并促进了戏曲小说的生成,整体表现出重感性而话语简单的态势。
二、纵向历时:遗民身份主导的遗民文学
纵向来看,元代文人的差别主要基于具体历史阶段的身份异同,可以粗略划分为:金元之际、宋元之际、元中期、元明之际的文人。由金入元或者由宋入元的文人作为旧朝遗民,在金元、宋元之际无疑有着存在的尴尬性,因而也避免不了其文学书写的尴尬。而由元入明的文人又作为新朝旧臣,在文学写作中总会留有旧有的影子。他们都在历史的碾进中接受朝代的更替,无论情愿与否,也无论是表面接受,还是内在认可,至少他们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要面对自己的思想信仰、生存问题,还有后人的评论。于是,随之产生了一个大的论题,即关于遗民作家群的研究。
在遗民群体中,往往会有一些自明其志、拒仕新朝的人,他们不能像文天祥、谢枋得那样,以激烈的抗争形式死节,而选择以隐居的方式表明其不合作之态度。由于其隐逸的直接目的性,他们的隐逸情怀不能是真的自然洒脱,而是加注了一种“忧怀激烈”的故国之音,以及倦于所见争战后的浮世幻灭之感和自身的生命愁惘,甚至个体穷达的无奈感伤。其情绪的激烈抒写已远离了隐者的恬然自得,而是自表现“失”了。如在金朝为翰林文字的李俊民,金南渡后隐于嵩山,元朝招之不仕,四库馆臣说其“集中于入元后只书甲子,隐然自比陶潜,故所作诗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竒崛为工”[9](p.2200)。李俊民在《即事》一诗中感叹争战:“铁马长驱汗血流,眼前戈甲几时休?”[10](p.61)在《白文举王百一索句送行》中怅怀世事:“世事纷纷乱似麻,不堪愁里度年华。”[10](p.45)李俊民目睹战乱,感受着浮世人生,时空流易,千变万化,伴随着一种怅惘愁怀,《和子荣》一诗中吟咏:“浮云世事日千变,流水生涯天一方”[11](p.108),《调祁定之》中说:“浮世几场漂杵血,流年一局烂柯棋。”[11](p.112)将战乱、浮世、人生、离别、时间等主题同时表现了出来。这与真正的隐逸主题和隐逸诗风,如清新、潇散、恬淡、自然等大相径庭。戴表元是由宋入元的文人,一生大多数时间隐于浙东山水之间。他的歌行体诗中多有直接写悯伤时乱者,悲忧感愤,抒情直接,平白如话,无奈的愁怀呼之而出,情绪十分浓烈。《夜寒行》直接诉说:“昨日天寒不成醉,今日天寒不成寐。醉迟得酒可强欢,寐少愁多频发喟。”[13](p.19)这也大不同于真正的隐逸诗风,倒是近于元白歌行。在感怀世乱之外,他还感叹着个人境遇的“穷”“拙”,《丁丑岁初归鄞城》说:“城郭三年别,风霜两鬓新。穷多违意事,拙作背时人。雁迹沙场信,龙腥瀚海尘。独歌心未已,笔砚且相亲。”[12](p.47)
即使在他的一些清丽的绝句中,也总是隐隐地埋藏着时流世乱、独身难安的伏笔,如《西兴马上》:“去时风雨客匆匆,归路霜晴水树红。一抹淡山天上下,马蹄新出浪花中。”[13]风雨之后的“马蹄”“浪花”总有余悸未平之感,而晴天“淡山”“水树”始红,也有着霜冷之痕和风雨之迹。
对一介文人会产生影响或冲击的时间断限除了王朝的更迭,还有他个人人生中的大事经历,这又包括入仕前后、归隐前后、入职及游历行迹的地方变更,如在京还是在地方,其青年、壮年、晚年的差别,影响思想情感而发生较大变化的事件,如学于某人、某个文人集会等,这些都是历时性考察文人所应注意的问题,构成个别文人的诸多时段和区分特征的研究。
三、基于叙事抒情的杂糅多体文学:以元曲为代表的叙事介入和抒情的自由解放
而从文学作品来看,元代文学有其自身的作品构成和文体分布,并且具有元代特色。叙事性和抒情性的粗线融合是元代诸体文学的主要特点,这表现在新生成并成熟的文体,如散曲、杂剧,也表现在旧有文体形式内容的变化上。直白的抒情和直接的叙事又是这样的文体特点中呈现的一种趋势。
元曲是元代代表性的文体,元曲的生成和文学特性本身足以说明,元代文学的叙事增强和抒情的自由,因而本文暂不讨论其他文体样式。
元曲的叙事性较以往的文学样式大大增强。“曲”是元代的标志性文体,张晶先生将其解为,“歌诗”“剧诗”,反映了其诗语本质和不成熟的叙事性。他说:“曲分散曲(小令、套数)与戏曲(杂剧、传奇):前者是歌诗,是词体的解放和扩展,也是民歌和市民小唱的一种演进;后者是剧诗,是散曲和戏剧相结合的产物,在歌诗基础上再加宾白和科介,是具有更高综合性的艺术。”[7](p.378)他把散曲理解为词、民歌、市民小唱的演进。将戏曲理解为散曲基础上的戏剧性(宾白、科杰)注入,他对元曲“歌诗”“剧诗”的“诗”性定位则是看到“曲”这一种文体的诗性抒情本质。然而,它又毕竟由以诗歌为代表的正统雅文学的抒情性走向了叙事性和舞台表演性。散曲是诗与杂剧的过渡,散曲中的重头小令增加了语言表述的空间,更是故事性与抒情性的结合。同时,戏曲是韵语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的粗略结合,因于戏剧中诗词的几近泛滥的介入,用以表现人物心理、描画场景、连接叙事等,我们可以不准确地说杂剧是小说与诗词的结合。
曲的音乐性和舞台演出性使其叙事性带上了更为直观的娱乐视听效应,而抒情的效果也更为强烈。由“诗”到“歌”,而且是“民歌”“市民小唱”,由吟咏诵读到歌唱,这是韵语文学在音乐性上的质的膨胀,这就是“曲”区别于以往其他韵语文学的本质特征,也是“曲”这一名目的生成的原因。不论是“散曲”,还是“戏曲”,都是“曲”,都有音乐介入,只是介入的音乐媒介不同。散曲又称“乐府”“小乐府”“新乐府”,因为它与音乐有关。然而,散曲又称“清曲”,因为相对于“戏曲”而言,它是“清唱”的,主要是人声歌唱,不像“戏曲”还需加入宾白和动作,也不需其他乐器的配合。明代魏良辅说:“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不比戏场借锣鼓之势。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14]
在叙事性增强的同时,元曲的抒情更为自由和形象生活化,将文学的抒情直接化为生活的事件,使抒情具有具体的事由和内容。张晶先生对于“曲”的“歌诗”“剧诗”解,将“曲”的“诗”语性、音乐性、舞台叙事性等三个特征十分有层次地概括了起来。而这三个特征都有利于加重“曲”的自由抒情的特点。诗语文学本来就是语言艺术,是语言想象的抒情,音乐是听觉艺术,更是直观的听觉抒情,它们都使得“曲”的抒情性具有更浓郁、更直接、更自由的特点。基于叙事性和舞台要求而对于诗语体裁、入乐曲调限制的放宽,例如,口语衬字的加入,多种曲牌曲调的大量汇入和灵活运用,不仅营造了诗语叙事的空间,也使得抒情表现的空间大大得以拓展,“曲”的抒情有了程度上和容量上的伸缩,总之,抒情更加自由了。对此,明人王骥德有很好的概述,他说:“
晋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为渐近于自然。吾谓: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夫诗之限于律与绝也,即不尽于意,欲为一字之意,不可得也。词之限于调也,即不尽于吻,欲为一语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则调可累用,字可衬增。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吾谓: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15](p.178)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词如诗,曲如赋”[16](p.363)。“赋”体乃是“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7](p.134),它写物,写人的情志,而且语言修饰的空间很大,能“铺采摛文”,抒情自然也就相对自由得多。“曲如赋”,则曲的抒情写志也就相对诗词要自由得多。
抒情结合叙事,文体和风格都呈自由解放之势,这是元代文学的一个特点。叙事性也渗入其他诸多文体,使得元代的诗词文也具有元代的豪放、直白特色,当然,这也带来雅俗之辩。而诗与剧、诗与散曲、文与散曲、文与杂剧、诗与文等文体的多元通融,也促成了元代文学的杂糅多体和自由之势。在诗学上,元人的诗法诗格类著作较多,这既影响后来的诗学走向,也体现了元代文学风气重实际和直白功利等特点。
四、诗文中的抒情自由:个性突出与心态平和
除了以北方作为为主导的元曲,在多由南方作家构成的诗词文的领域,也即元代文坛上,还有两股风气,即重个性自由和平易正大之风。文风中的个性突出,首先是文人的个性别出,文人的个性又与其出生和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系。由地域分野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而促成的文学上的类属个性,在元代文学中十分明显。另外,这也与元代盛世一统的大征候相呼应。
在元代对文人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蒙元统治者不太重视诗文正统文学,而对后起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戏剧较为感兴趣,这促成了文坛上“文倡于下”的整体特征。与宋代文人多由科举为官参政,实现其人生价值有所不同,元代诗文作家的生存模式和生活内容多是隐逸、游历、雅集、题画,几乎形成了当时诗坛的风气。在自由的存在状态,一统的政治气候和大元气象笼罩下,元代的文人更加自由,这促使形成了元代文坛两种大的趋势:一是个性突出,二是心态平和。前者在元代初期和晚期,由于兴衰错落,朝代改易,社会风云变幻,波及影响文人的心态情绪,尤其突出。元初有江西庐陵刘将孙、赵文等,提倡性情。元后期有杨维桢,更是个性张扬。但在明朝建立,朱元璋主世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相对自由被统治者收回,一些极具个性和思想的文人也被压抑,甚至残害,由元入明的高启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后者则主要在元代一统、社会较为安定的情况下,形成一种普遍的盛世文风。这当然也有宋代程朱理学沿流到元代所产生的影响。理学的心性平和自然,境界阔大端宁,也与元代安宁一统,文人宽松的环境和相对自由的生存状态十分契合。许多文人同时也是主于理学的儒者,如吴澄等人。这种身份兼具与思想基调,使得元代中期的诗文理论和主张主于“自然”“自得”。这里又包含求真不伪的意味,要求真实的感情和不矫揉造作的创作,在这点上,它与张扬个性的、追求自然真性情一类的文人又是一致的。然而,理学思想为基的儒者文人们又讲求“约情归性”,以“天理民彝”为标准,这一方面由个体的“情”位移到普遍的“性”;另一方面,又由个人关注滑向了社会关怀,并且在程度上从激烈动荡,走向深邃平和。
在元代相对自由的大气候下,元代文坛始终贯穿着求真不伪的思想主导,只是情绪上由浓到淡、从张至敛、由个体到社会,这个趋势在元代后期又开始反归,整体上完成了一个随王朝兴衰而由个性到共性再到个性的过程。这是其大体上的脉络走向。在这一整体的风向之下,在元代相对自由的话语环境中,文坛风格多样,对诗法的要求也比较自由,各有所宗,或“师古”,或“师心”,或主唐,或宗宋,呈现出自由之势。
总之,纵观元代的文人构成,可以从共时的民族性问题及历时的遗民问题来进行把握。而关于元代的整体文学风貌,则可以从抒情和叙事两个文学特性来观照,元曲的生成与文学特点足以说明并代表元代文学的一种整体趋势,即自由杂糅。而在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样式中,抒情也更为自由,个性的突出和平易正大的文风,其实都是元代文学抒情自由的一种表现。
[参考文献]
[1]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自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郑思肖.心史[M].广智书局校印丛书第一种.
[5]邓绍基.序[M]//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6]韩儒林,陈得芝.元朝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8]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上:凡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纪昀,陆锡熊等原著总纂,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李俊民,杨奂,杨弘道.李俊民集、杨奂集、杨弘道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11]顾嗣立.元诗选: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戴表元.剡源集附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
[13]戴表元.剡源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魏良辅. 曲律[M].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5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5]王骥德,陈多,叶长海注译.王骥德曲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6]刘熙载,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
[17]刘勰著,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作者系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