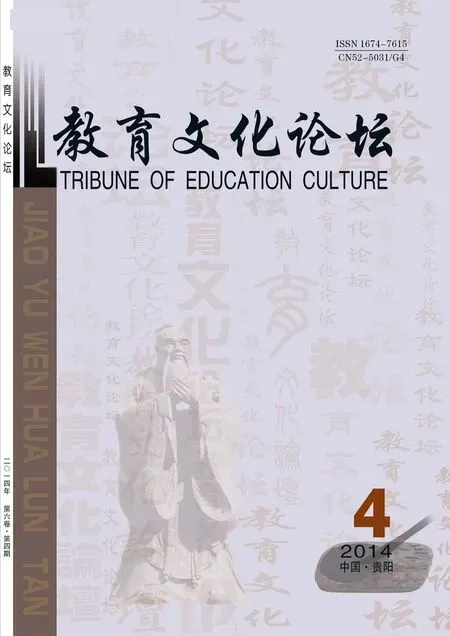从神性到陌生人力量:贵州傩面具的艺术人类学考察
2014-04-17梁宏信
梁宏信
(贵州民族大学 研究生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引 言
傩以驱鬼酬神为主要内容,伴随着仪式性演示和模拟性表演特征。[1] 1傩祭是傩活动的最初形态,始源于黄帝时期。商周时,因社会各阶层的重视而逐渐形成固定的制度,每在“季春之月”、“仲秋之月”和“季冬之月”定期举行“天子之傩”、“国傩”和“乡傩”等活动。汉至隋唐朝时期延袭旧制,通过定期举办傩事以驱鬼逐疫、祈福纳吉;至唐朝时,“民间傩仪将傩祭的驱逐仪式与祈求仪式结合了起来,傩祭适用范围大大扩展,这为宋代傩仪系统的重大改革作了铺垫。”[2] 8
宋时,道家思想空前膨胀,其势力逐渐延伸至傩仪体系中,使得道家神祗成为傩祭的主体神。与此同时,文化的高度繁荣也使得各个文化系统间相互借鉴与融合,傩活动吸收了歌舞、戏剧、曲艺及其他艺术类因子,使其内部的戏剧因子得以凝聚与升华,逐步从纯粹祭祀性傩祭向兼祭祀、表演和娱乐于一身的“傩戏”形态过渡。明清之后,官方傩仪体系衰微并从此一蹶不振,傩活动转向民间寻求生存空间,民间傩戏又进一步发展。
有趣的是,审视整个傩的发展史,面具的使用至今仍以一种“活形态”广泛存在。在傩活动中,它作为一种标识性符号一直为傩最典型的特征,更是驱傩仪式区别于一般巫术仪式的标识物。《周礼·夏官》中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3] 232其中主事的“方相氏”即以“掌披熊皮”、头戴“黄金四目”面具的形象出现。秦汉时期,除方相氏外,行傩时的“侲子”及汉末增添的十二神兽角色,也都是身披假形、头戴面具形象,如“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4] 3127
进入唐宋后,傩戏的逐步成形使傩面具的艺术化程度大大加深。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中载:“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载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5] 253此中驱傩者所戴的“假面”即为傩面具,此时的傩面具因加入更多的艺术修饰而被称之“假面”。到明清时期,傩面具的发展再次达到一个高潮,从数量、角色类型及其艺术水平都超过此前。
傩面具作为巫术-宗教性凝结物,一直传承至今。在贵州的田野作业中发现,境内保存的傩面具类型齐面、艺术形态丰富:从形制极为朴陋的布依族“哑面”面具、彝族“撮泰吉”面具,到形相兼备的仡佬族、土家族、苗族傩堂戏(傩坛戏)面具、布依族“做祧”面具,再到意蕴丰富深邃的安顺地戏面具,这一序列涵盖了傩面具的各个发展层次,是贵州傩面具文化研究的活形态资料。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及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对贵州傩面具的艺术形态、角色获得和宗教艺术等方面作出讨论,以呈现艺术人类学层面的思考。
一、几种类型:贵州傩面具的艺术形态
贵州傩面具在造型上丰富多彩、千容百态且个性相异,根植于流传数千年的傩事之中,它的艺术形态自然地与傩戏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据此,有学者试图将贵州傩划分为两个系列、三个层次:“第一个系列为民间傩系列,包括汉、苗、侗、土家、彝、仡佬等民族的傩戏。在此系列中,彝族的傩戏‘撮泰吉’(变人戏)处于最低层次,它是傩祭向傩戏的初步过渡,是傩戏的雏型。而汉、苗、侗、土家、彝、仡佬等民族地区的傩戏,虽有相当的傩祭成分,但戏剧倾向明显,是傩戏的单一仪式形式过渡的中间层次。最高层次的傩戏是地戏,地戏属傩戏的另一个系列——军傩系列。”[6] 77-78以此为基础,而进一步勾勒了在傩戏不同发展层次上的傩面具艺术特征。这种考察无可厚非地展现了贵州木质傩面具的艺术层次及其艺术特性,但从现存的傩形态全貌来看,尚有不足的地方,尤为突出的是忽略了被称之为“前傩戏”的布依族仪式性傩戏“哑面”及其笋壳面具的存在,对贵州傩戏及傩面具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因此,对于贵州傩面具的考察理应加入对“哑面”及其笋壳面具的讨论。
贵州布依族“哑面”的笋壳面具应该是贵州傩面具的最初形态,其文化形态较撮泰吉(变人戏)更古老,可从其傩的戏剧化水平及面具的艺术水平两个方面来评判。首先,从戏剧化层面而言,“哑面”的戏剧化程度较低,其叙事情节简单,呈现有四个角色(神职人员、兄、妹与阿鲁)的互动场面,分三段进行:挑逗、交媾与哺育,前后为15-20分钟。而且整个表演过程只有动作没有台词,是一种“哑剧”形态。其次,从面具的艺术水平看,“哑面”面具均为笋壳材质,只有二男一女3个面具,“包含的原始文化信息更为遥远,是一种典型的源于本土文化的原始祭祀戏剧遗存,并且形态保存相当完好。”[7] 37“在表演中,表演者的衣着是:绕棺引导者为常人衣着或摩公衣着;其余三人上穿兽皮(一般为羊皮),下围树叶裙(一般为芭焦叶裙)。所戴面具均为笋壳制作。制作过程如下:用一大的笋壳,上部眼睛处挖两条缝,鼻子处挖两个小孔,然后用火碳棍画出眼睛、鼻子、嘴巴等,并在脸上画一些线条。面具分男女,男性面具的鼻子变形为一个长长的、粗大的男性生殖器的样子,并在男根龟头尿道口处,用红色点染之。女性面具的鼻子如常。”[8]57-66面具的造型原始而朴陋。因此可以说,“哑面”面具为贵州傩面具的一种原初形态。布依族仪式性傩戏“哑面”的笋壳面具是一种只分男女,没有年龄体现的面具形态。相较而言,同处于前傩戏序列的彝族傩戏“撮泰吉”,它使用的面具则更为“成熟”一些:“撮泰吉”面具是一种从造型上可以体现角色年龄的木质傩面具。尽管其中出现的5个面具雕工粗陋,俱为黑色,但面具的纹饰和五官已经有着较为清晰的辨识度,除可以看出其代表角色性别外,彼此间的年龄差异也能从面具上“读出”。
相对“前傩戏”的“哑面”面具和“撮泰吉”面具而言,更为成熟的是傩堂戏(傩坛戏)面具、“做祧”面具和地戏面具。它们傩戏的戏剧化程度普遍较高,相应的面具角色品类繁多,而且面具色彩及纹饰丰富,雕刻工艺水平高,能很好地体现出角色的性别、年龄、容貌及性格等。傩堂戏(傩坛戏)的正神面具多以红、白、黑三色为底色,部分面具的额角、脸部及颚的过渡处柔和性欠缺,且冠部做工都比较简单、线条粗犷,略显粗糙。“但是运用的是大笔触雕刻,定型的手法很熟练,具有写实、虚拟结合的造型美。眼窝、眼泡,双颊外的刀锋见棱见角,收刀处极其大胆。单一着色,勾绘只少素着笔,具有古朴拙没的感觉。”[9] 80-84例如唐氏太婆的老态龙钟、山王的可怖獠牙面容、炳灵的白净书生面相和秦童的滑稽歪嘴形象等,总体上可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布依族“做祧”面具也仅算是一种中间层次的面具形态。其面具角色除少许的道教及佛教神祗外,多数为布依族信奉的“土俗神”,包括有万岁天尊圣母、华林仙官、托生花王太庙、莫一、莫二、冯敖老爷等36个。在面具工艺设计上,这些面具更多地融入了地方性的和民族性的文化元素,但刀迹及棱角明显,色泽上也比较普通,整体上缺乏安顺地戏面具的细腻、均匀与华贵。
地戏面具在艺术形态上较上述几个类型的傩面具更具表现力,雕工和用材都极为讲究,特别是在面具的纹饰和着色上投入较大的精力。面具的刀工细腻、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特别是头盔纹饰繁缛、镂雕精细和面部光圆且色彩鲜艳有光泽、韵味十足,全面显示出地戏面具与前述几个类型的大为不同,也是其艺术形态的高处。
总体来说,贵州傩面具的几个类型展示了黔域民间傩的发展程度及其自身的艺术形态特点:它从最为古朴、粗糙、只辩性别的原始形态逐步发展到性别、年龄、容貌及性格等皆可辨识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具角色由具体“人形”面具取代了抽象的指示性/示意性面具。然而,作为一种巫术-宗教性的艺术文化,傩面具与这种特殊的巫术仪式活动展开密切相关——它的艺术造型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神性角色的表现力,而傩仪式的开展也给这种面具增添了神秘的巫术-宗教性魅力。可以说,二者处于一种互构关系之中,这种互构关系又表现在面具角色获得的整个过程之中:神格的面具化与陌生人力量的有意作为。
二、角色获得:神格的面具化
角色是傩面具存在的最基本形式。然而,与一般戏剧的面具角色不同,傩面具的角色是一种神性角色,角色除了形还有“灵”的存在,换句话说,傩面具是角色与角色神性的复合物,它既是角色扮演的一个道具,也是傩系统神祗的化身和载体。
傩面具的角色获得可以在造型上加以设计与装饰,而角色的神性获得则需要通过一序列的仪式来实现,而这个过程从面具的制作开始便一直进行着。例如,在制作地戏面具时,其制作前后都需要举行相应的仪式,以使面具具有相应角色的神性。通常是面具艺人接受村寨地戏队‘神头’的邀请后,选好时辰和马櫈,在诵请师词中烧香、叩头祈请鲁班师祖,然后手提雄鸡作祭祈请师祖和神灵以庇佑镂雕面具工作顺利进行,赋予了面具制作的神圣性。当这些祭祀结束后,工匠便将制作面具的一截木头放在马櫈上,作‘起工’之势,表示面具制作开始。[10] 25-33即为“起工仪式”;而在一副新的面具制作完成后,还需要举行一套“开光仪式”,同样是敬酒、烧香和诵祭祀词,以此来使面具获得角色的神性或具有神的能力,完成其从世俗物向具有神性象征物的转换。通过这样的神性力量和品性的“激活”与“注入”,这些面具就成了傩系统神祗的化身。[11] 148面具角色也才完成其的神圣化。然而,这个过程还并不完结,它在此后的不断被重复使用中,愿望的达成或“灵验”使它的神性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面具角色的“有神性”才逐步被“确认”。
除仪式性傩戏“哑面”外,其他种类的傩戏表演之前都会举行严肃、神圣的“开箱仪式”。这个仪式就如同傩面具被法坛师从“沉睡”的状态唤醒,激活附身其上的神性。在傩堂戏(傩坛戏)的表演中,“开洞”戏成为其开戏后的第一出戏,坛师从“桃源三洞”请出神灵,是傩面具神性角色获得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其神性的被强化一个关键。只有如此,傩事活动的巫术-宗教性才能得以显现出来,为世俗世界完成驱鬼逐疫、祈福纳吉、酬神还愿的事务。
傩面具获得相关的角色神性是扮演者神性角色获得的基础。然而,对于扮饰者的人而言,傩面具存在的本身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如同许多仪式中出现的面罩一样,有意将这些作为神鬼扮演的人与平凡的此世分隔,以便聚合到另一个神圣世界,完成世俗人到神性角色的转换。这种隔离即是“将自己与平凡世界的分隔”[12] 168,同时也是将自己与自己俗世身份的分隔。我们知道,在傩祭、傩舞、傩戏等傩活动中,神、鬼、兽、人等神性角色的扮饰者都是平凡世界的普通人,因此神性角色的获得除了依靠面具本身具有的神性外,这种与此世的分隔也是一个重要的仪式过程,只有将平凡世界的本身隔离掉,扮饰者才能实现向神性角色的转换或过渡。这种转换在傩活动中明显体现,如地戏的表演者为了强化这种与此世的隔离,往往还会事先在头上套一层黑纱(面罩),再戴上富有神性的面具;黔东南部分村寨的“耍变婆”活动,“老变婆”的扮饰者除了套黑纱(面罩)外,还会用黑布将双手双脚包裹起来,使自己完全与世俗世界隔离开。
回归到傩面具与扮饰者神性角色获得的关系上,与此世的隔离仪式无疑是扮饰者获得神性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其神性角色的获得仍依赖于圣化了的傩面具角色本身。这种“依赖”就是一种来自乔治·弗雷泽(James Frazer)的“交感巫术”。“交感巫术”是弗雷泽经典文著《金枝》(Golden Bough)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交感巫术”蕴含着两个原则——相似律和接触律,相应地是模拟巫术和顺势巫术——“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13] 21将这一理论运用在傩面具与扮饰者神性角色获得的问题上同样具有解释力:一方面,傩面具以神的形象进行制作,在形貌上实现了神性角色的存在感。且在扮饰这个角色时,扮饰者在言行举止上都会由内而外地扮成它,神行合一;另一方面,面具的神性赋予使得神格面具化,那么扮饰者戴上这种面具即是一种“亲密接触”的传染巫术,神性角色的获得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将此二者结合讨论,傩面具及神性角色获得、与扮饰者的神性角色获得、傩事活动的巫术-宗教性即体现着这种“交感巫术”的存在。
由此可见,扮演者的神性角色获得依赖于圣化了的傩面具,而傩面具的神性是在一系列的持续性的相关仪式中获得并强化,通过这种彼此之间互构的行动或方式而建立起傩面具及傩的神性力量,用以维系着傩的存在和继续。
三、陌生人力量:一种宗教艺术
角色转换仪式和交感巫术只是角色神性获得的两个“手段”。那么,是何种力量促使傩面具与扮饰者的人二者通过转换仪式和交感巫术实现完美结合的呢?在此,不得不提及一种被称之为“陌生人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的存在才使得傩面具发挥作用,成就世俗扮饰者的神性角色,发挥着傩的神秘巫术-宗教性力量。
“陌生人力量”对我们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接触傩面具都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它通常给人一种与日常生活相异的、神秘的、一种“很不自在”的感受,它是一种切实的身体实践性和感受性体验。
这里所谓的“陌生人”并非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外来人或外乡人。借用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的话,陌生人即“不是指今天来和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和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人,它虽然没有继续游移,但是没有完全克服来和去的脱离。”他以“漫游者”这种与我们“既不太远,又不太近的人”来形成对“陌生人”的界定,其内含了“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14]512换话句话说,陌生人与群体之间存有一种特殊的近距离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近乎暧昧又是彼此不熟知底细。
正因为“陌生人”与群体之间保持这样一种特殊的“接近”和“距离”,因而被认为具有与常人不一样的力量,这种论述已为许多早期民俗学家的讨论话题。法国民俗学者范·热内普(Van Gennep)就认为,“陌生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神圣的,具备巫术-宗教性力量,并拥有超自然之仁慈或邪恶力。”[15]31它这种神秘莫测力量的存在又让人们产生敬畏感,以至于在乔治·弗雷泽(James Frazer,1922)和恩斯特·克劳利(Eenst Crawley,1932)等人的论述中“陌生人”常常以被禁忌的角色出现,因此有必要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然而,正是陌生人的这种神秘特性和敬畏感的存在,也为许多巫术仪式所利用,傩活动无疑便是如此。而傩面具即是使傩产生这种“陌生人力量”的关键所在。
上述指出,“陌生人”就是距群体既不太远、也不太近的人,因为距离太远,将失去与生活群体之间的联系,对群体毫无意义可言;而太近又会成为自己人,不再“陌生”。[16]99因此,陌生人与群体之间总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关系。”傩面具中展现的神性角色即是这种特征:在所熟知的傩堂戏(傩坛戏)神系统里,无论是凶恶的山王、形象可怖的将军、面相狰狞的勾簿判官,还是笑容可掬的引兵土地、洪门土地及土地婆,它们并非是离我们生活过于遥远的角色,而是一些围绕着我们的生活展开的神灵;与此相反的是,在傩堂戏中出现一些历史传奇人物,如孟姜女、庞氏女、薛仁贵、薛丁山等,他们亦似乎就是我们历史生活的一份子,但却总保持着一种我们无法接近的距离。因此,在他们与常人之间的“接近”和“距离”中产生着一股张力,在这个张力使得“陌生人力量”得以发挥。
然而,陌生人又必须与常人不同,处于“另类”集团之中。因此,傩面具在造型上总会以一种极为夸张手法突出神性角色与常人的“不一样”,上述早期的驱傩者方相氏所戴“黄金四目”面具就是一个典型,这种“黄金四目”面具是一种由熊皮假头和青铜假面合套而成的复合式面具,[17]4套上这样的面具,即可把驱傩者和常人明显地区别开来,形成游移在群体之间的“陌生人”角色。同样地,在当下的黔北、黔东北与黔东地区仡佬族、土家族、苗族傩堂戏(傩坛戏)里,所有的傩面具都与常人面相不一样。典型的如山王面具,“这个面具面目凶恶,有可以翻动的眼帘,嘴巴可以活动,大嘴,下颚有两颗獠牙。据说,这两颗獠牙是两颗真的野猪獠牙安装上去的。在其色彩上为黑色和鲜红色,是邪恶和血腥的象征,有时候也可以转化为有力量的象征。但这个面具最特殊的是耳部还有两个类似于面像的雕像,民间称这种雕像为‘抱耳神’,有了这个抱耳神,使整个面具就有了三个头像。”[18] 10-14由此可见,在傩活动中,通过这样的面具将神性角色进行陌生化,成为与正常人相异的“陌生人”,使其具有常人所不能的能力。
另一方面,从扮饰者的角度来看,借用面具使其“陌生化”也是格外的必要。日常生活中的扮饰者与世俗群体彼此之间“知根知底”,通常被认为是世俗的同类,不具备完成驱鬼逐疫、祈福纳吉、酬神还愿等事务的能力。然而,当他戴上形貌与众不同的面具并处于驱傩仪式的特殊场合之中,就会与群体之间形成有特殊距离感的“陌生人”,这种“接近”和“距离”使得人们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畏和信任感,即会将那些世俗人无法自己实现的,驱鬼逐疫、祈福纳吉、酬神还愿等事务交予它来完成。
傩面具使驱傩者从常人生活中陌生化,成为距世俗群体“既不太远,又不太近”的陌生人,赋予了其神秘的巫术-宗教性力量,即“陌生人力量”。这种神秘莫测力量的存在正是傩面具的一种宗教艺术体现。与此同时,这种与日常的接近与距离,也为平凡世界的人感受“陌生人力量”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
结 语
傩面具作为傩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神格的面具化体现。它孕育于古老的巫术文化之中,带有浓重的巫术—宗教特性。它不仅从其艺术形态上体现了这种特性的存在,还在神性角色获得和角色神性等方面也展示着这种基本特性的存在。从傩发展的早期开始,面具就一直为傩事活动所运用,随着纯粹祭祀性傩祭向多艺术因子复合的傩戏过渡,傩面具在数量、造型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贵州境内现存的几个傩戏类型中找到不同层次的傩面具形态。
角色是傩面具最基本属性,其神性角色及角色神性的获得需经相应的转换仪式来实现,即便是极为朴陋的“哑面”笋壳面具和“撮泰吉”面具也同样如此。除了面具本身角色神性获得外,在驱傩仪式的整个展演过程中角色转换仪式也必不可少。然而,角色神性的转换与获得往往依赖于既是角色扮演道具的,也是傩系统神祗化身和载体的傩面具来实现,它就如同一张“神圣帷幕”分隔着角色的世俗性与神圣性,是世俗人向神性角色转换必须合上的帷幕。这张帷幕的闭合即会产生一种被称之为“陌生人力量”,这种神秘力量使驱傩者从常人生活中陌生化,成为具有驱鬼逐疫、祈福纳吉、酬神还愿等巫术-宗教能力的神性角色。正因如此,“陌生人力量”不遗余力地驱使着人们将这张神圣帷幕合上,使巫术-宗教的力量降临。可见,拉上帷幕的力量亦正是来自这种被称之为“陌生人力量”的力量。
由此可见,对于巫术—宗教性艺术文化本体的傩面具而言,除了来自艺术学与美学的艺术性审视及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的文化性表述外,这种来自艺术人类学的思考也是一种必要。关键是,在这种艺术人类学的思考中寻找到了傩面具对于傩活动的极端重要意义及价值,它为贵州傩面具的保护和传承及其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 李子和.信仰·生命·艺术的交响——中国傩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2] 李海平.中国傩面具及其文化内涵[D].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
[3] 林河.中国巫傩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4] 【宋】范晔 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 【宋】孟元老 撰,邓元诚 注.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朱晓君,张超,徐人平.贵州傩面具的层次及其艺术特性[J].艺术探索,2012(02).
[7] 顾朴光,吴秋林.贵州少数民族面具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8] 吴秋林.布依族仪式性傩戏“哑面”[J].民族研究,2005(01).
[9] 杨亭.土家族傩面具的审美发生、形态及意义[J].四川戏剧,2013(03).
[10] 杨嘉铭.屯堡文化中的耀眼光点—安顺地戏及其面具制作技艺的田野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09).
[11] 顾朴光,吴秋林.贵州少数民族面具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12]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3] 【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 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14] 【德】格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5]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6]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17] 顾朴光,吴秋林.贵州少数民族面具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18] 吴秋林.图像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务川仡佬族傩面山王[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