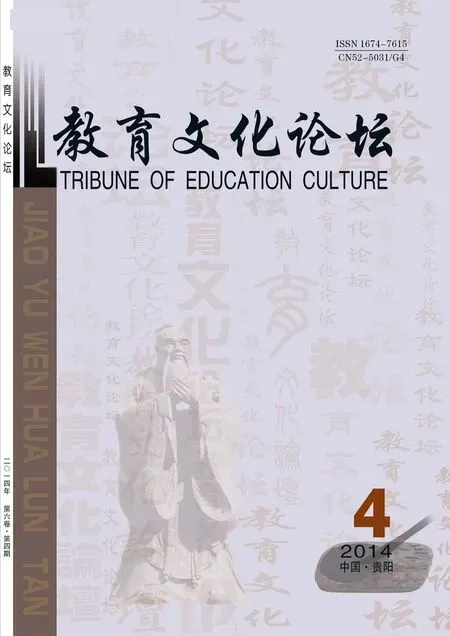傩堂戏的经济成分透析
2014-08-06许钢伟
许钢伟
(贵州师范大学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一
就笔者目前所见资料,“傩堂戏”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湖南省艺术研究1982年编辑的《湖南戏曲传统剧本·傩堂戏专辑(师道戏)》和《湖南傩堂戏资料汇编》。其实,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中,傩堂戏有还傩愿、冲傩、还愿、跳神、跳端公、舡(扛)神、打锣鼓等多种称谓。
根据各地文献记载和实地参与观察,将傩堂戏界定为:一种以掌坛师为首的巫师坛班在事主家进行的消灾祈福的祭祀活动,它以冲傩还愿为主要存在形态,以傩公傩母为标志神灵,以歌舞娱神、符咒驱鬼为表演形式,在祭祀过程中伴有面具戏表演。
需要指出的是,说傩堂戏是傩戏没问题,反之则不妥,因为傩堂戏只是傩戏的一种。以此说来,凡属于傩戏具有的特点,都应适合于傩堂戏;而傩堂戏具有的特点,则未必适合于傩戏。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研究者在研究傩戏时,所论述的傩戏包括傩堂戏在内,但所下的结论却并不符合傩堂戏的实际情况。
二
王廷信在“仪式戏剧”概念基础上提出“祭仪剧”这一概念,并在论述祭仪剧的民俗性特征时,举了贵州德江县傩堂戏的例子。然而,他在论述祭仪剧的自娱性这一特点时说:“祭仪剧与其说是演给人看,还不如说是自己演着玩儿。这种戏剧艺人并没有完全职业化,也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下层民众借着祭祀鬼神、驱凶纳福的仪式进行自娱的一种方式。”[1]若依王先生的这种论断,则祭仪剧不以营利为目的;傩堂戏属于祭仪剧,那么傩堂戏自然也“不以营利为目的”了。但这并不符合傩堂戏的实际情况。
孙文辉在论述戏剧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时指出:“戏剧进入市场之后,戏剧艺术就分化为两种本质相同、而性质有所不同的戏剧类型——即市场戏剧和礼仪戏剧。礼仪戏剧属于‘祭祀戏剧’范畴。当然,祭祀戏剧不是指与迷信相关联的那种戏剧活动,而是一种广义上的、与政治或宗教(即与庆祝、纪念、誓师、酬谢、宣传等等)有关联的戏剧活动。”[2]又说“戏剧进入市场,不是向市场提供一种商品,而是为消费者提供一种服务。市场戏剧的演出(即商业性演出),属于服务产业,即第三产业。而祭祀戏剧不在其列。”[3]按照孙先生的这种看法,祭祀戏剧不属于“商业性演出”的市场戏剧,而是“一条自戏剧发生以来、从古到今不曾间断的历史文化长链,它包括原始戏剧和礼仪戏剧两种既有着内在联系、又有功能差异的戏剧形态。”[4]并且他认为“由于祭祀戏剧与市场毫无瓜葛,因此,它对于市场经济中的风险和利益诱惑,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市场不可能淘汰祭祀戏剧,祭祀戏剧与人类共存亡。” “作为祭祀戏剧的傩戏,千百年来几乎一仍旧贯”。[5]按照他的这种说法,作为祭祀戏剧的傩戏也与市场无关,市场自然也不可能淘汰傩戏。若真如他所言,则傩戏的传承不会面临危机。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窃以为,这种对祭祀戏剧的论断过于武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孙氏没有认识到祭祀戏剧中其实存在与市场有联系的傩戏类型,比如傩堂戏。
黄竹三在论述古代宗教祭祀戏剧时将傩戏作为其中的一类,认为“傩祭中所演的戏剧是为傩戏,他们都与禳灾逐疫有关,和一般赛社戏剧主要为了颂扬神灵是有区别的。比如贵州德江县的傩堂戏、河北武安市的《捉黄鬼》、山西雁北的《斩旱魃》。”[6]客观地说,对傩戏的这种认识并无不妥。但是他说“宗教祭祀戏剧除少数由乐户专业演出外,绝大部分有民众参与扮演。演出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借以自娱”,[7]就值得商榷了。很明显,黄先生的认识和前述王廷信的观点是一样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解,傩堂戏演出自然也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袁琛和[日本]诹访春雄在一篇探讨中国的傩与日本的能二者关系的文章中,制作了一份对比中日两国农村中的戏剧与城市中的戏剧的表格[8],如下:

农村(地方)城市(中央)中国傩堂戏、傩公戏等(傩)的衍生物京剧及越剧等地方戏曲日本神乐、田乐等能、歌舞伎等受众相对固定(村民)相对疏离演出时间时间固定时间非固定商业性免费收费
表格对比的最后一项是戏剧的商业性,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傩堂戏、傩公戏等傩的衍生物,以及日本的神乐、田乐等,都是在固定时间免费向相对固定的受众——村民表演的;而中国城市中的京剧、及越剧等地方戏曲,以及日本的能、歌舞伎等,则是面向相对疏离的受众收费表演的。
日本城市与农村中的戏剧演出情况笔者不太了解,但就中国的傩堂戏来说,上述认识有失偏颇。因为傩堂戏对观众免费,并不等于傩堂戏真的就是免费的演出。举办傩堂戏的主人家是要为傩堂戏付费的。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连观赏傩堂戏的亲友也要出钱,从《增修仁怀厅志》及《辰州府志》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上述几位研究者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包括傩堂戏在内的傩戏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但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傩堂戏的实际情况。导致这种认识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研究者在强调宗教性、祭祀性、仪式性等傩戏的共性时,忽视了作为傩戏之一种的傩堂戏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傩堂戏不同于其他傩戏类型,它包含着浓重的经济成分。
三
其实,也并非没有研究者意识到傩堂戏的经济成分。胡健国主编的《傩堂戏志》中,谈及傩堂戏活动的机构时,曾指出掌坛师作为傩坛负责人,集人事权和经济权于一身[9],可惜未能深究。李怀荪在对湘西傩堂戏的调查中,也注意到傩堂戏演出组织及其经济分配形式:
湘西一带称巫师为“老师”,称少数民族的巫师为“土老师”、“苗老师”。几乎所有的“老师”,同时又是傩堂戏艺人。他们亦巫亦艺的组织称为“堂子”或“坛门”。每个坛门都有掌坛师,由当地有声望的巫师担任。他需拥有行巫所用的法器,又有扮演傩堂戏所用的行箱;他主持巫事,又是傩堂戏演唱的组织者。其余的巫师,多是与他同一坛门,且有着师承关系的长辈、同辈或晚辈。掌坛师掌管着坛门的人事权和经济权。坛门的经济分配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掌坛师雇请,二是视收入情况,实行按股分账。[10]
张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不应当将傩堂戏神秘化,而应当从经济原因加以研究:
实际上,傩戏是出现很晚的剧种,比目连戏晚得多,是受了目连戏的影响才有的。这种地方巫教很盛行,过去没有戏曲的时候,做法事的师公就神神叨叨的,像踩火链、上刀梯等,我小时候看过,的确是烧红的砖上走的。但光这样不行,要搞好几天,不得不演戏,傩堂戏就应运而生。这种情况在南方大概很普遍,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把傩戏神秘化了,我是不赞成把它神秘化的,应当从经济原因加以研究。[11]
张庚认为傩堂戏是做法事的师公受到戏曲的影响才产生的,并且不赞成把傩堂戏神秘化,主张应从经济原因加以研究。这种对傩堂戏的经济成分的认识无疑是敏锐的。可惜的是,这一看法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和足够的重视。
由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王秋桂主持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涉及大陆多个省份的傩舞、傩戏调查,出版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其中,个别调查报告对傩堂戏的经济成分也有所反映。先看贵州岑巩县的一个例子:
周良忠坛班是一个祖祖辈辈相传下来的祖坛,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掌坛师,属江西玉皇派,自称周法兵是教派的创始人。周良忠之父周乾坤做掌坛师时,周氏祖坛香火很旺。据黄贵华回忆,周父行傩几乎成了专职,不事农活,还有钱吃鸦片。一九三三年大有乡冲傩,一共还二十一堂愿脚,仅大米就得三千多斤,鸡和其他利市不计其数,就够吃一年了。[12]
可见,当时参与“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的调查者也注意到了傩堂戏的经济成分,但因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仪式,所以对傩堂戏的经济成分只是点到而已,未能给予详述。
其实,关于傩堂戏的经济成分,古代相关的文献材料早有记载。先看乾隆湖南《辰州府志》:
疾病服药之外,惟听命于巫。幸而愈,则巫之功;不愈,则医之过。…… 又三五岁一祀钱神,其祭以小瓦罐插六七寸竹管于内,用五色绸条十余层裹于管头,置于正寝,割牲延巫。或一日或三日,各曰还傩愿,唱孟姜女戏。亲友来观者,以钱掷赏,名曰歌钱。其曲最为鄙俚。每一会费至百余金,亲友所掷,亦积至数十金。巫人以为利。薮厅邑中不为所愚者鲜矣。[13]
再看嘉庆贵州《黄平州志》:
苗巫曰鬼师,汉巫曰端公。鬼师鸡狗之属,间有用牛,汉人多效之,但不用牛耳。端公用猪、羊、鸡、鸭,每费八九两不等,名曰冲锣,跳舞叫号,语鲜伦次。信者殊多,习俗移人,贤者不免。[14]
傩堂戏作为获利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从事傩堂戏活动的巫师不但逐“利”,并且还巧立名目,增加收入。且看光绪贵州《增修仁怀厅志》的记载:
凡年终腊月庚申日,民间每庆坛神,必杀猪,招巫跳舞歌唱,彻夜不息。亲友贺者亦甚夥。盖欲观其跳唱,亦且得以燕饮也。巫装女样如戏子中旦脚,向贺客歌唱酌酒,必赏以钱。又有所谓打阴兵者,以小刀穿手肚中,向客索赏。又有所谓坐九州者,主人于地下摆设肴馔,请同贺者围坐,巫执壶酌酒,口中歌唱,亦求赏钱。将圆满之时,巫师以小刀砍其额出血,滴于坛旗上,谓之砍洪山,亦必向主人及客索赏。[15]
巫师增加各种表演项目,主要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赏钱,即“巫人以为利”。他们的“苦心”经营,也确实换来了傩堂戏演出的不菲收入。无论是“每费八九两不等”,还是“会费百余金”,以及亲友所掷的“数十金”,最后都落入巫人囊中。并且从“信者殊多”及“薮厅邑中不为所愚者鲜矣”来看,当时傩堂戏还是很有市场的。这种情况并非黄州独有,前引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在论述了庆坛的情况后说到:“道光初年,此风尤甚。”[16]由此短短八个字,我们不难想见当时仁怀地区庆坛活动的频繁。今天为人所熟知的傩堂戏集中地——黔东北地区,傩堂戏同样活动频繁。试看民国时期《沿河县志》的记载:
男巫曰端公。凡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属端公诅焉,谓之跳端公。跳一日者,谓之跳神;三日者,谓之打太保;五日至七日者,谓之大傩。城乡均染此习,冬季则无时不有。胡端《禁端公论》谓:“黔蜀之地,风教之至恶者,莫如端公,不悉禁,必为大害。”是亦宜禁也。[17]
“城乡均染此习”说明傩堂戏受众广泛,普及面广;“冬季则无时不有”足见傩堂戏演出频繁,市场旺盛。而这也正是修志者深深认同胡端“黔蜀之地,风教之至恶者,莫如端公,不悉禁,必为大害”之论且呼吁“是亦宜禁也”的原因所在。
与黔东北毗邻的湖南湘西地区,傩堂戏的情况与黔东北相似。石启贵对湘西地区苗族的实地调查也为我们描述了当地傩堂戏的市场情况:
还傩愿,苗谓“撬弄”(qaod nongx)。傩神是普通之代名词,并非神号。……秋冬祭之独盛,春或有之,夏时极少。小村落,至少年还二三堂,大村落,至少年还七八堂,或十余堂亦不等。在社会上,几乎造成还傩愿之一种风俗。有因病痛而还者,有因求嗣而还者,有因生育而还者,有因发财升官而还者。其情形故属不同,其耗费实属同样。有单愿双愿之别,单愿者需费无多,双愿需款甚钜,单愿猪羊各一,双愿猪羊各二,鸡鱼三牲肉粑香米亦同。[18]
傩堂戏坛班的活动范围,多以掌坛师所在村落为中心,辐射周围的一些村落。按照石启贵先生的描述,“小村落,至少年还二三堂,大村落,至少年还七八堂,或十余堂亦不等。”,若以此计算,则一个坛班活动范围内的村落加起来,每年至少不下几十堂。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湘西地区的傩堂戏市场的繁荣景象。
另外,从某些地方傩堂戏从业者的传承情况也可看出傩堂戏曾经很有市场。清道光《遵义府志》载:“闻昔数十年,大巫多有传授,迎者极恭敬,礼谢亦丰。今其教衰且贱,业者糊口而已。”[19]由此来看,至少在修《遵义府志》之前的数十年,在遵义地区从事傩堂戏演出的“大巫”不仅受人尊敬,而且收入不菲,即所谓的“迎者极恭敬,礼谢亦丰”。而这恰恰是“大巫多有传授”的原因所在。另外,该志中还说“今民间或疾或祟,即招巫祈塞驱逐之,曰禳傩。其傩必以夜,至冬为盛。盖先时因事许愿,故报塞多在岁晚。谚曰:三黄九水腊端公。黄,黄牯,水,水牛,皆言其喜走时也。”[20]无论是“至冬为盛”,还是“腊端公”,除了表明傩堂戏活动时间集中在冬季外,还说明到了冬季,端公们接的活儿特别多,“生意”特别好。
旺盛的市场,给从事傩堂戏演出的掌坛师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其中的佼佼者甚至由农民变成了富甲一方的地主。笔者在贵州省江口县民和乡凯文下寨调查时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据掌坛师樊志友、樊绍权两兄弟介绍,他家是祖坛,在祖父樊德祯(法名樊法斌,生于1909年)掌坛时,坛门最为兴旺:
就是他做的很多(樊绍权),他做发财了,好多人来请他,做不完了就喊徒弟们来帮做(樊志友),日子由他定。最多的时候一个日子有四个地方同时做,别人去做,用的都是他的法名。因为假如你来找我,你是信任我,所以哪怕不是他本人去,也打他的法名(樊绍权)。隔得近的,他还是要跑过去看一下(樊志友)。这个还愿主要是上熟,是最主要的法事,一般由他自己做(樊绍权)*资料提供人:樊绍权、樊志友,时间:2012年7月30日,地点:江口县民和乡凯文下寨樊绍权家。。
以前我家是地主,坝上田谷子每年都有六七百挑,请常年(方言,指长工)都请到十多个。我公又会讲会说,比他们显很了(太富),才三十几岁就被土匪杀了。我太(曾祖父)和公(祖父)的时候家里是很兴盛的。*资料提供人:樊志友,时间:2012年7月31日,地点:江口县民和乡凯文下寨樊志友家。
樊氏祖坛在樊法斌掌坛时靠傩堂戏使樊家成为当地的地主,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可谓掌坛师中的富有者。这种掌坛师靠行傩提高了生活水平的例子,不独出现在黔东北。有研究者在鄂西南地区调查后,也指出了这种情况:
巫师们在当地社会中地位十分特殊。其一、他们是当时民间唯一的专业文化阶层。现在的统计多半说是业余从事,这完全是土改的原因。当时登记成专业就成了‘职业迷信者’,就丧失了分田的权利。所以乐于等同于只办丧事的佛、道班子和响器班子。据我们调查,凡坛门较旺的巫师,基本上不从事生产劳动。[21]
湘西的情况,跟黔东北和鄂西南差不多:
通过抛牌过印,新坛弟子成为一名可以单独行傩的正式巫师。此后,行傩的所得,便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旧时,在湘西南民间,巫傩是一种为乡民所羡慕的职业。道艺高超、香火旺盛的巫师,常有以此项收入购置田产而成为小康者。即使是道艺平平的巫师,他的行傩所得也足以养家糊口。[22]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民间为什么会有“发财赛神”[23]的谚语了。正是由于掌坛师靠着冲傩还愿改善了生活,甚至成为富裕人家,使得这一行业在这一地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傩堂戏生意好,操此业的掌坛师们的收入自然就多,并且他们希望他们的这种好光景能够一直保持下去。这一点在傩坛请职仪式中吃分家饭时授法师傅赐封给徒弟的话里可以看出:
整个传法事项完毕,摆上酒、肉、菜、饭,学法弟子与参加传法的众土老师共同吃“分家饭”。授法师将第一杯酒喝掉一半,将剩下的半杯亲手递给学法弟子,赐封说:“你吃了这杯酒,法门长久开,钱米长久有。”授法师又用筷子挟起一块肉,咬一口,然后递给学法弟子,赐封说:“你吃了这块肉,神门大开师门旺,兵马不停走十方。坛旺人旺师门旺,了愿撤愿勾良愿。”[24]
“钱米长久有”和“坛旺人旺师门旺”,既是授法师对徒弟另立新坛的祝福,也是授法师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坛门的良好祝愿。傩堂戏从业者可以说从学习傩堂戏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奔“利”而来的。巫师以傩堂戏为增加收入的手段,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李岚20世纪90年代在黔东北地区德江县对傩堂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她指出:“虽然现代傩堂戏的演员都是不脱产的农民,但他们的表演是按劳取酬的。”[25]笔者在贵州省德江县进行傩堂戏传承的调查时,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笔者2012年、2014年田野调查时参与了六次傩事活动,得到了两组傩班人数、收入以及分配的数据。
2012年的数据:
2012年12月20-22日,张春江坛班为德江县潮砥镇关茶村皂角堆组村民张连彪的儿子张铭过关,进出三天,报酬为3000元。此次过关,除了张春江、杨秀辉和安明胜三位掌坛师外,还有一位神婆,一位花灯爱好者,共五人,每人分得600元。
2012年12月23-25日,安永柏坛班为德江县共和乡上坪村张仙界组村民杨光齐的小孩过关、岳母还愿,进出三天,报酬3600元。此次过关还愿,除了安永柏、张玉文两位掌坛师外,还有徒弟三人,还有佛、道场师傅两人,一共七人。除去返还给过关小孩的100元,坛班每人分得500元。
2012年12月25-26日,周权友坛班为德江县城水晶湾覃家坳居民安明玉家冲傩,进出两天,报酬2000元。此次还愿,除了周权友、张毓福、杨再富三位掌坛师外,还有两位未请职学徒,一共五人,每人分得400元。*此组数据是笔者2012年12月在德江调查时所得,信息提供人依次为掌坛师张春江、安永柏、周权友。
2014年的数据:
2014年1月3-4日,张毓福坛班为德江县稳坪镇苦竹坝村民张玉权家还傩愿,进出两天,报酬1600元(实付1400元)。此次还傩愿,除了张毓福、张春江、杨贵光三位掌坛师外,还有何智婵、张前锋、张连宣三位学徒,一共6人,每人分得240元(猪头和鸡牲折合为现金)。
2014年1月7-8日李世坤坛班为德江县煎茶镇偏岩村泥池坝组吴风林家过关,进出两天,报酬1200元。此次过关,除了李世坤、苏畅富、苏畅江、晏臣修四位掌坛师外,还有一位赶坛者苏信常,一共5人,每人分得240元。
2014年1月9-10日,安永柏坛班为德江县稳坪镇冯家寨冯大强家还傩愿,进出两天,报酬1740元。此次还傩愿,除了掌坛师安永柏外,还有张华军、安军、安旭飞、安伟四位学徒,一共5人,每人分得350元。*此组数据为笔者2014年1月在德江调查傩堂戏传承时所得,信息提供人依次为掌坛师张毓褔、李世坤、安永柏。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傩坛班成员每人每天的报酬没有低于100元的,多在120-200元之间。可以说,现在德江掌坛师冲傩还愿仍然可以称得上“礼谢亦丰”。而这也许是傩堂戏在德江较好地得到传承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傩堂戏都明显以营利为目的。傩堂戏的经济成分不仅存在,而且表现的很充分。显然,傩戏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傩堂戏的实际情况。因此,傩戏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认识有其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傩戏以营利为目的就是对的。王颖泰认为专事傩文化的巫师将戏曲“歌舞演故事”借鉴到傩仪中,使傩仪具有“酬人”的功能,认为傩戏因此具有了初始的商业性,并且傩戏发展到近代,商业性就更为明确和突出了。*王颖泰.另一种传承:关于黔北傩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几个问题[A].中国·遵义·黔北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G].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260.这种傩戏具有商业性的看法,与王廷信诸先生认为傩戏不以营利为目的刚好相反,其明显的不足是以偏概全,没有考虑到傩戏中确实存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类型(如河北、江西等地区的傩戏)。因此,傩戏与经济(或市场)是否有关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从各种傩戏类型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
[1] 王廷信.祭仪剧——中国民间戏剧的主要形式[J].戏剧,1996(04).
[2] [3][4][5] 孙文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戏剧艺术[J].东方艺术,1996(03).
[6] [7] 黄竹三.古代宗教祭祀戏剧[J].古典文学知识,2002(01).
[8] 袁琛,[日]诹访春雄.中国的傩与日本的能——浅析两者的传承关系及发展轨迹不同之原因[J].江西社会科学,2005(03).
[9] 胡健国.傩堂戏志[R].湖南省戏曲研究所编.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二)[G].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549.
[10] 李怀荪.湘西傩戏调查报告[R].见顾朴光,潘朝霖,柏果成编.中国傩戏调查报告[G].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87.
[11] 张庚.中国戏曲在农村的发展以及它与宗教的关系[R].戏曲研究(第46辑)[G].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3-4.
[12] 杨兰等.贵州省岑巩县注溪乡岑王村老屋基喜傩神调查报告[R].王秋桂主编.民俗曲艺丛书[G].台北:施合郑基金会,1995:40.
[13] 【清】席绍保等修,谢鸣谦、谢鸣盛纂.辰州府志(一)[R].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59册)[G],据清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刻本影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71.
[14] 【清】李台修,王孚镛纂.黄平州志[R].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0册)[G].嘉庆六年刻本,一九六五年贵州省图书馆据道光三十年增补本复制油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73.
[15][16] 【清】崇俊修,王椿纂,王培森校补.增修仁怀厅志[R].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8册)[G].据光绪二十八年刻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2006:240.
[17] 杨化育修,覃梦杜纂.沿河县志[R].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80号)[G].据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338.
[18]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77-478.
[19][20] [清]平翰等修,郑珍、莫友芝纂.遵义府志[R].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2册)[G].据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2006:417.
[21] 雷翔.混融社会中的整合力量——《还坛神》调查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1996(02).
[22] 李怀荪.湘西南的巫师葬丧仪式送亡师[J].民俗曲艺, 1999(18).
[23] 胡翯修、饶燮乾等纂.镇宁县志[R].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4册)[G].据民国三十六年石印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2006:518.
[24] 李华林.德江傩堂戏[G].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559.
[25] 李岚.信仰的再创造——人类学视野中的傩[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