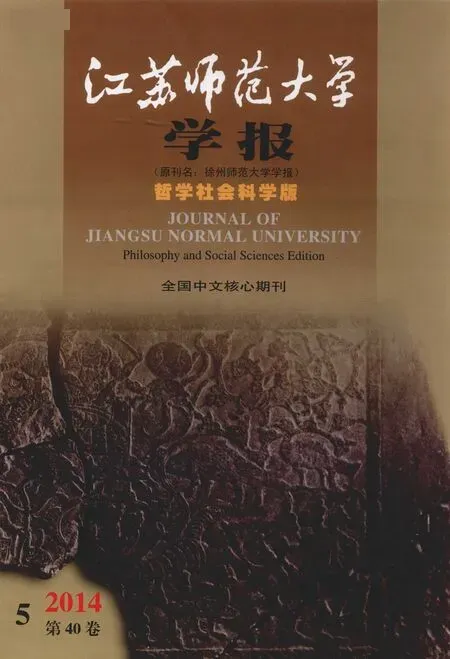中国经学史诠释之方法论考察
——以熊十力“释经法”为中心
2014-04-17聂民玉石永超
聂民玉石永超
(1.保定学院政法系,河北保定 071000;2.河北科技学院汽车工程系,河北保定 071000)
中国经学史诠释之方法论考察
——以熊十力“释经法”为中心
聂民玉1石永超2
(1.保定学院政法系,河北保定 071000;2.河北科技学院汽车工程系,河北保定 071000)
中国经学史;诠释方法;熊十力;“譬喻”;“辨伪”;局限性
我国最早的文化典籍为“六经”,中国哲学史大都以对传统典籍“六经”的诠释而展开。这六部经典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之所以延续不绝,相对于其他文明古国来讲,主要的就是源于不断地对“六经”进行阐释的结果,因此,探讨诠释“六经”的“方法论”尤为重要。自近代以来,学者们不断地借鉴诠释传统经学的“方法论”,以“现代哲学”的眼光和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经学史的材料,使经学史的材料成为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重要学术资源,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先生也不例外,为了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也离不开对“六经”进行诠释,这势必会产生阐释经学的“方法论”的问题。熊先生以“譬喻”和“辨伪”法为武器,开始了对“六经”的阐释,并建构了自己的“道德形上学”体系,因之而成为“现代儒学三圣”。当然,熊先生的“释经法”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的诠释方法均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中国经学史上对“方法论”的诠释
经学史就是关于经学发展的历史。何谓“经学”?清代学者皮锡瑞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辗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手定,得称为经。”[1]从此之后,凡是对“六经”加以注释的,谓之传、记、集解、学或笺等,如:何晏注《论语》、杜预注《春秋》,名为“集解”;蔡扈注《月令》,谓之“章句”;范宁注《谷梁》,谓之“解”;何休注《公羊》,谓之“学”;郑玄遍注群经,多称作“笺”等。这六部经典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之所以延续不绝,相对于其他文明古国来讲,主要的就是源于不断地对“六经”进行阐释的结果,从而形成了经学史。
既然中国文化延续不绝,其主要是源于不断地对“六经”进行阐释的结果,那么就有一个无法回避也必须厘清的问题,那就是诠释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中国哲学家也在不断地探讨阐释经典的方法。读经学史本身,就要和古人进行心灵的对话,不但要揣摩古人的本意,还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可以说,孟子是比较早的一个,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解经方法可谓经典。孟子通过解说《诗经》,提出了“以意逆志”法,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有遗民,靡有孓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2]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诗人的本意,而要通过自己读作品的感受去推测诗人的本意,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诗。如果拘于词句,那么《云汉》这首诗说的“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一个留存”,相信这句话,那就会认为周朝真是一个人也没有了。“以意逆志”的“意”就是指读者的心情或者读者自己的切身体会,而“志”就是作者的思想。这里的“逆”不是“对抗”,其中一层涵义是“顺”,另一层涵义是“心无古今,志在作者,而意在后人,由百世下,迎溯百世曰逆”,也就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遥契,心灵的对话,这种遥契不拘滞于文本的字面涵义,尽管存在“文本的距离”,读者当以自己的体认遥契或推测经典作者的原意。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比兴》中,也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进行了诠释:“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3]。孟子提出的另一种解经方法就是“知人论世”,“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有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有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有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4]。孟子这种所谓“知人论世”的解经方法,强调在历史脉络中解读经典“文本”之意涵,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暗示着,经典作者生存于历史情境之中,因此,作者之意只能在世变的脉络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诠释和同情的了解。也就是说,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不要离开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来研究,即所谓“时代背景分析”的方法。孟子提出的这两种解经方法,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化诠释经典方法的基本路向。
到两汉时期,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所谓今文经学,是指汉代学者根据当时通用的文字即隶书记录下来的儒学经典而阐发的学问,在西汉时期广为流行;所谓古文经学,是指汉代学者根据从民间或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儒学经典而产生的学问,它盛行于东汉时期。其实,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今文经学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来注经,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是“义理之学”,强调“经世致用”。而古文经学则采取“我注六经”的态度,近于史学,侧重于“考据之学”,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所接受,这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它完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第一次转向即“经学的政治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典型的“六经注我”的著作,开始了经学政治化的历程。他提出“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及“性三品”说。到魏晋时期,王弼和郭象等,把经学玄学化了。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等著作,阐述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并提出了“以静制动”和“英雄史观”的思想与“得意忘象”的认识论方法。郭象的《庄子注》,提出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独化论”,继而提出了“安命论”,旨在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尽管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解经方法,但其在无意和有意之间,仍表明作者采取了“六经注我”法。
汉、宋学之别,其实就是两种不同诠释方法的区别,汉学注重的是“文本”层面,注重“文本”的真伪,而宋学关注的是“义理”层面,注重“文本”的“微言大义”。到宋明理学时期,宋明儒学的进路偏重于诠释的主动性,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二程提出了“体贴”二字,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对儒家经典长期琢磨而“体贴”得出的。他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集》外书卷十二)这“体贴”二字,正与程颢《秋日偶成》中所描述的“自得”有异曲同工之妙,“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静观皆自得”中的“自得”二字,与黄俊杰先生所指出的“身心体验”之学相一致,黄俊杰先生说:儒家经典的诠释工作是解释者与经典相互渗透、互为主体的一种解释活动,使经典诠释学成为一种身心体验之学,宋明儒者之解经尤其如此[5]。
除“体贴”以外,“敬”也是宋明理学家解读儒家经典常用的一个方法和态度。何为“敬”?我们可以借鉴徐复观对“敬”字的诠释与解读。他说:“敬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精神的凝敛与集中,可以把因发酵而涨大了的自我,回复到原有的分量;于是先前由涨大了的自我而来的主观成见所结成的薄雾,也自然会随涨大部分的收缩而烟消云散,以浮出自己所研究的客观物件;使自己清明的智性,直接投射于客观对象之上;随工夫的积累,而深入到客观对象之中;即不言科学方法,也常能暗合于科学方法。”[6]朱子读书法之精髓,则非“敬”字莫属,他说:“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7]所以,朱熹反复强调:“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读者对儒家经典的“敬”,可以对作者产生“同情的了解”。何谓“真了解”?我们还是赞同陈寅恪先生所作的判断,他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8]
让哲学问题与现实问题、古代哲学与现代生活“对话”,激活文本中潜在的后现代意识,是近现代儒者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近现代儒者使用诠释学的方法更加主动和自觉。成中英提出了“本体论诠释学”,他认为哲学就是诠释“本体”的哲学,如果哲学不阐释“本体”,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哲学。“鹅湖学派”的傅伟勋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依据层次分为五层,从低到高表述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谓)。有人讲,傅伟勋有过度诠释之嫌,笔者认为这比“诠释不足”要好。首先是“实谓”,即这个“文本”实际上说了什么?这一层实际涵盖了笔者前面所说的点校、训诂、考据、辨伪、辑轶等。要想弄清文本实际上说了什么,就离不开文字训诂等一系列小学功夫与文献学功夫。假如对前面的思想史遗产完全不了解,就没有办法做个案的研究。第二层是“意谓”,即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傅先生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有人讨论说,这才是真正的诠释学的开始。第三层是“蕴谓”,即作者可能要说什么?或他所说的可能蕴涵着什么?第四层是“当谓”,即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最后一层是“必谓”(后来傅先生修改为“创谓”),即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有人批评说,“必谓”(或“创谓”)也应放在诠释学之外。也就是说,属于诠释学之内的只有“意谓”、“蕴谓”和“当谓”。“实谓”是进入诠释学的一个功夫与前提,是前面的准备工作。“意谓”、“蕴谓”和“当谓”才是诠释的过程。“必谓”(或“创谓”)则是今人的解读,应排除在诠释过程之外[9]。
那么,关于傅伟勋先生所说的“实谓”阶段,是否应排除在“诠释学”过程之外呢?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人认为,训诂、考据或者文献学的研讨,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一直到校勘、辨伪与辑佚等,不能算作解释学的内容,但它们肯定是解释学之前即我们研读中国哲学文本之前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笔者比较赞成徐复观先生的观点,他说:“某人的思想固然要通过考证(包括训诂、校勘等)而始能确定;但考证中的判断,也常要凭思想的把握而始能确定。……前后相关的文句,是有思想的脉络在里面的。这即说明考证与义理在研究历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就研究的人来讲,作考证工作,搜集材料,要靠思想去导引;鉴别材料,解释材料,组织材料,都是工作者的思想在操作。而‘思想力’的培养,必须通过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而始能得到锻炼、拓展、提升的机会。所以思想力的培养,是教学与治学上的基本要求。岂有不求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而能培养自己的思想力?岂有没有思想力的人能做考据工作?”[10]
中国哲学界由于受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影响,采取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余英时把“逻辑方法”称为“内在理路”法,程志华把“逻辑方法”称为“内在诠释法”,把“历史方法”称为“外在诠释法”,他认为治哲学史的方法应该是“内在诠释法”,而反对“外在诠释法”。程志华认为,“历史”的方法即“外在诠释”法,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即存在以论本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时势生思潮”的理路,即在“本质”之外去把握“存在”。在思想史上,以“外在诠释”为理路的并不鲜见,如胡适的“剥皮主义”固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亦是如此。比如,侯外庐先生在治思想史时,思考的重点就在于哲学思想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外在诠释”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理路,它用在哲学史研究中难免有“错位”嫌疑。与“外在诠释”的预设相反,“内在诠释”预设内在的理论线索是有规律可循的,时代背景等外在线索最终要通过内在线索起作用,因而认为内在线索是导致概念、义理变迁的决定因素。任何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学术思想都具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意志”,其理论学说的历史进程就是这种“意志”的展开和客观实现。“内在诠释”即“逻辑”的方法,作为一种哲学的理路,它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更为“匹配”。从特征上讲,“内在诠释”是将诠释对象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即利益的语境下“解放”出来,不是“即存在以论本质”,而是“即本质以论本质”,是在“本质”自身的框架内诠释本质的“内在秩序”[11]。
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法应该统一起来。排斥逻辑方法的历史主义方法是经验主义的,排斥历史方法的逻辑方法也是空洞抽象的。笔者不完全同意程志华的方法,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要采取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即“内在诠释”与“外在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其实,哲学史就是哲学,或者哲学就是哲学史。不要把史与哲分割开来,文史哲是一家。在一定程度上,治“史”如果没有“哲”作为灵魂、统帅,那么,治“史”就可能是一些史料的简单堆积。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冯友兰先生那里也有相似的表达。他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归结概括为两种,即“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方法,“照着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历史”的方法,“接着讲”就是“逻辑”的方法即“哲学”的方法。冯友兰先生曾反复声明,他的哲学“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理学、大小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接着’宋明以来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理学讲的”[12]。“阐旧邦以辅新命”,“旧邦”、“新命”之语,出于《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阐旧邦”就得“照着讲”,注重原始文本的原义,注重哲学“史”,也就是说,要“返本”。“接着讲”就是辅“新命”,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开新”。从经学史上来看,解读“六经”的方法有两种,即“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后者是“照着讲”,而前者则是“接着讲”。对待“六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经史结合”即史论结合,也就是说,“照着讲”与“接着讲”相结合的方法,才是正确的释经之方法。
牟宗三先生对“注释”即“诠释”的方法步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将其概括为“三步”。笔者认为,这“三步”可以说是对中国经学史诠释“方法论”的最后之厘清。他说:
至于注释之方向,在以前有汉宋之争,我以为这种争论是无谓的。注释的目的是在恰当的了解,并期望能适应各阶层。因此,专门的、通俗的、深入浅出的注释与解说都有其适当的价值,唯一的条件是不能歪曲与背离。因此,客观地讲,将来注释的新方向大体不外以下三步骤:第一步须通晓章句,此须有训诂校勘的根据;第二步通过语意的恰当了解须能形成一恰当的概念,此须有义理的训练;第三步通过恰当的概念随时能应付新挑战,经由比较抉择疏通新问题,开发义理的新层面,此须有哲学的通识[13]。
笔者认为,牟宗三先生的“三步”法,为我们对“六经”的注释提供了很好的“门径”,其第三步恰好和傅伟勋先生的“创谓”阶段相同。
熊十力先生也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和自觉,他完成了“形而上学化的经学系统”即“本体论”的建构,这一建构需要一套“方法论”的理论支撑。
二、熊十力“释经”的方法论
当然,熊十力先生也不例外,为了建构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理论体系,他也必须对“六经”进行阐释,这就会产生阐释的“方法论”问题。熊先生以“譬喻”和“辨伪”法为武器,开始了其哲学体系的建构。
1.“譬喻”
“譬”字在《论语》中有一处,“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14]。熊十力认为此“譬”字,是使人由譬而启悟,洞达“为仁之方”。熊十力先生汲取了孔子这一方法,在《乾坤衍》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譬喻”说,主要是通过提供不同的语境显示文本的用心,只有理解时“得意忘言”,才能在阐释时运用譬喻式的阐释方式。
熊十力在《乾坤衍》中是这样叙述“譬喻”的,他说:“在孔子之《周易》中便不同于占卜之象,固已改为譬喻矣。譬喻根本不同于占卜之象者,凡哲学界伟大著作,发表其广大深远的义蕴,遇难以直达之义,往往借譬喻以达意。譬喻,固必于意中所欲说明之义有少分相似(少分,犹俗说些微,即只有很少的一点儿相似也)。”[15]熊先生认为,孔子在《周易》中所取之“象”,不同于古占卜家所取之“象”,孔子所取之“象”已有“譬喻”意。为什么采用“譬喻”,他认为,为了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有的可以直抒胸臆,而有的却不能直接表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即为了清楚表达自己的见解,所以不得不借“譬喻以达意”。在使用“譬喻”的方法时,往往借“这个很少一点儿相似”,便可以极大地扩大、创造文本的自由度或者说“释经”的自由空间,便于发表其广大而深远的义蕴。
熊先生认为,当“遇难以直达之义”时,就使用“譬喻”法。熊先生“经学哲学化”的内核是其“体用不二”。为了清楚表达自己的这一“内核”,他反复用“大海水”与“众沤”作譬喻,来说明本体与现象(用)的关系。“本体”是什么,如果直接说“本体”是抽象的、绝待的、无形的、一元的、明觉的、空寂而生化的,不解释人们或许还明白,越解释可能就越糊涂。因此,他为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借用“譬喻”来表达其广大而深远的意蕴。他说:
体与用本不二而究有分,虽分而仍不二,故喻如大海水与众沤。大海水全成众沤,非一一沤各别有自体。故众沤与大海水本不二。然虽不二,而有一一沤相可说,故众沤与大海水毕竟有分。体与用本不二而究有分,义亦犹是。沤相,虽宛尔万殊,而一一沤皆揽大海水为体故,故众沤与大海水仍自不二。体与用虽分而仍不二,义亦犹是。体用义,至难言。如上举大海水与众沤喻,最为方便。学者由此喻,应可悟入。哲学家或只承认有现前变动不居的万象为互相联系之完整体,即计此为实在。如此计者,实只知有现象而不承认现象之有其本体,是犹童稚临洋岸,只见众沤而不知有大海水[16]。
熊十力通过阐述“众沤”与“大海水”的关系,来表达其内核“体用不二”之旨,可谓形象、贴切、生动,仿佛使人真有一种一面在看大海水波浪翻涌,一面在体会其“体用不二”妙处的意境。杜维明教授指出:“熊十力的体用论把体用关系比喻为大海与众沤的动态和整合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范畴的现代诠释,很有启发新思的作用。”[17]
熊十力为了说明实体(本体)如何能够变动、成为功用的,也就是说“实体”变动的“动力”之源来自哪里。他借用“譬喻”说,以“谷种子”为“喻体”来展开形象描述,给人以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实体”竟是如此。他说:
吾人从全体观察,便见得宇宙万有之实体是具有复杂性,绝不是单纯性,实体如果是单纯性,即实体内部本无矛盾,如何得起变动、成功用。犹复当知,宇宙万有动而愈出,此其层出不穷之故,亦不得不推原于宇宙实体内部含载复杂性。吾且举一譬喻,如谷种子的性质不单纯故,遂有生芽、生根干、生枝、生叶、开花、与结成粒子的种种可能。若种子本无多样性,则只能生芽而已,那得有根干枝叶以及花和粒子等发展乎?世人有说种子生了芽,种子便消灭。芽既生,而有根干、有枝叶、有花和粒子等,则皆是芽的发展而已。余谓此说甚误。种子生了芽,种子的形状才消灭,而芽的形状已新生。即此新芽的形状,便是继续过去的种子而以新形出现。种子含藏的多样性,亦隐与新芽相依俱存,故种子不曾消灭也。新芽既生以后,根干和枝叶以及花与粒子先后纷然俱起,亦都是种子本来含有多样性之开发也。谷物既从种子而生,即种子不在谷物自身以外。谷物之类不绝,其种性绝不会消灭。但谷物因生存的需要,有随时、地等缘,而改造其种性之可能。由此譬喻,可悟宇宙实体本来含载复杂性,理不容疑[18]。
既然是“譬喻”,这里就有一个“喻体”问题,在熊先生看来,这个“喻体”就是“象”。我们知道,《易经》所采取的思维是“象”性思维,凡物都有象,以象为中介,通过观象,可以取意。但人们观“象”的角度不同,所取得的意蕴也不同。熊十力先生认为,对《周易》“象”的解释,大概分三期,只有孔子所取之“象”,才开始扫尽术数,而发明“内圣外王”之大道,才具有“譬喻”的意义,这就给熊十力先生的经典诠释以新的合理的自由空间。他说:“《易》之象有三期不同:伏羲观万物而悟阴阳变化,因作八卦直取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欲人因象而悟变化之理也。此为第一期。上古术数家利用八卦为占卜之经典,其设卦问吉凶,则取象渐多矣。此为第二期。孔子作《周易》,始扫尽术数,发明内圣外王之大道。(此为第三期)。”[19]熊先生赞同孔子所采取的“譬喻”方式,变旧文而为新义,这一创造性诠释的意义,大大缓和了甚至化解了创造意识与真实文本之间的紧张性和冲突,给自己阐释《周易》中的哲学“本体论”思想提供了自由而广阔的空间。
《易经》所采取的思维是“象”性思维,“象”性思维是一种非线形的思维方式,而“逻格斯”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注重规范、规定,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解《易》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象数派,一派是义理派。熊十力先生认为,这两派都取象、观象,但取象的意义不同。他说:
汉人治《易经》,皆主象数。占卜家在各卦各爻所取之象,本是对于占侯吉凶者,直举象以启示之。如《乾》卦之初爻居下,即有隐而未见之情状,故取潜龙为其象。将令卜得乾之初爻者,玩此象,敛藏自修,厚养潜力,毋躁进而取败。举此一例,可见各卦各爻每举实物为象,明告占者令其取法。这个取象的意义,绝不可当作譬喻来说。取象,是将卦爻的本旨直接显示出来,教占者仿效。譬喻,则是出语或行文遇到难以表达出的道理,往往用譬喻以助说明。故占卜家之取象,不可作譬喻看[20]。
熊先生认为,只有“义理派”的取象、观象才有“譬喻”的意义,是为了出语或行文遇到难以表达出的道理时所使用,这时的“取象”、“观象”才是“象”性思维方式。
2.“辨伪”
熊十力在《乾坤衍》“自序”中,详细阐述了其书名的由来,并阐发其大义,同时也间接说明了其解经方法。他说:
吾书以《乾坤衍》名,何耶?昔者孔子托于伏羲氏六十四卦而作《周易》,尝曰:“《乾》《坤》,其《易》之蕴耶?”又曰:“《乾》《坤》,其《易》之门耶?”孔子自明其述作之本怀如此。可见《易》道在《乾》《坤》,而后《易经》全部可通也。衍者,推演开扩之谓。引伸而长之,触类而通之,是为衍。余学《易》而识《乾》《坤》,用功在于衍也,故以名吾书。书共二分。第一分,辨伪;(孔子《六经》皆为小儒所改窜、变乱,汉儒传至今日之《五经》,皆非孔子原本。《六经》本一贯,欲辨正《易经》之伪,不得不通《六经》而总辨之。)第二分,广义。(推演、扩充,以弘广《大易》之义也。《易经》称“大”,尊之之辞也。)[21]
“引伸而长之,触类而通之,是为衍”,正是“六经注我”法的通俗解释。
熊先生认为,学者读经,必先立志、责志,“尚志以立基”,否则不可喻圣人之志,读儒家经典,就如同童子诵数而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就是说,如果采取“六经注我”,“我”必须先有“志”。他说:“夫学者必自有其志,而后可读经。何者?六经,圣人之言也。圣人之言,发于其志。学者在由圣人之言,以通其志,非徒诵其言而已。通圣人之志者,必自有其志者也。所以者何?一言乎志,则众人与圣人同也。同而后可以相喻。……故学者如不能立志、责志,则其读经,如童子诵数而已,终不可喻圣人之志。”[22]这与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法相同。当然,在熊先生的语境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众人与圣人同也”,这表明熊先生认为原始经典,今人可以与古人对话,但问题是,今人所处的时代和语境或者说“视域”,已时过境迁,怎样进行对话或者“视域融合”,熊先生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一大缺憾。梁漱溟先生也认为,在读经之前,先有自己的一套思想即先有自己的意见并作主,也就是说先有自己的“意”,他说:“我是先自己有一套思想再来看孔家诸经的,看了孔经,先有自己意见再来看宋明人书的,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23]
为什么要对《六经》进行“辨伪”,熊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说:
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盖始于六国之儒。韩非《显学篇》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云云。据韩非所说而推之,孔子后学分派,各各自称为真孔。由此可知,各派必将孔子之《六经》,各就其所取与所舍者,尽力改窜。发扬其所取之部分,必删削其所舍之部分,以为其自称真孔之实证。如汉人传来之《五经》,几乎完全是小康思想。此乃小康派所改窜之《五经》,实非孔子五经之真本也。又复须知,凡改窜正经者,对于其所舍之部分,不得不留存极少数文句,以隐示己所由改作。至于己所取之部分,则极力铺张,欲以遮掩或淆乱己所欲舍之方面,而使相反之义,在己所改窜之文字中,将失其本义,而与己之所改定者,己不可辨[24]。
熊十力认为,要读懂“六经”,就需要先“辨伪”,如果“伪”不辨,就不能通“六经”“内圣外王”之道。熊十力先生借用韩非的《显学篇》来强调“辨伪”的重要性,原因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已达到顶峰,不可能超过,因此,后学再沿此方向前进必难有理论建树,其后必然会呈现“裂散”格局或出现“拐点”,出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局面,各各自称为真孔、真墨。各派对孔子之《六经》,各就其所取与所舍,尽力改窜,这样“六经”将会失其本义或其本义不明。他说:“余欲说《易》,先以辨伪。伪,不辨,则《易》学真义不可得而明也。然今之辨伪,不专就《易经》之辨,而乃总论六经以辨其伪,何耶?余惟六经以《易》为本,故欲通群经者,不可不通《易》。而欲通《易》者,又不可不通群经。六经发明内圣、外王之道,本来一贯,宜观其会通也。然则辨《易》之伪,何可不总论六经而辨其伪乎!”[25]言外之意,“六经”中所包涵的“内圣外王”之道被小康之儒所淹没,如果不通过对“六经”的“辨伪”,就不能通晓“六经”之大道。
熊先生“辨伪”的一个特点是,借“辨伪”之手段,阐述自己的“微言大义”,“辨伪”其实质就是为了“广义”;换句话说,“辨伪”本身就是“广义”,可见,这仍然是传统的“六经注我”法,目的是对专制主义之毒进行抨击,努力寻找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根芽。先举一例可以看出,就拿对“群龙无首”的解释来看,他说:“群龙者,全人类之道德智慧以至知识才能,皆发展到极盛,是谓群龙。古代以龙为至灵至贵之物,全人类皆圣明,故取譬于群龙也。是时人类皆平等,无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别,故云无首。无首者,无有首长也。”[26]这种诠释虽有“诠释过度”之嫌,但体现了熊先生从传统文化和智慧中开发出现代文明的路向。这也是现代新儒家进行哲学建构的基本方式之一。
三、对中国经学史诠释“方法论”之批导
中国哲学有着异于西方哲学的语言、逻辑、认识理论,有反归约主义、非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之特色,有主观修养与客观认知并举、理智与直觉巧妙结合的优点和长处。一句话,中国传统经学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法。当然,这种理论方法也有明显的缺陷。
中国“经学”的诠释学理论,没有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因此,要想实现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借鉴西方的“诠释学”理论。现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在诠释学上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造,提出了比较系统化、理论化的“诠释学”方法,笔者认为其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他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预设”,即反对施莱尓马赫和狄尔泰提出的“客观的诠释学”观点,提出任何解释都没有纯客观的东西,任何解释都打上了主观的烙印,都加入了读者自己的见解,所以他主张“主观的诠释学”观点。由于西方哲学主流采取科学主义的方法,主张主客二分、对立,认为主体能够完全认识客体(即文本)。科学方法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下定义”,这些在自然科学里可以行得通,但在人文社科领域如“友谊”、“美”、“幸福”、“爱情”等问题上,是不能下定义的,而只能靠个人生命的体验、实践才能体会,此即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意义所在。即,对同一“文本”,由于不同的人欲求不同,或者有不同的“视域”,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也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这是在所难免的。其实,由于时间的流失、岁月的沧桑、时代的变迁,诠释者有着自己特定的视域,或者说都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总是携带有历史的记忆即传统的痕迹,如果否定了传统或丧失了历史记忆就会丧失我们所理解的视域,就找不到理解文本的起点。为此,伽达默尔又提出了第二种诠释经典文本的方法即“视域融合”法。他说:“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27]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视域”就是视力所能看到的范围和界限,那它就是有限的,同时所看到的范围和界限与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有重要关系,也就是人所持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即“视域”不同。每个人的“视域”之所以不同,这与人的学历尤其是社会阅历有关。但同时伽达默尔又认为,“视域”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历史变化中,但它在本质上却是开放的,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封闭视域”,而是一个“开放视域”。目的不是对历史的传承,而是注重表达读者自己的见解,不断实现理解者的个人视域和客观历史视域的融合、互动和交流,即所谓的“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认为,人们在读文本时有两种“视域”,一种是开始阅读时受历史影响的“视域”,另一种是进入文本阅读后受历史影响的“视域”;随着阅读的不断推进,这两种视域会不断地产生张力、冲突,又不断地融合,消解主观性,逐渐地接近客观性,或者说逐渐接近文本的原意。因此,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可以称之为“主观的诠释学”。当然,通过“视域融合”,能否保证文本的“客观性”,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通过诠释如何创造和限定传统。所以,伽达默尔在《真理和方法》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传统并不是由我们继承的现成的事物,而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因为我们解释了传统的进程,并且参与了这一进程,因此我们进一步限定了传统。”[28]伽达默尔认为,传统的东西并非是一宗现成之物,它需要我们理解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传统的进展,是一个需要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过程。一句话,理解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冲突的过程。
熊先生并没有提出自己一套系统的完整的诠释学理论,而是采取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对“六经”进行诠释。主要采取“譬喻”和“辨伪”的方式来“广义”。从大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法,仍然未脱离“六经注我”的窠臼。就拿“譬喻”来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熊先生为了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采取少分相似的“譬喻”法,这扩大了释经的空间和张力,但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这样对“文本”的认识与把握也就存在主观性与相对主义的弊端,“文本”诠释的客观性就无法保证,这就难免会出现“过度诠释”和随意之嫌,这与西方哲学的主流所追求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相一致,获得真理的方法,大相径庭。同时,熊先生也对“六经”进行“辨伪”。当然,“辨伪”的目的是为了“广义”。在整个“辨伪”过程中,熊先生以自己心中预设的“志”或“意”,对“六经”加以取舍和评判,难免有失公允,难免陷入“独断论”的泥淖。这些缺陷,不仅是熊先生一个人的缺憾,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史诠释方法论的不足。当然,尽管熊先生的释经方法论有诸多不足,但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实现其“返本开新”,当然难免有“过度诠释”之嫌。
总之,熊先生的哲学方法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应该汲取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即重逻辑、重分析的“逻各斯”(Logos)精神,即科学精神比较突出。而中国哲学在人生伦理学方面比较发达,“尊德性而道问学”,比较注重“努斯”(N ous)精神,重直觉、重体悟,轻逻辑、轻分析,科学精神比较缺乏。因此,我们应该在保持中国哲学方法论特色的同时,实现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融通,以此来克服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不足,使中国哲学能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1]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流传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页。
[2][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5、251页。
[3]朱自清:《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79页。
[5]黄俊杰:《从儒家经典诠释史观点论解经者的“历史性”及其相关问题》,《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
[6]徐复观:《研究中国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中国广播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
[7]郭齐、尹波点校:《答程正思》,《朱熹集》(第五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0页。
[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9]徐复观:《治古代思想史方法》,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水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10]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52页。
[11]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形上学之可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2页。
[12]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13]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鹅湖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
[1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
[15][18][19][20][22][24][25][26]萧萐父:《熊十力全集》(第七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4、505-506、495、491-492、333、340-341、447、571页。
[16][21]萧萐父:《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704页。
[17]杜维明:《体用论的动态体系及心学非主观主义》,载《中国哲学范畴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
[2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
[27]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0页。
[2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Interpretation the"Methodology"of Chinese Classics——The Investigation which Take Xiong Shili's"Exegetical Study"as the Focus
NIE Min-yu1SHI Yong-chao2
(1.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Law,Baoding University,Baoding 071000,China;
2.Department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He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aoding 071000,China)
Chinese classics;interpretating method;Xiong Shili;metaphor;"discrimination";limitations
The earliest cultural works in China are the"Six Classics",and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is mostly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Six Classics".The six classics have a history of over two thousand years.Compared with other ancient civilizations,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culture is also a special phenomenon.I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stant exploration of the"Six Classics".Therefore,it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explore and interpret the"methodology"of"Six Classics".The methodolog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is borrowed and the vision and method of the modern philosophy are used to re-examine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study materials,mak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become the important academic resources of constructing our own ideological system and building our own philosophy.Xiong Shili is certainly no exception.In order to construct his own philosophy system,he also can not do it with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ix Classics",which must cause the problems abou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thodology".Mr.Xiong takes"metaphor"and"falsifying"as hiSWeapon,starts on the"Six Classics"interpretation,constructs his"moral metaphysics"system and become a"modern Confucian trinity".Nevertheless,Mr.Xiong's"exegetical study"and even the whole exegetical methodology history of China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B2
A
2095-5170(2014)05-0093-08
[责任编辑:李文亚]
2014-05-29
本文系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中国哲学”(2013)项目资助、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熊十力经学思想研究”(H B12Z X002)的阶段性成果。
聂民玉,男,河北唐县人,保定学院政法系教授,哲学博士;石永超,男,河北顺平人,河北科技学院汽车工程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