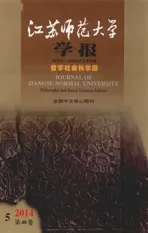《大学》理财之道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启示
2014-11-10刘礼明
刘礼明
(江苏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大学》原出《礼记》之篇,一说为曾子所作,后经程子、朱子编次章句,遂成《四书》之一并位列首章,成为古代官员士子的必读之书和科举取士的官定教科书。笔者以前对《大学》的认知仅囿于程子的开篇阐言:“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1]意即此乃教人修习道德的入门之著。如今潜心涵泳,切己体察,方感悟到《大学》虽篇帙短小,但除阐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深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纲领外,还卓有见识地提出了弥足珍贵的理财之道,不愧孙中山先生所称“中国独有之宝贝”。
一、《大学》:中国理财思想之基源
《大学》既是古代教育理论之精髓,也是儒家治国安邦之纲领。汉代郑玄在《礼记正义》中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代孔颖达认为:“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2]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的曾仕强教授在《中道管理》一书中多处谈到《大学》,称其是迄今最好的管理哲学,尊称“《大学》是所有管理的总纲”[3]。事实上,《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纲领,除教化人修以德行外,还蕴涵着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而道德和经济不仅并行不悖,甚而相融合一。因而,《大学》也被人称之为“中国式管理之本”,其中的财经思想亦可谓中国理财思想之基源。
“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4]意思是说,财货可以聚拢人心,而对于财物的管理和使用要有一个正当的说法,禁止民众不合理的开支,才是最合宜的理财之法。而真正意义上能代表和诠释儒家理财思想的,笔者以为是《大学》。过去,在许多商店和商人府第门联上常常挂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的对联,说明《大学》中论及理财之处甚多,其深邃的理财论断堪称精彩,得到当时人们的极力尊崇,也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如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丘浚认为:“《大学》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5]就连自称“异端学说”的标杆人物、被称为“儒家叛徒”的明代思想家、史学家李贽也对《大学》中精彩的理财论断给予赞许。他在《四书评》一书中曾对《大学》这样评说:“此末后五节总把用人理财合说一番。字字精神,句句警策,最为吃紧,最为详明,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何也?民以食为天,从古圣帝明王无不留心于此者,故知《大学》一书,平天下之底本也。有志者岂可视为举业筌蹄而已耶?”[6]可见《大学》理财思想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大学》作为儒家经典,其经济主张和理财思想多被后儒演绎为“微言大意”而渐趋丰富,其对促进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重要作用亦是不容低估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先生所言:“曾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阶段的儒家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为一般经济思想的开拓奠定了基础。截至十九世纪中两千多年的旧中国,谈经济问题而不以孔丘的经济为指导者,均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其经济思想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7]受儒家理财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卓有见识的理财家,如汉代的孔仅、桑弘羊,唐代的刘晏、杨炎,宋代的王安石、叶适,乃至明清时代的丘浚、张居正、钱维诚等,他们无论在理财的学术思想方面,还是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上,都做出了卓著贡献。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儒家的治国理财思想因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普遍适用的大道,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之一,不仅为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所认可、推崇,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从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The Econo mic Principles of Conf ucius and His School)的问世可见一斑。《孔门理财学》英文直译意思是“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理论”,据说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陈焕章本人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孔门理财学》刚出版不久,在美国最权威的经济理论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学者罗斯(E.Ross)撰写的不乏褒奖的书评文章。之后,英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M.Keynes)也在其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其撰写的书评。可见,《孔门理财学》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理财思想在世界经济论坛中的重要位置。正如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中所作的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不过于诸子学说,尚未详备耳。”[8]由此可见,以《大学》为代表的儒家理财思想,不仅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财经思想发展的起源和重要标志,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大意义。诚如曾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伟大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所言:“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过程,到国、家、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9]基于此,1988年1月,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向世界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0]
二、《大学》理财之道探微
《大学》作为中国原初的理财经典,其所昭示后人的理财之道高度体现了传统儒学的管理思想,其中的精辟论述不仅是古典财经理论的精髓,也可谓是现代经管理论的建构基础。
(一)“三纲八目”——理财者之素养追求
《大学》开宗明义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阐明了从天子到百姓,无论身份贵贱,无分地位高低,都要以修养自身品德作为生存立世之本,通过“三纲八目”内外兼修,实现“内圣外王”之愿景。
“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大基本纲领。所谓“明明德”,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云:“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11]伍庸伯认为“人生是离不开社会的,说‘明明德’,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明明德。”[12]因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自觉地彰明人类禀受于天的光明德行,而作为理财者、管理者则尤应如此。所谓“亲民”,古训“亲”、“新”可通用,程子认为“亲,当作新”,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要求管理者能够鼓己助人,日新其德,不断向善,永远做个新人。“止于至善”之意,朱熹注解为:“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13]意即激励人们不断进行身心修炼直至真善美的至高境界,此乃“明明德”和“亲民”之目标归宿和理想境界,也是管理者的道德追求和最终期许。
“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大条目。此八目并非毫无关联,而是扣合相关,层层递进。正如《大学》所论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4]
关于“格物”、“致知”两德目,《大学》如是论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5]“格物”就是要求人们要注重调查研究,做到亲历其事,亲操其物,在实践中获取真知。“致知”则要求人们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认清事物的本质规律,从而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正认知。
关于“诚意”、“正心”两德目,《大学》主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16]意即告诫警醒世人,凡事要发于内心,表里如一,不矫饰造作,不自欺欺人,应独善其身。作为管理者更要注重道德自律,不断加强意识和行为修养,尤其要在“慎独”上下功夫,不被所谓财货享受蒙蔽了思想,时刻保持意念真诚、心思端正,此乃执政做人之本色也。
关于“修、齐、治、平”,《大学》认为:“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17]说明“齐家”与“修身”之间的重要关系。事实上,一个人只有自身的品德端正,才能教化他人,也才能经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推而广之,一个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不高,如何管理好单位事务?此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8]“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19]号召管理者要以德治国,广施仁政,实现四海升平,天下大治。
“三纲八目”以简练的语言和丰富的内涵揭示了管理者人格修炼的一般过程。“三大纲领”提出了修德向善的目标和方向,“八大条目”给出了修炼的方法和途径,实为管理者修养之大道,对于塑造理财者良好的道德人格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二)“心安理得”——理财决策之心智模式
理财是组织系统中的一项重要管理活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现代管理科学创始人赫·阿·西蒙(H.A.Si mon)认为“管理就是决策”[20]。正确的决策,能够使组织的各项资源发挥出应有效用,从而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错误的决策,则会有损组织管理活力,甚至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故而可见,决策在组织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意义。而组织系统中的决策活动实质就是管理决策者心智活动的过程、结果和表现形式,其思维活动的正确性直接决定了决策活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现实生活中,决策者身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心智活动受到众多的外部干扰而易生偏差,难以在审慎的情境中作出合理的判断与决策。正因如此,有关决策心理学的研究正日趋成为一个热点。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大学》里已经非常精辟地概括了科学决策的心智模式。
《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21]此即《大学》科学决策“心安理得”之六大过程。如下图所示:

科学决策的心智模式
管理者作决策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认知取向、价值追求和处事原则,才能够超越困扰,镇定不乱;只有镇定不乱才能够宁静致远,心不妄动;只有心不妄动才能够随遇而安,安然空明;只有安然空明才能够去私止欲,谋虑周全;只有谋虑周全才能够利益天下,心安理得,从而达到至善之境界。作为理财决策者较之一般人要直面更多的世俗诱惑,如何能够在诱惑和干扰面前做到立场坚定,心不妄动,思虑周详,科学决策,无愧他人和组织的信任与重托,需要理财决策者认真地加以思考。
(三)“絜矩之道”——理财之组织规范
“絜矩之道”是儒家具有代表意义的管理思想之一,《大学》里所言“絜矩之道”既是人们明德处事的行为准则,也是组织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对于规范理财行为同样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絜矩之道”原指建筑上反复测量以求水平精准之法,后被引申喻示为审事度理,推此及彼,公平中正的规范管理之道。正如伍庸伯先生所言:“‘絜’是量度之谓。‘矩’则所以为方也。絜矩之道,盖所以预矫其偏,俾其出于正也。”[22]关于“絜矩之道”,简而言之,就是“上行下效”,“不令而行”之意。“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23]这段话表面意思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忠恕伦理,因其“本于客观普遍不易之理而来,因而便是一原理了”[24]。用之衡量事物,则可使其归于方正;用之处心制事,则万物皆得其自然之所,人人能得以自尽其心;假之用人、理财治理国家,则能以事物发展本质规律为准绳,“智周万物”,“涵养万民”,达到“上下四方,各就其中”的至高管理境界。
(四)“损余补缺”——理财之调控策略
俗语有云:“财者,民生之大命,人情之同欲”。财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关乎百姓的生活和国民的生计,更与组织的生存、政权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故此,有关财经制度的改革及其调控手段的实施,一直为古今中外民众所关注,更成为执政管理者和财经思想家的工作重心和谋虑焦点。
构建一个“小康”、“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追求,而“有余”和“不足”的不公平现象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客观存在。正因如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虽道出百姓心声,但在封建社会却只能成为幻想的“乌托邦”。尽管如此,中国历代高明的统治者、有德行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探索,并竭力倡导和实践着“小康”、“大同”的社会目标。《大学》所提出的“损余补缺”的宏观财经调控措施就折射了儒家“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和对公平和谐社会的美好向往。
《大学》主张管理者为政之道在于彰达公平与正义,明晰“仁与富”、“义与利”之博弈关系,遵行“以仁为本”的财经管理法则,实现“博施于民”的天道仁政。为此,《大学》教诫执政理财者首先要明确“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聚,财散则民散”、“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理财指导原则,做到“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一切施政以人民福祉为先,“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25],就会“德明天下”、“民存政举”。尽管从表面或一时之阈看来,散财于民,可能会使国家或集体利益暂时受损,但《道德经》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万古不易的真理:“天道好还”,其结果正如孔子答冉有所言:“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6]
《大学》除了在国家层面上追求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外,还反对专利垄断和财富的过分集中,主张对为富者财富进行宏观调控。《大学》引用春秋知名贤臣鲁国大夫孟献子的一段论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27]孟献子的这段论述正是《大学》“损余补缺”思想的进一步体现,也是《大学》理财之具体宏观调控手段。
(五)“开源节流”——理财之亘古法则
“开源节流”在经济学上可谓是一个万古不易的理财法则,公认为荀况所首创,语出《荀子·富国篇》:“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28]由此可看出开源节流对于理财治生之重要意义,荀子把它赞誉为治国理财的最高方针。事实上,开源节流一直是先秦诸子较为普遍的经济主张,也是我国治国经世的不朽思想。如《史记·孔子世家》里引述了孔子“政在节财”[29]的治国主张;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30],在《墨子·七患》里提出了“生财密,用之节”[31]的理财思想。难怪胡寄窗教授认为:“荀卿的财政观点几乎全部继承了早期儒家的传统而未敢越雷池一步。”[32]在儒家经典的《大学》里,就深有见地地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开源节流思想。
《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意思是说,创造财富的人要多,消耗财富的要人少;生产时应提高效率,消费时则按时节用。这样,国家的财政就能够恒久充裕。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也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事实上,“生产与消费,形成一个永久的循环”,“随便在什么时候,社会的现实财富之量,比较起来,都是微小的。”[33]因此,衡量国家和组织财富的充足与否不能只看绝对量,而应该从其生产和消费的相对关系上去考量。《大学》的生产决定消费论恰恰说明了这一道理。受此启发,原财政部长金人庆悟出了生财、聚财、用财“三财之道”:“生财为本,聚财同时要考虑生财,要聚之有度,并非收的越多越好,但也不是一味地放水养鱼;同样的,用财也要科学,要讲效益,要有利于生财。而生财是为了更好地聚财、用财”[34]。温家宝当选总理后首次答记者问时,把《大学》的生财之道一字一顿地加以引用。可见,《大学》理财之道已成为当前我国重要的施政纲领之一,也体现了我国发展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意义之所在。
三、《大学》理财之道对现代大学的启示
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大众化的进程中,大学经济活动变得异常复杂,经济形势亦日趋严峻,许多大学财务状况险象环生,甚而岌岌可危。如何科学理财,促进现代大学的财富增值和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人们深思笃行。笔者以为《大学》理财之道对当今之大学具有如下启示:
(一)责任与修养
财力资源是大学组织赖以生存和谋求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依法科学理财,首先有赖于建立一支具有较精专业、较强责任和较高素养的职业化理财队伍。在此方面,《大学》的“三纲八目”历久弥新,不仅指明了当代理财者道德修养的目标和追求,而且指出了涵养身心的方法和路径。大学理财者应按此要求“修己”、“慎独”,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避免违法悖德事件的不幸发生。现代大学还应确立“财为人人所有,人人皆为理财者”的经营理念和职责诉求,铭记《大学》“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意涵和警示,遵循理财决策“心安理得”之心智模式,营造开明、开放、廉洁、高效的财务运行环境,力求通过理财者职业素养的提升,带动大学机构职能的优化和管理水平的改善,以应对新形势下大学跨越式发展对财务工作的巨大挑战。
(二)规范与创新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35]谕示人们原则和规范对于为人处事之重要意义。对于现代大学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而言,“要使这样一个经济体能够有序、健康地运行,没有科学、严密、系统的经济、财务制度是无法实现的”[36]。因此,大学要按照《大学》“絜矩之道”的启示,遵循财政法规、财经规律和理财法则,规范一切经济行为和理财活动,重点完善内部控制和科学决策制度,增强自我约束和规避风险能力,保证大学各项经济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同时,大学还需要极大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勇气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解决发展新机遇所必需的资源不足等新问题,探索建立与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三)效益与公平
现代大学在探索跨越式发展进程中,也把和谐校园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和目标追求,亦即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效益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和必然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时代尤为引人注目的社会价值追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与《大学》“损有余,补不足”的宏观调控思想有着共同主旨。毋庸置疑,市场经济法则催生激活了大学的生产力和潜在效益,但同时也引发了校园贫富悬殊、院系财政分化的不良现象,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业已显现,诸如:利于知识创新的学术生态遭受侵扰,教学和研究受到金钱的腐蚀,教师的忠诚度不断衰减,专业学术人才日见流失,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活力受到束缚,等等。鉴此情况,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教授呼吁“大学在建设性地顺应社会合理需要的同时,要坚决地保护其功能和价值的关键领域”[37]。因此,大学在追求办学效益的同时,如何充分利用财政调控手段,改革内部分配制度,通过资源配置和策略调整,达成大学内部的和谐公平,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时代课题。
(四)生财与节用
《大学》的“生财大道”进一步诠释了“开源节流”的万古理财法则。如今,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由上级财政拨款的大学经费来源模式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财政拨款、学生学费、产业收入、科研经费、社会捐赠、银行贷款等多渠道、多形式的筹资格局。此种境况无疑使“生财”位为大学理财之先。大学应广辟财源,积极挖潜,不断扩增经济实力。可利用其人才、专业、科研等资源优势,在服务社会中增大教育服务收入;加强学校经营性资产的管理,提高校属企业经济效益;依法合理借贷,取得地方政府和金融业的支持;注重对外宣传和联系,获得更多的社会捐赠;调动教职工的科研积极性,争取纵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等等。《大学》“生者众,食者寡;为者疾,用者舒”的理财思想,揭示了“节用”对于现代大学理财之教育意义。“成由俭,败由奢”。大学应从内部管理上下工夫,严法纪、禁奢靡;精简机构,裁撤冗余;节约成本,减少浪费;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增值。如是,大学之财始得恒足,大学之业方得永昌矣!
[1]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页。
[2][11]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之六《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81、981页。
[3]曾仕强:《中道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http://book.qq.co m.
[4][14][15][16][17][19][21][23][25][27]孔子等:《四书五经》,兴华等译,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7、3、6-7、7-8、8-9、10、3、10、11-13、13页。
[5]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6]李贽:《四书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
[7]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0页。
[8]转引自梁婕:《“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
[9]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10]张焱宇:《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3期。
[12][22][24]伍庸伯、严立三著、梁漱溟编:《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8、79、79页。
[13]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页。
[18]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9页。
[20]李同明:《经济管理决策——决策学、经济数学在经济管理决策中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6]古棣、戚文、周英:《孔子批判(下)·〈论语〉译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28]吉林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选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9页。
[29]司马迁著、张大可注释:《史记新注》,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0页。
[30]赵宗乙:《淮南子译注》(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5页。
[31]徐翠兰、王涛译注:《墨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3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9页。
[34]夏祖军:《做大“蛋糕”:财政工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财经报》,2006年12月14日,第1版。
[35]孟轲:《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孟子》,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36]陈伟光:《新形势下提高高校财务管理水平的思考》,《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9期。
[37]Colin Lucas.Knowledge is a matter of values,it poses a moral question.In The University of the 21st Century:Proceedings of the Foru 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entennial of Peking University,May,1998.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268-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