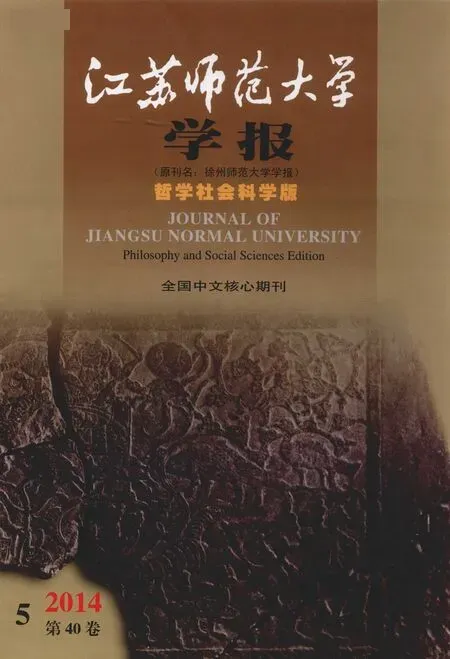类型演变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动向研究
——兼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策略
2014-04-17李永乐
李永乐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类型演变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动向研究
——兼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策略
李永乐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类型演变;认知动向;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世界文化遗产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文物、建筑群和遗址。通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30多年来,逐渐演变出六种世界文化遗产具体或特定的类型:跨境遗产、系列遗产、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文化景观、遗产运河、遗产线路。考察世界文化遗产类型概念与内涵的演变,可以发现,国际遗产界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呈现以下动向:更加关注大空间尺度、整体性的遗产;更加重视跨区域、跨群体交流而形成的遗产;更加重视遗产的活态性与动态性;更加关注人类与自然互动融合形成的遗产。据此,我国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应慎重选择申报类型,巧妙选择申报方式,突出强调特定价值,以提高申报成功率。
当下的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世界遗产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评定与管理的依据和基础性文件。在《公约》和《操作指南》中,明确提出和界定了多种世界文化遗产种类。对世界文化遗产分类以及某些具体类型(如文化景观、遗产线路、历史城镇等),阮仪三[1]、单霁翔[2]、吕舟[3]、俞孔坚[4]、孙华[5]、喻学才[6]、王晶[7]等专家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与分析,但尚缺乏对世界文化遗产类型演变的系统性研究。依据《公约》和《操作指南》[8],对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系统梳理,考察其演变历程,可以探究人类对世界文化遗产认知的动向与发展趋势。
一、世界文化遗产基本类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最高权威性文件,被视为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宪法”。《公约》的第1条,是关于文化遗产的定义,该定义把世界文化遗产规定为三类,在此称之为“基本类型”。第一种是“文物”(m onu ments),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的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第二种是“建筑群”(groups of buildings),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第三种是“遗址”(sites),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二、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的演变
《公约》自颁布之日起一直保持稳定,尚没有颁布过修订版,相反,《操作指南》的修订工作却持续不断。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先后发布了25个版本的《操作指南》,提出过多种世界文化遗产类型及其相关概念。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经历了从《公约》规定的三种基本类型到《操作指南》提出的多种具体或特定类型的演变历程。
1.从“建筑群”到“城市建筑群”、“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的演变
“城市建筑群”(groups of urban buildings)(有学者译为“市内建筑群”)的概念首次出现在1987年《操作指南》中,它是从《公约》“建筑群”基本类型中演变而来的。在2005年《操作指南》中,“城市建筑群”进一步演变为“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historic tow ns and tow n centres)。“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包括三类:第一,现已无人居住但保留了考古证据的城镇;第二,尚有人居住的历史城镇。评估这种城镇的真实性更加困难,保护政策也存在更多问题;第三,20世纪的新城镇。
《操作指南》关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的规定中提到了“历史中心”(historic centres)和“历史地区”(historic areas)的概念,指的是包围在现代城市之中的古代城镇区域,它们是“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类型的具体形式。
2.从“遗址”到“文化景观”的演变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类型是从《公约》规定的“遗址”基本类型演变而来,代表“人类与自然共同的杰作”。1992年12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1994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的“文化景观”首次出现在《操作指南》中,并延续至今。文化景观包括三类:第一,人类刻意设计和创造的景观(包括园林和公园景观);第二,有机演进的景观。此类文化景观一般最初源于社会、经济、行政或宗教的需要,通过与自然环境相联系和相适应而发展成目前的形式;第三,关联性文化景观。
3.从“文化景观”到“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的演变
“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s)是人类建造的水路,“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是人类迁徙、流动与交往形成的路线[9],二者都是从“文化景观”演变而来的遗产类型。1994年,文化遗产专家会议在西班牙召开,讨论了“线路”和文化路线(culturalitineraries)的概念。同年,《操作指南》在阐述文化景观时,指出:长距离线性区域是指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运输和沟通交流网络,是文化景观的一部分。199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遗产运河”的专家会议报告。2005年,“遗产线路”和“遗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特定,正式写入《操作指南》。
4.“跨境遗产”、“系列遗产”类型的演变
1972年《公约》规定的基本类型,一般是指位于一个缔约国境内或独立地理空间的遗产。1984年的《操作指南》规定:位于不同地理空间的一系列文化财产可以作为一项遗产申报,当文化财产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境内时,这些缔约国可以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和“跨境遗产”(transboundary properties)作为世界遗产类型正式出现在《操作指南》中。“跨境遗产”是指位于几个接壤的缔约国境内的遗产,位于一个缔约国境内的现有世界遗产的扩展部分也可以申请成为跨境遗产。“系列遗产”是指包括几个相关组成部分、具有某一地域特征的同类遗产的集合或属于同一历史文化群体的遗产集合。
数十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机构通过了一系列宪章、决议、建议、宣言等,对乡土建筑遗产、历史园林、20世纪遗产、考古遗产、木结构遗产、水下遗产、工业遗产等文化遗产类型进行了阐述和规定。上述遗产类型虽然没有列入《操作指南》,但也同样反映了文化遗产分类逐步细化和具体化、文化遗产保护逐渐专门化和深化的趋势。
三、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动向
《公约》和《操作指南》呈现出的世界文化遗产类型从三种基本类型到六种具体或特定类型(历史城镇与城镇中心、文化景观、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系列遗产、跨境遗产)的演变,反映了国际遗产界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动向。
1.更加关注大空间尺度、整体性的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类型演变历程表明,在大空间尺度内具有整体性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类型的提出,说明世界文化遗产的关注重点,从单体或连接的建筑群转向城镇或区域整体。《操作指南》关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的具体规定中指出,只有当历史中心和历史区域包含大量具有重大意义的古建筑,能够显示一个具有极高价值的城镇的典型特征时,才有资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若干孤立的和无关联的建筑,不应被列入。遗产线路是“线性的文化景观,或者是具有整体性的由若干组成部分构成的文化景观的综合体”。这一概念强调,遗产线路不等于各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线路整体的价值高于各组成元素之和,整体性是该类型遗产的重要特征。
“系列遗产”类型的出现,说明世界文化遗产更加关注属于同一群体或地域的同类遗产的整体性,在系列遗产中,每一处独立的单体遗产都不能代表该系列遗产的整体价值。“跨境遗产”把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境内的遗产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鼓励不同的国家联合申报。在系列遗产和跨境遗产申报中,经常通过扩展项目的方式,实现遗产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保护。
意大利“瓦拉迪那托的晚期巴洛克城镇”(Late Baroque Tow ns of the Val di N oto)遗产,包括8个晚期巴洛克城镇,200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该项目符合“系列提名”的要求,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及伦巴第‘圣山’”(Sacri M onti of Pied m ont and Lo mbardy)遗产包括9座小教堂建筑群,分布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和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8个省。波兰的南部小波兰木制教堂(W ooden Churches of Southern Little Poland)遗产包括6座教堂,分布在波兰东南部6个城镇之中。2003年,两项遗产均作为系列项目申报,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肯定并双双入选。
1987年,英国申报的“哈德恩城墙”(H adrian’SW all)遗产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5年,德国的“北日耳曼—雷蒂亚边界墙”(U pper German-Raetian Limes)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把两者合并为一项跨境遗产:“古罗马帝国边境线”(Frontiers of the Roman E m pire),2008年,位于苏格兰的“安东尼城墙”(A ntonine W all)以扩展项目列入。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曾扩展到三大洲,通过跨境遗产及其扩展项目,古罗马帝国边境线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得以实现。
1999年,印度的“大吉宁喜马拉雅铁路”(Darjeeling Himalayan Railway)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世界遗产大会决定把“尼尔吉里山地铁路”(Nilgiri M ountain Railway)作为扩展项目列入,并重新命名该项遗产为“印度山地铁路”(M ountain Railways of India),2008年,“喀尔喀—西姆拉铁路”(Kalka-Shimla Railway)作为扩展项目列入。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属印度时期,印度共建成了5条类似的山间铁路,至此,其中的3条已经列入“印度山地铁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第四条也正在酝酿申请列入。
2014年6月,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跨境遗产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它经过的路线长度大约5000公里,包括各类共33处遗迹,申报遗产区总面积42 680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234 464公顷。
2.更加重视跨区域、跨群体交流形成的遗产
1980年版《操作指南》中世界文化遗产评选标准第2条规定:“在一段时期内或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从1996年开始,该条标准增加了“体现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内容。世界文化遗产趋向于更加注重跨区域、跨群体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遗产,“遗产运河”与“遗产线路”类型的提出,就体现出这种趋势。
遗产线路是建立在交流的理念之上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交流和对话的精华与集中体现,构成遗产线路的各种有形要素的文化意义来自于跨区域的交流与多维对话。经济方面,运河通过货物、人员运输等途径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社会方面,运河促进了财富和社会、文化成果的再分配,促进了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遗产线路最初的目标或许是单一的,但其后来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管理以及宗教、价值观等不同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世界文化遗产“大吉宁喜马拉雅铁路”,连接了孟加拉的印度教文化和山区的佛教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2000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乳香之路”(Land of Frankincense),是北非著名的乳香贸易线路,通过乳香贸易,从地中海、红海到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等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得以加强。2002年,德国的“中上游莱茵河河谷”(U pper Middle Rhine Valley)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是狭窄河谷中发展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的典范,两千年来,作为欧洲最重要的运输线路之一,它一直在促进着地中海和欧洲北部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2004年,日本“纪伊山地的圣地与参拜道”(Sacred Sites and Pilgrimage Routes in the Kii M ountain Range)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来自中国、朝鲜半岛的佛教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之间相互融合的见证。2005年,“熏香之路—内盖夫的沙漠城镇”(Incense Route-Desert Cities in the Negev)申遗成功,“熏香之路”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间的香料贸易路线,它促进了阿拉伯南部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带动了地区间文化的碰撞与交融。2014年,作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和“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丝绸之路”申遗成功。
3.更加关注遗产的活态性与动态性
文化景观遗产反映了在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及其居住地的演化。在传统生活方式与当今社会的密切交融中,文化景观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既是历史演化的重要物证,自身又处于演变过程之中。文化景观处于不断进化与更新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承继性。1999年成为世界遗产的“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H ortobágy National Park-the Puszta)文化景观,其最重要的价值是霍尔托巴吉草原自由放牧(无围墙)的传统土地利用形式,这种传统家畜牧养方式已经保持了2000多年[10]。201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哥伦比亚咖啡文化景观”(The Coffee Cultural Landscape of Colo m bia),是当地农民为了克服高山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咖啡种植模式,这种独特的坡地和高山生产模式,持续生产着世界上著名的哥伦比亚优质咖啡,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其“是可持续的并且富有生产能力的”。上述两项文化景观遗产,不同于静态景观,它们是至今仍存在和延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有生命力的活态遗产,此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正越来越受到重视。
文化景观遗产往往既包括物质要素,还包括具有很强活态性的非物质要素,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作用。例如2009年申遗成功的我国五台山文化景观,丰富的宗教活动和仪式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活态的非物质文化(宗教仪式与朝拜路线)影响了相关遗址、遗迹的分布,丰富和发展了遗产的环境特征。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五台山是伴随寺庙发展起来的山岳宗教传统文化的杰出见证,其文化传统至今依然生机勃勃[11]。
关于“遗产线路”类型,《操作指南》指出,遗产线路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动态性文化景观,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是遗产线路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关于“遗产运河”类型,《操作指南》强调,运河的特征在于它动态的演变过程,运河的重要性体现在:运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运河曾经对自然景观造成了并将继续造成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运河,如法国“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加拿大“里多运河”(Rideau Canal)、英国“旁特塞斯特引水渠及运河”(Pontcysyllte A queduct and Canal)、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7世纪同心圆型运河区”(Seventeenth-century canal ring area of A msterda m inside the Singelgracht),虽然有的遗产原初功能已经改变,但大都至今仍在使用,是“活”着的遗产。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大运河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依然是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
4.更加关注人类与自然互动融合形成的遗产
1980年版《操作指南》中世界文化遗产评选标准第5条规定:“代表某一文化的传统人类聚落的突出范例。”1994年,该条评选标准添加了“土地利用”的内容,2002年,再次添加了“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海洋利用”的内容。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人类与自然互动融合形成的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类型的出现,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文化景观遗产强调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通常反映人类持续利用土地的特定技术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特定的精神关系,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体现了“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2]。第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指出:“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极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3]文化景观遗产反映了某种特定自然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其遗产价值主要反映在人地关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等方面[14]。近年来,文化景观类型世界遗产数量呈加速增长的态势,1998年,全球仅有12项文化景观世界遗产,200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8项,2010年,为65项,2014年,文化景观世界遗产项目总数已经达到89项。越来越多的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明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产生的杰作。
新西兰“汤加里罗国家公园”(Tongariro National Park)里有活火山、死活山和丰富的生态系统,1990年,该项目以自然遗产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3年,经过重新评估,人们发现地处国家公园中心的群山对毛利人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公园重新以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87年,澳大利亚“乌卢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因其壮观的地质构造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后来,人们发现,公园中的巨石及其周围环境对土著人具有神圣的意义,是当地人的信仰崇拜物。1994年,公园被重新认定为文化景观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2004年,挪威的“维嘎群岛文化景观”(Vegaøyan——T he Vega Archipelago)成为世界遗产。1500年来,在靠近北极圈极地的恶劣环境下,当地海岛居民依靠捕鱼和加工鸭绒毛,创造了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人类对海洋的利用,是海岛居民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独特景观。2012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格朗普雷景观”(Landscape of Grand Pré),是阿卡迪亚人和普兰特人农耕文明发展的见证,反映了北美大西洋沿海区域的欧洲定居者适应自然环境的历程。2013年,位于我国云南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在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中,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完美融合,是人类有效利用社会和环境资源进行土地管理的典范,从精神、生态和视觉上都体现了人类与环境令人惊叹的和谐。通过相互依赖的“天人合一”系统,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体现了对自然、个人和社区的尊重。
四、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策略
近年来,国际上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情日渐高涨,竞争日趋激烈。根据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动向,要提高申报成功率,就要采取恰当的申报策略。
1.慎重选择申报类型
我国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要客观评价遗产自身价值,敏锐捕捉国际遗产界对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选择最恰当的申报类型,以提高申报成功率。五台山起初是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类型,但自然遗产部分的申请遭到否决,经过紧急磋商,我国决定临时调整申报类型,以文化景观类型申报,最终申遗成功。
我国遗产线路、遗产运河类型的世界遗产数量极少,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更加强调平衡性的背景下,此两类遗产的申报形势比较有利。茶马古道、蜀道等可以考虑以遗产线路类型申报,灵渠应该以遗产运河类型申报。在跨境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再加上遗产申报限额因素,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应该优先考虑联合沿线国家以跨境遗产类型申报。
最近10年,文化景观类型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增长很快,成为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宠儿”,但约80%分布在欧洲,亚洲地区数量较少,我国仅有4项。国人自古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景观遗产极为丰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潜力巨大,应该深入挖掘,积极申报。鼓浪屿、瘦西湖与盐商园林、普洱景迈山古茶园、芒康盐井古盐田、坎儿井等应该考虑以文化景观类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有的遗产项目包括多个遗产个体,空间上分布在不同区域,时间上跨越不同朝代,但属于同类遗产的集合或属于同一历史文化群体的遗产集合,应该按照系列遗产类型申报。在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中国明清城墙项目分布在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陕西6个省8个市(县),江南水乡古镇项目分布在江苏、浙江省的10个市(县),中国白酒老作坊项目分布在山西、四川省的8个市(县),土司遗址分布在湖北、湖南、贵州省的4个市(县),侗族村寨分布在湖南、广西、贵州的6个县,苗族村寨分布在贵州省的6个县,以上项目按照系列遗产类型来申报,其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2.巧妙选择申报方式
为了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同时受限于遗产申报数量,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要尽量走“捆绑”申遗或联合申遗的道路,这种“捆绑”或联合,既可以基于空间相近性,也可以基于类型同一性。青城山和都江堰作为一个项目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都是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中国明清城墙、江南水乡古镇、中国白酒老作坊、辽代木构建筑、晋陕古民居、红山文化遗址、闽浙木拱廊桥、土司遗址、侗族村寨、古蜀文明遗址、藏羌碉楼与村寨、苗族村寨等都应该采取“捆绑”申遗的方式。
在扩展项目不占申报名额的情况下,通过扩展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种很好的申报方式。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2000年申遗时,仅包括明显陵、清东陵和清西陵,2003年和2004年,明十三陵、明孝陵和盛京三陵先后作为扩展项目申遗成功。沈阳故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苏州艺圃、耦园、沧浪亭、狮子林和退思园等均是作为扩展项目申遗成功的。今后,我国在申报包含众多遗产点的项目时,可以先选择典型性和代表性强、原真性和完整性完好的部分先行申报,申遗成功后,其他部分再以扩展项目的形式申报。例如江南水乡古镇项目包括甪直、周庄、千灯、锦溪、沙溪、同里、乌镇、西塘、南浔、新市等10个古镇,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对于过于商业化的古镇可以先放一放,待其保护管理状况达到世界遗产标准后,再以扩展项目列入。
3.重点强调特定价值
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系列遗产、跨境遗产等强调遗产的整体性,遗产线路强调遗产促进了不同地区和群体间经济、文化与价值观的交流,遗产运河强调遗产的动态性、活态性以及沟通功能,文化景观则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与融合及其动态演变过程。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应依据不同的遗产类型,深入挖掘、突出强调该种类型的特殊遗产价值。例如,灵渠以遗产运河类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要强调灵渠贯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山区越岭运河,是人类和自然环境互动,从而创造农耕文明河谷文化景观的杰出范例,而且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三坊七巷以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则要突出强调该项目包括大量古建筑(159座),基本保留了唐宋时代福州的城市格局和城镇特征,是“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坎儿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则要强调这种创始于汉代的水利灌溉工程,是生活在干旱荒漠地区的居民适应环境、与大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独特文化景观,而且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
[1]阮仪三、丁援:《价值评估、文化线路和大运河保护》,《中国名城》,2008年第1期。
[2]单霁翔:《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探索》,《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3]吕舟:《第六批国保单位公布后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8日。
[4]俞孔坚:《世界遗产概念挑战中国: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有感》,《中国园林》,2004年第11期。
[5]Sun H ua.W orld Heritage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ed Issues—A Case Study of the‘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 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0,2(5):6954-6961.
[6]喻学才、王健民:《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定义的局限性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7]王晶:《文化线路申报世界遗产的探讨》,《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http://w hc.unesco.org/en/convention/
[9]丁援:《文化线路:有形与无形之间》,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84页。
[10](匈牙利)伽柏·斯拉给:《人类的利用如何增加文化景观的自然遗产价值》,《中国园林》,2012年第8期。
[11]邬东璠、庄优波、杨锐:《五台山文化景观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及其保护探讨》,《风景园林》,2012年第1期。
[1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4页。
[13]单霁翔:《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上)》,《东南文化》,2010年第2期。
[14]陈同滨:《文化景观申遗:现实与可能》,《人民日报》,2010年5月6日。
On the Cognitive Trend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ypes Evolution
LI Yong-le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types evolution;cognitive trends;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nd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ypes evolved from three basic types to six concrete or specific types.By research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ypes and its evolvement,we can find the cognitive trend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First,people pay more focused on the heritag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gration and continuity within large scale field.Second,the heritage which reflects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economy and culture between regions and groups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Third,more and more dynamic and living heritages enter people's field of vision.Fourth,the heritage combining cultural and natural elements attracts more attention.When declaring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we should tak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K917
A
2095-5170(2014)05-0080-06
[责任编辑:刘一兵]
2014-06-1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京杭大运河(江浙段)遗产廊道构建与可持续旅游开发研究”(12 YJCZ H 117)、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阶段性成果。
李永乐,男,山东临沂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