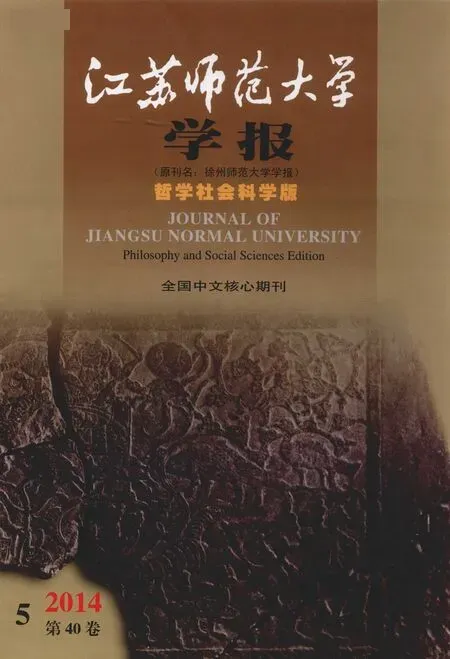清华简《耆夜》成篇问题再论
2014-04-17张国安
张国安
(广西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新出清华简《耆夜》记录了武王八年,戡耆(黎)凯旋,于“文大室”行所谓“饮至礼”的情形。兹录整理者释文如次:
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车酋乘》:“车酋乘既饬,人备(服)余不胄;(虘又)士奋甲,繄民之秀;方臧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后爵乃复。”
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贔贔》:“贔贔戎服,臧武赳赳,毖情(精)谋猷,裕德乃救;王有旨酒,我忧以;既醉又侑,明日勿稻。”
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明(盟),於月又(有)盈缺,岁有臬刂(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
清华简乃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流失香港市场而不明出土来历的战国竹简,总计2300多枚,《耆夜》只是其中之一篇。由于该批竹简的原始出土地始终未明,故竹简《保训》篇公布伊始,便有学者撰文对其真实性加以质疑,甚至提出现代造伪说,其中最有影响且最有力者当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姜广辉教授的4篇文章[2]。姜文发表之后,随即就有学者撰写释疑文章作出了有力回应[3]。纯从技术的角度考虑,清华简作伪确属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具体实施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需要有一支人才结构合理、组织严密、管理有序、有长期合作精神的造假团队。这对现代造假者来说,即便有强烈的动机驱使,但要完全做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质言之,类似于清华简这样大规模、高技术含量的造假,其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虽然清华简来历一时难明,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遭遇各式各样的问题和质疑,但若要做到彻底证伪也同样是不容易的,正如质疑者姜广辉教授本人所说的那样;“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笔者以为,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早期文献在传播过程中,由其传承形态、传播方式、传播目的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传述本身所自然累积的历时性痕迹,不宜用作文献真伪判决的决定因素。
本文立足于商周礼仪嬗变及周代乐政、乐教的角度,对《耆夜》之性质、成篇过程等相关问题加以考辨,结果表明:清华简《耆夜》故事虽非周初史家实录而属后代追述,且其成书又晚,但其歌诗及叙事原型始出当在西周。其原型始出便以乐政、乐教之乐语形态存在并传播,直至春秋战国之际在晋楚演为书篇。《耆夜》述作之义在于,突出周公、毕公在早期饮至礼上的形象,以阐扬周公当初制礼作乐之精神,强化乐政德教。
一、“饮至”礼仪与《耆夜》定性
(一)“饮至”之名与《耆夜》
《耆夜》涉及“饮至”礼。关于“饮至”,《左传》多有记录:
故春搜、夏苗、秋犭尔、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左传》隐公五年)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左传》桓公二年)
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左传·隐公五年》,杨伯峻注云:“凡国君出外,行时必告于宗庙,还时亦必告于宗庙。还时之告,于从者有慰劳,谓之饮至。其有功者书之于策,谓之策勋或书劳。”[4]杨注是以《传》注《传》。襄公十三年《传》:“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杜注云:“书勋劳于策也。桓二年《传》曰:‘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桓十六年《传》又曰:‘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然则还告庙及饮至及书劳三事,偏行一礼则亦书至,悉阙乃不书至。《传》因献子之事以发明凡例。”由杨《注》及杜《注》可知,春秋凡诸侯有大事出入,还必行饮至礼。广义的“饮至”包括告庙、饮至、书劳三事,而狭义的“饮至”实即慰劳表彰出入从者(或戎事凯旋之将士)之燕飨之礼。而见诸《耆夜》文篇的显然属狭义的饮至礼。伏俊琏、冷江山谓“饮至”仪式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赏赐策命,第二阶段是赋诗言志,饮酒祝福”[5]。此乃广而言之,但未及告庙。至于“赋诗言志”一节则基于《耆夜》本篇,结合《左传》、《国语》所记飨宴礼仪推知。
“饮至”之名虽见于《耆夜》及《左传》等传世文献,但西周铭文则多以飨、宴名之。不过李学勤、王宇信认为,“饮至礼”在周原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中都有反映。周原甲骨 H11:132片刻有“王酓秦”一辞,李学勤、王宇信释云:“由铭文看(按:即《方鼎》,《集成》2739),‘酓秦酓’也许是‘饮至’一类庆祝凯旋的礼仪,此礼不见于殷墟卜辞。本辞中的王很可能是周王,不是商王。”[6]周代甲骨文的“”(秦)字,马叙伦早有通“臻”之说,义为以杵臼等容器捣碎稻粱等谷物[7]。陈致以马说为据,又依音转通假原理,断鼎铭中的“‘酓秦’当是‘饮臻’,亦即春秋经传中的‘饮至’”,从而得出“周初已行饮至礼”的结论[8],呼应了李、王之说。以文字训诂而言,“酓秦”读为“饮至”固无不可。但就文法而言,尚需斟酌。我们来看方鼎原文:
铭文讲述的是: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击溃了丰伯和薄姑,班师回朝,于周人宗庙举行祭,并于戊辰日,酓秦酓。因周公赏赐贝百朋,而作此宝鼎。叙事语境显然与文献所述饮至礼合,但“酓秦酓”如读成“饮至饮”,则其句读当为:“饮至,饮。”如此,则原文语读便是:戊辰日行饮至礼,饮酒。饮至礼本来就包括了饮酒,“酓”(饮酒)独字为句,特为强调,固无必要。其语气、语义及语用之于铭文都显不类。本铭文重在记事而不在仪注,断不会有此等文法。“酓秦酓”当依旧释读“饮秦酒”为是[9]。
尽管饮至之名不见于西周金文,但并不意味着西周无“饮至”之礼,饮至礼亦是饮酒之礼,同于飨燕,只是飨燕因礼用有别而有“饮至”之名。就此而言,《耆夜》述及饮至之礼并无不妥,但“饮至”之名的出现,则意味着《耆夜》故事已非史笔实录形态,而是有时空距离的再度叙事。如此,则《耆夜》所记饮酒咏歌之礼仪是渊源早周之历史,还是后世作者凭依春秋史事或《左传》、《国语》所记而作的悬想,就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了。
(二)《耆夜》“饮至”与传世文献所载飨燕之差异
已有学者将《三礼》和《左传》、《国语》所记飨燕之礼与《耆夜》“饮至”礼仪作了比较,两者有较大差异。马楠指出:“简文又云武王奠爵壽(醻、酬)毕公、周公,周公奠爵壽毕公、武王,又秉爵自饮。其礼与《仪礼》所载一献、旅酬、无筭爵皆异。”对其间差异,马楠作出解释:
或饮至之礼,与凡常饮酒礼不合;或武王之初,行礼与《仪礼》不同,难以质言。今强做一解,以作引玉之资。案《左传》昭元年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赵孟爲客”。行一献之后,“穆伯(叔孙豹)赋《鹊巢》,又赋《采蘩》”,《鹊巢》爲赵孟(客)而赋,“言鹊有巢而鸠居之,喻晋君有国,赵孟治之”;《采蘩》为郑伯(主人)而赋,“义取蘩菜薄物,可以荐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与此简文周公所行礼相合。如此,郑伯(主人)兼享赵孟(客)、叔孙豹、曹大夫之礼,当为郑伯献赵孟、赵孟酢郑伯、郑伯酬赵孟,赵孟奠爵不饮。此郑伯赵孟行一献之礼。郑伯与叔孙豹、曹大夫行一献亦然。于是有郑伯奠爵酬赵孟、郑伯奠爵酬叔孙豹之节。行一献礼终,叔孙豹酬赵孟而赋《鹊巢》,酬主人而赋《采蘩》,先赵孟后郑伯者,以宾客爲一坐所尊,故行礼先之。似可以说此简文奠爵酬酒之礼。[10]
其实,所引《左传》赋诗乃于献礼之后,而篇中并无“郑伯酬赵孟,赵孟奠爵不饮”、“奠爵酬酒”之类的仪注之辞。可见,马氏以《左传》郑伯兼享赵孟、叔孙豹、曹大夫之礼比况简文奠爵酬酒之礼,有强添《仪礼》、《左传》之足以适《耆夜》之履的嫌疑。
依丁进《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一文,《耆夜》“饮至”与传世文献不合之处甚多,笔者据其义述之如次:后世饮酒礼“不以公卿为宾主”,而《耆夜》宾主皆为公卿。此《耆夜》不合一也;仪注宾客称谓,春秋中期以前称宾不称客,而《耆夜》既为西周文献则又称“客”,此不合二也;礼宾之位,凡客必在西,而《耆夜》则谓作册逸为“东堂之客”,此不合三也;君主燕礼不酬献主,而《耆夜》武王酬周公,此不合四也;《燕礼》“‘正歌’是第十一个仪节,‘间歌’与‘合乐’是第十四个仪节,在正歌、间歌与合乐仪节进行过程中,饮酒活动是停止的”,而《耆夜》则每酬必作歌,此不合五也;武王诗句“嘉爵速饮,后爵乃从”乃自劝快干此杯之义,而酬酒之义则是酬者先自饮此爵而后再洗斟此爵献于被酬者劝其干杯,两者矛盾,此不合六也;周公作《蟋蟀》之歌现训诫武王口吻,出离“献主”身份,有犯君臣尊卑之礼,此不合七也。由此七者,丁氏得出结论:
就礼学知识看,《耆夜》篇作者的知识背景没有达到清华简整理(者)所估计的战国中后期一般学者的水平,提出《耆夜》为战国时代楚人所作还为时过早,更不用说它为西周实录了。考虑到“清华简”来路不明,《耆夜》的真伪问题仍然有继续讨论的必要。[11]
丁进与马楠一样都注意到了《耆夜》“饮至”礼与传世文献所述礼制之间的差异,但在作出解释时所表现出的学术立场则与马氏迥异。相对而言马氏持论似乎谨慎得多,如同样涉及“东堂”之惑,虽力图融通,但终存其惑:
“东堂”即“东箱”,历来礼家聚讼不已,张惠言折衷前说,以为东序之东,东夹之南。则“东堂之客”当在东序之东,北面。案《聘礼》郑注,公袭于序坫之间(坫在堂东南角),即此东堂之前位。凡袭皆在隐处,若然,史佚在此悬远之位,颇为可疑。试别作一解,《燕礼》孤位在“阼阶西,北面”,君席之左;《聘礼·记》燕聘问之卿,则上介(聘卿之辅)为宾,宾(聘卿)位亦在主国君左,阼阶西,北面,所谓“苟敬”之位。昭二十五年《左传》,叔孙婼(昭子)聘宋,“明日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则昭子之位本在宋公之左,北面,改坐于宋公之右,西面。若然,此位过尊,亦似不合。姑陈义于此,以俟方家。[12]
而丁氏则以“‘东堂之客’在礼制上几乎没有理由出现”一句判语断然结之。其实关于“东堂之客”问题,整理者已说得很明白,“东堂或说即东箱、东厢,历来礼家聚讼不已,张惠言折衷前说,以为东序之东,东夹之南”[13]。可见,“东堂”之实指,传世文献本就含混其词,“历来礼家聚讼不已”,以虚对虚,又何以比较,更不要说得出什么唯一结论了。丁氏因不合而生疑,进而质疑《耆夜》文献真伪[14]。丁文在思维逻辑上的要害在于:若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有不合之处当首先以作伪论处。这显然不是科学历史学的思辨,而是形而上学。马楠的比较解释,虽说相对严谨,但就其试图牵合《耆夜》与传世文献之间缝隙的解释倾向而言,与丁氏思维在逻辑上亦有相似之处,只是其力图证明《耆夜》乃实录的学术立场不同而已。周代礼仪制度,本来就是历史的产物,岂能始终如一。而文献载籍作为书写的历史,各别而言,都只能是实存历史形态及其运动轨迹的碎片式反映。即便“三礼”所载,其间亦有不合,遑论“三礼”与《左传》、《国语》。仅就言志赋诗一节,就不见于“三礼”之仪注。若只能以“三礼”仪注为周礼正义,则“言志赋诗”就得存疑,或判之非周礼之正,或判《左传》、《国语》为伪书,如此,岂不谬哉。
《耆夜》“饮至”礼仪与《三礼》和《左传》、《国语》所记飨燕礼之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差异足以表明:《耆夜》既非后世作者凭依春秋史事或《三礼》、《左传》、《国语》知识而作的悬想,亦非“今人作伪”四字可以了结。
(三)《耆夜》文本分析与历时性考察
前此我们经由“饮至”之名的考察而点出《耆夜》文本属再度叙事而非实录的性质,已有的研究大多证明了这一点。依托文献的历史学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历史叙事本身的历时性考察。若对《耆夜》文本作叙述单元的切分,自然可以呈现许多可供考察判定其时代特征的历时性坐标点。丁进、程浩二氏文中所提及的“宾客问题”就是一个坐标点,由此坐标点,可发现《耆夜》带有春秋中期以后的叙述标记。陈致《清华简所见古饮至礼及〈旨阝夜〉中古佚诗试解》一文对《耆夜》诗篇的四言句式、成语运用及用韵特点的分析,亦是有关《耆夜》叙述的几个重要的历时性坐标点的考察,这几个点之所以能成为历时性的坐标点,是因为源于金文语料的分析归纳可以在此提供相对可靠的时间性参照。“通过对金文韵语与《周颂》诸篇的考察”,陈氏认为“四言成语的大量出现、四言体诗的形成,都应在西周中晚期,共王穆王时期以后”,而《耆夜》“三首古佚诗都是整齐的四言诗,而用韵精整”,故可判断清华简古佚诗及《蟋蟀》一诗不可能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作品。后受日本古屋昭弘教授“铎药两部合韵是战国时期的语音特征”之提醒,作者又进一步深化了先前所得结论:
如果二部合韵的确为战国时代的语音特征,那么简文《蟋蟀》就很有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特别是其第三四两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乃由毛诗中不入韵的“今我不乐”一句变化而出,这也许是清华简《蟋蟀》及其他古佚诗属于战国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至少是经过战国时代的文人加以编辑改订的。[15]
在《耆夜》成篇年代问题上,陈氏论文是通过《耆夜》文本叙述结构形式单元的历时性特征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亦有学者通过对《耆夜》文本的叙述指向即观念内容的历时性特征之分析得出相近的结论。刘光胜、李亚光基于《耆夜》涉及周公与酒文化之关联,而将其与具有同样性质的《尚书·酒诰》加以比较,发现“两篇虽都涉及周公与酒文化的关联,但主旨颇有不同。《尚书·酒浩》阐述的是周公禁酒的举措,清华简《耆夜》目的在于称颂周公康乐毋荒的盛德”。故“《尚书·酒诰》是史官对周公生前思想的真实记录,而清华简《耆夜》则可能是周公去世后尊崇周公思潮的反映”。作者虽然对《耆夜》成篇年代没有给出具体结论,但“《耆夜》则可能是周公去世后尊崇周公思潮的反映”一语,则已明确了其时间坐标及成篇性质,如再向前跨出一步或许便是刘成群在《清华简〈耆夜〉与尊隆文武、周公》一文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刘氏看来:
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儒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战国时期楚地“诗教”文化发达,《耆夜》中的一些诗作则可看成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16]
在《耆夜》成篇年代问题上,目前学界的意见已渐趋一致,但对其成篇过程及叙事性质的认识还是有差异的。依刘成群观点,《耆夜》诗篇属拟《诗》之作,周公作《蟋蟀》乃战国儒士伪托,《耆夜》乃至清华简所有文篇都只能视为战国时的伪托之书。陈致虽然亦以为清华简《蟋蟀》及其他诗篇属于战国时代作品,或者说经过战国时代文人加以编辑改订,但毕竟没有将《耆夜》定为伪托之书篇。如果为伪托,则《耆夜》叙事的史料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但如果不作伪托的定性,则《耆夜》诗篇至少可以视为《诗》之外的古逸诗,而其叙述亦当有史实指向,质而言之,其叙事虽非实录,但必有所本,并非向壁虚构。笔者以为,刘氏之说虽然有其可采之处,但毕竟推测大于实证,故不赞成《耆夜》为伪托之书的定性。我们看到的《耆夜》,其成篇在战国中晚期,清华简的技术鉴定已有科学结论,无须多辨。但构成《耆夜》叙述内容的素材来源,未必不可以追溯至西周晚期甚至更早,或者说《耆夜》叙述是有早期文献原型可据的。凡文本分析所揭示出的后世叙述元素,从逻辑上都可以解释为素材原型在传播过程中历时性元素的自然积淀。
关于构成《耆夜》叙述内容的素材来源,可分史事、礼制、歌诗三个单元分别加以考察。
《耆夜》的叙述框架由武王八年戡耆(黎)史事的记叙构建而成。《尚书》有《西伯戡黎》篇,至于戡黎之西伯究竟为文王还是武王,学术史上本来就有争议。有宋以来,成为著名的学术公案。其答案就有“文王戡黎说”、“武王戡黎说”、“文王、武王各戡耆、黎说”、“阙疑说”、“两个黎(耆)国说”五种之多[17]。《耆夜》简面世以来,戡黎公案又重新成为学者关注焦点。本文在此无须就戡黎公案多加饶舌,虽然我们尚不能像伏俊琏、冷江山那样断然作出由于“简文明确说是武王八年戡黎,则这一学术之争终于可以结束了”的判案,但可以指出:《耆夜》“武王八年戡耆”之记事与《尚书》、《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所具有的纪实性是等价的,《耆夜》叙述所及史事当有传承依据,并非想当然的虚构或史实捏造,武王戡黎的故事原型应该是存在的。
前此已指出,《耆夜》有关“饮至礼”的叙述,涉及到仪注内容的部分与后世飨燕之礼多有不合。但亦有相合的部分,如饮至礼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举行。李学勤说:“‘饮至’意在庆功,如《左传》桓公二年云:‘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解释说,师返,于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并说明‘舍爵’是‘设置酒杯,犹言饮酒’,都与简文相合。”[18]其他如礼设主、客(宾)、介,设司正监饮酒都与后世仪注相合。这里先就不合之处试作解释。
《耆夜》虽有主客(宾)之设,但不记主人献宾,而酬酒歌咏则构成了礼仪的主体。《耆夜》的述作者为何如此叙述,推测其可能性大致有:述作者出于对周礼的无知或如丁进所言礼学修养的缺失;述作者为实施某种表达意图而采取的叙事策略;曲折变相而自然地反映了当初之实情;或二、三种可能性兼而有之。下面逐一加以考察分析。
首先,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清华简的来历尽管不明,但若排除现代作伪的可能性,则其必来于战国时代某位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楚国贵族墓葬,否则不可能随葬如此之多的书类竹简文献。既然以之随葬,则说明这些文献是墓主人生前喜爱并经常阅读的书籍。战国之时,“周礼”之不行于列国,固然是事实。但作为知识、修养和文化身份象征的周礼并没有废绝,否则就不可能有“三礼”的成书与流传,自然也就不会有始皇之世的焚书。揆之常情常理,若这些书籍非主人平生著述,自然其述作者亦非连周礼常识都一无所知的平庸之辈。试想,如此平庸的著述又如何能通过礼学修养绝非平庸的楚国贵族的法眼,更不要说在天国与之相伴直至永远。分析表明,第一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其次,来看第二种可能性。简文全篇不计残缺字共376字,用于叙述史事者仅18字,与仪注有关的101字,剩下257字几乎全用于叙述歌咏诗篇。从内容分布及结构看,叙述史事及仪注只不过为歌咏诗篇的叙述提供一个叙述框架而已。篇中饮酒又只是虚写,并无实际饮酒的文字叙述。饮酒的事实主要是通过诗篇间接反映出来的,直接与饮酒有关的文字只有“夜爵酬”三个字的仪注。下面具体看看简文所叙歌咏诗篇。
武王酬毕公《乐乐旨酒》,依伏俊琏、冷江山语译,大意是:“喜乐的美酒,宴请二公。兄弟相亲相爱,众人和睦同心。你们那样壮盛,那样勇猛,端庄恭敬,肩负着国家的重任。第一杯酒先喝干吧,第二杯、第三杯正等你们来享用。”[19]诗中的描写虚实结合,实者,武王因毕、召二公戡黎一役功勋卓著,设宴慰勉之,劝其畅饮,尽享胜利之喜悦;虚者,武王赞美二公有美好品德,为纲为纪,堪负国家重任。
武王酬周公之《车酋乘》诗,“人备(服)余不胄”、“虘又士奋甲”两句有疑义。黄怀信疑“余不”有误,余不胄当指“甲胄”。又云“奋,举起。甲非奋物,疑当作‘戈’,涉前‘甲士’而误”[20]。黄释前者未安,后者可从。《集释》云:
“人服余不胄”一句不好理解,整理者未作解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以为“不”系衍文。谨按:“不”未必是衍文,该句的理解关键在“服”。
如果将“服”理解作穿戴,那么“不胄”是一个
名词,或可读作“丕胄”,当然,“丕”可能是语
助,“人服余丕胄”相当于“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如果将“服”理解作畏服,那么“不胄”当
指一种行为,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淮
南子·说林训》高注:“服,犹畏。”“人服余不
胄”当指敌人畏服我们周人不戴头盔而冲锋
陷阵的威猛气概。[21]
“人服余不胄”一句之释,当以《集释》为近是。要之,《车酋乘》一诗,主要描写戡黎之役,周军普通将士所表现出来的威猛勇武,谊作酬众将士(众宾)之歌,而用之于周公则难明其义。或当时饮至庆功,作诗咏歌只为劝酒合欢而不必考虑歌诗内容指向。若如此推测,则又与《乐乐旨酒》指实“二公”有不谐。这里尚有一种可能,篇中“周公”为“召公”之误。从歌诗语言、结构与内容看,《乐乐旨酒》、《车酋乘》可视为同一首乐歌的不同乐章。《车酋乘》虽赞美一般将士,但将士的威猛勇武,舍身忘死,英勇杀敌,正可视为担任戡黎战役统帅的毕、召二公“紝仁兄弟,庶民和同”、“穆穆克邦”之美好德行与杰出才能的实际体现。故《车酋乘》既赞美了参加饮至礼之众将士,又可视作《乐乐旨酒》赞颂表彰二公的延续。如此,正可与饮酒礼上毕、召二公宾、介身份相应[22]。
周公酬毕公诗,其意趣与武王诗迥异。“贔贔戎服,臧武赳赳。毖情(精)谋猷,裕德乃救(求)”四句,作为颂美毕公之辞,貌似与武王诗无异,尤其是前面两句。但后两句则很难归为一般颂美,辞中训诫意味扑面,呼之欲出。“毖”,《说文》曰“慎也”。“精”,专一也,《书·大禹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也。谋猷,谋略,此处当指谋划国是。“裕德”,宽大宏厚之德,犹天地生生之德。精一可得其中,得中即后世所谓中庸之德,立于中庸自然合乎天地生生之大德。两句大意为:谨慎精诚,谋划国是,以求合乎天地大德。如此诗句,若用于毕公显然过矣。《贔贔》之诗,作者心思早已越出戡黎功业,远虑之情跃然纸面。歌者何以如此深思远虑,下面的诗句给出了答案。“王有旨酒,我忧以;既醉又侑,明日勿稻。”“”,整理者无释。刘云认为,“”当读为“浮”。“浮”有罚酒的意思。《篇海类编·地理类·水部》:“浮,谓满爵罚之也。”“我忧以浮”的意思是:“我因爲在欢庆的酒宴上面有忧色,而被罚酒。周公在欢庆的酒宴上面有忧色,是其居安思危思想的表现,这一表现完全符合周公在历史上的形象。因为周公被罚酒了,所以他喝高了,所以诗中紧接着又说‘既醉又侑’”[23]。郭永秉以为,“”当联系上博竹书《吴命》6号简“宁心孚攵忧”和楚帛书“思孚攵奠四极”之“孚攵”字来解释。或可释为宁。“王有旨酒,我忧以”,“就是以王的美酒来安宁内心的忧愁之义”[24]。字释有歧义,刘说或近是,但句解似无据,因忧色而被罚酒也不合情理。笔者以为,“浮”此处即超过、过度的意思,属浮之引申义。《书·泰誓》:“惟受罪浮于桀”,孔传:“浮,过。”孔颖达疏云:“物在水上谓之浮,浮者髙之意,故为过也。”诗句大意为:王有美酒,我忧心的是饮酒过度。从“既醉又侑”看,周公之担忧并非无据,亦非多余。因为殷鉴就在目前,故诗篇以“明日勿稻”作结。“稻”,整理者释云:“稻,和《诗经》‘慆’字用法相同。《诗·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黄怀信疑借为“悼”,悲伤之意。黄释合乎诗义。“明日勿悼”,不仅是即景之叹,更是千年忧思。似乎在说,我们周人千万不能乐以忘忧,而应敬慎戒惧以免重蹈殷商覆辙。这与《酒诰》“勿辩乃司民湎于酒”之训诫几乎出于一人之口。
周公酬王诗《明明上帝》,虽开篇便颂扬上帝,但究其实还是颂扬周王之德。上帝明察秋毫,因为周王有馨香之德,才歆享周人祭祀。诗后部分有阙文,但意思尚完整。“月又(有)盈缺,岁有臬刂(歇)行”两句,字面意思无非说天道的运行与变化,但其寓意何在,并非一目了然。黄怀信认为,诗的意思是说“文王功德已经圆满,自当歇行。故作此祝诵,祝其颐养天年,万寿无疆”。为何王不是武王而是文王呢?其理由是:“武王于时年方壮勇,且文王尚在,周公不可能祝其万寿无疆,故此所酬之‘王’当是文王。”[25]复旦读书会则据郭永秉说,谓诗句“反映的大概就是古书中多见的‘天道有常’、‘天道无亲’的观念”[26]。黄释可备一说,但有待商榷的问题也不少,不可从。郭说较优,但“天道有常”的表述未必准确。“月有盈缺”,正是天道无常而变化的表现,“岁有臬刂行”也是如此。“臬刂行”正是人类在恒星背景上看到的岁星运行所表现出来的或赢(顺疾)或缩(慢逆)之无常变化,之所以谓之无常,是因为古人尚未充分把握其赢缩之规律。故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反映了“天道靡常”即“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徳,保厥位”(《书·咸有一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书·蔡仲之命》)的观念[27]。如此理解既可与诗篇颂扬周王德配上帝之义吻合,也与《尚书》诸篇反复申述的德观念及周公德政、德教思想一致。
周公《蟋蟀》诗与《唐风·蟋蟀》有相似之处,关于两者之关系暂不论。要者,简文《蟋蟀》在思想主旨上与其他两首周公诗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兹先引李学勤论述以明之:
简文周公作《蟋蟀》一诗,是在战胜庆功的“饮至”典礼上,大家尽情欢乐正是理所当然,周公只是在诗句中提醒应该“康乐而毋荒”,才符合“良士”的准则。要求周朝廷上下在得胜时保持戒惧,是这篇诗的中心思想。[28]
“康乐而毋荒”正是文献“常厥德”、“敬德”、“庸德”、“中德”、“和德”的具体体现[29]。
综上所述,《耆夜》所述“饮至”礼,歌咏诗篇是其主体。武王歌诗主旨在颂美、乐功、劝酒合欢,而周公歌诗则因饮酒之乐而生忧思,表现出了强烈的道德训诫意味,两者无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结合前此对《耆夜》的历时性分析,可见述作者如此结构全篇,显然意不在叙述当初史事,也不在于介绍饮至礼仪,而在于突出周公的思想形象。突出周公的思想形象,正是述作者主观意图之所在,而并非如刘成群所言宗隆文、武、周公。刘光胜、李亚光谓《耆夜》是周公去世后尊崇周公思潮的反映,庶几得之,但说其“目的在于称颂周公康乐毋荒的盛德”则偏矣。《耆夜》中的周公形象只表现为周公歌诗的思想,而不及周公现实中的德行,故称颂周公康乐毋荒的盛德显然不是述作者的中心意图之所在。那么《耆夜》突出周公的思想形象,其实际的意义又何在呢?待我们考察第三种可能性之后,其意义自然会水落石出。
《耆夜》不记献礼、简化叙事细节、重点介绍咏歌诗篇显然有助于突出周公的思想形象,就此而言,我们自然可以将之视为某种叙述的策略。问题是这样的叙述仅限于策略而毫无史学的意义吗?换言之,《耆夜》的叙述是否也曲折变相而自然地反映了“饮至礼”在其提供的史事框架中的某种实情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情就是,武王戡黎凯旋所举行的“饮至礼”与传世文献的周礼无关。众所周知,周初因于殷礼,何况周人在尚未取商而有天下之时呢。故《耆夜》中的礼仪与后世仪注有诸多不合,纯属正常,恰恰是当初实情之反映,这并不因《耆夜》成篇的早晚而改变。这是从不合的事例得出的结论,那么从公认相合的事例又能发现什么样的实情呢?下面拟通过“夜爵酬”三字仪注及设“司正”两例的分析加以揭示。
后世献礼有“酬”之仪节,《耆夜》虽不记献,但亦有“夜爵酬”仪节。“夜”,整理者的解释是:
夜,古音喻母铎部,在此读为“舍爵”之舍,舍在书母鱼部,可相通假。或说读为《说文》的“”字,音为端母铎部,该字今《书·顾命》作“咤”,训为“奠爵”,与“舍爵”同义。[30]亦有学者不赞成整理者的厘定释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耆夜〉研读札记》一文依裘锡圭先生未刊稿读为“举”,又云:“金文中习见的‘平夜’即‘平舆’,《仪礼·聘礼》:‘一人举爵,献从者,行酬’,‘举爵’与‘酬’连用与简文中的‘夜(举)爵酬’恰可对比。”[31]王宁对裘锡圭、读书会新释有如下评论:
《耆夜》之“夜”,裘锡圭先生读为“举”,夜、举可通假,应该没有问题,在文中也可通读。不过,窃以为如果从其篇名来看,读为“举”似乎还有可商量的余地。整理者读为“舍”,殆即古之“告庙”时“舍爵策勋”,《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战还饮至,舍爵策勋,是一种固定的礼制。《耆夜》如果读为“耆舍”,乃言戡耆战还饮至,舍爵策勋之事,合乎通篇内容,也符合古代礼制。如果篇名读爲“耆举”,“举”为举爵,总觉得无法涵盖全篇内容,而且有不辞之嫌。个人理解是:舍爵策勋为告庙礼制中一项,其具体行为就是参与者互相敬酒称贺,记其功勋。《耆夜》文中每言某人夜爵酬某人,“夜爵”当为舍爵,亦即置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爵中倒满酒;“酬”,《说文》:“醻,献醻,主人进客也”,段玉裁注:“如今俗之劝酒也。”舍爵醻某人就是爵中斟满酒向某人敬酒劝饮。这种礼数至今沿用,在酒桌上常听到的话就是:“我倒满,敬大家一杯”。所以,个人觉得把《耆夜》读为《耆舍》更为合理一些。[32]
王宁的批评不为无据,而且照顾到了篇题,将“夜爵酬”理解为敬酒劝饮也是对的,但其论证尚不够严密。王宁依据的是《左传·桓公二年》“舍爵策勋”仪注,确如王氏所言,舍爵即置爵,但“舍爵策勋”之置爵则是放下酒爵,停止饮酒。桓公二年《注》说得很明白:“爵,饮酒器也。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置爵,并不能理解为“在爵中倒满酒”。“在爵中倒满酒”便是饮酒,而饮酒策勋两事不可并行。可见若依王氏说解,则“夜爵酬某人”难免前后矛盾。当然,舍爵同奠爵,奠爵除理解为置爵外,也可理解为献爵。问题是作为仪注的“献”与“酬”乃献礼的不可同时举行的两个仪节,而篇中“夜爵酬”则是同一的动作行为。以上表明以后世仪注去解“夜爵酬”实难圆融,也许正是出于此一原因,裘锡圭读“夜”为“举”,尽管会遇到王宁所指出的问题。笔者以为,“夜爵”读为“舍爵”并没错,但“酬”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为后世献礼之“酬”。
此姷字转注字,“献酬,主人进客也”非本义。校者依《诗·楚茨·笺》加之,或《字林》文,本训捝矣。《广韵》引《仓颉》“主答客曰酬”,是酬字见《仓颉》,当为正文。然玄应《一切经音义》引《仓颉解诂》“詶,亦酬字,报也”,又引《仓颉》“酬作詶,主答客曰酬”。伦谓据玄应引知《仓颉》有詶无酬,以詶为酬。故《解诂》谓“詶,亦酬字”,又谓“酬作詶也”。或谓《解诂》明言主答客曰酬,而酬字不从言作詶字,则非以詶为酬也。伦谓《广韵》引《仓颉》“客报主人曰酢”,而本书酢是酢浆,客酌主人乃下文醋字义。盖注《仓颉》者以当时通用酬字,故作酬也,非《仓颉》中本作酬酢二字也。[33]
依马氏疏证,古文“有詶无酬,以詶为酬”;醻本义与酬酒无关,乃姷字转注字。《说文》:“姷,耦也。”醻又训为捝,擦拭之义。吴大徵引郘钟“既鬯爵”便用作此义。此或为“偶”义之引申。姷又通作侑,《周礼·膳夫》“以乐侑食”,《古音骈字续编》引作“以乐姷食”[34]。《集韵》:“酭,醻酒也;通作侑。”[35]是醻、酬、姷、侑字均可通用。《仓颉》有詶无酬,以詶为酬,詶疑即酬本字。《说文》:“詶,譸也。从言,州声。”丁福保云:“《说文》无咒字。《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咒、诅下云‘又作祝,《说文》作詶’。案:《说文》作詶者,言部。譸,詶也。譸,詶也。诅,詶也。詶即咒。又作祝者,《大雅》‘侯作侯祝’,《毛传》作祝咒也。”[36]马叙伦谓“詶,诅、呪正字”。故简文“”可厘定为“譸”。“譸”从言字,通詶、酬,其义为以歌永祝颂,姷饮姷食。“夜爵譸”之大致节序为:斟满酒杯置于客人之前、遂祝颂咏歌以劝酒助兴。
《耆夜》提到在饮至礼上吕尚父为司政,监饮酒之事。整理者释云:
《仪礼》的《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四篇皆有“司正”,立司正在行一献之礼、作乐之后,行无筭爵之前。胡匡衷《仪礼释官》:“案《国语》‘晋献公饮大夫酒,令司正实爵’注:‘司正,正宾主之礼者。’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38]
马楠又进一步释礼设司正的意义,“是既使宾主和乐,又使不失仪,《礼记·乡饮酒义》所谓‘和乐而不流’是也”[39]。学界基本上认定《耆夜》司正监饮酒的意义等同于后世《仪礼》司正的职能与意义。如此联系,仅就字面看,应该文理通顺,但如顾及全篇,则难免令人生疑。试想,既已礼设监酒,自然“和乐而不流”,周公又何来“我忧以浮”、“既醉又侑”之叹呢?莫非圣人之忧患意识总易被人想像作杞人忧天或无病呻吟状?《耆夜》作者即便纯粹虚构故事,亦不至于如此不考虑逻辑文理,如此肤浅吧。可见,以礼防饮酒过度未必是简文“监饮酒”之本义。笔者以为,当时背景的饮酒就是合欢,就是“嘉爵速饮,后爵乃从”、“既醉又侑”。故监酒其实是为了罚酒劝饮而设,若今乡俗,主人饮酒待客总要找位有酒量又善言辞的乡亲朋友以为陪客,此人总能找出各种口实劝人多饮直至其醉方休。凡劝饮之言辞,就语用而言,一般都有极强的感染力或心理影响力,令人不得不如此,仿佛咒语一般。《小雅·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序》云:“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可见,周礼完备的时代,亦有越礼而沉湎淫液之时,不要说戡黎凯旋,周礼未备的时代了。“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既然是沉湎淫液的写照,那么“既醉又侑”难道还能被视为彬彬有礼、和乐而不流吗?非也。
据陈致文,《耆夜》记太公师尚父为司政,监饮酒,李学勤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笔者揣测,李氏之觉得有趣,可能不止有趣这么简单,其实在李氏心中,对当时设《仪礼》之司正是有几分疑惑的,只是不愿明确说出自己的疑惑罢了,因为李氏是把《耆夜》中的叙事视为实录的。陈致似乎感觉到了李氏的疑虑,在提及李氏的“有趣说”之后,紧接着便说:
我认为西周金文中也有监饮酒的记述,如宣王时期的膳夫山鼎(《集成》2825,西周晚期):“王曰:山,命女司饮,献人于,用乍宪司贾,毋敢不善。”在这里,所谓献人根据《礼记·少仪》记载,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献上酒醴,肉干和牲畜的一种礼仪。我们可以看到周宣王命令膳夫山在献人礼中,司饮酒之职,并且制定章程,让人遵守。[40]
其实,鼎铭中膳夫山司饮之职即便同于后世饮酒礼中的司正,也不能说明多少问题,更不足以打消李氏可能有的疑惑,因为膳夫山所处的时代毕竟已是西周晚期了。
笔者以为,从《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匪言勿言,匪由勿语”可以反推周礼兴盛时“司正”的礼学意义。当宾客酩酊大醉,司正是要善意批评,婉言提醒的,甚至于有不当言语还要有史记录在案。司正之设的意义在于,即便在无算爵、无算乐的合欢之时亦须有礼有节。如此方有利于培养人之中德,才能做到和乐而不流。尽管如此,仍不意味着殷末周初饮酒礼无司正监饮酒,只是其时司正职能不同罢了。后期司正的职能恰恰是由早期如《耆夜》所述司罚酒劝酒的职能反向超越转化而来的,这种职能的变化见证了周代礼乐制度建设与完善的历史进程。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推论了。《耆夜》的叙述间接曲折地反映了周人早期历史因袭殷商饮酒礼(言礼或燕礼)的实况。早期言礼之“言”,其性质乃祝颂之歌。从武王歌诗与周公歌诗的对比以及周公歌诗的内容中不难看出,周公忧思远虑的缘由以及周公的德观念与德治思想,而此种观念与思想在《尚书》、《周易》中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精髓,指导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实践。叙述者突出周公在早期饮至礼上的思想形象意图在于告诉时人,历史上,周代礼乐制度的建设与周公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一并晓谕时人周公制礼作乐之精神及其深远意义之所在。《耆夜》叙述史实指向性甚为明显,必有原型可据,断非战国士人向壁虚构的伪托之作。《耆夜》叙述的性质及其成篇的时间下限已可明确,但其叙述初始成型及传播的情况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二、毕公事迹与《耆夜》传述者
已有的分析表明,《耆夜》全篇文理顺畅,文本单元之间呼应紧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周公之歌诗主旨一致,且与背景语境高度协调,有力地突出了周公在历史上的思想形象。此外,《耆夜》文本内容还有一点尤为值得关注,这就是文本叙述通过在饮至礼上毕公为客这一醒目的礼位,突出了毕公在伐耆战役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此叙述的《耆夜》,作为非实录的后世追忆之作,显然意在提醒世人莫忘商周之际的一段辉煌历史,这段历史星光灿烂,而毕公正是其中最灿烂的一颗。倘若《耆夜》中的叙述为渊源有自而世代相传的早期历史,则传承这段历史及其中歌诗者为周公或毕公后裔无疑。基于传世文献无有周公作《蟋蟀》之说及《蟋蟀》入《唐风》等史实,我们推测,传承《耆夜》故事及歌诗者为毕公一族的可能性最大。下面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试作推考和说明。
据传世先秦文献,毕公是历文、武、成、康四朝的股肱重臣和元老,在周代的历史上地位显赫。兹根据王朝历史顺序将文献中记载的与毕公有关的主要事迹罗列如下:
文王时期:
及其(文王——引者注)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国语·晋语》)
武王时期:
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伯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逸周书·克殷解》)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史记·魏世家》)
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逸周书·和寤解》)
周公、成王时期: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衞、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也……毕国在长安县西北。”)
(成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顾命》。传: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毕、毛称公,则三公矣。此先后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为之;宗伯第三,彤伯为之;司马第四,毕公领之;司寇第五,卫侯为之;司空第六,毛公领之。召、芮、彤、毕、卫、毛皆国名,入为天子公卿。)
康王时期: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康王之诰》。传:二公为二伯,各率其所掌诸侯,随其方为位。)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古文《毕命》。《书序》云“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周本纪》亦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据以上文献,由终而始回溯,则:康王时期,毕公与召公分别为东伯、西伯;继周公之子君陈之位为太师,领成周之众[41]保厘东郊。此期的毕公位极一时,是其一生中最隆盛的时期。成王时期,为三公六卿,领大司马职,王临终与召公等同为顾命大臣。周公时获封。武王时期参与伐商,克商而封于毕。伐商前与召公一道成为与武王共谋伐商大计者。文王时为文王所重,直追周公、召公之后。综观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重点:一,涉及毕公在文王时的记录最简,而文献材料来源则为《晋语》所载胥臣之所闻。二,武王克商之役,毕公当立功勋,但《克殷》无载,有关重大仪式的记述,毕公亦未在列,可见其地位亦远不如周、召二公突出。而《和寤》记武王图商,特召召公、毕公与谋。其事之于后来克商,意义可想而知,则《克殷》、《和寤》所载显然不一致。《和寤》成篇年代晚于《克殷》,已是学界共识[42]。三,《康王之诰》、《毕命》叙述康王时毕公之职位与《书序》、《周本纪》称“作册毕”,“作册毕公”似有不谐。四,《左传》谓毕公之封始于周公,与《魏世家》获封于武王说异。
以上所述四点相关联,首先可以看出先秦文献载录毕公事迹的分野,文篇大体可断为西周的文献之于成王以前的毕公事迹多缺载,惟《克殷》一篇有载,但毕公形象并不耀眼;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春秋以后文献反而突出了毕公在商周之际、武王克商过程中的显赫地位,而这些文献的材料来源,明显具有传说性质。其中《和寤》云武王“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与《耆夜》饮至礼“以毕公高为客,邵公奭为介”最相符契,稍有异者,二公位次正相颠倒。可见传世文献尊隆毕公莫过于《和寤》,而赋予毕公在周人开国历史上以无比尊荣,光环夺目,耀眼无比,登峰造极的则是《耆夜》。
那么,《耆夜》之外的其他出土文献所载情形又如何呢?
周原甲骨文有“毕公”(H11:45),“毕”(H11:80),何光岳据之认为:“毕公高乃周文王时所封,不是周武王所封,《史记·魏世家》误。”[43]若果如是,则《国语》富辰之语便有了实证。但周原甲骨文的断代不限于文王时期,而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晚期。其中“毕公”、“太保”应属周初及以后甲文[44]。故周原甲骨文,还不能确定毕公高于文王时就受封于毕。然而,《史记·魏世家》说亦未必可坚信。《周本纪》记武王封功臣谋士:“师尚父为首封,封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其中未提及毕公,这也许是太史公“互文”之书法所致。但即便如此,也间接说明毕公于克商一役,功勋不比其他诸公显得卓著。无论如何,《魏世家》所据应属战国魏国史记。其与《左传·禧公二十四年》云周公时受封于毕显然不合。
除甲骨文外,与毕公高有关的尚有同铭的两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史()簋》(《集成》4030,4031)和毕伯鼎、献簋。史簋铭曰:
此外与毕公高受封有关系的还有两件青铜器,一件是毕伯鼎,另一件是献簋(《集成》4205)。毕伯鼎为2007年发掘陕西梁带村北区M502号甲字型大墓时出土的-件有铭铜器,原款识为:
毕(毕)白(伯)克肇乍(作)朕丕显皇且(祖)受命毕(毕)公彝,用追亯(享)于子孙永宝用。[49]
铭中“受命毕公”之受命或与毕公高受封之事有关,但该铭并未提供进一步的有关毕公高的资讯。《献簋》则提供了传世文献失载的重要资讯,其铭云:
惟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尤,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李学勤认为献簋为康王前后器,“献系楷伯之臣,而自称‘身在毕公家’,推想楷伯为毕公别子,分封于楷”,也是楷国的始封之君[50]。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黎城县西关村发掘了一处西周中晚期墓地,出土了一件楷侯作青铜圆壶。高智、张崇宁认为,楷、耆、黎古音相近可通证明了山西黎城遗址就是文献上所说黎国之墓地[51]。清华简《耆夜》面世后,李学勤结合黎城遗址新发现和《耆夜》,对献簋又作了重新解读。周朝建立之后,将毕公之子分封到黎国,“显然是由于毕公是伐黎的主将,功绩最高”。“簋铭的楷(黎)伯是毕公之子,他与成王是同辈兄弟,如果王是康王,那就更低一辈了。铭中云‘楷伯于遘王’,‘于遘’意为往见,口气不甚卑下,可能即出此之故”[52]。李学勤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如此看来,《周本纪》所说武王克商之后的大封功臣谋士,若涉及毕公应该指的是毕公别子的黎国之封,那么《魏世家》“武王伐纣,而高封于毕”的说法就确实有误了。前面既说毕公封于毕始于文王可能性不大,则《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提及的周公成王之封建就值得考虑,也就是说毕公封于毕或与周公有关。但《左传》这条材料亦有可疑之处,因为文中涉及三叔,而三叔之封显然在武王之时。还是孔颖达《正义》说得中肯:
文、武、周公之子孙,为二十六国也。此二十六国,武王克商之后,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毕矣,非是一时封建,非尽周公所为。富辰尽以其事属周公者,以武王克殷,周公为辅,又摄政、制礼成一代大法,虽非悉周公所为,皆是周公之法,故归之于周公耳。昭二十八年《传》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彼言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归功于武王耳,亦非武王之时已建五十五国,其后不复封人也。昭二十六年《传》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九年《传》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则康王之世尚有封国,非独周公时也。且见于经、传者,管叔、蔡叔、霍叔,周公摄政之初以流言见黜,则三叔之国已是武王封矣。《尚书·康诰》之篇,周公营洛之时,始封康叔于卫;《洛诰》之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鲁;《书传》称成王削桐叶为珪,以封唐叔。如此之类,不得为武王封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岂周公自封哉?固当成王即政之后,或至康王之时,始封之耳。
可见,据传世先秦文献实无法确知毕公具体何时得封于毕,但从孔疏“周公之法”的提示中,我们亦隐约可以窥见武王之封与周公以后封建意义之不同。《周本纪》云武王克殷,“封诸侯,班赐宗彝”,首封先圣王之后,而功臣谋士又以师尚父为首。由此可以看出,武王之封建以异姓为重,乃受天命,合天下之表征,其举应为因袭前代之礼。至于三叔得封,纯出于一时形势所作的政治考量,“三监”之谓足显其义。大封亲戚以蕃屏周,乃周公之法,周礼之封建。故武王时,所封亲戚,其数不会太多。毕公得毕地为采邑,其子获封于黎的时间,还是以周公摄政至成王亲政之初这段时间可能性最大。召公、周公、康叔、唐叔受封皆于此期,想必毕公受封情形亦同。李学勤说,由于“毕公是伐黎的主将,功绩最高”,武王克商之后就将毕公之子分封到黎国。该说找不到任何其他文献依据。按照断代工程夏商周年表西周王年,以武王在位4年,成王在位22年(包括周公7年),康王25年计,从武王元年至《毕命》康王十二年,已历38年。传说文献谓邵公长寿者有之,但并无毕公长寿之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假设毕公可归为长寿之列,康王十二年毕公大概也不会超过七十。以七十计,伐纣年毕公不过三十二岁,则其长子亦不会超过十五六岁。况且武王四年崩时成王尚幼,毕公之子尚处幼年亦可推想。周初天下本未定,黎国之地又近戎狄、殷遗,此等要害之地,武王怎能放心交与一年幼之人呢,封毕公子于黎只有在武庚叛乱平定之后方有可能。
行文至此,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先秦载籍以及《周本纪》为何对毕公之封无明确记录,对楷伯黎侯之封连丝毫暗示都没有呢?这是否与《魏世家》所说毕氏“其后绝封”有某种关联呢?
关于毕氏的衰落或绝封的时间和原因,史籍无载。张天恩据出土文献推测是因西周中期或略早一点的某种变故而导致的[53]。因新出清华简《祭公》记穆王时期,“毕桓”为三公之一,故陈颖飞认为,“西周中期早段毕氏仍很兴盛”。除了《祭公》外,陈氏又旁征博引其他有关毕氏的金文材料,证明西周中期,尤其是穆王时期,毕氏的兴盛仍在延续,并推论也许是因为在厉王时期卷入了国人暴动所引发的政变,而导致了毕氏的衰落或绝封。陈氏的最终推断,所依据的也是毕伯鼎。毕伯鼎是2007年发掘陕西梁带村北区M502号甲字型大墓时出土的,发掘者报告推测北区墓地“在西周晚期早段的厉王时期已经形成,最早的墓葬有可能早到西周中晚期之交,甚至西周中期的偏晚阶段”,M502号墓属宣王时期或可略早。至于墓主身份,从器铭标识、与邻近墓葬关系及墓葬规格看,似为一代芮君。但随葬青铜礼器呈三鼎两簋组合,其他器又均为明器,级别明显偏低,与国君身份难以相合。对此一矛盾现象,发掘报告给出了或有意薄葬,或国力趋弱,或是级别稍低等三种可能性解释,未有定论。M502号墓最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毕伯为其先祖毕公所作的祭器毕伯鼎居然出现在芮国的墓葬中。发掘者猜测或为赙葬之器,反映了芮、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54]。“赙葬之器”的推测很难成立,正如陈颖飞所言,“毕伯鼎铭文写明是为‘受命毕公’作的祭器,不可能作为‘赙葬之器’送给他人。疑此器因毕氏‘绝封’而被携带到芮国”。“绝封”时间应在毕伯鼎铸造时间与M502号墓下葬之间,而陈氏断毕伯鼎为厉宣时器[55],故有如上之推断。从文献看,芮、毕两国同为姬姓,地望相近,同处“周之西土”(《左传》昭公九年);毕公、芮伯又同为成王顾命大臣(《顾命》),康王之六卿(《康王之诰》),毕、芮两家世代交好是不难理解的。厉王时期,芮伯芮良父为王之卿士而屡谏之事,《国语·周语》、《毛诗序》等文献多有记载。M502号墓主人的薄葬或乃此时芮国国力转衰之征兆,但其国运毕竟延续到了春秋中期为秦所灭之时。此前芮伯万奔魏期间,其母芮姜听政的芮国还创下大败秦师的战绩(《左传》桓公四年)。以上背景说明,若毕氏于厉宣之际遭难,有毕氏逃难至芮国并将国之重器带到芮国,应该说是有可能的。虽然毕伯鼎从铭辞风格看更似厉宣之前夷王时器,但这样的认定对上面的推论影响不大。毕氏厉宣中衰之后,沉寂了一百多年,直到魏祖毕万在晋国雄起方显复兴之象,其标志便是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毕万因军功而获封于由其新征服的魏国之地。
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
杜注:“黎氏,黎侯国。”赤狄不仅灭了黎侯国,还建立了潞国,得封为子,与春秋大国晋成为婚姻之国。可见黎之国灭已有时日矣,或在幽平之际。《卫风·式微》、《旄丘》序云:“黎侯寓于卫。”当在赤狄灭黎之后。由于酆舒事件,晋侯又灭了潞,“立黎侯而还”,此时已距黎灭国百年以上。
有了上面有关毕公家族兴衰史的简单考述作铺垫,我们可以初步回答前此所作的提问了。先秦载籍以及《周本纪》之所以对毕公之封无明确记录,对楷伯黎侯之封连丝毫暗示都没有,应该说与毕公之后“绝封”和沦落确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周本纪》云“昭王之时,王道微缺”。金文的研究表明,夷王之时,始行“堂下之礼”。自此以下,豪族崛起,争权夺利,王室衰微。宣王短暂中兴,后而复乱,不籍千亩,廷礼废置。其大势不可挡,一发而不可收,直至东周巨变[56]。此一大背景决定了,某些大家族的兴衰浮沉势必要影响到周王朝早期历史的传承与书写。故毕公家族历史在传世文献中之不彰显,不能说与毕氏家族百年衰落沉沦史的逆向淘洗没有一点关系。当然,如此推断还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西周王室的书类原始文献经幽平之变之后不可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进入东周之后,修复因文献毁损所造成的上古西周乃至三代的历史记忆缺失,应该成为东周王室长期的工作。而这种修复无非两种途径,一种便是可资参考的诸侯国文物史记;另一种便是仍然健在的世官、元老们的记忆口述。《国语·鲁语》载闵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王国维《说〈商颂〉》云:
考汉以前,初无校书之说,即令校字作校理解,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后取周太师之本以校之,不得言“得”,是《毛诗序》改校为得,已失《鲁语》之意矣。余疑《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太师,韩说本之。……而戴公之三十年,平王东迁,其时宗周既灭,文物随之。宋在东土,未有亡国之祸,先代礼乐,自当无恙,故献之周太师,以备四代之乐。[57]
正考父献《商颂》透露了东周王室补缺文物文献的资讯,《左传》称引《周书》亦名《周志》[58],则反映了从记忆口述到成为《书》篇的文献整理过程。罗家湘博士论文《〈逸周书〉研究》认为:“《寤敬》、《和寤》、《武寤》、《大聚》、《武儆》、《本典》、《史记》等篇章是春秋早期瞽史宣讲的记录。”笔者以为,凡带有春秋以后叙述印迹的《书》篇都有可能源自于瞽史宣讲和耆老口述,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西周文献大多应属春秋以后重新编订过的文献。而东周伊始,毕氏两支已亡,不可能直接参与东周王室的这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过程之中了。这也正是有关毕公一族早期历史的文献载录语焉不详的原因之一。而仅有的几条载有文、武时期毕公事迹的材料,一则为《国语·晋语》所载胥臣之传说,这已是毕万封魏之后的事了;还有一条便是《魏世家》记毕公高受命武王而封于毕,但这显然源于战国魏史记;余下两条材料出自《逸周书·克殷解》、《和寤解》。前此说过《克殷》的主体应为西周文字,但其叙毕公事迹并不显赫。相较而言,在周初伐商的过程中,《逸周书·和寤解》中的毕公的作用和地位显然高于《克殷》篇中的毕公。有趣的是,《逸周书》又出自三晋。蒙文通云:“《逸周书》是部古文派旧书,朱右曾说‘其间有晋史之辞’,就我看来,在孔子以前引此书的只有荀息、狼瞫、魏绛,都是晋人,说这部书出自晋国,应很可信。”[59]是书或不必全出自三晋,但《和寤解》一篇肯定不在例外,进而言之《和寤解》当源于毕氏传述无疑。春秋时毕氏世、庶两支先后都与晋国发生关系,那么传述者究竟是哪一支呢?毕魏可能性不大,因为若为毕魏,则《周本纪》、《魏世家》不会一字不著。既然《魏世家》提及毕公高因武王克商后而受封,又岂能忽略伐商之前毕公与召公一道为谋划图商战略而直接受诫于武王的伟大事迹。黎(楷)国与中原姬姓之国晋、卫距离最近,黎灭国之后,黎(楷)侯寓于卫,后又为晋复立。百年之中,黎(楷)国之人必有很多流寓晋、卫而融入两国者,黎(楷)国的风物、史迹与传说随之播散于晋卫之间,自可想像。由于春秋晚期黎(楷)国之复,赖于晋而非周天子册封,黎(楷)实乃晋之国中国,不可能复有独立史记,故黎(楷)国史迹成为晋史源之一而见诸晋国史籍文献亦在情理之中。《耆夜》尊隆毕公较《和寤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毕公、唐叔得封又在周公成王时,故黎(楷)人、晋人尊隆周公也合乎情理。《耆夜》叙述既以毕公为重又尊隆周公,这也许是其源自于楷人传述又成篇于晋史之笔的缘故[60]。由黎(楷)国传入的歌诗《蟋蟀》,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被定编为《唐风》的。
三、《耆夜》叙述始出时间与乐教意义
《耆夜》所载周公歌诗皆具有道德训诫意味,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与《周书》、《逸周书》所反映的西周早期德观念与周公思想是一致的,也正是《周礼》大司乐“中”、“和”、“祗”、“庸”乐德四教的内容。《周礼》乐德于“四德”之外尚有“孝”、“友”二德,武王酬毕公诗“恁仁兄弟,庶民和同”一句可与“友”德相应。至于“孝”德,《耆夜》叙述的内容并无直接反映,但其叙述形式本身则蕴涵了“孝”德之义。
金文中“效”、“型”、“孝”用法相通,“孝”多指效法有功德之先祖效力王命,协睦宗族,世享爵禄的意思。以有德(受命)祖先为典范,效法先祖明德是“孝”德的主要内容。最早反映“孝”德内容的是康王时《大盂鼎》(《集成》5·2837),其铭云: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慝,匍有四方。畯政厥民,在(于)御事,虘酒无敢(犹临酒无敢醉)。有柴烝祀,无敢(乱),故天翼临,子(慈)法保先王,□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已(祀)。
今余隹令盂绍荣,敬雍德巠,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于)!命女盂型(效法)乃嗣祖南公。王曰:盂乃绍夹死司戎,敏谏罚讼;夙夕绍(助)我一人烝(君)四方(于)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辞朕命。[61]
鼎铭证实了《史记·周本纪》“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的说法。与大盂鼎内容可遥相呼应的是厉、宣时期的毛公鼎、生簋、史克盨等器,诸器铭文都以追述文、武受命,效法祖先遗则与德业的方式,表现出了特有的时代危机意识和强烈的复古精神,希望从周初开国的德业中找到走出王朝危机的精神力量。白川静认为,昭穆时期称扬祖业的祭祀开始盛行,“意味着新的礼乐时代的到来”,又说:“金文中载述有关德性的文辞,大体始自夷王时代,不过当时是以颂扬祖考之德的形式表现的”,“文辞尚称简素”[62]。其实,周公以后确立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因此,孝德势必要成为周代新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否则周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维持。纵览西周金文,以周王室为大宗的天下秩序愈是受到挑战,建立在追述、颂扬文、武受命,祖先德业基础上的孝德思想与精神就愈发得到强调与彰显,《耆夜》篇的叙事无疑也体现了这一孝德的思想与精神。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原始《耆夜》出现的时间及其意义作一个推测。
就彰显孝德而言,《大盂鼎》、《毛公鼎》无疑一致,但其间的差异亦是明显的。前者虽有忧患意识,但并无后者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源于周初对殷商亡天下之历史教训的反思以及对天命的敬畏,而危机意识则源于切近的现实体验。《耆夜》叙事与两者相比,更接近于《大盂鼎》,但与之不同的是,其主旨不是强调文、武受命,或公侯王臣受命于周王,而是颂扬祖先的武功事业,且被颂扬的对象与主角不是周王而是毕公高。由此可以推定《耆夜》不属于王室叙事而是出于毕公高后裔。如果说昭穆时期称扬祖业的祭祀开始盛行,则《耆夜》便有可能是这一新礼乐文化勃兴的产物。就具体的祭祀背景而言,或与续毕公高宗祀的后世毕公、毕伯有关。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若《耆夜》与祭祀毕公高相联系的话,则其叙事应该涉及毕公高始受封于毕的内容,但所见文本又并非如此。结合《耆夜》颂扬毕公高之德业重点放在克商之前的戡黎一役,以及《献簋》载楷伯之臣献自称“身在毕公家”可以推定,第一代楷伯为毕公高长子,《耆夜》始作与楷氏一族有关,这一推论可与此前推定的《耆夜》由楷氏传述至春秋的观点相呼应。始作的时间应在毕公殁后,昭、穆时期的可能性最大。进而言之,简本《蟋蟀》等乐歌此前应该在楷国的言礼上经常演奏并以之教化楷国的贵族子孙,但至昭、穆时期及其后,乐歌当初的语境早已剥离,瞽史乐官与耆老在言礼的仪式上便以乐语道古、口耳相传的方式重新赋予了《蟋蟀》等乐歌颂扬祖先功德的意义,强化了乐歌的德教功能。
行文至此,尽管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说,《耆夜》中的所有乐歌都是武王戡黎之后所举行的饮至礼的产物;也无法最终确定,周公名下歌诗,其辞必出自周公之口,但《耆夜》叙事始出时间不早于昭穆时期,其述作之义应和了周公当初制礼作乐之思想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亦可推断:在西周言礼的仪式上,歌咏祝颂可以代言且具德教之功能;昭、穆之时乐歌(包括乐舞)、乐德、乐语三位一体的乐教结构已经形成。此一推断,距离事实大抵亦不会太远。
[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 150页。
[2]姜广辉:《〈保训〉“十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4日;《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光明日报》,2009年6月8日;《〈保训〉疑伪新证五则》,《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
[3]王连龙:《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28日、《清华简〈保训〉篇真伪讨论中的文献辨伪方法论问题——以姜广辉先生《〈保训〉疑伪新证五则》为例》,《古代文明》,2011年第2期;姚小鸥:《〈保训〉释疑》,《中州学刊》,2010年第5期;周宝宏《清华简〈耆夜〉没有确证证明为伪作——与姜广辉诸先生商榷》,《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由于本文写成于2012年,故文中未涉及姜教授《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宜撰专文讨论之。这里,笔者赞同周宝宏在商榷文章中所陈观点。
[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页。
[5][19]伏俊琏、冷江山:《清华简〈旨阝夜〉与西周时期的“饮至”典礼》,《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6]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4页。
[7]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十三,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册6,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页。
[8][15][40]陈致:《清华简所见古饮至礼及〈旨阝夜〉中古佚诗试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1辑,中西书局,2010年版。
[9]秦酓,酒名。或指秦地之酒,或指以“秦”这种植物所酿制之酒。
[10]马楠:《清华简〈旨阝夜〉礼制小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1]丁进:《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12]马楠:《清华简〈旨阝夜〉礼制小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2页。
[14]程浩针对丁进质疑,撰专文予以驳斥。程氏之辨大多言之成理,亦有释疑解惑之效,限于篇幅,兹不赘述,可参看其原文《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3期。
[16]刘成群:《清华简〈旨阝夜〉与尊隆文武、周公》,《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又,曹建国亦有“伪托之说”。
[17]陈民镇、江林昌:《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
[18]李学勤:《清华简〈旨阝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4日。
[20][25]黄怀信:《清华简〈耆夜〉句解》,《文物》,2012年第1期。
[21]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壹)集释》第五篇,文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链接htt p//www.g wz.f udan.edu.cn/Src Show.asp?Src_ID=1657.本文凡称《集释》者皆指是文,不再详注。
[22]《乐乐旨酒》诗中有“宴以二公”,毕公为客,召公为介,故知二公当有毕公。黄怀信云“‘酬毕公’下,疑脱‘召公’二字”有其道理,但被酬者不可能同时为二公,故疑下酬周公为召公之误。又,李学勤、陈致皆谓武王诗中二公乃毕公、周公,陈致云诗“穆穆克邦”一句是用以“赞颂周公与毕公有为纲为纪,经略天下的才能”,或有失察之处。参:黄怀信《清华简〈耆夜〉句解》,《文物》,2012年第1期;李学勤《清华简〈旨阝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4日;陈致《清华简所见古饮至礼及〈旨阝夜〉中古佚诗试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1辑,中西书局,2010年版。
[23]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耆夜〉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 p://www.gwz.f udan.edu.cn/Src Sho w.asp?Src_ID=1347,2011年1月5日)一文下的评论,2011年1月7日。
[24]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耆夜〉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 p://www.g wz.f udan.edu.cn/Src Sho w.asp?Src_ID=1347,2011年1月5日)一文下的评论,2011年1月9日。
[26]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耆夜〉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 p://www.g wz.f udan.edu.cn/Src Sho w.asp?Src_ID=1347,2011年1月5日)一文下的评论,2011年1月6日。
[27]《史记·天官书》云:“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天官书》说的是星占,之所以有星占,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岁星之顺逆乃一无常也。面对“无常”,《尚书》中强调人事、一德,这与星占巫术的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一德”实即“中庸之德”,“中庸之德”为常。
[28]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中国文化》,第33期。
[29]关于简本《蟋蟀》诗,笔者撰有专论:《〈蟋蟀〉诗清华简本与今本之比较研究》,待发。
[3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2页。
[31]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耆夜〉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 p://www.g wz.f udan.edu.cn/Src Sho w.asp?Src_ID=1347,2011年1月5日。
[32]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耆夜〉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 wz.f udan.edu.cn/Src Show.asp?Src_ID=1347,2011年1月5日)一文下的评论,2011年1月11日。
[33]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八,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05页。
[34]庄履丰、庄鼎铉:《古音骈字续编》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丁度:《集韵》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李圃:《古文字诂林》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37]张国安:《“言”与商周礼仪及其歌咏——汉文化歌唱传统探源》,《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待刊)。
[3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2页。
[39]马楠:《清华简〈旨阝夜〉礼制小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41]此处“成周之众”或即金文中的“成周八师”、“殷八师”,参杨宽《西周史》,第412页。
[42]学者一般认为《克殷》为西周作品,而《和寤》则不早于春秋早期。参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王连龙:《最近二十年来逸周书研究概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43]何光岳:《毕国的来源和迁徙》,《求索》,1997年第5期。
[44]李学勤:《续论周原甲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陈全芳、侯志义、陈敏:《西周甲文注》,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
[45]陈梦家断为成康器,郭沫若、唐兰定为康王器。参: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页;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45页;唐兰:《史簋的时代》,《考古》,1972年第5期。
[4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57页。
[48][55]陈颖飞:《清华简毕公高、毕桓与西周毕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
[4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6期。
[51]高智、张崇宁:《西伯既戡黎-西周黎侯铜器的出土与黎国墓地的确认》,《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7年第34期。
[52]李学勤:《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载《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版。
[53]张天恩:《论毕伯鼎铭文的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2008)》,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54]参《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2007年发掘简报》,张天恩:《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的局部整合》,《文物》,2010年第6期。
[56]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57]王国维:《说商颂》,载《观堂集林》(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58]如《左传》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名堂。’”
[59]蒙文通:《蒙文通文集》卷三,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7页。
[60]《耆夜》等书类文献,后于楚昭王时由晋入楚。参拙文《〈蟋蟀〉诗清华简本与今本之比较研究》(待发)。
[61][62]释文参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65、73、175-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