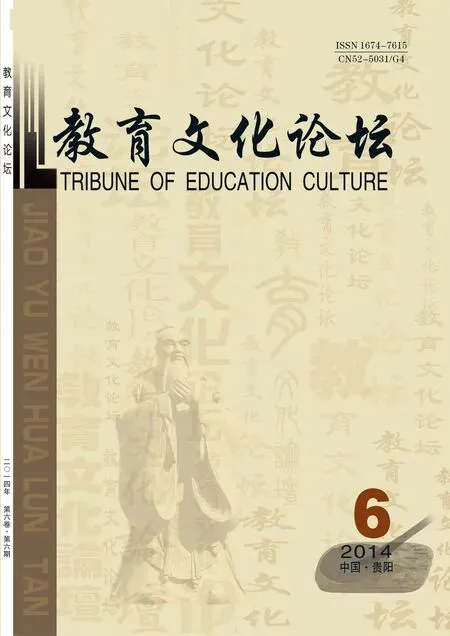《原道》与《人论》之于民族教育启示及比较
2014-04-17田夏彪
田夏彪
(大理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21世纪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蔓延,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呈现出“一体化”态势。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正面临着“一体化”的冲击而丧失民族传统文化的危险。鉴此,我国教育领域不少研究者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主张,以求能够积极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多元文化教育”毕竟是舶来之品,是西方国家在处理各民族文化的“平等权”基础上产生。可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在各种权利方面是平等一致的,不存在西方的文化种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之整体。另外,多元文化教育常常指向不同民族“文化元”之间的相互共存,“文化元”背后隐含着不同主体集团的“独立性”,如“国家集团与少数民族集团”、“不同少数民族集团”、“同一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集团” 之间的“权力”争夺色彩。这与我国各民族成员共为国家主人的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仅能作为一种借鉴,而非照搬。那么,如何认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呢?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特征是什么?该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刘勰的《原道》篇和卡西尔的《人论》著作中的思想内涵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一、民族教育的文化之“道”
教育活动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并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教育实践受到了人类社会活动形成的文化环境的制约。何谓文化?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和习惯。[1]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指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2]从学者给出的文化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自身就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教育融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并逐渐发展,它指向于文化内容的各个方面,通过教育活动过程而传承文化;文化内容的各个方面则规引着教育实践活动,教育活动实践须符合人类文化的属性和发展方向。
可以说,文化与教育之间是一种相互共生的关系。的确,在人类形成了各种文化以后,作为传承文化的教育活动就具有了某种特定文化的基因,因为教育是在特定文化“母体”中孕育与成长。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文化是什么的“实体”以及与之对应的教育映射关系层面上,没有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形成的基础、过程、历史等方面,忽略了文化的生命的机制,使得教育呈现出“有改革而无发展”的局面。就少数民族教育而言,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之间的共生关系,理应从孕育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生成性过程来加以把握,而非简单地将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处理成“文化和教育”互不相干的两样东西或它们的简单相加。
刘勰的《原道》篇对“文”的形成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及教育有很好的启示性。《原道》开篇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也就是说,“文”的形成来源于山川、地貌、日月等天地自然系统,这些是文形成的基础。那么,为什么说这些自然之物是“文”的基础呢?原因在于人类产生以后,在与周围环境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这些相对外在于己的各种自然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在大脑中形成了对这些环境的最初“印象”,并且不断对这些“印象”进行有意识的加工,于是有了“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的结果。由此出发,我们在进行少数民族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不应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中 “道”的成分,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先天而在的“万品”,如“云霞、草木、泉石”等,这些自然存在之物是以“自然之道”的形式存在,是天地系统本身及存在方式;第二层是“道”为人对天地系统及存在方式的反映,即“心生则言立,言立则文明”的“文生之道”;第三层是“道”的意义层面,指的是人类在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过程中形成的“体验或意义”,这是“道”的本体。这三层含义是我们在认识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应该具有的整体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第二层含义上,即在讨论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上,只注重有形的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结合,而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然之道”和“意义之道”。
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应还原文化形成的“本原之道”。正如谢松龄先生所说的,“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意显现为象,象著明为言的过程。……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他们的创造历程,都是意→象→言;在此,意是体,象、言是用。——人类总是先有了某种体验,或某种意,才去创造表达无形的意(体验)的、有形的象和言,使意(体验)得以显现。象、言是显现意体之用。”[3]此外,在注重文化的“意”体的同时,理应考虑“意”形成的条件即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自然环境中所蕴涵的各种关系。总之,少数民族文化由自然、社会、人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存在系统,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与文化整体发生共生关系,在发挥少数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少数民族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要关注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过程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方式、习俗、制度、艺术”等等文化表象,更应关注文化表象背后的意义体验或心理关怀。
二、民族教育的“符号系统”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在与天地万物并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以其超强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围绕着“文化”而展开,这种“文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描述为是符号的动物,人借助于各种符号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换句话说,人创造了符号或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符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过程以符号为纽带而展开,符号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媒介。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的本性的提示,人通过符号化的过程展开其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等等符号系统,不同的符号系统反映了人类对特定发展阶段中周围世界的“解释”,是其“体验或意义”的外化。因此,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探求人类生活形式的“根源”必须从符号(文化)入手。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必然离不开符号系统的支撑。不同的符号系统,需要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理解,只有符合特定符号系统运行的方式来实施教育,才可能发挥出教育对符号系统的功效。
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承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对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持批判的态度,而批判其这一观点的最好的武器也是卡西尔本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符号理论”。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科学文化所给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所带来的极大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变成符号的“权威”,可以凌驾于所有的“符号系统”之上。从人类社会纵向发展来看,符号系统可能会发生不断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系统的唯一性,仅仅可能的是新的符号系统与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部分联系得更紧密。但从人类社会生活横向来看,人类生活的展开离不开多种符号系统的参与,不同符号系统或不同符号系统组成的符号系统整体才能诠释人类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意义整体”。 因此,少数民族教育在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文化的系统性,而不仅仅将教育局限于文化系统中的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文化系统决定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
三、民族教育特征之分析
从上述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之“道”和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教育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宗教、民俗、生产劳动、语言、服饰、建筑等等形成的文化系统中,文化系统整体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呈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并且,少数民族文化系统在整体地影响少数民族教育的同时,文化系统中的每一子系统也从特定方面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在具有民族文化特征之外,又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
(一)少数民族教育类型的多样性
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教育存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教育从广义来讲,应该囊括人类的一切教育实践活动[4],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5]。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教育形式或教育实践活动,它们对人类的生产生活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同理,少数民族教育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和各种不同的社会教育形式,如家庭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宗教活动教育、礼俗活动教育等等。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不同的教育类型中,获得适应少数民族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知识、能力,积极投入改造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生活中。
(二)少数民族教育价值的双重性
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发展。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要加快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本民族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选择的两重性,少数民族价值取向必须统一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来说同样重要,作为生存保障的经济发展来说,给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是必须的,而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说,代表一个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民族发展的重任。为此,少数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理应关注这两个方面。
(三)少数民族教育功能的多元性
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是由不同的活动构成的,这些不同的活动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等。作为不同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也以不同的形式发挥其功能,有效地促进构成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子系统的发展。同时少数民族教育的功能具有综合性,其对民族社会整体的推进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子系统各自单一发展后的累加,而是一个统一融合三者的过程,也就是民族社会整体发展与各子系统并非表现为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并且少数民族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每一子系统的发展作用,又是以少数民族教育促进这一子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次子系统的整体发展为前提。因此,少数民族教育的功能非为单元,而是多维统筹的,它从多方面、多层次展示了教育的多功能性。
(四)少数民族教育资源的丰富性
少数民族教育处在少数民族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中,由自然、人、社会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化系统都对少数民族教育发挥作用。换言之,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是少数民族教育的资源,少数民族教育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资源中获取养料,从不同方面把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培养成和谐的主体。比如,宗教活动中的自然崇拜等,能够培养社会成员的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民族节日活动则通过全体民族社会成员的参与,能够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形成民族成员的友好关系及民族认同感等。
综上所述,刘勰的《原道》和卡西尔的《人论》提出的关于对“文”的认识和“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观点,给我们认识民族教育及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民族教育与民族社会的天地系统相共生,民族社会的天地系统既是民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关注的对象。但对《原道》和《人论》二者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刘勰在《原道》中指出的“文”具有的“道”之三个层次内涵比卡西尔《人论》中的“人是符号的动物”更能体现出自然、“文”(符号)、意义所构成的天、地、人“三材”的整体性,使得我们意识到人除了与符号系统发生联系外,符号的形成与自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符号是人类观察自然的“印象凝聚”,及关注符号背后的价值或意义层面是“文”的本体所在。同理,民族教育也应将天地自然系统和人与天地系统发生联系后形成的文化及文化中蕴涵的“精神”作为发展的价值选择。只有正视民族教育的多特征性,并遵循民族教育的文化之“道”,才能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发掘出“新生支点”,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6]
[1] (英)泰勒.原始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2] 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9.
[3] 谢松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 1.
[4] 张诗亚.祭坛与讲坛——西南民族宗教教育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1-5.
[5] 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4.
[6] 胡芳.马克思东方文化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J].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