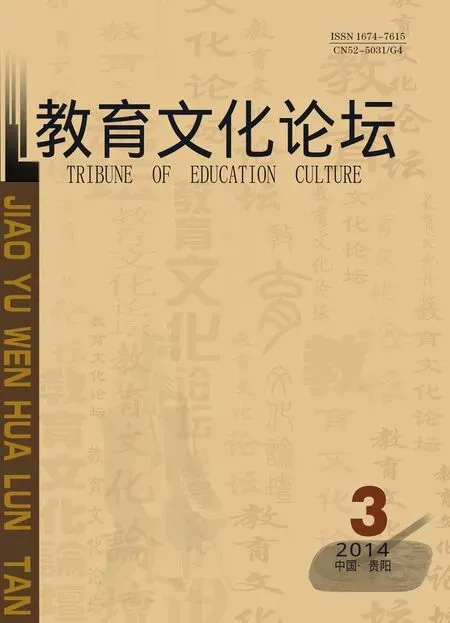近代教育期刊主编与近代教育的发展
——以《中华教育界》主编陈启天为例
2014-04-17喻永庆
喻永庆
(中南民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期刊主编作为期刊的精神核心与舆论的领导者,他们大到期刊的选题规划、栏目设置、专号组织,小到稿件的征集、取舍与字句的修改,都能层层把关,对期刊的办刊理念与发展方向起着关键作用。在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的近代中国,众多的期刊成为推动文化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工具。而其中,期刊的主编无一不是社会的精神领袖与时代潮流的引导者,就像陈独秀之于《新青年》、胡适之于《独立评论》、邹韬奋之于《生活》,他们借助自己的才识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文化的传播、知识的传承、思潮的推进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他们的办刊思想与编辑理念,当前文学界、史学界、新闻传播学界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广泛探讨。相比之下,近代教育中影响较大的期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教育与职业》等杂志,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国外先进教育的引入、教育制度的变迁、教育思潮的传播等方面都影响甚巨。在这一过程中,主编的积极引导同样不可小觑,但当前教育界对此却鲜有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鉴于此,本文以《中华教育界》主编陈启天为例,通过对该时期《中华教育界》撰稿人的构成及特征研究,系统探讨陈启天在办刊过程中撰稿人的聚合途径,藉此全面展示教育期刊中主编办刊的实况,丰富近代教育期刊研究。
一、《中华教育界》撰稿人的构成与特征
《中华教育界》创刊于1912年3月,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发行,1937年8月因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出版至25卷第2期后停刊,1947年1月复刊,1950年12月因中华书局业务方向转移,出版至复刊第4卷第12期后终刊。《中华教育界》刊行近30年,共出版发行29卷312期,几乎横跨整个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教育期刊中刊行时间长、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在教育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陈启天自东南大学教育科毕业后担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陈启天(1893-1984),湖北黄陂人,又名翊林,字修平,号寄园。早期就读于武昌高等农务学堂附小、附中。1912年入武昌中华大学政治经济别科,1915年毕业后,先后任教中华大学中学部、文华大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并开始接受国家主义学说,与余家菊、李璜等人力倡“国家主义教育”,并使之成为当时极有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潮。1924年毕业后,入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主编《中华教育界》,同年与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创办《醒狮周报》,组织国家教育协会,将“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国家事业、国家工具、国家制度”为其奋斗目标,号召并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后由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转赴四川成都大学讲授中国教育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课程。后从教育转向政治,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工商部部长、中国青年党党主席,1984年病逝于台湾。著有《国家主义论》、《中国国家主义运动史》、《近代中国教育史》、《寄园回忆录》等著作。在1924年7月到1926年11月主编《中华教育界》期间,他对该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教育改造国家为办刊宗旨,不断调整栏目设置,加强期刊与现实教育的联系,使得《中华教育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教育界及社会上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他也有计划地刊发了10期专号,如“收回教育权运动号”、“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留学问题号”、“师范教育号”、“小学爱国教材号”、“公民教育号”等,聚集了一大批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先进人士。
根据笔者对《中华教育界》主要撰稿人的考察,*根据陈启天时期的《中华教育界》的署名作者(共176人),制作了“撰稿人及刊文数统计表”,因篇幅限制,本文略去此表。本文后面的分析,凡依据该表的资料,不再一一注出。陈启天时期《中华教育界》撰稿人主要由下列四类人群构成:
第一,大学教师。虽然统计表中多数人都有过大学从教的经历,但在陈启天担任《中华教育界》主编的时间段内,仅有俞子夷、李璜、廖世承、穆济波、杨廉、程湘帆、汪懋祖、夏承枫、陈鹤琴、郑宗海、朱君毅、余家菊、程宗潮、舒新城、邱椿等人在大学担任教职。其中,除李璜曾先后任教于国立武昌大学和北京大学,舒新城执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邱椿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教员外,其他人则先后担任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教职。如此众多的东南大学教师担任撰稿人,主要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国际上新的教育思潮与教育理论的掀起与大量引进,东南大学教育科渐渐成为新教育运动的主要阵地,在全国影响颇大。与此同时,《中华教育界》为适应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毅然进行了革新,广泛地向东南大学教育科师生征稿。正如其所提倡:“我们这本月刊从第十卷第一期起,彻底改革,担任撰述的人以南北两高师和各处有经验有研究的青年占大多数”,[1]虽然提到南北高师,但此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竟无一人,这与主编陈启天是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毕业生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东南大学教育科这些撰稿人,多为新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与推动者,在当时的教育改革中居于领导地位,影响着当时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小学教师。《中华教育界》自1912年3月创刊以来,一直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其办刊宗旨,在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以中小学教育研究为主导的办刊理念,积极参入中小学的教学和改革活动。这一传统在陈启天任主编之时也得到相应的继承,他在改革之初就申明:“至于本志取材的分量以关于小学的为多,则照旧不变”。[2]并在实际中践行着这一方针,从撰稿人当时所属单位,以及撰稿人人数上我们可以得到印证。从统计数量上看,当时任中小学教师的有52人,占表格中统计人数的55%,如胡叔异、沈子善、罗廷光、顾克彬、沈百英、杨效春、张宗麟、郑朝熙、祝其乐、王克仁、张锡昌、曹刍、蒋息岑、葛承训、唐瑴、周邦道、李琯卿、马客谈、吴俊升、王崇植、周调阳、盛朗西、施仁夫、古楳等人,他们此时或为一线的教员,或为教育管理人员,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与体会,发表着他们对教育、教学的真实感受。
第三,杂志编辑。这部分人在《中华教育界》撰稿人队伍中所占比例不大,共8人,如陆费逵、朱文叔、沈百英、李步青、余家菊、范寿康、邹恩润(韬奋)、常乃德等人,其中陆费逵、朱文叔、李步青(廉方)、余家菊为中华书局编辑,且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总经理;范寿康、沈百英、常乃德三人为商务印书馆编辑;邹恩润(韬奋)则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刊物《教育与职业》的主编。除去邹恩润(韬奋),其他都为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这主要由于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都有教科书编辑、出版业务,他们需要一些从事过教育,对教育有追求的编辑人员。从李步青(廉方)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余夙治教育学,专究国民教育,尤致力于教材研究”。[3]另外,从这些编辑人员服务的时间上看,他们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如余家菊在任职中华书局编辑之前作为武昌师范大学教授,而在中华书局工作不到半年又任东南大学教授,常乃德、李步青、范寿康等人也是如此。可见,杂志编辑大多数只是一个跳板,或者说是从一个职业到另一个职业的中转站,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教育的热情,他们从不同学科与角度研究教育与教科书问题。
第四,在校学生。《中华教育界》创刊之初,其撰稿人主要以中华书局编辑与广大一线中小学教师为主。自第10卷起,该杂志进行了革新,将一些在校学生纳入撰稿人范围,这种情形在陈启天任主编之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学生既包括国外留学生,也包括国内大学的学生,如周太玄、常道直、王光祈等人此时为国外留学生,其中周太玄留学法国,常道直留学美国、王光祈留学德国,他们加入到撰稿人行列,对欧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进行了引进。而罗廷光、胡家健、沈子善、卫士生等人同为东南大学的学生,相对于上述第一类新教育的倡导者来说,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新一代青年,最初他们作为新教育的追随者,后来也加入到倡导者行列,日后并成为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活跃分子或领军人物。
二、《中华教育界》撰稿人的年龄结构与教育背景
在教育背景上,《中华教育界》撰稿人所接受的教育也存在差别,为方便说明,笔者进行了分类。一类是留学日本。1870年代与1880年代出生的属于这一类,如范源廉、郑朝熙、李步青(廉方)、俞子夷等人,其中范源廉1901年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李步青与郑朝熙分别于1902年与1908年考入日本仙台弘文学院;俞子夷也于1903年东渡日本学习,之后又受江苏教育会的选派,考察日本教育。这类撰稿人中,他们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为了改变落后的教育现状,东渡日本,以速成的方式,学习或考察日本先进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实验,并于回国后在教育领域进行着改革活动,给当时沉闷的教育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一类是留学欧美,这类撰稿人主要集中在1890年代,如郑宗海、汪懋祖、廖世承、陈鹤琴、程其保、朱君毅、陶行知、常道直、邱椿、杜佐周等人留学美国,并且都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周太玄、李璜、王光祈等人留学法国;余家菊留学英国。这一群体出生于1890-1900年间,伴随1901年的清末新政中新式学堂的大量兴办,他们的中小学教育大多就读于此类学堂,传统书院教育相对较少,一些人在结束国内高等教育或预科培训后直接留学国外,选择欧美为其学习目的地。在统计中,这一年龄段只有范守康留学日本,但他同上一年龄段最大的区别是就读于日本正规的大学,并获得了学位。另外,该年龄段人多数选择教育为自己的专业,并回国后在大学教育科中任教。这在中国教育学科专业化的起步年代,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颇多。
一类是就读于国内大学,以1890年代与1900年代两个年龄段为多,他们集中于1920年前后进入大学学习,在陈启天担任主编之时,一些人已经毕业,并在中小学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另一些人则正享受着大学生活。在这类群体中,除周调阳、常乃德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穆济波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鲁继曾毕业于之江大学,李儒勉毕业于金陵大学,邹恩润(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大多数人毕业或正就读于东南大学,如陈启天、罗廷光、沈子善、古楳、胡叔异、夏承枫、程宗潮、吴俊升、祝其乐、邰爽秋、张宗麟、曹刍、李清悚、钱希乃、卫士生、胡家健等人,他们作为南京高师或东南大学教育科不同年级的学生。这群人可以说都系统地接受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大学的教育,并且在入大学之前有过从事教育的经历,对当时中国教育与教学的现状了如指掌。进入大学后,他们受教于他们的导师,普遍接受了欧美最新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成为中国本土培养的最早教育学专业人才。从整体上看,这一群体都具有较丰富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作为新教育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拥护者,对教育改革赋予了极大的热情。而当时的重要教育改革与实验,因这一代人的加入和支持而取得骄人的成绩。
最后一类是毕业于中学或师范学校,如沈百英、马客谈、李琯卿等人,他们大多毕业于中等学校或师范学校,长期在中小学担任教职,这类群体在《中华教育界》撰稿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原因主要同该刊关注中小学教育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些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属于这类群体,如陆费逵中学毕业,他作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坚信以出版辅助教育的理念,并在实际行动中大力宣传“出版救国”、“教育救国”,发表大量的教育改革文章。这些出版人、编辑人在《中华教育界》上担任撰稿人,与近代出版机构教科书的编辑与发行紧密相连。
三、《中华教育界》撰稿人的聚合途径
前面我们探讨了陈启天时期《中华教育界》撰稿人的构成、年龄结构与教育背景,从中可以了解到,此时期《中华教育界》撰稿人的构成特征、教育背景两个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仍能够在《中华教育界》上形成聚合之势,同主编陈启天的个人能力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此时的《中华教育界》,形成了以陈启天为中心,以革新教育与教育救国为奋斗目标,依靠师友、同学、同道、同乡、同事等关系的大力支援,逐渐成为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阵地。
1.师友:厚爱与援引
陈启天曾两次报考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前身),对此他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自五年秋教书至今年(1918年,笔者注),渐觉未学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因有专攻教育之志。惜予无力留学外国,乃于暑假中往考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以取入国文史地部,未入学”。[4]18第二年夏他再次报考,被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录取,但应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之聘,又未入学。后因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政治运动、学校罢课,复课无期,于是函询“南高教务主任兼教育专修科主任陶行知先生,可否准我再入学,陶行知回信说,‘可以破例照准’”,[4]85于是陈启天在其他同学入学半年之后成为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甲子级一员。此时,陈启天已经29岁,之前已经是武昌中华大学政治经济别科毕业生,并先后在汉口民新学校、中华大学中学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职,又经过两次入学考试并得到教育专修科主任陶行知的亲自同意。这些情况在他的同班中可能是少有的情况,也因此会增添了他的一些知名度。对此,陈启天这样说道:“我既曾在大学毕业,又曾在小学、中学以及大学教了四年半的书,现在又来入高师,自然容易引起师友的注意。加之甲子级应于民国九年秋入学,而我一个人迟了半年才入学,更容易引起师友的注意。”[4]85就这样,1921年春至1924年夏,陈启天就读于南京高师及后来的东南大学教育科。在学业上,陈启天同样也是十分突出,他在读书期间相当勤奋,并开始撰写论文,“我此时的文字,尚不十分成熟。不过从他人看来,多把我当做一个特殊的学生看待。我藉写文字,一面促进研究的兴趣,一面补助个人的用费”,[4]88以致患上“咳血与脑痛”,对这他日后回忆:“吾以病躯而犹能力学者,一则以予向学之志甚坚,不成不休,一则赖有诸师友之鼓励奖进而。”[4]20此外,陈启天在学校学生活动中担任的一些要职与参加一些政治与学术运动,下文有详细论述,这都可能引起师长的关注,并同他们形成亲密的关系,为日后的约稿也提供了便利。
基于的协整常系数检验发现,现货与各期货合约之间在各分位数下的协整系数并不相同。因此,下一步需要使用分位数Wald检验来检验各分位数下β=1的原假设是否成立,结果检验见表5。
而东南大学教育科中教师在当时教育上的影响,也成为陈启天乐于征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教育科教师队伍中,如陶行知、汪懋祖、郑宗海、程湘帆、朱君毅、程稚秋(其保)、廖世承、陈鹤琴、俞子夷等人,他们大多留学国外,在教育领域都学有所长。如俞子夷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小学教育专家,一直从事教学方法的改革试验。陶行知组织发起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直关注着平民教育的教育与实验;陈鹤琴作为中国幼儿教育的开拓者,开展形式各样的幼儿教育研究;廖世承、朱君毅二人积极从事智力测验及教育实验活动,廖世承在担任东南大学附中主任期间,使得“东大附中几执全国中等学校的牛耳,投考人数,为全国称首”。[5]187如此众多的教育专家汇集在南京高师或东南大学教育科,在当时大学教育科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是中国教育科学化的试验先驱人物,始终站在教育发展的最前沿,引领着当时教育的变革。
虽然东南大学教育科教师在《中华教育界》的刊文并不算多,仅有25篇,但这些论文的导向性与前瞻性相当强。这些撰稿人及他们的论文出现在《中华教育界》,一来扩大了该刊在当时教育界中的影响,增加销售量。二来分享了教育中的最新问题与发展趋势,推动着教育改革的深入。
2.同学:相互砥砺与共同奋进
东南大学教育科作为当时中国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教育学科之一,这不仅得力于一群留学美国的教师身先士卒,而且也同东南大学教育科毕业生在当时社会或教育改革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东南大学教育科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
在入学的资格上。东南大学教育科是在1918年成立的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最初的招生简章中,对招生人数及教育教学经验的要求较严。如在学科及学额上,规定“现招教育、体育、农业、商业专修科各一班,每班二十五人”;在入学资格上,需要“具有完全师范或中学及同等程度之学校毕业、身体坚强、品行端正而有志于教育者。惟教育专修科生除上列资格外,须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经验,应由服务之机关缮具说明书”,[6]706从招生简章可以了解到,招生的人数较少,只有二十五人,利于小班教学。教育经验作为是否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符合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特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也是这样遵守的,如吴俊升报考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之前在如皋师范附属小学担任一年级国文一年,[7]11古楳报考之前曾在梅县第七区立高等小学校担任教师,[8]25施仁夫则为江苏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师,[9]162-163因为有了从事中小学教育经验,加上他们心中的一些改变教育现状的理想,使他们研习教育更有针对性,对问题的把握也能做到有的放矢。
在培养模式上。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教师大多以留美为主,他们耳濡目染美国新教育运动,并根据国内教育学发展现状,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与专业化运动。在课程的培养上,生物学、遗传学、测量学、心理学等最新研究成果加入其中。1919年入学的教育专修科学生章柳泉对他的学习课程有这样的回忆:“我入学的第一学期,就有一门介绍科学常识的课,陶老师(陶行知)在这门课中给我们讲遗传学,从达尔文到德弗里斯,特别市孟得尔的杂交试验。第二年我们就学‘科学的发展史’。生物学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课程。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科学基础,我们学得很不少,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实验心理学’是重点,共学两年,做过很多实验,还开设‘心理学史’课程。此外还有教育统计学,‘测验之编制与应用’。”[10]332东南大学教育科这种培养模式,在当时教育科学发展程度不高时代,对于提升教育科学的学科品质,系统培养教育科学人才,使学生掌握教育、心理专业知识与以后开展教育实验活动都是大有裨益的。
正是由于东南大学教育科这种培养模式,使得其学生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与科学开展教育实验的能力,这些使得他们成为陈启天时期《中华教育界》撰稿人的必要条件,而他们与陈启天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成为《中华教育界》撰稿人。
陈启天是东南大学教育科一个活跃分子,他积极参加各种教育研究与社团活动,由此练就他较强的组织与领导能力,并同其他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他的东南大学的生活:“关于课外活动,我曾参加教育科甲子级会、教育研究会、学生自治会及鄂籍学友会等。甲子级会是同班同学增进友谊,砥砺德行,并处理级务的一种组织。我承同学的厚爱,被推为会长,连任三年,始终彼此都很相得,没有恶感,因此我领悟同学的友情非常纯诚,实不下于兄弟。教育科研究会,我只做了一个会员,参加开会,并偶尔为教育季刊写稿。”[4]88-89
陈启天时期的《中华教育界》撰稿人中,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毕业生或在校学生占较大的比例,刊发的文章也较多。这些人,要么作为陈启天的学长,如曹刍、夏承枫、顾克彬、周邦道、胡叔异、唐瑴、施仁夫、钱希乃、杨效春、葛承训等人,[11]要么是他的同班同学,如吴俊升、凌纯声、古楳、徐益棠、祝其乐 潘子庚、程宗潮、邰爽秋等人。[4]20还有就是他的学弟,如罗廷光、沈子善、李清悚、张宗麟、胡家健、王倘、甘豫源、卫士生等人,这些人是我国较早培养的一批教育学专业人才,在东南大学教育科这个大家庭中,他们不仅接受着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真挚的友谊,使得他们能在陈启天主编的《中华教育界》上集结。
3.同道:思想的吸引与呼应
陈启天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坚持“奋斗、实践、坚韧、简朴”为信约,以《少年中国》为其机关刊物,会员主要来自于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学校的青年学生。对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间的理想与共同追求,黄钟苏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少年中国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会员莫不反对封建主义,崇尚进取,重视新知识,于各种新制度极感兴趣,思想自由,不受约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13]3由此可知,初期的少中会员虽然学习与研究的领域不同,但他们为了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时代的共同目标团结起来。对于会友间的友谊,左舜生后来回忆道:“在最初几年‘少中’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钩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13]455可见,早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他们之间只有同志间的友谊,加上学术上的相互关照,俨然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陈启天也开始接触各种不同领域的人,“我于民国八年由王光祈在武昌介绍入少中。民国十年我到南京以后,发现少中会友多纯洁可爱,有志上进。因与常相往还,使我得到精神上的鼓励不少。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即少中给我们尚友天下之士的机会,使我们的知交,不仅限于同乡与同学,至于我后来参加中国青年党活动,除时事关系外,也与少中有关系。”[4]85因为早期少中会这种兄弟加战友的亲密关系,陈启天认识了王光祈、周太玄、常乃德、李璜、穆济波、王崇植、常道直、舒新城等少中会人,并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在陈启天担任《中华教育界》主编之时,他们多数人成为《中华教育界》重要撰稿人。
随着少年中国学会分裂之后,国家主义派核心人物王光祈、周太玄此时留学国外,陈启天此时逐渐成长为国家主义派的领袖人物,思想也开始趋向于国家主义学说,“民国十三年夏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后,即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教育界》月刊两年半,几乎每期都有我的教育文字发表。我在未主编《中华教育界》以前的教育文字,多半依据民主主义的原则,讨论各种教育问题。……但在主编《中华教育界》的时候,又多半是依据国家主义的原则,讨论各种教育问题”。[4]97为了扩大国家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将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陈启天担任主编之后就对《中华教育界》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新希望是以教育的言论促进教育的改革而形成中华民国立国的国魂。……第二新希望是以教育的言论提醒目前中国混乱而无宗旨的教育不足救亡建国,而反对国人借重外人在华文化事业的趋势以免于无形中速亡覆国。”[14]在确定办刊方向后,陈启天立即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稿。
由于国家主义教育提倡的“教育建国论”与先前的“教育救国论”不谋而合,其思想在当时教育界与知识界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原来少中会中思想倾向国家主义的会员与拥护国家主义教育学说的人士积极撰文投稿,《中华教育界》很快组织好了这次专号,并以两个专号的形式刊载了这次征文活动。这些文章既包括理论上的建构,也包括国际比较研究,还包括国家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运用,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国家主义教育进行了诉说,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极大的反响。对此,《中华教育界》还陆续刊发了留学问题号、师范教育号、小学爱国教材号、公民教育号等专号,掀起了宣传与推广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热潮。在此基础上,陈启天以倡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者为重要发起人,成立了国家教育协会。该会以“国家主义的精神以谋教育的改进”为宗旨,成立之初发起人有39人。如余家菊、李璜、陈启天、曹刍、李儒勉、范寿康、舒新城、常道直、罗廷光、周邦道、唐瑴、穆济波、杨廉、邰爽秋、周调阳、李琯卿、祝其乐、古楳等。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华教育界》团结了一大批教育界人士,他们有的作为陈启天的同学,有的作为陈启天的老师,有的作为陈启天的同事,也有的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或教育管理人员,他们为了共同信仰——教育改造国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与不同的角度发表着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
4.同乡与同事:相忍相谅与鼎力支持
在撰稿人中,陈启天与余家菊、任启珊三人同为湖北黄陂人。其中,陈启天与余家菊的人生发展轨迹极其相似,不论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学术研究方向,还是他们服务单位,都存在交集。陈启天1906年进入黄陂县道明高等小学堂学习,余家菊也于1909年考入该校,陈启天对此这样回忆道:余家菊“比我的年龄小四、五岁,与我不在同班,在校时期自少个别往来的机会,不过每周仍在操场上共同运动两三次”,但“出校以后与我的关系很多”。[4]71-72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余家菊于1912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并于1916年就读于该校中国哲学门。陈启天则于1912年考入中华大学政治经济别科,1915年毕业。对于此时二人的关系,陈启天说:“同学各省人皆有,而乡人独多。与予往来较密者,为任启珊、陈伯康、熊国英、阮子印、吴中行、余家菊、恽代英、梁绍文诸人”。[4]15陈启天毕业后应任启珊之约,在汉口民新学校任教,而仍在校学习的余家菊也同在该校兼课,后二人同在中华大学中学部教书。1919年,经王光祈的介绍,陈启天与余家菊同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秋王光祈自北京来鄂,介绍恽代英、余家菊、梁绍文与予四人入少年中国学会”。[4]19翌年,陈启天考入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研习教育,余家菊则入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就读,也研习教育。期间,他们“同赴长沙就职第一师范”,之后经过学习之后,又同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后来成为中国青年党重要人物。
从上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陈启天与余家菊人生有数次的交汇点,同乡、小学与大学校友、同校教员、研习学科相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等。这些相同的经历,我们如不从人物内心的角度去审视,可以断定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而实际上,对于二人的关系,陈启天与余家菊在回忆录中记载都很少,相比于陈启天,余家菊则仅有一段话的介绍:“修平(陈启天,字修平,笔者注)长予五岁,而与共甘苦最久,而气质思想皆不相近,始终相忍相谅,实为难能”。[15]204余家菊所说的“气质思想皆不相近”,这从他俩对待中青党的态度上可以略知一二,余家菊认为自己加入中国青年党,“第一是是因为朋友们的面子关系,第二是因为要合力宣扬国家主义,在实际上我的思想与青年党主要人物的思想都不相同,周旋其间很是苦恼。我支持青年党三四十年只基于义务的感情而并不是基于自发的兴趣。”[15]35而陈启天对于中青党有这样的记载:“我与初建的中青却有两点因缘:一是中青海外建党时期的五个中央委员,有三个委员(曾琦、李璜、何鲁之)与我同为少中会友,自然容易接近。二是我在中青建党以前,已在国内提出国家主义的主张,自然更容易接近。所以中青由海外建党时期进到国内建党时期以后,我便始而参加中青的宣传,继而参加中青的组织了。”[4]143从他们二人对于加入中青党的态度,以及后来他们的整个政治活动,我们可以了解到,陈启天热衷于政治,善于利用一切关系来发展自己,余家菊则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自由主义者。但这种态度并没有影响二人的感情,他们“共甘苦最久”,又“终相忍相谅”,是二人关系的最真实写照。余家菊此时作为《中华教育界》重要的撰稿人,发表了14篇文章,大多是关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这是他们同乡惺惺相惜的最好注脚。
陈启天在1924年7月至1926年11月担任《中华教育界》主编期间,以“教育改造国家”为其办刊宗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汇聚一大批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教育史上又一重要的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其对民国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与留学教育政策的制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中,《中华教育界》主编陈启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影响可谓是厥功甚伟。近代教育期刊主编中类似陈启天还有很多,我们只有深入地进行挖掘,还原近代教育期刊编辑生活的原生态,探讨他们独特的办刊风格与办刊思想,这些对我们处在一个期刊泛滥的当代中国,如何有效地发挥期刊的参入教育、服务教育的功能不失有很好的历史借鉴意义。
[1] 佚名.本社启事[J]. 中华教育界, 1920(1).
[2] 佚名.本志的新希望[J]. 中华教育界,1924(1).
[3] 李廉方.京山新志(序)[Z].武汉:湖北通志馆, 1949.
[4] 陈启天.寄园回忆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5] 廖世承.我的少年时代[A],良友人物(1926-1945)[C].上海: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 潘懋元,刘海峰.近代教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7] 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
[8] 古楳.卅五年的回忆[M].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9] 施毓湘.化雨春风启后学 老年硕德仰前贤——回忆老教育家施仁夫[A].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C].1984.
[10] 章柳泉.忆行知师在南京高师时的几件事[A].纪念陶行知[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11] 佚名.本届毕业生状况[N].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1923-10-22.
[12] 沈云龙.王光祈先生纪念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13] 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14] 佚名.本志的新希望[J].中华教育界,1924(1).
[15] 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M].台北:财团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