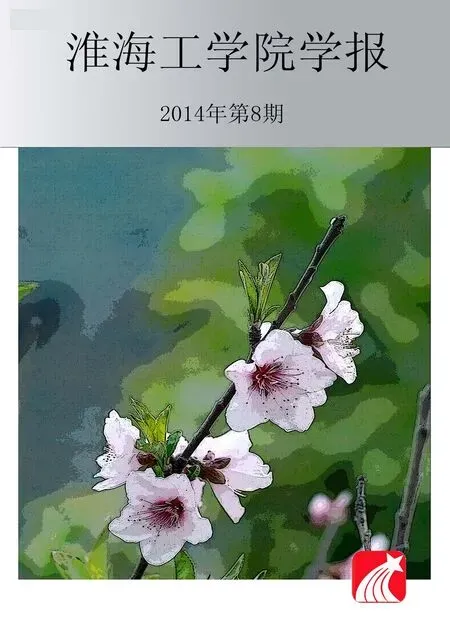独特视角下的底层关怀
——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解读*
2014-04-17盛翠菊董诗顶
盛翠菊,董诗顶
(1.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2.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江苏 徐州 22100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经济结构的巨变与城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农民工进城”这一突出的社会现象,人口的大迁移逐渐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稳定自足的乡村社会结构。所以从更深层次而言,农民工进城不仅是一场持续的人口迁移,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与精神变迁。而文学则是记录与思考这一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载体,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所说:“关注打工文学,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更包含了我们对劳动者的敬意和深情。”[1]江苏作为当代中国一个容纳农民工的重要区域,江苏作家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考察、分析农民工进城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平台。
农民工题材小说在此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描写农民进城务工生活的小说。农民进城务工现象作为一种潮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工潮”居高不下,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创作也随之大量出现,成为近年来江苏作家小说创作的热点之一。以农民工作为小说叙事对象的江苏作家人数多、名头大,他们的此类作品影响大、质量高,像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储福金的《倾听到什么》、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和《回家的路》、葛安荣的《都市漂流》、王一梅的《城市的眼睛》、陈武的《换一个地方》、余一鸣的《我不吃活物的脸》、徐玲的《流动的花朵》、朱文颍的《蚀》、顾坚的《青果》、罗望子的《非暴力征服》、李洁冰的《青花灿烂》、胡继风的《等待回家的民工》和《鸟背上的故乡》、陈文海的《不喝酒的民工》等。
总体考察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可以发现,相比较于物质上的贫困,农民工进城以后精神层面的诉求是江苏作家们更为关注的焦点。在这一点上,苏北作家尤为关注,究其原因,是因为苏北从事此类小说的作家,其早期生存境况有别于苏南作家,他们大多是出生在农村或有过到城市打工的经历,比如赵本夫、陈武、王大进和胡继风都是出生在农村,其中陈武和王大进都曾经是农民工,这也使得他们在创作时专注于“对城乡冲突的展示,对农民工都市生活的描写,对农民工精神世界的揭示”[2],换句话来说,他们是在写自己或自己的兄弟姐妹,因此,也就能更加真实地表现这一群体的城市生存状态。女性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相对弱势的群体,也同样成为江苏作家笔触较为集中之处,突显了江苏作家独特视角下的底层关怀。
一、文化视角:城乡文化相遇而对峙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题材小说是乡土小说的延伸,它们“将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向城市拓展,将‘进城农民’及其流寓的城市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3]。如果将江苏作家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创作放在20世纪乡土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中审视,其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持续关注,显示了它独特的视角(本文从广义的角度采用视角这个概念,即看问题的角度)。文化视角是“五四”时期的小说家观察农民的主要角度,“从‘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开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最早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形象,从民族文化历史时代的高度对‘农民意识’进行无情的揭露鞭挞”[4]。鲁迅更关注的是《故乡》中的闰土精神上的麻木,而非物质上的贫困。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在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谱系中以其对农民精神世界的关注,显示了其独特的审视眼光,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这种“内部”叙事特征尤为明显。范小青的《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和《这鸟,像人一样说话》、赵本夫的《洛洛》和《寻找月亮》、李洁冰的《天堂入口》等,均涉及到农民工精神层面的诉求,表现出了江苏作家独特的视角。
农民工进城后的身份认同危机,是近年来江苏作家农民工题材小说始终关注的一个焦点。农民工进城以后,对城市的陌生感以及城里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使这群乡下人承受着各种精神压力,他们一直在追求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城里人”。《洛女》(赵本夫)、《天堂入口》(李洁冰)、《这鸟,像人一样说话》(范小青)、《城市之光》(范小青)、《安岗之梦》(赵本夫)、《鸟背上的故乡》(胡继风)等作品,通过生活细节揭示了一种以身份认同为表现形式的城乡价值冲突,这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除了工作之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种精神平等的诉求。
《寻找月亮》中的月儿一直努力想变成“城里人”,当钱坤在“月牙儿休闲中心”找到月儿时,月儿给了钱坤一个纸条:“钱老师,你不要再来了,我还没有变成城里的女孩子,他们不让我做城里的女孩子,说这样才好挣钱,我一定要做城里的女孩子,等我挣足了钱就能做城里女孩子了,还有二年,我去找你,你还会喜欢我吗?”《洛女》中的洛洛每晚捡垃圾回来一定要洗澡,每晚洗澡以后,她都会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去逛街,其衣着打扮和街上的女孩子并无二致,但后来其身份被一个女孩无意之间发现,女孩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洛洛所有的朋友,于是他们愤怒了,把洛洛带到一个溜冰场,不由分说就把她打了一顿,骂她是个骗子、贱货,说以前吃过她买的东西恶心,现在想起来就想吐,说她根本就不配和他们做朋友。《天堂入口》中的仲开林从矿场里死里逃生,流落到城里,沦为乞丐,被城里姑娘娄晓敏搭救,他努力想获得一个城里人的身份,想跟娄晓敏在身份上对等;后来在仲开林的“搏命”中逐步消解了他们之间身份的差距,娄晓敏最终才知道这么多年的善举叠加,并没将她托到天堂,她走过九十九级台阶,却在最后一蹬拾级而上的时候,鬼使神差地跌倒,地狱之门正朝她訇然洞开。《欲望之路》中,农村出身的邓一群大学毕业后,在权力机关挣扎,并且最终“成功”变成“城里人”。《这鸟,像人一样说话》讲述了由一件小区失窃案引发的“外地话”和“本地话”的故事,语言成了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说本地话的本地人是好人,外地人是“贼”,这个无形的标签也突显了城乡之间的对峙。范小青《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中的老胡进城以后,先在一处居民区拆迁工程干活,这里的“居民丢失了东西不问青红皂白就怪到农民工头上,他们用当地的方言说农民工的很多坏话”,这使得老胡如“芒刺在背”,后误买赃车被冤枉成偷车贼,却无力反驳,自此以后,老胡在城里手足无措,在拿到厨师结业证并找到一份厨师工作后,仍如坐针毡,如作贼一般,心理产生了扭曲。《城市之光》中,田二伏被冤枉偷车子时,城里人是这样说的:“外地人贼胚。乡下贱骨头。偷了东西还赖。贼骨头要请他吃生活的。不吃生活下回还要偷。外地人来了,我们就不太平了。外地人来了,我们就不安逸了。外地人不来,我们门也用不着关的。外地人不来,我们不要太定心哦。……”农民工为了改变生活贫困的状况,带着梦想来到城市,可是城市的现实却残酷地宣告了他们苦难生活的继续,“城市之光”诱惑着乡下人“像鸟一样飞来飞去”,乡村人把“我城”想象成“城市之光”,但事实上,城市不是他们的“我城”,“城市之光”也只是他们的幻觉。
二、女性视角:女性农民工的城市挣扎
女性视角也是江苏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常用视角,“因为她们不仅是构筑故事的最佳方式,同时又是透视乡土与城市的最好视角”[5]。江苏作家笔下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农民工形象,赵本夫《寻找月亮》中的月儿、《无土时代》中的刘玉芬、《洛女》中的洛洛、范小青《城乡简史》中的王才老婆、《城市民谣》中的林红、《城市之光》中的马小翠和荷叶、《父亲还在渔隐街》中的娟子、余一鸣《不二》中的孙霞、《淹没》中的大兰子和刘冬梅、胡继风《鸟背上的故乡》中的翠珍、李洁冰《青花灿烂》中的青花、罗望子《非暴力征服》中的乔乔和柔方、陈武《换一个地方》中的于红红和蔡小菜、顾坚《青果》中的银凤和春英、徐玲《流动的花朵》中的王弟他妈、王大进《幸福的女人》中的那个女人、荆歌《爱你有多深》中的马华、巴桥《姐姐》中的阿珍以及《阿瑶》中的阿瑶、王涌津《夏萤》中的玉萤、《流浪脚手架》中的玉兰、《心碎的青春》中的玉琴、《秋千》中的玉秀、《乌金泥》中的玉芬等。这些小说既有物质上对底层农民工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更有对女性农民工精神上诉求,表现了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农民工城市境遇的困窘。
女性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时,她们所面临的处境比男性农民工更为严峻。因为性别的差异,女性农民工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在物欲的诱惑之下,在金钱与伦理道德的两难抉择中逐渐沉沦。赵本夫《寻找月亮》中的月儿,在“月牙儿休闲中心”做了迎合城里男人“口味”的舞女,因为城里男人“已经恶心那些刮掉眉毛刮掉腋毛甚至刮净全身体毛的女子,现在要看看一个带着山野气的毛绒绒的真女子,就像吃够了美味佳肴的城里人要改改口味吃点野味”。余一鸣《不二》中的孙霞在城里做生意,利用自己的相貌勾引男人,以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利益,身体是她唯一的资本,她只能抛弃一个女性应有的情感和尊严,游走在一个个欲望的陷阱里,在满足别人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目标。陈武《换一个地方》中的蔡小菜,被生活所迫,只能靠出卖色相讨生活。范小青《城市之光》中的荷叶在歌舞厅打工,她只想在城市里多挣点钱,找个城里人嫁了,然后让父母也过城里人的生活。王大进《幸福的女人》中的“那个女人”,在城市中做了一名卖淫女。赵本夫《无土时代》中的小简在歌舞厅里上班,因为喜欢有钱的感觉,于是沦为“三陪”。王涌津《秋千》中的玉秀进城打工,最终沦为卖淫女。这些女性为了金钱,干着低贱的工作,甚至靠出卖身体过日子,这让人们看到了女性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心酸。
作家笔下也不乏一些善良淳朴的女性农民工形象,她们独立自主,在城市的种种诱惑下尚能不断追逐自己的梦想,“她们进城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乡村文化语境进入城市后,用自己的勤劳实现自己的价值”[6]。陈武《换一个地方》中坚守自己本性的于红红、胡继风《鸟背上的故乡》中节俭持家的翠珍、赵本夫《无土时代》中的希望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文秀、顾坚《青果》中的银凤及春英等,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女性代表,她们朴实、善良、勤劳,没有城市女性的娇气,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不懈努力。她们的奋斗故事,或多或少向读者传达了作家们对此类群体的温情关怀。
三、农民工子女视角:无处安放的“流动花朵”
当下,农民工子女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农民工家庭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被托付给老人和亲戚照顾,像野草一样生长,在亲情和监管双重缺失的情况下,这些孩子的心理和生理容易发生畸变,甚至走向堕落。这些孩子的父母,其本意几乎是一致的,都是想进城赚钱,从而能够给孩子提供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事与愿违,物质上的富裕换来的却是情感和精神的荒漠化。而流动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在城市所面临的是教育问题(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资源匮乏)以及城市适应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进行研究剖析,江苏作家则通过小说文本把这一问题演绎出来。
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形象,留守儿童有王大进《花自飘零水自流》中的大秀和二秀、王巨成《穿过忧伤的花季》中的罗大勇和陈军、陈武《丁家喜和金二奶,还有老鼠和屁》中的大左、胡继风《鸟背上的故乡》中的桥桥以及百合、小米、壮壮、胡小榆、丑蛋、黑妮、刘青稻、施大毛、菱花、田乐乐、宁弯弯等。流动儿童有胡继风《鸟背上的故乡》中的胡四海、范小青《城乡简史》中的王小才、徐玲《流动的花朵》中的王弟和刘端端、黄国荣《城北人》中的一群流动儿童、王一梅《城市的眼睛》中的朱迪和毛威等。
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些小说文本中的留守儿童大多处于“空巢家庭”“隔代抚养”的状况,长期缺少父母关爱,生活条件艰苦,心理和生理方面都出现问题。《跟小满姐姐学尿床》里的小米觉得妈妈像个小偷,总是偷偷摸摸地溜走了,小米每次都牢牢搂着妈妈的脖子睡觉,但早晨一睁开眼,妈妈还是不见了,她非常想念妈妈,终于想到用尿床把妈妈留下,结果换来的却是妈妈的责骂。殷健灵《蜻蜓,蜻蜓》中的安安,八岁时妈妈到城里打工,安安从小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安安打心眼里讨厌这个“狼外婆”,她故意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整日都不和外婆说话;妈妈放在原处的梳子、衣服、被褥,安安一点儿都没有动,还像妈妈走前那样整整齐齐,安安每天都要把妈妈的照片看上很多遍,她就这样一个人呆着,谁来也不说话,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呆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封写给妈妈的信》中的百合被寄养在叔叔家里,百合性格孤僻自闭,她觉得妈妈就像一个客人,只在过年时才来串门;在给妈妈的信里,百合写道:“妈妈,一只秧鸡都知道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你连一只秧鸡也不如……”
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城市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也同样不容乐观,这些“流动的花朵”在面对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市时,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鸟背上的故乡》中在路灯下学习的单丹丹和怯懦无助的胡四海、《流动的花朵》中自卑又坚强的王弟、《城市的眼睛》中无法正常入学的朱迪等,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些小说文本都突出刻画了城市流动儿童所面临的生活、心理、教育等方面的状况。《鸟背上的故乡》中,胡四海从小在城里长大,因为长期跟随父母在外漂泊,他的普通话夹杂着全国各地的口音,遭到了城市孩子的嘲笑;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说自己是小胡庄的孩子时,村庄的孩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对小伙伴们熟悉的田地、河畔、偷苹果、捉泥鳅等一概不知;爸爸告诉他:“下次再有人这样问,你就说你是城里的孩子。”但这更让胡四海感到难过:“假如自己是城里的孩子,自己为什么要去读‘农民工子弟学校’呢?城里的小学为何不要我?”“我既不是城市的孩子,也不是村庄的孩子——对于城市来说,我只是一个来自村庄的客人,就像对于村庄来说,我只是一个来自城市的客人一样。”如此尴尬的两难身份,正是当下农民工及其子女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流动的花朵》中,学校将王弟他们这群“外地生”赶出原来的教室,放到一起组成新的班级,最终被驱逐出公办学校,来到了所谓的“新市民学校”;王弟对于这种划分有着强烈的不满,那些看起来旧旧的桌椅在他们眼里就是城里孩子用剩下的,他们一个个叫嚷着:“什么新市民学校嘛!什么绿叶学校嘛!连课桌椅都没有!我们站着写字吗?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啊?”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最后,小说文本也通过政府、老师以及城里孩子左伟等给予王弟他们一些帮助,让人们看到了城市温情的一面,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也不乏阳光。
参考文献:
[1]张宪.打工文学是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N].工人日报,2008-03-14(6).
[2]周水涛.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现状及特征考察[J].小说评论,2008(6):82-86.
[3]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J].学术月刊,2010(1):110-118.
[4]肖佩华.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流变轨迹[J].江西社会科学,2000(6):32-36.
[5]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J].文学评论,2005(4):32-39.
[6]吴妍妍.近年来女性农民工文学形象考察[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12):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