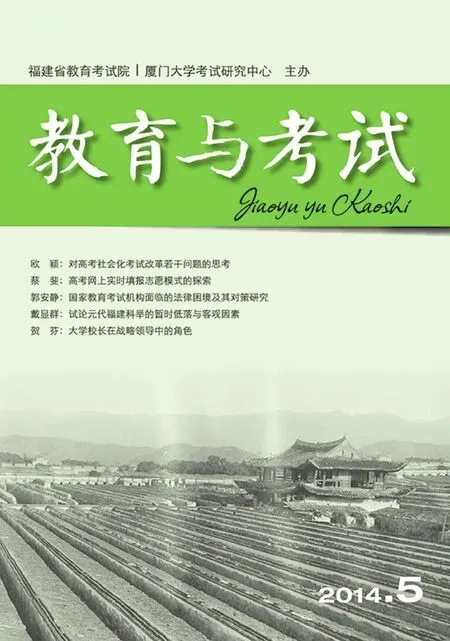从选拔人才到培养人才
——高校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型
2014-04-17解德渤
解德渤
从选拔人才到培养人才
——高校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型
解德渤
“钱学森之问”“新李约瑟命题”,这些关于中国能否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的质问,引发了人们对教育的诸多思考。文章通过“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脉络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双重理性”的逻辑脉络对该问题予以尝试性回答。
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创造人才;人才培养理念
“钱学森之问”已经引发了人们尤其是高校管理者以及教育者关于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的诸多思考。但是反观现实,我们发现目前高校的育人理念较多地倾向于如何选拔优秀人才,而非如何去创造优秀人才。选拔优秀人才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前提与基础,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水平考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考生的真实水平,但并不能全面地反映考生水平。这也正是近年来高考备受诟病且亟待改革的原因之一。培养优秀人才同样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应有之义。当前学术界虽积极探索、努力追寻,但价值取向与行动效果却不容乐观。反观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可谓璀璨耀眼,那时我们并不缺少大师,也不缺少优秀的学生,可是为什么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却在培养拔尖人才上“无能为力”?本文通过“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脉络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双重理性”的逻辑脉络对该问题予以尝试性回答。
一、价值理性指导下“培养优秀人才”的铮铮业绩
就思想领域而言,民国时期是一个中西思想碰撞、交融的时代,一个教育发展独立、自由的时代,一个学术大师云集、创生的时代。当然,这种大学的自治权以及学术自由与特定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不无关系。但在一定程度来讲,文化因素的影响无疑是更为深刻与持久的,即思想观念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理性的育人观念是这一时期教育成就显赫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民国时期真正意义的高等教育改革开启于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之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抨击了“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1〕的治学痼疾,至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大学之自治、学术之自由、人才之培养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育人理念是在价值理性指导之下的,倾向于“如何培养优秀人才”而不是“如何选拔优秀人才”。这种价值理性表现为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绝对价值所持的自觉信仰,这种行为并不考虑有无现实的成效而主要关注行为本身的意义,或者讲价值理性关注的是一种更为符合长远意义的目的合理性〔2〕。在这种价值理性引导下,这一时期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一大批大学校长以及知名学者在人才培养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努力。从“破格录取”和转系制度上,我们便可“窥其一斑”。
不同的办学主体、不同的办学层次以及特殊的政治自由环境为高校自主招生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初步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招生过程破格录取、“特事特办”的现象时有发生,旨在突破传统的人才选拔标准以不拘一格招收人才。“五四运动”之前,胡适同蔡元培商定破格录取了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的罗家伦,罗家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长。1929年,钱钟书数学仅得15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1931年,吴晗文史、英文满分,而数学仅6分;钱伟长国文、历史均满分,而英文得0分,无缘北大,二人均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3〕。诸如此类,“破格录取”就是通过选拔的方式培养优秀人才(为培养而选拔),但目前部分高校是通过选拔的方式选拔优秀人才(为选拔而选拔)。这恰恰是违背了选拔的初衷。
如果说破格录取是对特殊人才的一种尊重与保护的话,那么转系转学制度则是赋予优秀人才的另外一种自由与“救济”。其中,转系制度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体现得尤其突出。该制度的受益者为数极众,如李健吾、钱伟长、李赋宁、钟开莱、何兆武等。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除季羡林外,林庚、吴祖缃、李长之都是转系生。转系与转学制度打通了人才兴趣的专业壁垒以及人才发展的院校壁垒。当时北大、清华、中大等名校均有转学考试。比如,胡风1925年考取了清华大学英文系,可是他放弃了清华的学籍,而进入北大预科读书,1926年又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还有北大的李长之,中大的巫宝三,南开的曹禺、孙毓棠、何炳棣和宗璞,上海的于光远、王铁崖等都转往清华大学。日后的朱光亚、李政道也是因转学而成为西南联大的学子〔4〕。在一定程度而言,转系转学制度使得优秀学子不至于因各种外在的制度因素而遭埋没,这对于今天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二、工具理性支配下“选拔优秀人才”的阵阵痛楚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自主探索的关键时期。但是与政治经济不同,教育不应该也不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提携式发展”,它长期的“培育式发展”的过程,需要的是不过分计较得失的心态胸怀与价值理性,但是目前在喧嚣的市场环境下,部分学校教育同样是“浑身铜臭味儿”,高等教育也不能幸免,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亦步亦趋。不同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把对行动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的思考作为取向,不断对各种可能的目的与实现目的的相应手段、措施以及行动的结果进行理智上的权衡〔5〕。但在大多数情境中,在功利主义的诱导下,工具理性的扩张似乎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价值理性的式微。
自恢复高考以来,我们秉承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较多地采用国家统一高考的方式实现人才的选拔,当然近年来自主招考制度也逐步兴起。统一高考在实现人才选拔功能的同时,也扮演了塑造畸形人才、埋没潜在人才、社会阶层再造、变相人才外流的幕后“帮凶”。其中,高考固定的思维模式以及制度的不可抗拒使得较多的学生“不厌其烦”地演练各种试题而无暇通识教育的发展,即便存在所谓的发展学生身心的部分课程,也只是做做形式或者为高考加分而已。统一的命题模式与录取标准使得部分特殊人才埋没于高考之中而不得“鱼跃龙门”,这就使得部分学子尤其是寒门子弟不仅不能通过高考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反而高考无形中成为社会阶层再造的一种工具。此外,部分优秀学生迫于高考压力或者旨在实现更好的发展选择出国留学,从而出现“育天下英才而送走之”的窘境。固然,出国留学是个人的自主选择,但对于国家来讲无疑是莫大的人力资本损失。
“成就奖励”同样是工具理性支配下的高等教育的特有产物。体育明星、娱乐明星在体育圈或娱乐圈取得一定的成就后,为了奖励这些人所做的贡献或者取得的成绩,通过教育的形式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体育明星如邓亚萍就读清华大学,姚明、刘国梁、丁俊晖就读上海交通大学,李宁就读北京大学,刘翔就读华东师范大学等的本科、硕士或者博士。当然更有甚者,娱乐明星担任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聘成龙、南开大学聘唐国强、中国人民大学聘周星驰、国防科技大学聘赵本山、暨南大学聘张铁林、安徽大学聘牛群、海南大学聘水均益、海南师范大学聘曾志伟、四川师范大学聘李湘等等。这些现象不得不让我们感慨:大学你怎么啦?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形式奖励这些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为什么偏偏要颠覆“高等教育”的神圣。现象的背后是基于工具理性扩张的利益链条。试想大学是否应该这样,在这种工具理性扩张的理念下大学到底还能走多远。
三、双重理性平衡下“创造优秀人才”的理性回归
纯粹的价值理性或工具理性都无法在长远利益下实现对优秀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唯有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在人才选拔上,我们既要坚持国家统一高考制度又要积极探索自主招生模式,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在统一高考与自主招生之间,形成人才选拔的互补,从而使得“人尽其才”。我们应注意到统一高考由于区域不平衡造成的“学优而不同”的结果,还应不断反思自主招生模式推行的意义。但是,当前部分自主招生院校仍然是按照统一、标准化的通才模式进行选拔,“自主招生”只是统一高考的“变种”形式而已。因此,在人才选拔机制上,我们应在统一与多元、效率与公平、主体与互补上努力寻求契合点并使之保有一定的张力。
在人才培养上,我们既要加强通识教育又要积极开展专业教育,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强调“一般的普适价值”,后者强调“个别的特定意义”。然而,在操作层面上最大的症结点在于,实用主义“大放厥词”的今天,秉承永恒主义哲学观的通识教育其价值往往被忽视,孰不知通识教育是将人塑造为“完人”的最有效的教育形式,而非专业教育——将人塑造为“专人”。在1941年清华30周年校庆时,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指出,通识教育是“—般生活之准备”,而专业教育是“特种事业之准备”。因而,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6〕。因此,在人才培养机制上,我们应客观看待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价值地位,而非以眼前的利益作为价值取舍的标准,着力把握“通”与“专”、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价值链接,以优化教育格局、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人才创造上,我们既需要探求普遍真理又要积极投身实践活动,正确处理知识积累与实践探索之间的关系。知识积累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是创造人才的有效途径。但时至今日,知识未尽、实践不力。“今大学中之教育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利之一端也。……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甚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7〕因此,在人才创造机制上,我们需要通过革新教学方法、改善师生关系等途径,在知识与实践之间搭建“沟通”与“对话”的平台。
人才之养成唯有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并保有一定的张力,也就是坚持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才是教育改革尤其是高校育人理念变革以及育人行为转向的根本途径。换言之,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与人才创造改革工作应在永恒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共同指导下稳健前进。
〔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M〕.蔡元培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5-6.
〔2〕〔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3、48.
〔3〕〔4〕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J〕.开放时代,2009(1).
〔6〕〔7〕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责任编辑:郑芳)
解德渤,男,河北衡水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厦门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