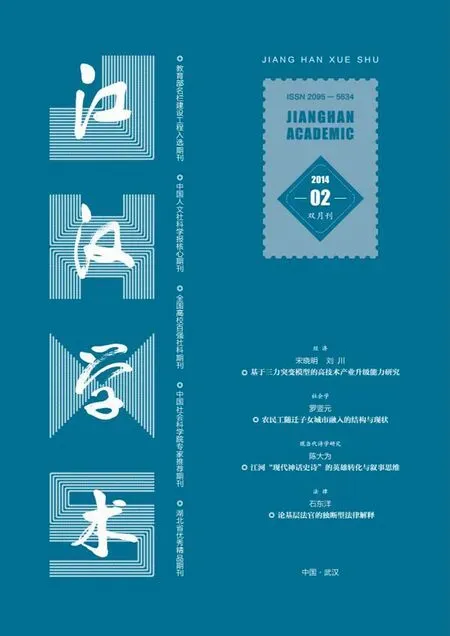论顾城的“自我”及其诗歌的语言
2014-04-16岛由子
[日]岛由子
(近畿大学 文艺学院, 大阪 东大阪 577-8502)
顾城1956年生于北京,1993年在新西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期间留下了很多诗歌、散文、小说和绘画。现在我们按年代顺序来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诗歌中的语言经过了几次显著的变化。或许已有很多读者也发现这个变化跟顾城的诗歌观念,尤其是他的“自我”论有密切的关系。
本论文根据顾城的诗歌论来整理顾城的诗歌,尤其针对它语言和形式的变迁,来考察顾城始终探求的诗歌理想和他的创作留给现在和未来的读者的课题。
另外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篇论文里把顾城的创作时期划分为各个阶段所依据的资料是顾城1993年所接受的,由张穗子所做的采访——《无目的的“我”》[1]232-236。
一、诗人的诞生:“自然的我”
顾城的创作是从听到自然中秘密的声音开始的[1]232。他记录这个大自然给予他的启发时,选择了诗歌这样的表现形式,这跟他父亲顾工是著名诗人这样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关系。
顾城少年时代的作品里大部分都是歌颂大自然的,而且形式上虽然不规则,但有些诗歌押韵,语言表现超出常规,已经具备了诗歌形式。
下面引用他1968年写的《星月的来由》
树枝想去撕裂天空,
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
它透出天外的光亮,
人们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①
也许不用笔者指出,这首短诗的语言不合常规。比如说,第一行可以看出拟人法,在第二行中诗人把天空处理为可以穿孔的东西。这些都是常见的诗歌技巧。而且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十二三岁,可以认为他当时已掌握了一些诗歌技巧。但如果粗略地总结他少年时代的诗歌作品的话,可以说他的语言已不再拘泥于单纯为了表达的语言规则了。其原因或许与他的年龄有关,因为儿童的语言能力还不发达,他们要表达自己时只好拼凑自己所认识的词汇,所以顾城少年时代的诗歌语言或许还没有超越儿童特有的语言表现范畴。
另外,这首诗的每行末尾都是鼻母音kong,long,liang,xing,诗歌整体的韵律也很好。他第一次创作诗歌是在1962年,是顾城口述,他姐姐记录的作品②。而且在顾城小时候,向父亲报告自己创作诗歌时说“我又想出来一首诗”[2]147。在还不完全识字的少年时代,顾城更加关心语言的发音和节奏。
顾城自己也说过,他儿童时代自己创造出自己的语言试图跟别人说过话[3]83,也在“月光”的读音中陶醉过[3]84,他对语言抱有超越传达功能的感觉。他这样独特的语言感觉和使用一般随着上学,跟周围的朋友和家人交流的过程中会慢慢被修正的。但是,顾城的儿童时代正处于用顾城的语言来说是“文化空白”、“现代的原始状态”[4]264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在写下《星月的来由》的第二年,就是1969年,他们一家随父下放到了山东的农村。
关于创作开始的时期,顾城指定的是一家下放到山东的农村时代,即1970年前后[5]。
到了山东的农村,因为很少人来接近他一家人[2]148,也“没有烧的,没有吃的”,“书呢?自然没有”,顾城自己变得“像枯枝那么脆弱”,但随着春天的来临他发现那里富有给自己带来灵感的大自然[3]89。他说“在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一种生命的感觉就醒来了”。他继续叙述着自己的体验:
有一群鸟慢慢慢慢向我飞来,……在我周围成千的鸟儿对我叫着,我感到一种激动。……我却有一种快乐、一种想说话的愿望,我想回答它们,回答它们的叫声。我觉得它们说着我不懂的语言,召唤我,但是我说不出话来……
它们走了,我觉得在那个瞬间我好像聋了,我听见另外一种声音,天、地、宇宙万物轻柔的对话,它们做着各种手势,它们之间的相思和默契;草因此生长,开出花朵,鸟因此飞来又飞去。这是自然毫无遮掩的秘密。我拿起笔找到一些字,开始写诗。
将近十五岁的一个夏天,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我写下了这个声音,就是1971年我写的《生命幻想曲》。[4]266
下面引用顾城这首初期代表作《生命幻想曲》(1971)的第二到第四部分:
没有目的,
在蓝天中荡漾。
让阳光的瀑布,
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
它拉着我,
用强光的绳索,
一步步,
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
我被风推着,
向东向西,
太阳消失在暮色里。
黑夜来了,
我驶进银河的港湾。
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
我抛下了
新月——黄金的锚。
在这首诗里描写的是,少年诗人自由地在大自然中嬉戏,体验地球昼夜的变幻,最后像诗的末尾“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的这样,觉悟到自己的使命。
这个作品里面也富有拟人、通感等语言和诗歌技巧。还有,对第三部分第一行的“太阳是我的纤夫”这个表现,顾工这样回忆道:“但这些诗句,那时是决不能发表,也不能让人看见,光是‘太阳’二字,就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杀身之祸。”[6]这样看来,农村时代的顾城的诗歌在语言规则和时代背景上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他独特的语言感觉,由于时代背景和孤独的环境“有幸”没有被修正③。他后来为了回到从前那个时代的创作形态,在新西兰激流岛上试图进行原始生活。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顾城在其农村时代形成了他自己创作的基本走向。
《生命幻想曲》是顾城在1971年夏天,跟父亲放猪的时候所写的。他后来如此回顾当时的情况:
我累了就躺下来,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天上睡觉。它睡着了就慢慢落下来,在接近河水的地方,被自己的影子惊醒,这时我感到了另一个我;远处的树林在响,就像我的手在动,河水在流淌中轻轻冲击沙地,粘土的河岸,就像我抚摸自己的膝盖;我像阳光一样在大地上行走,宁静如云。作为一个人的恐怖、害怕、矛盾都没有了,只有一个感觉,我要做的一切已经做了,所以正在开始。[4]266
这首诗不但成功地记下大自然给予诗人的启示,还表现着诗人跟自然合为一体的体验和喜悦。最后诗人逐渐离开这样合为一体的状态时,读者也可以读到少年的自我在逐渐觉醒。顾城把当时的“我”概括地叫做“自然的‘我’”,说明“这个‘我’与包括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兽等在内的‘我们’合为一体”[1]232。
不过,这样跟大自然自由交欢的顾城要迎接一个大变化了。1974年顾城一家回到北京。
二、回到城市:语言的规范化和“文化的我”
顾城1974年回到北京,他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他说“这时候我开始要对人说话了,我遇到了困难。鸟说话是自然的鸣叫,而人说话是有规则的,所谓语言的法则。”从山东农村回到北京,就是说从大自然回到城市,抱有自己的语言规则的顾城发现自己不能跟周围的人说话。但他“必须说话,并且生活”,所以为了跟人交流开始读书[4]267,也开始积极地加入社会。
这样环境的变化中,还有“文革”即将结束的时代背景,影响了他很多。“我在想祖国。在想她给予我们的,和需要我们给予的”[3]98。把动物和昆虫设定为主人公的寓言诗和歌颂革命家、红卫兵的作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作品在农村时代几乎都没有。顾城后来把当时的自己叫做“文化的我”,加上说明说:“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有很强的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我开始从人的角度评价这个世界。我注重对人说话。”[1]233看他这个发言,或直接读他的作品,读者都可以发现诗人对话的对象从大自然转移到人和社会。
他的代表作《一代人》(1979)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作的。由于题为“一代人”,这首诗一直被解释为:尽管经历过被象征为“黑夜”的“文革”,牺牲了儿童时代和青春,拥有了“黑色的眼睛”的“一代人”,还要追求象征“光明”的希望和理想的强烈意志。上面已提过,顾城把当时的自己叫做“文化的我”,他还说:“这个‘我’与当时能和我在精神上相通的‘我们’合为一个整体”。[1]233所以可以说《一代人》里的“我”同时也指同世代所有的青年,从这里也能看出顾城创作对象的变化。而且“黑暗”和“光明”的对立这种表现不是顾城的诗里特有的,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比喻④。
此外,通过发表作品认识的诗友对他也很有帮助。通过跟诗友交流,顾城也开始接触到诗歌技巧。顾城说他大概在1979年初正式开始接触诗歌技巧,也提到波德莱尔和他的“通感”[7]。不过,“通感”已在他早期、就是回到北京以前的作品里很常见。他回到北京后学习具体的诗歌技巧和理论这个经历,可以说给了他的创作不小的影响。
下面引用的也是顾城的代表作《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的第六部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使用“通感”,也可以看到诗人对社会和人类的使命感: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我想画下风
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岭
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
画下大海——
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
顾城在这首诗里设定自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或许这样的自我设定跟他面临青年期有关,“文化的我”诞生的原因,不仅是环境的变化,或许与他的年龄也有关联。
“朦胧诗论争”时,顾城也用“自我”这个词进行过反驳⑤,但顾城自己也逐渐对“自我”开始抱有怀疑,这个怀疑又给他带来了一次很大的创作变化。
三、对自我的惶惑:“反文化的我”
值得考察的是,顾城在说明引起广泛争论的《小诗六首》(1980)的时候,明确写着“最初触发这些小诗创作意念的,并不是理性”[8]。再如他的《一代人》(且不论其题名和后来普遍的解释),就是在非理性的世界(梦)里得到完成的。他父亲顾工这样记录顾城当时的创作方式和作品《一代人》(1979)诞生的情况:
儿子白天都是朦朦胧胧,夜晚却精神特大。他室内的灯光几乎都是彻夜不眠的。梦幻,却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在伴随着他,萦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最好的时刻。儿子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而是在枕边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起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名诗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涂抹到墙上去的……⑥[2]150
在作品《一代人》的创作现场,当然只有顾城本人。但考虑顾城的诗歌走向及后期展开的过程,顾工这段话还是比较可靠的。
顾城在散文里说,他1981年以后开始问自己为什么写诗,开始“惶惑”[9]139。他发现他回北京后依靠的“文化”不能完全说明他的创作体验。在这样的“惶惑”下,他开始对“文化”抱有怀疑,有一天他发动了“反文化的我”,破坏了语言的连接。顾城还说,《布林》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1]233。这个《布林》指的是1981年开始被创作的组诗《布林的档案》(1981—1991),“布林”是作者小时候想像的一个“孙悟空、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像下面那样继续描写其创作体验:
时间的活塞一直推压到1981年6月的一个中午,我突然醒来,我的梦发生了裂变,到处都是布林,他带来了奇异的世界。我的血液明亮极了,我的手完全听从灵感的支配,笔在纸上狂奔。我好像是自焚,又好像是再生,一瞬间就挣开了我苦苦索求的所有抒情方式。我一下就写出了五首《布林》,后来又陆续写了十几首,基本完成了一次自我更新的试验。[10]940-941
组诗《布林的档案》形式上是一个以“布林”为主人公的童话形式的作品。这个组诗以前顾城也写过很多以动物和昆虫为主人公的寓言诗,但都是描写动物和小虫子们的无知和愚蠢来批判社会的,有明确的主题。换句话说,都表现着作者要参加社会的明确的意志和对社会变革的使命感。
但是,组诗《布林的档案》全体展开的荒唐滑稽的语言和作品世界,好像是在嘲笑着社会的认知和理性,再加上在嘲笑着“文化”本身。下面引用组诗第一首《布林的出生及出国》(1981)的开头:
布林生下来时
蜘蛛正在开会
那是危险的舞会,在半空中
乐曲也不好听
布林哭了
哭出的全是口号
糟糕! 赞美诗可没那么响亮
接着他又笑了
笑得极合尺寸
像一个真正的竞选总统
于是,母马认为他长大了
他一迈步就跨出了摇篮
用一张干羊皮
作了公文包
里面包着一大堆
高度机密的尿布
他开始到政府大厦去上班
顾城自己也认为这个组诗“反思、反抒情的光亮太强了”[10]941,但是反思、反抒情何等强烈,反思、反抒情,换句话说“反文化”的后面都藏有作者的自我和主观。所以读者在这个组诗荒唐的语言里起码可以读出诗人对以主观的自我为主的抒情诗表示某种怀疑和反抗的态度。而且诗人也在组诗的一首诗里让布林表达“自己?自己是什么东西?”[11]。 就这样,顾城进入到“反文化的我”的阶段,“完成了一次自我更新的试验”[11]941。
但是,顾城很快发现“反文化”无法解决他的“惶惑”。
1983年顾城“生病”了。17岁时回北京的顾城,开始在社会里生活。他本来在农村/儿童时代很自由地运用语言,但回到城市他的语言因为必须跟人交流而慢慢被规范,让他无法呼吸。他“生起病来,看见自己像一个小虫,在字里爬”[12]200-201。
顾城从农村回到北京后的诗歌作品大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社会色彩的、有明确主题的诗,另外一种是意象诗。这两个方面表示的是,顾城一方面由于回到“文化”里生活,学好了以表达为主的日常语言,积极参加社会,但同时一方面他从自己的诗歌体验也深刻知道诗歌是从超越“文化”,就是超越社会或理性的地方来的,所以他“惶惑”在语言的理性和非理性,就是日常语言和诗的语言的矛盾中。
下面引用1983年被创作的《我不知道怎样爱你》的开头:
我不知道怎样爱你
走私者还在岛上呼吸
那盏捕蟹的小灯
还亮着,红的
非常神秘,异教徒
还在冰水中航行
在兽皮帆上擦油
在桨上涂蜡
把底舱受潮的酒桶
滚来滚去
我不知道怎样爱你
岸上有凶器,有黑靴子
有穿警服的夜
在拉衬衣,贝壳裂了
石灰岩一样粗糙的
云,正在聚集
正在无声无息地哭
咸咸地,哭
小女孩的草篮里
没放青鱼
我不知道怎样爱你
顾城当时正跟谢烨谈恋爱(同年结婚),但这首诗与其说是直接表达爱情的“情书”,不如说表现着谈恋爱的情绪带来的意象。同时,可以看到的是,顾城通过这样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创作,克服了(给他灵感的)大自然的丧失,创作又达到第二次高峰。
可是,意象不断涌出来,诗人不久发现自己控制不住意象,感到不安。所以他像在诗的末尾说“别说了,我不知道自己”⑥这样勉强结束了这首诗的创作。
他这样沉浸在内心世界得到灵感写诗,逐渐确信“自我”还有很多自己不能控制的非理性的部分。顾城谈到“为什么要表现自我”的问题时说过“更好的提法是,不是说表现,而是完成”[13]的理由也在此。顾城不但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创作诗,同时也要掌握诗的来源。所以,顾城探求的方向从理性的自我(“文化的我”),经过对理性的反抗(“反文化的我”),最后进入到自我非理性的部分,就是说“无我”[1]233的阶段。当然“无我”的“我”指的是理性和主观的自我,从这个阶段后他的作品里主观的“自我”消失,语言和意象的连接也消失,他迎接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四、摆脱自我的尝试:“无我”和超现实主义
摆脱“惶惑”的先兆也是在梦里得到的:
有一天我睡着了。觉得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胸口,很重,我就开始唱歌,唱一个哇哩哇啦的歌,没有内容,像我小时候学鸟叫一样,我于是醒了。我特别快乐,就听见一个人对我说:“关键不是唱什么,是在六点钟的地方唱歌。”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件事情。[9]143
虽然笔者不能完全解释和说明顾城这句话,但起码可以说顾城通过这个体验明白的是,语言或写诗最重要的不是说什么(主题、主观),而是要说起来。
然后,有一天别的声音来了。这就是他1986年写的《滴的里滴》。
这首诗已在笔者另外论文里分析过[14],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但笔者在这里要再次确认的是,顾城在创作组诗《颂歌世界》(1983—1985)和包括这首《滴的里滴》的组诗《水银》(1985—1988)之前,虽然已被松懈了很多,但是从诗里还可以读出语言或意象的连接。但创作这两个组诗以后,不但是语言,意象的连接也都消失了。换句话说,诗人主观的“自我”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滴的里滴》的创作体验也是梦境体验。下面引用顾城提到的向着《滴的里滴》的过程和其创作体验:
1985年我感到我几乎成了公共汽车,所有时尚的观念、书、思想都挤进我的脑子里。我的脑子一直在走,无法停止。……最后竟达到了一个疯狂的境地。我打碎了一些东西,超过了极限,我忽然又聋了,又听见一种声音,这一回不是鸟的声音,也不是天的声音,而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危险的声音。这声音到来的时候,我和这个世界的一切关系瓦解了,我处在一个明显的疯癫状态。就在我开始放弃自己的时候,那句话如期到来,我在梦里听到了它。……我终于像一滴水那样安静下来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冲突结束了。[4]273-274
下面引用顾城的《滴的里滴》第二部分:
远远的看是桶倒了
滴
好多精细的鱼
在空中跳舞
滴的里滴
鱼把树带到空中
滴
鱼把树带到空
中
棕色的腿耸在空
中
顾城的后期诗歌和超现实主义的相似性已被工藤明美指出⑧,还有顾城这首诗也根据“梦境”体验写成的事实也支持这个看法。在笔者阅读过的顾城的作品和资料的范围内,目前还没有见过顾城受这些包括超现实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具体证据。不过,顾城曾经提到“现代主义”,说“现代主义艺术确立了一个绝对的死亡”[9]144。
笔者在另一篇论文里把顾城的诗歌向着后期展开的过程跟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出现背景、其具体的实践和挫折做过比较,试图要把握顾城创作的轮廓⑨。现在不知道这个比较还是否有效,但是这个详细的比较让笔者能够像下面这样补充顾城刚才的话,他的意思是:原始时代人类没有理性和非理性明确的分别,或者可以说人类比现在更加自由地往来于理性和非理性世界。但是,随着文明的发达,人的精神逐渐偏于理性,逐渐对非理性开始感到恐惧,要放逐它得到安宁。某种情况下这个尝试很成功,但当这个理性世界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为了突破精神的死路,包括超现实主义的,所谓“现代主义”出现,破坏了文明。人工的文明当然没有生命,所以对于破坏没有生命的文明这个行为,顾城将其表现为“绝对的死亡”。
这跟顾城向后期诗歌展开的过程很相似。他说没有办法对抗现实,就依靠自己的梦想,没有办法改变世界,就依靠文化,没有办法在现实中间实现自己,就想到历史。但他发现依靠自己以外的东西无法解决“生命的矛盾”,后来这个支持物崩塌的时候,他也跟着倒下去。他说《滴的里滴》是“这个崩塌和解脱的声音”[1]274-275。
此外,“死亡”,还有“梦境”世界都是人一定要面对和迎接的体验。顾城和超现实主义者的创作体验以及经过这个体验所创造出来的意义中断的诗句使读者明白,这些东西并不是跟人的生活断绝的,而仅仅是人在文明发达的过程中被封闭的东西。
不过,笔者的目的不是要指出顾城的探求是跟超现实主义者完全一样的,也不是要指出顾城有没有受影响。
五、从“无我”到“没有目的的我”:顾城的“自然哲学”论
顾城的诗歌和语言在向着后期展开的过程中,他同时逐渐开始倾注在以老庄和禅为主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化中。他把这些哲学概括地叫做“自然哲学”,留下了不少文章。
在其中的一篇《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此文以后用略称《自然哲学纲要》)里,顾城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自然哲学”论。这篇文章是他1993年在德国演讲时的报告原稿,或许与演讲的地点在德国有关系,他在里面谈到西方文化,说“西方人偏重于思辩和逻辑,重论证”,也“认为‘有’高于‘无’,更愿意接受有限、明晰的概念”,建立了“精确庞大的体系”。也说这样的想法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但顾城继续说,在近代社会“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就是说科学的发展却让(西方)人面对“科学所发现的那个无情的无限的未知,侵蚀着它关于‘有’和‘存在’既定概念”,所以“如何修补这个体系,以避免未知的侵袭,似乎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项重要的工作”[15]161-162,作为一个解决方法顾城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中国哲学的“自然哲学”。当然,顾城提出的问题不是只属于“西方人”的,是一个当代社会和人类或大或小都面临的普遍的问题。笔者还没掌握好他这个自然哲学论,但现在起码可以说的是,顾城在他的自然哲学论里提到的“自然”是一种精神的和谐、精神的自然状态。他在《自然哲学纲要》里也说明,自然是“中国哲学的最终境界”,还说“它是人对自身观念的解脱,也是灵性对外界世界存在的超越。它是同一的,又是超越有无的,所以也可以说是最初最终的和谐”[15]155。而他在这篇《自然哲学纲要》里所说的“自然之境”可以说是,超越有无的和谐状态,就是没有境界的、超越有无、生死的,“没有目的”的一种心境。
作为实践“自然之境”的例子,顾城在《自然哲学纲要》提起的是中国古诗,他说“中国哲学的自然之境与中国的诗境相合,都是一种无目的的自然关照”,也指出“中国古诗最大的特点是缺失主语”、“少有抒情的‘我’”[15]164,从他这个言说里可以看到顾城为了摆脱“抒情的自我”借鉴了中国古诗。
下面为了再次确认他理想的创作形态,引用一段顾城1987年参加的研讨会发言的追记:
两个雨滴降落到大地上,微微接近,接近时变长,在临近汇合的最新鲜的刹那,他想起他们分离的一瞬。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都作为云、飞鸟、河水千百次生活过;都作为阳光生活过。当你有了眼睛,看世界,闻到春天的气味,听,声音一闪,你就想起了以前的生命。
我对朋友说:诗可写可不写,我可以感到这个光,它像一只金色的鸟,落在我面前,产生了奇迹。
我不要把它抓住、带走,我跟随着它,或者它跟随着我,只有当我们天然合一的时候,诗才成为可能。[12]202-203
从顾城所言的创作体验,我们可以看出,对他来说创作诗不只是探求死、梦等非理性世界。他通过写诗,要超越理性(生、觉醒)和非理性(死、梦)的界限,换句话说,是要超越自我的有无和意识连接的有无,最后从非理性的恐怖中解脱出来,得到安宁。
笔者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他在《自然哲学纲要》里提到的中国古诗的境界与上面引用的创作体验都跟他最早期的《生命幻想曲》的境界和体验很相似。
笔者认为,顾城后期在新西兰激流岛要试图过原始生活的目的也跟他的“自然哲学”和诗歌创作有关。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顾城为了恢复自己原来抱有的自由诗性在新西兰激流岛开始原始生活,经过了挫折后,发现“自然”同时也是一种自己心境的过程。
他在新西兰激流岛开始生活,他抱有“对自然有一种信仰”,“我对我的自性也有一种信仰”,说“我觉得我到了自然界之中我就不再有许多妄想,我到了自然之中,我的生命的自然的美就会显示出来”。
但是,面对现实的自然,他“碰到的是一种更加可怕的毁灭”,他发现“自然并不美好,自然中间有老鼠、跳蚤,并不是我们度假时候所看到的自然”。他接着说:
在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现代文明的情况下,你必须一天到晚要和自然做斗争……最主要的是,我在自然之中,我发现我的本性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属于天的,或者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它是盲目的,它就像蚂蚁一样到处乱爬,像章鱼一样舞手舞脚,它停不下来。我的思想也并没有停下来,思想只是一个借口,当我说“我不要”的时候,我的本性、魂魄依旧在活动,在折磨我,我必须找到一个形式来抵消它……我只是把这种能量释放出去。[1]280-281
顾城以为自己回到大自然生活,可以恢复他初期拥有的灵感。但他那个本性是由于时代背景和他的年龄“有幸”拥有的,他后来经过城市生活,也经过身体和精神的成长失去了这个本性,所以他后来回到大自然时只能发现自己和大自然、儿童时代已经是分离的。
而在他诗歌向着后期展开的过程中,他破坏了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也可以说打开非理性的“门”⑩),所以非理性不断侵入他的思考。
他没有明确说明,但他接着说为了释放自己控制不住的能量,每天打石头。然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专心打石头,忘记自己了。这时他发现了“自然”是一种心境:
有一天我看见钢钎和石缝之间迸出火花来,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山影在傍晚重叠起来,树上一只黑色的鸟停在很大的月亮里,边上的大树已经开满了鲜花(多少天来我并没有注意它)。我像一个婴儿那样醒来了,因为我不知不觉把我的思想、我自己全都忘记了。……我看不见这世界是因为我的心像波动的水一样,当我的心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一切。
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一切都没有改变、消失,但是我看见了它们。[1]282-283
顾城把实现他所说的“自然之境”的“我”叫做“没有目的的‘我’”,还加上说明说;“没有目的的‘我’,则是自由的”,“目的和概念已经不再束缚他,包括生死概念,人类的生存准则和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与他无关;他自性的灵动,使他处在永远的创造之中”[15]165。从他这个说明来看,他的“没有目的的‘我’”就是“无我”进一步发展的“我”。可是,虽然顾城这样在理论上发现了自己创作发展的可能性,但作品里好像并没有实现。
下面引用的是组诗《城》(1991—1993)中的一首《中华门》(1991)第一部分:
是早晨都有的冰雪
一共四个
她总是靠边骑车
小孩跟着攘一大块土
路就成了
据顾城说,组诗《城》的创作也是根据回北京的“梦”体验[16],也说这个“城”是自己的名字,也是北京[17]。从此读者可以理解到顾城在创作这个组诗时也是沉浸在自己心中的非理性世界中,并以语言呈现出来的。
把他的创作体验和组诗的失去意思连接的作品世界结合起来看的话,可以说顾城在创作这个组诗时,只不过是探求自己非理性的世界而已,并没有超越什么界限。
而且,像上述在顾城发现自然这个心境的过程中所指出的那样,非理性世界不断侵入并且“折磨”了顾城,所以顾城说“必须找到一个形式来抵消它”,所以顾城通过创作,就是用语言来修复界限的窟窿。他说“《城》这组诗,我只作了一半,还有好多城门没有修好”[16],他这个组诗的创作只不过是用语言(形式)来修围城的墙壁的门,关起非理性的世界得到安宁。
所以,我们在顾城的诗歌作品里看不到他实现了“自然之境”,或“没有目的的‘我’”的明确的证据,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创作组诗《城》的时候要修的不是围墙的墙壁,而是“城门”。“门”是人自己可以打开或关闭的,所以他要修理城门的意思就是他不但是要把非理性关起来,他还要通过修城门,自己以后自由地穿行于这两个世界,得到控制权。不过,修城门这个行为乍一看是可以超越非理性和理性的界限的,但是,修城门来控制这种心态也证明着诗人属于理性世界/文化,作为人试图控制非理性世界,从而超越理性有无的“自然”的欲望。而且他为了实现“自然之境”、达到“没有目的的‘我’”的阶段,他用的是,文化的象征之一的语言来实现,可以说这导致了他的挫折,也暗示着人类认知的界限。
六、结语:诗人留下的课题
总之,顾城的诗歌形式和语言的变化都跟他的自我论有关,他几个变化阶段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每天依靠的现实生活(理性世界)和(理性的)自我的脆弱。而他通过创作所要探求的是,怎样接受每个人都在内心抱有的非理性,怎样克服对它的恐惧,最后作为人得到安宁。但是,顾城在开始“修城门”时,自己结束了他的一生和创作。虽然用语言“修城门”这个行为只是用文化来控制“自然”的欲望,可他的尝试还留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虽然文明的发达导致了人类偏于理性的思想方式,让人更加感到自己的不完全,但我们不该否定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已经不能完全回到“自然”去生活,也不能把自己停在儿童时代,否定“成长”。同时笔者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探求不只是顾城一人在进行,所以,这篇论文或许刚刚到达当代文学研究的“起点”而已。不过,笔者还是要强调,顾城的诗和他的诗论,尤其是他后期诗歌和他的“自然哲学”论里面含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
注释:
① 本文的诗歌皆引自顾城:《顾城诗全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② 这首诗顾城写在明信片上,是寄给父亲单位的,以《写在明信片上》为题被收录在《顾城诗全集》(上卷)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次印刷版。顾城在《最美的永远是明天——剪接的自传》里提起这首诗说,“像所有六七岁的小孩一样,我对诗的认识只限于顺口溜式的押韵”。见《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③ 顾城曾经说过自己“有幸”生活在“文化空白”、“现代的原始状态”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开始走自己“新鲜的道路”。见顾城:《从自我到自然——演讲录之一》,《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④ 这一点已被岩佐昌暲指出。见岩佐昌暲:《读顾城的“一代人”》,《文学论辑》(日本)第35号,1989年12月。
⑤ 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诗刊》1980年第10期)里,有顾城为他和“他们这一代的某些诗”用“自我”这个词“展开激烈的辩护”这样的记述。
⑥ 这篇文章作为代序也被收录在《顾城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这里引用的部分有改动,但内容没有改变,所以在这里采用了笔者的收藏里最早的1993年版。《诗人顾城之死》里写着这篇文章的原载是《香港文学》1992年2月第86期。
⑦ 顾城:《黑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写着“别说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
⑧ 见工藤明美:《顾城的诗“滴的里滴”和语言》,《火锅子》(日本)第13号,1994年,工藤明美:《墓床其他》,《るしおる》(日本)第22号,1994年。
⑨ 1998年提交给大阪外国语大学(大阪大学外语系)。硕士论文的一部分作为《诗人·顾城论——诗的语言的变迁》的题名发表在《野草》(日本)第62号,1998年,中国文艺研究会。
⑩ 突破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的作品《滴的里滴》最后有“门开着门在轻轻摇晃”这样一句。见《顾城诗全集》(下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参考文献:
[1] 顾城.无目的的“我”——张穗子访谈[M]//顾城文选:卷一 别有天地.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232-236.
[2] 顾工.顾城和诗[M]//陈子善,编.诗人顾城之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47.
[3] 顾城.最美的永远是明天——剪接的自传[M]//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83.
[4] 顾城.从自我到自然——演讲录之一[M]//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264.
[5] 顾城.我曾像鸟一样飞翔[M]//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168.
[6] 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M]//诗刊,1980(10):49.
[7] 顾城.盗火者和女妖[M]//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108-110.
[8] 顾城.我寻找美——谈小诗六首[M]//顾城散文选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44.
[9] 顾城.生命是美丽的,生活也是美丽的[M]//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139.
[10] 顾城.关于布林[M]//顾城诗全集(上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940-941.
[11] 顾城.布林祈祷的原版录音[M]//顾城诗全集:上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805.
[12] 顾城.忘了录音[M]//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200-201.
[13] 顾城.生命和生命的芬芳[M]//顾城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152.
[14] 岛由子.试论顾城《滴的里滴》[M]//诗探索:理论卷,2013(1):47-56.
[15] 顾城.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M]//顾城文选:卷四·生生之境.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161-162.
[16] 顾城.组诗《城》序[M]//顾城诗全集:下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836.
[17] 刘洪彬.顾城,持不同政见的诗人?[J]争鸣,1994(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