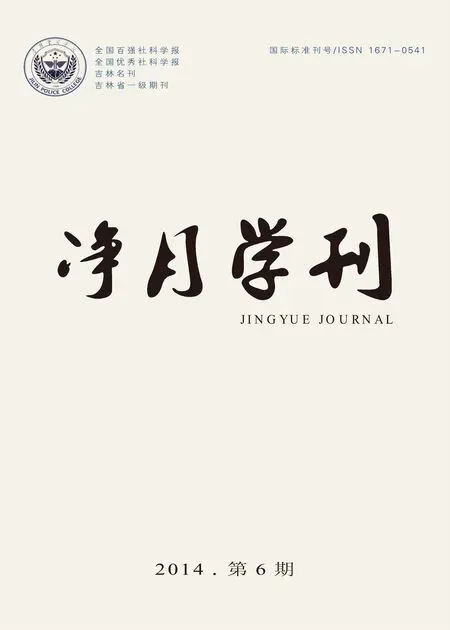治安调解的性质研究
2014-04-16荣晓莉
荣晓莉,李 娜
(吉林警察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治安调解的性质研究
荣晓莉,李 娜
(吉林警察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治安调解是指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劝说、教育并促使双方交换意见,达成协议,对治安案件做出处理的活动。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具有中立性、主体特定性和非终局性等公安行政调解的一般特征;在实践中,存在自愿原则受到限制、行政属性与中立性相冲突以及当事人私法上的处分权和公法上的请求保护权 (仅指公安机关)的紧张三个特性。
治安调解;行政调解;中立性;非终局性
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了治安调解以来,经过1994年修订之后,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2013年修改后重新公布)、2006年《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7年《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等法律或行政规章都对治安调解做出了规定。2013年1月1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加以修订并正式施行,虽然进一步明确了治安调解的范围与程序,但是关于治安调解的一些经典性问题仍未获解决。2010年之后学界对治安调解的关注度明显降低,恰逢东北亚“法与现代警务理论创新”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愿以拙文抛砖引玉,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以促进我国治安调解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治安调解的含义
对于什么是治安调解,我国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效力等级最高的便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这一规定仅明确了治安调解的适用范围,并没有说明什么是治安调解,新修订的《程序规定》也不例外。《程序规定》第153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非法侵入住宅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调解处理:1.亲友、邻里、同事、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的;2.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的;3.其他适用调解处理更易化解矛盾的。”目前明确规定治安调解含义的是《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2条的规定:“本规范所称治安调解,是指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劝说、教育并促使双方交换意见,达成协议,对治安案件做出处理的活动。”
学术界对治安调解的认识并不统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治安调解是指由公安机关主持的,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促使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议的活动。[1]
(二)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毁损他人财物等的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轻微的行为进行处理的一种特定方式,是我国调解制度中行政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2]
(三)治安调解是指公安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特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以第三人的身份主持进行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并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做结案处理的方式。[3]
(四)治安调解作为一种灵活解决治安案件的方式,是指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组织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特定违反治安管理案件的当事人和社区民众就案件中的人身、财产等权利损害赔偿达成协议,而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不再实施治安处罚的一种行政处理措施。[4]
以上四种观点与《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2条对治安调解的界定基本一致,即都指出治安调解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适用的案件范围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案件。区别在于对治安调解的性质认识不同,有的笼统地把治安调解界定为“活动”“结案处理的方式”或“行政处理措施”,有的则明确指出治安调解是“行政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亦采纳最后一种观点,即治安调解的性质是行政调解,但治安调解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调解,它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
二、治安调解的性质
(一)治安调解在性质上是行政调解
根据2011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条的规定,我国的大调解机制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部分构成。行政调解是介于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之间的一种调解制度,一般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5]另外,根据《意见》第8条至第17条的规定,行政调解又可划分为基层人民政府的调解和各行政主管部门及职能机构的调解,第五类是公安行政调解,即公安部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范对治安案件和交通事故纠纷进行的调解。
根据《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2条的规定,治安调解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以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劝说、教育并促使双方交换意见,达成协议,对治安案件做出处理的活动。可见,治安调解在性质上属于以上行政调解中第五类公安行政调解的范畴。
(二)治安调解作为公安行政调解的一般特征
1.治安调解缺乏强制性与单方性,因此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行为。一般行政行为的实施不以行政相对人同意为前提,最终的行政处理结果反映的是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并且行政行为一旦做出,相对人必须服从。治安调解的启动必须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公安机关不能强制调解;调解协议的达成必须是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公安机关处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双方当事人之外的中立的第三方地位,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调停和斡旋,调解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调解的结果并非由公安机关单方面决定。
2.治安调解是在公安行政机关的主持下进行的。在行政调解中,不同领域的纠纷由不同的行政部门主持,如土地管理部门、水利部门、环境保护专管部门、民政部门等,只有公安行政调解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进行的。治安调解便是经相对人同意,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进行调解的活动。公安机关是治安调解的主持者,而非调解结果的决定者,具有中立性。
3.治安调解具有非终局性。公安行政调解不是纠纷解决的最终手段,治安调解也是如此。根据《程序规定》第160条的规定,治安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公安机关可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有人认为,治安调解占用了大量警力,治安调解的非终局性限制了其解决纠纷的能力,也影响公安部门的本职警务工作,“导致民警工作陷入被动,造成司法资源浪费”,[6]进而否定治安调解存在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治安调解的纠纷本质上属于民事纠纷,只是这些民事纠纷中当事人的行为同时违反了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应当受到治安处罚,公安机关在处理此类行为时,认为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当事人不服调解结果进而诉诸法院正是司法终局性原则的要求。
三、治安调解的性质与相关制度设计的悖论
治安调解除了具备公安行政调解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在治安调解的性质设定上,治安调解制度自身存在的“内在悖论”。[7]
(一)自愿原则在治安调解的实践中受到限制
治安调解的自愿性和公安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在本质上是隶属型的法律关系存在悖论。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历来是“公法文化”,公民的私权意识较为淡薄,而警察历来是国家公权力的象征,其在行使职权时,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服从行政管理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即使《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了治安调解应遵循自愿原则,并规定公安机关是治安调解主持者,从理论上来说,公安机关在调解过程中是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治安调解的启动、治安调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自愿,然而公安人员与一般中立性的调解者不同,他们的身份本身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在调解过程中必然会突破中立性第三者角色。“这时调解者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调解者,而是与决定者具有实质的联系,使决定权与主持调解权融为一体。”[8]《程序规定》第160条规定,“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可见公安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处理具有决定权,当事人之间或者达成协议,或者接受治安处罚,公安人员所担任的这种双重角色(中立的调解主持者与治安处罚权的行使者)决定了其在同一治安案件中处于两难境地,把握自己的身份十分困难。“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做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进行强制。在具有潜在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权衡调解与即将决定这两种结果,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结果。”[9]这便导致治安调解的自愿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二)治安调解的行政属性和中立性相互冲突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轻微行为的非处罚的处理方式,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公安机关为履行治安管理职能所做出的行政行为,但是对此类行为的处理方式并非做出行政处罚,而是作为争议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故治安调解既具有行政相关性,又具有中立性。
但是,根据《程序规定》第155条的规定,“调解处理案件应当查明事实,收集证据”,可见,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事实,确定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并进一步明确行为人与被侵害人各自责任的基础上实施的活动。治安案件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调查的案件,公安机关有责任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区分当事人各自的责任。但从本质上来讲,公安机关是治安调解的主持人,也是当事人协商赔偿等有关实体事项的协调中间人。调解程序启动时,作为调解主持者的公安机关难免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所认定的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当事人受侵害造成的物质损失等事实,依据相关法律提前设定调解内容、预测调解协商范围和预期调解目标;调解过程中,通过对当事人教育、劝说等方法,适当地引导当事人协商,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10]因此,治安调解在制度设计上便存在悖论,由于公安机关在治安调解中承担举证责任,在成为特定案件的调解主持者之前,公安机关已提前介入该案并对该案的处理结果即当事人责任的承担有了自己的判断,导致公安机关所固有的行政属性与在治安调解中担任调解主持者角色所需具备的中立性的冲突。
(三)当事人私法上的处分权和公法上的请求保护权(仅指公安机关)的紧张关系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适用治安调解的案件的当事人的行为已违反了治安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受到治安处罚,但因情节轻微且具有特殊情形,公安机关可以选择调解。因此,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原则上只针对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这是公安机关行政管理权的应有之义。同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及时救济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公安机关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前者(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理)涉及到当事人公法上的请求保护权,后者(治安案件造成的损害赔偿)涉及当事人私法上的处分权。在治安调解所适用的民间纠纷中,当事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等私法上的实体权利往往受到侵害,当事人诉诸公安机关解决的是寻求公力救济。在此类治安案件中,公安机关的出警理由往往是针对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本身,对当事人私法权利的救济往往是以当事人寻求公法上的保护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治安案件中,私权利受到损害的当事人若想自己受到损害的私权利一并获得公安机关的救济,那么只能放弃请求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做出治安处罚的机会,从而寻求治安调解;当事人若不放弃追求治安处罚而适用治安调解,其私权利就不能得到公安机关的救济,但仍可以寻求其他途径的公法救济,比如向人民法院起诉。可见,治安调解对当事人私法权利的救济实际上是以当事人放弃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做出治安处罚为代价的,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协调好当事人的私法处分权和公法上的寻求保护权以及与公安机关治安调解的裁量权之间的内在关系。
[1]王宏君.治安管理处罚法教程[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
[2]兰香红.做好治安调解工作的原则和方法[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6).
[3]黄忠舫.治安调解适用分析[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6,(2).
[4]陈俊豪.论治安调解制度之完善[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
[5]崔卓兰.行政法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6][8][9]骆家林.我国治安调解制度的现状分析[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9).
[7]王彬.行政治安调解的反思与完善[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0,(3).
[10]梁桂英.治安调解的特性分析[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
(责任编辑:王佩贤)
D631.4
A
1671-0541(2014)06-0061-04
2014-09-20
荣晓莉(1963-),女,吉林长春人,吉林警察学院法律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公安法制;李娜(1979-),女,吉林警察学院法律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安法制。
本文系2011年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平安吉林”建设背景下的治安调解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3〕第4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