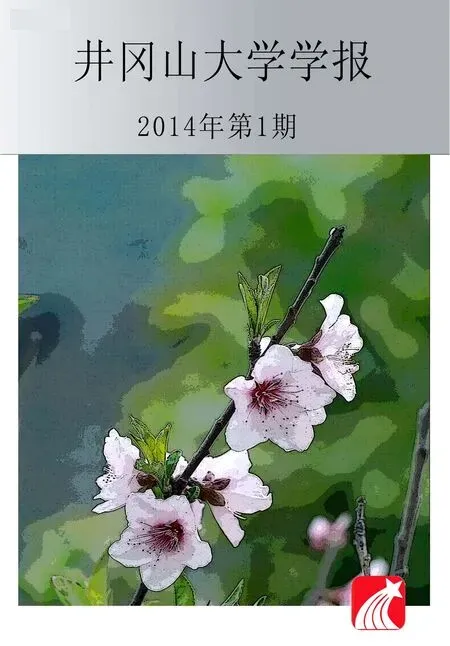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2014-04-15彭晖
彭晖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彭晖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琴;魏晋士人;生命活动;儒道思想
琴作为中国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乐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空灵的哲学意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所推崇。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八音之首”,“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修养之物”。尤其是魏晋时期,琴摆脱了匠人之气,成为当时士人倾心赏爱的乐器。这时的士人将琴作为其怡情养性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并操着这一“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神器,或抱琴行吟,或弦歌而治,以达到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目的。于是,琴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成为一种生命境界的表征,对后世古琴艺术的发展以及文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人与琴的这种不解之缘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文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直接渗透到古琴之中,从而使琴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琴与魏晋士人的生命体验
(一)士无故不彻琴瑟
魏晋时代,士人与琴如影随形,并至于心物相契的境界。尤其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西晋二十四友等人,他们是魏晋时代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的杰出代表,因此他们对琴的爱好,可以说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爱琴之风的盛行。
众多史料表明魏晋士人钟爱琴且善弹琴:
(阮瞻)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晋书·阮瞻传》)[1]P(1360)
(孙登)清静无为,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者。(《晋书·孙登别传》)
(戴安道)少有文艺,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闻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对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为王侯伶人。”(《晋书·戴逵传》)
(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尝有诗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又云:“乐琴书以消忧。”(《晋书·陶潜传》)
北宋朱长文《琴史》云:“(阮籍)尤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以为痴。”又云:“王冏令嵇绍操琴,绍推不受,曰:‘岂可操执丝竹为伶人之事。若释公服,私宴,所不敢辞也。’”又云:“王谢诸俊皆好声乐,太傅作相,虽朞丧不废乐。逸少尝云:‘年在桑榆,正赖丝竹陶写。其于琴也,孰谓不能?’”[2]
据《三国志》、《世说新语》、《晋书》传志等史料作出的初步统计,曹魏两晋200余年历史中,史籍中有姓名可考的知音、爱乐、解律之士多达140人,善操琴者30余人。文学作品中,仅出现琴或与琴相关的诗歌,就有160多首。[3](P86)当时士人爱琴
解音,风气之盛,自魏晋之际而至整个南北朝时期始终未衰。北宋朱长文《琴史》说“晋宋(刘宋)之间,缙绅犹多解音律,盖承汉魏嵇(康)蔡(邕)之余,风流未远。”琴己经深深地融入到魏晋士人的生活中,并成为其特有的生命艺术表达方式,他们弹琴自娱,听琴赋诗,以琴会友,借琴消忧甚至以琴吊唁,以此表现自己的人格风流和精神气度。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入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世说新语·伤逝》)[4](P644)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东晋名士王徽之(子猷)和王献之(子敬)喜爱古琴几乎到了生死难弃,须臾难离的地步。因“子敬素爱琴”,所以子猷才会以抚琴这种极为独特的方式来吊唁子敬,他想通过琴声来传达对子敬的依依深情,但万万没想到自己却因过度的悲伤而“弦不入调”。在他看来琴是有灵性的,琴随着子敬的亡故而亡故。没有了灵魂的琴弦自然是“不调”的,人亡琴亡,人琴俱亡!琴是子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魏晋士人当中,嵇康可谓是琴艺高手。嵇康曾作了一篇三千字的《琴赋》,文中自述“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福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5](P84)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曾说:“今但愿……。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此愿毕矣。”[5](P84)而他临终前所弹奏的那曲摄人心魄的《广陵散》,也给后人留下了魏晋风度的绝唱。这悲壮惨烈的一幕多少年来一直让人感慨不已。《晋书·嵇康传》中记载了有关嵇康临刑索琴之事:“康将刑东市,……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1](P1360)嵇康之死,最终完成了他此生的理想志愿。那凄婉悠扬的琴声,将嵇康临刑前从容不迫、凛然悲壮的神态升华为一种崇高的艺术风度。可见琴已成为嵇康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超越生死,追求生命永恒的媒介。
(二)弹琴咏诗,聊以忘忧
余时英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说道:“音乐与纯文学之独立,同源于士之内心自觉也。文学与音乐于是遂同为人生艺术之一部分,而可以相提并论。”[6](P298)作为音乐的演奏乐器之一,“琴”同文学一样都是抒发性灵、表现自我的一种文化象征符号,而成为人生艺术的内容之一。魏晋士人与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魏晋时期诗赋中,“琴”的身影频频出现,并以其独特的魅力极大地影响了魏晋时期诗赋的审美意境。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来对“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期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但由于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的相互倾轧,政局日趋恶化,这让他内心中感到巨大的压力,加上“典午之变”,司马懿大肆诛杀名士,因此,生死之忧始终不释于怀。为了躲避祸害,阮籍佯狂嗜酒,口不臧否人物。他表面上放浪形骸、任诞潇洒,其实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焦虑、痛苦、伤感、恐惧和忧郁。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阮籍选择了与诗、酒、琴为伴,并在咏诗、饮酒和弹琴中排遣其胸中之块垒,宣泄心中之忧思。他在《咏怀诗》首篇中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中充满了孤独苦闷的情绪,表现了个人无法获得自由,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其《咏怀诗》之四十七云:“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诗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慨叹,“素琴”更是营造了一种凄清的情境,“忧思”之情弥漫全诗。因为“忧思”,所以抚琴以忘忧,寄情于琴,宣泄内心的孤寂和忧思。阮籍正是在诗歌中,用琴来寄托他的情思,用琴来达到“忘忧”的目的,琴不仅是诗人在诗歌中抒发心志的一种表现手段,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意境。钟嵘《诗品》评论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同属“竹林七贤”的嵇康在琴艺上有着高超的造诣,他还用卓越的文学才华写下了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赋《琴赋》,他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琴“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是故怀戚者闻之,则莫不憯懔惨凄,愀怆伤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乐者闻之,则欨愉欢释,忭舞踊溢。留连兰漫,嗢噱终日。若和平者听之,则怡养悦愉,淑穆玄真。
恬虚乐古,弃事遗身。”嵇康处在那个时代,其内心跟阮籍一样是孤独的、寂寞的、苦闷的。在苦苦地挣扎于“名教与自然”激烈冲突中,为了逃避现实,嵇康选择用琴来怡情悦性、抒愤忘忧,用琴来体验并表现个体生命之真味。在嵇康看来,琴使他“导养神气,宣和情志”,所以琴声是他“处穷独而不闷者”的慰藉。琴可以在他独处时候“消忧”,忘却世俗的烦忧和羁绊,在琴声中宣泄自我,让自己的心灵达到自由的超然放达,无欲无求的生命境界。
不仅如此,“琴”这一意象在嵇康的诗歌中也频频出现:
习习谷风,吹我素琴。(《赠秀才从军·十二》)
鸣琴在御,谁与鼓弹。(《赠秀才从军·十五》)
弹琴咏诗,聊以忘忧。(《赠秀才从军·十六》)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赠秀才从军·十七》)
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答二郭诗三首》)
检视载籍,魏晋时期以琴入诗赋,用琴来抒发心志、排遣忧思的诗赋作品还有很多: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性,为我发悲音。(王粲《七哀诗·其二》)
何以除斯叹,付之于琴瑟。(刘伶《北芒客舍诗》)
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陆机《拟东城高且长》)
假乐器于神造兮,咏幽人于鸣琴。(陆云《逸民赋》)
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谢灵运《晚出西射堂》)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五》)[7]
可见,当诗人们“忧思之嗟”时,琴是他们寄托情感、排遣忧愁的精神伴侣,通过抚琴来抒发性灵,忘却世俗的烦扰和纷争。正是魏晋士人与琴的不解之缘,以及他们在诗赋中所创造出来的丰富的琴的意蕴,使得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更加含蓄悠长、意境深远。
(三)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
琴是中国士人抒发情感的工具和载体。士人们通过这一载体表达其对于人生、生命、价值的思考。尤其是在那个充满动荡与黑暗的魏晋时代,士人的生命朝夕不保,人生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强烈矛盾,使得士人们内心充满着忧郁与苦闷,于是琴就成为魏晋士人宣泄困闷与寄托人生理想的一种途径。正如嵇康在《琴赋》中所写的:琴“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云。”
众所周知,魏晋是一个名士辈出,风流彰显的时代,但同时,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又是一个蹙迫险恶,人人自危的时代。正如《晋书·阮籍传》所云:“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极为动荡、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为了争权夺势,对异己势力大加杀伐,许多名士成为这场政治灾难的牺牲品。腥风血雨的政治气氛,给士人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识者虑有危机”,士人们人人自危,朝不虑夕,普遍对自己的命运和生命感到极大的忧惧。他们对现实深感失望,内心极为苦闷。于是,他们对政治往往采取回避退隐的态度。另一方面,面对现实的黑暗,士人们对于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开始了新的思考。正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8](P356)为了在“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求生存,士人们或与世决绝,遁形隐迹;或放浪形骸,混世而超俗;或沉潜于老庄之道,寻求心灵的解脱和精神的自由。他们“以药来保养生命,以期永寿;以酒来浇灭心中的块垒,麻醉于纷乱的世事,以期获取暂时的逃避;用诗乐来寄予心声,抒发自己独特的性情。药、酒与音乐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三部曲。”[9](P22)然而,饮酒、服药,只能暂时麻痹自己;放荡形骸,纵情任诞并不能浇灭其心中之块垒,抚平其心中之伤痛。比较而言,“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陶醉于音乐之中,似乎更能缓解精神的紧张和内心的苦闷,也可借以宣泄淤积的忧思和愤懑,从而实现其精神的自由。而“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可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发声作乐,琴自然是首选之物。于是,琴便成为魏晋士人渲情泄愤、抒忧遣怀的最佳工具。在抚琴弄乐的过程中,魏晋士人找到了属于自我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使他们那孤独、忧郁、苦闷的“幽情”有了可以释放的方式与途
径,使他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可以说,栖情于琴,得道于乐,是魏晋士人由有限臻至无限的生活方式。
二、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
(一)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琴的历史极其久远,相传在圣人伏羲、神农时期就已出现。汉代桓谭《新论·琴道》云:“昔神农氏继伏羲氏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10]据说西周时期,琴曾是家传户有的乐器,广泛流传于宫廷和民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这一特殊阶层的兴起,琴的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逐步成为文人手中特有的一种“八音之首”的乐器。
真正将琴与士联系在一起的据说是孔子。孔子不仅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善操古琴的音乐家。他和弟子常常“弦歌不辍”,深为后世文人所仰慕。他曾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观点,在他看来,音乐对个人的作用不是什么外在的文饰,而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可以达到修身养心,陶冶情性、培养品格的效果,是完善人身修养的重要手段。所以他高度重视音乐在教育中的作用,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中的作用,对弟子教之以六艺,而六艺以礼、乐为首。他还精心整理“弦歌”,将琴曲、琴谱规范成“正乐”,又通过鼓琴以期达到和人心、齐行为的目的。由此可见,琴自创制之始就被赋予了士人的社会理想,因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儒家的礼乐思想。“乐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重要地位。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提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可见,古人把“礼”看作人生行为的规范,“乐”是人们心灵内在的追求。因此“乐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手段,通过“乐教”,可以教化人伦、移风易俗。魏晋名士阮籍在他的《乐论》中也提出了“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的观点,并更为明确地指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在这里,阮籍认为“乐”的本体即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并认为音乐的“八音”、“五声”均有处于“自然”的“本体”,是“不可妄易”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天然和谐,而以“乐”达致“风俗移易”的目的。嵇康也有相似的论说,他在《声无哀乐论》中指出:“故曰‘移风易俗,莫善於乐’。然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这里,嵇康认为“乐”的本体在于“心”的“和”,有了“无声之乐”才能真正助成“风俗”之美,产生“移风易俗”的作用。到宋代时,琴被至于至尊地位。陈旸在《乐书》中说道:“琴者,乐之统也”。可见,在历代士人思想观念中,“琴”是修善之物,琴之乐是治世之音,是天地间的“正音”。他们把琴及其所统之乐视为修身治国的理想工具,所以“士无故不彻琴瑟”。因此,可以说,琴寄托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愿望。
(二)导养神气,宣和情志
魏晋是一个“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士人中的大多数虽然饱含儒家经邦济世、悲天悯人的入世精神,但在与统治者一次次的交锋中,在对出仕的渴求和对现状的失望的矛盾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归隐山林,他们的内心开始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由是开启了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那些政治上的得意者依旧将孔子的“成于乐”思想作为“名教”工具来维护统治,而政治上的失意者不再崇尚庙堂之乐而是接受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此来摆脱名教束缚,走向大自然,从而达到一种“自然一体”、“万物一体”(阮籍《乐论》)的境界。然而要达致和平欢乐的理想社会,“乐”可发挥其作用。阮籍指出:“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及,故谓之乐也。”(《乐论》)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也指出“亡国之音哀以思”,“治世之音安以乐”,“安以乐”之“乐”“和心”“和气”,因而“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和”的境界呢?于是魏晋士人发现琴在所有乐器中具有最优异的品德,所谓“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琴最适宜君子作为其追求个体人格精神自由的修养之具,因为它“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因此魏晋士人希冀以琴自娱来修身养性,在聆听琴声中忘却尘世的喧嚣,最终达到天人和融
的境界。
另一方面,从中国士人所走的道路来看,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人格模式在魏晋时期基本上已经形成,即儒道互补的思想。因此,他们集儒家的济世观和道家的出世观于一身,其人格既有渴望建功立业,明道济世,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的一面,又有遗世独立,归隐山林,回归自然的一面,既重视名利“学而优则仕”,又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故而,这些士人得意时就是儒家,入仕为官,评判朝政;失意时就是道家,归隐山林,“乘桴浮于海”,走向出世之途。我们从嵇康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一个缩影,嵇康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他在《家诫》一文中写到:“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於必济。”“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这表明嵇康身上儒家思想的底蕴极其深厚,他强调立志、守志之重要,也非常注重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正如唐长儒先生指出的:“嵇康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他只是反对虚伪的名教,而他理想中真率自然之人格是与封建道德不可分割。”[11](P28)这实际上是对嵇康思想中深层的儒家因素的充分肯定。实际上,嵇康是企图把道家的崇尚自然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结合起来,并克服儒家压抑人性的方面。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当时政治的黑暗,嵇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只能到道家思想中去寻求慰藉,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美,期待“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在琴声中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他的确也真正做到了,一曲《广陵散》完成了他终身的心愿。
所以说琴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工具,在其离群索居,游于方外的退隐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通过“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而得意忘形,游心太玄,超越人生,超越个人,在茫茫无限的宇宙中去追求心灵和道的合一,达到“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反映在音乐上的审美取向就是“正中平和”与“静淡远虚。”对此,谢希逸在他的《琴论》中作了详细解释:“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12]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乐的本质是“和”,只有“无主於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才可“兼御群理,总发众情”(《声无哀乐论》),从化导众生的礼乐中追求个体人格的独立高洁,而琴中正蕴涵着这两方面的内容。[13](P276)于是魏晋士人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与时人关系密切的艺术形式——琴,并将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演化为他们独特的高雅风流、独立傲世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从而其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相统一的理想境界。
由是观之,魏晋时期“琴”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它“已由两汉时期以儒家道德教化为主的影响,融入了道家生命的体会。并突破传统由儒家乐教为主导的雅乐审美观,融汇入魏晋名士的玄理风格与生命情调。”[13]可见,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它表现出自我人格完善的理想追求,以及关爱自然、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记忆,这对中国文人的精神、气度、品格、行为产生了持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朱长文.琴史[A].[清]黄寅.栋亭十二种[M].上海:上海古书流通处,1921.
[3]许涛.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J].东岳论丛,1999(3).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刘莉.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研究[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汉]桓谭.新论[A].中国古代乐论选集[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11]唐长儒.社会文化史论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1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李美燕.琴道与美学[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Guqin and the Life style of Wei-Jin Literati
PENG Hui
(School of Humanities,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Guq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literati,especially in the Wei-Jin Dynasties.The Wei-Jin literati liked playingGuqin and Guqin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at that time. It reflects the aesthetic ideas and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has had an extremely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In their spiritualpursuit of self-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and Taoism,theGuqin becomes a cultural landscape to meet Chinese literati's complicated emotional needs.Their thoughts which represents in their Guqin music is the epitom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uqin;Wei and Jin Dynasties;life;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206.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1.016
1674-8107(2014)01-0093-06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
2013-09-17
彭晖(1971-),女,江西吉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