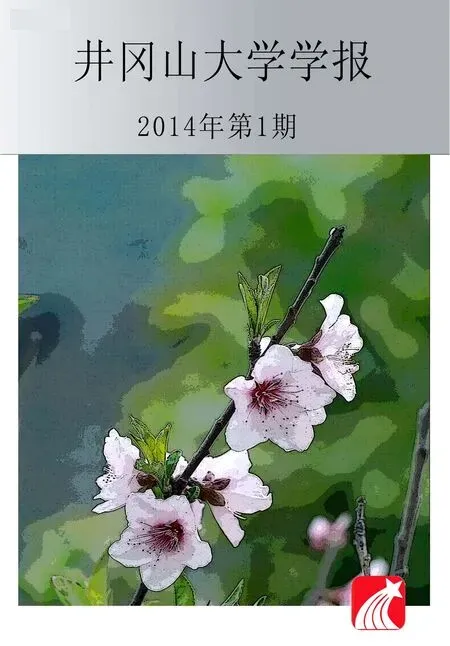进步抑或异化
——论基于精神需要和欲望的符号消费
2014-04-15汪怀君
汪怀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进步抑或异化
——论基于精神需要和欲望的符号消费
汪怀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基于精神需要的消费行为,关注的不再是物品的实用价值,而是物品的符号象征意义。人们越来越注重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终极价值与终极意义的追问。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反映。然而,消费也容易被贪婪的欲望所掌控,占有欲、财富欲、权力欲等驱使着人们近乎疯狂地膜拜物品所承载的社会意义。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就是符号消费异化的表现。
符号消费;精神需要;欲望
从远古到近现代、后现代,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必须消费。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像所有其他的生物,他们要想活下去不得不消费,而且,作为人而不仅仅是动物,他们的消费不仅仅是生存所需要的:人类的生存标准要高于‘单纯的生理’生存所需的必需品,因为除此之外,人类还有较复杂的社会标准,诸如体面、礼仪和‘美好生活’。”[1](P189)人们进行消费的目的除了满足物质资料的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后者更能体现人本质上的社会属性。注重消费物品的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是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进步性。然而,过分夸大物品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为欲望而消费,为消费而消费,走向了虚荣、虚伪、攀比的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呈现出异化状态。
一、需要与欲望
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由消费活动来维持的,而消费活动或消费行为的最基本的动机和内驱力源自于人的需要。消费的首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人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同于动物对外界的摄取,后者是纯粹本能的行为,而前者即使是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也关涉着诸多社会、环境、经济、文化与历史的因素。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观察人的动机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五种依次递升的最基本需要。需要层次理论揭示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多样性,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是诸多学者在谈论需要或需求理论时必然追溯的重要理论之一。马斯洛对人的需要作出了泛化的心理学阐释,但是缺乏更为广阔的社会伦理文化背景的精神解读。人是物理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结合体,人的需要也分为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物质需要的满足使得人类肉体生命得以延续,精神需要的满足使得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王宁认为,需要是维持人的生理、社会和精神存在的再生产(或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和动力。与人的这三种存在状态相对应,
需要分别是指人的物质匮乏状态、社会匮乏状态和精神匮乏状态。首先,需要是一种物质匮乏状态,这使得人有了对食物、水、服装、治疗和保安等方面的需要。物质匮乏还会反映在心理上,成为心理匮乏,如痛苦、紧张、不满足感、贫困感甚至是被剥夺感,因而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来克服这种匮乏。其次,需要是一种社会匮乏状态,指的是个人在社会资源方面的缺乏。社会资源包括配偶与家庭、朋友、归属群体、社会身份、地位和权力等。社会匮乏反映在心理上,就是孤独感、感情饥渴、危机感、挫折感、绝望、妒忌、失常等心理失衡状态。再次,需要是一种精神匮乏状态,指的是对意义、价值、信仰以及精神性产品(如宗教、文学艺术、娱乐、教育等)的需要。如果说人的物质匮乏状态揭示了人的动物性的一面的话,那么,人的精神匮乏状态则显示了人的神性的一面,人之特殊性在于追求精神自由、价值目标与意义世界。[2](P22-23)
当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由于匮乏而导致的紧张感、痛苦感、不安感随之就消失了,人感受着满足的快乐。这或许是古希腊快乐主义者最朴素的想法。伊壁鸠鲁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但他反对不加区分和权衡地去追求快乐。他把人的欲望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既非自然的也非必要的”,如获得荣誉等。第二类是“自然而非必要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备一点奶酪,想吃时可以享享口福之类的快乐。第三类是“既自然又必要的”,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等。伊壁鸠鲁认为只有靠第三种欲望,并满足这种欲望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因为过分的享受虽然能快乐,但也带来痛苦,对身体有害。所以,对于那些很难达到的欲望必定是人类所不必需的,因此也不必去追求。他认为,那些放荡不羁、过分追求肉体快乐的人,都没有分清人的各种欲望并根据理性加以权衡,而屈服于一时的“剧烈而倔强”的欲望,由于这种欲望永远不能满足,所以这种人就永远为不安所苦而得不到快乐和幸福。[3](P240-241)真正的快乐就在于精神的快乐,精神宁静、无所畏惧可以使人享受心灵的愉快和幸福。伊壁鸠鲁的“知足而乐”的思想,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他也没有严格地区分人的基本需要与“很难达到”的欲望的不同,但是他已经清晰地表明必要的满足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与幸福,非必要的欲愿望会给人带来伤害与痛苦。因此,人应该把握好自己,认识到哪些是自己所必需的,哪些是自己要舍弃的。与伊壁鸠鲁相反,柏拉图是完全否认物质生活幸福的禁欲主义者。他认为人的肉体感官的快乐是低级的,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从肉体的情欲束缚中解脱出来,或者说在于灵魂从肉体的“坟墓”中解脱出来。克制自己的情欲,用智慧和理性去追求幸福和至善。
人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他永远都处在匮乏与充实的交替过程中。似乎在人类的脚下,无论何时都有等待跨越的山峰,无论何时都有满足不了的匮乏,无论何时都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需要根源于人的欲望,人的欲望从来都不是一个“常数”,而毋宁说它是一个无限伸长的趋于无限大的“变量”。叔本华曾把它比喻为一个永远饥馋、永不饱和的“胃”,或是一个永远张开着的巨兽之口。一个能被满足的“欲望”不是欲望,而只是一个无限欲望系列中的一环。因为一种具体的得到了满足的欲望立刻会让位于一个更大的新的欲望。[4](P273-274)满足人的基本生理性需要、社会性需要、精神性需要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各类需要一旦被无尽的欲望所支配,就可能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横冲直撞,也可能像凶狠的恶狼一样不择手段。我们选择衣食住行,是源于基本需求还是源于嫉妒艳羡之心、攀比之心?是凭借公平合理的正当手段获得的,还是私下暗箱操作的结果?是否侵占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我们为了获得他人的爱,是纯洁地水到渠成还是欺骗性地自私占有?为了进入一个团体,是凭借自己的真实能力还是走后门拉关系?我们是否在真正地享受着高雅的艺术,还是不懂装懂,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所谓的品味?所以,满足人们生存生活、精神品鉴的基本需要是有限度的,它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其内容具有客观性。这种需要的满足的前提是受制于一定的客观社会生活条件,满足的方式和内容是相对恒定的,满足的过程是循规蹈矩的,具有较高的价值合理性和社会正当性。而满足人们各种食欲、性欲、占有欲、财富欲、权力欲、表现欲的“欲望”是无限度的,具有纯粹的主观性。这种欲望的满足不受制于任何外部条件,满足的方式和内容是变幻无常的,满足的过程是充满贪婪的,具有冲破一切规则与原则的势头,常常被评价为一种恶。
二、基于精神需要和欲望的符号消费
无论是古希腊的快乐主义者还是禁欲主义者的观点,以及现代人本主义者叔本华对“欲望”本性的揭露,都表明了这样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人应该节制肉体欲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幸福。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各种关系网络上的纽结,是在参照他人的同时给自己命名并定位的。因此,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属性。而这种社会属性除了表明人对国家与社会、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等社会文明与制度文明需求之外,还有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对人生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寻,这可以说是人的精神需要。在以往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匮乏的时期,人们只能满足温饱的需要,此时的最大愿望就是得到一片可以充饥的面包,一件可以御寒的衣服,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被遮蔽了,甚至是一种奢望。在阶级社会,锦衣玉食、谈诗论赋、议论国事是统治阶级或上层人士的特权。现代社会生产力极为发达、物质愈益丰富,即使是普通人吃饱穿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讲究起来,尤其越来越注重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我们可以从一幅国画意会画家的心境,向往那样空旷、古朴的田园生活;我们可以从一段音乐聆听其中的悲欢离合,与作曲者同悲戚;我们可以从一曲舞蹈感悟人生的跌宕起伏,奋勇向前;我们可以从一本著作中获得灵感,探索自然与人生的奥秘,或者被作者带入到思想的前沿,或者与作者同去针砭时弊。人与其说是一幅简单的黑白照片,毋宁说更是一幅缤纷的彩色照片。在这幅照片上有无限的意境、有数不清的各种文化符号。除此之外,任何人可以进行形而上学的终极追问,对肉体与灵魂、生与死、有限与无限作本体式的探究。对宗教信仰的精神追求,就显示了人类特别的文化智慧。生命是有限的,也是痛苦的,但只要听从上帝的召唤,就可获得拯救,达到永恒与不朽。“从根本上说,宗教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一种信仰的精神。人们可以不要信仰,但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文化体系与精神体系的大厦就没有屋顶,人们就无法实现人生矛盾和人伦矛盾的最后解决,在人伦关系中,人们就只能餐风饮露,饱尝人生的苦恼。”[5](P333)人类不能允许终极意义的空虚,因为这种空虚是透彻心扉的,是深入骨髓的,会带来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在这种情境下的人要么绝望离世,要么颓废度日,已然过着非人的日子。因此,“那些对于人们的生存是必需的消费,显然是合理的,但是,非必需的不一定是不合理的。人们的许多需要会超出必需,而只有在超出必需的层次上,人们才感受到不只是在生存,而且也在生活。……人不仅需要生存,而且需要发展。在历史上,社会生活的提高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往往源自这些超出必需的需要。”[6](P13)满足精神需要的文化符号消费,似乎就是非必需的,但正是这些高层次的消费才使得人区别于动物,走向文明社会,创造出一个理性与智慧的世界。
然而,即使是满足精神需要的文化符号消费,由于人类经常不能做到恰如其分,也会违背了初衷而显露出可怕的面目。符号消费最终会被贪婪的欲望所掌控,呈现出异化的状态。鲍曼说:“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不是关于需要满足的,甚至不是更崇高的认同需要,或适度的自信。消费活动的灵魂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这是一个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无法理解的和反复无常的、本质上没有所指的现象;这是一个自我产生和自我永恒的动机,以至于它不需要找一个目标或原因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或者进行辩解。尽管欲望是一系列连续而短命的物质对象,它是‘自恋’的:它把自身视为首要的目标;由于这个原因,它注定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不管其他的(身体或精神)的目标提升到什么样的高度。最重要的‘生存’,不是消费者身体或社会认同的生存,而是欲望本身的生存:恰恰是欲望——消费消费的欲望——造就了消费者。”[1](P190)布希亚声称消费是和需要的满足毫不相干的,消费无止境。“如果消费似乎是克制不住的,那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完全唯心的作为,(在一定的门槛之外)它和需要的满足以及现实原则,没有任何关系。理由在于,它的动力来源是物品中永远失望又隐含的计划。在记号中失去中介物的计划,将它的实存动力转移到消费物/记号的系统化和无止尽拥有至上。”[7](P277)传统社会学认为一旦人的需要得以满足,因匮乏而存在的紧张状态就会消失。然而,在消费社会,人的欲求即使在满足
之后也不会消失,而是更加强烈,人们想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消费。欲望的引诱使人类陷入疯狂的消费之中。基于欲望的消费使得人们几乎不关心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过分关注它的符号价值,即其所承载的社会意义。这时符号消费呈现为“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
关于“炫耀性消费”,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的论述。所谓炫耀性消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社会“有闲阶级”成员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对生活非必需品的奢侈性、浪费性消费,来炫耀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名望和声誉。“……为了有效地增进消费者的荣誉,就必须进行奢侈的、非必要的事物的消费。要博取好名声,就不能免于浪费。”[8](P73)毫无节制的消费,尤其是高档用品的消费,说明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有较高的地位,受人尊敬。反之,消费品不上档次,那就表明一个人地位低下,让人瞧不起。炫耀性消费之所以能够赢取名誉,原因就在于它包含着浪费因素,无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还是浪费财物,都是展示财富的手段。炫耀性消费与奢侈性消费总是息息相关的,通常意义下,二者可以和虚荣、虚伪、攀比、骄纵、贪婪和过度享乐等词汇相等同。曼德维尔甚至一反节俭是美德的传统观念,为奢侈作辩护。在他看来,被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标准所评判的“私恶”,如奢侈、挥霍等个人劣行,可以实现公共利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曼德维尔“私恶即公利”的立论基点在于人的本性都是自私利己的,人既是一种精明的动物,亦是一种格外自私而顽固的动物。个体无论何时都在追求着快乐和自我利益。他分析了贪婪与挥霍两种恶德。尽管贪婪可能导致众多的恶果,它却是社会极为需要的,因为它能够收集和聚敛那些被与之相反的恶德所丢弃和挥霍的东西。没有贪婪,奢侈很快便会缺少物质基础。贪婪若意味着对金钱的卑鄙贪恋,它便不再是挥霍的反面了。较之贪婪,挥霍是一种高贵罪孽,挥霍者是对整个社会的赐福,除了挥霍者自己之外,不会伤害其他任何人。贪婪与挥霍倘若能相互矫正它们各自的毒性,它们便能够互为帮助,并且常常可以混合为良药。[9](P78-83)尽管曼德维尔的理论在当时可谓异端另类,但也极具震撼力。这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多面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体。减少兽性、张扬神性始终是人的责任与使命。
三、符号消费:进步抑或异化
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应该懂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该将消费行为的符号化引至正确的方向,避免走向歧途,产生异化。人既是自然性、物质性存在,也是社会性、精神文化性存在,因而人的消费也呈现出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的双重性。应该说,文化消费更能体现人的本真价值,不是像动物一样本能性地消耗,而是探索更多、更好的消费品,品味其带来的精神愉悦,享受到不一样的消费服务。从远古到后现代时期,消费活动都体现着人类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象征性意义也在发生着质变。
消费是属人的精神性活动,因此,即使在人类极其原始的时代,它不同于植物对阳光、水分、养分的吸收,也不同于动物对自然物的消耗。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每一次跨越性进步都与生活资料的扩大紧密相关。这是因为,生活资料是人类繁衍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就此而言,原始人的消费是为了满足自身肉体的最基本需要。那么,是否据此认为这个时期的消费纯粹是物质性活动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始人有了语言,会使用文字,这是文明伊始的标志。正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若是物理性存在,那么他可以像动物一样按照生存本能食用一切食物。但是恰恰相反,在原始人的食谱上常常有某些禁忌。图腾崇拜就是很好的例证。原始人将某种动物如熊、狼、蛇等作为本氏族的神圣标志,是全族之忌物,禁杀禁猎;但有时也有极其相反的情况,有的氏族部落要猎取图腾兽为食,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图腾兽太完美了,食用之后,它的智慧与力量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当然在吃图腾兽之前,要举行庄严隆重的仪式。因此,原始人的消费模式最为简单,首先是物的消费,同时也是最初文化符号意义上的消费,二者原初地、混沌地结合在一起,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分化。
时间跳转到现代工业社会,消费不再是前工业社会中维持生存、自给自足的简单模式。而是大规模的消费模式。丹尼尔·贝尔言,工业社会是商品生产社会,“大规模生产商品是工业社会的特
征,这里,能源代替肌肉提供生产动力,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从而对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起着决定作用。机器与能源改变了劳动的性质,技能被分解为一个个比较简单的部分,工程师和半熟练工人取代了过去的工匠。”[10](P35)技术化、合理化是工业社会的突出特征,机器处于支配地位,人被当作物来对待。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使得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大量增加,人们被鼓励消费,大规模的商品消费成为可能。加之,大机器工业化模式,将劳动者束缚在生产流水线上,失去了对工作节奏的控制,也失去了任何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劳动者无力再进行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于是,走向市场去消费琳琅满目的商品。消费社会日益兴起,它是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模式紧密相关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是按照经济学原理铸成的,人们追求最大化与最优化。因而,在消费社会诞生之初,突显的是对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消费的是它的使用价值,满足的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以此来解决物质匮乏问题。这个时期的消费模式,表现为强调物的消费,遮蔽了文化符号意义上的消费,二者发生了一定的分离。
消费社会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而它又注定归属于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为基础,因此它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如果说在工业社会可以用商品数量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那么在后工业社会便可以用服务好坏和舒适程度高低来衡量人们的生活质量。”[10](P35-36)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或“消费服务”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消费的范围扩大,消费的样式多样化,消费产生了新的动力。人们除了购置生活需要的耐用消费品,继而转向追逐奢侈品和娱乐品。人们的欲望与兴趣关注的是饭馆、旅游、娱乐、体育、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服务是否完善。这个时期的消费,不再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消费置于首位,而是将其符号意义、象征意义上的消费放置至关重要的地位。“符号消费”由此终于形成。
在后现代社会,符号消费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产品满足精神性需求的过程,它通常代表着对“幸福”、“美好”、“理想”生活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消费是一种社会进步。熊辉指出,人们对消费品的符号意义的创造和追求一直没有停止,匮乏经济时代限于生产力的低下、物品的稀缺和大众购买力的限制,符号性物品的消费也仅仅限于少数富豪和贵族特权阶层,而一般大众中的少数分子一旦具备了消费能力,他们也是迫不及待地构筑和消费他们的符号世界。从历史上看,人们不曾对符合消费能力和身份地位的超出生物需要的消费提出质疑(排除在当时文化背景下被认为的极度奢侈和浪费),相反,正是超出生物需要的符号性消费是整个社会公认的和追求的“美好”、“幸福”生活的象征。人类总是在追求和实际消费“美好”“、幸福”生活的符号中不断发展和进步,当旧的“美好”、“幸福”生活符号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的符号时,又有新的“美好”“、幸福”符号产生,幸福的符号也从物质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精神领域。[11](P56-58)对幸福的无止境追求,也就意味着对幸福符号的消费永无终结。
当然,消费社会的文化消费与前消费社会的文化消费,它们的内涵、形式与特性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从属于物品实用价值的消费,离开了实用价值的消费,也就无所谓文化消费;前者远远抽离了物品实用价值的消费,表现为相对纯粹的文化符号意义的消费。当今社会,消费所表征的文化符号意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了消费社会所独有的消费文化。它是后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进步性。它造就了新的消费模式,在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重塑和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历史进步意义。
虽然消费社会的文化消费发挥着文化熏陶、心灵净化与境界提升的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它也逐渐远离经典、精英与崇高,走向平庸化、大众化与低俗化,甘愿做赤裸裸的欲望的奴隶。“消费主义”的价值观铺天盖地般地充斥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人们毫无顾虑、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消费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和最大幸福。作为后现代消费社会核心的“符号消费”难辞其咎,它与消费主义的合谋导致了当今时代的消费异化。这也正是我们对“符号消费”进行伦理批判的根据与缘由所在。
[1][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4]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5]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6]何小青.消费伦理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法]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9][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M].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0][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M].彭强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
[11]熊辉.人类社会进步:符号消费的逻辑[J].理论月刊,2007(1).
Progress or Alienation:Symbolic Consumption based on Spiritual Needs and Desires
WANG Huai-Jun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Petroleum at East China,Qindao 266580,China)
The purpose of consumption is to meet people's spiritual and material needs.Consumer behaviors based on spiritual needs focus no more on the goods'practical values but its symbolic meanings.People now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sumpt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roducts,and to the ultimate value and ultimate meaning.This i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reflection of social progress.However,consumption is also vulnerable to greedy desires,lusts such aspossession,wealth and power drive people to crazy worship of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ttached on goods.Consumption of luxury for showing off is a sign of symbol consumption alienation
Symbol consumption;spiritual needs;desire
B82-05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1.007
1674-8107(2014)01-0041-06
(责任编辑:吴凡明)
2013-09-18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消费异化与人的价值复归——符号消费伦理研究”(项目编号:11YJC7200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消费异化与人的价值复归——符号消费伦理研究”(项目编号:11CX04030B);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自主创新科研计划项目“女性消费与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3CX04047B)。
汪怀君(1978-),女,山东临清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