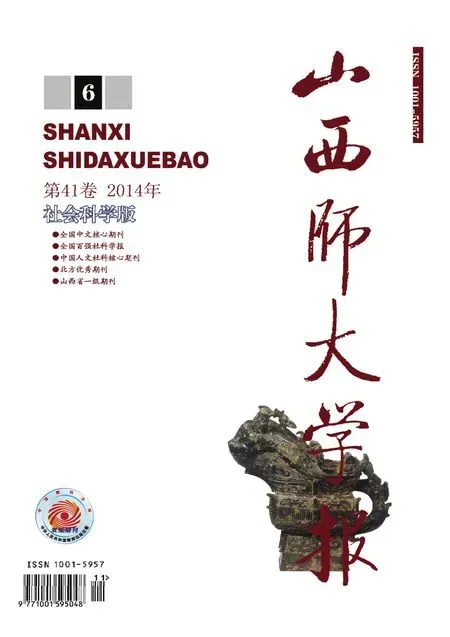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伪经验”时代的“经验”危机与“现实”困境
——以余华新作《第七天》为例
2014-04-11王岩
王 岩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0097)
在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余华始终保持着“先锋”的姿态,敏锐捕捉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走向和生存状态,从而向“本质性真实”不断逼近。《第七天》是余华继《兄弟》之后,力求“对现实发言”的又一次努力,堪称是对“现实”的“二次强攻”。作品重返“虚伪的形式”,但其“先锋”之“芒”并没有刺破“现实”生活表象的外壳,显得犹疑而无力。题材内容上的这一“现实”困境,其根源乃是余华的创作陷入了“经验”的危机。质言之,余华正在失去深入发掘蕴含着文化记忆、存在感受和人性深度的“经验”的能力,“经验原型”已然耗散,“经验内聚力”日趋贫弱,余华的艺术“感觉”被围困在“伪经验”时代符号化、碎片化的“现实”之中。《第七天》反映了余华“先锋”精神的萎缩以及整个当代文学创作的某种困境,为我们重新反思“先锋派”的形式实验提供了典型范本,作品也折射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独特的“经验”症候,因此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一、“经验原型”的耗散与母题的衰变
余华小说有一种耐人咀嚼的“纯粹”的力量,这源于他对小说所负载的“经验”和所依赖的叙述形式作了“提纯的简化”。在“简化”过程中,余华能够发掘出一组“最古老和最朴素的经验原型”,它是人们无法消除的心理症结,其在简单外表之下潜藏着“巨大丰富的浅文本”。其艺术潜能在于,使作品“穿越了‘道德’、‘历史’、‘社会’、‘现实’等等易于使叙述产生潴留的层面,以及对‘意义’的虚拟流连。”[1]123在叙述层面上,建构“经验原型”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母题的凝练和书写。“苦难”,即是余华创作的重要母题。《第七天》即是余华直面“现实”的“苦难叙述”,小说承续了“苦难”母题的诸多“基因”,但时代语境的转换和题材的特殊性,使得这些“基因”呈现诸多裂变,乃至衰变。而母题的衰变自然导致“经验原型”日趋耗散并走向消解,同时失去了概括力和穿透力。下面以“死亡叙述”和“父子关系”两个子母题为例说明之。
死亡叙述是“先锋”小说重要的叙事策略。早期余华以寓言式笔法,将死亡叙述处理为表达对“苦难生存”和“有关世界结构”理解的一种隐喻。《第七天》则直面“现实”世界,通过正面书写大量死亡事件,表达对这个“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的批判,从而滑向伦理道德层面。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造成了伦理颠覆、道德重建、价值冲突等诸多世俗性苦难,小说直接反映了这一困境:郑小敏的父母死于“暴力拆迁”,李青死于高官腐败案,李月珍死于揭露医院弃婴真相,民工伍超死于非法卖肾等。然而,余华将这一幕幕原生态的“现实”伦理悲剧仅归罪于善与恶、贫与富的二元对立,没有发掘其背后更加复杂幽深的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根源,没有提供“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比如作品的“第三天”,写医院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对27个6个月左右的胎儿做强行引产,并作为“医疗垃圾”处理掉了。对此,作品将其叙述为一起公共道德事件,着重表现医院对公众的瞒天过海、阳奉阴违,而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制度性困境和伦理困境被遮蔽了。作品中的死亡叙述绝非能唤起我们更多思考的“经验原型”,它既“矮化”了死亡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哲学意味,也“轻化”和“窄化”了死亡事件的社会意义。
父子关系是余华“先锋”叙事的又一重要内容。“父亲形象”既是其个人童年经验的直接书写,更是象征着历史、传统和权威的重要文化符码。早期作品对冷酷、阴险、龌龊的“父亲”塑造,其本质是对“文革”及其所代表的暴力专制传统的无情揭露和坚决拒斥。《第七天》承续了早期作品中的父子关系模式——儿子在养父(母)和生父(母)之间纠结辗转,在这一错位的伦理关系中,凸显常态下所没有的刻骨铭心的情感经验、生存体验和伦理秩序。小说塑造了一位极富爱心和温情的养父形象——扳道工杨金彪。他以纯粹的善良、淳朴和坚韧,收养了“我”这个“火车生下的孩子”,为了让我不受冷落和虐待,他宁可放弃婚姻生活,直至将“我”抚养成人。可以说,这是人过中年的余华,对父亲的又一次“相认”:通过对养父的倾情书写,隐含了他重寻童年父爱而不得,无奈之下,唯有借助养父表达对伟大父亲的想象和对温暖亲情的呼唤。然而,余华忽略了父子关系作为“经验原型”应当承载的更多社会历史内涵和艺术内蕴。具体而言,《第七天》既没有《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和一乐父子关系所反映的“民间”伦理,也没有《兄弟》中宋凡平和李光头父子关系所反映的厚重历史背景,父子亲情成为近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舐犊情深。艺术上,作品也放弃了《在细雨中呼喊》所成功运用的“非成人化视角”,使作品无形中失去了这一“视角”所“提供那种反抗既定语言秩序的感觉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2]447,成为关于童年生活的纯粹回忆。
如果说以上是从历时维度分析了余华对旧有“经验原型”和母题的承续,那么,下面探讨的则是余华力求发掘的新“经验原型”——“城市经验”。1990年代的余华放弃了形式技巧实验,转而进入“民间”立场,发掘出“民间”的“原始的生机和魅力”。《第七天》则首次将叙述立场完全转向“城市”,但这次极具“先锋”精神的话语实验并没有取得“民间”转向时的成功,余华对“城市”这一现代人主要的生存载体和精神寓所文化特质的认识,落入了“欲望”和“物质”的窠臼。作品中的“城市”景观:公交站牌、高楼大厦、购物中心、发廊宾馆等,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地理空间而存在,我们没有看到“城市”独特的生存模式和现代景观对人精神世界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经验”表达的艰难是当代文学面临的共同困境,面对快速变动的“城市”生存境遇,“作家们不是缺少叙事资源,而是难以找到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来统摄瞬息万变的都市经验,或者说驻足于城市生活的表象结构中,难以发现并捕捉到其中深邃的存在本质。”[3]此外,许多成长于“民间”的作家,对“城市”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从而失去了向“城市经验”敞开艺术感觉、延展智性思维的可能。出生于江南小镇海盐的余华,总是在小说中凸显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表达对“民间”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凋敝的忧虑:以前的村庄“有树林、竹林、池塘、油菜花、鸡鸭牛羊,现在的村庄冷冷清清,田地荒芜,树木竹子已被砍光,池塘也没有了。村里的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只看见一些老人坐在屋门前,还有一些孩子蹒跚走来。”[4]68可见,即便是对“民间”的匆匆一瞥,余华也迅速恢复了敏锐的感受力和概括力。而写了整整“七天”的“城里故事”,但却让我们觉得并未“进城”。因此,如何更深刻地发掘和表达“城市经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经验内聚力”的贫弱与“非意向性”虚构
《第七天》中“经验原型”耗散的根本原因是,作家以及整个时代“经验内聚力”的贫弱。进入1990年代以来,在商业主义大潮的冲击下,“文学及其文化实践不再凭依于意识形态的巨型寓言,不再致力于建构社会共同的想象关系”,“所有的艺术创新突然间都丧失了‘潜对话’的寓言性功能。”[5]337如何重新整合叙事资源,重建文学与历史、现实的“潜对话”,重获“一种实质性的、经验性的内聚力”成为当代文学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在艺术创造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是锻造有力的“意向性”虚构。伊瑟尔指出,“意向性是一种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过渡物’”[6]20,想象成分和现实“经验”在这里交汇成一个虚构的审美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重获人性的健全与和谐。唯有在这一层面上,文学虚构才真正获得了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和活力。《第七天》虚构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的亡灵世界——“死无葬身之地”,余华力求通过两个世界的映射表达对世事人生的思考。然而,两个世界之前的融通转换显得生涩随意,余华没有找到足以勾连两个世界的叙述方式,虚构呈现“非意向性”特征。
“如果让他画一棵树,他只画树的倒影。”莫言对余华的这一评价,确乎深刻揭示了其艺术思维的特质:将被“常识”遮盖和规训的“正面”现象“倒转”过来,在这一令人恍惚、战栗和异样的“倒转”中,现实、想象和幻觉的界限被打破,三者融合所形成的“临界感觉”向一切叙述话语敞开,有关人性、世界和存在的诸多困惑便可以得到重新认识。这也是余华获得“经验内聚力”的独特方法。《第七天》虚构的亡灵世界无疑是余华力求勾画的现实世界“倒影”,但他并没有发掘出这一虚构空间对现实世界的哲学启示意义和美学价值。作品的“临界感觉”始终没有真正敞开,叙述话语也因没有可供自由驰骋的“感觉”地带而犹疑萎缩了。因此,在更准确意义上,亡灵世界实乃“现实”世界的“正向投影”,而非“倒影”。余华将现实世界的规则程序直接移植到亡灵世界中,造成一种压抑甚至灵异的气氛,比如殡仪馆在门上贴“纸条”通知“我”去火化,已欠费两个月的手机竟突然接到殡仪馆的“催促”电话等。不难看出,余华分明捕捉到了生活中看似合乎情理和秩序,实则对人捆绑异化的诸多现象和细节,但他并没有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对其做深入的思考和提纯,仅制造了情绪上的某种差异感、灵异感和恐怖感。作品缺乏对现实世界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对虚构世界清醒的美学自觉。
“洞察力”阙如的另一体现就是对西方荒诞派艺术技巧的机械模仿。小说整体艺术构思都力求传达某种荒诞精神,“第五天”是荒诞技巧运用最突出、荒诞精神最强烈的段落。总体来看,余华主要想表达一种作为“指述技巧状态的‘荒诞’”[7],这是一种不同于“哲学术语”的“荒诞”表述形态,它强调的是艺术“技巧”本身的荒诞,具体体现为物性言说。例如,书中的张刚和李姓两人生前即有杀身之仇,死后化为“骨骼人”竟一起对弈达8年之久。两人从无胜负之分,却一直在“互相指责对方悔棋,而且追根溯源,指责对方悔棋的时间从天数变成月数,又从月数变成年数。”如此循环往复,不知所终。于是,大量铺排的两人对话失去了意义指涉的逻辑性,我们听到的只有声音和喧哗——一种被勾销了语境之后的“空洞能指”。这些有意味的“语言”的“模糊性”解构了“现实”生活中的规则秩序,“能够同时唤起多种感觉联想的成分”,“传递我们对于世界的直觉的真实”[8]181。这一“不可理解性”、“非解释性”和“神秘性”的荒诞体验促使人们对“现实”世界作深入思考。但是,《第七天》并没有创造出足以概括当下人们的生存“经验”,并给人以深刻哲理启示的“荒诞感”。
其实,余华面临的这一困境在其踏上“先锋”道路之初就已注定了。1980年代,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作品,“先锋”作家们迫不及待地加入了“技术补课”,模仿、追赶的大军。但在西方技巧实验热潮冷却之后,在国内语境发生变化之后,“先锋”派作家突然发现自己沦为被弃之“荒原”的孤儿,失去了艺术技巧探索的持续动力,也失去了对时代和现实“发言”的能力。他们在先锋时期从西方文学母体上接续的“血脉”,并未持续激活和孕育“先锋”精神的基因,也没有在本土语境中扎根。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伤感的现实:当形式上的先锋没落以后,人们才发现精神上的先锋似乎从未来过。“先锋”精神的萎缩,直接导致余华没有找到有效纾解“苦难”的方式。作品的“荒诞”意味并未上升至足以纾解“苦难”的哲理境界和神性维度。也许是意识到这一不足,余华在作品最后便直接表达对“死无葬身之地”的宣教式赞美,描绘了一个近乎仙境般的彼岸世界:“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4]225显然,如此直白和情绪性的叙述,因没有艺术话语的编织而显得空虚无力。可以说,这是余华在攀登“荒诞”艺术境界未果之后,不得已滑向了一种“伪宗教”情绪。
三、“伪经验”时代与文学的“现实”突围
本雅明在工业资本主义来临之际,极具预见性地指出在这一“机械复制”时代“经验”的“贫乏”和“贬值”。这里的“‘经验’并不完全是‘感性’的,当然它也并非抽象思维提炼的‘理性’,它是介于感性、理性之间的一种‘知性’,即作家在生活实践中积累而成的对于事物的独到感悟与认知。”[9]190如何深入发掘生活“经验”的深度,突破固有“经验”的边界,增强“交流经验”的能力,成为每一位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我们正在步入一个被过量“符号”和“信息”层层围困和重新编码的社会。如果说真正的“经验”指的是“通过长期的‘体验’所获得的智慧”,那么,我们现在所能获得的只是被过量“符号”和“信息”刺激产生的即时的体验。“经验”退化为“经历”。因此,不妨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为“伪经验”时代。
大众传媒是“伪经验”生产的直接推手,尤其是迅猛发展的电子媒介极大改变了人们“感知”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其建构的符号化“现实”,几乎成了人们感受和认识世界的“元语言”。《第七天》就充斥着大量来自电视和网络的“信息”,“这些现实的奇观性比较硬、比较重地压制了小说自身的逻辑,人物经常被这些现实热点拖着走(让人疑心那些现实事件都在某处等着人物),分散了小说原有的气质格调。”[10]具体而言,“符号”和“信息”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阻碍了“经历”向文学“经验”的转化。
首先,电子媒介传递的“现实”多是被“解释”和“简化”了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以其人物形象之复杂、故事情节之曲折和文化底蕴之深厚,拒绝被单一化“解释”。《第七天》所选取的素材都是近年来被主流官方话语和大众民间话语“解释”过的社会热点事件,其本身原来具有的可以进入小说文本的“故事”性因素,早已被媒介话语过滤、剔除掉了。正如本雅明所言,“到如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有利于讲故事艺术的存在,而几乎每一件都是有利于信息的发展的。事实上,讲故事艺术有一半的秘诀就在于,当一个人复述故事时,无需解释。”[11]310的确如此,余华1990年代的创作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发掘了拒绝“解释”的、而又无限丰富的“经验原型”。
其次,电子媒介传递的“现实”带来“当下性”的“震惊”体验。电子媒介传递的“信息”具有鲜明的“当下性”特征:“它只存在于那一刻;它完全屈服于那一刻,即刻向它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11]311电子媒介对“信息”近乎“共时性”的、无休止的传播,彻底消解了“故事”的“光晕”,只带来“震惊”体验,让我们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感觉日趋麻木。更重要的是,“震惊的因素在特殊印象中所占成分越大,意识也就越坚定不移地成为防备刺激的挡板;它的这种变化越充分,那些印象进入经验的机会就越少。”[12]175《第七天》反映的都是近年来造成巨大“震惊”效果的社会公共事件,但由于过度报道,这些“事件”在人们眼中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余华对这些“事件”的审美观照并未提供超出新闻媒体和普通大众的新认知元素。
再次,媒介话语独特的建构方式阻碍了“转折点”——产生“经验”的地带——的出现。真正的文学“经验”总是产生于作家对世界、人生和自我认知的“转折点”上。即是说,他原有的认知受到来自外界,甚至源于自我的严重挑战,精神陷入某种“危机时刻”。唯有如此,作家的认知才能进入“经验”世界,张开审视世界的“第三只眼”。余华曾言,他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就是认知“转折”的临界状态。但在“信息时代”,电子媒介“通过信息有条不紊的承接,强制性地造成了历史与社会新闻、事件与演出、消息与广告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13]113电子媒介已将我们所有的感知“符号化”、“同质化”和“能指化”,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一切都是线性的,“转折点”和“危机时刻”早已被消弭在永无止境的符号流中。
最后,媒介“信息”的消费性本质制造了情绪上的“伪参与感”。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新闻媒介常对事件做“戏剧化”处理,“煽”起受众廉价而轻浮的情绪。正如贝尔所指出的:“电视新闻青睐灾难和人类悲剧,它唤起的不是净化或理解,而是很快会消耗殆尽的滥情与怜悯情绪,以及对这些事件的伪仪式感和伪参与感。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会过于戏剧化,观众对它的反应也要么变得虚饰做作,要么厌倦不堪。”[14]111这种“伪参与感”既“麻痹”了人的“感觉神经”,也“钝化”了人的“智性”思维,更“冷却”了人对世界本应具有的“温情”,这对要求“亲身体验”的文学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由此可见,“伪经验”时代生产的符号化“现实”是不能直接进入文学的,那么,文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实”?如果说当下“现实”是贫乏的,“已完成”的,那么,文学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想象和虚构,带领我们突破充满“已然性”和“必然性”的“现实生活”的束缚,走向“可能生活”的境界。“可能生活”是“每个人意味着去实现的生活,……尽可能去实现各种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论的行动原则,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道德原则,这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基本条件。”[15]149“可能生活”保护和发展了人的本质力量,即自由和创造性,人们在其中可以认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从而尽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充盈而完整。作家对“现实”的关照和理解,不应仅停留于对当下日常生活、时代景观和社会热点的直接书写上,还应将视野延展到过往的历史中去,发现“现实”背后延续至今的、隐蔽的历史暗河。此外,我们对“现实”苦难的理解,应突破大众传媒强加于其上的情绪性宣泄和符号性消费的仪式,从人性的深度和存在的高度,审视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如此,便可以从混沌无边的“现实”中超拔出来,苏醒已麻木的“感觉神经”,重新体验和把握敏锐的批评意识和生存智慧,培养澄明周全的思辨能力,建构我们的生活态度与想象生活的方式。[16]《第七天》表明余华从新世纪以来对“现实”发起的“强攻”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从《兄弟》的“怪诞现实主义”,到《第七天》重返“虚伪的形式”,余华几乎耗尽了“先锋”艺术实验的可能性,我们隐约感到一次新的“转型”即将到来。但无论如何,能否重获“经验的内聚力”和“交流经验的能力”,才是余华能否重现“先锋”的锐气,能否在这一“伪经验”时代捍卫艺术尊严的关键。
[1] 张清华.文学的减法[A].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 陈晓明.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A].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 李敬泽,洪治纲,朱小如.艰难的城市表达[N].文汇报,2005-1-2(8).
[4] 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5]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德)沃尔夫冈5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汪正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 余虹.“荒诞”辨[J].外国文学评论,1994,(1).
[8] (英)马丁5艾斯林.荒诞派戏剧[M].华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9] 余华,等.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0] 陈晓明.文学如何反映当下现实[J].文艺研究,2012,(12).
[11] (德)瓦尔特5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张耀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2] (德)瓦尔特5本雅明.启迪[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13] (法)让5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4] (美)丹尼尔5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5]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生活和公正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6] 戴文红.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J].文学评论,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