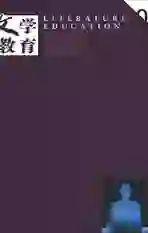余华《第七天》的言说与困境
2015-08-12李文静
李文静
内容摘要:《第七天》表面上叙述语调客观冷淡,实际文本背后是“活着”的温情。文本架构上,余华把“七天”作为纵向展开的标尺,把空间作为横向延伸的平面,将文本中大量的故事平铺互文。现实与虚构的错杂间离,既是作家对个体存在脆弱无助的现实言说,也体现作家对自我的深刻怀疑与精神困境。
关键词:余华 《第七天》 叙事 精神困境
《第七天》是余华推出的一部新作,他强调:“假如要说一部最能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第七天》保持着余华一贯的叙事风格,又有其独特之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冷漠叙述中的温情流露,二是时空架构下的寓言式书写。
一、冷漠叙述中的温情流露
《第七天》在故事层面的叙述值得关注。杨飞与李青的爱情故事,杨飞与养父的亲情故事等,诸多事件置于七天的维度之中。这些故事外部文本的互文与故事内部蕴含的鲜明对比造成叙述上的张力,具体体现在两种爱情和两种亲情上。
余华分别讲述了杨李、鼠妹和伍超的爱情故事。李青美丽动人,选择了从未主动搭讪的杨飞,杨飞胆小本分却与万人迷李青结为夫妻。李青的野心最终战胜小家庭的温情,现实婚姻崩塌。分别时,李青说:“我仍然爱你。”杨飞说:“我永远爱你。”杨飞与李青在身份上不具有对等性。他们作为有知识有理智的爱人,感情观实质是混乱的。相比之下,鼠妹与伍超的爱情“草根”了很多。他们充满吵闹,直至伍超欺骗鼠妹鼠妹赌气而死。至此,余华并没有将四个人感情的收束,反而“死”作为零界,开启鬼魂世界的书写。杨飞与李青的相遇:“ 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杨飞——呼唤仿佛飞越很远的路途……被拉长,然后像叹息一样掉落……”作者以一个声音开场,又给这个声音一个辽远的场景预设,呼唤声“被拉长”,然后“一截一截”飞越而来。这些动作都指向声音的发出者李青。结局:“她说:‘我要走了……”鬼魂世界里,杨李重蹈现实的覆辙,依然是“相遇——离去”的模式,而鼠妹和伍超爱情的发展:鼠妹一直牵挂伍超而后到的伍超先是遗憾后在“死无葬身之地”释然。同样是分别的结局,杨李的分别凄凉没有人情味,而鼠妹伍超虽然擦肩而过,但伍超一直扮演“追寻者”的角色,追寻爱情(鼠妹)走向鬼魂世界(死),继而进入“死无葬身之地”。综观两条爱情轨迹,表面上毫无关联,实际上杨飞作为两个事件的共同参与者,把这两条线打上了节点,两个事件的关联性即可瞥见。杨李代表的理智之爱最终导向陌路,而鼠妹伍超代表的非理智之爱最终达成圆满。掺杂金钱、权力等因素的“理智”之爱不纯粹,理智臣服于现实,相爱之人分道扬镳。相反,不理智的鼠妹式爱情反而因物质变得更加坚固,单纯的“为爱而爱情”得到圆满。余华对两种爱情的书写隐含着他对现代情感的忧虑,现代人于喧嚣之中,能够坚守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在追求另一些满足虚荣时丢弃了原本的质朴自然。再来看两种亲情。杨飞离开生母“家”时的情景:“她听后一愣……她没有劝说我改变主意……‘这些日子委屈你了。我没有说话。”而“我”回到养父身边时:“‘爸爸。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他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地看看我手里拖着的行李箱……他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挡了回去……”离开生母家时“一愣”,“询问”,最后以“委屈你了”作为既遗憾惋惜又迫于实际挽留不下的复杂心情的收束。这样的对话情景是冷淡的。而回到养父身边,养父与“我”的互动充满爱意,一系列的动作细节生动地把父亲看到我时的不解、激动表现出来。成年的“我”在杨金彪看来还是孩子。
《第七天》里,叙事层面上无论是写爱情还是亲情,余华以一种反常规的思维建构。理性的爱情难以圆满,非理性的爱情走向永恒;仅具有收养关系的父子之爱超越生死,而具有血缘的亲属除了淡漠与尴尬实质无爱可言。表面上,余华的叙述语调客观冷淡,实质上叙事之下反常规的思维和情感作为厚重的基底扎稳文本的叙述,同时隐藏在文本内部的温情微妙地渗入文本,整个文本在叙述上是庞杂的,但它在文本外部的淡定与内部潜藏着的情感架构形成互文而使叙事倾于完整,同时充满想象性的艺术张力。
二、时空框架下的寓言式书写
余华把大量社会事件置于“七天”之中,搭建起封闭完整的叙事框架。小说开篇:“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七天”的时间系统是一次完整的生死循环。第一天杨飞进入时间预设当中,第七天杨飞再次走到“死无葬身之地”文本戛然而止。奇怪的是,直至第七日,余华并没有交代线索人物杨飞的归宿。第七天结束即故事时间的结束,故事中的人物理应回归封闭的系统之中,但作者的叙述意犹未尽,随着叙述时间的停止留出后续,文本中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产生不一致。“在叙事时间框架中的故事时间不但被压缩或膨胀,还被任意改变方向。”余华“操纵”着小说时间,刻意拉伸叙事时间,将固定的故事时间压制在长远的叙事时间内,造成时间范围的延宕,对读者来说,扩大了对文本的想象,增添个人的阅读体验和情感。
小说描绘了两个空间,一是存在中的现实世界,二是虚拟的鬼魂世界。文本开篇抛出两种情景,将杨飞穿梭生死的状态推出。殡仪馆作为连接现实和鬼魂世界的中介,不可避免地包含世俗的因素,直到杨飞偶遇鼠妹,他们走到原野的尽头,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死无葬身之地”。从第一到第七天,杨飞游荡的轨迹:小范围的现实世界——殡仪馆——初期的鬼魂世界——“死无葬身之地”。从这个轨迹来看,感情上它有一个“幸福度”上升的趋势,空间上从小部分社会事件发生的场景到空间范围局限的殡仪馆,到“肉体鬼魂”混杂的鬼魂世界,最后到“死无葬身之地”,呈现出阔大的趋势,读者的视野随之打开。当然,杨飞反复穿梭于不同空间使得空间内部产生互动,表现在文本中即现实和虚幻界线模糊。“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地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8]现实投影于鬼魂世界,死者的灵魂游走在虚拟的世界里却不断被生前的记忆缠绕,而死者在虚拟世界中的再次生存具有了异于现实世界中的洞见,他们的见地折射出现实的荒诞。鬼魂世界是作家虚构的“乌托邦”,作家试图用虚构的“乌托邦”显示现实的荒诞。“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荒诞的叙述背后是真实的纸上再现。”[9]余华把杨飞的行踪作为一条明线,将现实和虚拟紧紧缠绕,杨飞不时地穿梭于两个世界,最后杨飞到达“死无葬身之地”达到文本高潮,具有寓言性质的“死无葬身之地”将荒诞表现到极致。空间场景的变换实现了由实到虚的演进,具有象征性的描绘将写作推向高潮。阅读效果上现实与幻想界限模糊,现实事件既是实有又成为小说虚构的情节,同时虚构也成为现实的一种存在镜像,在此现实与小说的虚拟合二为一相互拆解完成小说时空的全新建构。
余华《第七天》的时空安排巧妙。“七天”封闭的时间系统中囊括大量的社会事件,从现实到虚幻又描绘了变换着的场景。余华把时间作为纵向展开文本的标尺,把空间作为横向延伸的平面,将文本中大量的故事平铺互文,于此,整齐的时空坐标与复杂的互文故事交相错杂,织成一张既整合又错落的叙事网。丰富复杂的新闻故事充实全面系统的时空架构,简单整齐的时空框架反过来支撑饱满繁杂的文本,运用特别的方式关照现实,达成了作家所说的“既近又远”的写作。
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有意味的形式。《第七天》建构时与空的叙事框架,而后将大量的社会事件填充进入。他并没有像批判者所说只是简单将新闻串烧。无论是具有互文关系的诸多故事,还是形式上时与空的架构,其中都隐藏着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及前卫的叙事理念。余华在《第七天》的写作上保持一贯的风格,即极力地隐退自己,试图让小说中的人物走自己的路,达到“零度”。于是整个文本的叙事语调变得客观冷漠,看不出作家的影子,造成一种的错觉,但细读文本,在余华冷漠的叙述语调下,掩藏着一种“活着”的温情。余华“刻意”追求的“零度”并没有真正达成,他一味地使用冷漠的叙事语调、节制语言没有掩盖了蕴于底层的温情,而此时的作家本身也没有真正地“隐退”,他在无形中已经介入到叙述中参与了人物的情感互动。作家极力地压制情感,极力地分散注意,对于社会现象并没有作出评判和回应,而是以一种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态度完成叙述。正是这种局外人的眼光体现出对个体存在无助和矛盾的悲悯,表达了作者的怀疑和忧虑。余华是矛盾的。“现在的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他关注现实,以作家的方式言说真实,但他似乎并没有采用激进的方式来对现实作出回应,他“是由于无力持久地承受紧张而采取的犬儒姿态,还是由于洞察了内心的柔弱而突然发现了宇宙的无限和艺术的深邃”,他的态度是暧昧的也是复杂的。
参考文献:
[1]梁宁、余华.余华《第七天》用荒诞的笔触颠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J].大河报.2013,7.
[2][3][4][5][6]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24,51,72,73,2.
[7]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148.
[8]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
[9]周明全.以荒诞击穿荒诞——评余华新作《第七天》[J].当代作家评论:2013,6.
[10]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63.
[11]汪晖.无边的写作——《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序[J].当代作家评论:1999,3.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