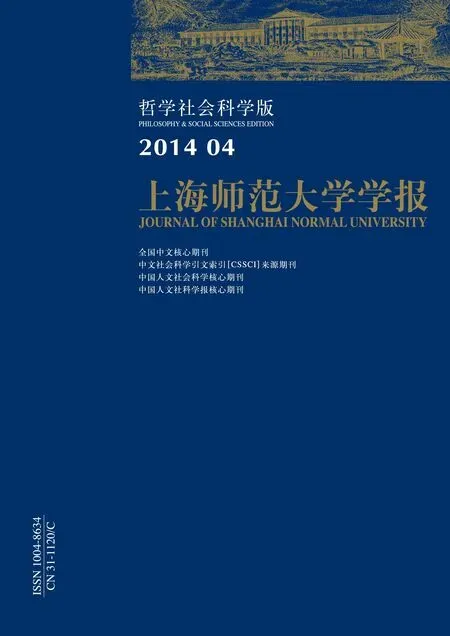元杂剧科举戏婚姻家庭关系中所涉法律问题考察
2014-04-10赵晓寰
[澳]赵晓寰
(悉尼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 悉尼市)
一、导言
元杂剧中,婚姻家庭戏占有显著的位置。在现存的一百五十余部元人杂剧中,以表现婚姻家庭生活为主要情节的作品几近四十种,这还不包括以神仙道化和忠臣烈士等为主要人物或主要情节但涉及到婚姻家庭的作品。而在这类作品中,科举又常常是导致打破婚姻恋爱关系中的平衡,构成戏剧冲突,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动因。科举的这一戏剧功能往往表现为一对有情人因科举而终成眷属,或是一对离散夫妻因科举而破镜重圆,抑或是一对儿女夫妻因科举而分离,最终在大团圆的结局安排下又重归于好。本文拟通过科举戏中的夫妻离合与科举之间的关联,来考察婚姻家庭关系变故中的法律问题。本文研究语料为《裴少俊墙头马上》、①《临江驿潇湘夜雨》②和《朱太守风雪渔樵记》③(以上三剧分别简称为《墙头马上》、 《潇湘雨》和《渔樵记》)。这三部元杂剧均涉及到科举和夫妻分离与破镜重圆,超出了单纯的爱情剧的范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家庭及其相关的社会、法律问题。剧情都充满曲折、矛盾、冲突和转折,悲喜交织,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男女都经历了一个由结合到变故再到复合的过程。
二、科举之于夫妻离合
元代长期重武轻文,科举长期停废,即使在这有限的几次科考中,统治者还实施了严厉的民族歧视政策。元代儒生希冀通过科举入仕的希望渺茫,纵有满腹经纶也无用武之处,社会地位无法比肩前朝士子,有些甚至沦落到与倡优和乞丐为伍的地步。文人自唐宋以来形成的风流倜傥的儒生形象和社会优越感到了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只存在于对历史的遥远追忆中,社会上流传着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正是“士不如娼”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④士子书生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也影响到他们传统的家庭地位。反映在夫妻婚姻关系上,妻子的地位不再像过去那样,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任凭男人摆布。《渔樵记》中朱买臣考中进身前,受到妻子的百般奚落、嘲弄,甚至谩骂殴打。描写中虽不无戏剧性的夸张,却多少反映了元代寒士的社会和家庭地位。
更糟糕的是,元代吏治败坏,学风不正,虽然元律明确规定了取士必须以德行为首,而试官须廉洁不可以容私作弊,⑤但科场上下泄密代笔,卖题鬻选,徇私舞弊,举不胜举,且愈演愈烈,至元末越发不可收拾,激起士人的怨愤。有别于唐宋科举中为党争而徇私,元代科举舞弊多是试官因贪财而枉法,“才德不如二百钱”,弥漫在科场上更多的是铜臭味。⑥对此,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非程文”条和收入其中的“弹文”均有记载。⑦较之文人笔记,元曲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揭露和鞭挞更形生动。《潇湘雨》通过试官赵钱和秀才崔通这两个人物,展示了科举考场和官员铨选过程中的腐败和新进举子经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而抛妻别娶这样的不仁不义之举。科举的长期废止,加之民族歧视,官场腐败,试场舞弊,使得众书生纵使有“济世之略,经纶天下之心”,却无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他们心灰意冷,只得退居乡野,躬耕田亩,肆力山林,如《渔樵记》中的朱买臣;或托庇福荫,相妻教子,怡然自乐,如《墙头马上》中的裴少俊。
在上述三部元杂剧中,文人的失意潦倒在《渔樵记》中描写得最为具体生动。在科举长期停废,进身无望的情况下,出生寒微的学子无法靠读书生存,不得不另谋生路,有的只好放下身段,入赘为上门女婿,靠打柴捕鱼为生,从事自己不擅长的体力劳动,有的甚至沦落到乞讨的田地。⑧布衣秀才朱买臣因为家境贫寒而入赘到家境殷实的刘二公家,寄人篱下,即使遭致妻子和岳丈的奚落和怠慢,也只好唾面自干,委曲求全。
当年朱买臣的岳丈刘二公将他作为入赘女婿迎进家门,是看中他的才学,盼望买臣有朝一日上朝应举,进取功名。可是婚后二十余载,朱买臣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科试应举的意向, 情急之下,刘二公便逼着他的女儿玉天仙演出了一出苦肉计。于是这位将仕进的希望寄托于举荐而非科举的穷书生在妻子百般威逼、辱骂的情况下负气离家踏上科举之路。倘若知道妻子和岳父羞辱他,逼迫他休妻目的是激将,使他义无反顾地进京应举,朱买臣断不会一纸休书,了断他跟妻子20年的情缘,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冷冬日凄然离家赴京应举。倘若没有山林道上巧遇大司徒严助并得到他的竭力荐举,这位饱学之士可能会在耕读之余与三五知己的交往中消磨他的一生。
《墙头马上》中,裴少俊的家庭地位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迥异于朱买臣。裴少俊出身官宦人家,父亲裴行俭乃工部尚书,从小锦衣玉食,属于儒家传统的世家子弟。虽然“学成满腹文章七步才”,少俊却于科举功名似乎兴趣寥寥。同样是官宦人家出身的李千金更是不在意少俊是否要取得功名才谈婚论嫁,她所追求的是婚姻美满的家庭生活。年轻人对功名的淡泊不可避免地与家长望子成龙、荣宗耀祖的愿望产生冲突。如传统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家长对子女偷期密约、私定终身更是无法容忍,视之为伤风败俗,有辱门户之举,一旦发现,竭力将其拆散,而允许成就婚姻大事的唯一条件就是男子必须取得功名,所以元杂剧中婚姻爱情戏的大团圆结局常常是男子状元及第后离散夫妻才破镜重圆,或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千金遇见裴少俊时已经18岁了,两家的父亲先前给他俩议结婚姻,但后来因为双方家长政见不合,儿女婚事就此挂起,不再提及。年岁日长,千金春心萌动却无所排遣。他们墙头马上,一见钟情。她完全摒弃那种官宦人家女子不嫁穷酸白衣寒士的门第等级观念,也不在意他将来是否科举求官;她声称自己只是“浊骨凡胎”,只要是两心相悦,情投意合,“也强于带满头花,向午门左右把状元接”。李千金将爱情和婚姻幸福放在科举功名的前面,比起裴少俊,她在追求婚姻自主和家庭幸福方面表现得更加执着和自信。她顶着世俗的道德规范,抛开婚姻礼教的束缚,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她与裴少俊一见钟情,密约偷期,私定终身,离家出走,无不体现了她那惊世骇俗的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执着追求。她的这种叛逆和执着的性格始终如一,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面对裴父的道德训诫,她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并援引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表示只要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即使先私合后婚娶,也无可厚非,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
相比之下,裴少俊却屈从于家长的淫威,在关键时刻表现得懦弱无能。当裴父威胁要将他“送到官司,依律施法”时,他竟然置七年的夫妻情分于不顾,违心地说道:“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为以妇人受官司凌辱?情愿写与休书便了。”裴少俊的这番表白伤透了李千金的心,她绝望地离去,唯一舍弃不下的是一双可爱的儿女。若不是看在儿女的份上,纵然裴少俊状元及第,功成名就,她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之夫妻复合。她不贪富贵,不恋权势,不重科举功名,自始自终都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保持着自尊和自信。
裴少俊性格上有其懦弱的一面,却非见风使舵、喜新厌旧之徒。他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才学过人,但他和《渔樵记》中的朱买臣一样,并不汲汲于科举功名。若不是家长的恐吓、威逼,很难想象裴少俊会离弃共同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李千金,抛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去上朝应举;同样,若非妻子苦苦相逼,强索休书,朱买臣也不会负气离家,进京取应。在对待婚姻家庭上,裴少俊虽然说不上如李千金那样重情守义,但绝非寡情薄意、忘恩负义。状元及第,除授洛阳县尹,裴少俊不待上任便屈尊纡贵,向李千金负荆请罪,求得宽恕,阖家团圆。这同样让人想起《渔樵记》中的朱买臣。当年他被媳妇踢出家门,万般无奈之下,进京应举,后金榜题名,拜官受爵,即返故里与乡亲叙旧,不念旧恶,与玉天仙冰释前嫌,重修夫妻关系。
对照之下,《潇湘雨》中崔通的负心与无情就显得令人痛恨和鄙视。《潇湘雨》是现存元杂剧中仅见的文人富贵易妻的婚变戏,这出戏也集中展现了官场的腐败和科举制度的弊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弊端丛生的科举制度对人性和道德的摧残与扭曲。试官赵钱一上场即自曝“清耿耿不受民钱,干剥剥只要生钞”,还寡廉鲜耻地宣称他判断人才的标准是“何必文章出人上,单要金银满秤盘”。在众多举子中,他一眼看中了崔通,于是对他进行所谓的覆试。他只因崔通猜中了一个谜底为“一”的字谜和联上了一首拙劣的打油诗,就胡乱称赞他的文采,并猴急地询问崔通是否婚娶。当崔通谎称尚未婚配时,忙不迭地将女儿许配于他。为防生变,他嘱令他们当下就拜堂行礼,随即脱下全套行头好让崔通穿戴整齐,带上新婚妻子立即离京赴任,而自己“弄的来身儿上精赤条条的”,一头钻进“那堂子里把个澡洗”。通过赵钱这个人物,元代科举考官丑态百出的嘴脸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
被这样的考官选中的秀才崔通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才”呢?崔通一上场就自言道:“黄灯青卷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他年金榜题名后,方信男儿要读书。”读书就是为了金榜题名,光耀门庭,一改腐儒穷酸的命运,婚姻也成为他进身发迹的阶梯之一。贪腐的试官正好遇到了功名心切的秀才,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崔通深谙官场中任人唯亲、官官相护的游戏规则,因此当试官问及是否婚娶时,便毫不犹豫地背弃对翠鸾的誓言,声言不曾娶妻,还私下辩称:“伯父家那个女子,又不是亲养的,知他哪里讨来的?我要他做甚么?宁可瞒昧神礻氏,不可坐失机会。”实际上,他大可不必隐瞒已有妻室的事实,因为试官已经告诉他:“若有婚,着他秦川做知县去。若无婚,我家中有一十八岁小姐与他为妻。”但崔通却有自己的算盘:娶了试官的女儿,就等于与官场联姻,确保仕途一帆风顺。设若崔通一开始便知道翠鸾生父的官职比试官要高很多,他万万不会负心背弃原配翠鸾。崔通为了做官才去参加科举考试,为了做官才抛妻别娶。
崔通将功名利禄置于爱情婚姻之上,全然不顾当初自己第一眼看到翠鸾时就赞道:“一个好女子也!”满心希望伯父为他成全这桩婚姻。崔通在新婚后临别时信誓旦旦地说: “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时过境迁,他早将誓言抛于脑后。 当结发妻子翠鸾千里迢迢找到他时,他竟丧心病狂地指使手下打得她遍体鳞伤。他还罗织罪名诬告她,将翠鸾脸上刺上“逃奴”两字来羞辱她。为置翠鸾于死地,崔通将她一个弱女子发配充军,即使试官女央求将翠鸾作为侍女留下也不为所动。他算计着翠鸾熬不过秋风阴雨,流放途中便会死于棒疮,这样便一劳永逸地除掉心头之患。较之不学无术、徇私舞弊的试官赵钱,状元及第的崔通心肠之歹毒、品德之败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小人,又岂能指望他勤政爱民,秉公执法,造福一方?崔通的及第得官不只是揭露了腐败的科举制度和官场文化,也是对腐败的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士子人性扭曲和道德沦丧的强力控诉。
嗣后剧情发生突变。翠鸾于押解流放中在临江驿与失散三年的父亲张天觉不期而遇。此时张天觉升任提刑廉访使,敕赐先斩后奏势剑金牌,巡视天下,惩处贪官污吏。于是,翠鸾不费吹灰之力讨得公道,争回属于自己的名分,而试官女顷刻间便被剥去凤冠霞帔由夫人贬为婢女侍妾。翠鸾和试官女在家庭中妻妾地位的戏剧性转换并非翠鸾奋争的结果,更不是崔通的良心发现,而是取决于她们各自父亲官位的高低。难怪试官女哭诉道:“一般的父亲,一般的做官,偏她这等威势,俺父亲一些儿救我不得!”她们都是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和婚姻礼教的受害者,然而不幸的是,她们对此却毫无觉悟,更可悲的是她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从属于男人的地位。翠鸾起初想要父亲斩杀崔通以报其负心绝情之仇,可是最终还是决定“饶了他这性命”。表面上翠鸾做出这个决定是看在义父的情面上,实际上是为自己着想:“这是孩儿终身之事。也曾想来,若杀了崔通,难道好教孩儿又招一个?”既然崔通不能杀,杀了自己就成了寡妇,翠鸾便将报复的对象转移到试官女身上,求告父亲“只是把他那妇人脸上,也刺‘泼妇’两字,打做梅香,服侍我便了”。 无奈人家父亲的官衔比自己的父亲高出一大截,试官女只得忍气吞声,应承道:“梅香便做梅香,”但她又不愿眼看翠鸾“独占”了老公,于是便提出:要做“也须是个通房”。
三、科举戏所涉法律问题
这几部元杂剧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比如婚姻缔结的法律程序和效力、私下同居是否受到法律维护、调整夫妻关系的法律规定、离婚的法律程序和规定、复婚的程序和调解过程;还涉及家庭暴力犯罪、停妻另娶犯重婚罪的问题,以及官员职务犯罪和徇私枉法的法律处罚等等。
在婚姻的缔结上,《礼记·昏义》写道:“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⑨可见在中国古代缔结婚姻关系的行为是家庭与家庭间的事,与祖先祭祀和血脉传承息息相关。在法律道德化的社会里,家庭伦理道德原则都是关于家庭社会关系的法律。无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良贱禁婚或门当户对,都是父母、祖父母来决定男女婚姻关系的缔结或解除。因袭了唐宋法律的元律同样包括了这些规条,规定直系尊亲属,尤其是男性的直系尊亲属,有绝对的主婚权。⑩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子女即使在成年以后,除非得了父母的授权,即使在外为官或经商,也没有婚姻自主权。婚礼的程序阶段都有详细要求,一旦婚姻订立,婚姻关系就受到法律保护,不许随意变更或转嫁。元代之前,婚书之于婚姻的缔结是可有可无的,如《唐律》所示,即使没有婚书,只要收纳彩礼就可认定为订立了婚约。元代才开始要求订立婚书,各方当事人在上面画押签字。《元典章》规定:“今后但为婚姻议定,写立婚书文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钱物。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议。”
《潇湘雨》中的婚姻约定,崔文远是崔通的伯父,属于男方的男性长辈,同时他又是翠鸾的义父,所以有权决定他们的婚姻,他议定的婚姻就符合法律和礼教。虽然翠鸾为自己的父亲不在场作主她的终身大事而难过,但还是服从了义父的安排。由此,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具有法律效力,当受到法律保护,而崔通隐瞒娶妻的事实再娶试官女,就犯了重婚罪。中国在先秦时期于礼制和法律上就已初步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秦汉至明清各代法律均有禁止有妻再娶或有夫再嫁的法条。《唐律》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总之,法律上只承认原配,除非妻死或离异,婚姻关系已经终了或撤销时,是不能另为婚姻的。对违反者的处罚在《唐律》和《宋刑统》都是“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元代法律同样不允许一夫多妻,坚决取缔重婚并予以严厉制裁,规定,“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若委自愿,听改为妾”。崔通并没有婚书将后娶的试官女定为妾,也没有与翠鸾脱离夫妻关系的休书,所以他再娶就违反了一夫一妻制,犯了重婚之罪。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和裴少俊先是密约偷期,接着双双私奔,后同居做了7年的地下夫妻,并育有一对非婚生儿女。他们的结合没有媒人、聘礼、邻里街坊的见证,父母长辈也不知情,这使得他们的夫妻关系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这些都是当时足够惊世骇俗的非凡举动,在传统守旧的人看来,不知触犯了多少条礼教规条,但开明通达的老院公却觉得这是一件和美之事:“相公不合烦恼合欢喜。这的是不曾使一份财礼,得这等花枝般媳妇儿,一双好儿女,合做一个大筵席。”与老院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裴尚书,他思想保守僵化,道貌岸然,俨然一个礼教的卫道士。当在后花园不期而遇千金时,裴尚书劈头盖脸一连问了三个涉及婚姻程序的要害问题:“谁是媒人?下了多少钱财?谁主婚来?”当得知他们私结连理,裴父严厉谴责李千金不知廉耻与人私奔,断定“这妇人决是倡优酒肄之家”。当千金反驳说自己“是官宦人家,不是下贱之人”时,他怒不可遏,斥骂她“妇人家共人淫奔,私情来往,这罪过逢赦不赦”,并威胁要“送与官司问去,打下你下半截来”。他怪罪千金枉坏了少俊的前程,辱没了裴家的上祖,“败坏风俗,做的个男游九郡,女嫁三夫”,并厉声责问:“既为官宦人家,如何与人私奔?”千金辩驳说自己只嫁于少俊一个人,他不以为然,抢白道:“可不道, ‘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说到这里,他已恼羞成怒,嚷道:“你还不归家去!”势要将她扫地出门。
李千金据理力争,但是面对裴父说要将她送官处理,她不得不退后一步,因为她清楚地知道,纵然她和裴少俊的结合是两情相悦,但告上公堂,私定终身和私奔的婚姻缔结方式是根本不会得到官府和法律支持的,最后将免不了吃官司受刑法,徒然受辱。裴父还以同样的方式威胁裴少俊要将他“送到官司,依律施行”。慑于父亲的淫威,可怜的少俊胆怯退缩了。公婆对他们横加指责,千金并不会觉得意外,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少俊却如此懦弱,没有主见,为迎合父母,竟违心地抛妻别子离家而去上朝应举。失望至极,李千金悲伤地离开裴府。
关于婚姻的解除,包括元律在内的中国古代法律规定了3种形式:“七出”、“义绝”与“和离”。“七出”是丈夫无须经官府即可休妻的法定理由,但为了保护家庭乃至社会的稳定,“七出”的执行还要受到“三不去”的制约。“七出”和“三不去”早在周代即已纳入礼教,至隋唐正式成为法律并为宋元等后代法典所继承。如《元典章》规定:“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公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嫉,七恶疾。”女方触犯“七出”中的任何一条,男方即可写休书,邀集双方亲、邻及见证人一同署名。法律规定出妻不仅必须具备上述理由,而且须给女方一定数量的钱物,否则妻族可向官府上诉。元律还规定,“若以夫出妻妾者,分郎写立休书,赴官告押执照,即听归宗,依理改嫁,以正夫妇之道”。弃妻也必须有男方父母长辈同意作主,并明立休书 而不能按指纹做凭证。裴尚书强逼儿子写休书给李千金,就是认定千金与少俊私定终身、私奔和姘居,他们的夫妻关系从一开始就是非法无效的,即使存在事实婚姻,也因为女方“淫佚”(私奔和姘居)犯了“七出”而可以一纸休书,将其弃去。
“三不去”规定了在哪3种情况下不可以休妻。《元典章》卷十八《户部》之四“休妻”条在列出“七出”同时还附上“三不去”之条款:“一经持公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即不得弃。”富贵易妻自古有之,为遏制这一伤风败俗的行为,自周代起即有“三不去”之规定,目的是防止男人婚后“忘恩”、“背德”和“穷穷”。
古代,丈夫虽有权出妻,但是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或“七出”而有“三不去”,便不能去妻,否则非但得不到法律承认,而且还要追究法律责任,被勒逼离去的妻须追还完聚。与“七出”不同,“义绝”为法律规定的当然离婚条件,有犯则必须强制离婚,否则法律加以处分。“义绝”是指夫妻之间情断义绝。“义绝”的法律规定首见于《唐律》,主要针对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而言。据此,“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宋代法规扩大了“义绝”的范围,增加了“诸令妻及子孙妇若女使为娼”这一条。元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义绝”的范围,将悔婚、改嫁、转嫁、典卖妻子、婚内逼奸、家庭暴力等,均视为有违夫妇之道,都判为“义绝”,断令女方归宗。如《元史·刑法志》所录:“诸夫妇不和睦,卖休买休者禁之,违者罪之,和离者不坐。”“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罪以本殴伤论,并离之;若妻不为父母悦,以致非理殴伤者,罪减三等,仍离之;诸职官殴妻坠胎者,笞三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注边远一任,妻离之;诸以非理苦虑未成婚男妇者,笞四十七,妇归宗,不追聘财。”很显然,崔通对翠鸾的恶行即犯了“义绝”,因此他和翠鸾的婚姻关系必须解除,而且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协离”或“和离”是指夫妻之一方虽没触犯“七出”和“义绝”,但双方同意离婚。唐代比较开明,法律上允许不和的夫妻“和离”,但后来不准妻子主动离婚的观念在宋代有所抬头,官方不再提倡离婚权,即使判离婚也是从维护男权角度出发。尽管传统礼教对妇女管束得很严,但在南宋末年的都市生活中,这种精神上的管束也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很多妇女与丈夫共同经营生意,在家庭里享有同等权威。两宋期间理学家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远没有深入民间,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妇女离婚与改嫁常有发生。辑录南宋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婚嫁”和洪迈(1123—1202)的《夷坚志》均载有许多妇女改嫁之事。
元代妇女在追求婚姻自主方面也表现出强烈的意愿,离婚再嫁甚为普遍。《元典章》记载,元中期武宗(1307—1311)时,“妇女夫亡守节者甚少,改嫁者历历有之”,为此元廷立法禁止命妇改嫁:“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立为定式。如不遵式,即将所受宣敕追夺,断罪离异。”《元史》卷二百一至二百二《列女传》也记载了很多妇女在丈夫死后,其宗族、父母、舅姑力劝其改嫁的事例,可见妇人改嫁是一种风气。上层统治阶级也不以再嫁为讳,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配之念已萌于中者”。“和离”,顾名思义,是以婚姻当事人的意愿为基础的,虽然妻子的意愿在离婚中常常处于次要地位,然而毕竟承认了妇女的离婚权,实际生活中也的确有女子首先提出离婚,即弃夫的行为,也的确有离弃后女子不愿意复婚的。这种情形也反映在杂剧中,如《渔樵记》中的玉天仙主动索要休书,《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对于裴少俊复婚的请求一再加以拒绝。
在婚姻的缔结方式上,本文所讨论的三部杂剧均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墙头马上》中的千金和少俊是私结连理,《潇湘雨》中的翠鸾和崔通是长辈主婚,而《渔樵记》中的朱买臣与玉天仙的结合则是男方入赘。倒插门的婚姻,虽不合于礼,但古已有之,这种婚姻关系中往往是女方家境比较殷实,但苦无男丁,便招进女婿以为老有所托,且男方的家境一般比较清苦,难以承受繁重的彩礼。如《通制条格》卷三“婚姻礼制”所载:“目今作赘召婿之家往往甚多,盖是贫穷不能娶妇,故使作赘,虽非古礼,亦难革拔。”因为家贫,招赘的女婿在妻子家里往往地位不高,如果上门招娶的媳妇横蛮刁钻,日子会更加难熬。《渔樵记》中,玉天仙对入赘的朱买臣恶语恶言,动辄撒泼打骂,视丈夫为出气筒,谈不上任何尊敬。如果她是嫁到男方家为妇,如此对待丈夫,就可能以犯“七出”而遭休弃,或因“义绝”而判强制离婚。然而此剧中,岳父与妻子合谋逼入赘女婿朱买臣写休书,只是为了激将他上朝应举,但朱买臣并没有意愿出舍,也没有违反有关入赘女婿出舍的任何规条,因此他们夫妇之间婚姻关系的解除并不具有法律基础,也不合情理。 从朱买臣被妻子玉天仙强索休书、逐出家门到他荣归故里、复与她和好,其间的戏剧性转变固然显得不无唐突之处,但不可否认这部戏在一定程度上是科举无望的寒门书生和因家贫而入赘为婿的男儿家庭社会地位的现实反映,特别是剧中复婚过程经历了乡邻的调解、友人的证词和岳父及朱妻的陈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民间婚姻的调解方式。
三部科举戏中,《潇湘雨》一剧尤其涉及家庭暴力和徇私枉法等诸多刑事法律问题,集中体现在负心郎崔通残暴冷酷地对待原配妻子翠鸾上。首先,夫妻离别了3年,不料崔通却“别寻了个女娇姿”,“抛弃了糟糠妻”, 这是停妻再娶,犯了重婚罪。其次,崔通诬赖她偷了家里的铜壶台盏而逃跑,这是滥用司法公器来捏造罪名,犯了诬陷罪。第三,他命令左右将翠鸾剥去外衣用棒子打,犯了滥用私刑、刑讯逼供罪。第四,当翠鸾指责他再娶停婚,提醒他当初所作的誓言,崔通不仅矢口否认,更不待翠鸾当着试官女的面说出这些誓词,就强令拖下去用刑。身为县官兼法官,却不许当事人申辩、陈情,严重违反了庭审规定。此外,当翠鸾责问崔通凭什么以无名的罪对她用刑时,崔通马上安上一个罪名给她,丧心病狂地叫人在翠鸾脸上刺字“逃奴”,并解往沙门岛。这样做公然违反不准刺字于妇人的法律规定。更有甚者,当翠鸾表白要与义父(也就是崔通的伯父)当面对质时,崔通匆忙派遣一个能快走的解子,命他即刻出发上路,并要求“一路上则要死的,不要活的”,这样这个案子就成了死无对证的无头案了。末了,连他自己也承认翠鸾“本等是我伯父与我配下的妻子,被我生各支拷做逃奴”。
此外,《潇湘雨》一剧还描述了试官的营私舞弊渎职行为。其实以清廉形象出现的翠鸾的父亲张天觉在查处崔通的时候也不无徇私枉法之举。张天觉科举高中,官拜谏议大夫,因“秉性忠真”,得罪朝中奸臣,为其所谗,削职为民,后因“廉能清正”复被圣上重用,擢升为天下提刑廉访使,主要职责就是巡视督察各级地方官员,皇上还御赐势剑金牌,可以先斩后奏。崔通的重婚、滥用私刑、随意编造罪名、将妇女刺字和充军发配流放,以及指使差人途中折磨暗算翠鸾,犯了十恶不赦之罪,没有任何理由姑息,更何况受迫害的是他自己的女儿。所以张天觉当即决定将崔通上报朝廷,“问他一个交结贡官,停妻再娶,纵容泼妇,枉法成招”,要治他一个“大大的罪名”,“将他两个押赴通衢,杀坏了者”。但是最后却碍于恩人崔文远的情面,顺从女儿的意愿,不仅免了崔通死罪,居然还将他官复原职,仍让女儿与他为妻。现在看来,张天觉的出现对崔通来说,无疑是件天大的喜事:他不仅左有妻右有妾,而且还得了个当朝权倾一时的钦差大臣为靠山。只可怜无辜的试官女,一眨眼由夫人贬作妾。在审理处置崔通案中,张天觉姑息养奸,没有将崔通绳之以法,也没有举报查处试官贡举过程中的腐败渎职的违法行为,无疑犯了渎职和包庇罪。可见这位天下廉访使大人也只是沽名钓誉,徒有“廉能清正”之虚名。如果为当今皇上信任的天下提刑廉访使也会徇私枉法,哪还能指望谁刚直不阿、秉公执法呢?这样的一个大团圆结局不能不说是对专制制度下的司法体系和科举制度的一个极大讽刺。
四、结语
科举作为士子求取功名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其影响渗透到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科举的逸文轶事不仅为正统文人津津乐道而录入笔记史料,也大量为通俗文学作家所采用,改编入小说戏曲。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看到的,科举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然也在元杂剧,特别是元杂剧婚姻家庭戏中得到反映。出身寒微的士子因科举成功而跃入龙门,进入上层社会,从而使得原来门户不当的男女婚姻合法化,获得家族和社会的承认。
科举是家庭关系的催化剂。从家庭夫妻关系稳定这个角度来看,科举的作用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破坏性的。虽然三部杂剧男主人公都无一例外金榜题名并且最后终于大团圆,但无论是高中前还是高中后,夫妻关系都因科举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渔樵记》中朱买臣因为科举而被逼与妻子离婚,离家出走。同样地,《墙头马上》中的裴少俊迫于父亲的胁迫,违心地抛妻别子上朝应举。科举之于家庭关系的破坏性作用最典型地表现在《潇湘雨》中崔通因科举发迹而抛妻别娶,还对千里迢迢寻夫的发妻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历史上,试官和朝廷要员常常诱逼新科状元为婿,或为义子、门生,以便结成官网,互相扶持,垄断政治和社会资源。新进士子也不得不加入这一统治阶层的的精英网络,以求立身官场,仕途顺达。这样的一种官场文化在元杂剧中也得到一定的反映。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潇湘雨》中的崔通,为了功名利禄,官运亨通,竟置伦理道德和法律于不顾,背信弃义,弃妻另娶,徇私舞弊,甚至草菅人命。当然也有一些重情守志的学子,如《渔樵记》中的朱买臣和《墙头马上》中的裴少俊,他们高中得官后不忘本,不弃旧,与一心投机钻营、满脑子功名利禄的儒林败类崔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剧中的几位女性虽有不同程度上的抗争精神,却背负了比男子更沉重的精神枷锁,为破镜重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无论是刁钻泼辣的玉天仙,还是性格刚烈的张翠鸾,抑或是才气心性甚高的李千金,作为生活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女性,她们最终不得不将自己置于道德伦理和社会习俗对妇女的评判之下,屈从于传统礼教和法律规条对妇女身心的束缚。于是,我们便看到玉天仙从一个不守妇道的悍妇一变而为一个祈求丈夫宽宥的贤妻,张翠鸾遭受了丈夫百般凌辱,李千金为裴父扫里出门;她们最后还得向世俗和礼教妥协,违心地接受大团圆的安排。
文学属于人类的精神领域,超越时代,但一旦涉及产生于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学作品,文学研究则无法规避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文学又是时代的产物,艺术地再现那个时代的家庭关系、法律和司法实践等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本文关于元杂剧科举戏的婚姻家庭关系中所涉法律问题考察的意义即在于此。
注释:
①白仁甫:《裴少俊墙头马上》,载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9年2刷,第1卷,第513-538页。
②杨显之:《临江驿潇湘夜雨》,载《全元戏曲》,第2卷,第377-406页。
③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载《全元戏曲》,第6卷,第382-417页。
④田建荣:《中国考试思想史》,第175页。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九儒十丐”之说出自元初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序》:“今之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参见赵翼:《陔余从考》卷四十二“九儒十丐”条,中华书局1963年1版,2006年2刷,第943页。
⑤关于元代科举特点及其弊端的简短总结,参见欧阳周:《中国元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9页 。
⑥同上,第115-118页。
⑦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非程文”,中华书局1959年版,2008年5刷,第344-346页。
⑧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19页。
⑨孙希旦:《礼记集解》第四十四“婚义”,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1989年1版,2010年,第5次印刷,下册,第1416页。
⑩《通制条格校注》卷三《户令》,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