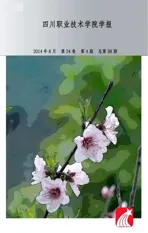语言翻译之可能性的哲学考量
——海德格尔语用观的启示
2014-04-10王晓龙
王晓龙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语言翻译之可能性的哲学考量
——海德格尔语用观的启示
王晓龙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通过哲学史的梳理,廓清了语言如何进入哲学的视域,揭示了语言蕴含的人的认识论本质及其对哲学造成的困惑。正是这一看似语言的限度将哲学带入了对语言的深思之中,即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的存在论思想,而语言翻译之可能也在这种深思中得到了解答。
语言;翻译;诗;道说
关于如何破除这堵墙(即语言可翻译吗?)在上世纪初叶引起一场大讨论,曾有人苦心孤诣,想要推行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世界语),以消除语言间的隔阂。如果推行这一语言,意味着各国历史文化必要推倒重来,有人喝彩,有人痛斥。无论当时怎样唇枪舌剑,争论的结果是语言的翻译活动仍在继续。这不应该只归功于市场的需求,我们应该深思文化命运本身及其决定其命运的东西。中国自鸠摩罗什译经以来,翻译一直弦歌不辍,正是通过这些翻译作品,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不禁要问:通过翻译这种影响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不只是翻译所面临的问题,文化的传承与诠释同样面临挑战与疑问。
1 语言是一个什么问题
要追问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语言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入手,必须进入语言哲学。而“语言”问题本就是哲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向的关键问题,在此问题上,翻译和哲学交织到了一条路上。语言哲学的转变被认为是哲学自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之后又一次重大的转变,这一思潮影响广泛,不仅吸引了语言学家的目光,而且吸引了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科学家,成为众多领域研究的一个共同主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在古希腊最早的宇宙论哲学家追问了终极存在之后,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人的认识本身的重要性:如果不厘清人的认识本身的问题,很可能对宇宙本体的最初论断只是一种妄想的独断论。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普罗泰戈拉发展出他的感觉主义,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认识由客观转换成主观,仿佛是主体能够单方面决定的,这一种感觉论认识到了主体的作用,但也消解了客观标准。希腊哲学在它的体系化时期就接住这个问题,由亚里士多德为哲学树立了坚强的理性的信心,于是,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影响之中。人们相信,在经验和理性的双重力量之下,人们就能够达到真理。但是心理学的发展证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前两种认识论的不足,以至于休谟提出,我们所有的科学知识难道不是一种心理联想律在作祟吗?这个问题深深困惑了康德,康德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来构建他的形而上学王国的,但哲学史已经证明它也只是逻辑预设下的空中楼阁,看似完美解决了休谟问题,却只是对可说与不可说的一种“明智选择”。
关于科学知识能否成立的问题,也就是语言所要面临的问题,即认识的根源问题———通过认识(语言)如何能够言及存在呢?这是哲学认识论深化的一个必然成果。围绕着这个问题,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方案,谢林和黑格尔都意识到了谓词的重要作用,谢林说……这样一些不到位的解释,其原因在于对同一律或者判断中系词含义的普遍误解,黑格尔在《小逻辑》也得出了他的真理观:旧形而上学的主要兴趣,即在于研究刚才所提到的那些谓词是否应用来加给他们的对象。但这些谓词都是有限制的知性概念,只能表示一种限制,而不能表达真理,谓词在黑格尔看来已经成为区分新旧哲学的唯一标准了。叔本华通过对意志的分析,认为只有在艺术作品(即语言的极致言说里)才能超越意志从而达至终极存在。尼采更是将一种诗意的言说作成自己的哲学表述方式,他说:科学问题是不可能在科学基础上被认识的。他将对哲学(及科学)的研究带入了一种对哲学(及科学)的表述方式的研究之中。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给予充分肯定,“在尼采形而上学的根据律中……本质统一性是以艺术与真理的价值的本质关系来命名的。”他也认为只有存在者保持诗意的生活,才能把握真理。
2 语言的限度及海德格尔“诗”与“思”的思想
既然语言已经进入认识论视域,对语言的怀疑就在所难免。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在他看来,语言是有限度的,语言只能对可尽之义务负责。这一股思潮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语言在柏拉图那里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均要服从那个理念,在这种居于从属的情况下,落于言荃的东西已经离最初的那个理念很远了。亚里士多德说,有声的表达是一种对心灵的体验的显示,而文字则是一种对声音的显示,通过语言与文字的双重复写还保留多少心灵的本真体验其本身已经很可疑了。
海德格尔在他哲学生命的后期也集中关注到了语言问题,他通过对古希腊哲学的追溯,将哲学带入对诗与思的思考之中。一个以存在学、生存论研究著称的哲学家在他的后期进入了对语言的沉思,其本身就耐人寻味。在《语言》一文中,海德格尔说,“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在者的本质属性,破解语言之谜将成为解开在者之谜与存在之谜的关键。
海德格尔并非要对语言作一种人类学解释,他说,“语言之词语有其神性的来源”。这虽然是中世纪神学的解释,但海德格尔正要寻找它与人的本性质素的莫大关联。存在与存在者的关联问题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海德格尔眼中,语言不仅仅是一个人类产生之后的现象,而是有着更深的内涵,“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并没有终止……说话聚集着它的持存方式和由之而持存的东西”,那语言通过什么方式持存,又可以持存些什么呢?
“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就在所说之话的诗意因素之中”,海德格尔认为,诗意的言说和言说的诗意可以成为持存之可能,“在诗歌之说话中,诗意想象力道出自身”,因为,诗意言说是有所召唤的说话,“人之说话是命名着的召唤”,它把天、地、人、神四位一体(世界)召唤进来,同时,“它邀请物,使物之为物与人相关涉”,物与世界的交涉通过语言得以可能,物与世界的关系被称为区分,区分是世界与物的维度,既非区别也非关联。而语言就是对这种区分之维度的把握,“语言乃作为世界与物的自行居有着的区分而成其本质”。
于是,“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话”。寂静之音,它召唤着聚集,聚集了在者、存在、世界与物,它乃是存在对存在者的慨然允诺。人以什么方式而说呢?“他们的说话方式乃是应和”,“应和”既为倾听又为获取。人能说话是因为首先听到了指令:区分之寂静。“只是因为人归属于寂静之音,终有一死的人才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作发声之说”。终有一死者正因为倾听到了来自语言本身的召唤而进入对“区分之寂静”的把握之中,才能够说话。语言本身在聚集、在呼唤、在释放、在言说,不是语言跟随人在说,而是人跟随语言在说,人是在倾听语言本身的区分之寂静的过程中做发声练习。
终有一死者是“那些怀念异乡人并且想随着异乡人漫游到人之本质的家园中去的终有一死者”,语言是终有一死者的归属。进一步,海德格尔得出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他说,语言也是存在的家,“根本不同的语言的本质源泉是同一的”,即存在。海德格尔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说“语言是存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云再漫无边际,也归属于天空,而天空也是通过云彩来显现的。
在《词语》一文中,海德格尔思考了语言的基本要素———词语,“词语让物作为物而在场。这样一种让就是造化。”纯粹的物自体在康德看来是不可认识的,海德格尔则认为物依靠物的语言化突破物自体才能够被人所认识,“诗人把……他的道说,允诺给词语的这一神秘”。而道说(即最古老的词语:逻各斯),道说意味着显示,绝不是事后的追加,而是当下显现,“道说把在场者释放到它的当下在场之中,把不在场者禁锢在它当下不在场者”。所以这一意味着显示的道说乃是一种经验,乃是一种面对着道之允诺的经验。
道是什么,“大道乃作为那种道说而运作,而在此种道说中语言向我们允诺他的本质。”终极存在,无,那种惚兮恍兮的东西,它是最遥远的遥远,也是最本质的本质。道与物自体一样其本身是不可知的,正是通过词语的经验打通了存在者、世界与物。语言成为存在者通向道本身的一条道路。
3 语言翻译之可能性
海德格尔对语言作出的类似唯心论的诠释,颠覆了以往我们对语言的人类学的看法,他至少给我们描绘了一种图景,即语言在沟通在者与存在的桥梁作用。海德格尔说:“‘哲学基本学说’并不是指学究们的理论教条,而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语言。”对哲学的研究进入到了对语言的研究之中,那么语言如何成为存在者通向存在的可取之途呢?
海德格尔在另一本关于路的书中说,“通过把语言本质经验为其显示居于大道之中的道说,我们理解的特性便近乎居有和成道了”,在海氏看来,语言要成为一条通往存在的路,必须进行语言转换,并不是对语种之间的转换(翻译),而是对语言的道说与道说的语言的转换,这即是将对语言之思转变为对存在的思或对存在的把握之途的思。那如何通过语言经验存在呢?
存在者对存在的体验式把握被海德格尔称为在场,“在场者之在场,也即在场与在场者的从两者之纯一性而来的二重性”,此二重性召唤人走向其本质,“在人与二重性的关联中占统治地位和起支撑作用的东西是语言。语言规定着解释学关联。”语言经验式的体验,实际是对存在的体验式把握。在这种体验式的把握中,语言超越了自身,存在也超越了自身。
语言之“用”召唤着人去保存二重性,“人在其本质中就是被用的,人之为人,归属于一种要求着人的用。”人之本质归属于大地,语言是大地上盛开的花朵。人和语言的关系彻底被颠倒过来,不是人用语言,而是语言用人。大道无形,贯穿一切存在者。大道在“用”中释放自己的本质,在“用”中把无声的道说带入有声的语言。人的说首先是一种听,只有首先对寂静之音(思想的允诺)的听,才能说。可以说,语言也允诺着自身。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之经验的思想对语言翻译之可能性的思考产生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如果我们只关注于语种本身的差异则无法消解语言间的隔阂,我们应该看到语言所承载的巨大的文化重量,文化枝叶之间虽有差异,但文化的根脉是共通的,其终极追求是一致的,比如人性美善、信仰、真理、自由、幸福、澄明之境等等。其次,我们大致理解了海德格尔通向终极存在的道路,即诗意体验的把握,那这是否只限于诗歌翻译吗?笔者认为,海德格尔思想的启示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对译者(或解读者)的要求,不论从事哪种翻译类型,译者应该训练诗意的体验方式,而不是只盯着语言字面的意义。禅宗《指月录》上说,我们常常关注的是那根指月的手指,而不是月亮本身,这是对现象的执着与迷惘。而翻译者只有抛弃“我执”与事相本身,进入在场,才能做沟通文化、语境之间的使者。再次,思想本身也在向我们允诺,思想具有期备性,“这种期备性的要旨在于揭示那个运作空间,在此运作空间内,存在本身能够在人的本质方面把人重新纳入一种原初的关联之中”。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倾听,倾听来自存在的声音,这与我们诗意的体验方式有关,人应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乃是与存在者和存在的对话,乃是时刻突破自身,乃是把握生命之流。
4 结语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序言里,曾担忧他的诗歌诠释会像沉钟因落雪而走音,他的担忧正是我们对诠释(翻译)的担忧。这一担忧在海德格尔语言的沉思中却完美的化解了,他所揭示的语言与存在论的关系是深刻的,他昭示着我们去重新考量语言与原始无名、与人的关系。也许翻译的发展就在等待着这种深思。对于翻译来说,重要的不是语言已经到位,而是在于思想(关于翻译的思想)到位。存在、人、翻译的确立契机是一致的。
[1]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3]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4]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陶海洋.东方杂志研究[D].南充大学博士论文,2013.
责任编辑:邓荣华
B505
A
1672-2094(2014)04-0091-03
2014-06-12
王晓龙(1986-),男,四川阆中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