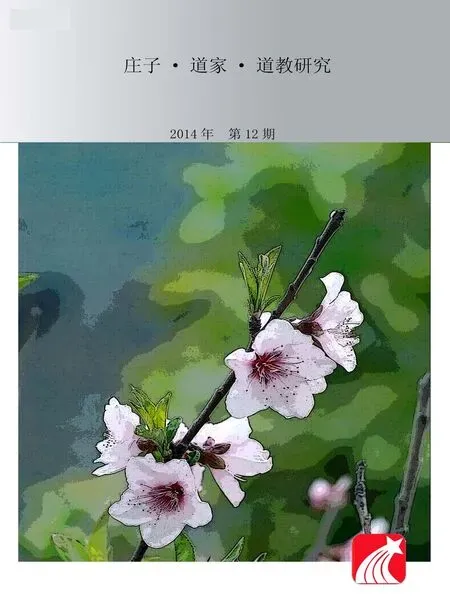从《颜氏家训》探究颜之推的道教思想
2014-04-10李平
李 平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家族信奉道教越来越多。陈寅恪云:“凡东西晋南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故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1]17《隋书·经籍志》云:“三吴及海边之际,信之逾甚。”在这种背景下,颜之推也难免受到道教的影响。纵然他声称自己不信道教,但还是吸收了道教的一些理论。通过《颜氏家训》可以看出道教对他的影响。
一、不致力于道
颜之推认为,道教不可全信。他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2]在他看来,许多人信奉道教,却没有能够得道,这不仅是修道人的个人努力问题,还有命运的问题,即“性命在天,或难钟值”[2]。显然,颜之推有一种宿命论思想,他用这种思想去解释道教徒虽努力修行却不能得道的事实。纵然他相信道教中有合理的因素,但他自己并不信奉道教,也不赞成子孙学习道教。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能够超然于物外的人很少。在颜之推看来,真正能够摆脱尘世对自己影响的人是极其稀少的,正所谓“遁迹山林,超然尘滓,千万不遇一尔”[2]。因为人生于世总会受到牵挂,而且值得牵挂的东西太多了,即“人生居世,触途牵絷”[2]。同时人“幼少之日,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资须,公私驱役”[2],这些都不是很容易抛弃的,所以颜之推认为,人们不容易超脱世俗。当然,颜之推有这种认识,与他自幼学习儒学有必然的关系。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所以,他认为人不容易摆脱世俗的羁袢。
其次,修炼道教是富人的事。在颜之推的眼中,修炼道教必须有足够的财富做支撑,因为信奉道教要耗费黄金、宝玉,需要炉鼎、器具,这些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加以金玉之费,炉器所需,益非贫士所办。”[2]《抱朴子·内篇·仙药》云:“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3]又云:“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然其道迟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3]从《抱朴子》所列的仙药可以看出,仙药大都名贵稀有,黄金、白银、玉石等都是贵重的,且有的服用量很大,像玉,需服一二百斤,这些都不是平常的家庭能够承受的。葛洪也说此类仙药“非清贫道士所能得也”。因此颜之推说学道是富人家的事,而希望子孙不要学习道教。
再者,修炼者多,成道者少。自古能够修炼成道者是极其稀少的,可谓“学如牛毛,成如麟角”[2],并用华山下的尸骨为证,认为“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2]。《抱朴子·内篇·仙药》亦云:“进趋犹有不达者焉,稼穑犹有不收者焉,商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无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难者,为之者何必皆成哉?”[3]得道成仙远比种庄稼、做生意、行军打仗艰难得多,修炼者不可能都能成仙,而且“仙道迟成,多所禁忌”[2],“自无超世之志,强力之才,不能守之”[3]。对于那些对道教缺少信念,以至于半途而废的人来说,只能是无果而返,“其或颇好心疑,中道而废,便谓仙道长生,果不可得耳”[3]。学道的人很多,成仙的人很少,而且能修道成仙的人也不是具有一般意志的人,所以颜之推不赞成子孙学习道教。
最后,即使所谓成道、成仙,最终也难免一死。他说:“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2]因为颜之推信奉佛教,佛教声称“生死轮回”、“六道轮回”。《杂阿含经》讲:“佛告诸比丘:‘诸比丘,若无明所盖,爱结所系,众生生死轮回,爱结不断,不尽苦边……’”[4]按佛教的说法,人总是要死的,然后再生,而人的生死轮回在不同的场域之中,即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地狱道、畜生道,具体要在那个场域中轮回,全看前世业报。《华严经·品序》云:“生死所趣,各缘业报。”[5]“业果业报决非以一期生命之死亡而终了,死亡不过是‘色身'——物质所构成的身体循环的物理法则由聚而散。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各人所造的业并不因物质身体之死亡而消灭。死亡之后,业力会自己驱引自己按一个新的方向、以一种新的形式,又形成了一个新生命。”[6]佛教的生死观与道教成仙后长生不老是相违背的,而颜之推最终相信人总是要死的。不过,颜之推似乎在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他并不是一概地反对道教,或用佛教攻击道教,他首先承认道教的成仙理论,然后认为即使是神仙也难免一死,这是他对道教新的认识。
正是考虑到人很难摆脱世俗的牵挂,修道要耗费大量钱财,得道艰难,即使得道也终究死去等诸多因素,颜之推教育子孙,“不愿汝曹专精于此”[2]。他不希望子孙修道,不是他不相信道教,而是综合道教修炼及自家条件等多种因素作出的审慎选择。
二、善用道术全身保命
颜之推不希望子孙专门学习道教,主要原因是他认为里面有的东西是不可信的,甚至是妖妄之言。如说:“吾家巫觋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2]但他还是相信道教理论也有合理的一面,并希望子孙运用道教的养生之术延年益寿。颜之推云:“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2]认为可以用道教的养生之术,调理护养气息,也可以用道教的药方补药滋养,而不致夭折。他举出实例说明道教的方术对于养生是有好处的,如说:“庾肩吾常服槐实,年七十余,目看细字,须发犹黑。”[2]可见槐实有健身、明目、乌发之功效。《抱朴子·内篇·仙药》云:“槐子以新瓮合泥封之,二十余日,其表皮皆烂,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补脑,久服之,令人发不白而长生。”[3]同时,他进一步说明用道教药方进补的人有很多:“邺中朝士,有单服杏仁、枸杞、黄精、朮、车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说尔。”[2]通过这些例子证明,道教的养生之术是有用的。杏仁、枸杞、黄精、朮、车前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皆有说明,在此不一一解释。
用道教的方术养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导引。道教养生的方法很多,包括导引、按摩、炼丹等。道教经典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甚至成仙。
道家认为,人死不能复生。“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7]卷72《不用大言无效诀》“夫人死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名为人也,不复起行也。”[7]卷90《冤流灾求奇方诀》正因如此,道教把死当做人生重大的事,所以道教注重养生,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颜之推要利用道家的养生之术来养生,具体来说就是用道家导引中的叩齿法来养生。《抱朴子》中的牢齿之法是:“朝叩齿三百下为良;行之数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辈小术,无损于事,亦可修也。”[2]这里,颜之推其实是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道教养生之功效。自己有牙病,通过坚持练习道教经典《抱朴子》的叩齿术,牙病痊愈了。所以,他要求子孙可以练习,并指出它有益于身体健康,且不耽误事情。《抱朴子》是东晋葛洪的代表作,葛洪是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一生勤于炼丹,修道养生。其《抱朴子·内篇》云:“牢齿之法,晨起叩齿三百下为良。”[3]后代道教经典也记载这一方法。《九真高上宝书神明经》云:“叩齿之法,左相叩,名曰:‘打天钟’;右相叩,名曰:‘捶天磬’。若卒遇凶恶不祥,当打天钟三十六遍。”[8]现代中医也认识到叩齿术确实是健身的好方法。
第二,审视药方。道教的养生之术,除了导引、按摩之类,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服用延年益寿之药。《抱朴子·内篇·仙药》云:“抱朴子曰:神农四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太乙禹馀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3]对于药方,道教开出的很多,但类别不同,功效也不同。就药方而言,有上药、中药、下药。颜之推认为,要认真辨析,不可盲从,对于一些药物吃了是否能升天,是否能延年益寿,要经过仔细的辨别。“凡欲饵药,陶隐居太清方中总录甚备,但须精审,不可轻脱。”[2]并说:“近有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不得节度,肠塞而死,为药所误者甚多。”[2]许多人因为迷信道家的药物而给自己带来伤害,这是没有认真区分药物真假的原因。他认为,人要通过药物的调理来保全生命,但要有个分寸,不能因此而耽误大事,“诸药饵法,不废世务也”[2]。
第三,内外兼修。道家注重养生,通过导引、炼丹等方式,加强对身体的调理,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这可以称得上是身体内的调节。道教注重内在修炼调理的同时,还力求避免外物的伤害。如说:“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2]这称为身体外的调节。颜之推深刻领悟到道教的这一养生全命的精髓,教育子孙既要通过调理保持身体的健康,又要避免外物对自己的伤害,这样才能全身保命。“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2]只重视调理保持身体的健康,不避免外物对自己的伤害或者不重视调理保持身体的健康,只知道避免外物对自己的伤害,这些都是不对的。为此他说:“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着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2]《庄子·达生》云:“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簿,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单豹善于调理身体,没有提防外物的侵害,结果被虎吃掉;张毅能提防外物的伤害,却不能调理身心,结果得病而死。《晋书·嵇康传》云:“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缺;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因谮‘康欲助贯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嵇康虽通晓养生之术,并著《养生论》,但恃才傲物,终得罪他人,惨遭杀害。显然也是没有注意外在的伤害。《晋书·石苞传》云:“苞少子崇,字季伦……少敏惠有谋。财产丰积,后房百亩,皆衣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崇有妓曰绿珠,孙秀使人求之,崇尽出数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择。’使者曰:‘本受命索绿珠。’崇曰:‘吾所爱,不可得也。’秀怒,乃矫诏收崇。”石崇注重养生,经常服用名贵的药物延年益寿,却因为贪念女色而招来杀身之祸。这也是没有避免外物伤害的结果。
第四,践行大义。道教重视养生,把长生不老当做道家的最高境界。正所谓:“生为天地之大德,德莫过于长生。”[2]颜之推也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教育子孙要重视养生,但是颜之推并非为养生而苟且偷生,他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人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去做冒险的事而危及自己的生命是可惜的。“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9]然而,君子如果因为践行大义而死,则是值得的,没有罪过的。他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2]为了忠孝仁义,为国而捐躯,为家而舍身,这些都是正当的。为此,他列举郡太守张嵊、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为国捐躯的事迹,并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曰:“侯景之乱,王公将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无全者。唯吴郡太守张嵊,建义不捷,为贼所害,辞色不挠;及鄱阳王世子谢夫人,登屋诟怒,见射而毙。夫人,谢遵女也。何贤智操行若此之难?婢妾引决若此之易?悲夫!”[2]吴郡太守张嵊为国尽忠,死得其所。谢夫人临危不惧,其操可表。他们都是践行大义而死,是值得称赞的,让人敬佩的。而那些临大义而苟且偷生的人,是让人气愤的。“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2]
可以看出,颜之推教育子孙不要修炼道教,但可以运用道教的方术养生;既要注重养生,又不要偷生。要养生是对生命的尊重,不偷生是对儒家忠义的践行。这里其实也是对儒家忠义观与道教生死观的调和。
三、功成身退
道教对颜之推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名利的追求上。颜之推要求子孙们好好学习,为自己做官创造条件。他主张:“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2]认为要做官就要有道德,没有道德的人是不具有做官的条件的。可见他是主张入世的。这与道教的主张有些也是相吻合的,因为道教主张出世,也主张入世,后人认为道教也是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班固认为,道家本身出自史官,他们记载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知道如何治理国家,所以说道教是“南面之术”。道家自身也认为道教是“南面之术”,如《抱朴子》云:“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昔黄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举;彭祖为大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伯阳为柱史,甯封为陶正,方回为闾士,吕望为太师,仇生仕于殷,马丹官于晋,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公藏器于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3]道教认为,在内可以修身、在外可以平天下的是上士,而那些专修道家经典、不关心世事的就是下士。像黄帝、彭祖、吕望等都是既修道又能治理天下的上士。可见,道教是赞成那些既有志于道、又有能力治理天下的上士的。
颜之推虽主张入世,但并非积极入世,认为能否做官要听命自然,如说:“爵禄不登,信由天命。”[2]这与儒家的积极入世有别。他憎恶那些跑官的人,称他们与强盗无异。“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2]自己去要官、跑官,是羞耻的事。可见,在做官的态度上,他与儒家不同,他不赞成主动追求官位。
另外,他主张做了官也要知足,为此他写下《止足》篇告诫子孙。“止足”出自《道德经》第44 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知止”,指对名利、福禄的追求都要知足。《纂图互注老子道德经》云:“知足之人绝利去欲,不辱于身。知可止则财利不累身;声色不乱于耳目,则身不危殆也。人能知止足,则福禄在已。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民不忧。故可长久。”[10]颜之推告诫子孙要知足,并说自己早有“身退”的想法,只是担心别人陷害,尚未隐退。他说:“吾近为黄门郎,已可收退;当时羇旅,惧罹谤讟,思为此计,仅未暇尔。”[2]颜之推的这些想法明显受到道教的影响。
颜之推对道教的认识是辩证的,其肯定道教中的合理因素,即使是神仙之术,也包含合理的成分,特别是道教中的养生之术是值得借鉴的。他利用道教中的叩齿术健身,用道教的药饵祛病延年,但认为道教的“符书章醮”是妖妄之言,不可相信。他赞成全身保命,又不苟且偷生;他主张入世,但又强调功成身退。这说明颜之推善于吸收道教的合理的因素为自己所用。颜之推之所以对道教采取如此的态度,这与他自幼学习儒家的思想以及魏晋南北朝独特的社会背景有重要的关系。就全身保命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纷乱的战争与频繁的王朝更替,让他感到国家并不长久,家庭却是最重要的,因此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儒家的思想讲忠孝,因此在忠孝面前就不能只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1]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M]∥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2]颜之推.颜氏家训[M]∥百子全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葛洪.抱朴子[M]∥百子全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杂阿含经:第10 卷[M]//大正藏.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5]华严经·品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4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太平经[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张君房.云笈七籤[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9]太清真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老子道德经[M].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