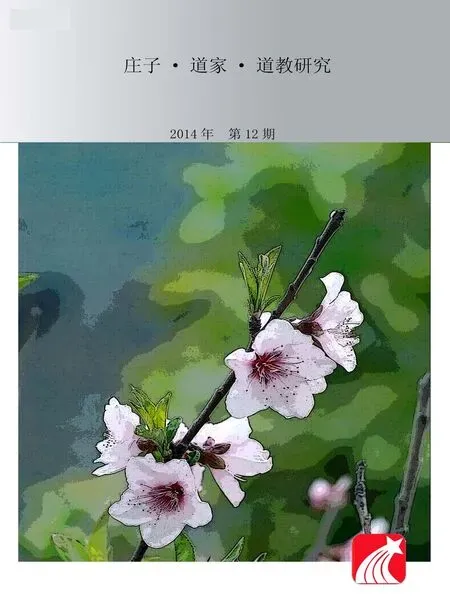道教中的“梵音”与中夏音
——《灵宝经》所见老子化胡说
2014-04-10皓月
王 皓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老子化胡说一般被认为是道教方面提出的,目的是表现自己超越佛教;但实际上最早可能是佛教为了能让中国人接受而提出的。从南朝开始,老子化胡说成为了道教宣扬自己优于佛教的重要依据①。
老子化胡说反映了历史上佛道相互影响的微妙关系,特别是道教经典之中,源自佛教的概念并不少见,而“梵音”(本文为了与佛教之中的梵音相区别,将道教中的梵音记为“梵音”)的概念也是其中之一。在“梵音”的概念被道教吸收之后,也相应地产生了表示中国音韵的中夏音的概念,而“梵音”成了与中夏音并列的道教两大音韵,都被认为是道经的正音。那么,道教何时开始使用“梵音”的概念呢?道教使用“梵音”的概念有什么目的呢?“梵音”和中夏音在道教之中又是被如何应用的呢?本文拟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些问题也与老子化胡说有重要的联系。
一、佛教的梵音
梵音源自印度的佛教,所以在分析道教的“梵音”之前,有必要对佛教梵音的概念进行介绍。梵音即印度梵语的音韵,相传为梵天所制,故得名梵音。而梵天,也就是大梵天,即色界初禅天之主。唐代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100《翻译部第二》写道:
何得经书乃云胡语?佛生天竺,彼土士族婆罗门者,总称为梵。梵者,清净也。承裔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为下。劫初来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为人。仍其本名,故称为梵。语言及书既象于天,是以彼云梵书、梵语。[1]第53册,1019
还有,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 记载:
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也。寓物合成,随事转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广,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语其大较,未异本源。而中印度特为详正,辞调和雅,与天同音,气韵清亮,为人轨则。[1]第51册,876据上述内容,可知梵音和梵字原本都是梵天所制,但是由于光音天在世界的初劫下凡时,吃了地上的食物,以致身体沉重,无法返回,于是成了人类的始祖,其所使用的梵音和梵字也就流布人间。人间流传的梵音根据地域的不同有所差异,以中印度最为正宗。
梵语的音韵之中存在十二摩多,也就是十二转声。关于梵语音韵的十二摩多,历代有数位高僧进行了汉译。在隋唐以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东晋时期法显所译《佛说大般泥洹经》卷5《文字品第十四》、北凉时期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卷8《如来性品第四》、梁代僧伽婆罗所译的《文殊师利问经》卷上《字母品第十四》等。
对比上述十二摩多的汉译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同样是表示一个音,各个译本所使用的汉字却有很大不同,这正说明了用汉字表示梵语音韵的方式存在极大的缺陷。因为汉字本身不是表音文字,而中国的音韵体系又包括众多小的音韵体系,根据小的音韵体系的不同,同一个汉字的发音也会出现差异,所以关于十二摩多的汉译,实际上不能准确地表达梵语的音韵[2]。但是,这种由汉字所记录的不准确的梵语的音韵,正是古代中国人所认识的梵音。而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其开始创造标音单词,最早就是受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如“佛陀”、“涅槃”等佛经中所使用的单词,都是梵语单词的音译。
二、作为道教两大音韵的“梵音”和中夏音的确立
由于东晋中期的《上清经》就已经开始吸收诸多佛教的概念,刘宋时期创作的《灵宝经》更是广泛吸收了佛教大乘的思想,所以道教经典之中源自梵语的单词越来越多,而道教之中出现“梵音”与中夏音两大音韵的说法,正是始于刘宋初期编纂的《灵宝经》。
在道教中,古代中国的音韵被统称为华夏音,但事实上,古代中国的音韵并非统一的音韵体系,随着王朝的更迭和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不同的音韵体系交替成为华夏音中的主流。自殷代至东汉时期,以关中和洛阳为代表的两大音韵体系为华夏音中的主流,而随着三国时期孙权在江南建立吴国,特别是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南方地区的开发程度逐渐提高,以致南方音韵体系成为与北方音韵体系相抗衡的音韵体系[3]。所以,在南朝刘宋时期,南方音韵体系可以说是当时华夏音的两大主流之一。道教所称的华夏音,应该就是当时作为中国音韵体系主流的北方音韵体系和南方音韵体系的统称。
关于“梵音”和中夏音,《灵宝经》的《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说:
其山(昆仑人鸟之山)众圣诵经,皆大梵天制音。不哀不伤,不迟不疾,弘雅要妙,闻者融然。昆仑山上诸仙,多作中夏九天诵咏,萧条远畅,清音泠朗,听者霄绝,使人忘情。时会众仙歌咏洞玄,合读齐唱,新声激响,窈窕遐闻,扬藻空洞,虚弦鸣弹,而玉清感悦矣。[4]第6册,644
说人鸟山上的众圣用“梵音”读经,而昆仑山上的众圣用中夏音读经。因为《无上秘要》卷23 所引《洞玄隐注经》中,道藏本《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中的“昆仑人鸟之山”被写作“须弥灵飞人鸟之山”,所以这里的人鸟山有可能影射佛教的须弥山,人鸟山上的众圣也使用“梵音”来读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五世纪初的道教方面,不仅知道佛教梵音的概念,而且知道梵音的含义是大梵天所制之音。因为佛教经典之中很早就说到了梵语是大梵天创造的语言,如三国吴支谦的《法句经序》之中说:
又诸佛兴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1]第4册,566说天竺的音韵与汉语的音韵不同,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比较难以翻译。还有,梁代僧佑(445-518)的《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之中,也说梵书是浄天(梵天)所作[5]78-87。
而《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之中,记载“梵音”和中夏音是道士读经的基本音韵:
太上玉经隐注曰:读经之法,法中夏之音,此是九天之正音也。第六十四大梵赞经讽诵制声,亦是正音。读经之音,当法此正音。[4]第6册,643-644
其中提到了读经时所使用的两种音韵,一种是中夏音,另一种是“梵音”,这两种音韵都是所谓的正音,所以道士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选择。
那么,为何“梵音”和中夏音这两种音韵都是道士读经的基本音韵呢?《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接着上文又说:
仙公曰:老子西化胡教外国读经时,多是大梵天音也。适道士所好者耳。[4]第6册644
即仙公(太极左仙公葛玄)解释说,“梵音”是老子化胡时在外国所使用的音韵。
老子化胡说在东汉時期已经出现,在三国时期基本确立,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兴盛。如《三国志》卷30《东夷传》裴注引用曹魏鱼豢的《魏略·西戎》写道: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6]859-860
说佛经的内容之所以与老子《道德经》不同,是因为佛经是老子经过西域去天竺时用来教化胡人的。
南宋谢守灏编《混元圣纪》卷4 中,也有老子化胡时使用“梵音”的记载:
至人(老子)通玄究微,应诸天诸地,异域方言,以至异类音声,莫不洞解。故与胡王问答,皆随其国之方言而与之言。当时随侍众真,即以正音纪录之,还传中夏。后人目曰《化胡经》也。犹齐人能为楚人言者,遇楚人则操南音与之言,及其纪之于册,则必用齐语矣。事出一人之手,不待翻译也。[4]第17册,820
其中说老子通晓各地的方言,在与胡王问答之时,就使用该国的方言“梵音”。而作为老子随从的众真,则用中夏音(正音)记录,并传回中国,即《老子化胡经》。按照化胡说的看法,佛教是由老子到了印度之后创造的,但这个观点必须解释的是,为何佛经原本都是由梵语写成,诸如“佛陀”、“涅槃”等佛经中的单词都是梵音的音译。因此,道教提出了上面的解释,并将“梵音”也作为道教中的正音。
成书时期大约在唐代之后的《洞玄灵宝度人经大梵隐语疏义》为《灵宝经》的《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之疏,其中写道:
问曰:西域天竺之音,多与梵音同,而中国音异,何也。答曰:音故是真文之音耳。道以音化彼,以文化此,故也。又问:音者,言也。文者,书也。书不尽言,文则为劣。答曰:不然。书不尽言,是世间之文耳。真文为三才之本,言教在布化之末,本胜末也。[4]第2册,519-520
即有人质疑,提出为何天竺之音与“梵音”相同,而中夏音(中国之音)却与“梵音”不同。对此的答复是,“道”(作为神格的老子)用声音来化胡,以文字来化中夏,所以天竺之音与“梵音”相同。又问,声音是语言,而文字用于记录,如果记录不了语言,那说明文字拙劣。对此的回答是,不能完全记录语言的文字是世俗的文字,而真文是三才(天地人)之本,语言的说教为次,作为本的真文胜过次的语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说到天竺之音与“梵音”相同,也就是说,道教中的“梵音”并不是与天竺之音同义,道经中出现的“梵音”都是指梵天音,而不是指天竺之音。还有一点是,这可以从新的角度解释道教经典重视“天书”的概念的原因。正如宋代郑樵《通志》卷35《论华梵下》指出:
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华书制字极密,点画极多。梵书比之,实相辽邈。故梵有无穷之音,而华有无穷之字。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采。华则字有变通,而音无锱铢。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7]511
说梵语依靠发音,而汉语依靠文字,所以梵语的发音很丰富,而汉字很丰富,梵人通过耳闻获得信息,而汉人通过目睹获得信息。因此,道教方面提出天书真文比印度记录梵音的佛典更为根本,是基于中国和印度的语言体系的特点。
三、道教之中“梵音”和中夏音的使用
在《灵宝经》中,“梵音”与中夏音并存,与此相对的是作为天书的秘篆文与隶书的释文也同时被使用。大约隋唐时期成书的《洞玄灵宝玄门大义》的《释赞颂第十一》有如下说明:
凡天书玉字,虽本出梵音,至于行教说经,亦随类得解。如书真文,本是三元八会梵天之音,今以隶书,又以此音译传书,则篆、隶两存。译则此显,而梵隐也。及《九天生神章》,则本文不传,梵音不出,但有隶字,而此音(中夏音)也。至于《内音玉字》,则有异同。同者亦以隶字传篆书。异者,不以此音(中夏音)译梵语。故文单,复不可解也。而天真皇人演之,仍用大梵之音,而语此间。即以此间之物,合玄都之事。故知真圣之音,音可以通施众物也。[4]第24册,739-740
其中举出,《灵宝经》的《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中所载的《九天生神章》没有秘篆文写成的本文,也没有记载梵音,而是用隶书(今之楷书)[8]256-257与中夏音写成。而《灵宝经》的《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中所载的三十二天的《内音玉字》同样是用隶书解释秘篆文,但在翻译时却使用了梵音的音译,而不是翻译成中夏音的汉文。所以,单独看《内音玉字》用隶书记录梵音的汉字,是无法得知其意思的。天真皇人记录《内音玉字》所使用的仍然是梵音,但却使用中夏之事物来解说《内音玉字》。
上面说到的《自然玉字》,是用梵音记录的三十二天的八字,共二百五十六字。《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卷3《大梵隐语无量洞章》说:
(元始)天尊普问四座大众,灵书八会,字无正形,其趣宛奥,难可寻详。天既降应,妙道宜明,便可注笔,解其正音,使皇道既,畅泽被十方。[4]第2册,545说元始天尊降三十二天二百五十六字大梵隐语无量之音。由于天书难以解读,所以元始天尊命令天真皇人标明其正音,并解明其义。
关于其中正音的含义,《洞玄灵宝度人经大梵隐语疏义》给予了解释,说:
正者,音中国之音也。天真皇人昔书其文以为正音者,以梵音名地上物,仍以为中国之正音也。论其音,在天上则为天上之正音,名太上之妙物,在他方国土亦得通用,名边国之异物,无所偏滞。此同是正音,但名物异耳。犹如外国亦用五音四声,中华亦用五音四声,物名不同,而出声者同也。一切万物皆然。天真皇人今日所解,止为中国之正音,不及边方异域也。[4]第2册,526
其中所谓正音就是中夏音(中国之音),这是否与《洞玄灵宝玄门大义》中说天真皇人用梵音来记录诸天内音玉字有矛盾呢?这应该是不矛盾的。因为根据随后的解释,中国和外国都用五音四声②,虽然事物的名称不同,但发出的声音还是一样的。天真皇人在解释《内音玉字》时,以中国的正音(中夏音)为基准。
此外,原本由秘篆文记载的天书《灵宝五篇真文》,其释文被称为中夏音(正音),因为参照《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中的《灵宝五篇真文》的释文可知,其内容已经完全汉译。关于这点,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写道:
诵毕,法师弟子各还复位,南北相对,披真文于案上,师诵真文序。毕,弟子再礼,次依《玉诀》正音,字字解说,口授读度,弟子承受诀言。[4]第9册,848
陆修静说,依照《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中用中夏音(正音)记录的释文,逐字解说《灵宝五篇真文》的内容。而《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中随后记载的《灵宝五篇真文》也不是秘篆文,而是《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中的隶书释文。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中使用隶书记录了秘篆文《内音玉字》的梵音的音译,但人们通过记录梵音的音译是无法解读其意思的,所以这种情况还需要像《内音玉字》那样,再对记录梵音的隶书的意思进行单独解释。所以,用隶书记录秘篆文的梵音的音译需要再进行一次解释。因此,像《灵宝五篇真文》这样,放弃了梵音,采用按照中夏音的意译的释文,就避免了再进行一次解释,在使用和理解时更为方便。
前面说到,道教基于化胡说,将“梵音”和中夏音都作为道经的正音。那么,当时的道士是不是也用“梵音”和中夏音两种音韵诵读经典内容呢?
推测成书时间大约在梁末至唐初的《灵宝经》的《洞玄灵宝丹水飞术运度小劫妙经》中写道:
大洞斋法,《素灵赞经》为颂,作罗天玄音。洞(玄)斋法,《玉京山经步虚颂》,梵天音。洞神斋法,《八素阴阳经》,中夏音。[4]第5册,857
说大洞斋法使用罗天玄音唱《素灵赞》,洞玄斋法使用“梵音”唱《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记载的《灵宝步虚辞》,而洞神斋法则使用中夏音唱《八素阴阳经》。大洞斋法使用的《素灵赞》,应该就是《上清经》的《洞真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最后的《太帝君偈大有妙赞》、《天帝君赞》、《太微天帝君诵》和《后圣金阙帝君诵》,因为《后圣金阙帝君诵》结尾说“谁能究此章,精诵《素灵赞》。以解九阴过,拨动七玄难。”关于洞神斋法所唱的《八素阴阳经》,梁代陶弘景《真诰》卷20 记载:“掾书《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回元隐道经》一卷,及《八素阴阳歌》一卷。”[4]第20册,606其中的《八素阴阳歌》大概就是指洞神斋法所唱的《八素阴阳经》。《无上秘要》卷20 所引《太上真人八素阳歌九章》中的《阳歌九章》和《阴歌六章》应该即是《真诰》中所说的《八素阴阳歌》。《无上秘要》卷38《授洞神三皇仪品》从《洞神经》引用了三首《阳歌》,即《阳歌九章》中的前三首[9]252,可知洞神斋法中应该也使用了《阳歌九章》和《阴歌六章》。
这样来看,《洞玄灵宝丹水飞术运度小劫妙经》中的这段内容,似乎记录了当时进行大洞斋法、洞玄斋法和洞神斋法的情况,其中提到了罗天玄音、“梵音”、中夏音这三种音韵,特别是说唱《灵宝步虚辞》使用“梵音”。罗天玄音,在其他经典中几乎看不到对其的记载,所以有可能是虚构的一种音韵。而“梵音”和中夏音的确是道教经典所记载的两大音韵,这是不是说明当时的道教科仪是使用“梵音”唱《灵宝步虚辞》呢?按照《玉经隐注》的说法,道士诵经时可以选择使用“梵音”或者中夏音,但事实上,所谓使用“梵音”似乎只是经典中虚构的情况,因为只说人鸟山上的众圣使用“梵音”诵经③。
《灵宝步虚辞》的内容虽然几乎可以直接解读,但其中出现了源自佛教经典的单词,包括“法轮”(第一首)、“诸天”(第二首)、“劫”(第二首)、“十方”(第三首)、“华林”(第三首)、“大乘”(第三首)、“六度”(第四首)、“梵行”(第四首)、“宿命”(第四首)、“魔王”(第四首)、“宿缘”(第四首)、“舍利”(第六首)等语[10]110-120,其中出现了梵音的音译单词,所以《洞玄灵宝丹水飞术运度小劫妙经》才说道士诵读《灵宝步虚辞》时,使用的是“梵音”。相比之下,《无上秘要》卷20《仙歌品》所载的《阳歌九章》和《阴歌六章》中几乎不使用佛教的音译单词,所以才会说被用于洞神斋法的《八素阴阳经》是使用的中夏音。
但是从整体来看,《洞玄灵宝丹水飞术运度小劫妙经》中提出罗天玄音对应大洞斋法、“梵音”对应洞玄斋法和中夏音对应洞神斋法应该是一种虚构,因为当时不存在名为罗天玄音的音韵。所以,即便道经经典中注明了“梵音”和中夏音的区别,但实际应该没有被严格遵守。通过对现在各地道观的调查和对民间道士的走访可以发现,道士诵经往往根据方言和民谣,无论是曲调还是发音,可谓复杂多样,无法简单地以“梵音”和中夏音划分。事实上,道教从理论上提出“梵音”和中夏音的概念,并非真是在指导道士如何诵经,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老子化胡说解释道经之中使用音译单词的原因,打消道教经典抄袭佛经的质疑。
注释:
①关于老子化胡说究竟是佛教信徒先提出的,还是道教支持者先提出的,学界存在争议,笔者倾向于是佛教信徒先提出的。关于老子化胡说,参见[日]吉冈义丰:《老子化胡経の原初形態》,载于同氏《道教と佛教·第三》,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日]镰田茂雄:《新中国佛教史》,东京:大东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二章“魏晋の佛教”之“四、道教の成立と佛教”之“《老子化胡経》”;[日]楠山春树:《東洋学叢書·老子伝説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9年2月;[日]洼德忠:《老子化胡说是谁提出的?——我的推测》,肖坤华译,《宗教学研究》1985年S1期;韩秉芳:《“老子化胡说”辨析》,载于连晓鸣主编:《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②五音是声韵学五声音阶上的五个级——宫、商、角、徵、羽,分别与喉、齿、牙、舌、唇的不同发音部位相配。参见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卷末附图神珙撰《反纽图》,以及北宋陈彭年等的《广韵》卷末附《辨音五字法》。四声是指表示音节的高低变化的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关于四声的形成时期和创始者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其形成于南朝时期。陈寅恪:《四声三问》,载于《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年第2 期。高华平:《“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载于《文学遗产》2005年第5 期。
③谢世维指出,通过《灵宝经》的《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的记载,可以推测当时道教使用诵经的音韵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原音韵的曲调,另一种是印度的梵呗。参见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49、250 页。不过,《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是说人鸟山上的众圣使用“梵音”诵经,关于现实之中的情况并没有记载。另外,谢世维还认为,“梵音”除了指代梵文发音之外,还指印度中亚等地随佛教经典传入的音乐诵唱方式。参见谢世维:《大梵弥罗:中古时期道教经典中的佛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版,第213 页。但是本文讨论的道经中的梵音是作为音韵的梵音,而不是作为诵唱方式的梵音。
[1]大正新修大藏经[Z].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2][日]水谷真成.梵語音を表わす漢字における声調の機能[C].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1968.
[3][日]赖惟勤.中国音韻論集:I[C].东京:汲古书院,1989.
[4]道藏[Z].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5]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
[6]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7]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Lothar Ledderose:Som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ix Dynasties[J].T'ong Pao 70,1984.
[9][日]大渊忍尔.道教とその経典[M].东京:创文社,1997.
[10]Kristofer Schipper:A Study of BUXU:Taoist Liturgical Hymn and Dance[C].Studies of Taoist Rituals and Music of Today.Pen-Yeh Tsao and Daniel P.L.Law,Hong Kong:The 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ical Research in HongKong,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