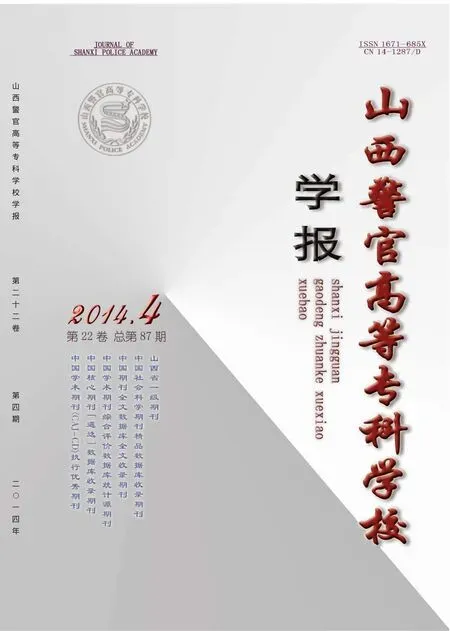寻衅滋事罪对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规制
2014-04-09江奥立
□江奥立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法学研究】
寻衅滋事罪对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规制
□江奥立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网络虚假言论纳入寻衅滋事罪进行规制颇受争议。具体而言,对寻衅滋事罪的信任感、信息网络化时代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上的差异构成了寻衅滋事罪认定的观念障碍,在运用本解释的过程中,对“虚假信息”、“公共场所”的理解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事实上,寻衅滋事罪自身的明确性,罪刑法定原则在网络时代的自我救赎,以及对言论相对自由的坚持,能够消除解释适用中的观念障碍。基于“信息差”的客观性,强调“虚假信息”中言论本身的恶性;回溯公共场所的社会功能,承认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亦能消除其中的技术障碍。
虚假言论;寻衅滋事;观念障碍与消解;技术障碍与消解
毫无疑问,当下社会已经迎来了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像QQ、微博等基于用户关系进行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逐渐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网络交流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和对象不特定的特点,从中人们可以进行更加便捷地交往。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以往不曾出现过的法律问题。网络谣言是新近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的被捕,表明了法律开始介入此类行为的决心。2013年9月6日,两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解释将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的行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对此,学界有支持者亦不乏反对者。本文试图综合各方意见,对上述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认定的观点作系统的肯定性的论述。
一、司法解释中以寻衅滋事罪认定的意见分歧
当法律决定用旧有的文本关注新兴的事态时,将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间距离”①在理解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阈,一个是文本的视阈,另一个是理解者的视阈。文本有其自身的视阈,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历史存在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理解者也有其自身的视阈,它是由理解者自身所处的历史境遇所赋予的。这样一来,两个视阈便存在差异,伽达默尔对此称之为“时间距离”。进行规范上契合。新近司法解释将散布谣言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认定,于是人们便以此为基点试图拉近事实与规范,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1.寻衅滋事罪是属于妨碍公共管理秩序的犯罪,根据2013年5月27日公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寻衅滋事发生的地点限于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有形的场所,信息网络只是一种交流平台,不属于公共场所。2.将网络上散布谣言的行为归结为是寻衅滋事罪第四款的“起哄闹事”并不合适。3.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代刑法的逻辑出发点,刑法第293条的适用有类推解释之嫌。[1]4.谣言”作为一种言论,不能因其内容“不符合事实”就能入罪。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把内容“符合事实”作为受保护的先决条件,因为法律不可能对人要求做不到的事情。传播内容不符事实的消息,也是一种言论,原则上也受宪法和法律保护。[2]
持赞成意见者则认为,1.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公共场所”概念作符合信息社会变化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对此,刑法在以往的解释中也存在先例,即将淫秽图片、视频也解释成“淫秽物品”。2.“公共场所”的理解具有特定性,这意味着“公共场所”概念的界定要结合具体犯罪行为的特点。3.在信息网络系统空间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不会造成信息网络系统空间“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但事实上,网络信息的传播直接影响到现实世界。因此,不存在欠缺“公共秩序”混乱要素的问题。[2]4.网络谣言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不仅可能引发社会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还可能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行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即使辟谣之后仍然余害难消。社会危害性的提高使得刑法介入评价成为必要。[3]
事实上,两种意见均有合理之处。在本文看来,合理的结论来自理论立场的坚定和争议概念的明晰,然而,旧规则与新事态在匹配的过程中必不可免地存在观念障碍和技术障碍,认真总结与剖析这些障碍是深入讨论该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本文写作的重点。
二、以寻衅滋事罪认定的观念障碍及消解
(一)对寻衅滋事罪的信任危机
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分解成数个罪名以此来摆脱外界的诟病,但即使如此,作为解构后数个罪名之一的寻衅滋事罪仍引来不少非议。“由于刑法第293 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类型,内容比较宽泛且使用了‘随意’、‘任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需要价值判断的表述,司法机关对本罪的认定产生了许多困难,刑法理论也认为寻衅滋事罪成了一个新的‘口袋罪’”[4]对寻衅滋事罪的描述看似条款明晰,但其可涵涉的范围却无法确定,这种似是而非的规定显然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对条款明确性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甚至提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不具有独特性,司法适用也缺乏可操作性,应该废止该罪名。[5]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寻衅滋事罪产生了信任危机,认为只要以本罪加以规制的情况都有冲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本文认为,这种认识并不理性,结合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法益分析,该罪名的构成要件有其独特之处。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按博登海默的看法,所谓公共秩序,是指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无序概念则表明存在着断裂(或非连续性)和无规则性的现象。[6]这样看来,“公共秩序做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它展示的是公共生活的有序状态和动态平衡的结构。”[7]喻言之,社会公共秩序成流体状,何谓破坏,何谓不破坏,抽象判断难有定论。寻衅滋事罪规定的四个行为类型,分别从社会交往中人的身体健康、财产安全、活动自由以及社会评价着手,以此作为判断破坏公共秩序的现实载体。换句话讲,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会构成寻衅滋事罪,只有发生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入罪,仅限于多数人在场的情况。其实,有没有破坏公共秩序的判断并不困难,真正让人无所适从的是危害性程度的辨别,寻衅滋事罪中多处提到“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表示危害性程度的用语,对这些高度抽象的规范用词的判断势必因人而异。2013年5月27日公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专门作出详细规定,通过对行为次数、行为方式等的设置,将抽象的综合判断转化成了具体要素的判断。在刑法理论与司法解释的共同努力下,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已然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明确性。
(二)信息网络化时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定位
当下刑法解释理论的研究似乎遇到了困境,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紧扣文义、严格解释的要求,时刻提醒解释者不要走太远;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青春狂躁症”*陈兴良教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死刑与宪法”系列讲座中提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相当于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青春期,从小孩到大人转换的年龄,那些对小孩的规范已经约束不了他,但是又没有掌握和适应大人的那些规范,同时又容易叛逆,容易违规。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状况,犹如青春期孩子常有的“青春狂躁症”。如期而至,爆发出各种各样不曾有过的刑法难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选择坚守刑法严格解释的立场,刑法无疑将成为一纸空文。如何权衡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挑战,是当代刑法解释理论必须考察的重要命题。
当代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工业社会经由其本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8]除了技术性风险以外,政治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等制度化风险也是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并不仅仅限于环境与健康,而且包括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变革:职业模式的转化、工作危险度的提高、传统与习俗对自我认同影响的不断减弱、传统家庭模式的衰弱和个人关系的民主化。[9]其中,网络的发展便是典型一例,通达的网络技术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也孕育出刑法所不曾关注过的领域,“网络空间”、“虚拟财产”等概念都亟待在刑法规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信息网络化的结局是“实然”与“应然”之间的距离骤然拉大,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匹配难以顺利进行,从而造成了刑法上的风险。面对如此多变的现实,刑法若仍以安分守己的姿态扮演其在法律体系中的角色实有自裹手足之嫌。换言之,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用语可能含义的探讨上,这是因为,“语言是开放的,它的意义边界并不存在警示的标志;语言本身无法实现自我界定,确定性系由社会实践所赋予。”[10]当社会出现新的事态时,刑法不该以既定的形态从上而下俯瞰,而应该通过由下及上的带有目的性的检视来确定文义的外延,最后实现刑法的社会规制机能。总而言之,社会转型期需要刑法解释负有一定弹性,严格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不能满足此要求。
(三)言论自由的相对保护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任何言论都必然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在立法上,有以美国为代表的绝对保护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相对保护模式之争。其中,美国的绝对保护模式认为,“在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普通立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联邦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及各州制定的法律,因限制个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行使而成为违宪的法律,并有权终止执行侵犯个人宪法基本权利法律的效力,宣告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法院直接适用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从基础上就杜绝了对于言论自由的立法限制。”[11]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布伦南大法官执笔写到,“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看,这些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促成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来不拒绝对不恰当、甚至错误的言论进行保护。在自由争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来意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12]这些观点时刻提醒解释者要对各类言论怀容忍之心。但是,恶意言论难道就真的没有法律评价的必要?
在很多场合,言论的杀伤力较之物理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将所有言论都披上言论自由的外衣,然后任之大行其道实在有悖法理。恶意言论应该接受刑法的规制,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虽然宪法在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时候没有明确指出恶意言论不受保护,但以宪法的整体精神来讲,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有前提的,若言论表达的效果是害及他人的权利或危害公共秩序的实现,这些内容势必不为言论自由所包括。从立法现实来看,刑法中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对言论的刑法规制并非一概排除。
其次,谣言作为典型的恶意言论存在现实的危害。正如庞勒所指出的那样,“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13]详言之,谣言具有以下三大危害,第一,谣言容易左右舆论导向,舆论则衍生道德审判,道德审判将动摇司法的独立性,化解法治壁垒;第二,正所谓“三人成虎”,谣言会使人们的是非观产生混乱;第三,客观事实的发现往往不易,谣言使得真相更加难以揭露。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技术就像一个放大镜,将这些危害性瞬间放大数倍,对此,刑法有必要考虑介入。
再次,学界在讨论言论自由的时候,一般针对言论的价值和言论的界限展开。言论界限的研究是为了言论价值而服务的,有什么样的言论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论界限观。对于言论价值,博克(Robert Bork)归纳为以下四点,促进个人才能之发展;自由表达带来快乐;增进社会的稳定以及保障政治真实之发现与传布。尼莫(Melville B Nimmer)将之归纳为,民主对话功能;自由表达本身即是目的;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的安全阀。其中,博克的观点尼莫有共同之处。[14]各家观点虽有不同,但大都表达出增进知识与获致真理;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这三种含义。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以上三种价值。然而,言论绝对保护的观点无形中违逆了宪法赋权的初衷,最终的目的也无法实现,显然不足以采之。
最后,正如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绝对的规则必然导致绝对的例外。言论的绝对保护者也并非真正容忍所有的言论。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联邦最高院判决《纽约时报》胜诉的重要原因是沙利文无法证明对方的恶意,言外之意,只要能够确定行为人的言论是恶意的,该言论就应该得到规制。孟德斯鸠的“如果有人说我们个人或我们政府的坏话,我们不愿意加以处罚:如果他是因轻浮而说的话,就应该轻视他;如果是因疯癫而说的话,就应该可怜他;如果是咒詈的话,就应宥恕他”[15]曾被绝对保护者视作圭臬,其中,被容忍的言论也没有包含恶意的言论。既然如此,言论的相对保护应该得到承认。
三、以寻衅滋事罪认定的技术障碍及消解
凝固的刑法与流动的社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疏远,解释的任务在于拉近刑法与社会的距离,使社会现实得到有效的调整。然而,刑法解释不是一劳永逸之事,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冲突的新型化都会促使司法者重新审视刑法,以及时回应不断变动的社会所提出的现实需求。在本次司法解释出台后,几个争议问题急需厘清。
问题一:何种虚假信息才值得寻衅滋事罪评价?
对此,理论上有多种观点,1.公共福祉理论。日本宪法规定,国民不得滥用宪法保障的权利,并规定国民负有为公共福祉而利用这一权利的责任。换言之,害及公共利益的言论不能受到保护;2.明确、即刻的危险原则。这一原则由霍姆斯大法官提出,认为如果言论具有实际、明确的有害性,并能够直接引起某种危害的,就需要法律调整;3.事后审查原则。该原则认为言论的危害性只有通过事后审查才能得出,是禁止“事前抑制原则”的逻辑成果;4.比例原则。该原则由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提出,要求在处理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时,要衡量、比较它们的轻重、大小,按照利益的位阶来进行取舍。[16]我们发现,这些观点之间没有形成必然的对立,只是或多或少在强调某一侧面的重要性,其中,明确、即刻的危险原则关注了言论本身的恶,即在具体环境之下可能具有的危害。公共福祉理论和比例原则则更重视言论所导致的损害结果,至于是什么言论并不重要。事后审查原则的逻辑在于从保障言论的自由发出,只有在确证言论造成实害时,这种言论才有必要纳入刑法的视野,因此,事后审查原则与公共福祉理论、比例原则更加亲和。
单纯的强调言论本身的恶或者言论所造成的实害都不妥当,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仅因为言论本身与事实不符或者言论内容比较刺耳就动用刑法,显然会过分压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另外,“明确、即刻的危险”也难谓一个富有可操作性的标准,这就更增加了以言论本身的恶性作为入刑标准的难度;另一方面,语言在传播过程中极易出现原意的失真,传播学上称之为“信息差”,“信息差是一种普遍存在,这种普遍存在和干扰的普遍存在是一致的。干扰不仅存在于传播过程中的传者、受者、语言和媒介,也存在于过程之外的情境与社会,因此,在人际语言传播中,信息差的产生是在所难免的。”[17]这种语言传播上的“信息差”,通常会将初始言论的小错误放大至大谬误,另外,在言论传播过程中,其他传播者都有意或无意地推波助澜。可见,仅因言论而导致社会秩序紊乱便追究言论发布者的责任并不公平。
在本文看来,言论本身的恶性与言论所造成的实害应予以同等关注。其中,对前者的判断不能仅局限于言论是否虚假,鉴于“信息差”的客观存在以及对处罚范围的限制,应对虚假信息的内容作有意义的限定。即本司法解释中寻衅滋事罪所认定的虚假言论,该是指让公民对国家、社会秩序产生不安感的信息。结合当下常见的谣言类型及社会的现实反映,可以认为以下几类虚假信息有评价的价值:1.网络政治谣言。主要指向党和政府,涉及政治内幕、政治事件、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等内容,让公众对国家秩序、政治稳定、政府工作产生怀疑和猜测,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如“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就属于这一类谣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宪法赋予公民建议权和批评权,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有理有据的反对,即使言辞激烈、结论偏颇也不能归结到这里的“网络政治谣言。”另外,对于个别官员的批评、揭发尽管内容虚构,由于不具备可能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恶性,因此也不是这里的“网络政治谣言”;2.网络灾害谣言。指捏造某种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或者捏造、夸大已发生灾害的危害性信息,引起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如引发“抢盐风波”的核辐射谣言、引发群众逃亡并导致4人遇难的响水县“爆炸谣言”等都属于这类谣言;3.网络恐怖谣言。这类谣言一般是虚构恐怖信息或危害公众安全事件信息,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引起公众对政府管理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如“‘针刺’闹到重庆”等属于这类谣言;4.网络犯罪谣言。这类谣言一般是捏造一些骇人听闻或令人发指的犯罪信息,引起公众愤怒、恐惧,引发公众对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或某些群体的不满。如“黔西部分乡镇儿童被抢劫盗肾”等属于这类谣言。5.网络食品及产品安全谣言。是指捏造或夸大某类食品或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引起公众对该类食品或产品的抵制,导致该类食品或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损失,如“皮革奶事件”等就属于这类谣言。综上,本文认为,司法解释中可作为寻衅滋事罪评价的“虚假信息”应包含四个要素,即故意散布、信息虚假、虚假信息的内容极易让人对国家、社会的秩序产生不安感(主要是以上五种类型)、事后审查确实造成现实社会秩序的混乱。
问题二:网络空间是公共场所?
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的公共秩序,这就意味着本罪的行为需要发生在公共场所,否则,无论如何也无法评价为本罪。依照传统的观点,刑法上的“公共场所”应指物理性空间,而《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司法解释延续了这种思路,指出“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这样看来,“公共场所”大体可以被认为是公众进行工作、学习、经济、文化、社交、娱乐、体育、参观、医疗、卫生、休息、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其设施的总称。其中并不包括虚拟空间,所以互联网还是无法纳入“公共场所”的范围内。然而,这种解读是否合适值得深思。
一方面,传统观点限于社会的发达程度,将“公共场所”限定在车站、码头、机场等具有物理性特征的场所,然而,随着互联网这一新媒介的产生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信息的传播与获取慢慢转移到了网络平台,人们的公共空间得到了极大的延伸。有认为,“公共场所,是指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4]至于出入场所是为了交换信息、交换物资抑或接受、提供服务在所不问,换言之,公共场所只是供不特定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平台。网络空间作为信息交换的平台,具有程度极高的开放性,网民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消息,同样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发布信息,毫无疑问,网络空间具备“公共场所”的特征。
另一方面,同样的法概念在不同的法规则下有不同解释的可能。“如果法律在不同的地方采用相同的概念与规定,则应认为这些概念与规定实际上是一致的。[18]
这是许多解释者的期待,但事实上不可能如此,如若将强奸罪中的“胁迫”与抢劫罪中的“胁迫”作相同的理解,像以揭发隐私为要挟的胁迫就无法被包含,这势必会缩小强奸罪成立的范围。又如根据强奸罪的规定,“妇女”是指已满14周岁的女性,未满14周岁的女性为“幼女”,若坚持这一规则,刑法第240条中的加重情节“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就无法包含“奸淫被拐卖的幼女”这种情况,这显然有失公正。事实上,法概念含义的确定与具体的行为类型紧密相联,如在聚众斗殴罪中,斗殴是物理性接触,此时就只能把公共场所解释为有形的物理性的场所。在寻衅滋事罪中,由于行为类型包含恶意言论,因此,对公共场所的理解也就不受物理性的限制。据此,《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单沿用对“公共场所”的传统理解实际上并不合适。
问题三:寻衅滋事罪第(四)类行为中前后“公共场所”如何理解?
在承认网络空间是公共场所之后,寻衅滋事罪第(四)类行为,即“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中前后两个“公共场所”就无法做等同理解。详言之,第一个“公共场所”指的是虚拟空间,第二个“公共场所”则指的是现实空间。虽然网络空间也存在一定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仅仅是为了保障信息传播的通畅和有效,网络作为信息交流的平台,只是人类交流空间的延伸,仅仅是破坏互联网信息交流的秩序尚不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定,换句话讲,只有在网络恶意信息蔓延至现实空间后导致现实生活秩序的混乱的场合,刑法才有必要介入。据此我们发现,在讨论网络空间是否为“公共场所”时,应对“公共场所”和“破坏公共秩序”两个概念作分别的理解。
[1]曲新久.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912/c40531-22898784.html.访问日期: 2013-09-15.
[2]林 达.为什么“散布谣言”不能轻易入罪[EB/OL].http://view.news.qq.com/a/20110314/000048.htm.访问日期:2013-09-15.
[3]于志刚.制裁谣言的罪名体系需扩大[EB/OL].http://edu.ifeng.com/gaoxiao/detail_2012_02/07/12353793_0.shtml,访问日期,2013-09-15.
[4]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政治与法律,2008(1).
[5]王良顺.寻衅滋事罪废止论.法商研究,2005(4).
[6]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27-228.
[7]陈绍芳.公共哲学视角的公共秩序价值解析.社会科学家,2009(1).
[8]乌尔里西·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2.
[9]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2.
[10]劳东燕.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7.
[11]邢 璐.德国网络言论自由保护与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德国研究,2006(3).
[12]斯伟江.你,生逢其时[EB/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1081943598.html.访问日期,2013-09-15.X
[1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9.
[14]侯 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北大法律评论,2000(3).
[1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99
[16]陈桃生.网络环境中的言论自由及其规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7]付义荣.试论人际语言传播中信息差的生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
[18]伯 阳.德国公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25.
(责任编辑:王战军)
RegulationsontheActionofSpreadingtheFalseInformationinOffenceofDefianceandAffray
JIANG Ao-li
(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0042,China)
The file“The Explanation of Several Issues on Applying the Law to Deal with the Cases of Using Information Network to Carry out the Slander and Other Criminal Cases”brought the false statements on the network in the regulation field of defiance and affray and caused heated disputes.Particularly,sense of trust on the offence of defiance and affray,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principle of a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in the network epoch and the difference on the cognition abo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formed the conceptual obstacles in identifying the offence of defiance and affray. In the course of using the explanation,there are great disagreement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false information”and“public places”.In fact,the clarity of the offence of defiance and affray,the self-redemp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in internet epoch and the persistence in the relative freedom of speech can contribute to removing the conceptual obstacle in applying the explanation.Emphasizing the malignancy of statement itself in the false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objectivity of the information difference,backdat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ublic places and admitting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public places can also eliminate the technical obstacle in it.
false information;defiance and affray;conceptual obstacle and eliminating;technical obstacle and eliminating
2014-06-30
江奥立(1990-),男,浙江瑞安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D924.32
A
1671-685X(2014)04-0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