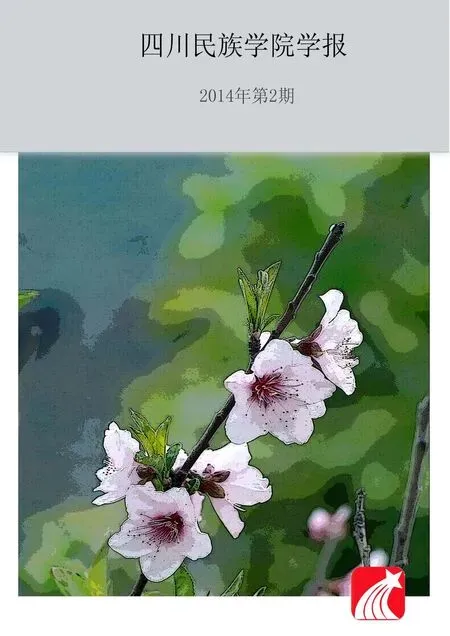国内近三十年来驻藏大臣制度研究综述
2014-04-09叶健
叶 健
驻藏大臣制度并非清朝立国之时就存在,它是历史的产物,伴随清军入藏平定内乱和抵御外侮之后设立,遂而成为定制。最初作为钦差大臣的驻藏官员,仅仅协理西藏事务,尔后其职权才日臻完善,其地位也与达赖、班禅平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直至1727年清廷才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并随清王朝的兴盛、衰落、灭亡而成为过去之制。鉴于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在民国时期已有研究此方面的学术专著,丁实存的《清代驻藏大臣考》是当时唯一一部专著。尔后,新中国时期,国内学界也并未对其深入研究,只有张林的《关于驻藏大臣的几件文物》[1]。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驻藏大臣的研究局面才得到改善,学术成果逐步增多。该文回溯此间的学术成就,并提出粗浅见解,不足之处望方正。
一、研究资料
有关研究驻藏大臣的史料,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或重刊的原始资料,如 (清)蒋良骐撰,林树惠、傅贵九校点的《东华录》,(清)魏源撰的《圣武记》。尔后,又出版不少编辑史料,如顾祖成、王观容、琼华等编的《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编的《清实录藏族史料》,吴丰培编的《景纹驻藏奏稿》《联豫驻藏奏稿》《清代藏事辑要续编》及《清代藏事奏牍》,还有再版的 (清)孟保撰的《西藏奏疏 (附西藏碑文)》,(清)张其勤著的《清代藏事辑要》。此外,《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有一节介绍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张羽新编著的《清朝治藏典章制度研究》也有所涉及。而关于驻藏大臣的专著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参考,如萧金松的《清代驻藏大臣之研究》,吴丰培、曾国庆编撰的《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和《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贺文宣编著的《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车明怀、李学琴编著的《天朝筹藏录·清朝筹边事略与驻藏大臣为政纪实》。
二、驻藏大臣制度之研究
至驻藏大臣设置的原因,林黎明、顾效荣、张云侠、曹育明、陈柏萍、平措塔杰、胡群琼均撰文论述过。其中,林黎明的《清朝前期对西藏的靖绥边计与驻藏大臣的设置》[2],认为驻藏大臣的设置就是使其适应清朝“恩威相济”的政策,以军事力量作为控制达赖这面宗教旗帜的保证,而派驻藏大臣的直接原因,即是防止准噶尔部分裂割据西藏,维护祖国的统一。顾效荣的《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简述》[3],认为设立驻藏大臣之起因有三个阶段,其一清廷在西藏地方政权的支柱,达赖与和硕特蒙古的地位即将不保,派官驻藏刻不容缓;其二发生蒙古准噶尔部袭扰西藏事件;其三西藏噶伦的内讧引发“卫藏战争”。其实,置驻藏大臣根本意图是对西藏地方充分行使主权、进行更加有效治理、巩固西南边防、冀望长治久安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曹育明[4]从组成社会结构的三方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出发,认为封建农奴制下的庄园经济的封闭性、藏传佛教之出世思想及其对现实观念的淡薄、不完全的贵族政治,致使西藏内乱不断,设立驻藏大臣能够充分展示国家的调节作用,而使清廷有效地治理西藏并使之内部稳定。胡群琼的《清初设驻藏大臣原因分析》[5],作者赞成顾效荣有关设置驻藏大臣原因的观点,还借用了曹育明以社会结构解释驻藏大臣建立的起源,认为政治经济原因、内忧外患、政策原因是驻藏大臣设置的三因素。
驻藏大臣设立的时间,学者们的分歧在于围绕驻藏大臣的创始和制度化的论证,认为设置于康熙年间者,看重于是否派人驻藏;赞成建立于雍正年间者,趋向于驻藏大臣的系统化与制度化。林黎明、顾效荣、张云侠等赞同1709年是清政府派人“前往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的时间。上述学者与吴丰培、曾国庆、张羽新以及陈柏萍等认为1727年是设立驻藏大臣制度的开端。其中顾效荣认为1709年至1723年是驻藏大臣制度酝酿期,而曾国庆[6]认为直至1727年之前是驻藏大臣的酝酿、试办阶段,因而只能把1727年清廷任命僧格和玛拉驻藏办事作为设立驻藏大臣及其制度的开端。苏发祥结合不同历史时期驻藏大臣职权的变化情况,把驻藏大臣制度的沿革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时期为1705至1725年,完善时期为1726至1751年,强化时期为1751至1793年,平稳过渡时期为1794至1845年,衰落时期为1845至1911年。赵心愚认为驻藏大臣制度确立于1727年的看法出现很早,至少雍正末乾隆初就已存在,并已成为当时一些学者和官员的主张[7]。平措塔杰[8]根据清中央官员实际到任时间,认为1706年为清廷派员入藏办事的发端,1728年是设置驻藏大臣的确切时间。该观点是学界中少有的论断。
关于驻藏大臣衙门位置的考察。欧朝贵认为驻藏大臣驻地及衙署曾经变动,先后于大昭寺东北方向的通司岗 (即双忠祠所在地)、甘丹康萨 (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私宅)、扎什城 (拉萨以北7里处、前扎什衙门兵营的前面)、拉萨正街商上官房,以及大昭寺西面的鲁布地方为衙署办事[9]。曾国庆在《关于驻藏大臣设立的几个问题》一文,也援用了欧的观点。
驻藏大臣的职权地位之研究,顾效荣认为清王朝授予驻藏大臣一开始就很大,“总理西藏事务”,并非只有协办之权。驻藏大臣作为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清王朝授予之职权大于达赖和颇罗鼐,有处理西藏一切事务之全权,即“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察明驻藏大臣办理”[10],并拥有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兵权、司法权、外事权、财税权等。之于此方面的研究,张羽新的《驻藏大臣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历史考察》[11]是较为权威的成果,他认为虽然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职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即从1727年至1750年的大约20余年的监督藏政时期、从1751年至1793年大约40年与达赖喇嘛共理藏政时期、从乾隆末年到清朝灭亡的130余年的主持藏政时期。但是其地位和职权却是一贯的,即“驻藏大臣既是‘钦差’,又是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法定地位和职权,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总揽事权,主持藏政”。范庆迎的《清代前期驻藏大臣权限的变化》[12],只是引用了张的观点,创新之处谈不上,属于概述性质的论述。冯智的《清初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及其体系》[13],认为清廷在西藏的用兵变化,使之认识到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对于维护西藏稳定和祖国统一极具重要的作用,遂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制度并逐一加强与完善,并将藏北三十九族地方及达木蒙古地方直接交予驻藏大臣,直至清末。冯的研究较于张的研究,其创新之处是细化了驻藏大臣的职权与地位的研究,以军事建制为切入点,深入论析了清廷在西藏的军事建制问题。此外,关于从礼仪问题看驻藏大臣之权威与地位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马林、刘丽媚①马林:《从礼仪之争看驻藏大臣同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6期;刘丽媚:《关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相见礼仪问题》,《中国藏学》1997年1期。。
之于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的研究,顾效荣最先论及,而曾国庆在顾的基础上作出系统地阐述,他的《论清代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14],认为在清一代百余位驻藏大臣中,出类拔萃者有之,颟顸误国者有之,庸庸碌碌者有之,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清朝的用人制度,即清廷一味任用满族“缘事革职”或“中材谨伤”旗人罚边效力赎罪,亦或是年迈多疾者履藏,“才堪办事之人多留京供职”,而大量博学多才,有志报国之汉、蒙等族臣民却闲置不用……。尽管如此,但客观立场上是不能抹煞驻藏大臣对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保护藏族人民的利益,促进中华各民族间亲密联系,抗击外侮、平息叛乱 (内讧),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扎西次仁的《从“拉萨痘碑”看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15],从历史遗存出发,认为和琳任期内充分履行了驻藏大臣在“赈恤黎民,安抚百姓”的责任。和琳担任驻藏大臣期间,西藏发生了空前的天花病 (出痘疹),他组织为病患捐资建房,并教给种接牛痘的方法,使得西藏的天花病很快得到控制和最终根治,这就是“拉萨痘碑”立碑之原委。同时陈柏萍、曾国庆、许广智、赵君、周强、车怀明从不同视野角度撰文研究驻藏大臣制度对西藏施政的影响与作用。其中曾国庆的《论驻藏大臣对治理西藏的影响》[16],认为从1727年至1911年的驻藏大臣不仅代表着封建王朝神圣的尊严和至高的权力,更体现了国家主权的意志。一部驻藏大臣制度史,实际上是一部清朝治理西藏的政治史,也是一部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史。许广智等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认为从1840年至1911年间先后有54名驻藏大臣赴任,由于清中央政府对外采取“妥协退让”策略,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使清政府与西藏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而且给英、俄帝国主义提供了契机,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了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又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抵制改革,遂投靠英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保证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保持元代以来形成的传统政治隶属关系[17]。周强的《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18],认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实施可谓是清政府治藏政策“法制化”的最高成果。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即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驻藏大臣人物之研究
(一)有关驻藏大臣前期 (雍正、乾隆时期)人物的研究
胡岩、曾国庆、马云华、邓锐龄、唐文基、张羽新、孙文杰等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了这一时期的驻藏大臣。其中胡岩《马腊、僧格驻藏考略》[19],作者分析了僧格、玛拉入藏的原因,认为以马腊、僧格二人为驻藏大臣和驻藏帮办大臣,统领留驻西藏的两千清军。严格地讲,虽然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但正是从马腊、僧格二人入藏开始,清朝改变了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时那种有事派人入藏办理,事毕令其返京复命的办法,而在西藏长期派驻大臣和军队。邓锐龄《1789-1790年鄂辉等西藏事宜章程》[20],认为鄂辉等所立的两件章程,在西藏边防军事设置、地方政府政务运作规范、执政者的权限上做了一些改革。然而两次廓尔喀之役相距极近,故执行尚未充分,但成为尔后福康安等的全面改革藏政的先声,如章程中第一次提出驻藏大臣应该每年巡视后藏地区的要求,被福康安等的善后章程所沿承。马云华《留保柱献佛》[21],认为留保柱护送六世班禅安全抵京朝觐,深得乾隆皇帝之赏识,是其一生最光辉的时期。尔后他却因擅自给七世班禅之父官职而触怒乾隆,被革职、永不叙用。留保柱向乾隆帝敬献佛像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谢罪。同时,他也是目前已知的驻藏大臣中进献佛像数量最多的官员。唐文基《浅论和琳》[22],作者从客观立场分析了和琳在藏期间的功绩,认为和琳一生最卓著之事,是在抗击廓尔喀斗争中以及尔后担任驻藏大臣期间,在西藏地区为维护国家统一所作的贡献。之所以他会蒙受不公正的评价,皆因其哥哥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之贪官。松筠作为驻藏大臣之佼佼者,故对其研究的学者甚多,如徐燕、顾浙秦、康建国、赵学东、崔艳萍、郭院林、张燕、周学军等等①研究松筠的学术成就可分为三类:(1)综合评价。纪大椿《论松筠》(《民族研究》1988年3期),牛小燕《论治边名臣松筠》([D]中央民族大学2006-05)。(2)对松筠任职西藏的经历和功过进行论述和评价。康建国、赵学东《驻藏大臣松筠的治藏功绩及其治边思想》(《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1期)。(3)研究松筠的著作并分析其思想。云峰《松筠及其〈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诗述评》(《西藏研究》1986年3期),徐燕《论松筠的经济思想》(《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期),顾浙秦《松筠和他的〈西招纪行诗〉》(《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1期),崔艳萍《驻藏大臣松筠和〈西招图略〉考略》(《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9年8期),郭院林、张燕《松筠“文化治边”思想及影响研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期)。(4)对松筠生辰的考察。周学军《松筠出生日期考辨》(《历史档案》2011年1期)。。德彬的《松筠治藏研究》[23],认为松筠在西藏做了三件大事:宣扬皇恩;在经济上进行调整和改革;加强西藏边防。作者通过对松筠治藏过程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清朝民族政策的得与失。刘忠的《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对西藏的改革》[24],分析了松筠在西藏进行改革的背景、内容及其意义,认为松筠的改革虽然有其局限性,但给当地的藏族群众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得到了藏民的拥护。
(二)有关驻藏大臣中期 (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人物的研究成果
赵鹏飞《驻藏大臣孟保及其处理西藏事务研究 (1838-1842)》[25],从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研究领域的空白,作者主要概述了孟保出任驻藏大臣的时代背景和其治理西藏边疆的功绩,力争给予孟保符合事实的评价。关于驻藏大臣琦善的研究,邓锐龄、张庆有、金雷、周伟洲根据不同知识结构论述了他们的观点。邓锐龄[26]认为琦善似乎不象《清史稿》所说的那样,从根本上废除了乾隆时建立的制度。确实,他放弃了驻藏大臣对于财政收支的审核,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驻藏大臣的一部分职权。但从全体上看,他所立的章程还是在扩大着这个权力的。而后驻藏大臣权力的削弱不应归结于琦善在藏期间的改革,而需与当时清政府在全国的政治效力相联系。不过,周伟洲的观点与之略有出入,赞成邓锐龄提出“琦善的改革致使驻藏大臣的权力受到削弱”的观点,考察了琦善在藏施政之情,认为琦善的《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中“奏请放弃对商上财政的审核权、奏罢训练藏军成例及停止派兵巡查部分地区 (哈拉乌苏),对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确有损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开启了今后驻藏大臣权力的削弱之倪端。琦善对此是难辞其咎的”[27]。
(三)关于研究驻藏大臣后期 (光绪、宣统时期)人物的学术成就
下文根据这一时期驻藏大臣登场的次序作简要的学术回溯。邓锐龄《清代驻藏大臣色楞额》[28],作者依据档案史料重现19世纪80年代清驻藏大臣色楞额在西藏的施政作为,着重叙述他所遇到的若干重大事件及应对方策。全篇论叙精详,弥补了旧史书色楞额传的不足,为今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至于研究文硕的学术论文,有五篇均论析了文硕的抗英情结,其中刘丽媚《文硕密折的保藏抗英情结》[29],认为文硕密折的保藏抗英情结,正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各族人民以反抗外来侵略者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清朝把文硕革职,正是对这种民族精神的打击和扼杀。近代史上,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研究文硕密折保藏抗英情结后得到的历史启示。张羽新《驻藏大臣长庚及其〈为西藏事上书〉》[30],认为对长庚的研究,有助于西藏地方史的研究和了解清朝治藏政策的变化。同时,他留下了一篇鲜为人知的《为西藏事上书》,反映了当时西藏政治风云的变幻和他的治藏思想,是一篇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
馨庵、康欣平、丁耀全、平措达吉等发表过有关有泰的研究论文,其中康欣平的《有泰与清末西藏政局的演变》[31]和《前倨后恭:有泰与联豫在西藏期间的交往》[32],前者作者认为“驻藏大臣有泰不顾清朝中央政府命他即刻赴边谈判的旨意,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最终使西藏地方被迫与英帝国主义签订《拉萨条约》”[33]。他的所作所为不仅给国家利权造成重大损失,而且成为促使清末民初西藏政局恶化的因素之一。后者,他认为虽然有泰与联豫在藏关系演变事很细小,但小细节关联着西藏近代史上张荫棠查办藏事的重要事件。从有泰与联豫关系之演变着手,在某种程度上亦可做到以小见大,从而丰富、深化对历史的理解。任新建的《凤全与巴塘事变》从这一事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来探讨巴塘事变的始末,对凤全进行了评述,认为巴塘事变的发生是清末康藏地区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将巴塘事变说成“巴塘人民的起义”是欠妥的,这一事件实质上是宗教上层和土司为维护自身利益,反对清政府新政,利用人民仇洋情绪与文化冲突而挑起的一场骚乱①子文:《“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1期,第54页。。
张荫棠在清末曾经负责查办藏事,并制定了一系列藏政改革的措施,因此研究张荫棠的学者是较多②研究张荫棠的成果可分为五类:(1)综合评价。曾国庆《论清季驻藏大臣张荫棠》(《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5期),关培凤《张荫棠:清末民初的“外交良才”》(《世界知识》2010年3期)。(2)对张荫棠查办藏事与新政的论述与评价。冯丽霞《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的性质》(《西藏研究》1987年4期),赵富良《试论张萌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西藏研究》1992年2期),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民族研究》2011年3期),汪霞《清末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在藏“新政”之研究 (1906-1907)》([D]四川师范大学2012-04)。(3)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的探讨。郭卫平《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l期),刘士岭《清末西藏新政失败的主观原因探析》(《兰州学刊》2007年3期)。(4)研究张荫棠的著作及其思想。康欣平系列文章《张荫棠外交思想探论——以1906-1908年间张荫棠的涉外言行考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2期)、《张荫棠治藏的思想资源》(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张荫棠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张荫棠筹藏时期为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2期),赵君《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前后的外交思想》(《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1期),陈鹏辉《普适伦理:张荫棠劝导藏俗改良的文化诠释》([D]西藏民族学院2012-04)。(5)研究概述。郑现杰《1979以来张荫棠治藏研究述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2期)。。许广智《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34],认为张荫棠藏俗改良的思想“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也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并认为查办藏事是西藏近代史上一次重要事件,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改革,为后来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康欣平专门论述张荫棠藏俗改良,否定“大民族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张荫棠藏俗改良的思想是“普适主义价值观”,但没有对什么是普适主义价值观、有何作用、在历史上的地位等作出具体的深入的阐述[35]。陈鹏辉《张荫棠遭弹劾考释》[36],作者分析了有泰、联豫在张荫棠被弹劾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张荫棠遭弹劫一案是一场有目的、有计划的诡谋,“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并非历史真相。张荫棠的藏俗改良是“强令”,而应该回到张荫棠的本意上来,即“劝导”藏俗改良。
至于研究联豫的学者,也有不少,如张世明、黄维忠、唐春芳、赵海静。其中,张世明《论联豫在清末新政期间对西藏的开发》[37],作者从联豫出任驻藏大臣的背景、联豫新政的主要内容分析,认为虽然联豫新政给西藏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一场失败了的开发,与内蒙古、川边藏区等边疆地区同时期的开发相比,无论从深度、广度上来说还是从速度上来说,均远远不如。此外,文章认为藏族人民拥有开发西藏的迫切要求与广泛的社会基础的缺乏是联豫西藏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新政与改革必须处理好民族关系,“因俗而革”,身为驻藏大臣的联豫措置失当,与达赖喇嘛等西藏僧俗上层人物失和,从而造成了新政的失败和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等严重不良后果。黄维忠《联豫功过论》[38],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对联豫持基本否定态度,理由即“擅自兴革”、“中饱私囊”、“踵成他人之事”。不过,张荫棠力辞帮办大臣之职,赵尔丰未能入藏,钟颖最后之被杀,均与联豫有所瓜葛,他实难摆脱干系。但要论其“罪”,只是“推波助澜”,并非主谋。上述诸事,复杂纷陈,并非其一人之力即能促成。联豫既然入藏,自抱有一番宏图,力行改革,但志大才疏。对新政的失败,其作为一个实际操作者,当然难辞其咎,但也不能过分抹杀其应有的功绩。赵海静《联豫新政对西藏地方出版印刷事业的影响》[39],认为联豫创办的白话报和设立的印书局不仅推动了西藏地方信息传播事业的脚步,为西藏地方吹进了一股近代文明的新风,而且使印刷出版技术第一次突破宗教领域范围,开始为政治、文化事业服务,成为一种大众消费。至此,西藏地方的出版印刷不再是宗教领域的专利,开启了西藏地方出版印刷事业新的发展时期。
赵尔丰派为驻藏大臣,因联豫阴阻辞职,并未到藏赴任。学界对于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赵尔丰的川滇事务上①研究赵尔丰的学术成就:曾国庆《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西藏研究》1989年4期),何云华《论赵尔丰人事思想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6期),李茂郁《论赵尔丰》(《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4期),刘玉、周文林《赵尔丰晚年的成就与悲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4期),顾旭娥《赵尔丰与清末川边新政》([D]郑州大学2005-05),张永攀《驻藏大臣赵尔丰的边事生涯》(《世界知识》2010年12期),张永攀《驻藏大臣赵尔丰与西藏》(《人民论坛》2010-06),卢霞《赵尔丰治边思想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1期),刘盛全《赵尔丰务边与“川滇”铭文大清铜币》(《收藏界》2012-11(总第131期))。,故而赵尔丰在西藏就无所谓事迹,这里对于研究其人的成果就不再论述。
四、研究特点与趋势
驻藏大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对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和清朝边疆治理与巩固发挥着作用。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置、发展、完善、衰微至终结历史使命,反映了清朝一代的兴衰。回溯国内学界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以下的特点与趋势:
(一)特点
纵观研究驻藏大臣的近百余篇学术论文,2000年以后的研究渐渐步入佳境,论文达到六十余篇。学术界将探讨的重点放在驻藏大臣的设置 (原因、时间)、职权与地位、作用等方面,对于驻藏大臣人物的研究则集中于驻藏大臣前期与后期的人物。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邓锐龄、吴丰培、曾国庆、贺文宣、车怀明②车明怀.简析江孜抗英斗争前后历任驻藏大臣的心态[J]中国藏学,2004(4);车明怀.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J]西藏研究,2012(6).、许广智、平措达杰、陈柏萍、康欣平等人。
至驻藏大臣设置的原因,最早涉足研究的人物是林黎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顾效荣,曾国庆对其作了系统的补充。学者们认为驻藏大臣设置之缘由有三:其一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庄园经济,其二防止准噶尔对西藏的侵扰和西藏上层内部之讧,其三优渥黄教,扶持达赖这面旗帜时需以军力为后盾。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施政,驻藏大臣的设立使之效果达到事半功倍。之于驻藏大臣设置的时间,学界存在基本趋向于“康熙说”和“雍正说”,大多认为1709年是清派员入藏之初始,1727年乃驻藏大臣制度的开始。但是贺文宣在其编著的《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持否定意见,认为驻藏大臣设立于1709年。
关于驻藏大臣职权与地位的变化,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1)吴丰培、曾国庆的五阶段论,认为驻藏大臣的职权经历了雏形 (1727-1751)、明定 (1751-1789)、扩大 (1789-1794)、完善 (1794-1845)、松弛 (1845-1911)五个不同的阶段;(2)萧金松的三阶段论,认为驻藏大臣的职权经历了初期的确立 (1727-1792)、中期的扩张 (1793-1843)、后期的演化(1844-1911)三个阶段;(3)张羽新的三时期论,即认为驻藏大臣的职权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监督藏政时期 (1727-1750)、与达赖喇嘛共理藏政时期 (1750-1793)以及主持藏政时期 (1750-1911)③祁美琴、赵阳:《关于清代藏史及驻藏大臣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藏学》2009年2期,第33页。。
对于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之研究,学者主要关注三方面:(1)驻藏大臣本身之作用;(2)其对治理西藏的影响;(3)其对清廷在西藏的统治与施政的效果。吴丰培、曾国庆是最赋代表性的学者,无论是二人编著的《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还是曾国庆的专著《清代藏史研究》和《清代藏族史》,亦或是其论文《论清代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和《论驻藏大臣对治理西藏的影响》,均作了系统地梳理。因此,这给今后研究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的学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于驻藏大臣人物的研究,文章依据曾国庆的观点把驻藏大臣人物的研究成就分为四类:(1)对于驻藏大臣前期 (雍正、乾隆时期)人物,学术界关注到的有僧格、玛拉、傅清、拉布敦、留保柱、鄂辉、和琳、和宁 (瑛)①张羽新:《〈卫藏通志〉的著者是和宁》,《西藏研究》1985年4期;孙文杰:《和瑛诗歌与西藏》,《西藏大学学报》2012年4期。、松筠,其中关于松筠的研究成果最多,达十余篇。(2)至驻藏大臣中期 (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人物,只有孟保和琦善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孟保的文章仅一篇。然对琦善的研究者,甚重,追其原因乃鸦片战争所致。不过,对琦善在藏期间的研究则较少,不足六篇,代表人物有邓锐龄、周伟洲。 (3)就驻藏大臣后期(光绪、宣统时期)人物,研究者对色楞额、文硕、升泰②祝少帅:《驻藏大臣升泰与西藏第一次抗英战争》,《西藏大学》2010年03月。、长庚、有泰、凤全、张荫棠、联豫、赵尔丰等人有所论述,以文硕、有泰、张荫棠、联豫、赵尔丰的学者最多,论及张荫棠的文章近十五篇之多,分析赵尔丰的论文近十篇,而涉及色楞额、文硕、升泰、长庚、凤全的文章分别仅一篇。(4)驻藏大臣衙门下属官员,学界只关注到回族马吉符,代表人物是房建昌③马肇璞,房建昌,马肇曾:《清末建设西藏保卫西藏的回族马吉符》,《回族研究》1993年2期;房建昌:《清光绪末年驻藏官员马吉符及其出使不丹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1期.。
(二)趋势
1.史料是历史学术研究的基石
论文缺乏史料的支撑,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至目前已经公开出版或刊印的驻藏大臣史料,汉文史籍较多,满文、藏文较少。学术界亟待加强满文、藏文资料翻译、收集与整理的工作,这一工作地顺利开展将为研究者扩展更为广阔的道路。
2.对于驻藏大臣设置的原因、时间、职权与地位、作用等的研究,学术界的观点已经趋于统一
文章认为今后学术界在此方面的探析,拓展空间狭小。不过,并非没有研究价值,学者们可以从宏观视角入手,将驻藏大臣制度置于清朝边疆治理政策的大局之下进行论证。亦或是具体到某个小的方面,以微观视角为基点,如关注驻藏大臣的某一职权 (宗教监督权、行政人事权、军事外交权等等)。
3.至驻藏大臣人物的研究,学界应重点关注驻藏大臣中期人物
在驻藏大臣前期与后期人物的研究时,需避开对松筠、文硕、有泰、张荫棠、联豫、赵尔丰等人的研究,其原因在于前人对此已经分析透彻。因此,后来再想迈出成功的步伐是十分不易之事,可取长补短,避重就轻,涉足无人问津的研究领域,例如驻藏大臣衙门下属官员的研究。
4.以往研究中区域间比较研究缺失,或较少
驻藏大臣制度是我国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北、东北地区历史上也存在类似的制度,如伊利都统、参赞、办事等,对其进行跨区域、民族的比较研究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5.在研究方法方面
以往研究中历史学主导,这类研究在制度史、事件史等宏大叙事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在聚焦单个人物研究方面,可能不够细致或清晰,因此,需要在史学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人类学、社会学等,进行大臣的社会文化史、生活史研究,这当是一个较新的切入点。
[1]张林.关于驻藏大臣的几件文物 [J].文物,1959年第7期
[2]林黎明.清朝前期对西藏的靖绥边计与驻藏大臣的设置[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3]顾效荣.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简述 [J].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
[4]曹育明.从西藏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看清代驻藏大臣的设置[J].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
[5]胡群琼.清初设驻藏大臣原因分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6]曾国庆.关于驻藏大臣设立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7]子文.“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p52
[8]平措塔杰.从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施政措施看驻藏大臣的设置[J].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9]祁美琴、赵阳.关于清代藏史及驻藏大臣研究的几点思考[J].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p25
[10][清]松筠.卫藏通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卷十二·条例
[11]张羽新.驻藏大臣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历史考察[J].中国藏学,1998年第2期
[12]范庆迎.清代前期驻藏大臣权限的变化 [J].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9期
[13]冯智.清初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及其体系 [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4]曾国庆.论清代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J].西藏研究,1998年第2期
[15]扎西次仁.从“拉萨痘碑”看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J].西藏民俗,2001年第2期
[16]曾国庆.论驻藏大臣对治理西藏的影响 [J].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17]子文.“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p53
[18]周强.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9]胡岩.马腊、僧格驻藏考略[J].中国藏学,1991年第4期
[20]邓锐龄.1789-1790年鄂辉等西藏事宜章程[J].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21]马云华.留保柱献佛 [J].紫禁城,2006年第Z2期
[22]唐文基.浅论和琳[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3]德彬.松笃治藏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藏
[24]刘忠.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绮对西藏的改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25]赵鹏飞.驻藏大臣孟保及其处理西藏事务研究 (1838-1842)[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
[26]邓锐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J].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27]周伟洲.驻藏大臣琦善改订西藏章程考 [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
[28]邓锐龄.清代驻藏大臣色楞额[J].中国藏学,2011年第4期
[29]刘丽媚.文硕密折的保藏抗英情结[J].中国藏学,2005年第4期
[30]张羽新.驻藏大臣长庚及其《为西藏事上书》[J].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31]康欣平.有泰与清末西藏政局的演变[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32]康欣平.前倨后恭:有泰与联豫在西藏期间的交往[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3]平措达吉、中德吉、旺宗等.驻藏大臣有泰评述[J].西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p97
[34]许广智.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J].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
[35]陈鹏辉.普适伦理:张荫棠劝导藏俗改良的文化诠释[D].咸阳:西藏民族学院,2012年
[36]陈鹏辉.张荫棠遭弹劾考释 [J].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
[37]张世明.论联豫在清末新政期间对西藏的开发[J].中国边疆史地导报,1990年第6期
[38]黄维忠.联豫功过论 [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39]赵海静.联豫新政对西藏地方出版印刷事业的影响 [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