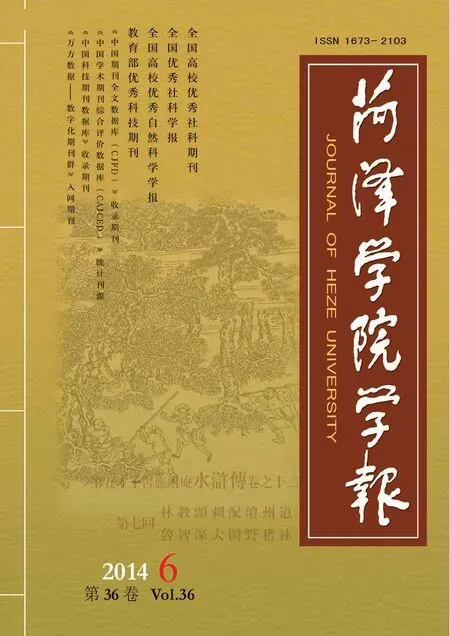反抗与疏离:论建国后老舍的创作及思想转变(1958—1966)*
2014-04-09查玉瑶张海元
查玉瑶,张海元
(1.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2.广州市执信中学,广东广州510080)
在《从话语范型看建国后老舍的创作及思想转变》(《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一文中,笔者具体分析了建国之初老舍的创作与思想转变的详细情况,认为从1950至1957年,是老舍对革命话语范型的自觉认同阶段,也即老舍的创作与思想从启蒙话语范型向革命话语范型转变,进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恋父”阶段。但从“双百方针”实施期间(1956—1957年)老舍的言行来看,他已经对革命话语范型这位文化上的“父亲”进行了反思。
弗洛姆认为:“父亲……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因此“父爱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所以父爱的本质是:“顺从是最大的道德,不顺从是最大的罪孽。”[1]160显然,老舍在“双百方针”期间的言行正是所谓的“最大的罪孽”。作为一位获得极高政治地位以及较高物质生活待遇的文化干部,他的行为显然违反了革命话语权力体系所设置的“禁区”。因此革命话语范型必然启动话语内部的“提纯程序”将老舍驱逐出“组织”。
因此,当老舍进入这一阶段之后,他的思想意识以及具体创作都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依旧积极创作以期获得革命话语范型对自我更大的认可。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从启蒙话语范型立场对革命话语范型进行反思并采取各种不同方式的“反抗”。而这种不自觉的反抗又必然招致革命话语范型对老舍更加严厉的压迫。当启蒙话语范型与革命话语范型无法调和的时候,老舍便逐渐开始回归传统以期在古典话语范型中寻求自我心灵的解脱。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仍是老舍对革命话语范型的持续认同。比如1958年11月发表的《红大院》,表现了北京某胡同居民在大跃进形势下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显著变化。1959年3月发表的《女店员》,表现了三个年轻姑娘和一个街道妇女卫大嫂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势力,走向新社会当了女售货员的故事。同年3月还发表了《全家福》,对新社会的警察进行了歌颂。1960年则为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创作了剧本《义和团》。1961年还写了儿童剧《宝船》并改编《荷珠配》等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诸如《团结互助,大家一起来跃进》之类的杂谈、评论等应景式文章及文学评论。
其次则是老舍对革命话语范型所进行的不自觉的反抗。众所周知,自建国以来,老舍一直都是紧跟路线政策,甚至还因此被称为“跟跟派”,比如他在对革命话语范型的认同阶段(1950—1957年)的一些代表作品就分别是歌颂政府治理污水、宣传婚姻法、宣传除四害、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等等。而在老舍对革命话语范型的不自觉反抗阶段,他创作的作品内容虽然与上个阶段一样,都是歌颂新社会的作品,但是相对而言,这些作品已经不是具体地配合某个重要运动或某个具体的政策。换句话讲,老舍在歌颂与迎合的同时也开始对革命话语范型进行反思与反抗。这种反抗是“反右”之后所出现的,其标志即是一贯紧跟政策的老舍没有写歌颂“反右”的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现象是老舍创作与思想转变的重要体现,也是本文区分他对革命话语范型认同与反抗阶段界限的重要依据。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意味深长的现象即是从1958年开始,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尤其是旧体诗)。据相关资料考察(甘海岚《老舍年谱》、张桂兴《老舍旧体诗辑注》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老舍全集》第十三卷。因老舍后期创作的旧体诗情况不一,统计结果也难免有误差,本文以三本著作中年度收录旧体诗最多者作为年度旧体诗创作数字),他在1958年创作约5首旧体诗,1959年创作约11首旧体诗,1960年创作约3首旧体诗,1961年创作约22首旧体诗,1962年创作的旧体诗则一度高达34首。
当然,老舍在解放前也曾创作过不少旧体诗及新诗,但解放后大量写作旧体诗确实从1958年开始。据笔者查证,至少从1950—1957年将近10年之间,老舍基本未创作任何旧体诗。从老舍与革命话语范型的关系角度来考察,这不能不算作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形式”。对旧体诗歌形式上的回归,一方面可能是老舍已然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另一方面旧体诗是老舍青年时期即熟练掌握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古典话语范型的代表。老舍的旧体诗写作也因此可以解读为启蒙话语范型在革命话语范型面前遭遇失败之后,创作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童年时期所掌握的传统话语范型的回归。
第三则是革命话语范型对老舍的“驱逐“。从革命话语与启蒙话语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二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方向、途径、目的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启蒙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在革命看来都是落后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部分,革命的这种态度将直接关涉革命观念的激进化,激进化的革命完全用政治取代意识形态,把革命等同于神学信仰;另一方面,二者有着共同的批判语言,无论是在反传统还是在反资产阶级方面,尤其突出的是,二者在‘籍思想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从而能够组建‘文化同盟,’‘扬弃成见’,携手共创20世纪现代性的精神天空。”[2]4,5
但是随着革命话语范型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启蒙话语范型也就走向了边缘化地位并面临被排除主流权力话语体系的困境。早在1951年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进行批判时,丁玲在《作为一种倾向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中就提出:“什么是小市民趣味呢?就是他们喜欢把一切严肃的问题,都给它趣味化,一切严肃的、政治的、思想的问题,都被他们在轻轻松松嘻皮笑脸中取消了。”[3]59显然,如果要用这段话批判老舍作品中表现城市底层市民的幽默的话,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所以,据周述曾回忆,在1960年春天,市委文化部(北京)曾组织一个活动要批判老舍,只是后来被“上面”干涉才没有批判。[4]137并且舒乙在《我的父亲老舍》一书中也提到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北京市确定的两面大“白旗”就是焦菊隐及老舍,而且报纸上的批判稿都已排好了版,只是后来临时变了卦。
傅光明曾总结说,1957年之后老舍创作上出现了停顿,他已经认识到只片面地强调政治,作品就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他不愿意再去盲目地配合政治,开始潜心写自己愿写的作品《正红旗下》。[4]299
其实,《正红旗下》的写作也与当时的政策密切相关。“三年自然灾害”之后,革命话语范型对文学的控制稍微放松,也因此产生了一个文艺及各种讨论的活跃时期,只是很快就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首当其冲的有钱谷融、巴人、李何林以及“三家村”等。到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从1963年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学及哲学各个领域开展了全面的批判运动。
回到老舍的思想状态,1961年底,老舍开始偷偷写作《正红旗下》,从权力、话语的角度来看,这是对自我启蒙知识话语的回归,也是对革命话语的反抗。但是这种对启蒙话语的回归到了1962年则“自动”停止。所以,如果说《正红旗下》的写作标志着老舍对革命话语的不自觉反抗以及对启蒙话语的回归,那么其停写则标志着老舍对启蒙话语的边缘地位表示无奈并进而放弃。因此,从1963年开始,老舍的思想意识开始“向后转”转向对传统的回归,对自我的寻找,表现出一种精神上的“恋母”倾向。也即从1963年至1966年老舍去世,他对革命话语范型进入疏离阶段。
从1963年开始到1966年8月底“身谏”太平湖,老舍进入了对革命话语范型的疏离期,也是一个为期长达四年的创作低潮期。据舒乙《我的父亲老舍》所言“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笔受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来自极左方面的压力。他干脆停了笔。1963年仅发表了四十篇短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只有一篇。”[5]145这在老舍的年谱上也有鲜明的记载与体现。但记得老舍在1944年抨击国民党文化专制时写作《病》一文说过:“我只知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假若不幸而人文共亡,我也不多说什么,或者,我就写作,死了,万事皆休,咱们各凭良心吧。”[6]352也就是说,对于老舍而言,基本上可以用“人、文共存亡”来概括他对于自己“笔”的重视。因此对这一个阶段老舍思想的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所谓创作的多寡。如果将考察视角放在另一种文学对象——旧体诗——之上,可以发现,这个时期恰恰是老舍创作的为数不多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1963年老舍创作至少30首旧体诗,1964年老舍创作至少14首旧体诗,1965年创作至少30首旧体诗,1966年约2首。在对革命话语范型的疏离阶段,他这种对旧体诗创作突然而至的热情要明显大于认同与反抗阶段,甚至还要远远高过建国之前。
前文也已提到,随着革命话语范型对“话语”控制的逐渐加紧,老舍的思想历程从建国初对革命话语的自觉认同(精神恋父)开始对革命话语表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认同与反抗交织,但总的来说还是不自觉的反抗(精神审父)。进入1963年之后,老舍对革命话语范型则采取了一种疏离的态度。所谓话语的疏离态度“是指话语主体为了应对特定的文化权力的作用而被迫采用的一种逃避现实,远离权力的心理防御策略。”“疏离的立场或逃避的心态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种精神心理指归,一种是在文学文本中构筑日常性的人伦情感空间,一种是在文学文本中营造审美性的自然(风俗)空间。”[1]389-391
1965年3月,老舍访日本期间曾写过一篇游记散文《致日本作家公开信》,但是这篇文章却不能发表。这对老舍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失语”信号。所以老舍的思想变化只能表现在他的旧体诗上:或通过赠人访友表现人类情感空间,或通过游山看水营造自然空间,即采取“一种逃避现实,远离权力的心理防御策略”。
通过与上一个阶段老舍的旧体诗创作对比,可以明显发现这个阶段的旧体诗更多地描写自然风光。比如在老舍对革命话语的不自觉反抗阶段,他1958年的《元旦试笔》二首、《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访东风人民公社而作》,1959年的《元旦高兴》、《火箭奔月》等诗歌都是歌颂型的应景诗歌。至1961年,老舍访问内蒙古,虽然写了《内蒙风光》五首及《内蒙东部纪游》四首这些倾向自然风光的诗歌,但其内容还是赞扬性的。再比如同年度创作的《茂林公社》、《三和牛马》、《昭旗宾馆》以及1962年《大好春光》十首(《参观内蒙古自治区十五年建设成就展览》《参观旅行内蒙古画家画展》《参观全国人像摄影展览》等)也是歌颂赞扬为主。
至1963年,老舍的旧体诗创作内容突然出现了重大转向,其诗歌内容由歌颂社会转变为赠答好友,如《赠李慕良》、《赠徐兰沅》、《赠申凤梅》、《赠张君秋》、《赠康濯》、《赠亚明》、《赠李夏阳》、《赠关山月》、《赠沈柔坚》、《赠友人归广州》、《赠玛拉沁夫》、《赠骆文》、《赠杜埃》、《赠李焕之》、《赠李可染》、《赠曹禺》、《赠阳翰笙》、《赠申伸》、《赠河北省歌舞剧院》、《赠东风豫剧团》、《赠小海燕评剧团》、《赠钱钟书》、《赠章老》等等。这些作品可以看做老舍面对内心压力所塑造的一个“日常性的人伦情感空间”。
进入1964年,老舍的诗歌则开始较多关注具体的“物”及“景”,如《咏茶》、《徽墨》、《登太白楼》、《游合肥包公祠》以及黄山之游所作的《黄山云》、《黄山奇》、《黄山松》、《自光明顶至始信峰》、《文殊院》等。这些诗歌则是老舍面对自我心理压力所营造的“审美性的自然(风俗)空间”。
1965年的诗歌多作于访问日本期间,其中如《赠木下顺二》、《赠白上吾夫》以及《游日十七首》,其中赠答诗与风景诗大约持平。
老舍创作的赠答诗“突增”,是基于对革命话语采取疏离立场之后的极大痛苦与革命话语范型对其的驱逐,也应了老舍生平“最怕的事——没有朋友”[5]序这一事实。同样,风景诗的“突增”一举超过了各种赞颂之作也说明了老舍对革命话语范型的疏离。再撇开诗歌内容谈形式,那么则是老舍对传统话语范型的自觉回归。据甘海岚《老舍年谱》记载,1913年,十五岁的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即开始用文言文写诗与散文。“到师范毕业时……文言体散文和旧体诗词都已经有了结实的底子。”[5]19但历数老舍各个阶段的创作实践,他创作旧体诗的“热情”还是以此时为最。
当然,老舍对旧体诗的创作“热情”源于对革命话语范型的疏离以及对传统话语范型的回归,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讲,可以称作“精神恋母”。而“恋母”情结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将自我“回归自然”,毁灭肉体存在,以期满足自我“回归子宫”寻求安全感的倾向。老舍这种自然的回归以及“回归自然”的冲动不仅体现在自己的旧体诗歌创作之上,还体现在自己与朋友的言谈交往之中。
据甘海岚《老舍年谱》记载,1966年2月6日,苏联汉学家M·施莱德访问老舍。后来他回忆说“临走时,老舍送给我一件实在令人惊叹不已的物品——一只细薄如蛋壳的古老的中国瓷杯”并说“我想,这只杯子你保存着更好些。”[7]518老舍做出这一举动并说出此番话语,想必已经坚决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但肯定又不舍得毁坏这只瓷杯。无独有偶,当老舍的死讯传到日本后,作家井上靖写了篇著名文章《壶》,高健写了知名小说《玉碎》都对老舍之死进行了探讨。由此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来老舍自尽是思虑很久之后的一个行动。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舒乙在后来指出:
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亲爱的老母了。[5]78
至此,老舍对革命话语的疏离达到了极致,这也是自我精神“恋母”支持下“回归自然”寻求安全感的极端方式。
[1]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洪子成.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傅光明,郑实.老舍之死口述实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舒乙.我的父亲老舍[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6]老舍.老舍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甘海岚.老舍年谱[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